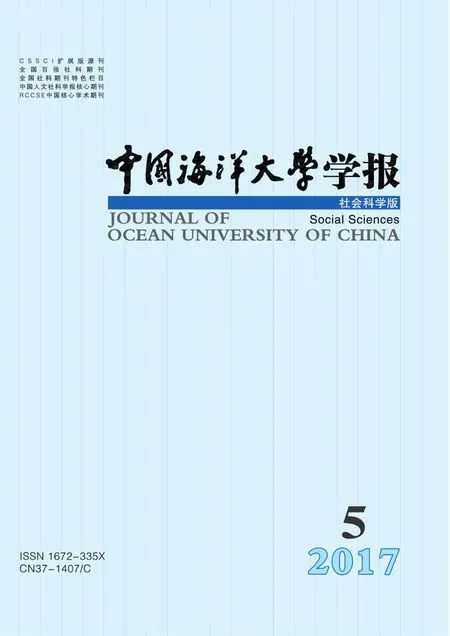“自我批评”与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生产
——以《人民日报》三篇“自我批评”的检讨文章为中心*
许永宁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自我批评”与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生产
——以《人民日报》三篇“自我批评”的检讨文章为中心*
许永宁
(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3)
以《人民日报》三篇“自我批评”的检讨文章为主体的文学批评话语,丰富而又具体地呈现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现实图景和文学的生态,进而剖析文学批评在新时期面临的文学困境和理论诉求。这一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生产不仅清晰地呈现出政治制度在文学批评话语中的规范和训导的制度设计作用,也反映出在新时期文学语境下,文学批评所呈现出的时代特点和批评特质。可以说,这一独特历史现象的文学批评活动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具有启发性的意味,开启了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释带入一个新的阶段,并且迅速将其历史化,从而在探索和反思的互训中,力图实现文学批评的客观化。
“自我批评”;文学批评;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以来,由于政治的松绑,文坛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学现象,如早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与文坛的热闹相似,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着一场有关“人性”问题的大讨论。现在看来,思想文化领域的“双百方针”的重提,政治领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以及具体针对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的措施都为文学的勃兴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一些文学作品的出现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不仅在文学领域内出现严肃认真的学术讨论,而且也波及到思想文化领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然而,这些新的文学现象出现很快招来一场强烈的政治批判。作为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文学,新时期以来借着政治的松绑而萌发出新的契机,却也因为政治的干预而变得扑朔迷离。但是,新时期文学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干预而失去其独有的特质,毕竟这已经不再是“文革”时期,文学的春天已经来临,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无论是从政治气候的大环境还是从作家个体的生存体验与认知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具体到以“自我批评”为方式的作家检讨机制而言,新时期以来的“自我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开始逐步失去了共和国初期其应有的效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新的趋向。
一
《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头版发表胡乔木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算是做了结论。作为党和政府重要机关刊物的《人民日报》,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位不言而喻,其影响力也自是毋庸置疑。长久以来以理论宣传和政治导向为重要内容的《人民日报》以长篇幅的文字来阐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由此可见其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向前追溯,1983年11月6日,周扬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拥护整党决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策——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做自我批评》,这样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做出“自我批评”的检讨,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已非同小可。大致同时,1984年1月9日和1984年3月5日,《人民日报》先后转载并刊发加有“编者按”的张笑天和徐敬亚在《吉林日报》的“自我批评”文章,分别是《永远不忘社会主义作家职责——关于<离离原上草>的自我批评》和《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进而推断,新时期在1983年至1984年间,以《人民日报》为阵地和导向的作家“自我批评”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型。
为什么是“自我批评”?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1]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自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自我批评’乃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开始,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等进一步将“自我批评”本土化,并且运用到政治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尤其以延安整风运动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自我批评”逐步从政治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因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和文学制度,引导与规训知识分子为新的政权服务。而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失去政治身份的作家很难谈得上“批评”,更多的只能是一种“被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其中具有三重功效:首先,从身份上讲,“自我批评”者失去了批评的资格,转而沦为被批评的对象。其次,从观念上说,“自我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被批评者对于政治的服膺,进而从思想上进行自我矮化。第三,“自我批评”从专业上已经成为彻底否定知识分子赖以存在的依据和价值。这样一来,“自我批评”成为改造知识分子思想强有力的武器,为新的政权的建立初步扫清思想上的障碍。
以共和国初期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自我批评”为例。1951年公映的《我们夫妇之间》是由作家萧也牧同名小说改编而来,一经公映即受到批判。陈涌在1951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批评萧也牧入城以后写的《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是“依据小资产阶级观点、低级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2]值得注意的是20天前的5月20日,《人民日报》刚发表毛泽东亲自执笔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对思想文化界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陈涌紧紧跟上,对当代作家萧也牧开了头一炮。萧也牧随后在1951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加有“编者按”的《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的“自我批评”检讨,其深刻地忏悔道:
我的作品里边所反映出来的:对于生活本质的歪曲,那虚伪的风格,那低级趣味,那玩弄人物的态度,以及严重的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把创作看成是个人的事业,看成是获取个人名誉地位的敲门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惜投机取巧、粗制滥造……那种低劣的品质,无一不是我骨头缝里的东西。[3]
这种从骨头缝里发出的自我批评,直接将作家的主体意识敲得零碎。无论是从思想认识上,还是作家自身的专业技能上都进行了自我的批判和否定。作家自我阉割和臣服非萧也牧所独有。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在发表《论“文学是人学”》的理论文章后也受到批判,在回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写作时,他说,“当我读到最初发表的一些批评文章时,我本来是想就一些问题进一步申述我的观点,提出答辩的。但后来,反右运动的浪潮愈卷愈猛,对我的批判愈来愈凶,我也愈来愈感觉到自己世界观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了。我真诚的认为我最应该做的工作是自我检查,而不是对别人的批判进行答辩”。[4](P56)钱谷融先生的“真诚”应该是对那个时期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认识发生变化最深刻的一种体验,以至于恍惚到失去自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应该说这是共和国初期知识分子或作家共有的一种精神上的体验。
制度上的设计并没有因为思想的解放而得到彻底的变化,这种“自我批评”方式带来的精神上的体验延续到新时期的文学活动中。在经历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一批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1982年《新苑》第2期刊发了张笑天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其中有关“人性”和“人道主义”的言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颇有争议。1983年1月,吉林省文学界就有关《离离原上草》的思想动向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并将会议的主要内容刊发在1983年《新苑》第2期,与此同时本期配发了笔谈形式的5篇批评文章。1983年8月15日,吉林省文学界进一步就《离离原上草》的“人性”问题进行了批评。无独有偶,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在未发表之前已经受到关注,并被中央领导点名批评。1983年《当代文艺思潮》第1期发表以后,更是引来广泛的批判,从吉林省文学界到甘肃省文学联合会都开会进行集中批判。迫于压力,张笑天和徐敬亚在《吉林日报》都发表了“自我批评”的检讨文章,先后被《新苑》《诗刊》《文艺报》以及《人民日报》转发。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的“自我批评”并非是共和国初期“自我批评”的一种完全继承和模板复制,相对而言,从批判开始,这种反批评的声音一直存在,尤以作家自身的声音最为独特和显著。面对来势汹汹的批评,作家张笑天曾在《江城》1983年第4期发表了《索性招惹它一回》的反批评文章,对于“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批评,“我没有被说服,我还将探索、写下去。”[5]这应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回想五六十年代作家遭遇批评之后的心态,张笑天无疑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发表前,曾复信《当代文艺思潮》编辑部,“虽然到目前为止,有些观点(大部分观点,我仍坚持!)我仍觉得是可以坚持、探讨的,但确也有很多失误的地方(语言上的失误和小观点上的失误),从整个认识上我也觉得有不适当的地方,对此,在适当的时候,我愿意形成文字。”[6]可以想见,徐敬亚与张笑天对于批评和讨论的反驳是如此的激烈。此后不久,徐敬亚又一次以《圭臬之死》的文章进行了理论上的探求,既有对《崛起的诗群》的反思和完善,又有对当时学术的批判与警醒。所以《圭臬之死》未经发表就导致《当代文艺思潮》停刊,可见其反批评的力度之大。
二
其实,从周扬、张笑天、徐敬亚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批评”的检讨文章开始,一种以“自我批评”为核心的“批评——反批评——自我批评”模式逐步形成。我们在讨论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无疑对以“自我批评”为核心的模式演变的话语方式产生了兴趣,进而言之,这种话语模式的展开不仅与新时期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生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也与自身所具有的功能与特性有密切关联。
首先,“自我批评”的呈现是以“批评”的出现为理论预设前提的,也就是其对立面,进而言之,“谁的批评”。这一看似必然的理论言说在新时期有了更多的可能和面向。“自我批评”只有建立在与“批评”相适应的关系中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没了“批评”,“自我批评”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自我批评”也就意味着一种功能关系的建立,在从属关系上,“批评”应是掌握了某种权力,并且具有了强制执行力的功效,正因为如此,“自我批评”也就有了具体可供参考的表述对象和话语范式。毛泽东曾说过,“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7](P1096)所以,“自我批评”成为一种政治的话语在新时期继续得到贯彻,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也就合理地成为其政治运动的注脚。面对“批评”者的强势,“自我批评”开始以各种方式或情态表现出忏悔的意愿。周扬的“自我批评”是其在病榻上以与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进行的,却也表明了“在一些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之后,还固执己见”的客观情状,进而以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实际情况所知甚少,对于我所看到或听到的许多现象也缺乏认真的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所以只知道要改革,但如何改革也还是茫然,既提不出中肯的意见,更经不起实际的检验”这样的“自我批评”完成检讨。[8]同时,张笑天和徐敬亚的“自我批评”主要就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和社会主义作家的职责两个方面进行检讨。实际情况是,很多的批评者并没有与文本建立起很好的对话关系,而是囿于政治思想的诉求,在文本的批评中上纲上线,进而对作者的创作产生怀疑和批判,形成一种恶性的环境与氛围,套话与空话充斥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完全丧失了针对具体问题批评的客观性。换句话说,“自我批评”检讨的不是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而是其在思想上表现出的动向,失去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效性和目的性。从反面而言,由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对话和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一定意义上为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保留了原始的样本和探索的轨迹,使其避免更多的陷入政治的论争中而损害文学批评应有的功能和特质。
其次,“反批评”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同构关系,也是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关键一环,更重要的是,“反批评”的出现,彰显了新时期文学批评独特的风景与魅力。如果说“谁的批评”主导的是一种权力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么“反批评”则是一种思想的状态,一种对于当下文学发展与社会变革新的认识。1983年3月7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3月16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全文刊发了周扬的这篇讲稿,随后中宣部组织力量进行批判。据顾骧回忆,周扬面对胡乔木的批评十分的愤怒,两人唇枪舌战,当面争执起来。[9](P68)张笑天在《离离原上草》的批判之后发文《索性招惹它一回》进行反批评,徐敬亚在受到批判之后仍坚持自己的大部分观点,可以说一种反批评的氛围逐渐形成。首先无论批评的恰当与否,以及反批评的正确与否,反批评的出现正视了新时期初期文学批评建设的实际问题,那就是可不可以有反批评,以及反批评在文学批评空间构建过程中的作用。其次反批评的出现与批评的主导是否都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以及学术的范畴,超出这个意义,批评仅成为一种声音的独秀,虽然有着争鸣的意味,但已经失却与作者或文本展开对话的功能。最后,“自我批评”的结果与反批评的出现有着莫大的关联,也正是因为其对批评的反驳,加快了自我批评出现的进程,不仅进一步引发了广泛意义的讨论,也承受了更重的外在压力。1983年,邓小平在“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中明确对反批评进行了批判,“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10](P46)这被认为是对反批评最严厉的批评,反批评受到压制,自我批评则成为唯一的出路和结束论争的方式。
最后,以“自我批评”为核心的同构关系中的批评与反批评不仅是建立一种共时性的场域之中,而且还存在于一种历时性的发展脉络里。从“自我批评”回溯,批评的产生和反批评的出现都离不开《人民日报》对这一问题的推动和关注。同样,以《人民日报》为主要的平台和载体背后,还贯穿有一系列的理论和观念的论争,而集中于1983年到1984年这一段时间的论争,其理论焦点主要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当然向前再追溯则主要是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大讨论。无论是何种形式或观点的理论论争,以3篇“自我批评”检讨文章而结束的方式,无疑在某种倾向上构成了一致,进而反观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张笑天《离离原上草》和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这3篇文章所引发的共同的思考和讨论,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即有关“人”的文学的话语论争,而这正是五四以来“人的文学”大力倡导和尊崇的。例如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言中谈到“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见。”[11](P5)茅盾认为“人的发见,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当时的文学批评和创作都是有意识或下意识的向着这个目标。个人主义(它的较悦耳的代名词,就是人的发见,或发展个性)……个人主义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要态度和过程,正是理所必然。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的意义亦即在此。”[12](P298)周作人也曾指出,“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13](P24)但是,在一系列批评文章中,惯用的“表现自我”“人性”以及“人道主义”等成了批判的对象,恰恰说明了在周扬、张笑天和徐敬亚等人的文章中,人的话语的重新出现显示出新时期文学一个新的精神向度,即重返五四,或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价值和理念重新审视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将失落了的“人”的文学重新纳入到文学的视野中,这无疑是最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以“自我批评”为核心的文学批评话语在新时期虽然表现得举步维艰,但是这种执着的探索以及敢于冒险的精神为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开了一个缝隙,逐渐对复苏的文学进行引导和促进。在价值的层面上开始出现文学批评话语新的萌芽,同时也重新唤起五四时期对于文学批评中“人”的话语的关注,为沉闷的铁屋子开了一扇窗。
三
今天,重读周扬等人的文章,不言自明地会发现其中或多或少的理论谬误和思想缺陷,这主要局限于时代的环境和个体的学术理论处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但是,这些粗糙甚至显得有些幼稚的理论探索为我们留下了真切的时代印迹,表达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诉求和文学反思。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追问何以形成新时期特有的文学批评话语,或者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新特点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围绕三篇“自我批评”文章的出现,及其背后的问题的讨论,这既有学术研究的方式和方法的严肃思考,也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掺杂其中,甚至可以说,以政治的思想运动为主角,文学领域的讨论研究为注脚的一次政治运动。不可否认,文学有反映时代的功能以及政治在文学活动中的干预和影响作用,但是,如果将原因仅仅归咎于政治的意识形态或者缠绕在其中的人事纠纷,似乎已经失去了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意义,正如杨念群所言,“应该承认,‘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尽管后现代史学已完全不承认两者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和界限,或者干脆有意模糊之。但我仍以为,‘文学文本’不能当作历史材料的主体加以分析,只能作为历史的辅助资料加以看待。事实也证明,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往往更多地与政治意识形态发生着复杂的纠葛支配关系,文学描写也常常代表作家相对单纯的政治立场,由此立场引申出的历史描写也会呈现出某种相对单一的特征,即使偶尔透露出所谓‘日常生活的焦虑’,其丰富性也是相当有限的,不能借此窥见革命更为复杂的一面”。[14]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秦川和顾骧访谈中提到的《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中第一条即是“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15](P119)将“人道主义”的讨论限定在学术问题范畴是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重大亮点,因而“自我批评”文章的出现及其有关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从学术论争开始的,这应是文学在新时期从政治中逐步剥离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新时期文学批评生产的一个重要前提。事实上,也只有打破或抛却政治的观念束缚,文学批评的独特功能才能展现出来。
从文学本位主义出发,不能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忽略文学发展过程中自身的规律和特定的存在。进而会发现,在就“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其实质则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的角度问题,我们很难说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有着本质的差异,更不可能否定资本主义没有人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论争只能导致政治干涉解决的结果。同样,关于张笑天《离离原上草》中的“人性”问题,“共同的人性”“抽象的人性”以及人性有无阶级性等问题的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已经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表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7页。此次重新提出,虽然仍然有着打棍子揪辫子的嫌疑,但是仅就这个问题进行重新讨论可以说已经输入了新鲜的空气,对僵化了的思想禁锢有着松动的痕迹。再说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中“表现自我”以及“现代派”的问题,正是由于对“现代”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一度为了规避政治风险带来的厄运,文学逐步转向技术层面的探寻,进而引发了八十年代的方法热,1985年也被称为方法年。而方法热的出现,“归根结底是一个去政治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摆脱文学工具论而走向独立主体意义的标志”。[16]
其二,运动的思维模式再一次运用到文学研究领域,在这种混装无差别的运动模式下,差异性思维的闪现,在交互影响中逐渐脱离原有的藩篱束缚。什么是运动思维?“运动思维”就是用激进的方式进行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用突变的方式推进事物发展、用人财物的规模集中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方法。[17]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深刻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社会发展的弊端,邓小平在谈思想战线问题时一再强调“对于当前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18](P390)但是这种运动的思维方式并不能立刻消失在现实生活中,“物理学上的惯性力实在太强大了。延续了几十年、渗透到全民意识深处的‘左’倾思潮,像飞速奔走的车轮,并不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刹闸而立即停止滚动,它还要在原有轨道上继续向前冲一段”。[9](P106)新时期“自我批评”的产生,即是这种惯性思维模式的典型产物。这场持续一年之久的“自我批评”,其主要的核心问题围绕着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方向和定位以及作家在社会主义文艺中的职能和贡献,这两项的最终指向都明确地导向与之同时产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只是在具体的理论论争上,“异化”和“人道主义”成为切入点。从运动的形式上看,具体的“自我批评”的产生,是在中央的授意与支持下,地方与中央联合唱主角。据张笑天回忆,地方上的批判是受了“上面的意思”:
1983年5月21日,当时的长影党委书记纪叶找我谈话,声称:“是上面委托我与你谈话”,就《离离原上草》这部有错误的小说对你帮助。在我追问下他告诉我。他说的“上面”不是省委领导,而是胡乔木,说他点了我的名。随后,有人告诉我,我在中央文件上也被点了名,同时点名的有戴厚英的《人啊人》,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以及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称后者为现代主义),也涉及到朱光潜等人所谓贬低鲁迅、郭沫若,抬高沈从文、徐志摩等问题。[19]
大致同时,冯牧在首都部分理论宣传工作者座谈会上也点名批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和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
最近有几个会我觉得很不正常,我看了心里很不痛快,就是长春一个电影文学会议,表面上围攻钟惦棐,实际上是一种放肆地又没有马列主义修养,文艺理论修养,随心所欲地。陈登科、张笑天写了一篇文章《索性招惹它一回》。人家批评他那个《离离原上草》,他的这个作品十分拙劣,够不上一个起码的文学水平的,根本达不到,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根本达不到发表水平的。人家批评他,他不但不引起警惕,反而写文章索性招惹俺—次。
……
包括你们登徐敬亚文章的那一期刊物,当然那期徐敬亚的文章是重头文章,削弱或者冲淡他的文章的极端错误的论点,而有些同志简单化了,简单化恐怕想起到中和、冲淡,以至于压倒错误的观点,我觉得效果可能适得其反。[6]
与张笑天相类似,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在西北文艺座谈会上受到中央领导贺敬之的点名批评。紧接着,地方上也开始了各种的批判。1983年1月29日,吉林省文学界在长春就《离离原上草》的真实性和思想动向进行了批评。1983年8月15日,吉林省文学界进一步就《离离原上草》的“人性”问题进行了批评。甘肃省文联相继召开座谈会就《当代文艺思潮》及《崛起的诗群》进行了批判,吉林省文学年会成了批判徐敬亚的大会。
与这种环境相左的是,由于运动的思维影响,“自我批评”在很大程度上的表现也成为一种程式的典范,并没有揭示出作家个体在创作过程中所犯“错误”的针对性,进而言之,这种针对性的丧失以及相互影响作用下的个性并没有受到批判和否定,而这正是文学批评所应当珍视和研究的,所以,模式与套路下所作的“自我批评”,失去了行之有效的忏悔效果,更不用说规范与训导作用的丧失。进而从反面也证实了,新时期的“自我批评”在忽略差异性的前提下,作家主体的个性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并没有因为创作中实质性的问题或者艺术性的问题受到批判,因而,“自我批评”所展现出的批评话语的生产有了更多的途径和方式。
结语
总之,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生产中,“自我批评”既是政治意识形态术语同时又承担文学批评话语的功能。既承续了五六十年代“自我批评”话语体系的特点与状态,又有了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的特质和诉求。在以《人民日报》为载体和平台的重要前提下,尤其是“自我批评”的检讨文章所衍生出的,新时期文学批评话语生产不仅清晰地呈现出政治制度的预设和规范,而且更重要地展示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复杂生态和历史纠葛。周扬等人个体理论话语的阐释,将“自我批评”的理论言说逐步从时代合唱的洪流中解放出来,逐步回归到个体审美与价值判断的艺术领域中。可以说,这一独特历史现象的文学批评活动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中具有启发性的意味,开启了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释带入一个新的阶段,并且迅速将其历史化,从而在探索和反思的互训中,力图实现文学批评的客观化。
[1]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N].人民日报,1950-06-24.
[2] 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N].人民日报,1951-06-10.
[3] 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N].人民日报,1951-10-26.
[4] 钱谷融.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三点说明[A].钱谷融文集·文论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5] 张笑天.索性惹它一回[J].江城,1983,(4):57.
[6] 段宏鸣.《当代文艺思潮》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7]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A].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周扬.拥护整党决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决策——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做自我批评[N].人民日报,1983-11-06.
[9] 徐庆全.与秦川谈周扬[A].知情者眼中的周扬[C].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10]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迫切任务(1983年10月12日)[A].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2] 茅盾.关于创作[A].茅盾文艺杂论集(上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13] 止庵编.周作人讲演集[C].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14] 杨念群.革命叙述与文化想象[J].读书,2012,(5):132-138.
[15] 徐庆全.与顾骧谈周扬[A].知情者眼中的周扬[C].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16] 李庆西.寻根文学再思考[J].上海文化,2009,(5):16-24.
[17] 徐光.论中国共产党的“三种思维”方式的变迁[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7,(4):18-22.
[18] 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1981年7月17日)[A].邓小平文选(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 张笑天.胡乔木印象[J].作家.2000,(2):51-54.
"Self-criticism"andGenerationofLiteraryCriticismDiscourseintheNewEra
Xu Yongni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New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Citing three articles of "self-criticism" in the People's Daily as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alistic view and literary ecolog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literary dilemma and theoretical request faced by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new era. The generation of the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system manifests the role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 has played in normalizing and guiding literary criticism discourse as well as the spirit of time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riticism in the context of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As a special historical phenomenon, th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era has opened up a new path to literary criticism development and had implications for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new era. The literary criticism has interpre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hen historicized it, and tried to make literary criticism objective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self-criticism;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ture in the new era
I206.7
:A
:1672-335X(2017)05-0123-06
责任编辑:高 雪
2016-09-06
:许永宁(1987- ),男,陕西旬邑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