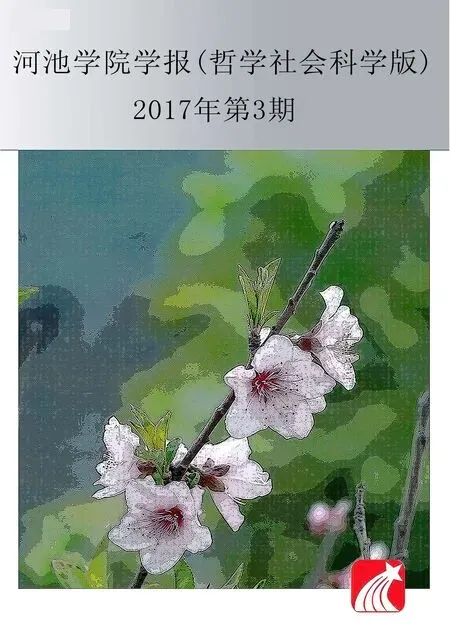从黑暗向光明旅行
——对电影《小姐》的女性主义解读
邹 蕾
(广西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从黑暗向光明旅行
——对电影《小姐》的女性主义解读
邹 蕾
(广西艺术学院 人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以女性主义视角对电影《小姐》进行解读,将电影中4个不同的女性人物,即依靠男权社会的“旧女性”与对抗男权社会的“新女性”进行对比,揭示出作品蕴含的现实意义。
女性主义;《小姐》;“他者”
韩国电影《小姐》以视角切换的方式再现了1930年日治时期的朝鲜,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两个女子之间,错综复杂的阴谋纠葛与被边缘化的同性罗曼史。最值得品位的是电影关于女性主义的表达,朴赞郁导演在戛纳电影节接受采访时表示:“电影的确是希望做到这点……我希望交给观众的是个开放的电影。所以我自己是偷偷这么做的,但希望用电影语言让观众来发现”[1],导演通过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刻画和主体性的构建,显示出一个男性对于女性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与深切关怀,使整部电影充满张力和感染力。本文以《小姐》为例,选择了其中4个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角色——姨母、佐佐木夫人、秀子(小姐)、淑熙(侍女),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对其进行解读,旨在探寻电影中女性群体的形象社会现实意义。
一、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对电影批评的影响
(一)女性主义的背景及内涵
女性主义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的法国,由此揭开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此后在英美等国流传开来直到遍及全世界。女性主义也被称为女权主义抑或是女权运动,是指女性们为了争取自己的社会权利(女性话语权、女性选举权、男女同工同酬等)所发起的运动或行为。女性主义的发展算不上久远,但却饱含着深刻的认识与长久的进步。女性主义理论从哲学理论中汲取营养,大致包含了3个层面的概念:政治层、理论层和实践层。
政治层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被划分成弱势群体那一刻开始,就已经置身于不利的社会大环境之中,这时两性间的不平等就演化成政治权利不平等。女性主义虽表现出提高女性地位的政治诉求,但其最终目标旨在倡导性别平等和消除一切不平等的现象。从理论层面看,女性主义理论是对当时社会和女性自己的一种全新的认识,其中主要强调了男女平等平权、肯定女性的价值观念,由此开辟了新的学说(或者说是方法论),“它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那种能够被用来指导和造就女权主义政治实践的知识”[2]2。实践上讲,女性主义认为只有女性自身提高平等的意识、两性之间拥有平等的权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站在同一起跑线。其中女性所拥有的权力应包括:话语权、话语主体和话语实践。实际上,女性主义可以说是多种层面组合而成的集合体,这种现象就导致了女性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发展出许多不同的理论,最终导致女性主义理论的分歧。总而言之,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女性依旧处于一种“第二性”的社会地位,这样的状况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但在女性主义的持续推动下已渐渐好转。
(二) 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的意义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在妇女解放运动带动下展开的理论与学术研究。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大致可以分为女性形象的研究、受众研究、电影传统3个类别,最常使用的批评模式是对于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研究。“女权电影理论和批评的目的,在力求瓦解目前在电影中存在的对女性在创造力上的压抑和在形象上的剥削。(这情况也适用于电视的领域内)以上的现象根源于男权社会中男女性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已自然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文化和其表意系统之中”[3]。即对电影中塑造出的特定女性形象进行分析,通过研究这些女性身上缺少的主体意识和被男权意识歪曲的形象,借此揭露和批判男权社会,用来唤醒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可以说女性主义电影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部分人的女性意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地位和主体意识也有所提高。因此,导演和编剧也开始有意塑造一些独立、坚强而又富有主体意识的鲜明女性形象,研究者也继续沿用女性形象的研究,这种批评模式研究电影作品(电影作品必须有一定的男女平等意识或者是女性主体意识)中女性形象身上所带有和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主体意识。
但是对于电影中女性形象研究这种批评模式的焦点过于集中在女性形象这种个体的分析,对于电影中的美学特征、文化内涵以及电影本身来说是脱节的,这样的研究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述和书写,并不能对电影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阐述。
二、《小姐》与女性主义思想的关联
朴赞郁导演在读完萨拉·沃特斯原著《荆棘之城》后构想拍一部维多利亚时期的电影,但BBC(英国广播公司)已经率先将其翻拍为《指匠情挑》,于是导演决定将时代背景和剧情移植到日本殖民朝鲜时期,以便能够加入更多自己所了解的殖民统治时期下的阶级元素与社会背景,更能表现电影想要表达的女性主义倾向。导演拍摄《小姐》的目的并不是要讲述主人公如何克服艰难险阻最终争取到权力,电影想要展示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作为个体的女性,以大时代描述小人物,最终体现人物的女性精神,而并不只是表达时代本身。
导演选择朝鲜日治时期的主要原因是那时的朝鲜正处于现代化与西化催生新事物的时期。1930年初,日本殖民者对于朝鲜半岛思维的管制开始出现松动,怀柔政策带来的是朝鲜人民思想的进步,因此整个社会思潮也正在改变着。女性的平权意识也逐渐于此时萌芽,她们已经开始有了对于性与家庭关系解放的观念。例如电影《小姐》中所展现的女同性恋思想,这是早期的朝鲜乃至日本殖民朝鲜年代初期的朝鲜人们不敢想象也不敢谈及的。《小姐》书写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个体生活,但导演并没有让历史凌驾于叙事,他想要描绘朝鲜日治时期重要的精神变迁,包括阶级矛盾、社会问题、医疗问题等等,但他最为关切的还是女性问题。
电影将改编的重点放在了“男与女”“贫与富”“同与异”“真与假”等方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突显“二元对立”的概念,但对于电影来说二元对立的最终导向是男女两性,在实际社会中男性与女性却又是不平等的,女性明显处于弱势、被动与孤立的“他者”地位。朴赞郁导演曾明确表示过《小姐》是一部带有女性主义的电影,他想用电影打破传统意义上对于女性的固有印象,正因如此,他并没有将原著中的女同性恋情节删除。的确,《小姐》展现出了女性主义电影应有的特点,秀子和淑熙在被压迫后表现出了对于男权的反抗、对于自由的追求,这是导演所鼓励、倡导与宣扬的;姨母和佐佐木夫人多与男权的无力反抗表现出女性的悲剧命运,这是导演所惋惜的,他将这样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希望人们借以反思。
三、女性主义思想在《小姐》中的体现
(一)女性角色的安排
1. 姨母
姨母是日本没落的贵族的后裔,出生以来所接受的男权教育告诉她,她毫无身份可言,她的婚姻必须围绕着家族利益进行,嫁给上月教明(即姨父)后姨母自然而然接受了这种在男性中转手的生活方式。姨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也是被动的、依赖的、模糊的“他者”角色。
2. 佐佐木夫人
佐佐木夫人是古宅的女管家,与姨父离婚后依然坚持留在古宅中工作,对姨父百依百顺,是男权生存规则下迷失自我的典型代表。佐佐木夫人从心里厌恶姨母和秀子,常常借助姨父的男性权威折磨她们,俨然成为男性权威下的“工具”,但她不仅惟命是从还自得其乐。佐佐木夫人同样是生活中的“他者”,秀子说过:“若是能如佐佐木夫人一般的疯狂,生活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熬。”
3. 秀子
秀子5岁跟随姨父生活在古宅中,在姨父的教化下,逐渐成为名噪一时的淫秽书籍朗诵者,电影中的秀子一直以冷艳、端庄与精明的形象出现,但与其他贵族小姐不同,她一直生活在痛苦、压抑与被拘禁的生活中,最后透过逃离古宅的一系列行动重拾自我。秀子是一个与传统女性爱情观相悖的新女性象征,她身上具有的特质与当代女性相似。
4. 淑熙
淑熙曾是一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扒手”,但迫于生活的窘境与现实的逆境,她不得不伙同藤原骗取秀子的巨额财产。在与秀子相处的日子里,她同情秀子的悲惨遭遇也想摆脱自己长久一来的境地,毅然决然帮助秀子也帮助自己逃离男权社会的压迫、摆脱长久以来的“他者”地位,最终获得真正的成长。
(二)女性形象的双重属性
如果从女性主义理论视角分析,更能感受到朴赞郁导演对于女性的理解和塑造。导演将故事焦点集中在电影中两类女性:一种是男权社会中的“旧女性”姨母和佐佐木夫人;另一种是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新女性”秀子和淑熙。
1. 活在阴暗中的“旧女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家是女性被派定的归宿同时也是牢笼,将她与世界隔绝蛰居于被动驯服的无自我意识的状态”[4]53。在日本殖民朝鲜时期男权当道的时期下,女性虽然是自然人,但她们从出生的第一天就被印上了“他者”的身份,就连女性也无意识的将自己的身体当作“工具”来使用。无论是贤良淑德的姨母,还是看似无坚不摧的佐佐木夫人,抑或是出逃前的秀子和淑熙都无一例外。
电影中最能体现女性“他者”身份与地位的就是婚姻。出生于日本贵族家庭的姨母是姨父理想中的结婚人选,他娶姨母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能从低贱的朝鲜人摇身一变成为上等的日本贵族,这也是姨父抛弃佐佐木夫人的原因之一。在姨父的眼里,姨母并不是以“人”的姿态而存在,她是“工具”,姨父利用姨母为绅士们朗诵淫秽书籍赚取权力、地位和金钱,这一切都传达出一个讯息:女人仅仅是“工具”而已,使用价值决定她的存在价值[5]。姨母也经常受到来自姨父的威胁,例如她随时有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这样一个“规训机构”,姨母也绝望的想要逃跑,但终归没能逃脱男权建立的稳固的牢笼,在姨母的眼神中观众可以读到女性隐忍外表下的绝望。姨母出现的镜头并不多,她的形象都是建立在秀子的回忆以及姨父的评价上,直至整部电影结束也没人知道她的姓名,呈现出传统女性处于没落的“他者”位置。
而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和家庭周围环境影响的佐佐木夫人就犹如“家庭天使”一般优雅、服从、持家,渐渐在男权建立的秩序下迷失了自我,被置于“他者”地位的人格逐步显露,即使成为“工具”还乐在其中。当姨母想要冲出书房牢笼的时候是她为姨父关上电闸门挡住了姨母的去路;当叛逆的秀子打了她一巴掌后也是她借助姨父男权威信教训秀子;离婚后仍以管家身份留在古宅照顾家人起居、处理家庭事务、营造温馨的家庭环境以及对姨父的指示言听计从。“对于传统社会难以实现经济独立需要依赖家庭的女性而言,离家出走是天然的悲剧”[6]。总的来说,佐佐木夫人是自愿接受这种地位的,因为只有家庭生活能为她带来满足感,她无法想象离开了这个家该如何生活下去,没有丈夫呵护、没有经济来源、没有孩子依靠的她不敢想象以后的日子。表面上她看似无坚不摧,实际上内心却是空虚无助。
纵观韩国的历史进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男性要求女性奉行类似中国古代儒家“贤德”的品质,用以维护男权社会秩序的稳定。直至今天,虽然人们早已为女性解开了作为“工具”的沉重枷锁,但世俗的偏见依然将女性视为另一层面的“工具”,这样的观念依旧束缚着当代女性的自由之身。
2. 活在晴朗下的“新女性”
女性的解放首先要意识到“女人为什么是‘他者’”,这种意识的产生正是女性主义首要关注的问题,郭赞曾指出,“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题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7]30。《小姐》中的两个主人公秀子和淑熙,她们在最初体现“旧女性”特征的基础上,又被导演赋予了“新女性”的内涵,后来的她们各自都怀着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
在电影中,导演首先采取了详细描述秀子受到压迫和伤害的叙事策略,为新女性竖起改革的标杆作为铺垫,密谋出逃古宅这一象征被认为是秀子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秀子尝试超越自身局限性,将从未得到的“自由”作为自我存在的根本目标,她先是和藤原密谋出逃、背叛藤原、联手淑熙逃离藤原以及和淑熙一起登上驶离朝鲜的邮轮,剧情一再反转,秀子所代表的新女性开始挣脱被动的局面,从最初的沉默到最后的爆发,她以激烈的对抗方式颠覆男权世界一贯的压迫,此时不平等的二元秩序被秀子一一击破,她从一个被害者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斩断了作为客体的“他者”必须依附主体的命运。以淑熙和秀子办理签证准备登船出逃的这场戏为例,秀子将自己打扮成男性,之前秀子都是以一袭长裙示人,裤子是模糊两性界限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符号。由于姨父、藤原以及前来观看她朗读的绅士们都是她生命中最残酷的压迫者,所以她穿上只有男性才能穿的服装来挑战男性权威,结果成功骗过签证官,这对于男权来说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身为侍女的淑熙渴望解救秀子,她的内心被挣脱束缚的声音唤醒,但在1930年的朝鲜,同性恋是禁忌,福柯认为:“一切没有被纳入生育和繁衍活动的性活动都是毫无立足之地的,也是不能说出来的。对此,大家要拒绝、否认和默不作声。它不仅不存在,而且也不应该存在,一旦它在言行中稍有表现,大家就要根除它”[8]4。所以,尽管秀子和淑熙彼此相爱,终归是在无人的时刻才能互诉衷肠。当淑熙作为秀子的守护神,撕烂姨父收藏的淫秽小说,斩断书房门口的蛇形雕塑,意味着淑熙女性意识的爆发,她想要抛弃社会强加给她的“他者”身份,且在同性爱情中认清了自我——认同、归属、支持,淑熙和秀子一同登上驶向上海的邮轮后,淑熙得到的不仅仅是爱情,还通过性别身份认同获得的平等、独立与解放,这使得她最终成长为同恋人秀子一样的新女性。
四、结论
从情感体验上来说,导演注重对于女性的生理特征的挖掘,将4个在男权社会生活的女性形象清晰展示在观众面前。电影作为当代重要的大众传媒之一,营造的拟态社会与所强调的理念更能成为优势意见[9]。《小姐》中4种女性的形象在现代社会里依旧存在,我们应该看到大众对于女性刻板印象正逐渐消减,与此同时又会赋予女性新的社会内涵,因此想要达到完全的性别平等相对困难。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女性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女性变得越来越自由,社会参与度显著提高,权力也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电影在反映现实社会性别观念的同时,也为观众展现了更为开放的性别观念,真正的女性主义,似乎也只有通过社会的进步,两性在经济地位以及本身的差距逐渐缩小的时候才会最终实现,因此女性们在争取性别平等的同时仍需进一步解放思想。
[1]派翠克.戛纳对话朴赞郁:说我拍女同“直男癌”也没办法[DB/OL].(2016-05-18)[2017-03-18].http://ent.163.com/16/0518/07/BNB4K7H30003503S.html.
[2]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1997.
[3]邱静美.西方女权电影理论与批评:介绍与分析[J].当代电影,1988(12):26-3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周怡.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以韩剧《清潭洞爱丽丝》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3(7):112-116.
[6]蔡萍.娜拉出走以后的新出路?——韩国电影《奇怪的她》女性命运主题解析[J].文艺争鸣,2016(10):188-192.
[7]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8]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郑光耀.传播学视阈下《太阳的后裔》爆红的质化分析[J].传媒观察,2016(6):15-16.
[责任编辑 韦杨波]
Travel from the Dark to the Bright——Feminism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lm“TheHandmaiden”
ZOU Lei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xi Arts Institute, Nanning, Guangxi 530022, China)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film The Handmaid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e author divides the four different female characters into two categories such as the “female in the old times” relying on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the “female in the new era” against patriarchal societ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film.
feminism;TheHandmaiden;the other
I235
A
1672-9021(2017)03-0010-05
邹蕾(1992-),女,广西桂林人,广西艺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艺术管理。
2017-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