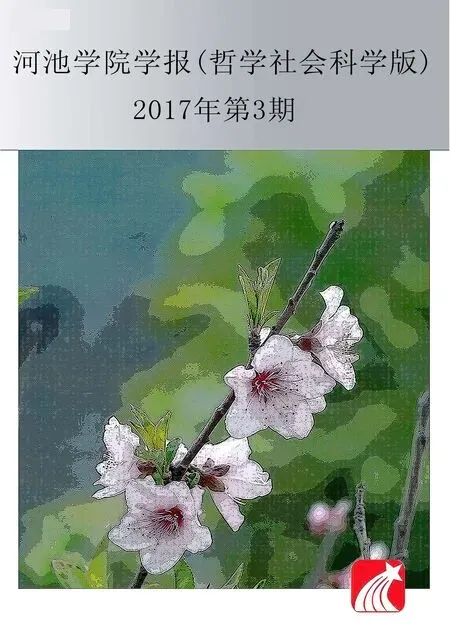动静相合:中国史诗研究的结构民俗学转向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读后
孟令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房山 102488)
动静相合:中国史诗研究的结构民俗学转向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读后
孟令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房山 102488)
《口传史诗诗学》是一部以“口头程式”为理论基础,探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程式句法的专著。“口头程式理论”有显著的结构主义遗留,而于语词、句法的结构分析中,得出的“程式”概念,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我国史诗研究起步较晚,且长期处于固化文本的思想深描,因此“口头程式理论”的借鉴与实践,将我国史诗研究带入从静至动的结构转向中。不过,这里的“结构”并非以建构分析模型为主旨,而是以具体语境中民俗事项的构成规律为核心的研究取向。
口传史诗诗学;朝戈金;结构民俗学;语境;转向
《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朝戈金著《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正文对该书内容的引用除特别说明外,仅于引文后注明页码。(下称《史诗诗学》)是中国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任朝戈金研究员(下称作者)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作为“田野与文本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00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口头程式理论”的重要译介者之一,是作者以中国史诗——蒙古史诗艺人冉皮勒所演述的《江格尔》之《铁臂萨布尔》诗章为个案的“语法程式”研究,而其主旨重在说明“史诗的句法核心就是程式,高明的史诗艺人总是善于调用各种程式手段,用最简单的格式、最俭省的表达、最快捷的语速,最大限度地唤起听众的共同知识与诗意想象”*见施爱东《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民俗研究》,2007年第2期,封面2。。作者于《史诗诗学》对“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的研究,是在诠释“口头程式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同时,以中国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思考在探究长篇叙事诗民间来源的可行性与可靠性。除《史诗诗学》外,作者还有《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合著,1995)、《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田野报告集,2004)、《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译著,下称《口头诗学》,2000)和《西方神话学读本》(2006)等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相关著述。
施爱东认为:“口头程式理论在现阶段民间文学研究中,远未发挥它的阐释效力,更遑论在作家文学研究上的应用了。也许20年后进行学术史回顾时,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史诗诗学》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的范式意义。”的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作者便不遗余力地向国内学界介绍“口头程式理论”,并在翻译《口头诗学》的同时,以亲身实践的方式创作了我国第一部以此为理论基础的《史诗诗学》。杨义指出:该书“确立了口传史诗诗学范畴,并从事相应研究的,这在国内还是首次”,而此项基于田野作业的思考在基础理论和分析模型的建设方面皆大有创新。郎樱认为:在个案中对史诗是“表演中创建”“程式是口承史诗之核心”等关键问题加以阐释,不仅精当而且具有创建,因此该书“突破了现有史诗研究格局,拓展了史诗诗学研究的新领域,对我国史诗学的研究必定会起到推动作用。”扎拉嘎则表示:作者在宏观把握史诗研究的同时,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其价值并不“局限于关于个别史诗文本的范围,而是直接延伸到关于蒙古史诗和中国史诗的整体研究,甚至延伸到关于中国口承文学和口承文化研究的多个领域”*见朝戈金著《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一书“扉页2”。。面对具体的史诗研究对象,作者曾定下从“词法和句法”向“母题或典型场景”再到“故事范型”的递进式研究路线,而本书则是第一层次的科学成果。那么,作者于本书究竟论述了哪些内容,他以何种方式构建了程式句法与史诗创编的关系,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对象。
一、从概念到文本:程式术语和史诗《江格尔》研究史
在《史诗诗学》的《绪论》中,作者借钟敬文先生对我国史诗理论体系建构不足的论述,阐明了创作本书的目的:通过一个特定的史诗诗章的文本分析,来阐释蒙古史诗《江格尔》的口头传统特征——程式化风格,进而探讨口传史诗的史诗特质[1]1,而其方法则是在尽可能广泛参考国内外史诗理论,如“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民族志诗学(Ethno poetics)”,尤其是“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的基础上,从语言构成的实证角度寻绎史诗局部文学因子的链接方式、基本特征和演唱模型,从而在深化方法论的同时,为建构中国史诗理论体系的理性认识和学术思考提供参考[1]4-8。在钟敬文先生看来:该著的学术初衷——“一方面,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去探究建设中国史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另一方面,要在方法论上尝试并倡导一种可资操作的实证研究,通过个案分析以支撑大幅度的理论探索”[2]3——直指我国史诗研究的当代转型(详见后文)。除此之外,作者还于《绪论》中对该书的研究对象、资料来源及相关术语的作了说明,从而为后文之论奠定了概念基础。总体来说,作者在该书中以包含《余论》在内的7个章节,详细阐述了他所借用的“口头程式理论”及其在具体个案——蒙古史诗艺人冉皮勒所演述的《江格尔》之《铁臂萨布尔》诗章——研究中的合法性,从而为其“表演中创编的史诗的句法核心就是程式语言”的论点提供了可靠的证据链。
在第一章“国内外《江格尔》研究概观”中,作者对其研究对象的学术史回顾,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江格尔》的历时研究主要有两条线索:文本搜集史和科学研究史,而世界蒙古学之“卡尔梅克”与“书面文学”则为蒙古史诗的学术走向奠定了实践基础[1]20。在延续200余年的《江格尔》搜集中,流传于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口承本和手抄本得以较早地进入国际视野。虽然我国系统搜集、记录《江格尔》史诗开始于1978年,但不久后便出版20余部整理本的事实则表明,我国学/政两界“对民间口承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时人对田野作业规程缺乏深入了解的史实,也影响了后期文本发表与科研成果的质量[1]29。“通观《江格尔》研究的学术史,蒙古史诗的第一批搜集者也就是其最初的研究者,不过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专题研究,当从符拉基米尔佐夫(B.Ya.Vladimirtsov)的《卫拉特蒙古英雄史诗》(1923年)算起。”[1]29-30作者对符氏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研究的重点介绍显示,该项成果不仅有史学成分,也有文化心理因素,而在梳理“语言形式、乐器、演奏曲调等”细节的同时,史诗歌手的学艺过程以及创编史诗的公式化套路等涉及口传史诗诗学的核心内容也得以描述。尔后,作者指出:“史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理想的镜子,是一个民族历史生活和文化传承的镜子”[1]45,而判断史诗传统成熟度的标准则在于作品篇幅的宏大程度和一批歌手的表演力和创造力。然而,在《史诗诗学》得以创作的20世纪90年代末,分布于卫拉特、巴尔虎-布里亚特、科尔沁-扎鲁特三个蒙古史诗演述中心的《江格尔》传统已然过了田野采集的黄金期,因此作者通过“口头程式理论”以“文本分析为切入点,从史诗演唱的当前情形反观历史,是有以流溯其源的意思。”[1]56
类型与属性在包括史诗在内的几乎所有文学文本的研究中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视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者对相关理论与方法的选择策略,甚至最终结论的“成败”。因此,在第二章“史诗文本的类型与属性”的开篇,作者便指出:“考察口传史诗的文本类型及其复杂性,并兼及这一口头传统的文本化过程(Textualising Progress)和文本迻译途径(Translating Approach),来看文本记录方式和整理状况之于文本研究的重要性”是“开展分析工作的基础”[1]57。作者由荷马史诗的文本类型出发,认为“史诗就流传方式而言,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作品”,而“蒙古英雄史诗均为民间集体创作与传承的口头作品,且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渐现于书面记载和刻本之中”[1]58。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存在,作者为读者呈现出五种——转述本、口述记录本、手抄本、现场录音整理本和印刷文本——有内在联系但又彼此分立的《江格尔》文本类型,从而指出:“基于口头传统的文本研究,除了对史诗文本类型要有清晰的理性认识”外,“田野作业中的实证性操作”和“后期文本整理中的科学化原则”恰是现代史诗“田野文本”研究转向的强力支撑。就此而论,“口头程式理论”的出现“并不是那种自誉为达到了所谓的‘新高度’而一经面世便立即造出轰动效应的‘新学说’,而是因其严谨、扎实的可操作性系统与其注重文本材料的实证性范式”才获取“经得起历史文化的验证”[1]71的长久生命力。
“口传史诗有其内在的、不可移易的质的规定性,它决定着史诗传统的基本架构和程式化的总体风格”[1]72。也就是说,处于口头传统中的史诗文本的属性,首先就具备了区别于书面文学“权威的精校本”的无“权威本”特点,而“从西方学者的田野作业报告和我个人的田野作业经历来看,优秀的史诗演唱者都不是靠记诵,也不是靠复颂,而是靠‘创编’来完成表演的”事实,则表明史诗的“‘一个’诗章与‘这一个’诗章”在内容上的不定性,换句话说,史诗虽有既定的主脉,但每次演述的“再创作”,却于“个体”与“一般”的文本“互涉”中,彰显了史诗演述者对“原本”或“母本”的正统“搁置”。作者认为“史诗文本间的互涉关联”是构筑庞大“史诗集群”的重要动力,而弗里教授(JohnMilesFoley,1947-2012)提出的“比较三通则”——“以传统为本(Tradition-Dependence)”“以文类为本(Genre-Dependence)”及“以文本为本(Text-Dependence)”则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分析提供了规范性的操作模型[1]82-83。给定文本所具有的“粘着性(Cohesion)”“突出性(Prominence)”和“整体性(Macrostructure)”结构要素则为“用一个特定的文本去投射一个宏大的演唱传统,并对这个传统的若干基本要素进行深入的说明”[1]85-86提供了可行性通道。既然口传史诗具有现场创编的表演性,因此对史诗的研究就不能抛开文本与特定时间的社会关系丛——语境(Context)——的对应性的关照,故而作者指出:“史诗的演唱,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信息传递过程”[1] 98,而共享“内部知识”的史诗歌手和听众的复杂互动,让“特殊化”的生活语言在特定时空的艺术化过程中走向程式化。
尽管有西方学者对程式复现频度超过20%的史诗口头性定位的机械分析法做出过批评,但“口头程式理论”所提供的阐释模式却给予我们“一个反证的思路”,那就是“我们可以从文本回到歌手,可以从文本的分析之中去复原一个歌手的程式化风格,也同样可以从一个文本的细部研究研究中去构拟一个歌手所置身的那个口头传统的基本风貌”[1]105。那么,该如何从一个给定的文本得出上述答案,而这个给定的文本又将如何确立,则是第三章“在文本与传统之间”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活形态的口头文学传统”的史诗叙事,“是随时处于变动之中的”[1] 106人为创造,而“所谓《江格尔》史诗,是指一个具有内部相当一致性的、具有相当长的流布过程的民间演唱传统”[1]110,因此,它复杂的结构类型、丰富的情节内容与多样的文本形态,让“从整体研究走向个案研究”的阐释策略成为可能。作者认为,“那种‘目的是根本的,结论是先设的,方法是随意的’研究,其结果无疑离‘文本事实’越来越远”[1]119,而他通过文本细读,发现既有成果之不足,进而定位名家以制定“一人一本”*在作者看来,“著名的史诗歌手大都熟谙本民族的口头传统,在表演尺度上合于口头传统的程式规范,在广泛的听众接受范围内,针对听众的种种反应来即兴创编或改变自己的演唱内容以及表达方式等,日渐形成各自独辟蹊径的演唱技艺,从而也参与了口头传统的继承与发展”。见朝戈金著《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19-120页。的取样原则和遴选标准,再经语言解析、文字转写和数据统计等分析流程,最终为史诗“程式句法”的中国探索确定了科学对象——冉皮勒《铁臂萨布尔》,而这一选择让作者意识到,“传统与文本,犹如因果链的两端,一头连着文化历时发展的‘因’,一头连着文化共时交汇的‘果’”,因此“阐释传统”不仅是“一个过程,一个动态的认知、体验、感悟、诠释与演绎的过程”,也是“涉及到不同层次的处理手段”[1]134。
二、从语词到句法:冉皮勒《铁臂萨布尔》的程式分析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不难看出,第三章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施爱东认为作者“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介绍他所借用的理论、解释其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合法性,并与之前的蒙古史诗研究展开了激烈的对话,其倡导中国式口头史诗与建立学术范式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见施爱东《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民俗研究》,2007年第2期,封面2。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这一对话所要形成的中国史诗研究范式,自第四章“语词程式”开始,作为研究样本的冉皮勒《铁臂萨布尔》则于作者设定的分析模式中逐步展开。在作者看来,在口传史诗中,“单词不是构造诗句的最小单位。虚词当然不是,实词也通常不是。是一些固定的、通常不再切分的词组和短语,才是最基本的构造单元。这些单元不仅相当稳固,而且还形成系统。这种单位就是‘程式’”[1]138。由此出发,冉皮勒《铁臂萨布尔》在“语词”上被作者划分出特性修饰词[1]17(人物)程式、马匹程式、器物和场所程式、数目和方位程式以及动作程式五个类型,而对此详细解析的结果则指出,“程式的确定”,不是“一个随机的过程”,而是与“民族文化”有某些联系的语词结构[1]164。对于“程式”在史诗传统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它赋予史诗演述者以经济俭省的表达能力,也就是说,在史诗演述人的心目中,“只要能用一个现成的方案解决的问题,决不会在几种方案中临时决定取舍”[1] 173。总之,“用于表达某种反复出现的基本观念的相对固定的句法和词语”程式,是在“口头表演和流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既不是可以随意创新和改投换面的大而无当的工具箱,也不是对格式的刻板遵守”[1] 173,而是具有动态效能的史诗传统的结构法则。
继语词程式后,第五章“程式化传统句法”则进入到与本书题名——程式句法——一致的论述中。在阿·波兹德涅耶夫、波佩等前辈学者看来,对蒙古史诗“作诗法(versification)”的总结一直都是件有难度的工作,但他们不甚完美的前期探究已然为后学的继续深入奠定了可资借鉴的基础。在对样本冉皮勒《铁臂萨布尔》诗章的分析中,作者首先关注了史诗步格(Meter)[1]17的程式化,他指出蒙古史诗具有“四步格”特征,而史诗的长短及其韵律的形成则在于“史诗的基本构造——程式——所决定的规律”[1] 183。其次,作者对史诗韵式的阐释告诉我们,蒙古史诗虽然以句首韵为核心特征,但不同史诗演述者在其学艺与演唱的实践中,也会不自觉地展现出尾韵和讲究“元音和谐律”的内韵,而在整个诗句中占绝对优势的“‘一口话’—‘单元’—‘整句程式’”的平行式[1]18,103则证明,“以诗句和诗句组合为基础的韵式”[1] 192根本无法脱离程式规则。虽然在对蒙古史诗的研究中平行式在本书出版前并未得到广泛关注,但英国学者鲍顿的《论蒙古叙事诗中的平行式》已然为这一研究的深入探索奠定了学理参照。正是基于前人探索,以及对“口头程式理论”的应用,作者于本章对平行式的三个类型——排比平行、递进平行与复合平行——做了大篇幅解读。由此得出,作为蒙古史诗风格化的一种手段,这些被广泛且多样使用的程式句法,尽管与汉诗尤其是古典诗歌高度发展起来的格律规明显不同[1]194,但却无法改变它“是民间诗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传统技巧手段”[1]203的事实,而作为句法的结构原则,平行式则为史诗演述者的现场创编在记忆上提供了技能与技巧的便利。
通过对给定文本——冉皮勒《铁臂萨布尔》诗章——的语词程式与句法程式的分析,作者对程式的表现形态做出如下总结:“程式是一个特定的单元,是特定的含义与词语的组合。它有相对固定的韵式和相对固定的形态,它由歌手群体所共享和传承,反复地出现在演唱文本中”[1] 204。由此可见,程式作为口传史诗结构句法的传统手段,其实际形态的代际传承是具有共享性的复现模式。接续上述分析,作者在第六章“程式的类型、系统及功能”中,进一步从语法层面阐释了口传史诗诗学固有的基本原则。在程式类型的探索中,作者给出了片语程式与整句程式、核心程式与附属程式、专属程式与通用程式三对彼此相连却又在功能上表现不尽相同的句法传统,而“程式在口传史诗的演唱中扮演角色的重要程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程式的多样性,或者说是使用的广泛性程度;二是程式的使用频度,或者说是反复出现的复现率”[1] 210。正如前文所言,从“口头程式理论”发展而来的程式频密度分析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非议,但这种以统计为基础的研究模式,却在探究史诗文本的口头性时获得很多有益的成果,而冉皮勒《铁臂萨布尔》诗章在语词、句式、韵式等方面表现出的高频度复现则告诉我们,史诗演述者的现场创编“所运用的最基本的材料,就是音韵优美、韵式繁复、含义凝练的固定表达程式”[1]217。通过对同一歌手的不同文本以及不同歌手的不同文本的比较,作者发现,这一类似于《诗经》套语(formula)的传统手段[1]226,实是运作于系统化的过程,而“系统化的功能是用最简单的格式,用最俭省的经济的表达式,传达某一‘类’富含许多细致变形的事物或者情境”[1]227。因此,对程式的理解和应用,则为解答口头诗歌是如何创作的诗学问题带来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助力。
冉皮勒《铁臂萨布尔》程式句法分析在“余论”中继续深入。“在口传文化中,传统的表达方式要经过缓慢的聚合”,才能形成“在语词上讲究言近旨远,在韵律上讲究起伏迭宕,在句法上讲究呼应对照”的程式,而“这样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表达方式”,是不会被“轻易丢弃或拆散的”[1] 231。因此,这种反复表述的、线性的而非互相包容的,且非口头史诗专利的句法结构,不仅表现于固化的文本,更于演述人的口头创编中生发活力。作者认为,口传史诗“包含着‘常项(式)’和‘变项(式)’成分,通过‘变项(式)’部分的替换,口头诗人得以在现场表演的压力下‘流畅地’讲述故事。句法上的‘俭省’和平行式的广泛运用,就是基于这种压力而来的”,不过,组装传统观念以演述史诗的方式并非易事,而宏大的篇幅决定了史诗“既要在句式上,在程式上俭省,又要在限度之内变异”[1]235。因此,即便文本与演唱有错位,步格与曲调有冲抵,听众对演述人有影响,可蕴含于史诗内部的精细规则——程式——却在传统的强大威势与专门化的制约中形成较弱的历时调适力——“一旦社会变迁最终带来了生活基本内容的大的改变,就等于抽去了史诗赖以存在的理由”[1]239。所以,面对大量固化,甚至正在固化的史诗演述活动,“口头程式理论”及其方法论在强调对活态史诗展开田野作业的同时,也鼓励史诗研究者对史诗文本做出“口头性”(创编)与文化内涵的结构解析。不过,这种学术探索“必须在民俗文化学构建中理解与阐释口传史诗的创作、流布和接受过程”,并“将民间创作置于民俗文化的动态语境中去考察和理解,也只有这样,才能对民间文学创作给予科学的认识和阐释”[1]243。
三、形态之于结构:程式在口头诗歌上的“名动”之辩
于上文,我们已然清晰地了解到作者采用“口头程式理论”及其方法论,对给定文本——冉皮勒《铁臂萨布尔》诗章——所作程式句法分析的整体样貌。不过,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文本之上,是很难想象这一具有典型语言学特征的实证性研究,在初始阶段的艰难性。在本书的“后记”里,作者回忆道:“史诗研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它需要比较好的文学基础,需要有文本解读分析的功夫;在多数情况下,还需要不止一种工作语言。此外,最好还要有田野作业规程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的经验。因而,胜任口头史诗的研究工作,非要相当年头的积累不可”[1]324。这一表述,从表面上看是在表明本研究的难度之大,实则是在告诫后来者,史诗研究需要有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积累。除此之外,作者于此对争论不休的史诗概念也提出了自己的评判见解,他认为尽管“史诗是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语言传统中普遍存在并共享一系列‘特定品质’的一种艺术样式”,但“对它的界定应当考虑这样几个环节:故事情节和故事主人公的属性、史诗叙述的‘视界’、史诗的审美特性、史诗的词语和句法形式、保有史诗传统的人们对它的‘取态’以及它在本土社会中的特定功能”,这不必非要接受某种经典样板,也不必非要以某一“典范”史诗的“典型”特征进行比附和衡量,“而是要‘以传统为本’,以特定语境中特定的文化为尺度”,不过“文化特殊性的泥沼”也需警惕[1]324-325。总之,在作者看来,本书是“围绕着程式句法问题,对一个给定的事实文本,进行比较精细的诗学阐释……来发掘和归纳口传史诗的诗学特质”[1]325,从而完成“经由程式句法这一‘建筑砖块’,从口传史诗诗学的'根部'进行深细的考察,以期为深入理解史诗传统及其诗学特质探明一些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1]327的宗旨。
钟敬文先生指出,《史诗诗学》是中国史诗研究时代转型的代表之作,并指出它在“有意识地以西方口头诗学理论为参照”[2] 16,打开了“我们的思路”,从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奠定了基础,而这种转型“最重要的是对已经搜集到的各种史诗文本,由基础的资料汇集而转向文学事实的科学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下的整体普查、占有资料而转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钟敬文先生虽未对史诗做出专论,但也于很多场合与文章中表露出他对史诗研究的思考,而对新世纪中国史诗研究转向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他为《史诗诗学》所写的《序》中,此文曾以《口传史诗诗学的几点思考——兼评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为题发表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基于此文,韩红星与冯文开对钟敬文先生的“转型”论述做了进一步阐释。详见韩红星《民俗泰斗钟敬文的中国史诗学转型研究方法》,《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2年第2期;冯文开《钟敬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史诗学》,《民间文化论坛》2010年第1期。[2]5。尽管钟敬文先生认为,“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普罗普的民间故事31种机能说,对于特定文化传统中的故事现象,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可“将它移植到史诗结构分析,去解释它同其他民间叙事文学在母题上的关系,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但是不是就很全面?毕竟史诗是韵文体的,在叙事上肯定有其特定的方式”[2]13,不过,这一论述却让我们意识到,“口头程式理论”在解决具体史诗(荷马史诗)口头性问题的分析中即便运用了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法,却也体现了形态—语言学的基本特征——“作为一种方法论,在基本架构上利用现代语言学、人类学研究成果,以史诗本文的语言学解析为基础,论证口头诗歌尤其是史诗的口述性的叙事特点,独特的诗学法则和美学特征”[1],因此从语词/句法到母题或典型场景,再到故事范型的层级分析模式,彰显了史诗演述“在每个层次上都借助于传统的结构,从简单的片语到大规模的情节设计”[4]15的本质属性。因此,对“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概念而经常使用的”,且为“思想和吟诵的诗行相结合”而产生的程式[1]42的研究便具有了结构分析的意味。故而笔者认为,钟敬文先生从作者《史诗诗学》中得出的转型认定,实可被视为“史诗研究的结构民俗学”转向。
在《民间文学的形态研究与共时研究》中,施爱东详细梳理了作为共时研究的形态学的发展历程。作为一种有着生物分类、功能主义和语言学基础的结构分析模式,在中国民俗学,尤其是在故事学领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既已得到广泛应用,而自“1980年代,因西方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在中国故事学界得到传播,许多故事学者才在‘历时的’(diachronous)研究范式之外,洞开了一片‘共时的’(synchronous)学术视野。”[4]虽然以普罗普为代表的形态学家对我国散文体叙事的结构研究影响深远,但这种研究依然有类于芬兰学派的母题/类型分析法,只不过它抛弃了对故事生活史的追溯,换句话说,故事形态学是“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故事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4],是与历时研究处于不同面向的成分构成分析法。由此可见,故事形态学似乎避免了因各种不确定因素而带来的“溯源”的不可靠性,但它对“系统描写”优先性的强调,使“其角色和功能分析取消了内容成分,导致了文本的极端缩减”,而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则认为“普罗普式”故事研究的形式主义困境就“在于它不能重构其本身由以出发的经验”,因而是与注重“语境”的“结构”不同的两种探索模式[4]。也许在普罗普重在捕捉民间叙事之自治原则和列维-斯特劳斯试图发现民间叙事之观念形态的相应理论系统化的同时(或之前),他(它)们的差异性即被以帕里、洛德为代表的古典学者所发现,因而在追溯“荷马问题”的过程中,回溯、借鉴并融合了语言学、形态学和人类学等诸种研究民间叙事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于20世纪60年代正式提出了适用于长篇叙事歌(尤指史诗)的新型结构分析法——口头程式理论,因此它在精神特征上不仅“与20世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试图重建历史和偏重历时性研究的偏好有明显的关联”,同时也“是形式主义和结构研究的某种接续”[4]。
尽管在现代民俗学领域,结构民俗学尚未得到确认,但作为民俗学重要研究对象的民间文学,尤其是散文体民间叙事,却在结构分析中存续了百年之久,而那些以探讨社会组织、称谓制度、神灵体系、行业规则等结构的民俗学著作,则为这一正在孕育的民俗学方法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例证基础。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结构所指的并不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甚至也不是一种经验实体或社会现实,而是指在经验实体之下存在一种深层模式”,而这种象征社会真实状态的结构原则“是人们所不能认识到的,需要人类学家的分析和概括才能发现的深层结构”[9]70-71。据此可知,“结构”的人类学观念是具体学者面对特定对象而于研究中建构的一种模型,因而人类学的“结构”是名词性的。与此不同,杨义认为,“结构一词,在叙事学体系中虽然已然是名词,但从它的中国词源上看,它是动词,或具有动词性。这一点非常关键,‘结构的动词性’是中国人对结构进行认知的独特所在”,而“任何结构如果包含着生命投入,都不应该视为凝止的,而应该是带动态性的”[10]35。在《史诗诗学》中,作者写道:对词法和句法的分析,实是在探究史诗创编的基本法是如何生成、如何运作、如何发挥作用的,并由此勘察“传统是如何模塑歌手和听众的,是如何既限制歌手的自由发挥,给予这种发挥一个基本的范围,又为这种发挥提供使用便利而又威力无比的手段”[1]134。由此可见,作为特定族群共享的叙事传统,具有典型生命投入性的史诗程式并非人为建构的分析模型,而是用以发现史诗演述中各类非凝止性影响因素的结构规则,所以结构之于程式是动词性的。藉此,笔者认为,结构民俗学不以建构分析模型为主旨,而是以具体语境中的民俗事项(本身或之间)的构成规律为核心研究取向的民俗学理论与研究方法。
四、语境的整体性关照:韵文体叙事的程式意义和问题
相较于延续百年且异彩纷呈的散文体叙事的结构(母题与类型)分析,韵文体叙事的同类研究却略显微势。然而,“口头程式理论”的出现,不仅为“荷马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同时也为其他史诗,如芬兰《卡勒瓦拉》、英国《贝奥武夫》、德国《尼伯龙根之歌》和法国《罗兰之歌》等的“集体性”和“口头性”确认带来了新路径,而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进驻,则为我国史诗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结构分析法。作为这类研究的首部作品,《史诗诗学》不仅具有开创性,同时兼具范例性,而鲜益《彝族口传史诗的语言学诗学研究——以<勒俄特衣>(巴胡母木本)为中心》[11],胡云、陈永香的《<梅葛><查姆>文本的程式语词和程式句法分析》[12]以及杨杰宏《东巴经籍文献中的口头程式句法研究》[13]等既是明证。随着《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故事的歌手》《荷马诸问题》[14]等有关“口头程式理论”的译著相继出版,“程式”不仅在我国各民族史诗中大放光彩,同时也被用于叙事诗、民歌、曲艺、演剧(戏剧)等民间叙事体裁中*为展现“口头程式理论”在韵文体叙事中的广泛应用,笔者在此对上述体裁各举一例以作说明。叙事诗——白洁:《土族叙事诗<福羊之歌>的口头程式解读》,《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民歌——那贞婷、曹义杰:《“花儿”牡丹程式探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曲艺——马春莲:《口头传统艺术——河洛大鼓的程式化特征探析》,《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1期;演剧——白海英:《民间演剧“程式化”分析——以家庭伦理剧为例》,《河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虽然目前尚未出现类似于《史诗诗学》的专著,但这依然大大拓展了韵文体叙事的研究策略和结构分析法的应用领域。
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一直在强调史诗程式的“解密”是来自于静态文本的“抽丝剥茧”,是传统民间文学研究模式的翻版,然而,对程式解读的本质则是对史诗演述传统的结构法则的探索,是对史诗演述人在具体语境中如何顺利完成史诗演唱活动的分析,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将史诗文本从表演情境中剥离出来,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进而研究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强调,这个文本不仅是传统中的文本,而且也是具体表演语境中的文本,它本身就是口头传承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特别要避免对它进行与生存其间的母体——活生生的史诗演唱传统——的双重割裂:把它与传统的民俗生活剥离,从而使它变形和失真;再将从孤立的文本分析得出的结论,拿来重新拟构传统的民俗生活,也包括拟构史诗演唱”[1]97-98。钟敬文先生在该书的《序》中也指出:“民间口传史诗的研究,应当注意甄别文本的属性,而文本分析的基本单位,不是简单排列的一个个异文,而是具体表演中的一次次演唱的科学录音本。这就不是各种异文经整理加工后的汇编,而是史诗演唱传统的有机活动系列,包括一位歌手对某一诗章的一次演唱,不同歌手对同一诗章的一次次演唱,诗章之间的关系,歌手群体的形成与消散,个体风格的变化,演唱传统的兴起、衰落与移转等等”[2]6。因此,作为探究口传诗歌创编规律和运行特征的“程式”分析是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动中取静,却又不是简单的文本回归。换句话说,文本(民俗事项)虽是静止的,但它却是在外部语境的创编与内部符号的结构中形成的文化综合体。总之,史诗研究的结构民俗学转向,是在动静相合的双重作用下完成的。
作者曾多次强调语境在史诗程式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而“广义的语境包含诸多因素,如历史、地理、民族、宗教、语言以及社会状况等。由于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内容、结构和形态的形成与变化,因而它们也成为解决传承与创作之间关系的重要关联。田野意义上的‘语境’是指特定时间的‘社会关系丛’,至少包括以下六要素:人作为主体的特殊性、时间点、地域点、过程、文化特质、意义生成与赋予”[1]15。据此可知,注重“语境”的“口头程式理论”在面对具体史诗时,所要考虑的并非仅限于静态文本本身,还有蕴藏于文本背后的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丛”。然而,正如尹虎彬所言:“限于西方主要语言传统,对东方尤其是中国各民族活形态的口头文学的研究甚少”的时代,这一理论一直局限于“大都运用在毫无演唱背景的书面史诗的研究上,强调本文而忽略背景”[3]的状态。《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的作者约翰·迈尔斯·弗里就曾在该书《作者中译本前言》中指出:在中国,“活形态的口头传统是极为宏福丰赡的宝藏,世代传承在其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口传研究当能取得领先地位。中国同行们正是出于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他们可以做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去体验口头传统,去记录口头传统,去研究口头传统。”[4]10-11就此而论,《史诗诗学》恰恰突破了“口头程式理论”创立者及其承继者偏重文本的缺憾。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作者在《史诗诗学》中所使用的给定文本虽有相应背景的阐释,但依然缺乏演述语境的介绍,而对语词、句法、步格、韵式、平行式、程式频密度和程式类别及其系统的分析与总结,同样具有局限于纯文本的倾向。毕竟,以结构分析为代表的共时研究和以文化解析为代表的历时研究,是很难同时进行的同一事物的两面。
总之,借助“口头程式理论”而创作的《史诗诗学》打破了我国传统史诗研究的基本套路,它不仅给予我们理解这一新方法论以途径,更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个案研究模式,而这一弥补西方程式分析法不足的中国例证,让“结构”的名词性认识转向动词性运用,从而为结构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归纳)带来“动静相合”的积极作用。不过,“语境”在史诗程式研究中未能充分展开的遗憾也让我们切实认识到“共时”与“历时”的分立性。尽管钟敬文先生曾说:“有意识地以西方口头诗学理论为参照,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以我国丰富厚重、形态鲜活的多民族史诗资源为根底,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也是完全可能的”,但他也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史诗的‘程式化’因素和‘非程式化’因素及其相关民俗含义,进一步的研究,以从整体上逐步完善史诗理论研究这个有益的学术工作”,并着实强调“这种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总结,必须实事求是地结合中国各民族的本土文化,要超越纯粹经验的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从民俗文化学的传统视角——立足于口头传统来进行研究,并将史诗诗学与民俗文化传统有机地整合为一体,应是当代中国史诗学这门学科所应追求的基本目标和学术框架”[2]16。因此,面对西方理论的中国进驻,我们虽不能以“西学中源”的自大心态对之,但也不能“妄自菲薄”的否定自己,只有在珍视自我的基础上,用在地化的“他山之石”才能“攻出好玉”。
[1]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2]钟敬文.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序[M]// 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3]尹虎彬.史诗的诗学:口头程式理论研究[J].民族文学研究,1996(3):86-94.
[4]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M].朝金戈,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6]施爱东.民间文学的形态研究与共时研究——以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为例[J].民族文学研究,2006(1):5-12.
[7]周福岩.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及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J].周口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1):54-57.
[8]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口头程式理论(Oral-Formulaic Theory)[J].民间文化论坛,2004(6):91-93.
[9]庄孔韶.人类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0]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1]鲜益.彝族口传史诗的语言学诗学研究——以《勒俄特衣》(巴胡母木本)为中心[D].成都:四川大学,2004.
[12]胡云,陈永香.《梅葛》《查姆》文本的程式语词和程式句法分析[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3(11):17-24.
[13]杨杰宏.东巴经籍文献中的口头程式句法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18-126.
[14]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M].巴莫曲布嫫,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韦杨波]
Combination of Dynamic and Static:Structural Folklore Turns of Chinese Epic Studies——Reading Postscript of Chao Gejin’sOralPoetics:FormulaicDictionofArimpil’sJangarSinging
MENG Lingfa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Fangshan District,Beijing 102488,China)
OralPoeticsis a monographs which is based on “oral formulaic” to discuss the formulaic diction of Mongolian epic Jangar Singing. “Oral Formulaic Theory” has a significant legacy of structur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formulaic” which comes from structural analysis of words and diction is not only a kind of theory, but also a kind of method. The study of epic in our country is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and lain in thick description of thought of solidified texts, so the reference and practice of “Oral Formulaic Theory” has brought Chinese epic study into structural turn from static to dynamic. However, the “structure” is not the purport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model, but is a core research orientation to study folk customs in specific context.
oral poetics;Chao Gejin;structural folklore;context;turns
I057
A
1672-9021(2017)03-0026-09
孟令法(1988-),男,江苏沛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口头传统与畲族民俗。
2017-03-15
——新一代江格尔奇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