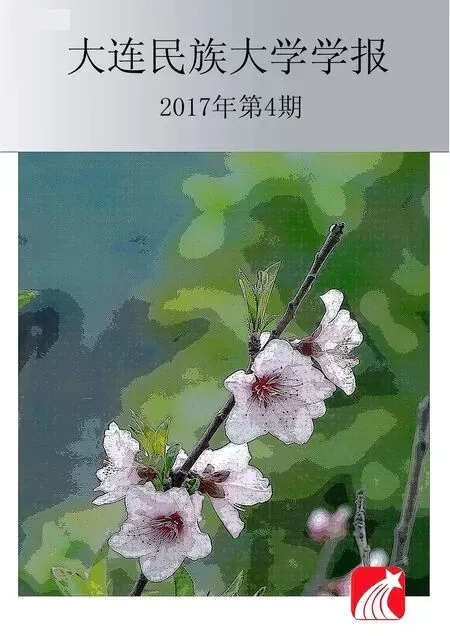薇拉·凯瑟作品中的生态文明审美观
谭晶华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5)
薇拉·凯瑟作品中的生态文明审美观
谭晶华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5)
结合薇拉·凯瑟小说作品的文本分析,从三个方面——生态整体主义审美观、生命共同体意识、“荒野”审美来探讨凯瑟小说中潜隐的生态文明审美观,旨在为正在构建之中的生态美学理论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并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所启示。
生态文明审美观;生态整体主义审美观;生命共同体意识;“荒野”审美
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一种新的文明观——生态文明观也应运而生。生态文明观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观和宇宙观,它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其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社会的可持续良性发展,以及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和方式,生态文明观正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同时,它也必将带来全新的审美观——生态文明审美观。生态文明审美观“从生态文明的视界来看自然环境审美。自然环境的美既不在生态,也不在文明,而在生态与文明的统一即生态文明”[1]。这种审美观克服了传统美学观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是将人类中心主义倾向的美学视界加以延展、进而包括自然作为价值主体的存在论美学观。
美国20世纪著名作家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一位具有生态整体主义意识的生态作家。她的生态创作源自其植根于自然的人生经历以及对人类生存体验的哲思。她对工业文明、过度城市化、消费主义的批判的背后是崇尚人与自然和谐、敬畏生命的生态情怀。凯瑟强调艺术的审美救赎功能,倡导自然的复魅,推崇人植根于自然的“活感性”的重建,彰显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的紧密联系,这与当代的生态文明审美观深深契合。探究凯瑟作品中的生态文明审美观,不仅为正在构建之中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而且将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很深刻的启示。本文结合凯瑟小说的文本分析,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凯瑟作品中的生态文明审美观。
一、生态整体主义审美观
生态文明审美以自然环境美中的生态整体性为尺度,即人们的审美标准以审美对象是否利于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为参照系。有利于生态系统和谐稳定的才是美的,反之,破坏生态整体和谐稳定就是丑的。生态审美遵循整体主义美学,其审美标准与传统美学以人类为中心式的主观化审美截然不同。主观化的欣赏是如画式的。例如,人们向往大草原、沙漠、湿地等美景,是因为能拍出好的照片,这样的欣赏仅停留在表面。如画的欣赏强调愉悦的景观体验,不会去凸显那些荒野中“野蛮的、巨大的、杂乱的土石堆”[2]。而生态整体主义审美依照的是生态整体的尺度,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固有秩序满怀敬畏之情的欣赏。这种审美欣赏的对象“很可能不是整洁、对称的、仅仅对人有利的,而是自然界的‘不可驾驭和混乱’,而且,决定和制约着这种不可驾驭和混乱状态的自然规律越是神秘、越是未被人认识,其美感就越强烈”[3]。
凯瑟在其小说《啊,拓荒者!》中对原始人“疯子”艾弗的深情描绘就体现了作家的生态整体主义审美观。艾弗是作家的代言人,他是凯瑟所推崇的自然之子形象。艾弗在邻居们眼里是个疯子,因为他样貌奇特,偏爱原始的生活方式,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他是一个长得很怪的老人。厚实、健壮的身体下面是两条短短的罗圈腿。一头乱蓬蓬的白发像马鬃一样披在红润的两颊上。他光着脚,但是穿着一件干净衬衫。脖子处敞开着……他自己有独特的宗教。” 不难看出,艾弗的外形具有前现代文明的原始先民特征。他栖居于自然荒野,不受现代文明繁缛规范的束缚,因而摆脱了现代文明的玷染。他信奉万物有灵,这种信仰和他简朴的生活方式使他能够参透自然之神秘,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智都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就连他的居所也与周围的自然景观巧妙地融合。在移民们居住的大分界线上,艾弗的荒野宅第与众不同。房子依偎着池塘而建。那是一个土坝上草皮下面的洞穴,上面挖了一道门和一扇窗,“这里没有草棚,没有牲口圈,没有一口井,连一条草丛里踩出来的道儿都没有。要不是有一个从土里伸出来的长了锈的烟囱,你真会从艾弗住房的屋顶上走过也想象不到你是走近了人居住的地方”[4]22。
而艾弗本人对他的野地宅第喜欢至极,因为他认为住在野性的地方,便离他的上帝很近。在这里他可以眺望那“粗犷的原野”“微笑的天空”“在炙热的阳光下晒得发白的卷曲的野草”、倾听“云雀的高歌”“鹌鹑的咕哝和长夏蝉鸣”。艾弗深知自己与其他物种间的亲情关系。他能够与动物交流,医治牲畜。“他从来不吃肉,不管是鲜肉还是腌肉”,将动物视为姐妹,禁止人在他居住的湖边打猎,“讨厌人住的地方的那些垃圾,” 希望有一个“獾太太”成为自己的妻子[4]23。 他已与周围的自然生态毫无界限,俨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他以虔敬、尊重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环境。他对自然的审美体验超越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在这里,没有现代人追捧的舒适的物质占有和享受,只有素朴的生活和与自然相栖共生的和谐美。凯瑟研究专家苏珊·罗素斯基(Susan J.Rosowski )也对其大加赞叹,称其为“美国化的自然之神”[5]。
凯瑟从小生长于美国西部内布拉斯加的原生态荒野,对那里的一草一木的描写都表现着她对原始自然的热爱与野性本真的推崇。对艾弗的自然本性的推崇彰显了凯瑟具有前瞻性的生态审美理念,即维护生态系统和谐稳定、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即使是狂野的、在传统审美观看来是不伦不类的审美观,也是美好的,值得人们敬畏尊重的。
荒野和野地是充满野性和活力的,在西方传统文明中常被视为需要进行管理和重新规范的混乱无序之地。在凯瑟看来,隐藏在这种理念之下的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式的偏见。凯瑟通过对艾弗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解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进而表达她的生态整体主义意识和审美观。
二、生命共同体意识
生命共同体意识是生态文明审美观的另一个主要特征。生命共同体是指人与宇宙万物、自然生灵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休戚与共、互蕴共荣的关系;自然中的任何生命个体都拥有其内在固有的价值,与人类的命运密切相关,他们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整体。生态文明审美观以保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为历史使命,“让人的审美视界扩展到生命的联系与网络”[1]。它强调人对自然的依存和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
薇拉·凯瑟的小说能使读者体验到强烈的震撼力与感染力,其作品中弥漫的生态共同体意识功不可没。凯瑟以敏锐的目光洞悉到20世纪初已出现的生态危机的本质——人性危机,即人类的伦理价值观、消费观、欲望动力论思想是自然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与此同时,自然生态的失衡更加剧了人性危机。人类要拯救心灵危机、实现自我,惟有重新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重返自然家园,回归自然生命共同体。
生命共同体中的“自我实现”理念是凯瑟生态美学的重要思想。“人类个体的自我实现要以融入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前提,人类只有在与自然互蕴共荣的关系中才能建构自我的价值。”[6]深层生态学认为,人类的自我实现需要在与自然的相栖共生中展开,代表自然界整体利益的“大我”(Self)与人类个体发展的“小我”(self)二者有机结合,人类才能在感性和理性、意识和无意识方面达到平衡,从而真正地实现自我。
在小说《啊,拓荒者!》中,亚历山德拉与人类中心主义者对待自然的态度截然不同。她的代表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兄弟们一心想从土地中榨取经济利益,视土地为“对人类不友好的”“喜怒无常的怪兽”, 并放弃土地去大城市里谋生。而亚历山德拉选择留在大分界线的原野上细心地照料土地,尊重并把它视为知己,与土地相知与共。她深知自己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的。“在狭长的山脊下,她看到未来在骚动着”[4] 14。 她是土地的守护神,她“以爱和渴求面向着它”,这片“美丽、富饶茁壮、光辉灿烂”的土地也以爱意和丰厚的收获回报她,并给予她精神上的指引和力量,使她满怀信心度过艰苦的岁月。“土壤中的活泼生机融入了自己的身体”[4]41,昔日的荒野变成了一片繁荣富庶的土地。“那散发着这样着装、洁净的芳香,孕育着这样强大的生机和繁殖力的褐色土地,俯首听命于犁耙;犁头到处,泥土发出轻柔的、幸福的叹息,乖乖滚到一旁,连犁刀的光泽都丝毫无损”[4]42。
亚历山德拉在与自然的相栖共生完成了自我实现。亚历山德拉的自我实现展现了凯瑟“生命与自然息息相通”的生态理念和人与万物紧密相联的生命共同体意识。
这正是当代生态美学所倡导的主体间性审美境界。在这种审美境界中,审美主体和客体超越了主客观的二元对立,体验者与体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关系。因此,两者之间距离感也已消融,体验者则以一种全方位的、多感官的方式深度沉浸于体验对象之中。生命与自然息息相通,紧密相连。人在与自然的交汇中获得宇宙的能量,重获生机与活力,纵然身处都市,依然能拥有一种“在家园感”。
在工业和科技引领下的文明中,人类在征服、利用自然的同时,欲望也愈发膨胀。人类过度的物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与泛滥,将无形中导致人的信仰、精神的扭曲与异化。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的联结也将分崩离析。人的感性与理性、意识与无意识也已然分离,精神生态危机失衡。凯瑟通过其创作向我们昭示着,仅靠理性去分析与实验研究,还不能真正地理解自然。理解自然需要人具有“活感性”,即主体间性的审美能力与融入自然的诗性智慧。在物欲横行、精神麻木的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的正是这种理智的提醒和生态关怀。
三、“荒野”审美
生态文明审美观提倡荒野的审美价值和精神意义。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荒野审美也逐渐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荒野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特别是受现代社会具破坏性的科技影响最小的地带或生态系统”[7]17。深层生态学家指出,“荒野是生物种类自由繁衍的生态地域,荒野之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过它所产生的经济利润和价值”[7]111。凯瑟是一位深入荒野实践、探寻荒野本质的作家。她的每一步作品都散发着原始荒野的气息,她的五次美国西南部荒野之旅为她的生态创作提供了灵感。在20世纪初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进程正危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关系的背景下,凯瑟创作了一系列以荒野为背景与主题、弘扬原始野性生命力与生态和谐的优秀小说作品。
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认为,“荒野乃是人类经验最重要的源,它“展示着我们的生命之根,是“荒野剥去了我们的文化修饰,激活了我们的本能。”荒野具有陶冶心灵的精神价值,正如罗尔斯顿所言:“在对我们进行价值教育上,荒野跟大学一样是必需的。”[8]然而,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逐渐深入,荒野不复存在,人们植根于自然的“强劲活力”变得“松弛懈怠”[9]。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控制、利用自然的欲望愈加膨胀,人类与其野性的自然家园与内在的精神健全已渐行渐远。
凯瑟敏锐地意识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并藉由小说创作,为我们展现了工业文明社会中如何回归“荒野”审美,进而重获人性的完满。她将荒野保护与重建人的野性活力联系在一起,提醒人们对荒野自然和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1890年前后,美国西部拓荒结束,原始荒野已不复存在。凯瑟忧心忡忡的感到,荒野的逝去将导致现代人精神懈怠与活力丧失。正如凯瑟在其短篇小说《邻居罗西基》中展现的那样,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像“一条生活在水族馆里的鱼儿那样”,没有自然空间,钢筋水泥化的城市犹如令人窒息的监狱。“这种苦恼就是大城市生活造成的;它们把你囚禁,用水泥把你团团封住,使你和外界分离,与大地隔绝”[10]。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地再现了现代人脱离其荒野之根、迷失自我的精神困境。
在高科技发达、人与自然都趋于物化的现代社会中,凯瑟看到了文明的误区,她将保护荒野与文化重建联系在一起,开始唤醒人们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形成一种自然、社会与精神和谐共存的强大的生态视野。同梭罗一样,她认为,保护荒野就是保护世界;荒野不是人类征服利用的对象,而是我们在现象世界中能体验到的生命最原初的基础,也是生命最原初的动力。凯瑟的作品不仅包含现代还乡的精神家园的自然寄情功能,其鲜明的特色是重新思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11]。在其笔下,富有生机活力的原始荒野不再是她同时代的男性作家所展现的有待开发的“绵延起伏的处女地”,而是一个拥有独立价值和话语权的存在。 例如,在《啊,拓荒者!》和《我的安东尼亚》中,凯瑟“没有把西部描写成一片等待着被人类摧残的处女地,而是把它构想成一个女性的自然界,从酣睡到苏醒,进而迸发出争取独立的吼声”[12]。
在凯瑟的创作中,荒野是纯净自然的体现,是工业文明的对立面,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毒剂。荒野在凯瑟的审美视野中既是自然存在,又是具有独特审美内涵的精神空间。它代表着整体关联、生机焕然的生态诗境。回归荒野即是重回自然的母体,复归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初共在。藉由其“荒野”审美,凯瑟旨在唤醒人们植根于自然的生命活力,重建彰显着野性生命力的生态和谐社会。
四、结 语
21世纪城市化、后工业化的进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类生态危机的梦魇依然挥之不散,那么,如何在后工业社会达到人在地球上“诗意”的、有尊严的栖居?凯瑟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即生态审美化的生存。即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野下,保护荒野,敬畏自然,并以生态审美的方式——主体间性的双向互动式审美体验,重建人与自然的本源联系。从而将人类的自我拓展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大我”,使人类的个体生命回归到深邃而具有灵性的生命共同体世界中。这种审美观正悄然浸润于我们的生命体验之中,它将带来全新的审美观念和相应的审美方式,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
[1] 陈望衡. 生态文明美: 当代环境审美的新形态[N]. 光明日报, 2015-07-15(14).
[2] 赵红梅. 美学走向荒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15.
[3] 王诺. 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8: 51.
[4] 薇拉·凯瑟. 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尼亚[M]. 资中筠, 周徽林,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3.
[5] ROSOWSKI SUSAN J. The Voyage Perilous: Willa Cather’s Romanticism[M].Lincoln&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6:141.
[6] 谭晶华. 薇拉·凯瑟小说中的生命共同体意识[J]. 名作欣赏,2013 (5): 89.
[7] DEVALL, BILL , SESSIONS, GEORGE. Deep Ecology: 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M]. Salt Lake City: Gibbs Smith Publisher, 1985.
[8]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M].刘耳, 叶平,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 213-216
[9] NASH, RODERICK.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150.
[10] 薇拉·凯瑟.薇拉·凯瑟精选集[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4:309.
[11] 纪秀明.传播与本土书写: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当代小说生态叙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64.
[12] ROSOWSKI, SUSUAN J .Birthing a Nation: Gender, Creativity and the West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79.
(责任编辑 王莉)
Aesthetic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Willa Cather′s Works
TAN Jing-hu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
This paper probes the aesthetic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Willa Cather′s works by analyzing the ecological holism, life-community awareness and wilderness aesthetics embodied in her writing.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useful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aesthetic stud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aesthetic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esthetics of ecological holism; life-community awareness; “wilderness” aesthetics
2016-10-27;最后
2016-11-30
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基金项目(2016lslktwx-09)。
谭晶华(1977-),女,满族,辽宁营口人,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2096-1383(2017)04-0339-04
I71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