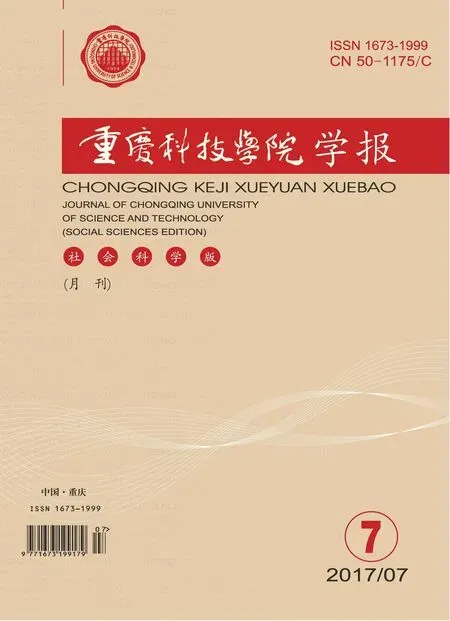京派与海派对“乡土”和“都市”的双向审视
王佳欢
京派与海派对“乡土”和“都市”的双向审视
王佳欢
京派和海派因为“京海之争”的存在,一直以来被定义为相互对立的2个流派,京派对“乡土”的执着和海派对“都市”的专注,似乎也证明了二者的对立性。但是,细读文本我们发现,京派作品中也存在“都市”书写,海派作品中也有对“乡土”的指涉。以“乡下人进城”和“城里人下乡”为着眼点,可以窥见京派和海派文人对“乡土”和“都市”的双向审视。
京派;海派;“乡土”;“都市”;“乡下人进城”;“城里人下乡”
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界迎来了现代都市小说创作的高峰期。现代与传统的碰撞,都市与乡土的流变,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群体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与交融。京派和海派由于对“乡土”和“都市”的情感指向有着截然相反的姿态,他们彼此之间在文学观点、文化风格、审美追求,以及地域情感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性。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界才有了著名的“京海派之争”。
京派作家大多以“乡土”的视角来审视“都市”,批判现代都市对人性的异化和压制以及对生命力的削弱;海派作家则大多生于都市、长于都市,缺乏具体的乡村生活经历,因此“乡土性”在他们的生活和文学写作中只有些许残余并被逐渐淡化[1]。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导致了研究者们多从二者的异质性方面入手来对其进行分析考察,往往忽略了京派与海派在对“乡土”和“都市”书写中的双向审视。
以此为背景,将京派与海派在对“乡土”和“都市”把握上的共同之处作为出发点,分析二者涉及的“乡下人进城”和“城里人下乡”的问题,并以此来揭示京派与海派在“乡土”和“都市”话题上的双向审视。
一、“乡下人进城”
虽然京派和海派对“都市”的书写有着大体不同的感情,但是,不能否定二者在对“乡土”和“都市”的审视视角上存在一致性的事实。对于“都市”的书写,京派文人也或多或少有些涉及,这其中不乏京派大家沈从文的作品,如小说集 《都市一妇人》《一个母亲》《如蕤》《八骏图》《主妇集》等。 此外,还有萧乾的《篱下集》《梦之谷》,废名的《追悼会》《晌午》等作品也符合京派文人的“都市”指涉。
(一)京派写“进城”
在沈从文众多具有田园乡土风格的作品中,《灯》属于比较都市化的作品。首先,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是都市化的“我”住在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里。其次,故事的发生也与都市有着某种关系,即身处都市的“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另外,故事中的次要人物也都来自于都市。相反,故事的2个主人公却并不是真正的城里人。
小说展开的形式是文人们惯用的讲故事的方式。先以“一个穿青衣服的女人常到住处来,见到桌上的一个旧式煤油灯,擦得非常清洁”为悬念,又因为这个女人“想知道这灯被主人重视的理由”,所以屋主人就告诉青衣女人关于这盏灯的故事。故事就这样展开了。说的是两年前的事情,“我”住在上海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担任教员职务,后来收到一封信,来信之人是随同“我”父亲征战多年,又为“我”祖父守过坟墓的“老兵”,这个老兵是个乡下人,写信“说是愿意来伺候我”,主动要求做“我”的厨子。他把“我”伺候得很好,除了关心“我”的衣食起居之外,甚至会特别热心留意“我”身边的女人。他仿佛把责任完全放在他自己身上,从此对于和“我”来往的女人都被他所注意了。他没事的时候还会问“我”一些学校的事:问“我”那些大学生将来做些什么事,是不是每个人都去做县长;又问学校每月应当送“我”多少钱,这薪水是不是像军队请饷一样。他期望有一天能够“把他从市上买来的呢布军服穿得整整齐齐,站到亚东饭店门前去为我结婚日子作‘迎宾主事’,还非常愿意穿了军服,把我的小孩子打扮得像一个将军的儿子,抱到公园中去玩!他在我的身上一定做了最夸张的梦,梦到我带了妻儿,光荣,金钱,回转乡下去,他骑了一匹马最先进城……让一个小县城的人如何惊讶到这一次荣归!”他注意到来“我”住处最频繁的一个蓝衣女子,误以为她是“我”未来的太太,就与这蓝衣女子有了一些亲近,有时还谈一些话。可是,当他知道蓝衣女子要嫁的人并不是“我”之后,他心中坚持了许久的一个梦又破碎了,甚至在“我”的面前哭了,从那以后他便不再如以前那样管“我”的事了。后来我们约好暑假一起回乡下,但由于战事突起未能成行,他要了路费就到南京去了,从此再无音信。
“我”租住在上海教书,可“我”并不是真正的都市人。从地域上说,“我”是从乡下来上海谋生的,这可以从小说的细节得知,如“我老家人……”厨子为“我”做的衣锦还乡的梦,约好同厨子“一块儿转回乡下去,因为我已经有八年不曾看过我那地方的天空,踹过我那地方的泥土”等等。从情感上来说,“我”并不喜欢这座城市以及这里的人们,小说开头写到上海电灯公司的失职推诿,上海商人的见利忘义,以及上海女房东的金钱算计,后来又提到同事们自作聪明的“雅谑”,学生们只听文坛轶事的空套子。这些都说明“我”并不能完全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相反,“我”和乡下来的厨子却是很聊得来。
沈从文的《灯》虽然花了大半篇幅在写“都市”,但是,“我”和“我”的厨子以“乡下人进城”的外来者身份并不能真正融入这座城市。虽然我们已经看似适应了城市的生活,可是“我”的内心仍是对城市的疏离和对故乡的亲切。“我”的厨子从乡下来,对“我”的父亲和“我”都忠实无比,是奴性也好,是亲情也罢,他对“我”的关怀就如一个长辈对一个晚辈一样,他不懂做学问的人将来未必是县长,也不懂女性朋友对于文人来说就只是朋友,他只是用他与生俱来的“乡下人”身份来照顾“我”,关心“我”的婚姻和健康。他正直单纯、朴实忠诚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到了城市而有所改变,反而感染了“我”,让“我”对城市里的一切也有了自己的感受。
京派文人写“进城”小说的,除了沈从文的《灯》以外,萧乾的短篇小说《篱下》也是类似题材。但是,和沈从文的《灯》有所不同的是,《篱下》是把一个乡下孩子的童真带到了与之不相称的城市中。下河摸泥鳅、上树摘枣儿、对花草撒尿、惹哭小表妹、和表弟打架等等,这些在乡下孩子眼中看似平常之事在城市中却是绝对禁止的,因此,最后被姨父赶出了城市。
无论是沈从文还是萧乾,他们都以京派文人的目光在文本中关照“乡下人”,审视他们在都市的生活状况,就像是审视自己的生活一样。他们并没有在作品中刻意抑城扬乡,小说中表现出了“乡下人”的无知愚昧、不懂礼节和顽劣泼皮,写到了“都市”的文明和便利。但是,从人物的情感来看,“乡下人”的无知凸显了他们的淳朴,“都市”的文明反而被虚繁的假象所掩盖了。
(二)海派写“进城”
海派文人写“乡下人进城”的作品有许多,这里主要讨论施蛰存的短篇小说《春阳》。
《春阳》写的是一个寡妇从乡下到上海去办事的心理活动过程。婵阿姨本来有个未婚夫,他是一个拥有3 000亩田的大地主的独子,但是在婚前75天,她的未婚夫死了,她在经过两天两夜的考虑之后,决定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抱着牌位做亲而获得大宗财产的合法继承权”。婵阿姨坐火车从乡下昆山来到上海的上海银行,在她开保险箱时,她注意到有个年轻的银行职员在看着她,对她很是热情。她办完事从银行出来,发现春日的暖阳照射着大地,心情也变得好起来。她决定在上海多逗留一些时间,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她开始后悔十几年前的决定。后来有个年轻男人似乎要在她对面的座位坐下来,但是犹豫之后又走向了别处,婵阿姨开始想象那个男人如果坐在自己对面是否会陪她一起看电影,那个男人是否是个银行职员。想到这里,婵阿姨竟想到在银行里一直看着自己的那个年轻职员,她想到他对她微笑,她似乎有些心动了。接着她想自己是否有必要再回到银行,也许她的人生以后就不会这么寂寞了。当她找到重回银行的借口时,却发现那个年轻职员只是把她当作一位普通的客户,并且称呼她为“太太”,她感到愤怒又羞愧。她在春阳下做的一场美梦就这样被现实惊扰醒了。
在施蛰存的小说中,“婵阿姨”这一形象被塑造成一个从乡下来的寡妇,打扮老土,内心寂寞,守着一大笔钱却相当吝啬,见到别人对她热情就以为人家对她有所爱慕。即使到了城市中,她也不会享受生活,而是精打细算每一项开支。施蛰存在这篇小说中,一改过去对都市繁华的描写,而集中描写婵阿姨的心理感受,把一个“乡下人进城”之后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京派与海派并非在任何方面都截然不同,无论是京派文人,还是海派文人,他们都不是绝对的只关注“乡下”或者“都市”。至少,两派在都市书写方面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状态,这种“异”与“同”共同构成并丰富了1930年代文学中的中国都市[2]。
京派和海派都有作品描写“乡下人进城”,但是,无论是在京派文人的笔下,还是在海派文人的笔下,他们都以“乡下人”的眼光打量着城市,善良却又无知、笨拙,并非想通过打拼而在城市立足,而是渴望将来能够衣锦还乡。
二、“城里人下乡”
京派和海派的作品在写“城里人下乡”的题材上也有一致之处。
(一)京派写“下乡”
沈从文的小说《三三》正如他的《边城》一样美丽,三三和翠翠心中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梦。三三和她的妈妈拥有一座人人羡慕的碾坊,三三在碾坊中长大,喜欢到屋后的小溪边和鱼、虾、鸡、鸭玩耍。到了该嫁人的年纪,她遇见了从城市中来乡下养病的“白脸”男子,“白脸”男子似乎很喜欢三三,他欣赏三三的美丽聪颖,跟管家说着碾坊主人的笑话,触动了三三朦胧的情思,但是三三执拗的性格却不愿经常见到他。三三看到一位“穿白袍戴白帽装扮古怪的女人”把一根“小小的管子塞到那‘白脸’男子口中去”,男子问“多少豆?”三三还从“白脸”男子那里得到了用瓶子装的糖,她还会在无聊的时候想象城里人的生活,甚至做梦都是梦到城市里。后来,三三终于答应要到寨子里去见见“白脸”男子和“戴白帽”的朋友,却意外得知“白脸”男子突然病逝的消息。三三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回忆失去的东西的名称,但却想不起来。
沈从文笔下的“白脸”男子虽然以“城里人”的身份参与乡村生活,但并没有把城市的虚伪造作和优越姿态等负面情感掺杂进来,他喜欢清静美丽的乡下,也喜欢在乡下孕育成长的三三。沈从文并没有把都市“白脸”男子刻画成令人厌烦的一类。
京派文人废名笔下也有一位从城市到乡下去的人,那便是莫须有先生。只因“乡下比城里贱得多”,他便下乡了。到了乡下的莫须有先生并不肯入乡随俗,而是用他那一派文人的语调对乡下的人和事评头论足,这在乡下人看来是多么的可笑。
(二)海派写“下乡”
海派文人施蛰存的小说《夜叉》也涉及“城里人下乡”的话题。“我”的朋友汴士明因为受到惊吓而神经错乱,“我”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因为祖母的丧葬,他离开上海来到杭州乡下亲戚家里小住,在一次游玩中,他看到一位白衣女子,诡异的是“就从这一瞥眼开始,一个闪着明亮的白光影子永远地舞动在我眼前”。回到住处,偶然发现附近山峰上曾经有过夜叉的传说,夜叉会化身美丽妇人引诱樵夫。晚饭后,他在林间散步时看见一棵大树旁边有一束白光,走近发现是一只白兔,但是再看一眼却变成了一位白衣妇人。于是,他觉得“这是一世纪来还未灭掉的夜叉,它变作女人,在庵外的小船中,它变作兔子,把我引诱到这里以后,又变作白衣妇人了。”出于对自己胆量和力气的自信,他开始跟踪这个夜叉,在跟踪的过程中,他甚至开始幻想与这个夜叉恋爱,以致“我的心骤然燃烧着一种荒诞的欲望”,最后他看到夜叉走进了一所坟屋,当他推开门,看到白衣女妖“蜷缩着一团,两手向前伸出,好像做着预备搏击的姿势”,他便决定先下手为强,扼死了这个女妖。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他忽然发现,这“女妖”竟是一个赶着去幽会的聋哑女人,并不是夜叉。因此,他的神经崩溃了,回到上海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的朋友从城市到乡下,他是个过分依赖文字的知识分子,他欣赏乡下的美景却又对乡下有着误解,他敏感多疑地把本来美好的一切都看成是可疑的对象,这正是城市中压抑的生活使他患上了神经衰弱症。
在京派和海派文人的作品中,“下乡”的城市人经常会说一些或者想一些有诗意却不实际的东西,认为乡下人的淳朴是迂腐,其实在乡下人的眼中,城里人才是最可笑的。
三、结语
沈从文和施蛰存所代表的2个文学流派,本来是存在巨大差异而论争不断的,但是,他们在“都市”和“乡土”“进城”和“下乡”的问题上都有着共同的文学指涉,并不是京派就扬“乡土”而抑“都市”,海派就颂“都市”而恶“乡土”。
对于“都市”,沈从文表达过自己的感受:“人多如蛆、杂声喧闹……雄身而雌声的人特别多,不祥之至。”他觉得“都市”的文明就意味着“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3]而施蛰存在大多数作品中虽然是描写“都市”的繁华热闹和文明的,但也多是从侧面指出“都市”的奢靡之风。实际上,较之施蛰存“海派”的其他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等,对于“都市”的浮躁、骚乱以及都市人扭曲变态的认知和描绘都毫不逊色。由此可见,无论京派还是海派,他们对于都市人病态的关注和发掘都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并渗透在其对“城里人下乡”的描述中,甚至执拗地认为乡间的淳朴、清新也难以治愈城里人的顽疾[4]。
京派和海派对于“都市”和“乡土”“进城”和“下乡”的默契,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在都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历史时期,出现都市病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用“乡土”淳朴、正直的思想去影响“都市”,也是文人们惯用的手法。他们在文字书写中饱含着对人性、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他们需要一个干净的“都市”。“乡土”是京派文人的家,“都市”是海派文人的家,“乡土”和“都市”共同构成了全人类的家。基于对家的美好憧憬,他们才能共同执笔描绘。
[1]潘旭科.想象、延续、残留、淡化:20世纪30年代京海派都市小说乡土性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4.
[2]李伟华.1930年代京海派小说的都市书写[D].郑州:郑州大学,2012.
[3]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 11卷[G].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86.
[4]林虹.“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J].河南社会科学,2010(5).
(编辑:文汝)
I209.99
A
1673-1999(2017)07-0074-03
王佳欢(1991—),女,郑州大学文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7-04-01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