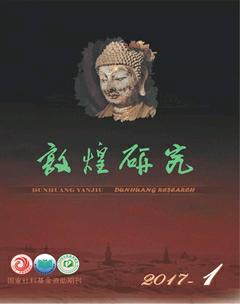敦煌民族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杨富学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14-02
敦煌(包括今瓜州县)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今敦煌地区现存的500余个洞窟中,除了汉人政权时代开凿的300余窟外,少数民族政权时代所开的洞窟也有170余个,约占洞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敦煌发现的60000件古代文献中,除汉文外,尚有吐蕃文写卷15000件左右,另有突厥文、吐火罗文、摩尼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献,此外还有用佉卢文、梵文、钵罗婆文(中古波斯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写成的文献。它们为我们认识历史上敦煌民族的社会活动、经济状况、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敦煌民族是敦煌学领域中内容复杂、研究难度较大的分支学科。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开启之后,西方学者就开始了对敦煌民族古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德国、英国、法国、芬兰、匈牙利、俄罗斯,对于敦煌民族古文字的解读成就卓著。最近几十年,美国、日本、土耳其奋起直追,大有迎头赶上甚或超越之势。
就突厥、回鹘民族古文字而言,学者们的关注开始于19世纪上半叶。早在1822年,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缪札(A.Rémusat)就曾预言如能解读这些突厥文碑文,这将对解决(该地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问题起巨大作用。正为此,许多学者都在致力于民族古文字的破解、识读工作。1893年12月15日,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Thomsen)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成功解读古代突厥卢尼文的成果。此后,许多国家的学者都投身于民族古文字的搜集、整理、转写、翻译和研究工作,刊布了大量的民族古文献研究成果,并很快为相关学科所利用,为丝绸之路研究,诸突厥语民族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史研究以及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促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没有哪一门学科能像突厥学这样多地受益于出土资料。
然而,反观我国,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在我国,1949年以前研究者不多,偶有论及者也都主要局限于利用汉籍史乘的記载来考证在敦煌活动过的古代诸族,如三苗、乌孙、月氏、匈奴等。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全面复兴,敦煌民族研究也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社会历史、古代文献、语言文字、宗教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尤以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我国不管是大陆地区还是台港澳学者,治“语”者多不通“史”、治“史”者多不通“语”,这是几十年来我国敦煌民族研究的通病。从事敦煌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就知识结构和素质而言,除要具备相关的史学知识和文献学知识外,还必须具备扎实的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知识,熟悉相关语言文字的史料。如学术界过去将莫高窟第464窟推定为元代,如果知道八思巴文创制于1269年,比西夏亡国晚半个世纪,就不会把第464窟推定在西夏。再如东千佛洞第2窟甬道入口左右壁皆有元代才传入中国的密教种子词,恐怕就要另外考虑该窟的时代了。国外学术界则不同,大凡从事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大多都是“语”、“史”兼通。我们应该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大力培养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才,进而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吐蕃、回鹘、粟特、西夏与于阗文文献本身的深入研究,同时还应充分利用这方面的成果,结合汉文史料的记载,对敦煌民族的社会、历史、地理、经济、文化、艺术、宗教、民族及东西文化交流等学科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
近期,以史金波先生为代表的团队在破读西夏文草书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这对西夏文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松井太等对敦煌回鹘文题记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日本学者武内绍人等对敦煌吐蕃文契约的研究也有重大收获;在回鹘文本研究方面,近期由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的7卷本《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对敦煌回鹘文文书的整理研究颇具国际视野。相对而言,国内回鹘文的年轻人才培养却令人担忧,年轻一代以研究古回鹘文为业者偏少,而且缺乏冯家昇、耿世民等老一代学者的古文化修养,学术研究单一化倾向明显。
综观我国学者对敦煌民族的研究里程,可以看出,最近20余年来国内学者对敦煌民族研究的成绩是巨大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许多过去一直模糊不清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但是,对敦煌民族的研究是不平衡的,目前主要偏重于吐蕃、粟特、回鹘与西夏,而对其他民族的研究就甚为薄弱。如裕固族起源于敦煌,但过去学术界很少有人进行研究。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裕固族族源的重新认识以及裕固族及其先民(主要指河西回鹘、蒙古豳王家族及元明时代形成的裕固族民族共同体)对敦煌文化贡献的研究,会成为热点问题之一。
在对敦煌民族的研究中,研究者多热衷于统治形式、王家世系、民族源流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等问题,但对经济、文化、宗教及政体等方面则很少有人问津。如敦煌晚期石窟的断代,其实就涉及民族历史文化问题,前提是要阐明回鹘、西夏、蒙古统治时期各民族文化的特点。例如,研究沙州回鹘石窟,就首先需要了解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吉木萨尔高昌回鹘佛寺遗址,而研究西夏石窟,那就要从银川山嘴沟石窟和武威下西沟岘石窟寻找坐标,元代石窟就要和鄂托克旗的阿尔寨石窟及时代明确的元代墓葬等进行比较。过去研究者将西夏石窟的坐标建立于敦煌,就容易出问题。因为文化传播总由中心向四周蔓延的。还有西夏文献的研究,目前很热火,但多为文献解读,而深入系统的研究却比较缺乏。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注意文献的时代,到底是西夏国时期还是元代的,常常交代不明,以至于西夏文献的研究者常常一遇到西夏文献,就将文物视作西夏。其实,元代西夏文更流行,正是元朝把西夏文推向了全国。
国内学者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有一种怪现象值得重视,即国内学界对敦煌吐蕃文文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流失到外国的那一部分上,却忽视国内藏品的研究。据有关人员的调查研究知,国内收藏的这种文献的数量并不比外国少,甚至还多于国外的收藏数,显然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这些原本“藏于深闺人未识”的古代文化遗产现在正在得到整理出版,但研究工作似乎还没有跟上。
除了吐蕃外,国内学人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利用过少。敦煌出土的与回鹘、粟特、西夏有关的文献,不管是汉文的,还是其他民族文字的,今天有不少都流失海外,因此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历史较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势必会走弯路,严重影响我们对敦煌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时还会做无益的重复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