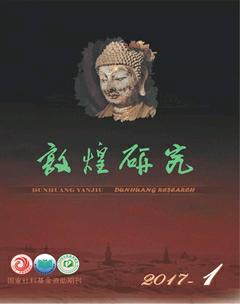初唐至盛唐时期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变的发展
八木春生 姚瑶



内容摘要:自贞观十六年(642)题记的第220窟开始,敦煌莫高窟中的唐代西方净土表现一改此前的画面中央绘树下说法图并在四周环绕千佛的形式,而利用大画面(整幅壁面)来表现西方净土景象的形式逐渐成为主流。唐前期第三期时,西方净土变的外围还增加了十六观和未生怨,来对《观无量寿经》进行详尽说明。其他变相图中也能看到这种对经典进行说明性表现的倾向,因此,可以说从唐前期第三期开始,变相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本文旨在探明自唐前期第二期出现的大画面西方净土变,其构图在第三、四期时分别发生了何种变化,并考察成因,以此深化对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诸窟的理解。
关键词: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西方净土变;粉本;十六观;弥勒经变
中图分类号:K87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35-19
序
自贞观十六年(642)题记的第220窟开始,敦煌莫高窟中的唐代西方净土表现一改此前的画面中央绘树下说法图并在四周环绕千佛的形式,而利用大画面(整幅壁面)来表现西方净土景象的形式逐渐成为主流。唐前期第三期时①,西方净土变的外围还增加了十六观和未生怨,来对《观无量寿经》进行详尽说明。其他变相图中也能看到这种对经典进行说明性表现的倾向,因此,可以说从唐前期第三期开始,变相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本文旨在探明自唐前期第二期时出现的大画面西方净土变,其构图在第三、四期时分别发生了何种变化,并考察成因,以此深化对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诸窟的理解。
第220窟南壁西方净土变大致由四个部分构成,由上至下依次是虚空段、宝池、宝地段,以及宝池两侧由楼阁所构成的宝楼部(图1)。这幅变相的一大特征是阿弥陀佛三尊位于宝池中。主尊阿弥陀佛内穿遮住左肩的内衣,外穿凉州式偏袒右肩式袈裟,双手作转法轮印,跏趺坐于宝池中的复瓣莲花座上,双足露出。主尊旁的菩萨立像两侧分别是跏趺坐于莲花上的观音和势至菩萨。阿弥陀佛三尊前方的莲花从根部衍生出9根莲茎,与其相连的每朵莲花上都有透明的莲蕾,其中画有或合掌、或倒立、或思惟状的童子,这被确认为九品往生的表现[1-2]。
上段虚空段里合计画有10铺阿弥陀佛来迎图,此外还有飞翔着的鼓和琵琶等乐器,其余部分填充着圆花纹样等。宝池两侧的宝楼部里有双层楼阁。此外,左右各有两尊体格略大的像,其中后方两尊是立于宝楼部与虚空段分界處的立佛像,前方两尊是坐于楼阁旁的菩萨像。宝地段和宝楼部之间架桥。宝地中央有2身跳胡旋舞的菩萨,两侧各有8身演奏着各种乐器的乐天,两端还绘有被认为是父子相会图的阿弥陀佛立像。
宝地前端设栏杆,下方铺四色砖,显出宝地是高于地表的。宝楼部也略高于宝地段。并且宝楼部与虚空段的分界处也铺着砖,这表明了虚空段还要更高一层。画面整体构图如同俯瞰的舞台一般。
一 唐前期第二期诸窟的西方净土变
根据樊锦诗和刘玉权的编年研究,唐前期第二期自贞观十六年(642)题记的第220窟开始,包括高宗、武则天时期(649—705)所造诸窟。其中,完工窟有21个,未完工窟有5个,还有3个窟是从前一期延续下来的[3]。这一时期的西方净土变不仅有大画面形式的,也有壁面中央形式的。
第334窟北壁的西方净土变不是大画面形式,上方和左右有千佛,下方为供养人像,近乎正方形的画面被唐草纹样带所包围(图2)。宝坛的前、后方皆有宝池,前者前方还有宝地。宝坛中央是作转法轮印、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的阿弥陀佛,高肉髻,腰部收细,着偏袒右肩式袈裟。莲花座上伸出4根宝幢,阿弥陀佛头部上方有与芒果系双树组合在一起的天盖。佛像两侧是游戏坐于圆形束腰莲花座上的观音和势至菩萨,头上同样有与芒果系双树相组合的天盖。这两尊菩萨像周围还各有6身菩萨像。观音和势至菩萨后方的宝池里飘出五色宝云,其上载有单层宝塔。这被认为与《观无量寿经》第二观水想观有关,在第220窟中也可见到[4]。宝坛前端铺四色砖(后方未见),其上设栏杆,但在中央处栏杆中断,从宝池中升起平台,这种形式同样可见于第220窟北壁药师净土变。平台上有两只凤凰。宝地中央凹陷,正中是跳胡旋舞的供养天,左右各有5身乐天。虚空间的两侧各有2铺阿弥陀佛三尊来迎图及飞翔着的鼓等乐器,将三尊像天盖间的空隙填满。
虽然第334窟北壁西方净土变中有从莲花座伸出4根宝幢这样忠实于《观无量寿经》的表现,但整体来看应是受到了第220窟南壁西方净土变的强烈影响。因此,第334窟西方净土变应晚于第220窟。但此窟的阿弥陀佛三尊像位于宝坛上而不是宝池中,这与第220窟有很大差异。而第220窟中仅见于北壁药师净土变的要素也被采用进来。另外,第340窟南壁西方净土变也与第334窟北壁相似,画面上方及左右环绕千佛,四周环绕连珠纹带。
二 唐前期第二期大画面西方净土变相图
A. 第341窟南壁
第341窟南壁西方净土变(图3a、3b)中也能看到第220窟南壁的强烈影响,而且由于使用了整幅壁面,在内容上要比上述第334窟北壁更加丰富。宝坛被栏杆围住,前、后方有宝池,与两侧的宝楼部间有水渠状宝池相连。宝坛的前部中央没有栏杆,由此处延伸出平台。前方宝池整体呈凸字形。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宝坛中央的有茎莲花座上,双足露出,作转法轮印,身着通肩式袈裟,腰部处的收细不明显(图4)。台座上伸出4根宝幢,其上还有天盖。与宝坛上的众多菩萨像一样,阿弥陀佛的脸部也经过后世的重修。主尊旁有两尊体格较大的观音和势至菩萨,游戏坐,头上有与芒果系树叶相组合的天盖,其上还有多层圆盖状宝幢。阿弥陀佛三尊旁密密麻麻地围绕着众多供养菩萨,其中还有从栏杆上探身者。
宝坛与两侧宝楼部虽然被水渠状宝池隔开,但彼此间有桥相连。宝楼部画出双层楼阁和阿弥陀佛立像,佛像头上有天盖和与其相连的圆盖状宝幢,身旁有众多的供养菩萨。宝坛后方的宝池位于高处,池中水流如瀑布般落下。前方宝池中,沿着宝坛边缘生出10朵大莲花,其上有9身安坐菩萨及1身童子(图5),菩萨大多朝向阿弥陀佛礼拜。宝池中央还有11身位于小莲花上的菩萨,但向阿弥陀佛回首者很少。共计11身的阿弥陀五尊像和三尊像及菩萨像乘于宝云上呈来迎状,此外还画有骑象菩萨三尊像(右)和骑狮菩萨三尊像(左)、飞天、乐器和宝云等。第220窟南壁西方净土变合计画出了10铺阿弥陀佛来迎图,东山健吾认为这与《观无量寿经》第十二观普想观的“见佛菩萨,满虚空中”有关[1]17。骑象菩萨三尊像和骑狮菩萨三尊像在第220窟北壁药师净土变中也可见到。宝地两侧各有1身坐于由芒果系树叶和圆盖状宝幢相组合的天盖下的菩萨像,头侧升起直达虚空间的宝云,其上载有被宝幢四面包围的单层建筑物(右),以及饰有3根宝幢的台座(左)。凹形宝地中央有2身跳胡旋舞的天人,两者身旁皆有伎乐天,除前述的坐于天盖下的菩萨像外还有单层建筑物(屋内有坐佛像,屋上有菩萨立像),这些要素也大多可见于第220窟西方净土变。但第341窟没有画出如何由宝地行进到宝坛和宝楼部。宝地两侧设台阶,由此可以下到宝池,有菩萨站在此处眺望宝池。虽然宝地与宝池之间大部分被栏杆隔开,但跳胡旋舞的天人附近及画面最前方没有栏杆。
和第334窟北壁一样(宝坛周围配有宝池),第341窟南壁西方净土变也从第220窟西方净土变和药师净土变中吸取了很多要素。但细节处不尽相同,例如没有用化生菩萨来表现九品往生,宝地段和宝楼部不相连等。但画面越向后延伸越高,采用了在略高于观者所立的水平位置处展开情景的舞台式构图,这无疑是在第220窟南壁西方净土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阿弥陀佛和菩萨数量的增加也可被认为是发展形态的一种表现。
B. 第329窟南壁
从第331窟北壁、第329窟南壁(图6)等西方净土变中可以看到,来自第220窟的影响逐渐减弱。它们与第220窟南壁和第341窟南壁最大的区别在于,宝坛上方造出了被宝池环绕的岛,并且岛上画有众多建筑物。此处以第329窟为例来进行说明。画面整体被连珠纹带包围。水渠状的宝池将画面分成上、中、下三段,宝池中畅游着水鸟。中段中央的宝坛上设莲花座,阿弥陀佛跏趺坐于其上,双足露出,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手指张开抚于膝上,遮住左肩的内衣上另有一层凉州式偏袒右肩式袈裟。佛像周围有8身菩萨像,除两尊胁侍菩萨立像外,其余皆是呈思惟状的菩萨坐像。宝坛上铺满饰有圆花纹样的宝砖。阿弥陀佛周围有4根宝幢,头上还有与芒果系树叶相组合的天盖。宝坛的前端中央伸出平台,栏杆也随之延伸,平台上有相对跪坐的供养菩萨。两侧宝坛如浮岛一般,与中央宝坛间有水渠状宝池,三个宝坛由桥相连接。右侧宝坛的天盖下有并腿坐于籐座上的菩萨像,使人联想到隋第二期和唐前期第一期诸窟及第57窟等的菩萨像,左侧宝坛的天盖下是游戏坐于莲花座上的菩萨像。此外,两侧宝坛上还各有1身朝向阿弥陀佛而立的菩萨,其他的菩萨或安坐,或呈交谈状。坐于天盖下的菩萨像应是观音和势至菩萨,它们所处宝坛的后部各架有一座桥,连接了上段的楼阁所在的陆地。
上段也和中段一样,形成了三个岛,中央岛仅可以通过左右两侧岛到达,与阿弥陀佛所处中央宝坛之间不直接相连。为了使第220窟南壁的阿弥陀佛天盖上部的建筑物独立出来,阿弥陀佛的头上必须得有一个岛,而它与原本位于宝坛两侧的宝楼部相结合且全部被配置在上方的结果,便在上段形成了三个岛。因此整个上段应被看作是宝楼部。中央岛上建有双层主楼,两侧还有辅楼,其中有菩萨像等。左右岛的靠外一侧有双层楼阁,另一侧是坐于与芒果系树叶相组合的天盖下的阿弥陀佛,身旁还有两尊菩萨立像,此外还有与宝树观相关的内部画有小楼阁的树木。两侧岛与后方虚空间之间没有栏杆,其对岸也未明确地表现出宝池。在栏杆的终点处宝池表现也随之消失,上方是画有宝云、飞天和乐器的狭长的虚空空间,因此宝池看起来像是在栏杆终点处突然完结了一般。虽然在此幅壁画的宝池中看不到湍急水流的表现,但在同窟北壁弥勒经变及第331窟北壁西方净土变中可以见到,且这两幅变相图上段的三个岛后方还有水渠状宝池,前者的画面深处还画出了砖。
下段的凹形宝地被栏杆全部围住,不同于第220窟南壁和第341窟南壁的中央处栏杆中断的表现。凹陷处栏杆的两端各立1根由宝相花堆叠而成的宝幢。和第341窟南壁一样,没有明确地画出如何由宝地行进至中段宝坛。宝地中央有跳胡旋舞的天人及乐天,还有在第220窟可见但第341窟无的所谓的父子相会图(但与第220窟相异的是,此处的佛像似乎坐于藤座状的东西上)。此外还画出双层楼阁。画面最前方的栏杆下有砖,显得高于观者所处位置。
C. 第321窟北壁、第335窟南壁、第71窟北壁
第321窟北壁及第71窟北壁的西方净土变等展示了从第220窟南壁、第334窟北壁向第329窟南壁发展的过程。和第341窟南壁一样,第321窟北壁的宝坛上方没有由宝楼部转化而成的上段(三个岛)(图7)。阿弥陀佛所处的宝坛被宝池所包围,但宝坛后方的水渠状宝池不分明。作转法轮印的阿弥陀佛头部上方有与芒果系树叶相组合的天盖,天盖后的宝云上载有双层楼阁,上层有坐佛,下层有倚坐佛,周围立4根宝幢。宽广的虚空间内还各有2朵仅带楼阁或3根宝幢的宝云,以及4铺阿弥陀佛三尊来迎图和飞天、乐器等。两侧宝坛与中央宝坛间架桥,与芒果系树叶相组合的天盖下有阿弥陀佛立像。天盖像被强风吹起一般张开(类似天盖也可见于第220窟北壁药师净土变)。上方有由圆盖组成的宝幢,内部还有几座楼阁。而原本在第220窟中与阿弥陀佛立像同处于宝楼部的楼阁,在此处被画于宝坛与宝地间的宝池中,这是第341窟南壁所未见的新形式。下段宝地的中央凹陷处栏杆没有中断,与第329窟南壁同。宝池中水流湍急,内有未敷莲花、莲花化生、迦陵频伽和水鸟等。宝坛中央平台边的莲花化生旁有长方形铭文,应是表现九品往生的。第335窟的窟门上有垂拱二年(686)题记,南壁西方净土变的构图与第321窟北壁几乎相同。但第335窟南壁中,宝坛后方宝池的对岸不仅有砖,而且砖上还有栏杆将宝池与虚空间隔开(图8)。因此第335窟南壁应晚于第341窟南壁(宝坛后方的宝池中似乎有什么)和第321窟北壁(虽构图相同,但宝楼位于宝池中)。
另一方面,第71窟北壁(图9)中,作转法轮印的阿弥陀佛跏趺坐于宝坛中央的莲花座上,右足露出。这幅图中出现了由三个岛所构成的上段,且上段后方还画出了水渠状宝池,由此可看出它比第329窟更加强调了岛的存在。但虚空空间非常狭小,其内画有4铺阿弥陀佛三尊来迎图和飞翔着的乐器、飞天等。上段中央岛上的双层楼阁与阿弥陀佛天盖间的位置关系不眀,相连的两侧岛上皆有阿弥陀佛立像和两尊菩萨立像,但无楼阁。遗憾的是,宝地部分脱落,仅能辨认出下段画有宝池,但整体构图不明,或许与第329窟南壁西方净土变类似。有研究指出,与此窟拥有几乎相同构图的第331窟是698年以前所营造的[5],再加上前述的第335窟有686年题记,由此可以推测第二期西方净土变相图的完成或许是在7世纪90年代前半期。另外,在第335窟与第329窟、第331窟之间,还有像第205窟北壁那样的,宝坛后方寶池中央陆地上的楼阁与两侧宝池里的楼阁由空中回廊相联结的构图。第二期西方净土变的发展过程如表1所示。
三 唐前期第三期诸窟的西方净土变相图
A. 无外缘部的西方净土变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三期相当于中宗、睿宗、玄宗前期开元时期(705—749)[3]171,亦可称为盛唐前期。樊锦诗和刘玉权将其又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第103窟、第215窟、第217窟等属于前者,第66窟、第445窟、第446窟等属于后者。第一类的营造时间被认为早于开元十四年(726)题记的第41窟[3]171。这一时期的完工窟有34个,未完工窟有10个,从前期延续下来的有5个[3]159。第三期西方净土变中,既有继承了第二期形式的,也有在画面左右及下部(外缘部)画出十六观和未生怨的,后者合计有20余例[6]。
a. 第445窟南壁
第445窟南壁西方净土变(图10)继承了第二期的形式。画面被分成了上、中、下三段,但上段未被宝池划分成三个岛。上段中央的单层建筑物(其中似乎有立佛像和菩萨立像)与中央宝坛的阿弥陀佛的天盖之间位置关系不明,这也见于第220窟南壁和第71窟北壁。宝坛上的阿弥陀佛在遮住左肩的内衣之上还穿有一层凉州式偏袒右肩袈裟,作转法轮印,结跏趺坐于饰有宝幢的莲花座上,仅右足露出。肉髻与地发间饰有珠子[6]56,这种形式未曾见于第二期诸窟。阿弥陀佛周围遍坐菩萨像,与第二期第341窟南壁共通。两侧宝坛上分别坐有观音和势至菩萨,与中央宝坛之间架桥。宝池中涌出的宝云上载有饰4根宝幢的台座,阿弥陀佛三尊(8身)乘着宝云飞腾在虚空空间中,这些皆是自第220窟南壁开始且被第341窟南壁等所继承了下来的形式。宝坛前部的形状较复杂,中央部分一度向外凸出再向内凹陷形成平台,两侧又继续凸出(现不存)。下段宝地和中段的三个宝坛间由四座桥相连,临宝池一侧没有栏杆。左侧两座桥左边的地方还有建筑物(右侧破损)。宝地的中央部分凹陷,地面很窄,因此跳胡旋舞的天人被安置在中央宝坛的平台上,乐天则位于斜后方的顶部饰圆盖形宝幢的建筑物里。同样的建筑物在第341窟南壁也能见到。宝地的两端宽敞,画有所谓的父子相会图。前方宝池中央的莲花化生旁有长方形铭文,应该是表现九品往生的。但与初唐时期不同的是,此处的宝池中没有画出湍急的水流。
b. 第124窟北壁
这时期还有未受到初唐时期西方净土变影响的例子,例如第124窟北壁(图11)。虽然变色严重,但可以看出画面最前方栏杆的中央部分向前方延伸,由此可知阿弥陀佛像及其他诸像皆位于宝坛上。未看到宝池,诸像背后似乎也有栏杆。或许因为是小窟,虚空间中仅能看到2铺乘着宝云的阿弥陀佛三尊像及乐器,此外也没有楼阁。另外,还出现了作转法轮印的阿弥陀佛从眉间白毫射出三道像光一样的细线,跏趺坐于八角形台座上等新形式,且台座旁无宝幢这一点也几乎不见于第二期诸窟。两侧的游戏坐于天盖下的菩萨像上分别画有化佛和宝瓶?譹?訛[6]55。
B. 有外缘部的西方净土变
a. 第217窟北壁
关于第217窟的营造时间有诸多说法,目前尚无定论。段文杰认为是在神龙年间(705—706)?譺?訛[7],史苇湘认为是神龙至景云年间(705—711)?譻?訛[8],贺世哲认为是神龙年间以前的初唐末期[5]518。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则认为是景云年间(710—711)?譼?訛[9]。还有诸多研究认为它是初唐和盛唐的分界点,张景峰指出,第217窟西壁下部供养人像之下还有一层壁画,这层壁画上也绘有供养人像?譽?訛。
在有十六观和未生怨图外缘部的西方净土变中,未见到像唐前期第二期诸窟(第329窟南壁等690年代后半期的几个窟)那样的关于宝池表现的复杂构图。第217窟北壁及第215窟北壁等的画面虽然被分为上、中、下三段,但和第445窟一样,上段未被宝池隔断形成三个岛。第217窟北壁(图12)中,主楼和侧楼由回廊所连接的建筑物,以及下部如石墙般小台的精妙建筑物等全部集中在上段。而原本位于宝池左右的宝楼部消失,这应是受到了第329窟的影响。上段还能见到原位于宝楼部的阿弥陀佛立像。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与主楼由回廊相连的)侧楼上部与左侧建筑物的上部(下部如石墙般小台的建筑物以左),两者在细节处一致(图13)。
初唐窟中虽然也有例如第321窟北壁那样的杰出楼阁表现,但却不像第217窟北壁这般,同一壁面内的楼阁连细节处也一致。第三期诸窟中有几例可以被认为是使用了与第217窟北壁相同的建筑物粉本。根据山崎淑子的研究,从敦煌莫高窟唐前期第二期第220窟的菩萨像头部使用了相同模子开始,到第三期时,出现了像第217窟和第103窟这样不同窟之间也使用同样模子的情况。她还指出,在建筑物表现方面,第217窟北壁与第123窟南壁的楼阁可能局部使用了同样的粉本[10]。而第103窟北壁(图14b)和第66窟北壁西方净土变(图15b)中,也能看到使用了与第217窟北壁相同局部粉本的楼阁。虽然无法说是使用了模子,但像这样的屋顶前方右侧的屋檐向上翻折等细节处甚至也一致的例子,不见于第二期诸窟。而且,可以看出第103窟北壁与第66窟北壁在更大范围中使用了粉本,两者的主楼和侧楼上部几乎一致。
另外,不同于第二期的阿弥陀佛坐于有茎莲花上,第217窟北壁阿弥陀佛坐在高椅背的束腰莲花座上,与第103窟北壁、第66窟北壁及前文所举的第124窟北壁的西方净土变相同,是第三期才出现的变化。
b. 第103窟北壁(图14a)、第66窟北壁(图15a)
宝池在整体画面中所占的比例减少,是第三期西方净土变的特征之一。第217窟北壁也略能看到这种倾向,但第103窟北壁和第66窟北壁更为明显。虽然宝池依然存在,但表现被减弱,画面上、中、下三段的区分不明显。此外,宝坛上的阿弥陀佛与宝地间的距离变短。第66窟北壁,水渠状宝池似乎位于阿弥陀佛的背后极近的地方,膝下附近可以窥到身后的宝池。宝坛与上段宝楼部之间仅画出一点宝池,因此楼阁看起来像是全都建在宝坛上一样。第103窟北壁中也是,仅在左侧大菩萨坐像的左侧、右侧大菩萨坐像的右侧,以及宝坛和宝地之间画出些许宝池,所以乍一看像是所有楼阁都位于宝坛上。与受第二期影响的第217窟北壁不同,第103窟北壁和第66窟北壁西方净土变应是受到了第124窟北壁的影响,因为它们也像第124窟那样,从阿弥陀佛的肉髻与地发相连处的珠子中散发出10朵(第66窟有9朵)载有坐佛像的飞腾宝云(图16、图11)。《观无量寿经》说道,释迦从白毫中射出光普照十方无量世界,因此有研究认为这是释迦佛[6]117。在第217窟北壁的未生怨图“释迦耆阇崛山说法图”中也能看到从释迦的头上涌出10朵载有小佛像的宝云的图像。但另一方面,第四期的第171窟北壁西方净土变右侧的十六观中,第九观和第十观的画面分别是佛像头上8朵载有坐佛像的宝云及菩萨头上6朵载有坐佛像的宝云。大西磨希子认为前者与第九观真身想经文的“于圆光中,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后者与第十观的观音菩萨像“眉间毫相备七宝色,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一一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有关[4]105。若是如此的话,肉髻和地发相连处涌出的宝云及其上所载的化佛便未必是与释迦有关的图像。《大阿弥陀经》中(《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坛过度人道经》,《大正大藏经》,卷363)说道“阿弥陀佛顶中光明所焰照。千万佛国……”因此西方净土变相图中阿弥陀佛头上所涌出的宝云也可以看作是光的表现。但其上若有10身化佛的话,也有可能是表现了十方诸佛[6]152,或许可以考虑为释迦与阿弥陀的神格被融合到了一起。第220窟南壁等唐前期第二期诸窟中的虚空间仅画出了阿弥陀佛来迎图,而进入第三期后,采用了从佛的肉髻与地发相连處散发出宝云来表现光与十方诸佛的图像。另外,第66窟北壁的虚空间合计画出8铺乘着宝云飞腾的阿弥陀佛像及三尊像,但这未见于第103窟北壁。
四 唐前期第四期西方净土变
A. 第171窟
玄宗天宝时期至肃宗、代宗时期的第四期第一类(天宝-代宗初期)?譹?訛[3]181诸窟中,第171窟的西方净土变最为人所熟知。除正壁以外,此窟的南北壁(图17、图18)及东壁皆画西方净土变,且南北壁的构图几乎一致,十六观和未生怨的配置也彼此对应。东壁有窟门,宝池的形状不同于南北壁,余下部分皆相同。十六观和未生怨“三壁的图像是共通的”,由此“可以知道是根据同一粉本所画出的”[4]101。西方净土变分上、中、下三段,但与第66窟及第103窟相同,上、中段间的宝池与宝坛前方的宝池之间没有连接二者的竖着的水渠状宝池。上段画有众多楼阁,还有空中回廊。中段阿弥陀佛头部上方的天盖与上段中央的两栋前后并置的楼阁之间界限不明,这与大多数第三期窟相同。上段与中段宝坛间架有连接二者的寬桥。阿弥陀佛肉髻与地发间的珠子中涌现出2朵坐有化佛的宝云。此外,沿着天盖还画有8身化佛,这应该也是从阿弥陀佛散发出来的。观音和势至菩萨也分别从额头处涌现出5朵宝云,每朵上皆有三尊像。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乘着宝云的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三尊像。观音和势至菩萨的斜前方有双层楼阁。宝坛上有众多菩萨像。上段与中段间虽有宝池,但因架有宽桥,所以几乎看不到宝池。和第445窟南壁有诸多类似之处,例如宝坛前部反复凹凸,除左右两端的立佛像(父子相会图)以外的宝地部分极端狭窄,仅表现出一列砖,宝坛前方的宝池里有包裹于莲蕾内的童子等九品往生图像。但不同的是,第171窟中,狭窄宝地的中央向上方凸起,用栏杆围出小宝池,里面也画出一部分九品往生图像。另外,由宝地向宝坛行进的方法不明确。
主尊阿弥陀佛身着凉州式偏袒右肩式袈裟,作转法轮印,结跏趺坐且双足露出。这种形式很常见,但初唐窟中袈裟未从双膝垂下形成悬裳座。这尊佛像的细节部分与第66窟北壁像相似(图19、图20),两者的仰莲瓣形式也共通,因此无疑是使用了同一粉本。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幅西方净土变的整体构图及楼阁形式等与第66窟的没有共通之处,因此应该仅主尊阿弥陀佛使用了粉本。虽然与第217窟北壁所使用的粉本部分不同,但第171窟也与第66窟北壁西方净土变有关系。另外,现在被编在第四期第一类的第44窟北壁西方净土变的主尊,虽不如第171窟的相似度高,但应也是使用了与第66窟北壁阿弥陀佛坐像相同的粉本。并且,第44窟北壁西方净土变和前述第124窟北壁有着类似特征,其形状特殊的宝地也与第171窟有关联,由此可知第44窟北壁西方净土变确实是第四期初的作品。
B. 第172窟
同属于第四期第一类的第172窟中,南北壁西方净土变的构图也几乎相同,两者的十六观和未生怨也呈对应状配置。上段中央前后并置的两栋楼阁和阿弥陀佛(即宝坛)之间建有大殿,上段的两栋主楼和左右的翼楼由回廊相连呈コ形,宝坛的三面被建筑物包围,这些形式南北壁是共通的。比起上段与中段由宽桥相连的第171窟,第172窟显得更加一体化。南北壁的建筑物形式几乎一致,且两者的宝地中央皆朝向画面外架有桥,使观者觉得可以进入画面中笔直地参拜于阿弥陀佛前,由这些匠心独运的表现可以看出南北壁使用了同样的粉本,画面的基本构图也是随这些粉本而决定的。但此外还有很多部分是由画工任意裁定的,所以南北壁并不完全相同。具体说来的话,北壁阿弥陀佛结转法轮印,身着偏袒右肩式袈裟(图21),而南壁佛像则右手上举于胸前,左手置于膝上,身着双层袈裟,仅外层是偏袒右肩式袈裟,且袈裟的一端被钩纽吊于左肩下方(图22)。北壁阿弥陀佛头上涌出3身坐于宝云上的阿弥陀佛三尊像,相隔不远处还有2身乘着宝云朝画面外飞翔的阿弥陀佛三尊像,以及向下方飞去的4身阿弥陀佛三尊来迎图。而南壁阿弥陀佛则是从肉髻和地发的交界处涌出3身(2身阿弥陀三尊像,1身五尊像),两侧各3身,共计9身的乘着宝云的阿弥陀三尊像和五尊像。与第171窟一样,宝地被竖着的水渠状宝池分成三块。但第172窟位于两侧宝地上的所谓的父子相会图中,主尊是坐像而不是立像。另外,北壁的宝坛和宝地间还有三个小岛,中央岛上有跳胡旋舞的天人。南壁中则没有这样的岛,天人在中央宝地上跳胡旋舞。而且北壁中,宝坛与其后方建有大殿的部分间可以看到段差,大殿部分与上段之间也能看到段差,且铺有宝砖,即画面越往后方越高。北壁上段左右翼廊的柱子间隙里能窥到水的表现,由此可知上段的后方还有宝池。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北壁阿弥陀佛周围楼阁的外侧,即画面上方的左右两端能看到大河和绿地。
C. 第320窟北壁
第320窟北壁的十六观(图23)中有宝池里的球体和插有莲花的宝瓶等与《观无量寿经》关系不明的特殊图像,因此有研究指出,它与第172窟南北壁的十六观“可以看做是同系的”(后述)[4]130。第320窟北壁虽是从第三期延续下来的,但属于第二类,完成时期略晚[3]181。从第320窟北壁西方净土变的构图,以及所谓的父子相会图位于左右两个宝地,跳胡旋舞的天人在中央宝地上等细节来看的话,与第172窟特别是南壁西方净土变有着很近的关系。因此这两个窟的西方净土变或是基于同样的粉本而画出的,抑或是第320窟北壁的画工模仿了第172窟南壁。但第320窟北壁中,虽然建筑物呈コ形围在宝坛三面,且上段有主楼,但其后方没有并置的楼阁,也没有连接中段宝坛的桥与大殿。两者的建筑物虽然形式类似,但细节方面有所差异。第320窟北壁的阿弥陀佛像头上涌出5朵宝云,中央3朵上载有三尊像,左右2朵载有楼阁。两侧飞腾着的三尊像减少至2身。构图被简化,并且出现了图像混乱,例如宝坛两侧的楼阁中不是阿弥陀佛而是安坐思惟菩萨等。
和第320窟一样,第45窟也被认为是第三期未完工第四期继续营造的洞窟?譹?訛[3]181。此窟的北壁西方净土变中(图24),宝坛周围的宝池变得更加复杂曲折。但这种宝坛被水渠状宝池环绕的形式应可以看作是第217窟等第三期初期的变形。上段的大殿似乎是前后两幢并置,但仔细辨认的话,回廊向左右两侧伸展出,宝池也随之蜿蜒延伸至两侧的楼阁。这与第二期第341窟弥勒经变中的兜率天表现类似。阿弥陀佛头部涌出4朵宝云,2朵载有三尊像,另2朵仅画五色云。此外还有乘着宝云下降的三尊像。虽然与第172窟南北壁及第320窟北壁的粉本没有关系,但应或多或少地受到其影响。
D. 第148窟东壁
第四期末的第148窟东壁南侧的西方净土变(图25)约在大历十一年(776)左右,与第172窟北壁相似。阿弥陀佛的三面环绕有楼阁和回廊,宝坛与宝地间有三个小岛,中央岛上有跳胡旋舞的天人,左右岛上有乐天。另外,宝地被分隔成两块,皆画有阿弥陀佛呈坐姿的所谓的父子相会图。和第320窟北壁一样,可能使用了与第172窟北壁相同的粉本,或是基于其而画出。位于虚空空间的从阿弥陀佛周围涌出的宝云上载有单层塔,这在第二期诸窟中常见,但第三期窟中很少见。从朝向画面外飞翔的三尊像上也可以看到第172窟北壁的影响。乘宝云下降的阿弥陀佛三尊像中的1身有“无量寿佛”题记。另外,上段和宝坛之间无桥,同第320窟北壁。但第172窟南北壁的建于宝坛与上段间的大殿,在第148窟东壁里被移到了上段,而原本位于上段主楼后方的低楼则演变成左右两侧的小建筑物。宝地仅由描画了父子相会图的两座岛组成,与跳胡旋舞的天人和乐天所在的小岛之间没有桥相连,因此,虽然画面最前方画出了进入画面的平台,但观者无法沿着道路到达宝坛。宝地附近宝池中的莲花化生旁有长方形题榜,写有“上品上生”等题记。中村兴二对此说道“三辈的表现完全消失,或许是想要表现九品或者更高的等级。而向舞乐段上升的往生者可能是最高等级吧”[11]。第172窟南北壁和第320窟北壁里虽有化生但无长方形题榜。而第二期的第321窟北壁和第三期的无外缘部的第445窟南壁及第四期的第171窟中能看到长方形题榜。
五 唐前期第三、四期诸窟西方
净土变的构图以及与外缘部的关系
A. 十六观图像
根据大西磨希子的研究,第217窟北壁左侧外缘部的十六观图中(右侧是未生怨图)画出了十三观,被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场景,其中没有第七观,而与第二观有关的内容则多次出现,有诸多图像上的混乱[4]117-121。施萍婷也指出右侧未生怨图中有内容不明处[6]126。此外第103窟北壁和第215窟北壁等中也可见到十六观图像的混乱,其中第103窟北壁重复出现了宝池、佛、菩萨的图像,这与第217窟北壁相同[4]313-314。而第66窟北壁中,左右两侧的外缘部被分成两竖列,分别画出十六观和未生怨,前者被划分为一个个独立场景,基本遵循了经典内容[4]111。虽然第171窟和第45窟北壁、第148窟东壁等的十六观皆是依照经典内容而画,但第45窟北壁和第148窟东壁场景被简化,这相异于第66窟北壁和第171窟等。此外,如前文所述,第172窟南北壁和第320窟北壁皆含有無法从《观无量寿经》中找到依据的特殊图像(宝池中的球体和插有莲花的宝瓶),由此可以认为这两窟使用了不同于上述几窟的十六观粉本[4]112,123-130。
B. 十六观表现和西方净土变
综合唐前期第三、四期西方净土变构图上的变迁以及十六观图像与《观无量寿经》的关系来看的话,总结如下:从第三期初期的第217窟北壁开始,十六观与未生怨被配置在西方净土变外缘部,但此处的十六观图像与经典内容不一致。第103窟北壁的十六观图中不仅可以看到与第217窟相同的配置顺序错误及图像重复等混乱,而且其西方净土变本身还有几处楼阁使用了与第217窟北壁相同的粉本,由此可以看出这两窟之间的联系。但与第103窟北壁使用了相同建筑物粉本,且同样采用了从佛像肉髻与地发间的珠子中涌出宝云的新题材的第66窟北壁中,十六观图像遵循了经典内容。第66窟和使用了与第66窟北壁同样阿弥陀佛粉本的第四期第171窟,两窟不仅十六观图像与经典内容几乎一致,而且还有其他诸多共通点[4]111。
第171窟南北壁的西方净土变构图几乎相同,由此可知它们使用了整幅画面的粉本。第四期前期时,正确表现了经典内容的十六观粉本与由第三期西方净土变中的几部分所构成的“整幅画面的粉本”组合到了一起。第172窟南北壁也可以看出是使用了“整幅画面的粉本”,而且第四期后半的第320窟北壁以及同期末期的第148窟东壁也使用了与第172窟相同的“整幅画面的粉本”,或是基于第172窟而画出的。第172窟南北壁及第320窟北壁的十六观图中出现了无法从经典中找到出处的特殊图像,这样的十六观表现区别于其他窟所属的系统。但第148窟东壁的十六观图像与经典内容几乎一致。
与唐前期第二期西方净土变中可以看到构图上的自立性发展不同,第三期的显著特征是使用了粉本(虽然只是一部分)?譹?訛。而到第四期时,出现了将此前的几个粉本组合在一起的“整幅画面的粉本”,第171窟的壁面便是基于这样的粉本而画出的。第172窟中流入了其他系统的“整幅画面的粉本”,除基本构图外细节方面由画工任意裁定,直到第四期末期时还能看到受其强烈影响的壁画。第三期初期时,西方净土变粉本的使用系统和十六观图粉本的使用系统未必一致,而到了第四期后期时,特定系统的西方净土变粉本和十六观粉本开始成组出现。除第320窟外,第201窟南北壁也使用了与第172窟相同的粉本抑或是模仿了它,并且从南壁十六观图的宝池中的球体及插着莲花的宝瓶等处也可确认这一事实。以上所述如表2所示。
六 西方净土变构图以外的特征
A. 与西方净土变相组合的变相图
唐前期第二期诸窟中,与西方净土变相组合的弥勒经变有:第71窟南壁、第78窟北壁、第329窟北壁、第331窟南壁和第341窟北壁。与其相组合的其他变相图有:第220窟北壁的药师净土变、第321窟南壁的宝雨经变或十轮经变、第335窟北壁的维摩诘经变。另外,第211窟的南北壁都是西方净土变。第334窟南壁、第340窟北壁及第372窟北壁是被千佛环绕的净土变或说法图,王惠民认为这些皆为弥勒三会图[12]。若是如此的话,这三窟也都是西方净土变与弥勒经变的组合。
第三期时,与西方净土变相组合的弥勒经变有:第116窟北壁、第124窟南壁、第208窟北壁、第215窟南壁、第218窟北壁、第445窟北壁、第446窟北壁等。其中,第124窟南壁和第445窟南壁、第446窟南壁的西方净土变没有外缘部,王惠民认为第124窟应属于初唐武周时期(第二期)[12]42。第103窟南壁是法华经变,第120窟北壁和第122窟南壁是说法图,第217窟南壁是法华经变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譹?訛。第66窟南北壁皆是西方净土变,但南壁与第220窟南壁一样,阿弥陀佛位于宝池之中。
第四期时,第113窟北壁是弥勒经变,第44窟人字披南壁是中唐时代的西方净土变,第45窟南壁是观音经变,第148窟东壁北侧是药师净土变,第194窟南壁是维摩诘经变,第320窟南壁是千佛与释迦说法图。第171窟及第172窟南北壁皆为西方净土变。
从第三期开始,无外缘部西方净土变的数量急剧减少,而有外缘部西方净土变与弥勒经变之外的其他变相组合的例子有增加的趋势。另外,第四期出现了像第171窟这样的不仅南北壁而且东壁也画出了有外缘部西方净土变的例子?譺?訛。第三、四期中,很多窟南北壁不存或是被中唐时期的壁画或千佛所覆盖。因此虽不能断言,但西方净土变与弥勒经变组合的比例在总体中可能有所下降[13]。
B. 第三期开始诸变相图的特征
第二期第341窟北壁、第329窟北壁及第331窟南壁的弥勒经变与各窟的西方净土变有着极为相似的构图(图26)。进入第三期后,第445窟北壁弥勒经变中宝池消失,但与此同时在初会场景之前增加了推倒七宝幢的图,并在其左右详细表现出了国王和八万四千大臣剃发等场景[14](图27)。此外,还画出树上生衣、一种七收、迦叶山中禅定等新题材。第二期第220窟北壁药师净土变和东壁维摩诘经变、第321窟南壁宝雨经(十轮经?)变等中已经可以看到对经典内容进行说明的表现。而从第三期开始,弥勒经变等各种变相图中故事画增多,内容变得丰富。此外,还出现了像第323窟(被编入第二期或第三期)?譹?訛那样的画有“张骞出使西域图”和“佛图澄听铃声断凶吉图”等佛教史迹故事画的窟。由此不难看出,唐前期第二期的南北壁变相图主要描绘了人们理想的往生之处的样子[15],而进入第三期后,变相图则侧重于对经典内容和佛教历史进行详细的说明。
C. 粉本的使用及对经典的理解
以第220窟南壁为代表的唐前期第二期无外缘部西方净土变中,虽然也画出了与九品往生相关的化生童子这样受《观无量寿经》影响的图像,但到第三期时,由于出现了十六观与未生怨图的外缘部,西方净土变本身对于《观无量寿经》内容的反映变得不再显著。此外,画面上方像瀑布般落下的宝池表现也消失。第二期至第三期的这种图像上的变化不是自立性发展的结果,应该考虑是受西安传入的新情况影响所致。同时,粉本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唐前期第四期初时还出现了使用整幅画面粉本的窟。第四期第171窟使用了与第三期第66窟同样的阿弥陀佛粉本,由此可知第四期与第三期是有所关联的。但第172窟的西方净土变与第171窟之间看不到很强的联系。第172窟以后,第四期后期的一些窟也采用了与它相同的粉本(或是基于第172窟南北壁的壁画而画出),所以在几个窟中出现了基本构图几乎一致的西方净土变。可能正是在此时,至此为止相互独立的西方净土变粉本和十六观粉本开始成组出现。但这些十六观图中出现了无法用《观无量寿经》解释的内容,并不是基于对经典正确理解后的表现。另外,第172窟北壁楼阁的外侧不知为何画出了绿地(图28)。
虽不知其含意,但楼阁中飞出的飞天将楼阁与绿地联结到了一起,因此绿地应该也与西方净土有着某种关联。而前文中也曾提到,第172窟上段左右翼廊的柱子间隙里可看到水的表现,这是大河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楼阁外侧的大河与楼阁内部的宝池也是相连的。因为这与十六观中初观的情景相似,或许可以理解为是表现了地上世界。若是如此的话,虽然西方净土被像城壁一样的楼阁和回廊包围住?譹?訛,但或许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它应该与大地相毗连,而不是遥不可及地存在。第172窟南北壁中,宝地的最下部向画面外侧架桥,观者通过它与西方净土变相连,可以直接参拜于阿弥陀佛前。虽然这也很难从经典中找到出处,但显示了西方净土是对观者开放的,而不是高不可攀的[16]。因此,使用了整幅画面粉本且对十六观有着正确理解的第171窟可以看做是西方净土变的完成形态,但从对后世的影响这一角度来看的话,第172窟西方净土变应该获得最高的评价。
结 语
大历十一年(776)题记第148窟东壁西方净土变的大部分构图与第172窟南北壁及第320窟北壁几乎一致。但如前文所述,第172窟与第320窟的十六观系统相异于其他窟,而第148窟的十六观与第171窟等一样,符合《观无量寿经》的顺序及内容。与此相对应的东壁门口北侧的药师净土变有着和西方净土变相似的构图,且外缘部还配有十二大愿和九横死,这在中唐之后也成为定式[17]。而且南壁上部的弥勒经变中,上部画弥勒上生经变,中部和下部画弥勒三会、弥勒访迦叶、一种七收等十五幅故事画[14]299-301。由此来看的话,第148窟中的各种变相图近乎是完成形态。但此窟西方净土变的构图本身比第320窟更加有条理,而且虽然外缘部的顺序、内容与经典相符,但表现更加简化。综合以上诸点考虑的话,这一时期的西方净土变及各种变相图,其形式变得更加适于对经典内容进行说明,并定型化。
8世纪70年代中期,人们期望往生净土的热情消退,并且对了解净土情景的兴趣也减弱。石窟内部不再是体现地上所出现的净土世界,也不再是详尽展示施主所期望的往生之处的场景。变相图的制作目的或许更偏重于对施主及其家族或年轻僧侣的教育,这也与西方净土变等各种变相图的定型化有关。而整幅画面粉本的使用无疑加速了这种变化。
本文注意到,西方净土变由唐前期第二期的中央宝坛前后画宝池这样的簡单构图,向宝坛上部出现了被宝池围住的三座岛所构成的上段,画面整体被分成了上(宝楼部分)、中(宝坛部分)、下(宝地部分)的三段式复杂构图的发展过程。此外,在有十六观和未生怨外缘部的第三、四期的西方净土变中,粉本的使用范围扩大,并且还与十六观粉本组合到一起,本文也对此进行了分析。综合以上考察,辨明了唐前期第二期至第四期的各时期西方净土变的特征及变迁过程。
第二期西方净土变的构图变化应是敦煌莫高窟的自立性发展的结果,但由第二期向第三期发展时所见到的变化,应该是在西安传入的新情况的影响下所产生的。而与此相对的,第三期至第四期时,粉本的使用范围由局部扩大到整幅画面,这又是敦煌莫高窟的自立性发展的结果。第四期前期末,从外部再度传入了粉本,而且此后以此为基础的西方净土变逐渐成为主流。由此看来,以西安佛教美术为中心的外部影响与敦煌莫高窟的自立性发展交叉演变,而与此同时西方净土变等各种变相图的制作目的也在变化着,这便是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诸窟的最大特征。
参考文献:
[1]东山健吾.敦煌莫高窟第二二〇窟試論[J].佛教芸術:第133号.毎日新闻社,1980:16.
[2]田口荣一.主室南壁阿弥陀浄土変相および东壁維摩詰経変相について[M]//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敦煌学术调查团.敦煌石窟学術調査第三次報告書.1989:41.
[3]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C]//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149,150.
[4]大西磨希子.西方浄土変の研究[M].中央公论美术出版,2007:28-36.
[5]贺世哲.从供養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G]//敦煌石窟论稿.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4:516.
[6]敦煌石窟全集:五:阿弥陀经画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15.
[7]段文杰.唐代前期の莫高窟芸術[M]//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东京:平凡社,1981.
[8]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M]//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41.
[9]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86.
[10]山崎淑子.敦煌莫高窟における初唐から盛唐への過渡期の一様相[J].成城文藝:第一七四号.成城大学文艺学部,2001:11,13.
[11]中村兴二.西方浄土変の研究二八、一四八窟东壁[J].日本美術工芸:518.1981:49.
[12]王恵民.敦煌隋至初唐的弥勒图像考察[C]//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42-44.
[13]杨明芬.唐代西方净土礼忏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44.
[14]李永宁,蔡伟堂.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G]//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经变编.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297.
[15]八木春生.敦煌莫高窟第二二〇窟に関する一考察[J].佛教藝術:第324号,毎日新闻社,2012.
[16]中村兴二.西方浄土変の研究二六、一七二窟南北壁[J].日本美術工芸:516,1981:50.
[17]沙武田.敦煌画稿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4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