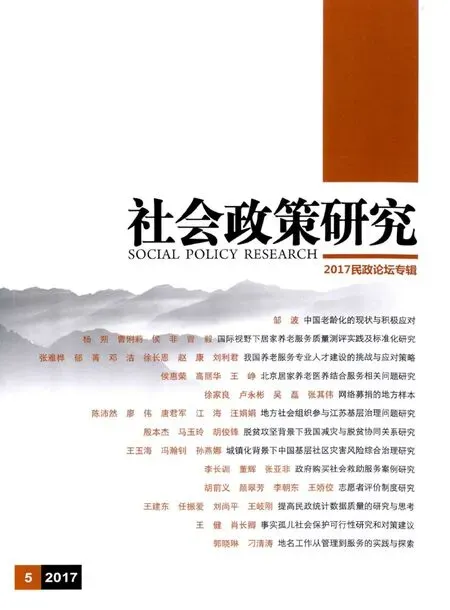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问题研究
陈沛然 廖 伟 唐君军 江 海 汪娟娟
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强调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并首次采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这是我国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变换的必要环节的重要生长点,社会组织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逐渐萌芽并生长起来的(王名,2009;王诗宗、宋程成,2013)。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格局持续发生着深刻变革,社会成员不断被“再组织化”,各类社会组织(既包括“学会”、“研究会”、“协会”、“商会”、“促进会”、“联合会”等会员制组织,也包括基金会、民办学校、民办医院、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等公益服务实体的非会员制组织)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地方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彰显,其活动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效拓展了社会的包容力与多元化格局,同时也提高了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及其张力,极大地加快了国家和地区社会化发展的步伐,使得社会自治的格局日趋明显(纪莺莺,2013;王诗宗、宋 程 成、 许 鹿,2014;Debin,2013;Kuah-Pearce,2015)。
“十三五”期间,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对从整体上推进江苏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意义。但如何更好地激发地方社会组织的活力,如何完善其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方法、制度安排及效果评价等,在现阶段都还没能形成一个统一、合理的逻辑和范式,使得地方社会组织在江苏基层社会治理中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因此,研究和分析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现行机制的缺陷和不足,深入探讨地方社会组织融入江苏基层治理的问题与机制创新,对于促进江苏地方社会组织的发展、深化江苏基层社会体制改革、推进江苏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回顾与现实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政府和社会都将从传统的管理体系向现代的治理体系转变,这一转变过程提出了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社会组织在中国迅猛发展起来,并以其独特的优势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载体,也是现代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支柱。
(一)江苏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的嬗变
基于对江苏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的回顾,可以梳理出从单中心秩序到多中心秩序、从法制到法治、从全能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从集权到分权的演变轨迹。
1.从单中心秩序到多中心秩序
20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逐渐开始对党和政府进行适度分离,政治领导责任归属于党,而行政管理责任则归属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策,江苏相继对政企和政社的分开进行贯彻实行。到了八十年代末,随着江苏农村村民委员会制度、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推行以及城市基层民主的不断探索与践行,江苏基层社会治理单极秩序的理念和方式开始逐渐向多元秩序格局。再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江苏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地方社会组织力量也迅速萌芽与壮大,它们积极参与到江苏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中并愈来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至此,由“省委—省政府—地方市场—地方社会组织—江苏公民”组成的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多中心秩序已经初具形态。
2.从法制到法治
同样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民主与法制开始提上国家议程,江苏许多的法律工作者和理论学者也开始关注并倡导“依法治国”。“法治”与“法制”,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法制”强调依法治国、执法为民、服务大局、公平正义和党的领导,而“法治”除了强调这些内容以外,更加重视了法律本身的权威性,任何组织与个人的行为均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随着江苏社会建设的不断深入,江苏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容与任务也越发深入和具体,整个江苏基层社会治理也成为了江苏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法治体系逐步确立与完善的过程。
3.从全能型地方政府到服务型地方政府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江苏将“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深入贯彻中央“人本政府、效率政府、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实现民主参与监督的政府才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的精神,并结合江苏社会治理的实际,从行政体制改革、社会建设与发展、服务民生三个角度展开了系统阐述。当前,江苏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建设已经呈现出五个方面的总体特征,即强调政府服务责任,建设责任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支出,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品;完善公共服务的各种法规政策,为服务政府提供制度保障;改善政府服务质量,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4.从集权到分权
随着江苏基层社会治理内容与结构的变革,政府的分权与授权也在有条不紊地深入推进。在传统的单极化管理秩序下,地方政府集中了各领域的权力,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方组织与社会自治。当经济社会水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后,多元主体在江苏基层社会治理中开始逐渐显露出积极的作用。地方政府开始分权予社会,如城市基层自治、农村村民自治等都是地方政府权力分散的重要表现。随着江苏地方社会组织的萌芽与发展,以及它们在社会治理当中独特功能与影响,江苏政府开始广泛培育与扶持地方社会组织并积极引导其参与到江苏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中来,多元共治的良性局面逐步形成。
(二)当前江苏地方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突出问题
地方社会组织要成为社会管理的参与者,成为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就必须不断完善内部治理,加强机构自身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发展的竞争力。江苏省社会组织在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因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自身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自身定位不准、发展不平衡和资金人才缺乏这三方面。
1.地方社会组织自身定位不准
传统社会治理机制中,地方社会组织往往依赖于政府的保护,这是由于地方社会组织筹集资金的能力还有待完善,而资金又是任何一个组织赖以行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地方社会组织不能加强其自身筹集资金的能力,仅仅靠政府的资金支持是不现实的。江苏的地方社会组织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如同其他地区一样,政府都对其进行各种资金、政策的扶持,但是,随着地方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多,地方社会组织之间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优胜劣汰,弱者必然要接受被淘汰的命运。虽然目前江苏的地方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得到了飞速发展,质量也有很大提髙,但是地方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很弱。地方社会组织必须认识到自身在现代社会治理机制中的角色定位,认清自身的责任,勇于担当,才能尽快成长起来。
2.地方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
江苏地方社会组织的发展,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领域以及城乡之间,都有着较大的差距。对不同的区域而言,江苏东部地区的地方社会组织发展较快,而西部地区发展较慢;沿海地区的地方社会组织发展较快,而内陆地区发展较慢。不仅如此,同为西部地区,不同类别的地方社会组织发展也有较大的差距。目前江苏省内,苏州、南京、无锡等地是社会组织发展最快的地区,而宿迁、徐州等地的社会组织发展速度则较为缓慢。除了社会组织在数量上存在差异外,社会组织的类型也是经济发达城市多于经济欠发达城市。
3.地方社会组织人才缺乏
江苏地方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机构,基于此,地方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大多是合作,而非西方发达国家常见的对抗。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地方社会组织对于政府的监督功能,也降低了地方社会组织自身的独立性,阻碍了地方社会组织自身功能的发挥。此外,江苏不少地方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来自政府行政机关,相当一部分是机构改革分流的人员或者是第一线退下来的离退休人员,他们大都知识结构老化且缺乏领导管理能力。同时又由于地方社会组织没有真正的人事任免权,大批年轻且具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员被拒之门外,造成了地方社会组织发展的人才资源短缺。地方社会组织专业人员的缺乏和资金的不足直接导致了地方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不足,是地方社会组织缺乏创新能力、活动能力、管理能力的主要原因。
三、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困境及其原因
基层社会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种其他组织在内的治理主体,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谋求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不断地探索、实践各种社会治理方式方法,而达到善治的过程。目前,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研究认为,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动力缺乏与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机制缺陷是其中最重要的深层原因。
(一)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动力缺乏
虽然在各方的努力下,江苏地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地方社会组织的作用不断扩大,但是由于体制及执行的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以及相关能力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在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环境等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1.源动力方面的问题
一是地方社会组织的发展资金普遍不足。“没有钱”一直是困扰社会组织发展和参与基层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而那些地方社会组织则在资金方面表现得更为困难。一方面受限于地方社会组织自身规模、层次和公信力等,难以获得充足的发展资金;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对地方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整体不足,这使得地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往往是偶发性、短期性,而非是长期性的和计划性。
二是地方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普遍不高。由于地方社会组织的发展资金长期匮乏,因而其工作人员多为“兼职”或“志愿”性质,缺少较高层次、较为系统或较强针对性的工作培训,“换了一批又一批”是其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常态,而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这使得地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人员的专业素质问题被暴露了出来。
三是地方社会组织的社会资源普遍匮乏。地方社会组织在众多重要社会资源的占有方面往往受限于它们的组织规模、地域和专业范围,大多只能依赖自身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充裕度和稳定性都比较差。即便是那些带有部分官方性质的地方社会组织,其社会资源的获取实质上也只是其官方背景的有限延伸,有效性和可支配性也难以保证。
2.主动性方面的问题
一是地方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不高、信息公开水平偏低。由于地方社会组织在自身公信力建设方面的自主性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也不够,普遍存在信息公开不充分、不完全的问题(尤其是涉及资金来源及其使用的问题),这使得地方社会组织的公信力难以确立。
二是地方社会组织项目实施的随意性强。由于地方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的局限性,使得其参与基层治理的水平较低、管控能力较差,受具体成员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在治理过程中,常常会偏离既定目标或无法长期坚持,项目实施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从而造成了服务对象一定的反感。
三是地方社会组织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反馈不充分。由于地方社会组织资金、人力与社会资源大多来源于其他社会主体,因此地方社会组织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对于其自身发展和参与地方治理作用的发挥都至关重要。各类社会主体将资源投入地方社会组织之后,经常得不到后续反馈,这使得很多社会主体对地方社会组织的关注度和投入度难以持续,也不愿意将资源投入地方社会组织。
3.外部动力方面的问题
一是经济领域的分配制度尚不完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领域掌握的经济资源有所扩大,由于分配制度不尽合理,社会资源向少数富裕阶层迅速集中,而占社会结构主体的中低收入阶层所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不足。这种不平衡使得地方社会组织在从社会领域获取资源的过程中遇到了重大困难。
二是社会领域的发展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与许多地方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相比,社会领域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社会力量的发育水平较低,公民对地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视程度缺乏。
(二)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机制缺陷
目前,江苏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加速推进了社会转型的进程,政府在社会领域职能让渡的持续进行以及对社会组织的关注与重视,拓宽了江苏地方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发育的空间,使其能够广泛地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然而由于受到现实与历史、制度与观念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相较于上海、广东等省市,江苏地方社会组织的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相应的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实现网络治理中竞争与合作、交流与学习、共享与互补、多元与共治的新型社会治理格局还有相当的差距。具体而言,江苏地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适应机制有待增强
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适应机制不完善集中表现为,地方社会组织的主体合法性不被普遍认可、地方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存在一定偏离、地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够通畅等。目前,虽然地方社会组织在江苏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功能和作用得到了初步的发挥,但是其主体合法性仍旧不被完全认可,取得江苏各级政府和社区公众的广泛认同是促进地方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先决条件。此外,地方社会组织应当如何参与到江苏基层治理中,应当依据什么样的秩序和规范开展基层社会治理活动,都是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2.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信任机制有待提高
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信任机制不完善集中表现为,地方政府对地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高、地方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相互信任严重缺乏、地方社会组织缺乏有效的公信力等。一方面,地方社会组织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比如许多地方组织自身定位不准,没有完全认识到自身在现代社会治理机制中的角色定位和认清自身的责任,这导致许多地方社会组织得不到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广泛信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去监管地方社会组织的运行。
3.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
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合作机制不完善集中表现为,合作信息的传递不对称、合作资源整合与利用不充分、对参与合作治理的合法性还存有疑虑等。地方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基础是政府愿意把部分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事项交给社会,同时地方社会组织也要能够承担政府转移的职能。从这个层面来看,“社”是指社会组织,只有依赖大量的社会组织来开展服务,才能促进政社互动。在此过程中,大量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是推动政社互动的基础,也是良性政社互动的保证。目前,江苏地方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还需更紧密。
4.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扶持机制有待改善
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扶持机制不完善集中表现为,制度供给相对滞后、资金扶持力度不够、综合培育不成体系等。由于自身原因,地方社会组织筹集资金的能力还有待完善,而资金又是任何一个组织赖以行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地方社会组织除了加强其自身的筹集资金的能力,还需要从其他渠道获得资金来源。此外,地方社会组织发展的人才资源短缺也直接导致了其自身能力的不足,这也阻碍了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5.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维护机制有待健全
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维护机制不健全集中表现为,缺乏化解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之间冲突的核心机制、对地方社会组织缺乏有效的监督与评价等。目前,江苏各级政府对地方社会组织的监管模式为“严进宽管”,很多地方组织是否能够有效地进行基层社会治理还有待考察。随着江苏各种地方社会组织数量的不断增多,地方社会组织之间也会自然而然形成优胜劣汰,弱者必然要接受被淘汰的命运。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对已有的地方社会组织进行评价需要江苏各级政府统一制定。
四、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动力与机制创新
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其自身组织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衡量江苏基层社会治理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总体来看,要使地方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动力和机制上的创新。
(一)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动力建设
促进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首先必须解决源动力方面的问题,即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资金、人员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来源问题;其次是发挥地方社会组织作为行为主体的积极性,解决主动力问题;最后还必须构建有利于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外部环境,解决外部动力问题。具体地看,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可以有以下一些积极的政策建议。
1.加强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源动力建设
一是制定优惠政策、加强资金投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其他政策支持、引导企业积极投身地方社会组织,地方社会组织从企业中获得发展的资金支持,并接受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监督。这是一种当前可适用的相对良性的资金供应体系。特别是对于那些处于起步阶段的地方社会组织,地方政府和企业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尊重其发展的规律性,特别是在资金、人员等方面要尽可能给予更多的扶持和照顾。对于在基层治理领域表现突出的地方社会组织,地方政府要有相应的奖励机制,在资金方面给予倾斜,只有促进多元主体间的竞争,才能增强地方社会组织的活力。
二是推动成员的积极参与。每个成员的积极参与是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重要保障,地方社会组织的整体意志来自每个成员个人意志的结合,有效率的地方社会组织应是社会成员自觉建立的。因此,一方面,需要提高地方社会组织成员的专业水平,让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重要性成为其个人的自觉认识;另一方面,也要扩大每一个成员对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监督作用,发挥群众优势,这对在江苏基层治理领域发挥地方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重视与多元主体的合作。加强地方社会组织的自身建设还必须加强其与地方政府部门和其他私人部门之间的横向与纵向联系,在江苏基层治理领域内与多元化的主体展开合作,并通过实施一系列内部自律规范与自我评估机制,提高地方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与监督体制。这种多元化的合作既可以加强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能力,又可以优化整个江苏基层治理系统的结构,实现良性互动。
2.推进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主动力建设
一是加强地方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地方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其积极主动投身江苏基层治理的主要行为动力。随着地方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地方社会组织自主性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推进地方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建设需要循序渐进,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地方社会组织要从自身内部入手,变革组织结构、精简优化人员构成、创新工作组织模式等。
二是推动地方社会组织的正规化。要想提升地方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加强地方社会组织在资金、人员以及其他社会资源上的获取能力,地方社会组织的正规化建设是一条必由之路。地方社会组织正规化建设,既包含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的正规化,也涉及项目管理、资金使用、平台建设等多个方面。首先就必须完善地方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进一步明确其志愿性、公益性,也要优化相关的组织结构,根据社会组织结构扁平化的特点安排相关的组织构架。在人员使用方面,既要加强志愿者培训,充分发挥志愿者的作用,扩大其志愿性,也要加强专职正式雇员的培训与开发,使得其自身的组织结构更加稳定和专业。此外,项目管理与资金审计必须实现专业化、透明化,做到层层公开、面面俱到,实现各个环节的可查可控。
三是推进地方社会组织评估。推进地方社会组织评估是对其成员与基层治理主体的职责所在,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态度,也是地方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与资源获取能力的重要保证。地方社会组织评估涉及多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第三方监督、自我监督与政府部门监管,形成“三位一体”的地方社会组织评估体系,从而达到优中选优,促进地方社会组织之间开展竞争,提升其运行效率、降低运行成本,促进其不断改革创新。
3.重视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外部动力建设
一是进一步加大地方经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税收减免政策,使得企业与个人能把更多的财富用于地方社会组织的建设,充分扩充地方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视地方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投入;此外还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得社会资源分配更加公平,进一步增加企业、个人与社会所占有的经济资源,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
二是进一步推进社会力量建设。地方政府应当立足于基层社区建设,扩大基层自治,放手壮大基层社会力量,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引导社会各界投身到社会力量建设中来,充实社会领域所掌握的资源;另一方面加快地方政府改革,将部分职能转移到社会领域,改变长久以来地方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依赖的关系。
三是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和法规建设。地方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相关法制化、规范化改革,加强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相关税法、组织法、管理法修订,解决相关法律法规中不完善、不系统、相互抵触的问题,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使地方社会组织在相关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净化地方社会组织的活动空间。
(二)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
目前,对于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单个组织类型或单个作用方面进行讨论和安排,虽然突出了重点,但缺乏对地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视野,无法实现对地方社会组织或基层社会治理的系统推进。为突破这一桎梏,本研究将地方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视为整个社会治理网络系统的组成部分,拟建立起适应机制、信任机制、合作机制、扶持机制、维护机制五个彼此独立又相互配合的机制体系。
1.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适应机制
一是要确立地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主体地位。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治理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和重要价值所在,面对不断成长的社会力量和不断增多的参与诉求,以地方社会组织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一的整体治理格局的建立,能够稳固江苏地方社会组织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更有效地发挥地方社会组织在江苏基层治理领域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实现其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也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顺利开展铺平道路。
二是要重塑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强政府、弱社会”的状态在我国持续已久,从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来看,我国的地方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深受政府影响。因此,地方社会组织依附政府是基于现实的选择。但这种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需要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改变现有的管理模式,重塑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三是对地方社会组织的基层社会治理活动进行流程再造。怎么样让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可能,并且依据什么样的秩序、规范、步骤和方式开展基层社会治理活动,这需要地方政府改变传统模式下的操作流程,对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整个程序进行流程再造。
2.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信任机制
一是要以全面信息公开作为立信之法。地方社会组织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吸引社会捐赠和获得政府支持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社会上拥有的公信力,公信力是地方社会组织的生命线。实行完善的信息公开,提高地方社会组织运作的透明度,是地方社会组织获取江苏各级政府与社会广泛信任的根本途径。如果地方社会组织日常管理和项目运作不透明,公众就会怀疑社会组织滥用社会资源来牟取私利。地方社会组织的运行情况只有被充分了解和监督,地方政府与社会才会继续给予良好的评价和有力的支持。
二是要以组织伦理道德建设作为守信之根。由于诸多原因,江苏近年来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社会贫富及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信任和认同降低,社会伦理和道德建设下滑,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持续累积,潜在的社会风险和社会安全问题逐步显现,整个社会对加强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完善社会服务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对此,只有加强对地方社会组织的伦理道德建设,约束其基层社会治理行为,才能保持其原则、性质和宗旨不变质,才能有效抑制地方社会组织公益腐败现象的产生。
三是要以提升地方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作为固信之路。社会组织在江苏乃至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合法性和法律地位的取得也极为短暂,发展很不成熟,自身能力还较为欠缺。因此,只有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坚定不移地走民间化发展方向,例行制度化管理,开展经常化活动,提供优质化服务,树立亲民化形象,社会组织才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以及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归根到底,地方社会组织自身能力的高低强弱是其获得信任和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路径。
3.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合作机制
一是要搭建完善地方政府信息交流平台,实现治理信息共享。由于政府职能的特殊性,必须要求政府在促进公共物品的供给、改善和公平分配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这些服务职能是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开展的。通过搭建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塑造真正的公共信息服务面貌,能够让地方社会组织充分了解江苏各级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公共治理方向,把握与各级政府合作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机会。
二是要整合与利用合作资源,拓宽合作范围。除了常规的政府购买服务外,基层政府可以逐步尝试在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公正等社会问题的解决中与地方社会组织联手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可以采用“委托-代理”的形式,这种由政府通过合同、协议来授权,以社会组织自身名义具体运作某个公共事务项目的做法是对二者传统合作关系的突破。地方社会组织通过对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专业技能、领域知识以及需求信息等资源的利用,能很好地弥补地方政府管理模式的诸类不足,以便更好地回应社会需求。
三是要消除基层社会治理合作的合法性疑虑。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与其存亡密切相关。社会组织在江苏基层治理中的发展面临着双重合法性的问题:第一,要获得外部的合法性,即社会组织要被外界承认能够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的集体利益,否则无法以合法的身份与外界互动;第二,要获得内部的合法性,社会组织要获得其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授权,特定社会群体要认可该社会组织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这需要从法律、观念、文化和社会期待等层面入手,使社会合作治理活动能够与社会合法性要求相符,消除江苏各级政府等其他治理主体与地方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治理的顾忌以及组织内部的忧虑,充分保证基层社会治理活动的连续性和有效性。
4.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扶持机制
一是要优化基层设计以构建系统的政治扶持体系。这需要通过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的配套的制度安排和实施细则,来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和地方社会组织的发展。经由标准化走向制度化,规范基层政府的权责边界和治理规程。基层治理制度化的核心在于基层政府权责和行为的规范问题。将基层治理主体和治理行为逐步纳入标准化规范体系,明确不同治理主体的地位,对治理流程、互动过程等进行细化规范,对基层公共事务“由谁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结果”等作出明确、具体、可操作的标准化规定,是实现基层治理制度化的有效途径。
二是要设计多渠道和多方位的经济扶持。江苏各级政府对地方社会组织的管理涵盖了地方社会组织的身份登记注册、内部治理规范、外部活动领域监管等多个方面,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全面监管”。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属于规范意义上的“非营利组织”,因此,一方面要保证其获得经济资金能够严格用于社会事业而非私有占据,另一方面也要给予其相应的经济优惠以激励其继续服务于社会事业的积极性。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构建地方政府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经济扶持的系统框架。
三是统筹针对地方社会组织的综合培育体系。社会组织人才是地方社会组织中具有一定管理与服务技能,并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具有奉献精神和创新意识,乐于为社会组织做出积极贡献的复合型人才。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是构建与社会组织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发展机制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管理与社会创新建设的重大举措。可以通过建立地方社会组织孵化机制、完善地方社会组织人才保障机制、加强地方社会组织文化建设等针对性举措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全面培养。
5.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维护机制
一是要改进对地方社会组织的监管模式。改善目前江苏各级政府对地方社会组织“严进宽管”的监管模式,让地方社会组织能合法有序地进行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法治化是社会组织监管的基本方式。历史表明,无视法律、践踏规则,或许可以满足一时一己之需,却会让社会的齿轮处处“卡壳”,难以有序运行。依法依规依章,力戒以往临时性、政策性的集中清理整顿,强化地方社会组织监管的法治化建设是历史的潮流和趋势。基于目前地方社会组织法律法规监管体系不完善的状况,当务之急是加快立法步伐,尽量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逐步构建健全完善的江苏社会组织法律监管体系。
二是要完善化解冲突的行政调解机制。行政调解工作是增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迫切需要。社会治理结构的转型面临多元治理主体发育不足、参与机制的缺乏、行政功能部分替代等困境。为避免基层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和地方社会自组织的“边缘化”,以行政调解作为主要调解手段,对于促进地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向更深层次拓展,提升地方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力和生存能力十分必要。
三是要建立科学的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评估指标。为了提高地方社会组织的运营效率,使政府、公众能有效地对社会组织行为进行监督,建立科学的社会组织评估指标十分必要,这不仅是基层社会治理维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对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进行持续创新的重要内容。评估指标的建立一方面要从社会组织的愿景与使命这一组织目标出发,通过跟踪地方社会组织从筹划、注册到最终成立运作的全过程,找到一系列能够反映社会组织的评估指标。另一方面,依据这些评估指标的内在联系将相关性较大的指标合并成若干个维度,用以反映地方社会组织在不同方面的特征和表现,也是对评估范围的基本类型划分。
五、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协同作用”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纳入到国家的发展规划当中来。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地方社会组织作为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社会职能转移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柱,在社会治理领域起到了愈加重要的作用。江苏地方社会组织是随着江苏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逐渐萌芽并生长起来的。本文基于江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探讨“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治理的机制创新”问题的过程中,努力在江苏地方社会组织发展和江苏基层社会治理进步两个方面间找到最有益的契合点,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纳入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进行系统考虑,为地方社会组织参与江苏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研究和实践提供有效指导和有益参考。本研究根据治理关系纵向性的特点实现层层相接,根据治理方式横向性的特点实现环环相扣,提出建立起适应机制、信任机制、合作机制、扶持机制、维护机制五个彼此独立又相互配合的机制体系,实现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创新,对优化社会组织持续创新环境、营造持续创新氛围,不断谋求适当的改变,真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毕素华,《中国特色社会福利项目的运行与反思:政府包揽抑或福利多元》,《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48-52页。
[2]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第70-83页。
[3]杭行、刘伟亭,《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深层次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58-64页。
[4]黄晓春、嵇欣,《非协同治理与策略性应对——社会组织自主性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98-123页。
[5]纪莺莺,《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视角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219-241页。
[6]李培林,《我国社会组织体制的改革和未来》,《社会》,2013年,第3期,第1-10页。
[7]马立、曹锦清,《地方社会组织生长的政策支持: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71-77页。
[8]彭善民,《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自主管理创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64-67页。
[9]邱梦华,《利益、认同与制度:城市地方社会组织的生长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97-106页。
[10]孙荣,《社会组织如何融入基层治理创新》,《学术前沿》,2015年,第1期,第62-71页。
[11]王名,《走向公民社会: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及趋势》,《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第5-12页。
[12]王诗宗、宋程成,《独立抑或自主:中国社会组织特征问题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50-66页。
[13]王诗宗、宋程成、许鹿,《中国社会组织多重特征的机制性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42-59页。
[14]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57-61页。
[15]吴结兵、沈台风,《社会组织促进居民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研究》,《管理世界》,2015年,第8期,第58-66页。
[16]郑功成,《中国社会福利改革与发展战略:从照顾弱者到普惠全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47-60页。
[17]郑功成,《中国社会福利的现状与发展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2-10页。
[18]Cohen, A. M.(2014). Change and Program Evaluation in Social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 31(4),210-226.
[19]Debin, H.(2013). Legal Logic of the Generation of Chinese Village Community Order.Canadian Social Science, 9(3): 149-152.
[20]Fewell, J.(2014).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Social Organization. Asian-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s, 27(9):1311-1318.
[21]Fernandes, J. M., Magalhães, P. C.(2016).Government survival in semi-presidential regim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49(1): 61-80.
[22]Friesen, J. P., Kay, A. C., Eibach, R.P., et al.(2014). Seeking structure in social organization: compensatory control and the psychological advantages of hierarch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06(4),590-609.
[23]Mueller, E. F., Jungwirth, C.(2014).Comparing Top-Down and Bottom-Up Cluster Initiatives from a Principal-Agent Perspective: What We Can Learn for Designing Governance Regimes.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 66(7),357-381.
[24]Andrés, R. & Enrique, G.(2015).Quality of Government and the Returns of Investment: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Cohesion Expenditure in European Regions. Regional Studies,49(8),1274-1290.
[25]Persson, L.(2016). Government consumption smoothing in a balanced budget regime.International Tax and Public Finance,23(2),1-27.
[26]Rahmann, R.(2015). Elemen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by Raymond Firth. Physics Procedia,70(3): 923-926.
[27]Verschuere, B. & Corte, J. D.(2015).Nonprofit Advocacy Under a Third-Party Government Regime: Cooperation or Conflict?.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6(1), 22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