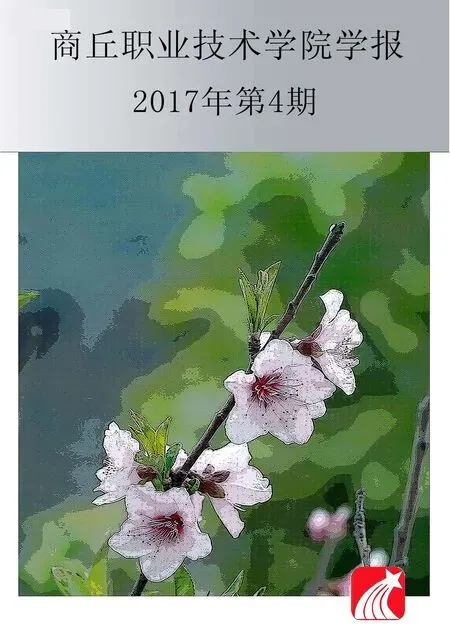城市化进程中乡土叙事的策略变迁
经宽蓉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与旅游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城市化进程中乡土叙事的策略变迁
经宽蓉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与旅游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城市化进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必然过程,它的发生,不仅从地域、结构等物质条件方面改变农村,更深层次的是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精神上价值观念的变迁。在这历史性的变革当中,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农民经历着转型和新生,这期间也有辛酸与陈腐。这为当下的乡土叙事提供了广大的空间。
城市化进程;乡土叙事;策略变迁
乡土文学自“五四”以来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样式之一,从诞生以来就秉持着现实主义的品格,理性地叙述着中国大地的变迁。乡土叙事在情感表达方面,一直保持两种观念,其一是通过对乡土叙事细致的刻画,表达刻骨铭心的怀念之情,以及对乡土无限惬意生活的向往;其二就是对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乡土落后和愚昧的批判。
城市化进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的必然过程,它的发生,不仅从地域、结构等物质条件方面改变农村,更深层次的是因为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从而产生精神上价值观念的变迁。在这历史性的变革当中,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农民经历着转型和新生,这期间也有辛酸与陈腐。这为当下的乡土叙事提供了广大的空间。
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农耕文明在我们这个年代已经退至边缘,关于城市与乡村,往往被简化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从而使作家获得自身叙述的完满,很多当代作家避开了乡土社会完全可能会有的复杂矛盾,显得过于理想化。现实的乡土世界,有没有一些作家描述的温馨、纯朴,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城市化对农村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而留在农村的是一些老人、妇女和儿童,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农村固有的观念与城市体制格格不入,想真正融入城市并不容易,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处于困境之中,感到失落与彷徨。而留守在乡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由于家庭中坚力量的缺失,乡村原有的面貌与精神都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土地观念、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被异质的价值所取代,这些都意味着中国农村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新阶段。作家们作为当代知识分子,承担着记载社会变革的重任,乡土叙事也跟随着社会变革的步伐,艺术观念有了突破,新的叙述内容和叙事形态也应运而生[]134。
一、农民进城的后遗症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一个时间的片段都是在同泥土、汗水、劳作、耕种的交流中留下的,是劳作与休息间与牲口的交流,与农具的相伴留下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希望在城市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于是,乡村“留守老人”“留守孩子”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民走出乡村后,留下的是一处处日见凋敝、荒凉的家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劳动力缺失,土地荒废,再也没有以前繁茂的景象。
在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中,通过写农具,我们可以看到农村的日益荒凉。对于小说中的老人来讲,农具是有生命的老伙伴,这些伙伴陪伴老人一起劳作,即使不小心伤害老人的身体,却依然对其感情深厚,对于老人们来说,农具不仅可以抚摸,还可以交流,是有生命和感情的,农具陪伴老人从壮年到衰老。在《残耱》中,李锐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在漫天飞舞黄土的地里,只有渐渐老去的老人和他的两个老伙伴,一头黑骡子和一具坏了的耱。李锐是这样刻画老人的,老人感到自己的无助,感到了自己与现实的不合,感到了老人曾经一直固守的东西在慢慢消散,李锐让读者跟随老人的眼泪和悲伤,体会到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荒凉。
荒凉源于人们对农村原有生活方式的逃离,源于对传统农具的背弃。家园的废弃导致了田园情趣的消失,李锐在小说中多处描述这样的场景,炊烟、瓦房、树林、小河,这些原本可以构成田园诗中美轮美奂的景象,可是这里的基调却是悲凉的、荒芜的,原本应该怡然自得的乡间美景在主人公心里已经成为过去[]216。
乡村的荒芜还源于老人们的去世,这些老人不仅仅是村里的乡亲,更是自己过去岁月的见证者,过去的村庄十分热闹,老人的去世使乡村变得越来越冷清,没有他们,走进城里的年轻人便慢慢和村庄减少联系,越来越少回到村里,以往发生的事情,对于年轻人来说,有时候都难以分辨到底是梦还是现实。
贾平凹是农民的儿子,他对乡土有着难以割舍的眷恋。在他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始终用冷静、客观的笔触记录发生在中国大地上农村的事、农村的人。他的长篇小说《秦腔》是他对中国最后的乡土所发出的“废乡”式的哀鸣。小说中,贾平凹运用朴实的陕西方言,通过细碎的乡村日常生活场景,展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悲喜交加的生活图景。
贾平凹首先站在理性的立场,肯定了城市化进程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在小说中,他站在客观的角度,描述了乡村走向城镇化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两种经济方式发生的微妙变化。农民进城成为打工者,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清风街修了312国道,交通的便利,为偏僻的山村带来了新鲜事物与资讯,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使商品流通更为便捷,同时慢慢打破了清风街固有的单一的经济模式,使得更为活跃而多元的商品经济在山村流行。在这场变革中,清风街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改变,更多了些现代化的生活场景。
面对乡村走向城镇化的必然趋势,这期间确实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发展,贾平凹也冷静进行着思考,他感到更多的是焦虑和不安。在这场大变革中,农村的一切充满生机,可是一切又都混乱着、转变着。农村再也没有以往的宁静与安详,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又出现了更多令人担忧的事情,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农村经营模式,甚至破坏了原本的农业生产。清风街修了条312国道,开了新的农贸市场,却因此破坏了几十亩良田和果林,代价也是相当大的,当年土地承包的受益人却在这场变革中承受巨大的痛苦,因为改革牺牲了他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开始无奈地放弃土地,带着惶恐与悲伤进入城市,希冀在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村里壮年的出走,使得乡村劳动力缺失,剩下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良田开始荒废。小说中夏天智去世时,村里竟然找不到壮汉抬棺,而进入城市的乡村人,往往在城市从事最为艰苦的工作,生活在城市的边缘,是城市最为弱势的群体。与此同时,乡村中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愈演愈烈。在《秦腔》中,贾平凹通过深刻的农村体悟,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农村在经历城市化过程中发生的极为真实的场景,乡村在走向城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有着诱人的前景,一方面却承受着痛苦,在这场变革中,古老、宁静的乡村已经渐行渐远[]247。
王安忆的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也是她无奈地为逝去的“乡土中国”唱的一支哀婉的挽歌。小说以散漫的笔触写了一个名叫华舍的小镇发生的故事,原本和谐、宁静的小镇,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杂乱与陌生。村庄荒芜、老屋杂草丛生,原本清澈的河塘变成了污水沟,所有的一切都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化形态的改变。
二、城市化进程中乡土世界的精神变异
中国城镇化的脚步使乡村不仅在物质的层面上有很大的变迁,使得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发生很大的变化,更深刻的是,在乡村走向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村人的思维观念和价值体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甚至是重构,几千年来乡村式的思维与传统文明在历史洪流的撞击下显得不合时宜。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厌倦城市、回望乡土的乡土叙述者对曾经痴迷的精神家园重新审视,更客观地重新认识现代的乡土,因为亲近土地,才更深刻地认识土地。
贾平凹的《秦腔》可谓他对乡土中国的再度审视与重构,小说以疯子引生为视角全方位地关注故乡,以夏氏家族为描写对象,通过对秦腔这一传统文艺形式传承的描写,展现了清风街这个小镇在城市化过程中,受到现代文明洗礼,生活改变的方方面面,表达了贾平凹对现代乡村深切的关怀。“秦腔”这一乡村传统文化的代表,在时代发展过程中,艰难地传承,它不能再作为艺术而存在,仅仅成为现代人谋生的一种手段。像夏天智、夏天义这些乡村传统文化与秩序的守护者,结局是带着固守的传统观念被埋葬于黄土之中。《秦腔》呈现了传统乡村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不仅是乡人思想观念和生存方式的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道义与乡间民俗也发生了可怕的断裂。孝道是中华文明的传统道义,在小说中意识却日益淡薄,夏天义有五个儿子,可儿子间相互推诿,甚至有的公然表示不愿赡养父母;清风街的女子进城打工成为卖淫女,回村却毫无羞耻感,在小镇私通也是相当普遍,清风街上新建的酒楼里还出现了三陪女;邻里之间原本是那么和睦,现在却为了蝇头小利打得头破血流。在这样纷杂混乱的文化景象中,贾平凹算是为古老的农业传统文化奏响了一支哀曲,让我们在憧憬现代文明的同时,为传统农业文明的颓败感到无奈与惆怅。
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使得中国人普遍产生无归属感的心理,审视城市、回望乡土、再审视乡土,这是作家心灵探索的轨迹,他们在城与乡之间挣扎着、寻找着。刘玉栋,一位现居于城市而生于鲁北平原乡村的作家,对乡村有着特别的感悟,在他的“齐周雾村”系列小说中,展示给我们的不仅是乡村的温暖,也是现代乡村的现实。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鲁迅作为乡土文学的开路者,就以启蒙者的姿态将目光投向经历现代化进程的乡土中国,他把笔触伸向传统与现代转变期间的精神领域,希望改造国民劣根性。乡土文学发展至今,依然没能摆脱陈腐的封建文化禁锢,乡人在权势与暴力的奴役下又奴役着别人。在《雾似的村庄》中,汝东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英雄团长,战功显赫,为了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他放弃了大好前程,假装生病离开了部队,可是当他脱掉那身带给他荣誉的军装,慈眉善目地回到家乡时,迎接他的却是无穷的嘲讽与讥笑,家乡不接纳他,甚至不接纳他的儿女,儿女们在歧视中长大,女儿和外来的知青私奔了,二儿子在贫穷中生病去世,小儿子忍辱负重考上大学却再也不想回乡,只有大儿子乃木卖艺维持生计陪着他,可是乃木双目失明,最终还是受不了乡人的侮辱,自缢身亡,这一切彻底毁灭了汝东对家乡的念想,汝东最终离开了齐周雾村,古朴的乡村也许只是存在于他的梦里,现实的乡村世故得让人心痛。
人心向善,然而在现实生活面前,善良的人性有时又脆弱不堪;无权无势的乡民是暴虐权力的受害者,有时他们又不自觉地沦为权势人物的帮闲,为他们推波助澜。《干燥的季节》中养鱼人王喜祥的父亲因为对镇里收修路的集资款发了几句牢骚,就被催款队打伤而中风,一个身强力壮的屠夫变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瘫子,然而这并没有击碎王喜祥对权利拥有者的幻想,当他的鱼塘要起鱼的时候,他急急忙忙为村长送上第一桶鱼,是村人对他鱼塘的哄抢和村长儿子对他当众的侮辱殴打激醒了他,从此,村里多了一个眼放凶光的屠夫,少了一个温和善良的养鱼人。
现实的乡村,乡人畏惧权贵却又依附权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金钱崇拜成为乡村另一精神痼疾。《苦夏》里的马东,曾经因为盗窃入狱几年,可是出来后干了几年外贸,竟然暴富,回乡后当上了村长,村里人为了跟他发财,不仅没有追究他的过去,当年检举他的同伴也来讨好、巴结他,甚至无视他与妻子的不伦之情。《乡村夜》中那位孙子,小小年纪退学回家,与同伙拦路抢劫,认为这样来钱比较快,最后竟去抢开小卖铺爷爷的钱匣子。如此可见,金钱已经腐蚀了乡人的心灵,金钱甚至打败了亲情,将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道德观念打得岌岌可危[]13。
三、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脚步,乡土叙事在历史的演进中,敏锐地发现乡土世界的改变,从内容到精神,突破了中国乡土文学原有的叙事策略,将叙事领域扩展到“农民进城”和乡土世界的精神领域,颠覆了传统农民的形象,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和变迁。
故乡,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超越现实安放灵魂的地方,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故乡的血,它是我们的母亲。乡土,是人类永远的精神家园。故乡在经历城市化的进程中,遭遇困难,乡民在这历史性的变革中,也经历着无奈与辛酸,我们应该带着悲悯之心深刻认识与反省,带着它走出困境,而不是讥讽与嘲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根系乡土,乡村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故乡。乡土叙述者正是用他们的乡土小说,清醒、深刻地认识当下乡村,有感动也有惶惑。
[1] 丁 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袁培尧]
2017-03-17
经宽蓉(1983- ),女,回族,江苏镇江人,镇江高等专科学校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7.42
A
1671-8127(2017)04-00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