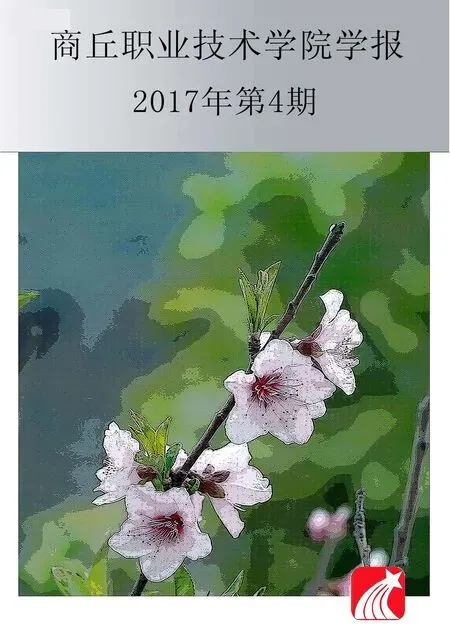汇编、考释唐前志怪小说的扛鼎之作
——兼评李剑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
王方领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
汇编、考释唐前志怪小说的扛鼎之作
——兼评李剑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
王方领
(阜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
《唐前志怪小说辑释》的最大特点是专注志怪一体,审慎处理阙文,详加考辨异文,善用原始材料、海外文献对史实遗闻、名物制度、生僻字词细加考释;且在文后附录翔实的参考资料作为补充,力求全面准确。同时,作者首创的“辑释体”兼具学术性和实用性,对后世文体创作影响很大。
唐前志怪;垦荒;辑释体;学术性;实用性
唐前志怪小说内容纷繁复杂,关涉到文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神话学等诸多方面,要想把各种故事理出头绪已属不易,整理、注释就更难。《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一书,是李剑国先生在撰述《唐前志怪小说史》的过程中,受鲁迅先生《古小说钩沉》的启发而创作的。不过,《古小说钩沉》包含各类文体,而《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则专注于志怪一类,“此书虽然是辑佚汇编,但是就全面系统地呈现这类小说的全貌来说,不得不说是一项创举”[1]92。全书按时间发展的顺序共分成三编,先秦两汉为第一编,魏晋为第二编,南北朝为第三编,以此体现小说内部的发展规律。“唐前志怪书多达百余种,本书所辑,力求别择佳制,取其旨趣隐约人事、讽喻社会者;题材新颖别致、幻设优美者;情味隽永、文辞生动者。惟短书卮言,难以责备,且虑及全局,则不免降格以求耳。”[2]2诚如作者在例言中所说,唐前志怪小说现存上百种,作者是去粗取精,选取了每个朝代较有代表性的,让读者窥知唐前小说的面貌。
作者考释谨严又注重说理,所采用的资料翔实而准确,每改一处,都征引数种文献来佐证;有时又广搜海外文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另外,作者在辑释过程中还穿插大量的知识,对文中出现的历史掌故、名物制度,详陈其来龙去脉,力求给读者较为详备的参考。“慎事比勘,商略异同,条畅源流,印证史志,使脉略分明,义理俱豁”,[2]4正如何满子先生在《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小引中讲的一样,作者坚持一切从材料出发、用事实说话,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作为研究唐前志怪的集大成之作,作者科学谨严的校书态度和夹注其中丰富的知识,具有鲜明的特征和很高的学术价值。
一、辑佚注释所呈现的特点
“本书所辑,力求别裁佳制……尽量采用佳椠或今人注本。”[2]2作者坚持选用最好的本子进行校对,文中所用之版本,都是经过其精心选取的“善本”,以求准确无误。另外,如书中所用底本有误,就根据别本进行校正,并且给出文章来源、作出校语。自古以来,作为稗官野史的小说,地位低下,正统文人大多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是不入流的“杂言、小道”;又由于去古较远,所以辑校、注释的难度很大。再加上图书自身损毁等原因,致使小说大量散佚,特别是唐前志怪小说集,很少能完整保存下来。李剑国先生在充分吸收前人辑佚成果的基础上,对如何辑释唐前古小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甄选材料,取材广泛,“无一字无来历”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孤文断句,更不能推见其旨。去古既远,流裔弥繁[3]3”(《古小说钩沉·序》),要从只言片语里去恢复古书原貌,可见难度之大。本书所取之材料,大多以唐前为主,以确保资料的原始性、可靠性。据学者统计,李剑国先生在《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中引用的古书近百种,远超《古小说钩沉》的六十余种[4]34-39。仅辑释《汲冢琐语》就用了《左传》《国语》《礼记》《史记》《北堂书钞》等二十三种古书;辑释《十洲记》时,参考了《隋书》《太平御览》《道藏》等四十余种文献,足见作者取材之广泛,辑释之谨严。例如《山海经·精卫》“詨”条:“‘其鸣自詨’谓其鸣声正如其名(精卫),亦即以其鸣声而名之也。”仅就 “詨”字的训诂,就考辨了《广韵》《文选》《太平御览》《事类赋注》这五种古书来说明。又如《神异经·山臊》“不应滥于王者”条:“注文前三句原为正文……盖亦为西汉人作也。”为了证明前三条注文是西汉人误增入正文的,作者也列举了《周礼》《诗经》《太平御览》《说郛》等九种文献来加以证明。
有时还注意到用海外文献来佐证国内资料,使考证更具有说服力。“《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搜神后记》十卷,陶潜撰,《日本国见在目录》同……玄宗时徐坚等撰《初学记》引有陶潜《搜神后记》、陶潜《搜神记》。”为了证明《搜神后记》的作者是陶潜,就征引海外文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来说明,使得材料更加翔实。同时,作者为了考辨与佛道相关的故事,又广求《高僧传序》《道藏》《破邪论》《致慧皎书》等道释文献进行校对。“唐释法琳《破邪论》卷下、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亦并有存目……法琳《辩正论·十代奉佛上篇》云:‘宋氏诸王并怀文藻,大习佛经,每月六斋,自持八戒,笃好文雅,义庆最优。’”这里就是用当时的佛道典籍,来说明刘宋王朝当时的社会风气——崇尚佛道故事。
(二)对阙文详加考辨,广采勤收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5]1112可见脱文现象较早就出现了。《四库提要》也指出:“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作为稗官野史的小说,其命运似乎更是多舛。近人聂崇岐在《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序》中说:“总上述二十种艺文志所著录之典籍,自先秦以迄清末,其有名可稽考者,盖不下四万余种,然求其存于今者,恐已不及半数。”由于人为、图书自身损坏等原因,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散佚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感慨研究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的“文献不足征”。所以,作者在辑释时广采异本,力求把阙文补齐,以恢复古书原貌。如《陆氏异林·钟繇》“钟繇”条:“钟繇,字元长,颍川人。裴注所引原无姓,据《太平御览》补。”原文中只称“繇”,作者据《御览》补充了其姓氏“钟”。又如《录异传·如愿》“忽”字条:“‘忽’字原无,据《初学记》《类林杂说》补。”
也有原书阙字,他人增补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要考证这类阙文,更见功夫。《志怪·夏侯弘》“尚时对死马坐”条:“《御览》卷八九七‘尚时’下阙四字,《广记》作‘尚对死马坐’,鲍本作‘尚对死马生’,‘生’当为‘坐’字之伪,今据补四字。”作者根据前人的辑补进行甄别,在证明“生”字之伪后,又据他本补了四字。又如《续齐谐记·屈原》的“每至此日”条:“‘每’字原无,据《玉烛宝典》,《艺文类聚》,《初学记》,《史记正义》,《唐会要》,《御览》卷三一、卷八五一、卷九三,《事物纪原》卷八及卷九(引作《齐谐记》),《事文类聚》,《类编故事》补。”为了一个“每”字,就对九种著作详加考索,足见资料之翔实。还有《杜兰香传》“神女姓杜字兰香”条:“自此至下文‘当还求君’,据《类聚》卷七九引《杜兰香别传》辑。《说郛》卷七《诸传摘玄·杜兰香别传》文同。此句原只‘杜兰香’三字,据《御览》卷三九六引曹毗《神女杜兰香传》改。《御览》卷九六四引《杜兰香传》同,‘字’作‘名’。”作者据《艺文类聚》辑补之后,又根据《太平御览》校得“字”原作“名”。
作者在处理阙文时,广求异本,博览兼收,细加辨析,敢于对前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并详加考证,此乃实事求是、科学谨严的治学态度。
(三)对异文审慎处理,用材料说话
由于版本不同,同一内容往往会有篇幅、文字等差异。该书作者本着审慎、谨严的态度定夺文字顺序,广求异本,每改动一个字都有翔实的文献来佐证,力求恢复古书原貌、正本清源。此外,“作者原著一律保留,以小号字别之”,足见作者科学、谨严之态度。
采用对校的方法,审慎处理异文。如《汲冢琐语·晋治氏女徒》“三马当以舞僮告舞嚚”条:“原作‘三马当以告舞僮舞嚚’,文有错乱,据严、洪、马辑校本改。”对于错乱的异文,作者在这里查阅了三个版本进行校对,做到了准确、公正。又如《汉孝武故事·王母降武帝》“百余人”条:“以上二句原作‘后上杀诸道士妖妄者百余人’,此据《类说》改,《类说》原无‘者’字。”不仅根据古书更正了原文顺序,还指出了所据底本的衍字,对阅读者有很大的帮助。
据上下文意,再佐以材料考证,不妄下结论。如《博物志·猴玃》“取女”条:“取女,原作‘取男’,据《稗海》《四库全书》《百字全书》本及《寰宇记》正。《御览》引作‘取女不取男’,《搜神记》作‘故取女,男不取也’。”上文已说“此得男子气自死”,所以下文不可能再出现“取男”一说;但作者没有仅凭上下文意思就妄下结论,而是征引《搜神记》《寰宇记》等文献来佐证,更让人信服。又如《蜀王本纪·望帝》“望帝”条:“‘宇死’以下据《文选·蜀都赋》注引《蜀记》,原作‘子规’。《文选》注则谓俗云化为子规,刘知几《史通·杂说下》亦云:‘称杜魄化而为鹃。’……《事物纪原》亦云‘(杜宇)其魄化为鸟,因名’,是则《本纪》原有二说。”我们都知道子规是种鸟,但是作者还是根据其他文献,考证出原来两种不同的叫法,都是正确的。
以上这些方面,无不体现作者在考辨古小说时用力之精、涉猎之广、校勘之谨严。
二、《唐前志怪小说辑释》的价值
《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作为研究唐前志怪小说的专书,不仅为学界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古小说选本,而且其首创的辑释体例更是影响深远。文中注释旁征博引,详陈与之有关的历史传说、奇闻异事,又富于知识性和工具性。
(一)创立“垦荒”性质的辑释体
《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专录唐前志怪,解决了这方面无专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带有“垦荒”的性质。“今传志怪之作,篇秩稍完具者,强半见于《太平广记》,其他载籍引录者大抵为断章残句。清代辑逸之风盛行,罗掘更多,卓然可观,然皆肆力于一家一篇之作,未尝通盘汇求,贯穿一体者。”[2]4诚如何满子先生所言,前人大多只关注一家一篇的搜集。今天所流传下来的篇秩稍完备的唐前志怪一类的著作,可谓少之又少,更未尝有人做专门研究。
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放眼全局、广收丛残、汇纳百家”搜集整理唐前古小说的第一人。不过其在1911年辑录的《古小说钩沉》,实际上兼收志人、志怪两类小说,而且其目的是“盖意在存唐前诸体小说之涯略,非仅为志怪小说而设也。”所以,《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在严格意义上说,是专录志怪小说的第一书。
概括来说,辑释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辑佚、注解、附录的参考资料。辑佚,就是作者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广泛搜求文献资料,“勤求群书,慎事比勘,商略异同,条畅源流”,为读者提供可靠、准确的小说选本。李剑国先生博览广收,积极吸收前人辑佚的有益成果,再加上自己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里辑出了大量散佚之文,解决了很多没弄明白的问题。如《拾遗记·夷光修明》“异味进于吴”条:“以上三句原阙,据《稗海》《四库全书》本及《太平广记》卷二七二引《王子年拾遗记》补。”作者遍求其他文献,辑出了“越谋灭吴,蓄天下奇宝、美人、异味进于吴”三句,交待了小说的背景,使我们对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有了整体上的把握。又如《甄异传·阿褐》“君林”条:“以上七字《广记》原引作‘吴县张君林’,据《御览》卷九七四补。”作者根据《太平广记》辑出“吴县张牧,字君林”七字,交待了小说的主人公,使得小说更完整。注解,就是对文中出现的疑难字词、山川名物、故事掌故进行解释。如《汲冢琐语》,一开始就介绍了书名的来源“出自西晋武帝咸宁五年(二七九)所发现汲县战国魏襄王冢中”。如《志怪·鬼子》“徐元礼”条注:“廷尉,官名,又名廷尉卿、大理,秦汉魏晋均置,掌司法。”不仅交待了廷尉是秦汉魏晋间的官名,还介绍了职责——掌司法。附录的参考资料,就是注释的补充材料,以供读者查阅相关的史实和掌故。有的是补充小说的主人公,如《山海经·夸父》“夸父”条及《灵鬼志·嵇康》“嵇康”条;有的是叙录文中出现的山名、地名,如《搜神记·李寄》“庸岭”条及《搜神记·紫珪》“女坟湖”条;有的是说明文中故事、掌故,如《列异传·望夫石》“望夫石”条及《神异经·山臊》“山臊”条。李剑国先生创立的辑释体例,将三部分有机整合,构成了唐前志怪小说的资料档案,对于读者来说是极为方便的。
(二)极富知识性和工具性
“注释侧重名物制度、史实遗闻及生僻词语”[2]3,唐前的名物制度和逸事琐语,由于年代较远,理解起来较有困难。作者对小说中出现的历史掌故、节日习俗、神话传说,都做了较为详细而谨严的考辨。书中不仅资料详实、旁征博引,而且“其于同一故事流变衍化,与夫孕育后世小说戏曲者,亦梳理其大凡”[2]4,为我们学习、研究整个小说史都是极有帮助的。
唐前小说中包含很多的器物制度、上古神话等逸闻掌故,给后世学者的研究造成了很大不便。此书着重对这类词语、故事进行解释,真可谓泽被后世、影响深远。如《搜神后记·卢充》“三月三日”条:“三月三日,即上巳节,古颇重之。初为三月第一个巳日,魏以后定为三月三日。《后汉书·礼仪志上》曰:‘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曰:‘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宋书·礼志》曰:‘旧说后汉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产二女,上巳产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并亡,俗以为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于东流水上为祈禳,自洁濯,谓之禊祀。分流行觞,遂成曲水。’……自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为全面介绍上巳节,作者征引了《周礼》《韩诗》《后汉书》《荆楚岁时记》《宋书》等文献523个字来详加说明,使我们对上元节的产生、发展及后世的演变、影响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又如《搜神记·韩冯夫妇》“康王”条:“康王,名偃,战国宋国国君,前三二八年逐其兄剔成肝自立为君,十一年称王,后又称东帝,旋改王。前二八六年,齐湣王联合魏楚灭宋,杀康王,在位凡四十三年。”作者在这里交待了康王杀兄自立为君的历史事实,使我们全面地了解了康王的为人,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全文。
积极吸收前人辑佚的有益成果,又敢于打破陈规,与时俱进。“《山海经》之性质,鲁迅以为‘古之巫书’(《中国小说史略》)……按是书所记皆山川动植、远国异民、杂厕神话传说,非平实之地书,盖地理博物书与巫书之混合也。而其内容之幻诞,正又可做小说观。然其内容支离破碎,缺少情节,作为志怪小说体犹未具,只可作为准小说观耳。”[2]6在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得出此书应是地理博物的“准小说”,正确评价了该书的性质。再如《幽明录》,作者对刘义庆其人、其文,都做了不失公允的评价。称其文则“内容包罗万象,博采广收,文辞焕发,乃志怪佳制。”称其人则“若论南朝稗家巨搫,非义庆莫当也焉。”综之,我们读了这部书以后,不仅可以知道每部小说讲了什么内容,而且对小说的作者、版本流传情况、作品成就以及文学史地位,都有了很好的把握。
三、结语
李剑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作为研究唐前志怪小说的力作,填补了这方面无专书的空白。先生博览勤收,每做一处考释均言之有据、资料准确而翔实;先生秉承章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朴学传统,坚持一切从材料本身出发,其谨严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后辈学习。期待先生再出新作!
[1] 宁稼雨.六朝小说学术档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2]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 鲁 迅.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 顾 农.关于《古小说钩沉》(上)[J].鲁迅研究月刊,1991(1).
[5]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3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辑 袁培尧]
Masterpieces of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arlier Tang Dynasty Supernatural Stories-Comment onLIJianguo’sTheEarlierTangDynastyNovelsInterpretation
WANG Fangling
(FuyangNormalUniversity,FuYang236000,China)
The biggest characteristic ofTheEarlierTangDynastyNovelsInterpretationis carefully detailed textual variants, the extensive use of original materials and the overseas literature on historical facts, anecdotes, uncommon words with accurate references and materials as a supplementaffiliated in the end. At the same time, the way of interpringisscientific and instrumental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futur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mythical stories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assart; the way of interpring; scientific; instrumental
2017-04-10
王方领(1990- ),男,河南商丘人,阜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
I207.41
A
1671-8127(2017)04-00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