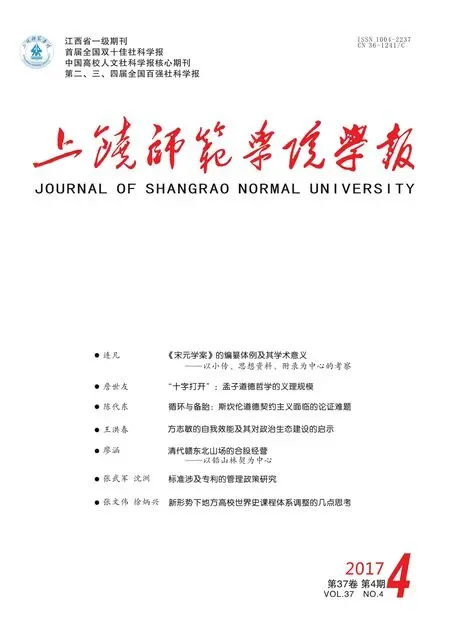“十字打开”:孟子道德哲学的义理规模
詹 世 友
(上饶师范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十字打开”:孟子道德哲学的义理规模
詹 世 友
(上饶师范学院 政治与法律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孟子慨然以传扬和发挥孔子仁学为职志,以“十字打开”的方式,向上奠定道德价值的形上基础,贞定了出自本心的仁义原则,抉发儒家“性善论”千古一脉,向下追求日常生活之善,贯通物质追求和理义追求之同欲;横向上则把“四端”推扩至五伦及万物,并展开了道德修养的工夫次第,描述了道德境界的完整进阶,从而使仁学的深层内蕴及义理规模得以敞亮,极有益于道德,极有功于儒门。
十字打开;孟子;仁义原则;性善论;道德修养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各自得孔子之道的一端,对继承和发展孔子学说的贡献都很有限。但孔子之孙子思专重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注重人心的修养;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集中发明人的本心,认为道德价值植根于人心,人心本具善端,是德性成长之根基,是能够安己、安人、安天下的道德生命大本源。为此,孟子开辟了对道德价值进行形上追求,又把形上本体与形下的人心表现贯通起来的学术理路,从而使得孔子“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的学说敞亮出来了,而展现了其仁学应有的义理规模。南宋陆九渊倡导心学,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对孟子思想的运思脉络和精神方向体验得十分真切,他说:“夫子以仁发明斯道,其言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遁,盖时不同也。”[1]398“十字打开”,意味着孟子把孔子仁学展开的方式是从纵向上,上契心之本体,下求日常生活之善;从横向上以四端为基点,推扩到五伦及万物,以先立乎其大、求放心、寡欲、养浩然之气等等作为塑造德性的修养工夫细目,并阐明了道德修养及其境界的次第和进阶。
一、奠定道德价值的形上基础
孟子首重奠定道德价值的形上基础。他认为,道德价值根源于人们的感官或者“小体”所及范围之外的本体即“大体”(心体)之中,人们要获得道德价值,就不能从人的感性偏好或者外在的物质利益中去吸取行为动机,而是要直接证觉心体本有的价值,这一价值是内在固有的,而非从外部获得的。按照康德的说法,那种“仅仅从先天原则出发阐明其学说的哲学”是“纯粹哲学”,而“如果它被限制在一定的知性对象上,就叫做形而上学”[2],所以,道德形而上学是一门关于理性的对象(即理念,它没有在经验中相应的对象)如道德法则、义务、善良意志等等的学说,而孟子的心体所蕴之价值正是超越于感性经验之外的理性的对象,也就是仁和义这两个道德原则,孟子也认为仁义原则是天所予我的,是先天原则,所以,这种学说明显属于道德形而上学。当然,形而上学的客体并不是我们在现象中能够观察到的,而只能在与感性偏好的对象相对的立场上才朗现出来。
职是之故,《孟子》开篇即揭“义利之辨”。利显然是指我们可以通过感官直接经验到的对象,而义则处于经验之外。在《孟子》文本中,确实大多不言利而只讲仁义,似乎是迂腐之论。实际上,孟子的主要观点是义在利先,要以义生利,所以,义利是有着紧密联系的。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行仁义在孟子那里,虽然其目的确实是为了利,但孟子始终强调求利行为必须得到道德价值的指导,这样才能得到健康的利、长远的利,而不会是相互矛盾、相互取消的利。
孟子认为,如果我们的行为动机只是求利,则我们的行为就将没有一种绝对的价值指导,就会处于相互算计的极端利己的状态之中,而产生无穷的冲突,大而言之,在国家内部,人们的行为就是唯利之所图,相互侵夺,于是纲纪废弛,民不聊生,统治阶层争权夺利,而至于身死国危的最坏结局。孟子叙述了这种局面:“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万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3]201这种局面就连那种一味求利的人们也是不愿意看到的。由此,孟子就凸显了与“利”相对的“义”的极端重要性:“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3]201-202从理论的角度说,“义”必定不同于求利的动机,其来源也不可能是经验的感性偏好,而只能来源于我们作为行为主体的本心之中。其功能就是对求利行为进行先天的道德价值的规范和引导。以义求利,则人们的求利行为就会在一种良好的秩序中来进行,就不会处于相互算计、侵夺之中而引起无穷的冲突,而是人们彼此都能和平地获得和拥有自己的利益,从而使大家各遂其欲,各达其情,这样,整个社会的利益就会累积起来;而且,这样的局面对百姓来说会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而使民归附:“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3]211仕立于朝、民耕于野、商贾藏于市、行旅出于途等等,都肯定是求利,但却是在仁政的框架下和仁义的感召下来求利,这样的利才会是正常的利、长久的利。所以,在仁义的规范和引导下,我们可以获得社会之善。这是仁义的社会功能,从而也表明仁义是一种道德价值。显然,人们包括国君都是愿意追求这样的社会局面的。然而,为什么许多人却不去追求呢?
这就牵涉到我们如何才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体验到仁义原则的崇高性和可贵性,以及先义后利、以义生利的必然性问题。这并不容易,因为这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道德思维方式。我们知道,感性偏好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去追求,但是,仁义道德却不是大家都会自然而然地去追求的。因为心体是处于感性经验之外的,要使人们去寻求朗现心体之善,却必须有一种思维的转向,即能够思入本体。孟子明确地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3]341。思总要思些什么,即要思维某些对象。显然,心之官所思的对象即是一种理性的客体(仁义),而非感性经验的客体(利)。所以,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201这是启发人们在求利之前,先要追求一种绝对的道德价值概念,由此,我们思维中将会朗现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孟子断言仁义原则必定只有人心通过理性思维才能获得。所以,在关于如何获得人的道德觉解的问题上,孟子始终启发人们超越感性偏好而直契自我本心的向上一维。
首先,有仁义原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由此,人才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3]298能否存养这个“几希”,也是君子和庶民的本质区别之所在。仁义原则,在人与禽兽的区别上说,是有和没有的问题,在君子与庶民的区别上说,是立志存养和丢弃一旁的问题,不立志于为仁义,就会孳孳为利。孟子这样决断地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3]364孟子认为,仁义原则是人本有的,但人同时也是会追求感性偏好满足,所以,人们很可能会因为沉溺于追求外在利益而违背仁义原则,从而陷溺其本心。但从我们本来可以具有道德自觉而挺立起自己的道德人格而言,这样做就是自暴自弃。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3]286-287可以说,在《孟子》一书中,最大量的言说是在启发人们的道德自觉和自尊,但在理论上最难阐明的也是如何才能让人们获得这种道德觉解。孟子采用的是把人的低级欲求与高级欲求进行类比的方式,来说明追求理义也可以是人的一种自然倾向,而不像康德那样认为这种欲求的动力来自何处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正如陈来先生所说,“中国哲学的本体也是真实存在,但不是外在化、对象化、静止的脱离现实,而是一个整体的存在,动态的存在,过程的全体,是人对生命体验中建立的真实。”[4]所以,在中国哲学中,本体与生命表现是贯通的,可以从生命表现中证求本体。
其次,孟子说,我们可以悦理义。在孟子看来,感性偏好的对象(利)的追求既然是人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么,对理智对象(理义)的追求也必定是人所共同拥有的,这虽然是推测之词,但却是在鼓励我们认识自己的道德本质,而且这也是我们可以从内心体证的:“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3]336刍豢之悦我口,是因为刍豢是口腹之官能追求的对象,其美味能满足我们的嗜好,这一点很好理解;至于理义之悦我心,是因为理义是在心中的,是形上的本体层面的,是心官之思的对象。显然,当心之官能沉思理义,就能够满足自己,从而获得一种愉悦感。当然,心官沉思理义,目的是为了诉诸行动,即能够出自理义而作出实践行为,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会真正享受到自由,于是能够获得愉悦感。这种愉悦感就驱动着我们去实现仁义,这就是我们行仁义的动力之所在。朱熹引程子之语说:“此语亲切有味。须实体察得理义之悦心,真犹刍豢之悦口,始得。”[3]330孟子还区分了“由仁义行”和“行仁义”,前者是沉思了理义,而直接作出要实现仁义价值的行为;后者是作出了外在的不违背仁义原则要求的行为,却不是出于仁义原则而行动。这样,就彻底确立了心体的本源地位和自律地位。康德也在这个问题上抓住了关键点,区分了“出于义务”和“合乎义务”的行为,认为只有前者是具有道德价值的,后者则不具备道德价值。康德与孟子的真正区别在于:康德认为道德法则是先天的、纯粹形式性的,不能杂有感性情感,义务是由于敬重法则而来的行为必要性,但这种敬重情感从何而来是我们不能探究的;而孟子认为仁义法则发端于人先天的良知本性即一种先天的道德情感,故而悦理义是必然的,于是我们必定能够怀着喜悦而欲求仁义,并“由仁义行”而非仅仅“行仁义”。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共同点,即都奠定了道德价值的形上基础。所以,牟宗三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视域来分析孟子的相关学说,我们认为是有重要意义的:“康德这一步扭转在西方是空前的,这也是哥伯尼式的革命。但在中国,则先秦儒家孟子早已如此。”[5]182
再其次,启发人们的仁义自觉和人格意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孟子讲了“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说明谋利而不以正道,就会带来羞耻感,因为这样做,我们会敏锐地感到我们的人格受到了贬低。从人们的这种反应里,我们也能体验到人心中有对仁义的认知,以及拥有仁义原则的本体人格之可贵。各种感性偏好对我们来说是善的,但是仁义则是最高的本体的善。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二者能够同时兼得,但在二者只能取其一的境遇中,舍前者而取后者就是一种道德性的关键决断。孟子如此激越地写道:“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3]338-339在一个具有道德自觉的人那里,在义与生命的比较中,会激起舍生取义的人格尊严感。这充分彰显了仁义原则的本源地位,也彰显了仁义原则对感性偏好追求的绝对优先性。
二、抉发儒家性善论千古一脉
孟子逢人就宣扬人性本善之说,是因为他不但贞定了仁义原则是超越感性偏好对象之上的道德理性思维的对象,从而为道德价值奠定了形上基础,而且他还要探究仁义原则的本源。在他看来,仁义原则就存在于人的本心之中,但却是以端点、萌芽的方式即“四端”先天地存在着的。这就意味着,孟子认为,人的本心的性质是一种先天的、本身固有的、对于他人表示善意的意向结构,从情感能力说,我们对处于困境中的同类会心生恻隐;从对自己行止的价值觉察来说,我们对恶事会产生羞耻感;从人际相处能力说,我们对于他人会表示尊敬和辞让;对行为动机是否具有道德性我们会有一种内在的自我理智判断。可以说,它们是道德理性。梁漱溟认为,我们确知它们都是对个人的直接感性偏好欲求满足的一种延迟,具有了空间,从而可以让理性之风吹进来。“理性恰是从本能解放出来的自由活动,旷然无所为而为”,其本然状态是一种无私的情感,“是一体相通无所隔碍的伟大生命表现”[6]。所以,四端是道德理性的特点,而非心理学或病理学的特点。可以说,梁漱溟以哲学的方式对四端的本质进行了清楚的阐述,从而使孟子的四端说之旨大明于天下。
3.精益求精,把好项目复核关。审计质量是审计工作的生命线,而审计质量提升的核心在于审计工作规范的严格执行。为确保审计工作质量,审计组长应组织运行好审计复核机制,充分履行好审计复核职责。比如,重点审核审计程序是否合规、审计内容是否完整、审计查证事实是否清楚、问题定性是否准确、审计依据是否充分、审计评价是否客观、审计建议是否可行等等,做到各负其责,层层把关,确保审计复核工作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具有善端,即善的价值的端点,从这个端点出发,使之发扬光大,及于事事物物之上,则世界上的人与人的关系,如相互对待之道、利益分配之方就都能合义,具备善的秩序。那么,孟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否正确呢?孟子对人性善的论证方式值得我们注意。我们认为,他的论证方式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可以有效驳斥有关人性恶、人性可善可恶的观点。
他首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3]239。又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3]335。这样的说法,是否是独断呢?比如荀子会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欲,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7]也就是说,荀子认为人天生有向恶的端点。实际上,从人的现实行为表现中来观察,我们的确既有善的行为,也有恶的行为,它们都应该有来自人的本性的因素作为起始点,所以,荀子的性恶论也不为无据。但是,孟子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他并不是不知道我们天生会去追求感性偏好的满足,显然,这种天然的倾向也可以看做人之本性,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看做人之本性,因为这样的本性与其他动物的本性是相同的;而真正为人所先天固有的、把人与其他动物从源头上区分开来的是人的善性。他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3]377-378他说得很明白,对感性享受的追求,是我们本性中所固有的倾向,但如果人们只是去追求其满足,则能否达到还要取决于许多内外因素,即命运。所以说,追求感性享受的确是人的本性,但其能否实现还要受制于命运的因素,故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是性;而仁义礼智等德性,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修养而获得的,只要我们能够按照存养扩充善端的方法去修养,我们命定能够获得这些德性,由于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不说它是命,而把它称作性。同时,孟子认为人心具有仁义礼智四德之端点,而且这是我们先天固有的,所以,把它看作是性,也是平凡成立的,这就把人与其他动物从本性上区分开来了,从而彰显了人之为人的道德本质。所以,孟子对道德价值进行形上奠基是其关键观点。如果没有这一奠基,他很难有效论证人性本善。在一百多年之后,荀子仍然要从追求感性偏好的欲望倾向出发来论证人性本恶,就是因为他根本不能认同道德价值的形上基础。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是人的先天的心灵情感特点,它既是人类之间的同情共感,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生命甚至物品之上,这就是仁爱之德,所以,恻隐之心是仁德之端点;而羞恶之心,是对恶事感到羞耻的价值觉察,如果推扩到人们的所有行为之中,则我们对什么是正当的(义)就会产生一种理性的追求,所以说,羞恶之心是义德之端点。这两个端点有些特别,因为孟子对仁和义的实际根源还作了另一种界说,使得这两种说法如何统一成为了一个问题。孟子一方面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3]239另一方面又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3]292-293在这一界说中,智、礼、乐等都是以事亲和从兄为内容的,足见孟子是如何重视这两个血缘关系事项的。显然,第一种说法是普遍主义的,指向所有人,即是说,恻隐之心是对所有处于困境之中的人的一种怜悯之情,而羞恶之心则是对所有恶事的一种羞耻之感;后一种说法是特殊主义的,指向自己的双亲和兄弟,即仁实际上起源于对自己父母的孝敬和服侍,义实际上起源于对兄长的敬爱和服从。那么,这两种说法如何相互贯通呢?我们认为,第一种说法是指人们均有先天的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这是一种先天的道德情感性质,它们在一种普遍的人际关系和与世界的关系中表现出来,指明它们是先天性和普遍性的善意的意向结构和倾向。第二种说法却转换了一个角度,即从人们切身的社群生活出发,指明事亲和从兄是人的自然血缘亲情的表现,所以,它们天然合理,不需要论证。它们牵涉到父母与孩子之间、兄弟之间的本然情感。因为父母和孩子是自然血亲,所以,父母自然爱孩子,孩子自然知道要孝敬父母;而兄弟之间因为有自然的血缘关系,兄长自然会关心弟弟,弟弟自然会敬爱兄长。这就是一切正常的人伦情感的起始,以此为根基,就能发展出各种人伦关系的应然要求。同时,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然血缘关系,所以,这种情感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最初是局限于自己的小型血亲共同体之中的。孟子特别重视事亲、从兄,诸事以事亲为大,全心全意地事亲,就能发展为舜那样的大孝。同时,社会国家正是由这样的小型共同体组成的,所以,“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3]287。每个家庭都治理好了,国家也就治理好了,天下就会太平了。另一方面,就广泛的人际关系而言,我们的四端就将起作用,即这种善的情感又可以外推到所有人身上,能够扩展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209的仁爱胸怀,也就是说,人们的孝悌情感可以外推到家庭以外的同类身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这两种人类同感就会起作用,事亲扩展为爱人,从兄扩展为敬长,一般来说,首先指向帮助有困难之人和不损害他人。所以,在孟子那里,这两种对仁和义之根源的界定都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在我们看来,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指向血缘亲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则指向人类同感,二者协同起作用,才能成就仁义之德,治理天下,因此,这二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更为重要是,“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成为了儒家在人伦关系上的基本观念,那就是爱由亲始,原因是人出生有自,归于一本,那就是自己的父母。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情感就是血缘亲情。这看起来似乎有局限,不似兼爱天下之人来得广泛、高远。墨家兼爱天下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打动许多人,就是因为其辞高而旨远。但是,这在孟子看来,是一种虚饰,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道德高调。因为把他人的父母和自己的父母同样孝敬,那是不可能的,一是对别人父母的爱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而且别人的父母有其自己的子女来孝敬;二是这错认了人之本,是“二本”,因为所有人都只有一个明确的双亲。墨家夷子就犯了“二本”的毛病,他主张“爱无差等,施由亲始”[3]266,似乎说得很周全,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张,他提倡的那种兼爱德性就是无根之论。孟子则主张,爱必然有差等,施爱必然从双亲开始,这是我们的本。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孟子主张“爱有差等”并不是说不要爱他人,而是说,我们只有首先对父母行孝敬,从这里培养自己的德性,我们的德性才有生长的基础。种德如种根,只有先从亲亲、孝悌做起,我们的德性才能逐渐成长起来,并推扩开来,及于所有人甚至天下万物身上,这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3]370。这种推扩能力,其实就根植于我们先天固有的、对他人表示善意的意向结构即“四端”之中。
其次,孟子指明了我们如何才能朗现人的善端,对此,他具有十分明确的方法论意识,那就是类似于现象学的还原法。见孺子将入井,我们会伸手以救,这时,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而这样做的。当我们把诸如获得现实的好处如利益、赢得好名声甚至生理反应等等后天的动机都排除掉后(“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3]239),我们仍然会去救他,那么,那种先天的、要救人于危难的纯然善良的动机就会朗现出来了。由此,我们就能贞定我们本有的善端。
孟子揭橥性善论之旨,虽然在当时和随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受到了许多批评,也引起了许多争论,比如告子的无善无不善、荀子的性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扬雄的性善恶混论。单从道德哲学的思辨深度来看,这些人性论观点都不能与孟子的性善论相比,因为所有这些人性论观点都只是从现象性的感性偏好来立论,而缺乏对道德价值的形上奠基。孟子当然知道人的自然本性中有追求感性偏好满足的倾向,但他不把这看作“性”;而对仁义的追求则需要道德理性的自觉,需要思入本体,超越把外物作为自己的动机而直接契悟本心,即所谓“存心”,这确实不容易。但很显然,仁义原则是我们本心的内容,所以,可以把这作为“性”。可以说,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不能存心,就不能彰显我们作为有理性道德存在者的本性。
我们认为,不能契悟人的本心的学派,就不可能坚定地主张性善论。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告子、荀子、董仲舒、扬雄等人不主张性善论。但是,宋明理学由于受到道教和佛教心性论的激发,而建立了儒家的心性本体论,所以,必定要在本体界来确定绝对的道德价值的来源,这样就必然要像孟子一样主张性善论。陆九渊的学术思想是“因读孟子而自得之”,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确立了本心概念,在形上层面体证到心之本体,所以他说:“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149这样,心与性的界限就没有了,从而主张心即性,性即理,所以自然而然地主张性善论;朱熹主张心统性情,心因有气禀之杂,故不能立即说心即理,而性是纯然善的,主张性即理,所以性必然是善的,因此,朱熹也是性善论的坚定主张者。他反对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只是因为他认为,日常的心因为有气禀之杂,故有时而昏。他批评陆九渊说:“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8]但真正的本体之心,则去除了气禀的昏蔽,故此时心即是纯然善的,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说“心即理”也是可以的;王阳明则更是把孟子的心学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为善去恶是良知,知善知恶是格物。”[9]117心之体之所以是无善无恶的,是因为心之体处于形上层次,所以心之体的性质不是具体行为中的善或恶,而是超越了具体善或恶的“至善”,所以王阳明也必定要持性善论的主张,这从王阳明像陆九渊一样主张“心即性,性即理”的观点中可以看得很明白。需要说明的是,王阳明所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告子所说“性无善无不善”是两回事,因为王阳明是从心之本体说的,而告子是从物欲追求说的。可以说,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中,对自宋代以来的儒家学说而言,性善论是其一致主张,这表明孟子的性善论为宋明以来的新儒家开启了一个本体论视域,奠定了一个基本价值立场,从而抉发了儒家性善论思想发展的千古一脉。
三、开启道德思维普遍性维度
孟子的伦理思想特别重视把人心之善端推扩至事事物物,从而体现了一种有根底的普遍性的道德思维方式。所谓道德思维的普遍性维度,必定有以下几个特点:1. 在人格上每个人都被同等对待,并不以现实的道德品质状况为条件,也不以其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为前提。2. 在人伦关系方面,虽然有亲疏远近之分,但是,亲疏是由血缘关系的远近造成的,这是一个自然事实,爱有差等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爱自己的亲人与爱别人是有程度差别的。亲亲应成为我们修养德性的自然情感基础,同时,这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同样的;在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上,我们需要把对待亲人的情感推扩到所有人身上,当然这是我们的“四心”发用所及的范围。3. 在道德行为的目的上,就是要使人们都能达情遂欲,能够养生送死而无憾;进一步要启发人的善心,使人们都能够行孝悌忠信,成就德性,从而敦风化俗,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是每个人的生命使命。孟子的道德思维方式明显地具有以上的特点。
首先,由于孟子在与感性偏好相对应的意义上,显露了心之本体的概念,所以,就每个人都有着形上层次的心体而言,每个人在人格上都是同等的。有人问孟子,大家都是人,为何有大人和小人之分。他说:“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3]341这个大体就是心体,小体就是五官之体。每个人都有大体和小体,决定一个人成为大人或者小人的,是道德意志的抉择。每个人都有道德人格的尊严则是肯定的。所以,就是那种以乞讨为生的人,也有自己的尊严,不能忍受侮辱。比如,孟子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3]339任何人都有这种人格意识。只要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而不让本心受到各种外在的利益的蒙蔽,则我们的人格就都能够挺立起来。他主张人皆可以成尧舜,并引颜回的话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3]254在这个意义上说,孟子否定了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观点,从而肯定了善端的普遍性。当然,他也认为,现实中确实有君子和小人之分,但其区别不在于人性,而在于是存心,还是使本心放失。只要能够求放心,并能存养扩充四端,小人也能成为君子。
其次,孟子虽然认为有些人有先知先觉,但是他也同时认为,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也是所有人的生存使命。所以,先知先觉的人,就应该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先知先觉之人应该行尧舜之道,使君成为尧舜之君,民成为尧舜之民。商汤王几次聘任伊尹,伊尹几次推辞不就,但最后接受了,他是基于这样一种使命担当意识的:“‘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3]315-316要使人们成为有道德的人,就是要启发其良知良能,就是要能从孝悌做起,进而推扩之,而成就仁义之德。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3]360道德的要求并不高远,而是简单易行的,应该启发人们从切身处做起,从亲亲、敬长做起,这样就会使社会秩序井然,人际和谐。所以孟子说:“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之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3]287孟子首先重视特殊性的亲情关系,主要是认为这是我们的德性生长之根。亲情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所以,人人都应该亲其亲,长其长,这样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仁义之德。所以,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是普遍主义的。
最后,要让所有人都能够达情遂欲,能够养生送死而无憾,这既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也是所有百姓能够治礼义、行道德的前提。对孟子而言,仁就是要尽量普遍地爱人,义就是不要损害人,行事正当合宜。对于统治者而言,仁义原则的内容就是两类:一类是要促进百姓的幸福或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求,这就必然要求统治者对自己无限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进行节制;另一类是百姓人伦秩序的建立。这就需要在保障百姓生活需要的前提下,再对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即设立庠序学校来进行教化,使百姓能够明人伦,知礼仪,从而化民成俗。
在孟子那里,其方便说法就是要与民同乐。君主好乐、好色、好货,都必须与百姓共之。这些作为生活的需求,都是应该得到满足的,关键是统治者追求感性偏好生活的满足,就要首先保证百姓的生活基本需求能够得到满足。比如,梁惠王喜欢园林,孟子就开导他说:文王也以民力经营灵台灵囿灵沼,但文王行仁政而使百姓安居乐业,所以,百姓就怀着喜悦的心情为文王出力。这是因为“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3]202,也就是说,贤能之人先促使百姓生活幸福,然后才追求自己的享乐,所以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那些残害百姓的暴君,民众就会咒骂他,他即使拥有美好园林,也是无法真正得到快乐的,“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3]202。孟子这样循循善诱,说国君如好乐,没有关系,但前提是要能与民同乐,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国君如好色,没有关系,比如文王的祖父古公甫就极其喜爱他妃子,但要能够真正遂愿,前提是要能让百姓都外无旷夫,内无怨女;国君如好货,也没有关系,以前公刘也好货,但前提是要与百姓共之,这样就不会有危害了。总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216。
但是,孟子也明白,各种感性偏好、欲望即使相同,也不足以成为道德原则,因为道德原则是独立于感性偏好的。然而,感性偏好、欲望的满足又是生活之必需,所以,能使民快乐,能组成家庭,能获取财货,就是统治者行仁政的首要关注目标。这就需要统治者具有以民为本的思想,实际上这就是仁爱之心的发用,也就是仁爱原则在行动中的对象。首先要制民之产,民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在孟子那里,就是要使百姓拥有一些固定的田产以产出一家人的生活必需品,“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3]212。所以,不能随意征用人力,要使百姓耕作有时;要省敛薄赋,不能与民争利;不能嗜好杀人,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更一步,在百姓能够得到生活保障的情况下,才能“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教育人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263,这样才能使人们明人伦,睦人际,风俗醇厚。只要这样行仁政,就必然能王天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有人会认为孟子在对待劳心者与劳力者的问题上,似乎对前者有道德要求,对后者则只是要求其劳动。实际上,他是从社会分工来说明人们中应该有劳心者和劳力者的,“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262。认为劳心者作为君主,应该专注于发明自己的本心,行仁政,使劳力者能够获得物质生活必需品;作为臣子,就应该格君心之非。而劳力者首先要致力于生产劳动,取得养家之必需,另外也要以物质产品奉养君子。但是,劳力者也是一个道德存在者,所以也要促进其道德品质的养成。孟子认为,劳力者也是人,也是其道德本质,所以,每个人都应追求达到道德自觉,修养其道德品质,因为这是每个人的生存使命。因此,孟子的道德思维方式有着典型的普遍主义特征。
四、展开道德修养的全幅规模
孟子的道德思维的落脚点是展开道德修养的全幅规模。孟子的道德修养论注重奠定品德成长的基础,并展示修养的途径、方法、进程及其境界。道德功夫的修养步骤是:存养扩充四端、求放心、先立乎其大者、反求诸己、养浩然之气等等,并展现为“善、信、美、大、圣、神”等道德境界的进阶。其核心是居仁由义,以圣人为规矩,把普遍的道德原则与自己的生命力量融为一体,达到义精仁熟。
第一,孟子的道德修养论的前提是性善论,坚持认为善本为人所固有,而非由外烁。当然,性善之说的实质在于,人心中有善端,并非已善。善端的含义,从孟子自己所指示的情况看,是指人有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3]239。也就是说,人心中有发展为仁义礼智四德的发端。虽然他有时也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3]334-335,似乎四心即是四德,但是这个说法并不是很严格的。既然人心中有德性的发端,那么,只要顺着其发展方向进行存养扩充,即可获得成熟的德性。可以说,恻隐、羞恶、辞让之心是情感性的,是非之心是理智判断性的,但在未接触事物时,它们只是一种先天的善意的意向结构,只有在接触事物之后,才会具有目的,如表现为尊重他人的人格,促进他人的幸福,促进他人的道德完善等等。比如,恻隐之心就是不忍人之心,但是只有在发为不忍人之政的措施的过程中,才能成就仁德;能对具体的恶事感到羞耻,从而不为非义,而作正当之事,才能说是有了义德;能在具体的情境下,自尊而尊人,才能说是有了礼德;能在具体的问题上判断道德是非,并且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才能说有了智德。把四端具体地落实到事事物物之中,使我们的具体行为具备道德价值,这就是推扩四端的过程,也是成德的过程。
第二,既然人心本有善端,首先就是要存此心、养此心。其具体的功夫从肯定的角度说,就是先立乎其大者,从否定的角度说就是求放心。就修养功夫而言,肯定性的功夫就是要“先立乎其大”,否定性的工夫就是要“求放心”。先立乎其大,就是说要先运用心官之思的功能,觉察到本心的崇高价值,从而使自己的道德人格得以挺立。心体(大体)挺立了,取得了优先地位,则五官之体(小体)就不会有力量来凌驾于本心之上;同时,孟子明白,人们容易从躯壳上起意,即直接追求感官享受。但是耳目之官不思,就会“蔽于物”,而“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3]341,这样追求物质享受的行为就没有方向,将流于极恶而不自知,于是,人的本心就放失了。孟子在此问题上特别警醒,认为人都本有美善之心,但是如果以物欲追求来斫丧人之本心,则本心就会失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3]337人之本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人蔽于物欲,而流于恶,并不是因为人性不善,而是因为本心走失了的缘故。在此关头,孟子努力启迪人心的自觉:我们的鸡犬走失了,一定都知道去寻找,那么,我们的良心走失了,就更应该去找回;我们的手指畸形不如人,会非常不痛快,如果我们的心不如人,就更应该恨自己。所以,知道去找回自己的放失之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自觉。找到本心之后,就需要涵养本心,加意培植,要一心主于此,持久不懈地推扩本心之善,使之生长起来,成长到正大的状态,“苟得其养,无物不长”[3]337。如果心有旁骛,或一曝十寒,则此心之善就不可能得以涵养而生长。
第三,反求诸己。每个人都有本然善心,又是行为的主体,其动机是自己的,其行为却会现实地施于他人,而且期待着自己的行为能引起他人的正向反应。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自己的善意举动得不到别人的回应,甚至会被误解,更有甚者,还有可能被人讹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选择?孟子认为在这些情况下,应反求诸己,即要反思自己是否真正怀有仁义之心,是否绝对真诚,是否有不谨慎的地方。所以,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3]283显然,只有对有正常行为模式的人,或者说可以进行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想象的人才可以这样反求诸己。爱他人而不能与他人亲近,则我们应该反思自己是否真正有仁爱之心;治理人们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则要反思我们的智慧之德是否足够;礼敬他人却不能得到他人的应答,则要反思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礼敬。所以,与人打交道,其关键还是要看自己是否做到身正。这是道德修养的一种重要方法。但对于不仁之人,则没有什么可谈的,因为其心放失,而物欲炽盛。这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仁义行为所施予的对象,只能远离他们。孟子说:“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3]285那些不仁不义的人,就是自作孽的人,他们的人生失败是自作自受。
第四,养浩然之气。由于孟子并没有在本体与现象之间划出一条鸿沟,所以性和气之间是可以相互勾连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思虑、行为都是由气推动的,故道德动机和志向就是在气中表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道德之志与气的关系。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3]231“‘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3]232这里说得很明白,即道德志向是气的统帅,而气只不过是充满在我们身体之中的。所以,我们确立了道德志向,则气就会跟随着促进它,即促使道德志向的实现。所以,我们应该坚定自己的志向,而不能任性使气。因为如果你不能坚守志向,就只会有气的盲动;如果我们把气安定了,使之不盲动,则我们的道德志向就会出现于自己的内心。但在一般人那里,作出各种行动,只是由气的冲动而作出行为,所以,其本心就会无法显露。因此,在修身上,需要一段养气的工夫。养气的目的是使气不能盲动。这就首先需要存“夜气”。所谓夜气,就是指人们在深夜思虑、行为止歇时,我们的气不与物相摩相荡,安定下来了,无物欲之杂,这时,我们的本然善心就能显露,能够产生良知善念。在此时涵养贞定,则等到第二天清晨时,那平旦之气就是清纯的,保持着气的这种清纯性质而与物相接,就能让我们的气为着促进仁义之善而运动起来。我认为,王阳明对夜气说的体认是真切的:“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9]106
但是孟子并不到此为止,他认为还要有第二段工夫即养浩然之气,那就是把气与义和道融合起来,从而使气在义和道的率领和规范下而得到无止境的涵养。气与义和道相互融合、相互贯通,从而使气得到道义的约束和引导而使生命活力具备道德价值,又使得道义原则获得生命活力的载体:“‘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3]232“‘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3]232-233孟子说他“知言”,是说浩然之气配义与道,这是正言,而非淫辞、诐辞、邪辞。因为道义是普遍的道德原则,在其规范下,则气的生长发展可以永循正道,刚健有为,因为它是集义所生;这样养气,可以没有任何限制,永远不会过度,永远不会于道德有所妨害,而是可以充盈宇宙而浩然流行。所以,孟子认为,道德理义还需要有充沛的生命力才能得以履行,养浩然之气就能促使我们的道德生命变得正大刚健。
第五,道德修养的境界进阶。道德是需要修养的。孟子把道德修养境界的进阶描述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3]378显然,这是符合道德德性逐渐发展的次第的。首先我们必须能够产生追求仁义道德的动力,也就是说要认识到仁义原则是值得追求的,要有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的道德自觉与道德追求,基于此,才能说我们具有了善的道德价值。所以,孟子通过那么多的比喻和警醒之语,来告诉大家仁义原则是值得追求的。如果我们会去欲求仁义原则,就表明我们是向善的,这就是所谓“可欲之谓善”。
假如我们能够把仁义原则存于心中而不失,即使本心有放失也能找回来,真切体证自己本有的四端,并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始终以仁存心,以义存心,则知仁义道德是实有诸己的,这才能是说我们具有真实的道德意识。比如,瞽叟和象千方百计要害舜,未得逞而对舜表现得很亲爱,舜也很高兴,难道说舜的高兴是假装的吗?是虚伪吗?孟子说,君子只待人以道,故而道义在其心中是实有诸己的,所以才是诚信的。人们可以以某些计策去欺骗他,但是却不可能用不道德的方式去蒙蔽他:“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3]309这就是所谓“有诸己之谓信”。
即使能够保存本心而不失,但我们的四端还需要存养扩充,才能成长为美好的德性。道德修养从涵养我们的自然本心和行孝悌做起,就能发展出仁义德性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3]360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要抑制物欲,这样本心善性就会得到成长。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3]382显然,孟子的养心之法不是要窒灭欲望,而是要先义后利。放纵欲望,则本心善性就被窒碍了,而无法生长;寡欲,四端就会扩充自己,德性就会生长起来。所以孟子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3]380这样我们的内心就真正被充实起来了,我们在日常行为中才能真正居仁由义。能够时时居仁由义,就是我们具备了美好的德性的标志。这就是所谓“充实之谓美”。
本心善性得到存养扩充,美好的德性生长起来了,还需要使德性流布于全身,给生命以道德滋养,其仪态、行为举止就都会焕发一种德性的光辉:“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3]362同时,他就会自然而然地以先天下为己任,培养出一种大丈夫精神:“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3]270大就大在其意志坚定,能够恭行大道,德性深厚,没有任何外在的威逼利诱能动其心性,没有任何艰难困苦能够沮其斗志,境界阔大,焕发出一种高大的道德人格的光辉。这就是“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
具有了稳定宏大的德性,就能无一毫人欲之杂,并且不会受到邪气的干扰,德性纯正,中道而立。其德性之发,能使人们无一不被其泽,无一不受到他的仁心的兴发和浸润,敦礼义,厚风俗,家庭亲爱和睦,邻里礼敬和谐,人民不知不觉地徙恶迁善。孟子在“圣”的境界中,讲了四个人,即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伯夷在商亡之后,义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清净自守,可说的是“圣之清者”;伊尹秉“一夫之不获,犹己推而纳诸沟中”的志向,自任之重如此,可谓“圣之任者”;柳下惠做任何事都必以其道,处在任何地位上都能尽其职守,在任何情况下都仁和之极,可以说是“圣之和者”;孔子则“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3]235,可谓“圣之时者”。四圣以孔子为集其大成者。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3]375认为圣人能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言谈行为感染人们,其流风遗响,能教化百代。如果圣者有位,则能够通过行仁政,广施教化,使百姓欣然向善,社会有序,风俗醇厚。所以,孟子说:“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3]359这就达到了“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的境界。关于“神”的境界,实际上就是圣人的德性圆熟,其发用施行出神入化,普通人难以知晓。所以,二程说:“不是圣人上别有一等神人,但圣人有不可知处便是神也。”[10]
孟子的道德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孟子所处时代,各种学说互竞雄长,争夺言论市场,但孟子慨然以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为职志,在与各种学说特别是墨家学派、杨朱学派和农家学派的辩论中,以“十字打开”的方式构建了自己的道德哲学的义理结构,确立了其学术理路和精神方向。孟子“好辩”,是因为不得不辩。在辩论的过程中,孟子首先确立探本之论。在道德的出发点上,以心为本,从而获得仁义原则这一形上层次的道德价值基础以及四端作为仁义礼智诸德性的端点或萌芽;在人伦关系上,以亲缘关系为本,在伦理情感上,以孝悌为本,但其根本的学理指向是天下国家的政治伦理的治理。其探本之论,是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供一种自然的、其合理性不需论证的基础。所以,孟子既能够驳斥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同时又能批判“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3]276;从性善论出发,孟子鼓励“人皆可以为舜”的道德自信,采用一种普遍性的道德思维方式,论证塑造自己的道德品质是每个人的生存使命,并且具有逻辑上升次第地描述了道德修养工夫和道德境界的进阶。可以说,孔子而后,孟子是以其纯正的仁学信念、杰出的思辨能力和深切的道德体验,为儒家的仁学展开其全幅义理规模的第一人,极有益于道德,极有功于儒门。
[1] 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M].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 陈来.仁学本体论[M].北京:三联书店,2014:13.
[5] 牟宗三.圆善论[M].台北:学生书局,1985:182.
[6] 梁漱溟.人心与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85.
[7] 安小兰,译注.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267.
[8]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77.
[9]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0] 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213.
[责任编辑 邱忠善]
“Open Cross”: Righteousness Scope of Mencius' Moral Philosophy
ZHAN Shiyo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
Mencius aimed at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Confucius' doctrine of “ren(仁)”with an academic ambition. He demonstrated this doctrine in a way of “open cross”(clearly),i.e,upward,he laid a ontological foundation for moral values,and ascertained the principles of ren(仁)and yi(义)which stem from people's conscience,and explored Confucian theory of “good nature” as an eternal vein; downward,he sought the goodness in daily life,and made wealth-seeking and morality-seeking run into the same appetite;sideward,he extended the“four stems of our mind”into the five ethical relations and all things, gave the steps of moral cultivation, and described the complete progress of moral realm. By doing so, he made clear the deep connotations of principles of ren(仁)and the righteousness scope, which greatly benefited morality and Confucian School.
open cross; Mencius; principles of ren(仁)and yi(义); theory of “good nature”; moral cultivation
2017-07-10
江西省教育科学重点课题(12ZD087)
詹世友(1964-),男,江西余干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伦理学与政治哲学。E-mail:Shiyouzhang 1964@163.com
B222.5
A
1004-2237(2017)04-0019-12
10.3969/j.issn.1004-2237.2017.0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