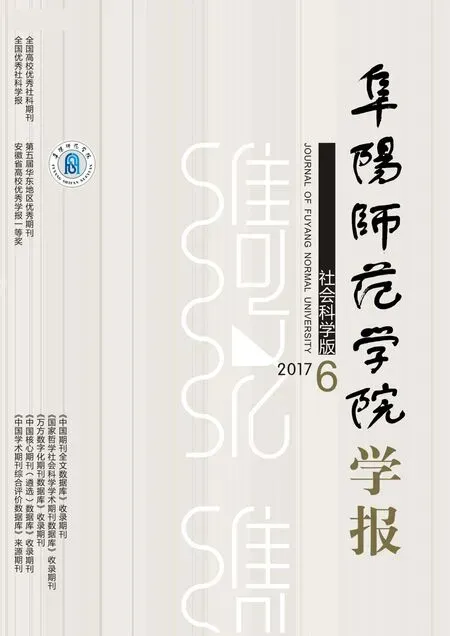《新语》对《吕氏春秋》的接受研究
王启才
《新语》对《吕氏春秋》的接受研究
王启才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吕氏春秋》与《新语》分别成书于秦即将统一的前期与大汉甫立之际,面临的诸多问题非常相似,《新语》在新政权意识形态建构的紧迫性,以何种方略治国,加强德治教化、弥补秦任法之不足,对政权的合理性与权力制衡等方面,对《吕氏春秋》有所借鉴。就具体内容而言,有32处征引了《吕氏春秋》,有些旨意、语词与吕书相近,还有的文异义同。《吕氏春秋》启下,《新语》承上,在秦汉之际大变局中,共同在意识形态、政治文化领域有探索建构之功,影响深远,洵有探讨之必要。
《新语》;《吕氏春秋》;征引;借鉴;接受
《吕氏春秋》成书于公元前239年左右,是先秦的一部重要典籍,也是战国、秦汉转折之际的一部承上启下的的重要著作,该书在汉代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若单从典籍的承传时间看,《新语》离《吕氏春秋》最近,其成书约在高祖7年(公元前200年)至9年(公元前198年)之间,相距不过三四十年。陆贾(约前240年—前170年)青壮年即生活在秦朝,《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许诺“一字千金”,轰动一时,特殊的发布方式助推了该书的广泛传播,且始皇焚书时并未禁止该书,陆贾目睹了秦的灭亡,又熟读《诗》《书》,为荀子后学,吕不韦门客中荀子后学如李斯之辈也一定不少,如此说来,被秦冷落抛弃的《吕氏春秋》,自然会引起陆贾的注意与兴趣。
“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1],秦即将统一与大汉政权甫立之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略同,吕不韦与陆贾,一个是投机商人、政治家,一个是舌辩之士,外交家、政治家,走的都不是纯学术路子,都很有远见,且务实,根据所处的时代社会量身打造的都是统治术,现实针对性都强,又都是新出炉的帝王启蒙教科书,《吕氏春秋》以“春秋”名书,陆贾曾撰写《楚汉春秋》,《史通》说:“吕、陆二氏,各著一书,唯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曰‘春秋’”[2],刘知几将二书并列,说明《楚汉春秋》受到了吕书的影响,二书相同点与影响传承关系明显,但以此为选题的寥寥,就连延娟芹《秦汉时期<吕氏春秋>的接受研究》一书也只是一带而过[3],所以有专门探讨之必要。
一、相似性问题的镜鉴
细读《新语》文本,其与《吕氏春秋》有不少相似的问题,可以看出对《吕氏春秋》的接受与借鉴,大而言之,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新政权意识形态建构的紧迫性问题。《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前夕,秦偏于西隅,任法而强,但无意识形态建设的自觉与必要的文化积累,随着秦军事政治的统一,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迫在眉睫,为此,吕不韦在三秦之地广招门客,把齐鲁等地的知识精英吸引过来,其编书的目的,按照《吕氏春秋·序意》黄帝“诲颛顼”“法天地”与《史记·吕不韦列传》“……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号曰《吕氏春秋》”的说法:一是教诲秦王;二是为即将统一的帝国提供治国指导思想;三是进行文化建设,与荀卿之徒一争高下。不管其具体著述动机是哪种,或兼而有之,吕不韦为新政权建构意识形态的自觉性是非常强的。
陆贾写书的背景与此相似。强秦短祚,大汉甫立,刘邦君臣军功出身,布衣将相,文化水平不高,对于“马上”攻取天下信心足,但对如何守成、怎样治理天下,准备不足,认识不到位,得天下之喜与重蹈强秦覆辙之忧相伴而生。高帝刘邦轻贱儒生,曾以儒冠为尿器。谋士陆贾看在眼里,忧在心中,时时在刘邦面前称说《诗》《书》,虽然弄得刘邦很不高兴,但达到了引起重视的目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陆贾与刘邦“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的对话,就是证明。好在刘邦从谏如流,将意识形态建构的任务交给了陆贾,让他谈“秦何以失天下,汉何以得天下,及古今成败之国”,陆贾不负使命,“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结集十二篇,高帝命名曰“新语”[4]2362。
(二)以何种方略治国?《吕氏春秋·慎大》说:“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新政权建立后是秉承以往,还是改弦易辙,寻求新的治国方略?怎样才能保持长治久安?这是君臣上下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经过百家争鸣,到战国后期,诸子有合流的趋势,这种倾向在《易传》《荀子》中业已显现,《吕氏春秋》看到百家的长处,以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襟,提出“用众”“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兼儒墨、合名法”[5],目的是集众长以补己短,达到最佳治理效果。
陆贾针对秦任法的缺陷,提出攻守易势,文武并用:“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4]2361,“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6]。前文说过,吕不韦、陆贾都是务实的政治家,拿来主义,改造利用,择善而从,并不恪守某一家,所以从二书主导倾向上看,都是杂家,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都有,所不同的是,《吕氏春秋》有农家遗风,《新语》有纵横家习气。
(三)加强德治教化,弥补秦任法之不足。早在吕不韦时期,对君主的专制暴虐就看得很清楚,曾激烈地进行批评,如《至忠》说:“人主无不恶暴劫者,而日致之,恶之何益”,《任数》说:“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似顺》说:“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等等,《吕氏春秋》还试图用儒家“德”“义”来纠法家之偏,如《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精通》说:“德也者,万民之宰也。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饰乎仁”,《孟春纪》说:“是月也,以立春……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适威》说:“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吕氏春秋》推崇修身教化, 2次征引《孝经》,专设《孝行览》,特别推崇孝道:“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甚至主张“知之盛者莫于成身,成身莫大于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该章还把“孝”从家族伦常范围推衍到整个社会,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在宫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7]《执一》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国为天下为。” 这些伦理政治主张,对于弥补秦任法之不足,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惜乎不韦身死书废。
陆贾是秦亡汉兴的亲历者,对秦暴政亡国有切肤之痛,“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有鉴于此,《新语》得出只有以“仁义”治天下,才能“亲近致远”,所以仁义道德是政治的根本,在《新语》中,“仁义”“德治”是最主要观点,道、德、道德和仁、义、仁义,构成系列主要概念,如《道基》说:“百姓以德附,骨肉以仁亲”,《本行》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明诫》说:“君明于德,可以及于远;臣笃于义,可以至于大”,《慎微》说:“是以君子居乱世,则合道德……修父子之礼,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道,圣从之所不失也。”可见 “行仁义,法先圣”,尚道德,是国家安定的策略和手段。《新语》也非常重视教化、忠孝,《慎微》提倡 “修父子之礼,以及君臣之序”。汉代 “以孝治天下”,在诸子中,《新语》首倡孝道,书中提及“孝”的有4次,如《道基》说:“曾、闵以仁成大孝”,《至德》说:“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无为》说:“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者哉”,《慎微》说:“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这里可以看出受《孝经》《吕氏春秋》的影响,但《新语》的孝道比《吕氏春秋》更侧重日常人伦,操作性强,容易为民众所接受,所以,对移风易俗、安定社会,意义更大。
(四)对政权的合理性与权力制衡的论证。名不正则言不顺,对于新生政权,特别是经过武力征伐得来的政权,总须有人论证其合法性问题,这是新政权能否赢得民众支持、平稳过渡的重要问题。《吕氏春秋·应同》保存下来的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对《新语》的影响甚为明显,其曰: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8]
始皇对《吕氏春秋》采取的是弃置否定的态度,但对“五德终始说” 却是接受的,表现在:为适应水德的要求而建立了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其一,改年始,定颛顼历。《吕氏春秋·季冬》说:“某日立冬,盛德在水”,“五德终始说”认为,与水德相适应的季节是冬季,始皇遂把各地混乱的历法统一为颛顼历,以十月为一年的开始,“朝贺皆自十月朔”。其二,服色尚黑。秦朝规定:“衣服旄旌皆尚黑”“更名民曰‘黔首’”。其三,“数以六为纪”。《吕氏春秋·季冬》说:“其数六”,秦朝规定:“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9]
“五德终始说”后来成了论证政权合法性的理论依据。此外,《吕氏春秋》一书中还有不少限制君主的主张与措施,如“十二纪”中规定每月君主应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都很清楚,君主若恣意妄为,必有灾咎。同样的意思,《制乐》说:“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明理》讲得更清楚:“有豕生狗。国有此物,其主不知惊惶亟革,上帝降祸,凶灾必亟。其残亡死丧,殄绝无类,流散循饥无日矣。”
这为后来的《新语》《春秋繁露》等书所继承。当然,《吕氏春秋》一书还有不少限制君主的内容,如《行论》说:“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博志》说:“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恃君览》说:“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以天子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对于愚君、暗君,《吕氏春秋》提出要让贤;对于昏君、暴君,可用武力讨伐、推翻。这些内容为后代所少有或不敢。
刘邦“提三尺取天下”,布衣皇帝,其政权的合法性何在?这是新政权所面临的难题。陆贾已考虑到这个问题,他在《新语·道基》中其实已作了回答,后文又不断地予以强化,那就是“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他援天入人,把从古至今的有道之君都视为圣人,他们都有“承天统地”“天人合策”之命,所以能“王世”而“万世不乱”。既然如此,“提三尺”而有天下的刘邦,其成功也是天意,也是圣人,其政权的神圣性、合法性不容置疑。
作为刘邦身边的重要谋士,陆贾对刘邦的个性了解很深,知道他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卓越品质,但皇帝也是人,他身上的缺点也不少,如读书甚少、傲慢无礼、粗鲁近俗、不拘小节、好女色,等等,如不对他进行规劝与限制,对社稷的稳固就很不利。但谋士怎么规劝君主,又是一大难题,陆贾从《吕氏春秋》中得到启示,抬出了天,以天制君,无疑是有效的方式之一,所以《新语》中有不少天人感应的内容,如《术事》说:“故性藏于人,则气达于天”,《明诫》说:“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慎微》说:“夫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警戒防患之意甚明。陆贾不仅说明了天人之间相互感应,而且说明了天人之间怎样感应,为何互相感应,天与政治联系紧密,这既是对《吕氏春秋》的继承,也是发展。
至于二书在贵因无为,顺势变革,反对战争,尚宽,慎刑,求贤,防微,结构的严谨清晰,语言的质朴浅显、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等方面的承继关系,限于篇幅,不再胪列。
二、语句征引
《新语》中不少内容有征引《吕氏春秋》之处,有些旨意、语词与吕书相近,还有的文异义同,兹列如下:
(1)《道基》:传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
按:这是《新语》的第一句话。此处“传”其实指的就是《吕氏春秋》,吕书《本生》第一句话就是“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东汉《论衡·感虛》引传书言:“汤遭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无以一人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传书”即指《吕氏春秋·顺民》。
(2)《道基》: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违天时,不夺物性。
按:此处与吕书“十二纪”旨意相近。
(3)《道基》:……于是后稷乃列封疆……辟土殖谷,以用养民。
按:《吕氏春秋·君守》说:“后稷作稼。”高诱注:“后,君;稷,官也……能植百谷蔬菜,以为稷。”
(4)《道基》:……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
按:《吕氏春秋·君守》说:“奚仲作车。”
(5)《道基》: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
按:《吕氏春秋·君守》说:“皋陶作刑。”
(6)《道基》:后世淫邪,增之以郑、卫之音。
按:《吕氏春秋·本生》说:“郑、卫之音,务以自乐。”
(7)《道基》:胶漆丹青、玄黄琦玮之色,以穷耳目之好,极工匠之巧。
按:《吕氏春秋·季春》说:“季春之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脂胶丹漆,毋或不良,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
(8)《道基》:骨肉以仁亲。
按:《吕氏春秋·精通》说:“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此之谓骨肉之亲。”
(9)《道基》:鲁之十二公,至今之为政,足以知成败之效。
按:《吕氏春秋·求人》说:“观于春秋,自鲁隐公以至于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
(10)《道基》:故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
按:《吕氏春秋·察今》说:“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琊;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
(11)《道基》:今有马而无王良之御。
按:《吕氏春秋·审分》说:“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
(12)《道基》: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
按:《吕氏春秋·贵因》说:“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
(13)《道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按:《吕氏春秋·适威》说:“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极也。”
(14)《道基》:故近河之地湿,而近山之木长者,以类相及也。高山出云,丘阜生气。
按:这句话虽有《易传》的影响,但受吕书的影响似更直接,《应同》说:“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召类》说:“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以龙致雨,以形逐影”。
(15)《辨惑》:斯乃阿上之意,从上之旨。
按:《吕氏春秋·长见》说:“阿郑君之心。”
(16)《辨惑》:夫众口毁誉,浮石沈木。群邪相抑,以直为曲。视之不察,以白为黑。
按:《吕氏春秋·离谓》说:“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应同》说:“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察今》说:“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
(17)《资质》:扁鹊,天下之良医也,而不能与灵巫争用者,知与不知故也。
按:《吕氏春秋·遇合》:“凡能听说者,必达乎议论者也。世主之能识议论者寡,所遇恶得不苟”,文异义同。
(18)《资质》:佞臣之党存于朝,则下不忠于君,下不忠于君,则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
按《吕氏春秋·遇合》:“夫不宜遇而遇者,则必废;宜遇而不遇者,此国之所以乱,世之所以衰也”,文异义同。
(19)《资质》:凡人莫不知善之为善,恶之为恶,莫不知学问有益于己,怠戏之无益于事也,然而为之者,情欲放溢,而不能胜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贤以自助,近贤以自辅,然圣贤或隐于田里……
按《吕氏春秋·遇合》:“故遇合也无常,说,适然也,若人之于食也,无不知悦美者,然美者未必遇;若人之于滋味,无不悦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直陈与用喻,说的都是一个道理。
(20)《慎微》:以伊尹负鼎,居于有莘之野……故释负鼎之志,为天子之佐。
按:吕书有《察微》《慎小》篇讲伊尹之事。《本味》篇有伊尹负鼎干汤的故事。
(21)《慎微》:曾子孝于父母,昏定晨省,调寒温,适轻重,勉之于糜粥之间,行之于衽席之上,而德美重于后世。
按:《吕氏春秋·孝行》说:“曾子曰:‘养有五道,修宫室,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
(22)《慎微》:若造父之御马,羿之用弩,则所谓难也。
按:《吕氏春秋·分职》说:“夫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具备》说:“今有羿、蜂蒙、繁弱于此,而无弦,则必不能中也”。
(23)《慎微》:若汤、武之君……革车三百,甲卒三千,征敌破众。
按:武王伐纣之事,除《战国策·赵策》《韩非子·初见秦》外,《吕氏春秋·简选》说:“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贵因》说:“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
(24)《至德》:不言而信,不怒而威。
按:《本生》说:“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
(25)《至德》:而欲建金石之统。
按:宋翔凤说:“‘统’本作‘功’”。《吕氏春秋·求人》说:“功绩铭乎金石。”
(26)《怀虑》:身死于凡人之手,为天下所笑者。
按:《吕氏春秋·疑似》说:“……幽王之身乃死于骊山之下,为天下笑。”
(27)《怀虑》: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故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统也……执一统物,虽寡必众,心佚情散,虽高必崩。
按:除《尸子·分篇》《韩非子·扬搉》外,《吕氏春秋·执一》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有度》说:“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
(28)《本行》:段干木徒步之士,修道行德,魏文侯过其闾而轼之。夫子陈、蔡之厄,豆饭菜羹,不足以接馁……历说诸侯。
按:《吕氏春秋·期贤》说:“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
《慎人》说:“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糁……”,《遇合》说:“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
(29)《明诫》:故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恶政生恶气,恶气生灾异。螟虫之类,随气而生;虹蜺之属,因政而见。治道失于下,则天文变于上;恶政流于民,则螟虫生于野……圣人之理,恩及昆虫,泽及草木,乘天气而生,随寒暑而动者,莫不延颈而望治,倾耳而听化。圣人察物,无所遗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鸟兽草木昆虫。
按:此段旨意与《吕氏春秋·应同》相近。又《精通》说:“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天下皆延颈举踵矣。”
(30)《思务》:是以吴王夫差知艾陵之可以取胜。
按:《吕氏春秋·知化》说:“夫差兴师伐齐,战于艾陵,大败齐师。”
(31)《思务》:久而不弊,劳而不废。
按:《吕氏春秋·本味》说:“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
(32)《思务》:是以墨子之门多勇士。
按:《吕氏春秋·上德》说:“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还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遂反死之。”
此外,就连《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陆贾回答刘邦的话:“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也可能是受《吕氏春秋·原乱》的影响:“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
还有不少关键词如天人、三王五帝、道、德、贤、仁义、无为等,二书含义相近,在《新语》书中出现频率较高。
《新语》全书12篇,篇幅都不长,却征引暗用《吕氏春秋》32次,可见其对《吕氏春秋》的推崇与喜爱。
三、认识与评价
从二书的编作者看,陆贾与吕不韦身份、个性不同,结局也不同。吕不韦门客三千,仲父侯王,权倾朝野,知进难退,亢龙有悔,自杀身亡,树倒猢狲散,后世毁誉不一。陆贾“优游”,多次深处矛盾漩涡,从容淡定,进退自如,纵横家、道家的才华与洒脱,全身而终,赢来后世的敬仰与赞赏。个中原因,除了其智慧与才华外,吕不韦的前车之鉴,也不无关系。
从二书对当世的影响看,《吕氏春秋》宏阔的视野,渊博的知识,齐整的架构,东汉桓谭用了一个“造”字进行赞赏;书成后轰动一时的传播方式,影响很大,始皇虽摈弃该书,但接受了“五德终始”、教化、养生等对其有利的东西,也并未焚毁该书,所以该书成为先秦唯一一部有确切记载成书年代,保存最完整、窜乱较少的书籍。《新语》可谓命题作文,其主题为刘邦钦定,虽有总体构思,但是分批写成的,每成一篇以奏议的形式上奏,在朝堂上当众宣读,受到激赏,君主称善,左右欢呼“万岁”,结集后皇帝赐名“新语”,对刘邦、曹参等产生了较大影响,《汉书》说:“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10],把陆贾造《新语》与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等并提,可见其在当时的作用之一斑。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即将统一的前夕,是杂家的代表作,《新语》成书于西汉初期,是西汉第一部带有杂家色彩的子书。二书以治国理政、建构意识形态为主,都带有针对性、实用性、综合性的色彩,因接受对象秦王嬴政、高帝刘邦文化水平都不高,所以都带有文化启蒙、政治教科书的性质,其理论深刻性、哲学思辨性并不怎么突出,时过境迁,二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冷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秦亡汉兴,“汉承秦制”,过秦戒汉成为一时的主题,在秦代被摈弃的《吕氏春秋》自然受到人们广泛的重视。由于陆贾的青壮年是在秦度过的,他年轻时在饱读《诗》《书》的同时,对先秦其他典籍如《周易》《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战国策》《左传》《春秋谷梁传》《孙子兵法》《鬼谷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都曾广泛涉猎,这从其著述征引和说辞中约略可以看出。从最容易接触到的当代作品看,应该是《韩非子》《吕氏春秋》。前者因强秦的速亡名声不好,后者被秦摈弃冷落,反而激起人们的兴趣,在汉初刘邦君臣布衣、军功出身的情况下,熟读经典能著述的,谋士陆贾是第一人,所以陆贾应该是汉代《吕氏春秋》的第一个接受者与传播者,《吕氏春秋》在汉代的影响,一是通过“十二月令”;二是通过《新语》的广泛征引、借鉴,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陆贾以后,贾谊的《新书》、奏议等作品受陆贾的影响明显,《新书》征引《吕氏春秋》虽少于《新语》,但“过秦”主题已经突出,贾山、晁错紧承其后,共同把“过秦”推向高潮。晁错的《贤良对策》、奏疏、《杂篇》,受《吕氏春秋》“十二纪”、《上农》等的影响依稀可见,“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11]。”值得一提的是,受《吕氏春秋》影响下的黄老思想、《新语》的因顺无为等主张,对汉初江山的稳固、“文景之治”的形成,是作了很大贡献的。
胡适提出,《新语》“乃是一种‘杂家’之言”“故最应放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间”[13],这是看出了《新语》在二者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吕氏春秋》本身就很重要,《新语》所征引、改造了的《吕氏春秋》内容,更加适应汉初的意识形态建构,这对《淮南子》的启迪意义较大,《淮南子》于是将《吕氏春秋》作为写作的蓝本,从构思、体例到词语征引,处处都有《吕氏春秋》的影子,单从语句征引看,就多达183次以上。《淮南子》以后,受《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深刻影响的是《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以“春秋”命名,其天人古今的思维模式,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内容,主张德主刑辅、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品格,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与《吕氏春秋》《新语》《淮南子》等的继承嬗变关系。以后东汉王充《论衡》批判、否定“天人感应”论,又追溯到《吕氏春秋》所记载的史料,并以此作为批判的靶心。
司马迁的《史记》对《吕氏春秋》与《新语》利用借鉴较多,相关论述已有,此不赘述。《史记》对陆贾《新语》《楚汉春秋》的接受,还可以作深入研究。《史记》为陆贾立传,不少重要的史料,来源于《楚汉春秋》,刘知几说“述楚汉事,专据此书”[11],可见陆贾的影响是很大的。
本文限于篇幅,对《新语》接受《吕氏春秋》的情况,以及《新语》对后世的影响,只点到西汉中前期为止。总的来说,前有《吕氏春秋》启下,后有《新语》承上,在秦汉之际的大变局中,共同在意识形态、政治文化领域有探索建构之功,影响深远,洵有探讨之必要。
[1]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8:11.
[2]刘知几.史通·题目[M].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4.
[3]延娟芹.秦汉时期《吕氏春秋》的接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9-50.
[4]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2 362.
[5]班固.汉书·艺文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 742.
[6]王利器.新语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6:44.
[7]吕氏春秋·孝行[M].高诱,注.毕沅,校. 徐小蛮,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68-269.
[8]吕氏春秋·应同[M]. 高诱,注.毕沅,校.徐小蛮,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51.
[9]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2011:203.
[10]班固.汉书·高帝纪第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62:61.
[11]刘知几.史通·杂说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43.
[12]胡适.胡适全集:第六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82.
On the Aceptance ofto
WANG Qi-cai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Anhui)
andare written in the early period of Qin and Han Dynasty respectively. And the problems the two books are facing seem very similar.makes a great difference to thein the urgency of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regime,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the strategy,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making up for any deficiencies in the law of the Qi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power and power balance, etc. In terms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there are 32 signs inthat have been drawn from the, some of which are similar to. The two books serve as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and they have a far-reaching effect on the area of ideology, politics, and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changing time between Qin and Han Dynasty. Thus, it is worthy to be discussed.
; Quote; Use of reference; Acceptance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6.12
I206
A
1004-4310(2017)06-0057-07
2017-09-20
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宋以降文献征引《吕氏春秋》研究”(16YJA751023);2016年安徽省高校学科(专业)拔尖人才学术资助重点项目(gxbjZD2016074)。
王启才,安徽阜阳人,阜阳师范学院教授,博士后,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