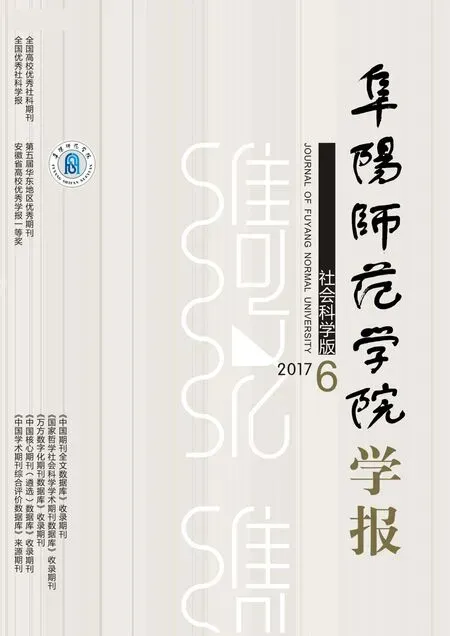武则天与初唐文学——以制举、铨选为中心
卢 娇
武则天与初唐文学——以制举、铨选为中心
卢 娇
(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00)
前人多关注武则天通过进士科对文学产生的影响,而忽视了其制举、铨选对文学的作用。其改制之前,制举和铨选在相当程度上都偏向于文学人才,这提高了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力。特别是武则天曾对制举寄予了选拔经邦济世之才的希望,改制后又极力发挥制举试策咨询时政的作用,这又在社会上引起了畅言王霸大略的风气,促使了文人精神风貌的转变。武则天改制前后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客观上抑制了藻丽文风的进一步发展,使之朝着简洁流利、富有气势的方向发展。
武则天;制举;铨选;文学
学界对武则天与唐代文学关系的研究,多以科举为媒介,特别是依据她对进士科的态度来考察其人才观,进而以此探讨其对诗歌发展所起到的具体导向作用(1)。实际上,武则天的人才观不仅体现在进士科,也体现在制举、铨选等环节,这后二者也是科举的一部分,也对士人的取向产生重要影响。
对“科举”的通行理解是“分科取士”,并专指以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那些尚未入仕为官的人才,使之获得进身的资格,唐前期由吏部主持,开元二十五年(737)后长期由礼部主持,总体是一种“初级选拔”。而陈飞先生在《唐代试策考述》中则提出了“广义科举”概念,泛指不同机构所有以分科考试的形式进行的人才选拔,可以是初级选拔,也可以是高级选拔,具体包括礼部的“科举”(进士、明经等常科)、吏部的“科目选”(开元年间始推行)、尚书省与中书门下的“制举”,以及其他方式的取士选官[1]286-287。在这样一种“大科举”观下,君主的人才观即可比较全面地反映在其科举态度中。因而在进士科之外,还应同时关注武则天对制举、铨选等选举方式的态度。
一、制举
除“广义科举”外,陈飞先生还在其著作中引入“广义制举”概念,将常科以外的所有与天子关系密切的举人活动都纳入制举[1]223-227,征举及响应天子号召的所有荐举包括自举均可视之为制举。
一般认为正规的制举考试科目通常只有试策一项,直至天宝十三年制举中的辞藻宏丽科才有了试诗的情况出现:
天宝十三载十月一日,御勤政楼,试四科举人。其辞藻宏丽,问策外更试诗赋各一道。(原注:制举试诗赋从此始)[2]1 393
制度化的制举考试或许确实至此才有了试诗,但早期的制举,方式比较灵活。隋代即有多次制举,均由五品以上京官及诸州总管、刺史举荐,但未明言考试。至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的下诏举人,除中央和地方官吏举荐外,“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己具陈艺能,当加显擢,授以不次”[3]32。也未明言考试。太宗贞观十三年(按:《唐会要》曰十五年)甚至曾“欲令人自举”,但最终因恐“长浇竞之风”[2]914而没有施行。可见早期的制举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制度[4]。即便明确有了考试,在应举人数不多、规模不大的情况下有时还采取对话、口试的方式。太宗即曾将诸州所举应孝廉茂才科的十一人“引入内殿,借以温言,略访政道”,在口试表现不佳时才“令于内省,更以墨对”[5]7 426。后来也有高宗亲临制举考试的记载,一次为显庆四年,“(显庆)四年春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6]79,当时没有交谈和口试环节;另一次为永隆元年(681),“高宗御武成殿,召诸州举人,亲问……员半千越次而进曰……高宗甚嗟赏之,及对策,擢为上等”[6]5 014-5 015。此次员半千为应岳牧举,高宗先施以口试,后又加以笔试试策,并因员口试表现佳而将其在笔试后擢为上等。武则天亲临正规的大规模的制举试也只有一次记载,即《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7]290此次亦无口试的记录。确实,当制举规模扩大以后,口试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但在规模较小或专征时,很可能有当面交谈的机会,这样君主根据应试科目、应试人特长或个人爱好随机考查其才学便成为可能,理论上也就有了试诗的可能性。事实上,也确有试诗的记载:
李义府侨居于蜀……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咏乌,立成。其诗曰……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7]281
虽然李义府这次属于荐举,但亦可称为“广义制举”。即便在那些有明确科目的制举中,诗歌也有用武之地。
麟德元年(664)七月丁未诏:
诏宜以三年正月,式遵故实,有事于岱宗……其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天下诸州,明扬才彦,或销声幽薮,或藏器下僚,并随岳牧举选。[2]96
此次要选拔的是那些“销声幽薮”“藏器下僚”的人才。诏下后,员半千上《陈情表》,自夸文才可比曹植、枚皋:
若使臣七步成文,一定无改,臣不愧子健。若使臣飞书走檄,援笔立成,臣不愧枚皋。陛下何惜玉阶前方寸地,不使臣批露肝胆,抑扬词翰?请陛下召天下 才子三五千人,与臣同试诗、策、判、笺、表、论……[3]1 682
虽然员半千此次上表没有结果,但起码说明在当时制举确实是有试诗的可能,起码诗是可以成为参加制举考试的优势的(并且还列在首位),(2)这主要是高宗、武后执政以来尚文风气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武则天也有当面试诗文的记录,
唐上官昭容……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8]
上官婉儿以罪人之后而得到武则天许可成为高宗才人,后来又成为武则天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其起始原因即在于其“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2013年8月出土《大唐故昭容上官氏墓志铭并序》)的文词才华,武则天所试也极有可能包括诗。而在杜审言受周季童、郭若讷构陷免官后:
后武后召审言,将用之,问曰:“卿喜否?”审言蹈舞谢,后令赋《欢喜诗》,叹重其文,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9]3 735
杜审言的重新起用完全是因为武后“叹重其文”,即其诗的缘故。郭震由于在地方上落拓不拘小节而名声在外,证圣元年(695)[10],武则天召见郭震本欲诘之:
语至夜,甚奇之,问蜀川之迹,对而不隐。令录旧文,乃上《古剑歌》,其词曰:……则天览而佳之,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阎朝隐等。遂授右武卫胄曹、右控鹤内供奉,寻迁奉宸监丞。[3]2 353
从郭震所授官职来看,完全得力于其诗。并且武则天主动“令录旧文”,索其为文又“令写数十本,遍赐学士李峤、阎朝隐等”,一方面可见武则天确实颇好“雕虫之艺”,重视文才,另一方面对郭震来说此乃莫大的荣耀,使之成为其他文人的一个楷模,李峤甚至还写了一首《宝剑篇》来和郭震诗。
以上所举都是诗歌成为君主对人才的一个考核项目,实际上,制举与诗歌的关系并非仅仅停留在有可能成为正式试项的层面上。只有在征举、荐举或谒阙自举,包括规模较小的狭义制举的口试环节中,直接考查诗歌的可能性才比较大,这自然能激起全社会对诗歌的普遍热情;而在那些有明确的试策科目的狭义制举的笔试中,虽不直接考查诗歌,但其取人标准和倾向也会对诗歌产生其它方面深远的影响。
隋时制举取人,主要是“五陵豪杰”“公卿将相之绪余”“侠少良家之子弟”(大业十三年)。高祖时的标准则是“奇才异形”(武德四年)、“志行可录”(武德五年)、“高年硕学”“直言极谏”(武德九年)。太宗时虽渐渐有了“文词秀美”(贞观十一年)、“文章秀异”(贞观十五年)、“鸿笔丽藻”(贞观十九年)、“含章杰出”(贞观二十一年)、“游情文藻”“下笔成章”(贞观二十三年)这些文学性科目,但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仍是“至孝纯著”“正直廉平”“言行忠谨”“志行修立”“廉洁正直”之类对德操上的要求。高宗即位初的几年,制举科目也多为“景行淳良”“志烈秋霜”及孝义之士、经学之士,取士的目的“也只是挑选‘材堪应幕’‘堪膺教胄’一类吏员、教官,或补充学艺、文藻、音律、历数方面的专门人才”[11]226。当武则天逐渐掌权之后,制举的取士标准和目的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诸科名目上来看,出现了“才蕴廊庙”(仪凤二年)、“才堪将相”(调露元年)、“文可以经邦国”“武可以定边疆”“蕴梁栋之弘才堪将相之重任”(垂拱元年)、“堪为宰相”(长安四年),这就将制举由倾向于选拔技能型专门人才逐渐提高到可以选拔高级官员,制举在选举制度中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以至出现了张鷟那样登进士第后又多次应制举的情况。另一方面,在武则天的影响下,制科也一度给予文学人才以一定的关注,诸如“藻思清华”(显庆五年)、“词赡文华”(乾封二年)、“词殚文律”“文学优赡”(上元三年)、“藻思宏赡”“词擅文宗”(调露元年)、“文藻流誉”(光宅元年)、“蓄文藻之思”(载初元年、天授元年)、“文擅词场”(大足元年)。不过与进士科不同的是,制举一般都与举荐相关,所以对德操是有要求的,加上它的科目,衡量人才的标准往往主要有三个方面:节操高尚,文思敏捷,雄才大略。也正因为需要举荐,制举导致的干谒之风远甚于进士科。因而才子们在干谒时一般就围绕上述三个方面来“露才扬己”“自媒自衒”,而且特别强调自己的经邦济世之才,“高谈王霸是当时士人干谒的普遍时尚”[11]224-225。如王勃就自谓能“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12]164。在这种风气下,士人关心时政、议论时政也就理所当然了。加之武则天又于垂拱二年(686)铸铜匦,南面为“招谏”,令言朝政得失者投之。万岁通天元年(696)又 “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极言时政得失”[6]125。所以就出现了诸如孙嘉之“垂拱、载初之际,始诣洛阳,献书阙下,极言时政,言多抵忤”[3]3 182这样的时代典型。试想如果没有武则天在制举中对经邦济世之才的期许,任其仅停留在选拔技能型专门人才的层面,没有她对“极言时政”的一再倡导,就不会形成这种全社会高涨的高谈王霸的风气及士人为君辅佐的自信心、进取心,盛唐诗歌中那动人的天真和自信也就无从谈起。如果说进士科的改革已经培养了普通士人的功名心,那么武则天对制举的改革则更直接激发了士人直抵卿相、致君尧舜的济世热情,影响了诗人们的精神面貌,从而影响到盛唐诗歌气象的形成。
不过不可否认,在武则天改制之后,制举中的文学因素较之前明显降低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的名目大大减少(前文所列文学名目多为改制之前),一是从制策的命题来看更侧重于咨询时政,这就使仅凭辞采难以在制策的对策中脱颖而出。在太宗、高宗朝,制举试策主要考察对儒家思想等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调露元年(679)高宗在亲试岳牧举人时问:
兵书云“天阵、地阵、人阵”,各何谓?
此次应举的员半千对曰:
臣观载籍,谓天阵星宿孤虚也;地阵山川向背也;人阵偏伍弥缝也。臣以为不然。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三军使兵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利,此人阵也。若用兵者,三者去矣,将何以战?
后高宗又问:
皇道、帝道、王道,何以区别?朕今可行何道?[5]7 426
从高宗所问及员半千所答来看,考核的是基础知识的运用,并没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再看武则天的策问:
垂拱四年(688)策词标文苑科问:顷者荆郊起祲,淮甸兴祆,朕惟罪彼元凶,余党并从宽宥。今敬、贞之辈,尤蕴狼心,不荷再生之恩,重构三藩之逆,还婴巨釁,便犯严科。岂止杀之方,乖于折衷;将小慈之泽,爽彼大猷?[13]85
此策的背景是,徐敬真因参加徐敬业叛乱而被流放,后欲逃奔匈奴,事发被捕押回洛阳,然其企图诬告魏元忠等朝士以免死,最终于永昌元年(689)八月被诛。策问反映的即是武则天对徐敬真一事和用刑宽猛的反思,策问的问题非常具体,有很强的咨询时政的意图。此次对策张说为天下第一。再如:
永昌元年(689)策贤良方正科问:至于考课之方,犹迷于去取;黜陟之义,尚惑于古今。[13]91
此问咨询的是很现实的官员选举方法,张柬之对策因切中时弊而被称善。显然,对这样的问题,如若再用类似上官仪在应进士科策问时“让袂九流,披怀万古,揽玉箓之奥义,观金简之遗文,睹皇王临御之迹,详政术枢机之旨”[13]11那样铺排的语体来回答,就很不切当也很不称旨了。策文的评价标准相应地由重文辞变为重识见。
可以说,唐代制举比进士科与时政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倾向是武则天奠定的。武则天改制以后更加倾向于通过制举选拔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吏干型人才。确实,改制后制举及第的人才当中有不少后来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对进士科的期望已经降低,其间进士及第者多数在政治、文学上表现平平。究其原因,一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武周朝各种政治矛盾比较突出,空前需要吏干人才,武则天甚至在天授三年(692)开试官之制,试图从实践中选拔人才,也算是对以言取人不利于不善言辞者的一个补救措施。另一方面则是因制举名义上是天子主持的选人,比常科更能达到“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的效果。
从武则天参政到改制期间,制举表现出了对文学人才的倾斜,文坛变得更加讲究辞藻的铺排和堆砌。但改制后制举考核内容的改变,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抑制“浮虚之余辞”的作用,如武则天对张说的评价是:“文思清新,艺能优洽。”[14]此时宫廷诗坛的诗风也有别于高宗在位时期,而是朝着更加简洁流畅的方向发展,文学上的“皮肤病”有明显好转,这与武则天对科举的改革不无关系。
虽然改制后在政事上武则天更多地倾向于吏干型人才,但文学之士尚有其它用武之地。垂拱二年(686)所铸铜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15]。这表明,武则天如果见到欣赏的文辞作品,还是会不次嘉奖的。如垂拱四年(688),“明堂初成,(刘)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6]5 013。又:
洛京福先寺仁俭禅师……唐天册万岁中,天后召入殿前。……翌日,进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览而嘉之,厚加赐赍,师皆不受。又令写歌辞传布天下,其词并敷演真理,以警时俗。[16]
圣历中,则天幸嵩岳,见(崔)融所撰《启母庙碑》,深加叹美,及封禅毕,乃命融撰朝觐碑文。自魏州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6]2 996
这类因诗文获嘉奖和那些武则天主动索取诗文、试诗文的事迹一样,都促使社会上形成了热衷诗文创作、仰慕诗文作者的风气,诗人们甚或养成了以诗相尚的心理: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刺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17]
身为武官,竟也附庸风雅,虽然其诗仅是“趁韵而已”,但折射出诗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及为众人所向往的社会现实,更不用说宫廷诗人所受的礼遇和优待了,且看杜甫《赠蜀僧闾丘师兄》:
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18]
虽然当时宫廷诗人们一般不过任著作郎或在控鹤府、奉宸府任职(当时政治上受重用的多为吏干型人才),但受到的优待恐是普通三省官员难以比拟的。正是由于把握住了武则天依然欣赏文才的心理,当上官婉儿忤旨当诛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以诗赎罪:
天后每对宰臣,令昭容卧于床桾下,记所奏事。一日宰相李(原注:“忘名”)对事,昭容窃窥,上觉,退朝怒甚,取甲刀箚于面上,不许拔,昭容遽为《乞拔刀子诗》。[19]
《新唐书》本传谓其“自通天(696)以来,内掌诏命”[9]3 488,则此事应发生在通天以后。因而尽管武则天改制前后对科举用人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并不妨碍诗歌在士人中持续的吸引力及社会对诗歌的热情。天授三年(692)薛谦光上疏时即谓“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敭,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6]3 138,即为应制举而“上启陈诗”的干谒仍在继续,社会对诗歌的热情并未衰减,加上武则天倡导而成的畅言王霸大略的风气,这些都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铨选
常科举子在及第后即可获得出身,制举及第则一般可立即授官,只有那些排名靠后的举子有时只赐出身而不授予官职,他们都要和常科及第举子及考满罢秩的六品以下的旨授官一起,参加吏部的铨选,通过后方可授官。关于铨试的内容,《通典》载:
其择人有四事:一曰身,(胡注: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胡注:取其词论辩正)三曰书,(胡注: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胡注:取其文理优长)[20]360
这里相当于以身、言、书、判设科,所以姑且视之为“广义科举”。这四科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试判一项。试判的目的本为考察吏治才干和断案水平,最初是取一些典型案例、疑难问题来考试,采用骈文的形式,录取标准是“文理优长”。但正如《大唐新语》所言:
国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选,主者将视其人,核之吏事。始取州、县、府、寺疑狱,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后日月淹久,选人滋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以为问目。其后官员不充,选人益众,乃征僻书、隐义以试之,惟惧选人之能知也。[7]305
即随着选人的激增,为增加难度,渐渐发展为在经书古籍、僻书隐义中寻找题目,录取标准相应发生了变化,主要考核经书学问和文辞水平,这样其实就违背了试判的初衷,故马端临《文献通考》:
按唐取人之法……今主司之命题……选人之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盖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21]
然而这种倾向从何时开始?武则天时期的试判究竟是以考察吏干之才为主,还是已经倾向于文辞?实际上,“选人滋多”与注官有限的矛盾在太宗朝后期尚不甚突出,据《唐代铨选与文学》,贞观时每年参加铨选的有数千人,到高宗即位初则超过万人,而至武则天时期则达数万人,垂拱后甚至多达五万人[22]104-105。选人越多淘汰率越高,试判的内容就越偏离吏事而趋向经书学问和文辞水平。《容斋随笔》亦谓:
唐铨选择人之法……以判为贵,故无不习熟,而判语必骈俪,今所传《龙筋凤髓判》及《白乐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数十语……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属一字亦可。[23]127
《龙筋凤髓判》乃张鷟所作,张上元二年(675,一说调露元年679)中进士,后中八科制举。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此集凡百题,自省台、寺监、百司,下及州县、类事、属辞,盖待选预备之具也。”[24]《玉海》谓:“《龙筋凤髓判》十卷,张鷟撰,杂抄唐人判语,分门为类。”[25]其编撰目的盖为选人试判提供范本。可见武则天时期至盛唐前期,试判还是如《龙筋凤髓判》所反映的一样根据一些典型案例来命题的,但因用的是骈俪文体,并有200字左右的篇幅,非常适合文士逞其才华,因而颇有利于读书善文者。故洪迈又谓《龙筋凤髓判》:
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是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如白乐天《甲乙判》,则读之愈多,使人不厌也。[23]358
确实,白居易的判词具有逻辑清晰、分析透彻、长于说理的特征,以讲道理、明是非为宗旨,语言比较流利朴素,而《龙筋凤髓判》则大量摘取文献典故,语言又比较缛丽,反映了初盛唐之际的“当时文格”。而武则天时期,更是竞尚词藻的文风占据文坛,其判文风格也必如《龙筋凤髓判》,其藻丽程度必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在张鷟之前,王勃也撰有《百道判》,但宋时业已失传[26],不过从王勃的骈丽文风来看,《百道判》的文风和性质也都应与《龙筋凤髓判》类似。这都说明在武则天时期,吏部试判是讲究文辞藻丽因而适宜于习文者应考的。所以杜审言的恃才傲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矣!”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6]4 999
其“书迹”谓考试四项之中的“书”,而其“文章”即是指所试之“判”。虽然关于此事发生的时间及真实性都有争议,但将“判”比拟屈、宋文章,无论如何都反映出当时候选人并非将“判”作为一般的公务性实用文体来看待,而是将其作为逞才使气的文字载体。当然,这同时也体现了时人包括典选官通过“判”来衡量候选人文辞才华并以此作为铨试成绩重要依据的社会风气。特别是为了缓解吏部在选人滋多情况下不断加大的工作压力,在规定糊名试判的同时武则天还曾抽调弘文馆学士来参与吏部选人的考判[27],后又认为此法“既乖委任之方,颇异铨衡之术”,其效果还不如前法,于天册万岁元年(695)下敕“其糊名入试,及令学士考判,宜停”[2]1 358。在学士考判的情况下,铨选试判重经史学问和文辞才华的风气必然会愈演愈烈。此时停止糊名入试及学士考判,对判文的褥丽之风应亦有一定的警醒作用。武则天此举与改制后人才选拔上的一系列改革有关,即后期总体来说在政治上更加倾向于吏治型人才,委之以政事,而对文学人才亦不偏废,使之在日益增多的宴会、出游等活动中发挥作用,因而宫廷内部的尚文风气并没有衰退。
正因为终武则天时期朝廷上下都洋溢着崇文的氛围,典选官也倾向于以文辞取人,因而出现了候选人为谋官或改官以自己的文章干谒吏部官员,甚至吏部官员直接向候选人索要文章的现象。如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骆宾王《上吏部裴侍郎启》及《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等。特别是骆宾王在后一启中还提到“昨引注日,垂索鄙文”[28],即时为吏部侍郎的裴行俭曾主动索要骆宾王的文章,于是后来献《帝京篇》一诗。因而王勃说:
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才于简牍之际……(《上吏部裴侍郎启》)[12]131
王勃明言裴行俭在铨试选人时以诗赋为先决条件,并认为以此选人不足取。从王勃启的口气来看,裴行俭也曾向其索要过文章,因而才会说:“尝著文章,非敢自媒,聊以恭命。谨录《古君臣赞》十篇并序……”[12]133干谒书启并附录诗文的现象可想而知在当时比较普遍。所以葛晓音先生说在唐初到进士试诗赋以前,“干谒成为诗人最重要的诗歌社交活动”[11]228,其对诗歌发展产生了很强的刺激作用。但这种铨选看重文辞的现象在当时招致的批评并不止王勃所言,垂拱中魏玄同上疏:“以刀笔求才,以簿书察行,法之弊久矣。”[20]407也是对以言取人的否定。
当然,唐代流外入流的官员人数大大超过因科举而获得出身的人数。所谓“流外”,包括“自勋品以至九品,以为诸司令史、赞者、典谒、亭长、掌固等品”[6]1 803,他们在入流之前也要参加吏部单独的“流外铨”,所试也为判。故《通典》谓:“又勋官三卫流外之徒,不待州县之举,直取之于书判,恐非先德行而后言才之义也。”[20]409参加流外铨的是“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官员之子,以及各州、县的佐吏”[22]204,他们还必须要有书法、计算或通晓时务的优长。当入流以后,就和其他流内的前资官和及第举子一样参加通常意义上的吏部铨选了。但实际上,这部分流外出身的吏员在仕途上会受到种种限制,无法与科举出身的文人相比。特别是武则天于神功元年(697)下敕:
量才受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差等。比来诸色伎术,因荣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遂使器用纰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29]
即流外官入流以后,其升迁和改任不得悖离其原本的伎术特长,并且有最高官职限制。这样一来,在吏部授职时,科举出身的举子和前资官的“就业空间”和前景要远大于流外入流的官员,并且那些清要职位或品秩较高的职位只会留给前者,这就使得满朝高级官员的出身逐渐汇归一途——科举,对未入仕的普通人来说,习天文、音乐、医术、卜筮等伎术远不如习文有前途。因为不仅在举人的进士科重文词、制举诸科也有不少倾向于文词,就是吏部授官时也会倾向于习文者,这自然就大大抬高了文人包括诗人的地位和竞争力,促使全社会尊重仰慕文人,也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进取心。
可见,在铨选领域,诗赋文辞特长是典选官看重的重要方面,向吏部官员献诗献赋也成了一时之风。这大大提高了文学的影响力。
结语
仅仅以进士科为媒介来探讨武则天的人才观及其对文学之影响是不够全面的,制举、铨选环节也体现着武则天的用人标准,这对文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创造了一个相对有利于文学人才晋升和发展的社会环境,直接引发了社会对诗赋等文学作品的研习和创作热情。在制举中,如果有口试环节,诗歌很可能会成为直接考核的内容。即便在笔试中,也有诸如“词赡文华”“词殚文律”等专为文词人才而设之科。此外,武则天还创造机会让士人投匦献诗献赋,甚至主动召见那些有文名的诗人并加以褒奖。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诗人直接因个人的诗文作品获得武则天的欣赏和擢拔,使他们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这都提高了诗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促成了社会对诗人价值的认可及对诗文的热衷。而在铨选的最重要科目试判当中,由于使用骈体,整个上层社会包括典选官都往往倾向于以文词取人,因而判文的写作又自然沾染了崇尚藻丽的风气,非读书习文者不善为。 并且吏部在对官员任命时,对流外入流的各类专业伎术人员有种种限制,而对科举出身的举子和前资官则相对比较宽松,武则天《厘革伎术官制》的诏令客观上起到了倡导士人走科举道路、提高科举文人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力的作用。
2.引发了诗人的功名心和政治热情。武则天曾对制举寄予了选拔经邦济世之才的希望,改制后又极力发挥制举试策咨询时政的作用,着力选拔吏治型人才,倡导百官、士人“极言时政”,这又在社会上引起了畅言王霸大略的风气,它势必会影响到诗人,促使其精神风貌的转变,为诗歌注入一剂激昂的兴奋剂。
3.武则天改制前后对科举的一系列改革,客观上又抑制了藻丽文风的进一步发展,使之朝着简洁流利、富有气势的方向发展,这亦可说是对唐代诗歌的一大贡献。
注释:
(1)如陈寅恪、尚定、杜晓勤、胡可先诸先生,认为武则天大力发展科举,特重进士一科,而进士科又侧重文词甚至开始“诗赋取士”,故而武则天促进了唐代诗歌的发展。吴宗国、傅璇琮、陈飞等先生则认为,武则天对进士科并未特加重视,也未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诗赋取士”,因而武则天与后来意义上唐诗的繁荣并无直接联系。分别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1年版)、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杜晓勤《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胡可先《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环境》(《陕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吴宗国《中国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傅璇琮《武则天与初唐文学》(《燕京学报》新7期)、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
(2)《梁屿墓志》谓其“制试杂文:《朝野多欢娱诗》《君臣同德赋》及第”(见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7页。)陈铁民先生认为梁屿此次所应为进士试,徐晓峰《唐代科举与应试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断为制举试,见该书第30页。
[1]陈飞.唐代试策考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67-68.
[5]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6]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7]刘肃.大唐新语[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李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2133.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203.
[11]葛晓音.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M]∥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王勃.王子安集注[M].蒋清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辛文房.唐才子传笺证[M].周绍良,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119.
[15]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6437.
[16]释普济.五灯会元[M].宋刻本.
[17]张鷟.朝野佥载[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4.
[18]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2307.
[19]段公路.北户录[M].清十万卷楼丛书本.
[20]杜佑.通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21]马端临.文献通考[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354.
[22]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3]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69.
[25]王应麟.玉海[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6]王尧臣.崇文总目[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46.
[28]骆宾王.骆临海集笺注[M].陈熙晋,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
[29]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洪丕谟,等,点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505.
Wu ZeTi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aking the Zhiju and Quanxuan Examination Systems as the Core
LU Ji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00, Anhui)
Peopl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Wu Zetian’s achievements on literature by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ignored her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by the zhiju and quanxuan examination systems. Before she became emperess, the zhiju and quanxuan examination systems tended to literary talents to a large extent, which enhanced 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Wu Zetian had a great hope for zhiju, hoping to select th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talents. She vigorously played the zhiju role of political advice,which caused a talk about the political in the community, and prompted the scholar spirit to change. Wu Zetian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forms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hich objectively inhibi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orgeous style of literature, and made it simple and fluent, full of momentum. This was also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her litera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Wu Zetian;the zhiju examination system;the quanxuan examination system; literature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6.13
I206.2
A
1004-4310(2017)06-0064-08
2017-10-06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武则天与唐诗演进”(SK2017A0334)。
卢娇(1982- ),女,安徽庐江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