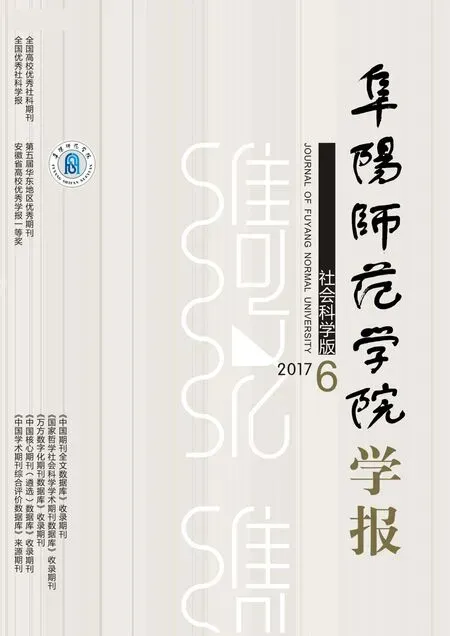因有画“肉”诮,遂以韩马“肥”——试辨前人对杜甫论画诗的一个误解
黄金灿
因有画“肉”诮,遂以韩马“肥”——试辨前人对杜甫论画诗的一个误解
黄金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文学系,北京 102488)
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有“干惟画肉不画骨”之句,唐人张彦远据此认为杜甫“徒以干马肥大,遂有画肉之诮”。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杜诗中“肉”与“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与“肉”相对的概念是“骨”,与“肥”相对的概念则是“瘦”。杜甫的“画肉之诮”不仅与前人的艺术理论一脉相承,更是与他的艺术理念消息相通。如果因为张氏的误会,就进而判定杜甫此论为“不解事之失言”,会对正确认识杜甫的艺术鉴赏力产生不良影响。
杜甫;论画诗;“肉”;“骨”
一
以鞍马为题材的艺术创作在唐代颇为流行,作为分科独立的鞍马绘画更是备受重视。盛唐出现画马名家曹霸与韩干,艺术成就得到普遍认可。韩干作画主张师法自然,《太平广记》卷211所引《唐画断》载有他“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的创见,这种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他的传世作品《照夜白图》《韩干牧马图》中不难体会。画作中马的形象既追求形似,又能“以其踊腾有力的身态刻画出不同凡响的高迈、暴烈的性情”[1]。他的老师曹霸在开元中已得名,画作以笔墨沉着、神采生动著称。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以下简称《丹青引》)中对他所画御马及所修补的《凌烟阁功臣图》盛赞不已。
在《丹青引》一诗中,杜甫有“干惟画肉不画骨”之句[2],从唐代开始就有人据此认为“少陵讥韩干画马‘不画骨’”是“不解事之失言”[3]。曹霸虽为韩干的老师,但其作品并未能如徒弟的作品一样流传后世。虽然汤垕在《画鉴》中称“余生平凡四见真迹”,但他对这些真迹描述偏于简略,后人无法据此判定曹霸画的马是否确如杜甫所言较胜于韩干。赵孟頫认为“唐人善画马者甚众,而曹、韩为之最,盖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众工之右耳”(《画鉴》引)[4]。这也仅是就师徒二人鞍马画的共同点而言,并没有谈到二人画作的水平高下。而一些注意到二人绘画艺术之不同的人,对杜甫诗中流露的“崇曹抑韩”倾向则提出异议,进而生出各种替韩干辩解的意见,这些意见有些是有益的,但另一些却是对杜甫的误解甚至攻讦。
例如唐人张彦远“徒以干马肥大,遂有画肉之诮”(《历代名画记》卷九)的论点就是以对杜诗的误解为前提而提出的,将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引入歧途,这不利于正确理解杜甫论画诗的艺术成就和杜甫的艺术观。张彦远认为杜甫根本不懂绘画艺术,甚至斥责“杜甫岂知画者”,玄宗“好大马”,故“干画马肥大”。言下之意是:不是韩干画得不好,而是杜甫没有眼光,不识肥马的好处。钱锺书先生认为杜甫有此失言也情有可原,因为“技艺各有专门名家”(《谈艺录》)。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杜甫的专长是作诗而不是作画,可正如歌德所说:“但是一个诗人不应设法当一个画家,他只要能通过语言把世界反映出来,就该心满意足了,正如他把登台表演留给演员去干一样。”[5]也就是说杜甫并不需要真的具有拿画笔创作的实践才能,通过语言的运用他同样可以把自己卓越的艺术见解表达出来,不能够因为不具有动手作画的纯熟技巧就断定杜甫不具有识得艺术作品好处的识见。
艺术来源于生活,实际生活中老杜是“识”肥马好处的。在杜甫的诗作里多次出现肥马,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肥马的好处认识得很清楚。杜甫说“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留花门》),可见肥马只要健康至少要比羸弱的瘦马要好,又说“衣马自肥轻”(《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衣马不复能轻肥”(《徒步归行》),“马肥”虽是与富足安逸相联系的,但毕竟也代表了大部分人欣羡的生活状态。“马肥”既是军事实力的表现又是生活富足的象征。杜甫对肥马好处是从来没有否认过的。同时,老杜也并不偏爱瘦马。认为老杜不识肥马好处,言外之意似乎是老杜很赏识瘦马的好处,考察杜甫的作品后发现,杜甫没有明显偏爱瘦马的倾向。从他的《瘦马行》里可以感觉到,对于“骨骼硉兀如堵墙”的嶙峋瘦马,杜甫有的只是怜悯而不是喜爱。不能否认,杜甫相对来讲更喜欢描写瘦马,但是喜欢描写瘦马与喜欢瘦马完全不同,喜欢描写瘦马是因为瘦马形象适合表现作者的一些特殊心情,由此就认为杜甫喜欢瘦马是不合实际的。杜甫描写马的肥瘦是视具体情况而定的,虽然杜甫有自己的较为固定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标准,但是他所看见的不同的马是有不同的外在及内在特点的,以杜甫尊重事实的一贯风格来看,他绝对不会违心地、机械地在所有的作品中把不同的马都描绘成一种样子。
误解之所以产生的关键就在于对杜甫《丹青引》一诗中“肉”字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张氏看到“肉”字就条件反射式地联想到了“肥”,然后把诗句中的“肉”看成了“肥”之同义词,这样就理所当然地得出杜甫觉得韩干把马画得太肥的结论;其实按照我们的常识,肥马固然浑身是肉,但不胖不瘦的骏马也得有肉,就连瘦马也不能没有肉。杜甫在《丹青引》中没有谈到马肥与不肥的问题。若是认为老杜不识“肉马”好处,还可勉强说得过去,说杜甫不识“肥马”好处,则完全转移了杜甫所讨论的话题。
二
杜集中有很多写马的诗,成就很高。我们以为,要准确理解杜甫的马诗必须准确理解他的《丹青引》,要准确理解《丹青引》,必须准确理解“干惟画肉不画骨”一句,要理解这一句必须准确理解句中这个“肉”字,这个字就像是通往桃花源的小孔,只有穿过它,才能到达杜甫马诗所表现的广阔天地。不然对杜甫的这个误解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同时,把握住了杜甫对“肉”字的使用,就不难反向寻找出杜甫鉴定骏马的标准,用此标准来欣赏骏马和马画,足以证明杜甫具有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否则,不管喜欢杜甫此类诗作的人把它们推崇得多高,误解他的人都会以杜甫对绘画之事不专业为理由来否定他的成就。
“肉”泛指动物或人的皮肉,经常与骨肉形体联合使用。如“肉刑”“手接飞鸟,骨腾肉飞”(《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厨门木象生肉足”(《论衡·感虚》)、“翠袖卷纱红映肉”(苏轼《海棠》诗)中的“肉”都是以此为基本义来组合成词句的。在杜诗中也有“岁晏风破肉”(《山寺》)、“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肉騣碨磊连钱动”(《骢马行》)等生动例句。可见,当“肉”和“骨”被用来描写马时,都是就马的相貌而言,不同的是前者指可见的外表,后者指外表包裹下的骨骼构架。只有做到骨肉相为表里、相得益彰,才是画马的最高境界。
骨和肉,一个是身体的内部支撑框架,一个是外部组成部分,合称的话通常可用于指涉身体的完整健全形态。杜甫在《丹青引》中说韩干“亦能画马穷殊相”,又说他“忍使骅骝气凋丧”,所谓“穷殊相”即是能准确描摹各种马的外表特征,所谓“气凋丧”即是说韩干所画之马未能把马的筋骨力量和神骏气概表现出来。用现在的话来说,在杜甫看来,韩干与其师曹霸相比略近于是画“匠”而不是画“家”。
“骨”这一概念,多用于品藻人物,“肉”也可用于品藻人物。“骨”是指某人具有忠直敢言、不屈不挠、不同流合污的品质,指具有精神、韵味、感情、意气方面的刚健有力之风格。如杜诗“魏侯骨耸精爽紧”(《魏将军歌》)、“秋水为神玉为骨”(《徐卿二子歌》)、“骨清虑不喧”(《别李义》)都是借赞骨来赞人,在《天育骠图歌》中用“卓立天骨森开张”来写马,使神驹宛然具有神人般的仙风道骨。杜甫在诗中用“骨”来品藻人物或动物,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指筋骨强壮有力,第二层意义是从第一层引发而来,指内在精神的刚健有力。如“骕骦一骨独当御”(《沙苑行》)、“飒爽动秋骨”(《画鹘行》)等句中,“骨”的两层意义兼而有之、融为一体。“骨”后来被借用于评论诗文,在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中运用的频率比较高,因而比对“肉”的概念的讨论要充分。“肉”若活用为一个形容词,就具有了形容一个人做事拖拖拉拉、慢慢吞吞,不够果断迅捷、不够雷厉风行的意思。如《说林》载:“范启云:‘韩康伯似肉鸭’。”古人品藻人物,遇高人则以鹤喻之,遇猛士则以鹰喻之,范启评价韩康伯用一“鸭”字,足见是对他慢吞吞的性格有不满,甚至觉得他“面目可憎”[6]。这样还不够,他还加了一个形容词性的“肉”字做状语,使韩康伯缓懦的形象顿时婉在目前。注家引此对《世说新语·轻诋篇》中“旧目韩康伯,将肘无风骨”进行解释是十分贴切的[7]。如今,江淮地区的方言中还用“肉鳖”来形容一个人做事不麻利。从“肉”使人产生迟缓感觉的角度来说,韩干“惟画肉”是无法体现出骏马的迅捷与力量的。李贺《马诗》第二十三首:“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句中的“肉马”,若解释为因迟缓无力而显得痴拙之凡马,要比直接解读为“痴肥”之凡马似乎略为准确[8]。
“肥”与“瘦”是一组相对立的概念,“肉”的相对立概念应该是“骨”而不是“瘦”。如在诗句“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新安吏》)、“高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佳人》)中就是“肥”与“瘦”、“骨”与“肉”分别构成一个组合的。骨肉合用,代指躯体,如同框架结构的建筑物,“骨”为支撑框架,必须坚固有力,“肉”为四壁与房顶的填充物,可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同样的,与“肥”相对的概念应该是“瘦”而不应该是“骨”;也就是说,“肉”并不等于“肥”,“骨”也并不等于“瘦”。“肥”“肉”二者是很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如“礼过宰肥羊”(《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不能说成“宰肉羊”;“草肥蕃马健”(《送杨六判官使西蕃》)、“熊罴觉自肥”(《晚晴》)、“鲂鱼肥美知第一”(《观打鱼歌》)中的“肥”也不能以“肉”来替换。在杜甫《严氏溪放歌行》的“肥肉大酒徒相要”之句中,“肉”是名词,“肥”是形容词作状语,可见肉与肥都分别可以单独做名词或形容词;杜甫又有“肉瘦怯豺狼”(《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之句,可见“肉”是可肥又可瘦的。杜甫说韩干笔下的马只“画肉不画骨”,意思说韩干画马不如其师所画更能骨肉停匀、比例得当,从而更能神似。仇兆鳌《杜诗详注》对《丽人行》:“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句中的“骨肉匀”进行解释时,先引《大招》:“丰肉微骨”,可能觉得有肉多骨少的嫌疑,又引周甸注:“骨肉匀,肥瘠相宜也。”可是“肥瘠”说的是肉的多少问题,和骨无关,于是又引《神女赋》:“‘秾不短,纤不长’,即骨肉匀也”来做进一步的补充,才对“骨肉匀”的内涵拿捏地比较到位[9]。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肥马”“肉马”“空多肉”之马区别开了。《李鄠县丈人胡马行》有“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俗马空多肉”之句,细揣诗意,与“多肉”相对待的正是“少骨”。这两句带有结论性的诗句是承接上面诗人对李丈人的胡马的描述而来的,对这匹马做直接正面描述的诗句是:“头上锐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诗人用“锐”和“批”“削”这样的硬性词汇,正是为了说明这匹马的骨力和精气神,而不是说这匹马很瘦,瘦到耳朵如秋竹批成,蹄子如寒玉削成。由此可见,在这首诗里“多肉”才勉强可以理解成“肥”,简单地把“肉”等同于“肥”而忽略了形容词“多”是完全错误的。同时这首诗还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细节,“不比俗马空多肉”告诉我们李丈人的这匹马虽然气高骨骏,但这匹马也是有“肉”的,只是不像其他的凡马那样空长了一身膘却缺少骨力与精气神。李丈人的这匹马有“肉”却骨力高骏,神采烁烁,这才是杜甫心目中的骏马尤其是天子马厩中的骏马的样子。那么杜甫说“干惟画肉不画骨”的意思就更加明白了,他根本没有提及马的肥瘦问题。一匹瘦马是绝对不可能算得上骏马的,但肥马也不可能算得上骏马,瘦马没有足够的能量,肥马则赘肉太多,它们都不可能日行千里。只有那些既拥有健壮的肌肉又具有骨力丰神的马才算得上骏马。杜甫在欣赏韩干马画的时候,看到了天子神驹的健美而强壮的肌肉,但他并不满意,因为他没有看见这匹马骧首踏蹄时显露出的有力骨骼乃至骨气,这才是杜甫的本意;张彦远据此而讥杜甫不识肥马好处其实是自己没有弄清“肥”与“肉”的区别。
“骨”“肉”二字本来是用于描述人或动物的体貌状况的,用来评论画作就具有了艺术理论内涵。杜甫在《丹青引》中说韩干“画肉不画骨”,结合他对“骨”“肉”二字的理解,可知若是“惟画肉”的话,马的外在筋骨之力没有表现出来时的虚弱状态和内在精神之力没有表现出来时的颓丧状态就都会暴露出来。诗人在《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中说:“雷霆劈长松,骨大却生筋。”在《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中说:“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可见对于“骨”的作用杜甫是反复强调的。“迥立阊阖生长风”“须臾九重真龙出”“忍使骅骝气凋丧”“将军画善盖有神”,这些诗句中诗人强调的诸如“风”“真”“气”“神”等特质,再加上一个“骨”,这就是诗人心中骏马应该具有的标准。这一审美标准应用于绘画就是要求融合内容的表现和形象的创造于一炉,在运用线条勾勒所表现之物的体貌时,渗透强烈的情感,注重绘画艺术中内外诸表现因素的统一;不论是较工细的密体,或是较粗放的疏体,在艺术形象的输出上,都要注意整个画面气氛的统一与具有运动感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当杜甫欣赏曹霸与韩干的鞍马画时,自然觉得骏马的内在精神气度只通过画“肉”是无法表现出来的。
分清了“肉”与“肥”的不同,也就正确把握了杜甫“画肉”之说的原意。由此可以断定的是,据《丹青引》无从推知韩马肥大与否。因为张彦远的观点是从杜甫“干惟画肉”说推论出来的,既然“肉”与“肥”是两码事,那由此推出韩干的“画马肥大”则完全是臆解了。同时,结合韩干创作实际来看,他画的马基本符合杜甫所说的“肉”的概念,那些丰满腴美的形体正是“肉”的体现。那些认为老杜不喜欢韩干所画之马的人犯了随意联想的错误,从“肉”联想到了“肥”,从“骨”联想到了“瘦”。他们自己混淆了概念,却要老杜来负责任,这是极不公平的。由于这种曲解,他们深信杜甫犯了“徒以干马肥大,遂有画肉之诮”的错误,殊不知是他们闹了“因有画肉之诮,遂以干马肥大”的误会。杜甫津津乐道的是因骨肉同时得到合理匀称的描绘而体现的马的神气之美,他何尝说到肥马和瘦马的优劣呢!
三
其实杜甫所持的这种审美理想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思潮,源于对传统理论的吸收和继承。绘画理论的出现是绘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而重气韵,重表现事物的风貌、气质,重人物的传神写照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精髓。如谢赫主张作画要达到“气韵生动”的要求,就是把生动地反映人物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作为艺术表现的最高准则。他评价晋明帝司马绍画:“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笔迹超越,亦有奇观。”[10]就用的是重神似的标准。当然对绘画风格的追求并不是单一的,在表现人物面貌、精神气质上早就有“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唐人张怀瓘语)的区别。实际上,无论是张僧繇“得其肉”的画法还是陆探微“得其骨”的画法都要以“得其神”为最终极的艺术追求。这也正是张、陆的画作都能成功展现许多同时代社会名流的风神的原因。到了唐朝,吴道子成熟时期的技法则更有特点,但也更显著地体现出两种画风的冲突。第一种是吴道子的“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凡俗”(《历代名画记》卷二)的卓异作风。从吴道子的特立独行可以看出当时依然存在着另一种与之对立的“密于盼际”“谨于象似”的画风。这种重形与重神的并存与冲突,被杜甫融合为自己的形神兼备、内外兼修的艺术追求;具体运用到他对鞍马画的鉴赏上就是要求画家创作的马的形象要在骨肉停匀中表现出神气完足的艺术特征。
理解了杜甫所持的艺术理想,对历史上关于“杜甫到底了不了解画”(徐复观语)的争论我们也就有了自己的看法。在这场因为杜甫一句诗引起的纷争中,一派人认为杜甫不懂绘画却妄下评断;反对前一派观点的人认为这是由于诗歌表现的需要,杜甫才故意说这样的违心之语。
自从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力证杜甫不知画以后,苏东坡似也赞同此论,他在《书韩干牧马图》中说:“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厩马多肉尻脽圆,肉中画骨夸尤难。”[11]这里可以看出苏轼的发难:御厩中的马本来就因为圆润多肉而看不到骨头,若偏要在肉中画出骨头来,这不是无中生有么?韩干自然主义的写实画法与曹霸把艺术理想放在第一位的创造性画法是不同的,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他们走着不同的创作道路”[12]。但“肉中画骨夸尤难”一句“分明是针对杜甫诗‘画肉不画骨’来说的”[13]。经苏轼这样一提倡,韩干画法的地位不可动摇,而杜甫因论韩干画马诗的“不得当”而饱受讥评也就势在当然了。到了倪云林一句“少陵歌诗雄百代,知画晓书真谩与”(《画竹诗》),竟把杜甫论书画的诗作的价值几乎全部推翻了。
这种说法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因此就另有一派人出来替杜甫辩解。明代王嗣奭说:“韩干亦非凡手,‘早入室’‘穷殊相’,已极形容矣,而借以形曹,非抑韩也。……此借客形主之法。”[14]认为这是由于诗歌表达的特殊需要,所以才有意这样说的。清人受他提示,对此说多有发挥。杨伦认为是“反衬霸之尽善,非必贬干也”[15]。浦起龙认为是“以韩干作衬,非贬韩,乃尊题法也”[2]。郭曾炘亦认为“特借宾形主,故语带抑扬耳”[16]。这些说法表面上是回应了前一派对杜甫的批评,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前提就是已承认老杜确实认为韩干所画之马太肥了;所有替老杜的辩解都是在这个前提下作出的,这就等于承认了老杜不知画。况且,他们把一个画艺问题转换成了诗艺问题,完全避开了对杜甫艺术鉴赏理论和审美理想的讨论;更有甚者,这种看法有将胸怀坦荡、心直口快的杜甫等同于某些违心奉承、满口假话的酸腐文人之嫌。杜甫在《丹青引》中对曹霸是推崇备至,在《画马赞》里对韩干也是十分赞赏,这看似矛盾的现象不仅不会让杜甫显得虚伪反而更显得他的为人实在。杜甫在《画马赞》中既有“雪垂白肉”之描写,亦有“瞻彼骏骨,实惟龙媒”的赞赏,这一方面说明韩干所画之马并不是完全没有骨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杜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鉴赏态度。杜甫在《丹青引》中所描绘的曹霸笔下的良相、猛将的形象和御马的形象是有极高的内在一致性的,因为他们都是既严守规矩又不失与众不同的个性,这正是杜甫严肃而又不失活泼的儒者风度的体现,也是“文质彬彬”的儒家艺术理想的体现。可以想见,即使是当着“初师曹霸,后自独擅”的名画家韩干的面,老杜也会说:“你的马画很绝妙,只是跟你师父比起来还逊色一些,因为你只画肉不画骨呀!”
综上可知,因为杜甫对韩干马画有“画肉”之评,张彦远以来诸人遂以为杜甫觉得韩干所画之马太肥,其实是张彦远诸人因为熟悉韩干的马画,在脑海中事先已经留存了一个“韩干画马肥大”的先验印象,进而从这个“韩马肥”的先验理解出发产生了对杜甫“画肉诮”之本意的误解。
[1]中央美院.中国美术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96.
[2]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289. 引诗凡出自本书的皆不再加注。
[3]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4.
[4]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注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189.
[5]歌德谈话录[M].爱克曼,辑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78.
[6]王达津.古典诗论中有关诗的形象思维表现的一些概念[M]//古典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81.
[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846.
[8]李贺诗集[M].叶葱奇,疏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99.
[9]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157.
[10]李来源,林木.中国古代画论发展史[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56.
[11]曾枣庄.苏诗汇评[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 586.
[1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54.
[1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56.
[14]王嗣奭.杜臆[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0.
[15]杨伦.杜诗镜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530.
[16]郭曾炘.读杜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56.
Flesh is Not Equal to Fat: Talking about a Misunderstanding of Du Fu’s Painting Poems
HUANG Jin-Can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Du Fu’s “Danqing song to Cao generals Pa” has the sentence “Han Gan but painted the flesh does not draw the bones”, so Zhang Yanyuan holds that Du Fu laughs at Han Gan for he only draws flesh. In fact, this is a misunderstanding. Du Fu’s “flesh” and “fat”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concepts. “Flesh” is relative to the concept of “bones”, and “fat” is relative to the concept of “thin”. Du Fu’s view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ecessors of the art theory but also consistent with his artistic concept. Because of Zhang’s misunderstanding, Du Fu’s artistic appreciation will be adversely affected.
Du Fu; painting poems; flesh; bones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6.14
I207
A
1004-4310(2017)06-0072-06
2017-11-03
黄金灿(1988— ),男,安徽凤台人,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与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