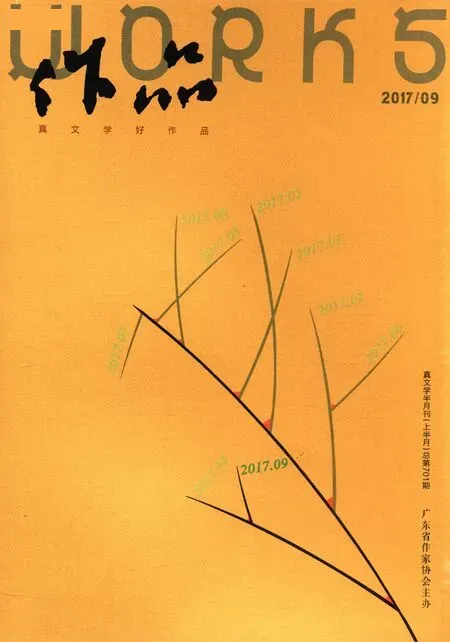失 灯
文/祁小鹿
失 灯
文/祁小鹿
祁小鹿
1995年生于青海大通。作品见于《星星》 《青海湖》 《江南诗》等刊物。
解读一篇小说,有很多角度,也有很多衡量好坏的标准,比如结构、故事、修辞……每一个方面都可以拎出来长篇大论。那么试问,结构精巧但故事乏味的小说是不是好小说?故事精彩但修辞陈旧的小说是不是好小说?同理,修辞精湛但故事拖沓结构无聊的小说是不是好小说?如此看来,一篇小说的优劣是交织并存的,作者的努力本质上是一个取长补短去芜存真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天分,但更多依靠勤勉。这是我阅读《失灯》这篇小说的一个感受,也是所有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智啊威
四爷在清晨敲开我家的门。他披着大衣,衣袖在微风里轻轻晃动,身后是微蓝的天空,透出连绵阴雨结束后的清新。他佝偻着身子,眼睛却直直地看我。我注意到他额头上的皱纹,一层压着一层,眼睛都被压成了一条缝,但我还是察觉到他疲倦眼神里尖锐犀利的光芒。我觉得他和往日看起来有些不同,至于哪里不同,我一时也看不出来。
“四爷,你来了。”我说着话,准备将这打扰我睡梦的人迎入家门。
但他似乎并不买账,挪挪嘴皮,吐出几个语焉不详的词语。他的脸上流露出痛苦隐忍的表情,好像在用力撑着身上的那件大衣。
“我的灯没有了,我来这里,来你家找找。”他终于说清楚了,眼巴巴地望着我,好像我背后藏着什么东西。这时我才觉察出他的异样——那盏他提惯了的灯不在他的手里。但是他的身体弯曲,左手臂依然下垂,好似有什么东西拽着他。我想那盏灯并没有丢失,只是隐形了。可是四爷失落不振的样子提醒我,那盏灯就是消失了。
他随我走进来,步子迟疑,眼光向四周依次扫去,生怕一不留神,便错过什么。他看了一圈,没有看到他寻找的东西,却仍觉得有所遗漏,愣愣地站在了立柜面前,手摸摸抽屉,又缩回手。他转头看看我,流露出为难的神色。
我没有说话。他站在原处,又抬头看看被烟熏黑的房梁,终于开口说话了:“索冬,你真的没见着我的灯吗?”
“嗯,没有。我连你都没见着,哪里看得见你的灯?”
他似乎认同了我说的话,从柜子前走到了房门口,神色更加暗淡,好像我把他最后的一根稻草捞走了。
“你阿妈去哪里了?”他又问。
“去锄草了。”我不耐烦地回答。他又打量一下周围,看了看菜园里那些生长茂盛的花草和蔬菜,似乎又想到了什么,突然转过头来,激动地说:“阿罗!肯定是阿罗拿走了我的灯。”他说着就往外走,心急火燎的样子。
阿罗住在村口,走到他家少说也要十多分钟,更别说像四爷这般踩蚂蚁的步伐了。我拉住四爷,提议给阿罗打电话,四爷却使劲摇摇头,做出副“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可以打电话”的神情。
我只好把手机塞进裤兜里,看他已经迈出了大门,我也不假思索地跟上了他。他的步子比之前快多了,不一会儿就到了阿罗家门前。门是开着的,但他并没有直接跨进去,而是站在门口,用拳头敲了几下门板。门里边的狗随即跳起来,大吠不停,被打扰了的愤怒从嘴边、眼里蹦出来。要不是被铁链拴着,它怕是早就咬住了四爷。房屋里却一点响动也没有。
“我进去看看吧。”我知道四爷向来如此,主人家不出来请他,他是不会进去的。他以前也不愿意我这样“冲”进去。
但是这次他迟疑了,顿一下说:“好,你进去问问吧。”
阿罗还没有起床,躲在被窝里玩手机,他听到声响抬了一下头,看到是我又把脑袋缩进了被窝。我把冰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像触电一样跳起来。
“你干什么?”他大叫。
“都几点了?还不起床。”我说。
他看了眼手机,似乎觉得不早了,便披上了衣服。“找我啥事?”他问。
“我来找灯,四爷的灯不见了。”
“灯。”他思索一下,说:“那灯早该扔了。”
“四爷怎么会把它扔了,你清楚的。要不他怎么让我来这里找?”
“这里?这里怎么会有他的灯?谁也用不着啊。”
“我想也不可能有的,但是你跟我说没用,你出去和四爷说吧,他就在门口。”
阿罗不愿意出去,被我生拉硬拽弄出去了。我们没出家门就看见四爷倚着门边不停地张望。阿罗告诉他并没有见着灯,他不信,跟着阿罗进门找,依然一无所获。
“我说了没有,这下你相信了吧!”阿罗说。
四爷木木地点点头,脸上仍是不愿相信的神情。含糊不清地对我说:“我们走吧,索冬。”
我冲阿罗做了个表示歉意的鬼脸,就跟着四爷走出去了,阿罗也没有送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到阿罗说了句含糊暧昧的话,大概是给手机里的什么人说的。
四爷这次走不动了,他摇晃着身体,左手臂依然下垂,好像准备要去捡什么东西。他的身体构成了一个不平衡的问号,需要有东西来扶正。我突然觉得有些难过,或许他的左手里拿一件东西,哪怕是一个瓶子,也会显得合理一些。
就像一个月之前,他提着一盏面目难辨的煤油灯,滑稽而合理。
白杨树刚抽出嫩黄新芽,喜鹊轻快的身影在树枝间闪现又消失。我坐在窗前,眼光随着鸟儿在窗外流转。四爷就是这时候闯入了我的视线,他换上了褐色的毛衣,裤子在清风里轻快地晃。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四爷都会换上这幅行头,去奓门找何爷爷下棋。
今年的冬天漫长了一些,同四爷下棋的三个老人只剩下何爷爷一个了。众人都说四爷也不行了,但彼时他看起来精神还算不错,穿得一丝不苟,全身不着一丝病气。想来说四爷不行了的由来已久,四爷是我祖父最小的兄弟,据说自小懦弱多病。尤今年,耳朵渐渐变聋,腰身越发佝偻,显露出一副无法掩盖的老态。
四爷走得小心翼翼,生怕不小心便摔了去。他左手提一盏黑黝黝的看似夜壶的东西,经年累月的污垢缠绕在上面,好似沉石,把四爷往地下拉。其实那就是四爷的煤油灯。自我有记忆起,四爷便有了那盏灯,但凡迈出家门便提在手里,就像有人总带着一把伞,一双筷子一样。
能否点亮那盏灯却始终没有得到验证。幼时我和几个调皮的孩子,缠着四爷让我们看看,那时村里早就通电,除停电时点一根蜡烛,平时都用电,煤油灯算得上稀奇的东西。但是四爷以“大白天点灯太浪费了”为由给拒绝了。后来我们尝试着偷来看看,几次都没有得逞,四爷却看得越紧了。
“这么盯着,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
阿罗和其他人都这样觉得,我们都失去了兴致。后来我想,我们失去兴致不是因为四爷看得太紧了,而是我们有了更稀奇的东西。比如:电视,手机,电脑等。只是四爷一直把那灯提在手里,依旧到处走,全然不受影响,好像神经不大正常。
四爷依然向前踽步,如履薄冰的样子。我的目光又流转到树上,喜鹊的影子忽隐忽现,以欢快的心情准备迎接春天。四爷也要去奓门那边,以此来迎接春天。奓门先前就是村庄的中心,也是众人的集聚地,现在那里修了广场,搬来了村委会的办公室,摆了些石墩,放了假山,以假乱真,却也吸引人。但凡天气好了,大家出了门,都无意识地往那边去了。
等四爷过了桥,我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便也整理了衣衫,出了门。
我加入了女人们的行列,并不是要和她们聊天,而是蹭村委会的网,下载视频,或者玩一会游戏。女人看了一眼我,也觉得平常,又无所顾忌地投入原先的话题。
收铜丝喽,一两换家电,一斤换手机。
“收铜丝啊,我家里有一些,不够一两怎么办?”
“我家也有,但是可不可以直接换成钱?”
“是啊,家里电器够了,不想再换成电器了,可以直接换成钱吗?”
……
人们挤挤嚷嚷地不停发问。里面的一个男人终于关了广告,把喇叭举到自己的嘴边,故作庄重地说:“大家安静一下。铜丝可以直接卖给我们,一斤三十块钱左右,大家可以把铜丝拿过来,让我们看看成色。家里面有不能用的旧电器的话,也可以把铜丝取出来再拿来。”
原本挤在那里的人霎时变稀疏了,大概是回家找铜丝了。没过一会儿桑子叔就背来了一台小彩电,他把电视放在地上,愣头愣脑地问里面的人:“这电视机里的铜丝怎么才能取出来啊?”
里面的那些人似乎没有预料有人会把电视机抬来,都有些吃惊,一时说不出话来。还是先前说话的男人说:“砸了,砸了才能取出铜丝。”
“什么?砸了?”桑子叔惊恐地说。
“这电视机你也看不成了,砸了取铜丝还省些事呢。”
桑子叔犹豫了一会儿,痛下决心似地说:“那就砸吧,反正放在家里也占地方。”
里面的人从车里找出来一把锤子,递给桑子叔,他准备下手时,四爷突然大声说话了:“桑子,这电视机不能砸!这可是你阿爸的血汗啊。”众人都将眼光投向了四爷,他手里提着灯,站在人堆旁,努力让自己站得直一些,但无济于事,他看起来像只被蛮力架起来的虾。
桑子叔犹豫了,他似乎想起了他已逝去的阿爸,脸突然变得忧郁。
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大家又把目光聚集到桑子叔身上。还是里面那个男人打破了沉默,他看着四爷说:“哟,你手里提的什么东西?”
“这个,你管不着。”四爷说。
“还不让人看了,难道是装了鬼,怕跑出来祸害吧?”
“这里面就是装了鬼魂,这灯就是能镇得住鬼怪妖魔。”四爷认真又得意地说。
众人都被四爷的话弄笑了,但站在人群外面的二婶没有笑,她受辱一般讪讪地收起手机和针线,迅速离开了奓门。二婶是四爷的儿媳,众人都知道他们素来不合。但那天众人的注意力聚集在那群陌生人上面,并没有人注意到二婶的变化。
最终电视机还是被砸了,不止是桑子叔家的,村里的大多数旧电视机都被砸了,那些金灿灿的铜丝像被人体解剖出的肠子,陈列在阳光下面,即使闭上眼也觉得刺目。四爷默默退回到自己的石墩,重新坐下去。他又开始了自己的等待,但是奇怪,那一天何爷爷并没有来。
第二天,我家的门又被四爷敲开了。他的腰似乎更弯曲了,扶在门框边像一把被用力拉扯的弓。他的眼神也变得更加暗淡了,苍老了。他看着我,眼里划过一丝光彩,但随即幻灭。
“四爷来了啊,进来坐吧。”我说。
“不了。索冬,我就是来问问你,你有没有见着我的灯?”他磕磕绊绊地说出那句话,语言能力好像瞬间钝化了。不止语言能力,他的记忆也似乎退化了。
“没有啊,四爷,你昨天不是来找过了吗?”
“啊!”四爷惊讶地张大了嘴。“昨天就找过了啊。”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头低下去,好像在脑中思索昨天的情景。“那我走了啊,我去阿罗家看看吧。他说我的灯点不亮,他肯定把灯拿去了。”
他转身准备离去,我上前拦住了他:“四爷,阿罗家昨天就去过了,也没有。”
“昨天去过了?没去啊。我要赶快去看看,不然灯要被那小子弄坏了。”他挣脱了我的胳膊,好似凭空生了几分力气,我胳膊竟隐隐觉得有些疼。
四爷渐渐走远了,看着他像一片树叶被风裹挟,摇摇晃晃地走上了桥,我便也进了门,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给菜园除草——是阿妈安排给我的任务,她说你不能再这样浪荡了。村里和我同龄的孩子还在上学,而我和阿罗没考上高中,就成了难兄难弟。我在菜园子里有些手足无措,太阳渐渐升起来,照在我的后背上,似乎要把我融化掉。村子是极安静的,偶尔能听到一两声狗吠,像掉入深井的石子,空落落的。
狗吠声渐渐大了起来,连起来成了一串儿。我从菜园里出来,去井边打水喝,听到一些人的叫嚷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隐隐地觉得会跟四爷有关系,却也无法确定,就坐在井边喝水。声音越来越大,我已经看见一行人急煎煎地走过来,四爷果然就在里面,他看上去是被人架起来拖着走。这样他的腰反而直了一些。
队伍经过我家时,我加入了他们。原来是四爷寻不着阿罗家,过了桥就逐一敲开大门,逢人就问有没有见着他的灯。他们怀疑我的二婶故意藏起了四爷的灯,欺负四爷。他们决定带着四爷,去找二婶讨个说法。
二婶在家,她家种的田少,二叔过完年就外出打工,她也老早就清闲了。她坐在台阶上面手捧着手机看着什么电视剧,看得泪水涟涟,身旁的儿子索春来被固定了的学步车所控制,但他似乎在渴望自由,小脚不停乱踩,见着我们,他高兴得手舞足蹈,露出两颗小乳牙。而二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一大波人的到来,依然沉浸在电视剧剧情里。直到我们来到台阶前,她才惊醒一般抬起头来。
“阿爸,你去哪里了?”她手忙脚乱地关了手机,对着四爷怒目以对,好像在怨恨他把这么多人引入家中。
“秀珍,我找我的灯……”
“你的灯不是被你扔进炕洞里了吗?你怎么又开始找了?”
“啊?怎么会啊?”四爷大吃一惊,把眼光投到炕洞边,好像在尽力回忆。
众人面面相觑,但他们似乎相信了二婶说的话,那种来时的气焰瞬间熄灭,像一股水流快速地流走了。他们走时还在自言自语,大抵意思是四爷老了,不中用了。讨说法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四爷疯了。这个消息在村里传播的速度之快,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和阿妈刚从四爷家出来,远在西城打工的阿爸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冬儿,你四爷疯了?真的吗?”阿爸开门见山。
“嗯,真的疯了。他前几天一直坐在炕上,哪里也不去,二婶今天才发现他把炕挖了一个洞。”
阿爸沉默了一阵才说:“联系你二叔,明天回家来。”
阿爸原先是兽医,但凡村里牲畜有个生育或病死,阿爸都会被请去。但近几年,众人都要外出打工,很少有人养牲畜了,走投无路的阿爸从去年便开始跟着二叔去西城打工。
二叔在当天晚上就回来了。我们守在四爷身边,他还在用一把勺子挖着炕,炕上的洞黑黝黝的,散发着草粪被燃烧被压制后的气味,好像随时都要把我们裹挟进去。他嘴里念叨着一句奇怪的话:
灯儿灯儿快出来,阿物阿物你走开。
任谁说话他都不理。阿爸站在炕边,看着他,好像看着难产的母牛,无计可施。
“我们要做一个灯。”阿爸说。
大家都表示认同他的观点,开始思考用什么材料才会像原来的那一个。
二婶说:“那种黑乎乎的瓶子,现在肯定找不到了,用泥糊一下玻璃瓶可能看起来会像一点。”
“你不知道那个煤油灯对四叔有多重要。”阿爸严肃地说:“四叔小时候爱下棋,常常下棋忘了时间。有一天夜里,四叔一个人回家,那时正好有人家办丧礼,纸做的人马把他吓得不轻,他急急忙忙地走着,过桥的时候被一块石头绊了。等他跌跌撞撞地赶回家,发现膝盖变得红肿,僵硬。他摔伤了骨头。等腿好了,别说赶夜路,就连门都不敢迈。爷爷想了个办法,让他提一盏灯,说这灯不仅能照明,还能压鬼。这样四叔才敢出门,这灯一提就是一辈子。”
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四爷还在挖炕,嘴里依然念念有词,像个虔诚的祈祷者。
还是阿爸说话了:“所以,你们要是有人藏起来了,就拿出来还给四叔吧。”他用深沉的眼光打量我,显然把我当做了嫌疑犯。
“阿爸你别看我,我用不着那玩意的。”
“不管是谁,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出灯出来,无论是找的还是做的,最好是一模一样的。”阿爸说。
众人都点点头,开始纷纷献计。我看到阿爸严肃怀疑的眼神从我身上离开,觉得轻松了很多。不过听他的话,似乎并没有消除对我的怀疑。我偷偷地看了两眼二婶,正好对上她看我的眼神,我假装看其他东西,头稍稍歪了一下。
二婶却慌神了。“你这孩子,这样看我算什么事情?难道是怀疑我偷了灯?我偷灯干什么?”
她问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她偷灯干什么,但我总觉得这事和她有关系。
阿爸替我解围:“听你说,四叔把灯扔进了炕里?你怎么知道的?”他盯着二婶,一双愤怒的眼睛似乎要喷出火花。
“是我亲眼看见的,他把灯扔进了炕洞里。”
“他把灯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怎么会扔进炕里?”
“这我怎么知道?你自己问他。”
问四爷?他还在挖炕,屁股撅得老高,看不见他的脑袋,只能听得见他嘴里念叨的词儿,他能回答什么呢?
二婶说完就急急地离开了屋子,生怕露出破绽似的。
阿爸把所有人分成了两队。一队由他带头,做灯。另一队由二叔带头,找灯。
阿爸命令阿妈去找瓶子,他们对于那盏灯的材质各执己见。阿爸觉得是那种有盖的铁罐子,不然怎么会那么黑;阿妈则认为是以前用来装药片的褐色玻璃瓶,黑是因为长期放在厨房熏的。他们实在争执不下,就决定两种都找。他命令我去别人家找煤油灯——这是几乎无法实现的事,所以他安排我这个不大靠得住的人去做。他自己则分出一半力气,去帮二叔们找灯。
阿妈不一会儿就抱回一大堆瓶子——透明饮料玻璃瓶居多,其余是塑料瓶,褐色药瓶和铁罐子的数量为零。
阿爸从门口一看到阿妈就开始呵斥她:“你这没头脑的婆娘,拿那些玻璃瓶就不说什么了,把塑料瓶拿来干什么?要做灯吗,一把火,啥都没有了。”
阿妈显然没有想到这些,站在门口,捧着那些瓶子,不知所措地望着里面。
我自然也是一无所获,跟在阿妈后面,看他们三个人埋头于堆在院子的炕灰里面,用短柄铁锨寻找着灯。我渴了,蹑手蹑脚地进门去,他们三个人警觉地抬起头来,我一看他们的脸就忍不住笑了。本来我不该笑的,我什么事都没有办成,不应该在这时候笑,更不应该笑出声。阿爸果然生气了,他不顾那张像刚从磨坊里出来的脸,提着铁锨就冲我跑过来。我向屋里跑,我一定是吓傻了,来不及思考。果然我跑进屋里就无处可逃,阿爸轻而易举地抓住我。就在他手里的铁锨向我头顶落下来的时候,二婶突然大叫起来。
“找到了,找到了,我就说在炕里吧,可让我找到了。”
阿爸应声放开抓我肩膀的手,提着铁锨出了屋。我也感到激动,不顾还未消除的危险,就跟着阿爸出去了。但二婶手里的东西让我们失望透顶,那哪里是灯啊?分明就是一根铁丝,甚至连铁丝都说不上,锈迹斑斑的,像半截没有完全燃烧的木棍。
“你这是什么灯?莫非你神经也不大正常了?”
“这是提灯的把儿,你看看,灯儿早就被烧了。”
“怎么可能?夏天谁还煨炕?”
“那几天正好下雨,天气冷,就煨了。”
阿爸再也说不上话,看得出他既不相信二婶的话,也找不出反驳她的理由。他心急火燎地站着,一下下翻动着手里的铁锨,炕灰随之上下翻动,呼啦呼啦地往他的裤腿上扑。
我偷偷溜进了屋里。四爷还在挖炕,没有了监管,他的动作似乎变快了很多。
我终于忍不住,提醒四爷:“四爷,炕灰已经被堆到院子里了,你开这个洞有什么用呢?”
这句话果然奏效,他停下手里的动作,木木地抬起头,用那双布满灰尘的眼睛打量我。他似乎在叫我拉他起来,我赶紧放下水杯,去炕边拉他。就在我的手伸出去的时候,突然听到咔嚓一声,那种硬物断裂了的声音,四爷歪了一下身子,似乎说了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从他挖的那个洞里掉了下去,他的炕也瞬间变成了一个大坑。
四爷的炕没了,他的一条腿也摔断了。二叔把四爷背进了南边的旧房子,南房阴冷,即使煨了炕,也不起作用。四爷的神志越发迷糊,嘴里只挂着一个词,灯。阿爸退而求其次,用阿妈找来的所有玻璃瓶做成了灯盏,他们一起把那些灯盏拿进南房。不得不惊叹阿爸的手艺,那些灯做得很漂亮,摇曳着一种与光束媲美的火焰,闪烁着古老而神秘的召唤,没人不因他的灯而陷入更远的沉思。但我总觉得那些灯太漂亮,反而显得虚假,就像一颗颗随时都会幻灭的泡沫。
有一天我问阿爸:“四爷的那盏灯可以点亮吗?”
他准备返回西城继续打工,这些天已经耽误了他很多。他停下手中正在收拾的行李,肯定地说:“不能。”
“你怎么知道不能?”
“我像你这样小的时候,对你四爷的灯充满了好奇,有一天我偷了过来,没有点亮它。
阿爸很快就离开了。我们的主心骨没了,二叔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拿不了主意,只会像木头一样坐在四爷的身边,一坐就是一整天。我想四爷年轻时也和二叔一样,让人忽略他的存在。而灯却恰恰补充了这个空缺。
无人再探究四爷的灯到底是怎样丢的。我怀疑是二婶,但这样的怀疑毫无根据。我怀疑更庞大更抽象的东西,也怀疑四爷——他注定要失灯的,他守不住灯,守不住一个本该消匿的东西。
四爷一直躺在床上,佝偻着身子,仍是准备提东西的样子。那些灯不知昼夜地亮着,灯光在他的脸上、身上游走,使他的衰老、黝黑无处可藏。而他看起来就像一盏黑黝黝的煤油灯,在这些光怪陆离的灯火之间显得格格不入。
祁小鹿作品互动短评
>>周阳依(文学青年,1994年生,四川自贡人。写小说,书评,影评,文学评论等。)
《失灯》是一篇极具寓言色彩的小说。让我不得不去思考的是这个故事所讲述的时代背景,于新旧两个时代的衔接之间,出现了一些失语状态的人。一盏煤油灯已是旧物,同是旧物的还有那些没有了生命更新力的老人,所以旧物与旧物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有着深厚的情谊,甚至是相依为命的伴侣。在所有的新鲜事物当中,老人更愿意把希望寄托于一盏灯,成为生活的信仰,反映出对新鲜事物的不接受。尤其感动的是当所有人都丢弃过去赶着换新装的时候,老人的出现代表着善意的提醒,有些东西丢不得!
>>张勇敢(1994年生,闽西客家人,现求学于重庆。)
小说语言平实,叙事性强,用四爷失去煤油灯的恐惧,写出了老一代人对过去的依赖和对现在、未来的忧虑,更可悲的是,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四爷们”也注定会像煤油灯一样,被这个时代淘汰。或许在失去灯的同时,在人们心中留住温暖的灯光,才会让这个世界不那么冰冷。
>>吴可彦(1990年生,出版有长篇小说《星期八》《茶生》、短篇小说集《八度空间》。)
亮晃晃的灯照出的是黑暗,点不亮的黑灯却是四爷生活的希望,四爷不是因为丢了灯而倒下,打倒四爷的是更庞大更抽象的东西,那个东西庞大抽象到无法形容,小说作者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们那是什么,那个东西也许就是生活本身,日常的叙述最终如梦魇一般可怖,最令人不安的是——从日常到可怖的转换并没有运用什么技巧,用的只是真实。
>>夏立楠(中短篇小说见《上海文学》《山东文学》《青年作家》《广州文艺》《ONE·一个》等期刊平台。)
小说语言朴实精练。“灯”是一种隐喻,象征“老人”的思想寄托和精神支柱,通过找灯展现了人们对老人的关怀,也从另一面体现出人性比较脆弱的一面,呼吁更多人在时代的变迁下,不要抛弃生活的“本真”,保持“原味”。
>>王净晶(2015年《中国诗歌》“新发现”夏令营学员,有文见《山东文学》《山东诗人》《中国大学生文集》等。)
可能是“戈多式”的“等”,可能是卡夫卡的“孤独意识”,四爷和他的灯是毫无缝隙地绝缘于“现代文明”的存在。 “他者”各有意味地表演,乡村文明的颓废,实则暗示了即将泯灭于现代化潮流中的“传统”的不可逆转性。失去的,存留的,应该是些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深思。
(责编:周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