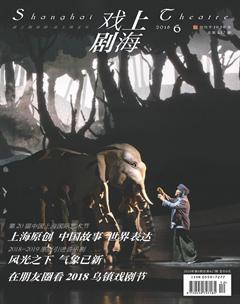形式与行动:斯坦尼与格洛托夫斯基的中国相遇
杨俊霞
第六届乌镇戏剧节有一个精彩的设计:在10月24日的演出中,由莫斯科艺术剧院带来的《19.14》在乌镇大剧院上演,格洛托夫斯基与理查兹中心的《客厅》在沈家戏园演出,遥相呼应。斯坦尼与格洛托夫斯基,两位大师透过传承者的作品,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小镇意外相遇了。
有着120年历史的世界名团莫斯科艺术剧院为第六届乌镇戏剧节带来的演出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品《19.14》。与莫艺悠久的历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剧导演亚历山大·莫洛奇尼科夫仅有26岁①的年龄。《19.14》选择用卡巴莱的形式将几个一战中法国、德国士兵的故事与战争的重大转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高频的语速、海量的台词、充满想象力的表演、快节奏的舞台调度……整个作品散发出的戏谑与激昂令人对莫艺的生命力叹为观止。
选择卡巴莱的形式表现一战,极其贴合一战时期欧洲社会的时代特点,它的作用并不仅仅只是让演出多了一个随时可以跳进跳出串联故事的主持人而已。卡巴莱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655年,词根甚至来源于更早时期的诺曼法语,现在常常用来指在餐厅、俱乐部及夜总会进行的混杂音乐、歌曲、舞蹈、朗诵、戏剧等表演形式的娱乐演出。1881年在法国巴黎蒙马特由鲁道夫·萨里斯创办的黑猫酒馆常常被看作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卡巴莱演出场地。作为当时流行文化的前沿阵地,黑猫酒馆不仅聚集了大批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歌手,还吸引了不少当时巴黎的有钱人及上层名流。在谈论艺术、政治、文学的氛围中,黑猫酒馆的卡巴莱演出尤其以时事热评及对权钱阶层的讽刺闻名。萨里斯发行的同名周刊《黑猫杂志》秉承同样风格,艺术、文学、掺杂时事新闻和政治讽刺小文,其中莫泊桑、雨果等大文豪发表了不少作品。黑猫酒馆风格卡巴莱的盛行不仅促使卡巴莱主题进一步分化:如侧重歌舞声色的红磨坊,侧重时事热点的福赛夜总会,逐渐转型文青甚至吸引了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的狡兔酒吧等;还将这种表演形式从法国输出辐射到更广泛的区域:混杂喜剧、戏剧、音乐、社会热点政治评论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卡巴莱总会”(1885),以黑色幽默和政治讽刺著称的德国卡巴莱(1901),以喜剧、独白、隐晦的政治讽刺等现场广播直播表演为特色的波兰卡巴莱(1905),以爵士、大型乐队、社会评论为特色的美国卡巴莱(1911),以先锋作家、艺术家、社会精英为目标人群的英国卡巴莱(1912)等。从文艺形式上来看,一战前的欧洲就是一个混乱、矛盾、激昂同时又歌舞升平的卡巴莱的欧洲。
更重要的是,卡巴莱形式的选择,令该作品“反战”的主题不言而喻。1916年,德国理论家、诗人雨果·巴尔在苏黎世开了一家卡巴莱“伏尔泰酒馆”。来自欧洲各国的诗人、艺术家、作家、设计师、舞蹈家、电影制片人等聚集在酒馆,在这个夹缝中的避难所里通过卡巴莱的形式发泄和抚慰他们紧张不安的心灵,表达对一战的绝望、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厌恶、对人类文明惨遭践踏感到的迷茫。他们愤世嫉俗,演奏街头摇滚、朗诵诗歌、创作一系列拼贴作品,通过“反艺术”的方式追求清醒的非理性状态,推崇无意义、碎片化、随性的艺术境界。这种秉持“破坏就是创造”原则的文艺思潮就是持续时间虽短但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达达主义。在《达达主义宣言》中,倡导人之一的特里斯唐·查拉这样定义它:“这是忍不住痛苦的嗷叫,这是各种束缚、矛盾、荒诞的东西和不合逻辑的事物的交织,这就是生命。”
形式揭示本质,卡巴莱的形式加上达达的精髓,令莫艺的《19.14》散发出非常原始而又强大的生命力。《19.14》整个舞台颜色基调是卡巴莱主色调红色,一如那个时代的浮夸和粉饰太平。现场音乐表现出有选择的“混搭”,爵士、摇滚、甚至还有当年靠在黑猫酒馆弹钢琴谋生的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的曲目。舞台时空结构转换灵活多变,凸显拼贴特色。舞台上空可以左右移动的方框型小舞台一会是卡巴莱主持人的演出場地,一会是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杀时乘坐的敞篷车,一会是将两国士兵运到前线的各种车辆,一会是轰炸战场的飞机、坦克、清理战场运送尸体的装备。1914年圣诞节西线两侧敌对双方士兵自动休战时舞台的干净空旷与几次史称绞肉机战壕战时舞台的混乱逼仄形成鲜明对比。莫艺演员表演真实细腻,同时又极富想象力。两个士兵“驾驶”着用浴缸和自行车“组装”成的坦克,手持圆号像机关枪一样向敌人扫射,荒诞而又寓意深刻。战壕战时,士兵们罩在军大衣里像无头苍蝇一样原地乱转,个体消亡只剩下恐慌的死亡符号。毒气面罩巨大、失重,令士兵动作滞缓怪诞,但仍难以阻挡死神的脚步。幸存士兵冷漠僵硬的肢体,加上“弹震症”令其无法控制的抽搐,仿佛扑杀不灭的战壕虱子,一点点吞噬战争幸存者的人性。演出中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仿佛一幅幅达达主义的绘画作品,新奇怪诞、挑衅叛逆、混乱激昂。
作为格洛托夫斯基的传承人,托马斯·理查兹带来的《客厅》让观众体验到的观剧感受并不“贫困”,反倒是非常VIP。从观众进场开始,《客厅》的表演就开始了。演员将观众一一安排到特定区域入座,贴心地为大家送上茶水咖啡和小点心,甚至还会为大家续杯。仿佛观众是去做客的客人,茶水之余观众安静又充满期待地等待主人的表演。演出结束时,客厅里喧嚣、奇幻的梦境戛然而止,剧中承载着角色澎湃内心情感的蛋糕,在长久的静默中被演员们安静地、非常有仪式感地派分给每位观众。在分享食物和香槟的过程中,在静谧的氛围里观众缓缓回味演员们已经结束了的表演,从狂欢的状态抽身,渐渐回归日常。细致地探索演员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曾经是格洛托夫斯基戏剧实验的重点。在其后期忘却观众、不再有意识地激发观众反应之前,格洛托夫斯基希望观众是“受邀的见证者”,观察并见证演出的进行。通过教堂弥撒般的仪式性的食物分享过程,理查兹试图简单、直接地在演员和观众之间建立格洛托夫斯基在《戏剧与宗教仪式》时期倡导的理想的观演关系——牧师和信徒的关系。
《客厅》演出没有字幕翻译,观众在第一时间会清楚地意识到剧本在这个演出中似乎没有那么重要。观众入场时会获得一张歌词单,看完后演员就会将其收走。即使你能将整张歌词单在极短的时间内背下其实也无济于事,因为它不是剧情大纲,只是抒情的语句片断。由于强调演员的主体性与创作性,剧本在格洛托夫斯基戏剧实践中的地位一降再降:如果说在“十三排剧院”时期还可以看到原作的痕迹,那么到实验剧院时期,剧本已经被当作是演出的“跳板或桥梁”,演员完全可以超越原作“自由飞翔”。
整个演出其实是一个男人光怪陆离的梦境:长途跋涉后疲惫不堪的男人回到家里,坐在客厅一角小憩,渐渐睡了过去,然后梦境生动地浮现出来。通过演员们的吟唱、领唱及默契地多声部重唱,在古老的歌谣中,男人对女人的渴望,与儿子的冲突,对年轻人婚礼的反对,接受与祝福,妻子怀抱的抚慰……拼图似碎片化地呈现在观众眼前。
整个演出过程中,托马斯·理查兹仿佛是“导游”一样,引导、安排着整个演出活动。事实上,《客厅》的演员们并不是在扮演角色,他们是在表现自己,他们用行动定义了格洛托夫斯基理论与实践的存在。格洛托夫斯基强调演员通过严苛的身体训练,达到心理力量与形体力量的高度统一,通过深度体验从而激发最原始的能量,打破演员内心与肢体的阻隔,实现内外能量的自由转换。在格洛托夫斯基看来,戏剧是使人们离开自己从而充实自己的手段。通过演员对内心最隐秘的自我的揭示,让观众也认识到自己的隐秘的精神世界。
两位杰出的大师,通过自己的实践与理论,对表演的本质、表演的现象、表演的意义给出了各自的答案。透过他们的继承者的艺术作品,大师们的理论印迹依然清晰可见。
(作者为云南艺术学院教授)
注释:
1.演出前戏剧节官方宣传导演为29岁,首演之后“小镇对话”环节导演自己确认仅有26岁,他已经为莫艺创作并导演了三部作品《19.14》(2014)、《反抗者》(2015)、《19.17光明之路》(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