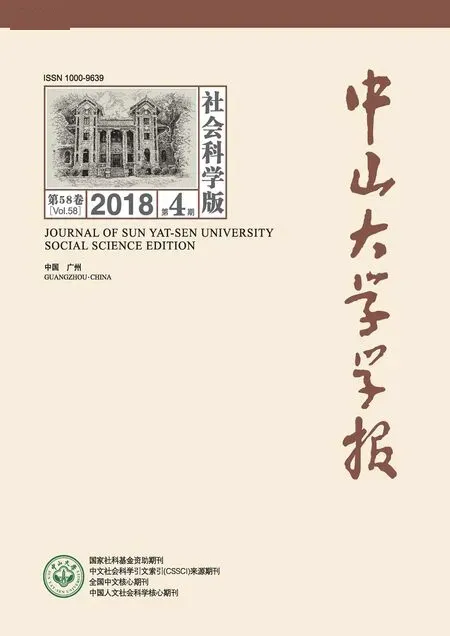《大学》“教—学”论与《中庸》“教—化”论*
——儒家政治的“真知”困境与可能出路
邹 晓 东
较之道家追求清静或逍遥之修炼,儒者修身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驾驭政治权力、用政治权力为社会谋福祉为指归。儒者修身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在于施教。在现代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映衬下,传统儒家政教显得专断而封闭*儒家政治在不完整的意义上也被称为“礼教”。新文化运动站在反对专制(追求民主)、谋求新知(科学)的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吃人的礼教”,这种批判已然构成当代学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辨析《大学》“教—学”论与《中庸》“教—化”论,有助于深度剖析这种政治传统的症结所在。总的来说,传统儒家政治低估了“真知”问题的棘手性:位高权重的执政者尤其是君主,因而多有机会以“圣明”或“天道”等真理性名义强力推行自己的既定政见。传统儒家政治的专断性与封闭性弊端便是由此而来。《中庸》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比《大学》深刻得多,但其用以解决“真知”问题的方案功亏一篑。本着这点认识,本文将致力于揭示《大学》对于“知识—理解”问题的轻忽,展示《中庸》对于“真知”问题的应对不力,检讨上述轻忽与应对不力对儒家政治观与政治实践的消极影响,最后还将尝试探讨走出困境的可能出路。由于当代并无现成的《大学》《中庸》权威解释可资采信*相关争论,参见邹晓东:《〈大学〉、〈中庸〉研究:七家批判与方法反思》,《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第122—128页。,我们须在解析《大学》《中庸》的“政治”理念的同时,适度回护自己所持文本解读的合理性。本文因而将采取文本解释与思想阐发相结合的写作模式。
一、“教—学”意识是《大学》的隐含前提
《大学》的主导性问题意识及其应对方案分别是什么?弄清楚这些,是探讨《大学》政治观的基础。
《礼记·大学》是现今可见的《大学》原始版本,但二程、朱熹等学者认为其文存在阙乱,尤其是缺少了进一步阐释“格物致知”的传文。为此,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大胆地“移其经而补其传”。随着朱学和《四书章句集注》的流布以及相关争论的不断展开,“格物致知”问题俨然成为《大学》解读的聚讼焦点*朱熹补传,参见《大学章句》,[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7页。后来的王阳明以重解“格物致知”为契机,向朱学发起挑战。。这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即:“格物致知何以可能”以及“如何格物致知”,构成了《大学》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经学家皮锡瑞尖锐地批评上述移经补传的做法为“疑经不已”,并斥之为“宋人习气”*参见《经学历史·经学变古时代》,[清]皮锡瑞著、潘斌选编:《皮锡瑞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33页。。顺着经学家的“尊重文本的原始实在性”意识,我们可进一步逆向追问:假设《礼记·大学》并无错乱或阙文,那么它究竟为何未能持之以恒地将“格物致知(如何求知)”放在最“本”、最“始”、最“先”的位置上予以重点解说?
《大学》开篇的“学”字实际上已经暗示了上述追问的答案。我们知道,“学”的对应面是“教”;通常认为,“教—学”的基本特征即“授受知识”。进言之,在上述“教—学”意识中,人们会倾向于认为“知识”是现成的,就在教师或教材那里。本着这种“知识现成”的“教—学”意识,《大学》作者当然不会鼓励读者“从零开始自行求知”——“教—学”授受要比各自为政地从零摸索高效得多!于是,我们看到《礼记·大学》开篇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礼记正义》卷66《大学第四十二》,[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36,2236—2237页。
“学”字当先,进而宣告“三在”宗旨,紧接着提倡“知止→定→静→安→虑→得”的“受教—为学”心法——这则开篇引言,实乃《大学》作者以教师身份发布的“施教—劝学”宣言。所谓“知止”明摆着就是要止于“三在”宗旨。由于发生在“能虑”“能得”之前,此“知止”遂只能理解为“指向目标”或“立志”,也即“有志于实现‘三在’宗旨”。志有“定”向方能专注地“静→安→虑”,进而在“知识—理解”上有“得”。懵懵懂懂的受教者之所以能够树立正确的志向,全赖诸如《大学》作者这样的优秀教师不吝赐教。
实际上,作为“定向”,“三在”宗旨还是显得过于模糊。《大学》若就此打住,而放任读者自行揣摩,则懵懂的学者势必难免在自己的臆想中走上歧途。作为尽职尽责的教师,《大学》作者进一步出示了相对具体的条目性指导: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正义》卷66《大学第四十二》,[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36,2236—2237页。
这些相对具体的“本末—终始—先后”之说旨在精调读者的志向,以便使读者(学习者)的“定→静→安→虑”,更准确地朝向正确的“知识—理解”之“得”。无论如何,有了精确的志向(“知所先后”),成功就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这个发语辞尤其值得玩味。它意味着,《大学》作者丝毫不认为上述条目性解说是他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恭敬地认为自己只是自古以来的优秀知识传统的继承者。可见,《大学》作者虽然以读者的教师自居,但却始终不忘自己也是先贤与传统的学生。换言之,《大学》作者显然是将自己定位为“学有所成的教师”,而非创制立法的天纵之圣。本着“学有所成的”过来人经验,他自然倾向于鼓励学生在“受教”中“为学”,而非凭一己之力自行“格物致知”。就此而言,“格物致知”命题大可放在那里作为对“传统之知”的起源与有效性的笼统说明,但却没有必要实打实地作为后学“求知”的方法论而大谈特谈。
二、“知而不行—意志薄弱”问题与“威势施教”的政治模式
“教—学”意识倾向于认为“应然之知是现成的”,就在教师、教材或传统那里。如此一来,能否以及如何将教师所代言的“应然之知”切实地“行”出来,就成为摆在师生面前的突出要务。“知而不行”非但会使知识传授沦为耳旁风,甚至还会使“教—学”活动本身都难以为继:“知道应该”教/学,但却“懒得”教/学。由于“已然知道”,此“懒得”遂显得更像是“非智力”性的“意志力”问题,也即当代中国人常说的“意志薄弱”问题。因为急于对治这个问题,《大学》接下来的解说性文字遂干脆跳过了“格物”和“致知”,而浓墨重彩地花费了近乎全篇三分之一的文字,苦口婆心地劝勉读者要“诚其意”。这进一步说明,“教—学”意识以及在这种意识下所突显出来的“知而不行—意志薄弱”问题,确实从总体上主导了《大学》的写作。
《大学》“所谓诚其意者”章的前两段文本如下: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礼记正义》卷66《大学第四十二》,前揭书,第2237—2238页。
其中,“见君子”“人之视己”“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等提法,明显充满了“外在监督”的意味。相应地,第一段中的“小人”,亦处处显露出畏惧“外在监督”的情态。这种“小人”在缺乏外在监督的场合下“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遇到外在监督)则遮遮掩掩文过饰非。就此而言,此等“小人”,其问题似并不在于不了解“君子”所代表的传统应然之知,而在于“不能实用其力”以致知而不行*就文本解读而言,朱熹的解释较之王阳明更为可取。参见[宋]朱熹:《大学章句》,前揭书,第7页。。与此“知而不行—明知故犯”相伴的,便是“不自慊”的罪疚感与遮遮掩掩的扭曲情态。
“人(指监督者)之视己(指小人),如见其肺肝然”这个提法,明显是以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共享相同的应然之知为前提。我们知道,能否以及如何认识“他心”,这在西方哲学中是一个难题;上述《大学》引文,却轻松地认为监督者具有轻易洞悉被监督者心态的能力。这并不是说西方哲学小题大做,或《大学》的相关提法是无稽之谈。《大学》作者之所以会有这种思想,乃是因为在拥有既定的应然之知的前提下,人的道德心理与外在反应极有规律可循:或者自觉遵行所持有的应然之知,从而快足于己(“自慊”“心广体胖”);或者明知故犯,心怀罪疚,且遮遮掩掩(“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可能。实际上,作为修身者,每一位合格的监督者都是从一定程度的“知而不行—意志薄弱”状态走过来的,对于上述道德心理与相应的外在表现心知肚明。借助其所观察到的“掩饰”迹象,这种监督者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二选一”的方式,辨认出“知而不行—意志薄弱”的小人心态。
但是,“共享相同的应然之知”这一前提当真成立吗?考虑到包括《大学》读者在内的许多社会成员尚需通过“受教—学习”日益精细化地了解掌握传统应然之知,以上前提在现实中严格来讲并不成立。如此一来,鉴于“他心”难题,“人(指监督者)之视己(指小人),如见其肺肝然”也就成了无稽之谈。这是《大学》的重要盲点所在,与其轻忽了“知识—理解”或“格物致知”问题密切相关。站在文本研究的角度看,上述“共享相同的应然之知”这一前提,正是《大学》作者在“教—学”意识下认定了“知识现成(就在教师、教材或传统中)”的表现。其所谓的“小人……见君子……”现象,大致也正是其在教学中的经验之谈:应然之知既定,知而不行问题突出,但因畏惧团体共识,知而不行者往往又会强加掩饰。
那么,从上述思路,能引申出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呢?在相信“应然之知既定”的“教—学”实践中,学生能够自觉地“诚其意(知而力行)”固然是好,但考虑到“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的劲头儿,我们便不得不承认“知而不行—意志薄弱”问题具有顽固性。在现实生活中,“小人”在监督者(执政者)不在场的情况下“为不善”,而一旦对簿公堂(“见君子”),这种“小人”又会极尽狡辩之能事为自己开脱(“掩其不善”)。这种“狡辩—开脱”恰与受教者所应有的“谦虚”心态截然相反,可谓《大学》“教—学”之道的死敌。“所谓诚其意者”章最后一段遂借诠释孔子语录之机,道出了对治这种顽疾的手腕: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礼记正义》卷66《大学第四十二》,前揭书,第2249页。
在前述“教—学”意识中,作为断案标准的“应然之知”被认为是既定的。对同一个案件,合格的法官自然不可能做出两样的判决。孔子因而也不追求在判案结论上标新立异(“听讼,吾犹人也”)。孔子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审案、断案,更有效地对治“知而不行—意志薄弱”心态,从而防患于未然(“使无讼”)。针对“小人”明知故犯复推诿狡辩的态势,《大学》作者在孔子语录之后,紧接着给出了“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的政治方案。简言之,那就是:执政者宜在听讼之际动用声色威势,震慑“小人”气焰,给明知故犯的意志薄弱者造成一种“怕觉”,以此整肃社会风气。如此一来,《大学》的“教—学”意识,便进而落实为一种“威势施教”的政治模式。
作为对比,《中庸》在谈论“教(教—化)”的时候,最后专门援引“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以及“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礼记正义》卷61《中庸第三十一》,[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45、2051页。作结。这意味着,“威势施教”在《中庸》看来并非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何以如此呢?
三、《中庸》的“真知”问题意识
《中庸》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篇,“天命之性”由此被设定为“道”和“教”的基础与起点。相形之下,《论语》《大学》基于“教—学”意识谈论儒家之“道”*《论语》全书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始,可以作为《论语》首重“教—学”的佐证。,“天命之性”并非必不可少的议题。《论语》中的子贡虽不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论语集注》卷3《公冶长第五》,[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9页。,却仍然可以师从孔子为学修德;而在《大学》中,“性”字仅一现,且位置比较靠后,被用来形容“既定的传统应然之知群众根基深厚故而不宜冒犯”*“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礼记正义》卷67《大学第四十二》,前揭书,第2254页)此“人”应理解为“众人”。,根本不成其为一个独立概念*宋明儒学将《大学》“明德”与《中庸》“天命之性”等同起来,努力制造一种《大学》持“性善”立场的图景。就文本解读而言,这种做法实在值得商榷。参见邹晓东:《〈大学〉“明德”并非〈中庸〉之“性”——基于思想史趋势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109—123页。。那么,原始孔门所不甚重视的“性与天道(天命之性)”议题,为何会一跃成为《中庸》的起点性概念呢?《中庸》又是基于什么样的问题意识,高抬“天命之性”的呢?
作为一段议论体文字,《中庸》首章更多地是在铺陈方案,其所针对的问题意识,则是通过接下来的孔子语录加以呈现的。同为孔子语录,《中庸》的语录体部分和《论语》遵循着非常不同的编辑理念。《论语》作为集体编辑的成果,旨在如实荟萃妙语箴言,节与节、章与章之间仅有相对松散的话题性关联*参见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9—137页。。《中庸》中的孔子语录,虽绝大多数可在《论语》中找到相似或相关的对应片段*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上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2—287页。,但作为个人(通常认为是子思)或另类的编纂成果,《中庸》对孔子语录的遴选与编连,则服务于阐发编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与解决方案。特别地,通过精心编纂前七则孔子语录,《中庸》作者成功地从孔子遗产中,托举出了主导全篇的“真知”问题意识。为节省篇幅计,我们仅分析其中四则: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第一则)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第三则)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第六则)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第七则)*《礼记正义》卷60《中庸第三十一》,前揭书,第1990—1993页。
先看第一则语录。“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意味着“人应该走中庸之道”。那么,何为“中庸”呢?“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之“时”意味着:实行中庸必须灵活机动,随时随地顾及处境,而非机械地墨守某些“中庸”规条。“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意味着:“小人之中庸也”只能是“小人自以为中庸”;“无忌惮”实即“自以为是”,包括墨守成规意义上的自以为是。“小人”自以为是,但实则为非——“何为真正的中庸”问题由此初露端倪,而其实质就是“真知”问题。
第三则语录的亮点在于:在细节表述上,它力求打通“知”“行”。在谈论“知者过之,愚者不及”时,它使用“行”字;而在谈论“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时,则使用“明”字。“行”在字面上指“实行”,“明”则带有“理解”义(如“不明乎善”之“明”)。以“行”字论“知”“愚”,暗含了“有什么样的知,就有什么样的行”的意识;以带有“理解”义的“明”字谈论“贤”“不肖”(较之“知”“愚”似更侧重“实行”方面),则隐含着将“实行”问题还原为“知识—理解”问题的意思。最后一句“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可谓画龙点睛,将“知者”“愚者”“贤者”“不肖者”的非“过之”即“不及”问题,明确地归结为了“知”的问题。
特别地,在《大学》式“教—学”意识中,应然之知既定,立志为善的贤者的意志力,只患“不及”而无所谓“过之”。“贤者过之”在《大学》式语境下乃是不可理喻之事。在“知识—理解”或“真知”问题意识下,“贤者过之”就很好理解了:由于“知识—理解”存在偏差,贤者所具有的坚强“意志力”,反而导致当事人在歧途上飞奔。在这种情况下,“立志为贤”反而沦为了“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而非《大学》意义上的“小人”。
第六则语录尤为给力。面对他人的劝诫或建议,自以为是之人常会不耐烦地表示:“予知”——也即“别说了,我知道”。观察其为人处事则发现,这些自称“予知”的人,往往正在自我损害而浑然不知——他们被自己的决策“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就此“莫之知”而言,其所谓“予知”并非“真知(正确的应然之知/真正的时中之知)”。至于“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这看似“知而不行”问题,但在上下文中却同样旨在否定“予知”,也即当事人所宣称的并非他所真正理解并认同的。这实际上就是王阳明后来所明确表达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或“真知必然实行”的“知行一体”思想。《大学》式的“知而不行”问题,就此也被归结为“真知”问题*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关于“知行一体”的生存分析论证(参见谢文郁:《真理情结:从柏拉图到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4日,第6版)。。
第七则语录涉及孔门标志性人物颜回。《论语·雍也》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集注》卷3《雍也第六》,[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7页。这既是一种身体力行的践行境界,同时是一种恰当的“知识—理解”境界,无论如何,缺乏通透之“知识—理解”的持守是“乐”不起来的。此所谓“择乎中庸,得一善”,刻画的正是颜回对“中庸”之“善”的“知识—理解”。较之“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的“假宣称”,颜回“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是不折不扣的“真知”。
这里也留下了一个问题:“期月守”或“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意义上的“真知”,会否压制“随时随地顾及处境”意义上的“真知”?反言之,“随时随地顾及处境”会否导致当事人在“知识—理解”上“无恒”?在理论上,或可假设处境本身具有恒常性,作为体贴处境的结果,“真知”因而也会具有稳定性。然而,一旦做出这种预设,各种“教条式的真知”而非“时中之知”,势必借机大行其道。这实在是一个“两难”问题,本文最后一节还会间接涉及。
四、“真知”问题求解:“率性”与“教—化”
“真知”问题的“真”字,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当事人是否真的认同某种“知识—理解”?很多时候,自己口头上宣称的不一定就是自己所真切认同的;所谓“知而不行”,其实正是“口头宣称”与“真切认同”之间的分裂。其二,当事人所认同的“知识—理解”是否真的适切当下处境,或者,真正适切当下处境的“知识—理解”是什么?
如何解决上述“真知”问题呢?《中庸》所由以呈现“真知”问题的孔子语录表明:即便追随优秀的教师(如孔子)、读优秀的教师所精心删正的教材(孔子删《诗》《书》),当事人在“知识—理解”上也还是会每每走偏。这说明,教师和教材无法直接向学生灌输处境化真知。在《大学》式“施教—受教”之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如果“真知”问题还是可解决的,则解决的希望恐怕只能寄托在每一个当事人生而固有(但未充分利用)的能力上。《中庸》开篇所谓“天命之性”正是指称这种固有能力: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正义》卷60《中庸第三十一》,前揭书,第1987—1988页。
传统经注在解释“天命之谓性”时,常常迫不及待地将“刚柔”“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教义注入“性体”。但是,这种“以教定性”的做法,根本无助于解决“真知”问题。在传统所谓的“体—用”推论中,学者自始至终只是根据自己对既定“教义”的现成理解界定“性体”,进而再根据这种界定推论何为当行之“道”与“教”。归根结底,这是一种“从教到教”或“从用到用”的循环推论,通过这种循环推论,推论者固有的“知识—理解”偏差将趋于强化。
实际上,“天命之谓性”作为一个准宗教命题,它只是在正面的宗教性情感中认定了“人生而固有可靠的内在向导(性)”,却并不试图进一步规定“向导本体(性体)”的具体内涵。在“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先后秩序中,“道”“教”之内涵须由“体察内在向导指引(率性)”实时赋予,而非反过来根据关于“道”的现成“教义”规定“何为向导本体(性)”。但是,在“天命之性”未经界定的情况下,读者将完全失去依据“性体”内涵对“率性”体验的具体内容进行预判的根据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何为“率性”,只有即时体验了才会知道。这是《中庸》“率性之谓道”的精髓所在。
在开篇三句之后,《中庸》首章进而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来形容上述“率性(体察内在向导指引)”体验。凡“可睹”“可闻”者皆可在概念中加以界定——“率性”若是“戒慎乎可睹者,恐惧乎可闻者”,便终究与“遵守既定规范(界定)”无异。这样的“率性”,无异于《大学》所谓的“诚其意(通过意志努力持守既定之知)”。《中庸》所谓的“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实则是一种“直接从未经界定的天命之性出发”的姿态。如此一来,《中庸》首章所谓的“故君子慎其独也”,也就与《大学》“所谓诚其意者”章中的“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拉开了距离。《大学》侧重从“舆论监督”“形于外”的角度谈论“慎其独”,认为社会成员只有练就了“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仍能诚心诚意遵守权威规范”的功夫,才能于外在舆论监督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中,因不逾矩而享有“自慊”“心广体胖”的从容境界。《中庸》与此不同,它在上述“不界定天命之性之具体内涵”的语境中,将“慎其独”重新界定为“即时体察未经界定的性的随机发见(率性)”。“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所刻画的,正是这种“内在”(相对于“外在监督”)且“即时”(相对于“现成界定”)的“率性—慎其独”体验,它“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中庸》首章第三段“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亦非如传统经注所认为的那样指称“性体”或“本体”。尽管本段使用了“大本”二字谓述此“中”,但“致中和”的“致”字(作为某种人为努力)却意味着:此“中”、此“和”并不是指天生固有的“性”,而是指通过人为努力才能达致的“境”。金景芳先生认为:“‘喜怒哀乐’是人在感情上的四种表现,这四种表现不是中,都是偏于一个方面。但是当它们都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无所偏倚,就叫做中。这句话是解释‘中’的定义。朱熹给《中庸》作注,说‘其未发’是性,这种解释显然是不对的。”*金景芳:《论〈中庸〉的“中”与“和”及〈大学〉的“格物”与“致知”》,《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第75页。受此启发,我们建议将此“中”字,理解为“观念—情感”无所偏向的“中立”心态。当事人需要付出相应的人为努力,使自己从现有“观念—情感”倾向中超拔出来,才能进入这种“中立”心态。这种“中立”心态之所以被视为“大本”,是因为:当事人唯有从既有的“观念—情感”倾向中摆脱出来,才能专心体察“性在内心中的即时发见(内在向导的即时指引)”。就此而言,“中立”心态构成了当事人“率性(体察内在向导即时指引)”的主观条件。“大本”二字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条件”地位。
按说,《中庸》对于“真知”问题的求解可以到此为止了。但在后半篇,《中庸》作者却又欲罢不能地将“真知”问题反加诸“率性”,从而触及“何为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正义》卷60《中庸第三十一》,前揭书,第2020页。
上述引文环环相扣地将政治归结为各级执政者的“诚身”问题,而“诚身”问题最后又被归结为“明乎善”问题。前已指出,“明”字有“知道”“理解”“认识”义。“明乎善”即“明白真正的善”——“明乎善”因而指向“真知”问题,一句“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将“真知”问题加到了“诚身/诚乎身”头上。在《中庸》首章所奠定的以“率性之谓道”为中心的语境下,《中庸》所谓“诚”本质上只能理解为“率性”。这样,“真知”问题就被反加诸“率性”头上。一旦走到这一步,问题就变得极为棘手,因为这等于取消了“率性”的自明性,也即转而强调“非真知”因素对“率性”的干扰。如此一来,要想真正做到“率性”,就必须另费一番周折。但是,凭什么进行这种“周折”呢?在缺乏“真知起点”的情况下,任何“周折”都只能徒劳无功地在充满偏差的“知识—理解”泥潭中打转。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庸》的“至圣—教化”论显示出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最终,“至圣”“至诚”之“君子”人物的出神入化的影响力,似乎被《中庸》设定为促成“真正的率性”的最后保障。这是怎样一种“保障”呢?前已指出,声色威势无法直接灌输“真知”,反而徒增“苟且—求免”的心机,大大分散了受教者自觉“率性”的注意力。在“真知出自率性”的大前提下,唯一有效的施教手段只能是:“至圣—至诚—君子”凭借其出神入化的感染力,潜移默化地感化受教者进入“体察内在向导指引”的“率性”的状态。所谓“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所谓“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所谓“君子笃恭而天下平”*《礼记正义》卷61《中庸第三十一》,前揭书,第2045页。,因而实即“君子(至圣者/至诚者)潜移默化地感化人民率其性”。这样,“天命之性—即时率性”意识下的“教—化”(《中庸》),也就与“外在监督—意志持守”意识下的“教—学”(《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五、不断扩展的“率性的处境”与“权威政见”的更新机制
如果执政者真的持有“真知”,那么,按照《大学》“所谓诚其意者”章的结语,严刑峻法作为“大畏民志”的强力措施,不失为执政者正当的执政手段。但是,执政者的“知识—理解”如果是可错的,则一味允许其凭借权力推行既定政见,就有可能酿成社会性灾难。在想当然的“知识现成”意识下,轻忽了政治中的“真知”问题,这是《大学》式政治观的根本盲点之所在。《中庸》意识到了普遍性的“真知”问题,并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人生而固有且绝对可靠的内在向导(天命之性)”上,认为“在具体处境中即时体察内在向导的指引(率性)”乃是“真知”的起点。
普遍的“天命之性(内在向导)”预设,加之个体本位的“率性(体察内在向导指引)”意识,逻辑上可以导出一种类似“基本人权”(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但深彻的“真知”问题意识,却促使《中庸》作者转而触及“何为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受此问题意识激发,孔门的重“教”传统在《中庸》后半篇被全面升华为“出神入化的‘至圣—至诚—君子’之‘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至诚如神”*《礼记正义》卷60《中庸第三十一》,前揭书,第2024、2025,2005页。意义上的“教—化”,必须是不着痕迹的“感化”,也即感动受教者自行进入“真正的率性(真正地体察内在向导指引)”状态。就此而言,《中庸》自始至终都未放弃“率性”意识,它清醒地意识到“知识—理解”归根结底只能是每一个当事人“亲自认知—亲自理解”。“教—化”只为促成“真正的率性”,故此它只能在“隐”“微”之际发挥作用,而不应沦为声色威势意义上的“监督—管教”,以免破坏“率性”的“自我体察”特征。
问题在于,《中庸》的“教—化”理念太过浪漫。在每个时代或时期,社会上一定会出现一名“至圣—至诚—君子”吗?即便总会出现,那又如何辨认?谁有资格做出判断?如何保证这种“至圣—至诚—君子”,一定登上作为政治顶峰的君主之位?“至圣—至诚—君子”若不在君主之位,其“教—化”功能会否打折扣?在这些问题上,《中庸》显得天马行空而矛盾丛生。一方面,“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礼记正义》卷60《中庸第三十一》,前揭书,第2024、2025,2005页。;但另一方面,《中庸》所极推崇的仲尼(孔子),却“有圣德无其位也”*《礼记正义》卷61《中庸第三十一》,前揭书,第2046页。。顺此悖论,读者甚至可以继续追问:就“知识—理解”水平而言,包括《中庸》作者本人在内的一切儒者,究竟有没有资格(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有资格)谈论“真正的大德”以及“真正的至圣—真正的至诚—真正的君子”?在上述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的情况下,“至圣—至诚—君子”以及“教—化”,在现实中就只能沦为“威势”君主的荣誉性虚衔(所谓“天子圣明”或“皇帝圣明”)。如此,则儒家政治中的“真知”问题就会继续停留在黑暗的深渊,“将执政者的政见偏差放大为社会灾难”的隐患亦会始终存在。化解问题与困境的出路究竟何在?
“教”的初衷在于“纠错”(包括改善“无知”状态),但《大学》《中庸》却不约而同地设定了“君师理应圣明/无误”的意识形态。如此一来,君主若承认自己的政见可错并试图纠错,在很大程度上就无异于自毁统治资格*传统所谓“罪己诏”并非常态,不意味着君主政见在一般意义上是可错的。作为偶发事件,“下罪己诏”对君主威望造成的打击往往是深重的——“君主理应圣明”的意识形态,实在难以接受“君主犯错”的事实。。有势力的野心家则会以此为契机,取而代之,并将自己打扮成“绝对圣明/无误的君主”。取而代之与自我打扮的过程,往往同时是社会剧烈动荡乃至兵荒马乱的过程。在“君师理应圣明/无误”的传统意识形态下,“纠君主之错”的代价是如此之高且未必有效!
鉴于此,不如干脆取消“君师理应圣明/无误”的设定,而实打实地将以君主为代表的执政者群体视为“既定政见”的持守者。“既定政见”并非“绝对真理”,但是因有君主所代表的政权为之背书,它在现实中具有显而易见的权威性。一种“知识—理解”是如何上位而成为“既定的权威政见”的呢?就“权力”的逻辑而言,有权有势者的“率性体认—应然之知”最容易成为“权威政见”。“权威政见”一旦上位,以君主为代表的执政者便会动用权力,通过颁布法令、下达文件、动用媒体等手段,约束反对声音,统一社会意见。社会因而将围绕此“既定的权威政见”形成集体意识与行动力。但作为一种“知识—理解”,“既定的权威政见”毕竟是可错的,健全的社会政治因而也须充分考虑“权威政见的更新与提升”问题。每一位社会成员的“率性体认”,则是更新、提升“既定的权威政见”的智力资源。为此,必须取消“什么是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追问,而郑重宣布“率性体认是自明的”。否则,无人敢以“率性”的名义,表达自己对于政治事务的意见。“率性自明”的意思就是:任何人在任何处境中只要真真切切地认为自己是在“体察内在向导的指引”,他就算是在“真正地率性”,他的体认对他而言就是此时此刻的“真知”。这是社会成员勇于表达与“既定的权威政见”相左的“异见”的底气所在。
在正常情况下,君主本人往往也是本着自己的“率性体认”,推行“既定的权威政见”。既然“率性体认是自明的”,异议者当然也就不能简单指责“君主不率性”,故而无法在“不率性”的意义上宣称“君主关于既定的权威政见的知解不是真知”。如此一来,就会出现“真知(君主或执政者的)—真知(其他社会成员的)”相互冲突的局面。如何摆脱这种僵局呢?
深入辨析“率性的处境”概念,有助于找到打破僵局的出路。前面指出,“时中”意义上的“真知”,只能是“适切处境的真知”。换言之,处境发生改变,“真知”随之俱变,这是“时中”的精髓。那么,什么是一个人“率性的处境”呢?严格来讲,除了内心深处(“隐”“微”之际)随时涌现的“性之发见”,以及当事人对于这种“发见”的即时体察之外,进入当事人意识中的其他一切皆为“处境”。分而言之,“处境”包括当事人过去的阅历与记忆(包括对既往率性体认的记忆),当事人正在遭遇或面对的事态,以及当事人对于未来的预期。就此而言,君主(执政者)有没有听到针对“既定的权威政见”的“异见”,对他来说乃是两种“处境”。普通社会成员“将自己的异见藏在心底”与“说出异见并因此承受各种政治压力”,对他来说构成了两种“处境”。可见,“异见”的表达会改变君主(执政者)与表达者的“处境”,而在改变着的“率性的处境”中,有关各方的“真知体认(率性体认)”也会改变,前述“真知(君主或执政者的)—真知(其他社会成员的)”相互冲突的局面因而出现松动。
随着“异见”表达趋于阶段性终点,也即暂无新的异见涌现,随着君主所能施行的教育说服工作已经做尽,也即暂时无法再从“既定的权威政见”开出新鲜有力的政令花样,以君主和异议人士为代表的相应政治事务的参与者们,就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相同或相近的“率性的处境”。考虑到在相同的“处境”意识下,“天命之性”不可能有相异的“发见”,相应政治事务的参与者们就会趋于达成“新的政见共识”。简言之,这是一种“执政者凭借政权持守‘既定的权威政见’,普通社会成员通过特定渠道表达自己的‘率性体认’与‘异见’,双方在‘率性’意识中相互承受政治压力,阶段性地就争议之事达成‘新的政见共识’”的动态机制。相形之下,传统儒家政治的“专断性”与“封闭性”,其根源就在于:君主(执政者)单方面坚持“既定的权威政见”,而武断地否定其他社会成员有资格在“自明的率性”中体认并发表“异见”,君主(执政者)与普通社会成员的“率性的处境”因而无法有效地在交融中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