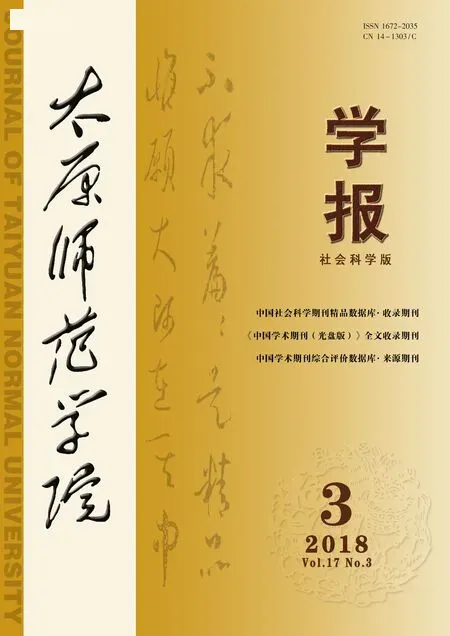现代性视域下的《域外小说集》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048)
现代性是通过现代化的进程得以产生、强化和呈示的。中国近代是翻译文学现代化的拐点。在这一领域揖别传统模式、跨入现代门槛的历史走势中,作为博学多才的文化巨人,鲁迅以“弄潮儿”的搏击勇气和高度的责任担当意识,通过自己的文化活动实践和理念,为中国翻译文学的现代转型做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引领中国翻译文学在现代化轨道上飞奔疾驰,并在诸多方面凸显了现代性的特征。他和胞弟周作人于1909年合作编译的《域外小说集》是对现代性之美的求索、体验和发现,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第一座丰碑,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在许多方面都显示了突出的超前性质、先锋意义和历史价值。由于种种原因,《域外小说集》在当时销路惨淡滞涩,读者反应冷清淡漠。十多年后,随着周氏兄弟在文坛有了相当的地位和话语权,此书增订、合订本又曾再版。然而其价值被真正发现和认识,时光已过去四十年了。1959年,冯至说:“我们不能不认为它是采取进步而严肃的态度介绍欧洲文学最早的第一燕。只可惜这只燕子来的时候太早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冰封雪冻的冬天。”[1]474到时下,《域外小说集》自然已成为热门话题。从整个研究格局来看,对其催生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形态、推进翻译策略的现代转型和加速图书装帧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功绩以及透露出来的现代性质的研究总结,仍是当务之急。
一、鲁迅早期翻译文学活动和《域外小说集》的成书情况
鲁迅自1902年赴日本留学,初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退学,返回东京后抱定用文学启蒙救国、改造社会的志向。次年夏筹办《新生》,因“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2]439而未果,旋即将所有为其撰写的宣扬新思想的文稿投向《河南》杂志,同时又陆续与周作人用文言语体翻译了一些短篇小说,于1909年3月和7月结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第二册在东京出版。这是周氏兄弟翻译小说的合集,亦可视为他们的第一部翻译文学专书。鲁迅的文学翻译活动始于他东渡日本的次年,当时他曾根据森田思轩日文译作——法国雨果《随见录》中《芳梯的来历》转译成汉语《哀尘》。“芳梯”今多译为“芳汀”。在《随见录》里,《芳汀的来历》“是一篇随笔或速写,当后来雨果写作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的第一部《芳汀》时,曾把这篇文字发展成为该书第五卷的第十二章《巴马达波先生的无聊》和第十三章《市公安局里面一些问题的解决》,人物虽稍有不同,但情节基本上是一致的”[3]133-134。它被称为“鲁迅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篇作品”[4]109,发表在1903年6月15日出版的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所办的《浙江潮》第5期上,有译者附记,署名庚辰。此后鲁迅求学于日本的数年间,在科学救国理念的驱动下,翻译了不少科学撰述,体裁兼及小说、诗歌和论著等。与此同时,他还十分热心于林纾的翻译小说,购置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林纾的作品。鲁迅精通日文、德文,以二者为翻译工作语言文字。他的翻译作品中,原作用日语或德语写成的几近半数,其余皆为通过日语、德语转译的俄语或北欧、东欧等小语种作品。
如果说《哀尘》标志着鲁迅留日时期翻译文学活动的辉煌起点,那么,六年后的《域外小说集》则完全可称为其这一阶段翻译文学活动的制高点。此书凡两册,第一册收7篇,第二册收9篇,体裁包括小说、童话、寓言等。16篇作品中,含有英、美、法、芬兰4国各1人1篇,俄国4人7篇,波兰1人3篇,波西尼亚1人2篇。每册后附本册的“以后译文”和单行本的“新译预告”。根据已出的16篇和诸多待出作品以及“略例”所言“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短篇小说)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东方)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5]170,可以看出鲁迅早年在文学译介方面视野之开阔、志向之明确、目标之高远、计划之盛大。第一册、第二册所选篇目的思想内容倾向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以及被压迫的弱小国家民族的反抗和呐喊,体现了鲁迅着眼于严肃文学和先进文化、引导读者了解异域优秀文艺作品,移植对于启蒙济世、唤醒国魂有裨益的译介宗旨。第一册中安德烈夫《谩》《默》和第二册中迦尔洵的《四日》是鲁迅翻译的,其余13篇皆为周作人所译。不过,某些周作人所译小说中的韵文,如显克微支的《灯台守》引用的密茨凯维支诗等亦出自鲁迅的手笔。在全书的整体筹措经营中,鲁迅起了主导作用。他不仅就这部小说集的创意、筹划、选题、搜罗、审择、集录、选择、鉴裁、排列等编纂事项事必躬亲,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而且在将它组合加工成一定的文化符号模式的整理、编辑、校订、付排,乃至印刷、制作、预告、发行等一系列活动流程中花费了很多的气力。从兄弟二人各自承担工作分量来看,可以说,周作人译得多,而除此之外的一切工作则几乎全由鲁迅来完成。周作人谓鲁迅在“字型和行款,纸张,从旧德文的文艺杂志上借用来的图案,许寿裳(此处回忆有误,实为陈师曾)写的篆字题目都很经过一番经营”[6]36。
鲁迅曾说到他“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7]176。不幸的是,只出到第二册便停顿下来。然而周氏兄弟仍以知难而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毅力在这块当时中国文学“新大陆”上辛勤耕耘。十多年后,周氏兄弟的成就和地位足以吸引世人的眼球了,于是“有几位著作家,忽然又提起《域外小说集》,因而也常有问到《域外小说集》的人”[7]177。1921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刊行了增订、合订本《域外小说集》。它在1909年东京版的基础上,又加上周作人于1910年至1917年间断断续续以文言翻译的21篇,共37篇。周作人所译34篇都经过鲁迅修订润色,旧版中太生僻的字也被改了不少。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氏三兄弟的《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共收短篇翻译小说30篇,其中鲁迅所译9篇,周作人所译18篇,周建人所译3篇。这两种都堪称《域外小说集》的续书。其选目也都突出地体现了鲁迅一以贯之、坚持不懈的宣传国外优秀文学、广泛涉猎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方针。前者在原有的16篇基础上,强国中只多出法国1人5篇,其余所增加为丹麦、俄国、希腊各1人1篇,原来已入选的波兰显克微支又加了1篇;后者所辑入,除了海上强国西班牙1人1篇外,其余为爱尔兰、俄国、波兰、芬兰、保加利亚、希腊、亚美尼亚共7人29篇。不同的是,《域外小说集》是用文言翻译的,而《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则是用白话翻译的。后者标明第一集,说明编译者有长远的规划,不幸的是,由于兄弟失和而夭折。
二、《域外小说集》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叙事文本体制
《域外小说集》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叙事文本体制的建构发挥了巨大影响。中国引进、翻译西洋小说的历史至少肇始于18世纪。1740年左右(乾隆年间)欧洲人携《圣经》等宗教典籍来华,伴随着圣经故事流播于中土的还有《伊索寓言》等。但这些文本中的人名、地名等称谓和涉及的风习、仪式等全中国化了,甚至大多只署译者之名,几乎接近于原创。嗣后,蠡勺居士于1872年翻译了19世纪中叶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由上海《申报》馆于1872年11月筹办的中国最早的文艺杂志《瀛寰琐记》(曾先后易名为《四溟琐记》、《寰宇琐记》)第3卷连载,持续到1879年停办。1896年,上海《时务报》曾连载过张坤德所译4篇描写呵尔唔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短篇小说,这是《域外小说集》之前中国人翻译西方短篇小说之先例。1898年,有“译界之王”誉称的林纾所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随后林纾众多译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风靡席卷之势盛行于广大读者群体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引发了大规模的西方小说汉译活动,一改此前译界疲软、萎靡之状。鲁迅兄弟也是“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的”[8]152。他们的《域外小说集》是步林纾其后的又一重要译作成果。
当时,流行于读者群体中的翻译小说绝大多数是林纾的长篇之作。林纾虽然在创作上受其所译西洋长篇小说的影响没有采用章回体小说的体制,但在翻译时出于作品市场流通效益的考虑,也尽可能地将原作与中国传统审美旨趣、价值观念、社会风习以及读者的接受心理定势和阅读习惯彼此接轨、吻合,甚至将西方故事披挂上伦理包装,亦即“外国故事中国化”,即使以牺牲原作的核心理念和艺术精神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在形式上也极力向中国数百年间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章回体靠拢,因此也比较适合中国读者的口味,带有浓重的“归化”色彩。鲁迅兄弟完全了解这一点,但出于为唤醒民众、改造社会而引进先进的文学观念和文体类型的考虑,他们义无反顾地将目光挪移至长篇小说之外,特地译介短篇小说,所选译的作品皆为在思想性、艺术性两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之篇什,在国人眼前展现出一片新的天地,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破天荒地使中国读者见识了这一来自异域的、在形态和风格上都与传统叙事小说样式迥然有别的新文体,开创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新纪元。鲁迅自谓:“《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7]168这番话确是译者心声之表露。
周氏兄弟对其他国家短篇小说作品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见长、注重故事性的态势,体现了新的审美观和小说创作观的多元取向。中国传统小说与说书艺术血脉相连,始终受制于话本体制的技巧章法,带有浓郁的“说话”痕迹,为发挥“说话人”的才气和作品对受众的吸引力,历来将情节的审美功能置于核心地位,极力追求情节的曲折委婉、奇险生动、跌宕起伏和故事的完满整一、前后相顾、首尾齐备,并嵌入许许多多的穿插敷衍。长篇皆为章回体,短篇也千篇一律地固守一成不变的格式并充斥一大堆套语,散文和韵文相间互补,叙述人语言皆采用第三人称,叙述语言的主体即作者,开头以“话说”引出故事,接榫处卖关子弄玄虚,结尾时以说教收束。一般来看,性格、心理和背景的描写大多采用粗线条笔法,缺乏静态、深细、专一的刻画。在叙事角度方面,全知叙事模式占居主导地位,像《红楼梦》这样能在全知、限知之间游刃有余地不断移步换形、灵动活泼、转接自如的作品寥若晨星。林纾不懂外文,翻译的小说是根据别人讲说再度复述,这种“述译”也没有从本质上彻底摆脱传统小说的痕迹。《域外小说集》的历史性意义就在于,它基本上“拿来”西方短篇小说的文体形态切换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古典型模式,尽可能干净、利落地突破了“说话”的窠臼。阿英把周氏兄弟与林纾进行对比后说:“周氏弟兄翻译,虽用的是古文,但依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晚清翻译小说,林纾影响虽是最大,但就对文学的理解上,以及忠实于原作方面,是不能不首推周氏弟兄的。”[9]187-189时隔九年,鲁迅又发表了有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小说之誉称的《狂人日记》,正式拉启了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序幕,并同很多新小说家一道,创作了很多现代性质的短篇小说,拉动中国小说进入了新的时代。诚如郁达夫所言,“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现代我们所说的小说,与其说是‘中国文学最近的一种新的格式’,还不如说是‘中国小说的世界化’比较的妥当”。[10]418
严家炎曾从内容的现代意识和描写对象、性格小说的出现、一系列新的小说结构和体式的产生、叙事视角的变革、重视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各种新创作方法的运用六个方面阐述了五四时期小说的现代性。[11]21-22毋庸置疑,这些现代性的表现都发端于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周羽认为此书中16篇译文包括四大类:在叙事模式和文本体制上与传统小说大抵相同或贴近的如淮尔特《安乐王子》、斯谛普虐克《一文钱》和显克微支《乐人扬珂》;描写生活的某个片段、基本符合胡适“横截面”说法的如契诃夫《戚施》和《塞外》、穆拉淑微支《不辰》、显克微支《天使》;属于早期心理小说的如迦尔洵《邂逅》和《四日》、安特来夫《谩》;以抒情化和散文化取代或淡化故事性、情节性的如亚伦·坡《默》、摩波商《月夜》、安特来夫《默》、显克微支《灯台守》、穆拉淑微支《莫诃末翁》、哀禾《先驱》。他认为其中后三类都代表了突破中国传统短篇小说的写作范式的路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早产的小说译文集在引进现代小说艺术图式方面所做的多方面的尝试,足足领先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理论的正式提出和本土现代短篇小说创作的跟进,差不多十年之久”[12]154。鲁迅翻译的三篇都以心理刻画见长,开中国现代心态型小说之先河,特别是《四日》,着力于意境和氛围的营造,文本结构中布满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与唐宋传奇小说和宋元说话四家中的“小说”于曲折离奇、波澜起伏的情节和人物的动态化言语、行为中流露心理活动的写法形成鲜明的对比。“鲁迅不仅改写了小说翻译史上的色调,也开启了文学翻译新的风气”[13]。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对于推动中国小说现代转向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鲁迅在译介域外文学、探索新的小说艺术图式方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尝试过很多途径和方法。他早期译过不少长篇科幻小说,其中相当数量的作品采用了章回体。当然,他终于找到了最能体现自己宏旨的方向。胡适认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这“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就是“一人的生活,一国的历史,一个社会的变迁”之“横截面”。[14]37前面所述张坤德的福尔摩斯探案短篇小说是零散披露于报纸上的,虽得沉湎于侦探小说的读者青睐,但情节千篇一律,皆以案发开场,以告破结束,更没有突破传统短篇小说前后照应、头足俱全的藩篱,未能体现“横截面”的特征,对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向没有产生丝毫的影响。林纾和魏易于1904年合译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于1907年合译的美国欧文的《见闻杂记》(即《拊掌录》)也均没有透露出现代性的信息。而《域外小说集》则是中国人翻译、结集的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著作,它使国人开阔了眼界,领略到与传统长篇巨帙面目迥异的短小精悍的新叙事文体,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活力,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形态和文本体制的基础,其划时代意义和前沿性蕴涵是不可估量的。然而这些反倒令其一出世就陷入命运多蹇、颇遭冷遇的境地。究其原因,其一,当时中国读者中,沉溺于传统长篇叙事习惯的人不欣赏西方短篇小说的模式,“《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7]178;其二,大量迷恋侦探、言情、世态小说的人又过于注重情节的生动委曲和人物性格的近情近理,而忽略思想价值;其三,青年时期的周氏兄弟初出茅庐,名气有限,也是此书未能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因素。《域外小说集》自然与国内接受群体的期待视野、阅读口味和审美情趣有所龃龉,因此销路不够理想。尽管如此,第一册出版后不到两个月就引起了日本人的关注。1909年5月,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就登出简短报道。鲁迅执着地宣称:“只是他的本质,却在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便在将来也该有存在的价值。”[7]177这番充满自信的话语的分量只有到今天才能够被人体味出来。这个“本质”,正是其超前性和现代性。完全可以说,《域外小说集》的空谷足音回荡着新时代文学之声息,是昭示中国小说现代转向的路标。“对照一下《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和他的小说的异同,就会发现彼此的关联。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始自于外来文学的催生,是确确实实的。”[15]15
三、《域外小说集》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语言转换策略
翻译的性质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林纾使用的虽是典雅的文言语体,但在词汇、句式上已带有相当的西化印痕。这无疑对于当时中国翻译文学的语言建构起了风向标的指示性作用,也为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和表率意义的参照系。说实在的,《域外小说集》初版时销路阻梗,“佶屈聱牙”委实也是一个使受众望而却步的原因。固然,文言在中国传统社会历来被视为高雅的话语形态,流行于上层文人中,文学作品为了提高自身的地位,获得处于社会主流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和首肯,采用文言也不失为一种智慧性的选择。然而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毕竟是多数。近代西方传教士就十分聪明地觉察到这一点,在华的教职人员于1890年在上海集会时议定建立三个部门分别用文言、浅近文言、白话翻译《圣经》,则是完全出于使教义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收到理想的传播和接受效应的考虑。尽管如此,仍不能把周氏兄弟选择文言语体完全看成是一种失策。作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译作产品,《域外小说集》确实未能完全脱尽时代的胎记,仍使用了典重古雅的文言语体。然而,若由于这一点否认它在翻译手段和策略上的有益的而且是成功的尝试和努力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实际上,它在推动文学翻译理念、方法的更新嬗替和引领翻译策略的现代化方面摸索出了较为理想的途径。
美国翻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在其出版于1995年的《译者的隐身》一书中提出归化和异化理论,认为归化采用目标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向读者靠拢,而异化则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向作者靠拢。前者即“意译”,后者即“直译”。周氏兄弟在对原作进行语言转换时虽选择了文言,但却严格遵循了直译的原则,特别是鲁迅,而这种方法在当时并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采纳。鲁迅早期的翻译活动实际上跟林纾大致是一个路子,“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如《地底旅行》《造人术》等带有明显的意译倾向,《月界旅行》更是将“其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16]164,而《斯巴达之魂》则被认为是一篇“译述”之作恐怕亦不为过。鲁迅后来曾追悔说自己“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17]99。但是,他终于在编译《域外小说集》时选择了直译,而且这一信念终生不移,并在其后的许多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硬译”之说。鲁迅从事翻译伊始,就表现出对翻译方法的自觉意识,这的确是他高出时辈的地方。
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的翻译方法一直是“译述”,即执笔者将通晓外文的人讲述的内容再用汉语表达出来,这种模式与其说是语言转换不如说是文义转述。此法自汉代翻译佛经以降一直沿用着。清末在华西方教会译介教义及相关著述和中国官办翻译机构译介西方科技知识也大都是依循这种办法,西洋教职人员口授而中土知识分子记述,特别是在早期。林纾本人不谙外文,依靠别人的讲述而加以润色,重新编写成“译著”,并且为了追求“归化”效果随意删减原作中的环境描写和心理刻画而仅通盘保留其故事情节,如《黑奴吁天录》就是明显的例子。对于其翻译方法属于“译述”还是“意译”,虽然人们的看法有所出入,但他绝对不可归入“直译”一派,这一点的确是不刊之论。随着翻译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翻译质量尤其是准确性的问题自然而然地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鲁迅曾说:“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对此不满,想加以纠正。”[18]196他所谓林纾的“误译”,当指“译述”之弊和“意译”之疏。当时中国的翻译家重视作品的可读性和接受度而忽略忠实于原作的技术诉求,对受众的审美趣味、阅读取向以及本土的伦理型文化特色考虑得多,也没有什么规范可资依据,在翻译中往往任意增减内容、本土化各种称谓,甚至改动原意。这种任性的中体西用式的“豪杰译”文风也是一把“双刃剑”,虽有助于激活读者在文化思想、民族心理方面的认同感,但也有损于文化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的异质感。这与鲁迅打开国人眼界、引进带有异质因子和进步思想的优秀文化以及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理念相抵牾。鲁迅对直译方法的选择绝非偶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认为只有秉持忠于原作、“弗失文情”、“任意删易,即为不诚”的原则,采取直译的表达方法才能够确保外来文化和新思想的真实性、精准性和整一性。周氏兄弟独具慧眼,特别心仪当时十分罕用的直译方法,在翻译中尽可能自觉地尊重、对应、保留原作中原汁原味的体式、顺序甚至语气,对人名、地名等皆用音译,甚至不顾那些浸淫传统文化很重的文人反对而使用叹号、问号、省略号和破折号等西式标点。许寿棠曾把鲁迅所译三篇与德译本对照,发现它们“字字忠实,丝丝不苟”,毫无任意增删、改动之处。[19]31
《域外小说集》虽用文言,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现代化,它把文言这一传统文化和文学的载道器物和流播媒介拨向“西化”乃至“现代化”的轨道,它所引入的一些西化的话语资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语言建构也有一定的铺垫和先导意义。所以说,周氏兄弟在晚清的这一尝试性努力具有突出的反拨和创新意义,在翻译策略上的直译技法明显透露出了现代性端倪。尽管从事物二重性和辩证法的角度来看,这种直译有时也难免失于矫枉过正,但总体来看,其积极效用和正面意义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当然,这样认识和阐明问题和肯定鲁迅的翻译策略不等于走极端,更不是完全否定坚持归化取向的意译。
四、《域外小说集》与中国现代图书装帧美学和广告艺术
鲁迅天分甚高,自幼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勤学苦练绘画技巧,打下了坚实的功底,临摹书中插图的水平常为长辈亲友所惊叹赞赏。在他步入文坛后,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这方面惊人的才能。他与许多书业界著名装帧设计家往来密切,对书体版式设计的热情有增无减,对美术和装帧的审鉴能力也日益提高。他被誉为“我国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开拓者、开山人”,是“五四以后第一个在他自己的作品上讲究装帧的实践家,他把封面设计、内容编排、印刷装订、选字、选纸等几个环节协调统一起来,使之净化而又美观,开创了书籍装帧的新局面”[20]61。《域外小说集》是他从策划鉴选、翻译编纂到校订编排、版式设计、印刷发行全程亲自主持、经营的第一部书,也是他从事现代图书装帧实践的第一部书。它与旧式书籍的外在形式完全不同,“装订均从新式”[5],在装帧技术上充分显示了其多才多艺的大手笔气质,也灼灼闪射着突出的现代特质和属性。其现代性主要反映在封面、扉页、插页设计和采用毛边装两个方面。
《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初版时,鲁迅亲自选购上好的洋纸为印制材料。封面采用罗纱纸(一种类似于布纹纸的高级纸材),底色为灰绿(或谓青灰),书冠由带状图案和小篆书名组成。图案选自旧的德国文艺杂志(或谓外国画册),呈长方形,精致雅洁,庄重和谐,位置和大小也十分妥洽,上面画着古希腊主司文艺的女神缪斯在旭日初升之际弹奏竖琴的情景,神态闲雅超逸、优游不迫、自然柔美。它标志着作品的性质,不但昭示着书中的内容来自异域,而且寄寓着编译者以文艺唤醒国魂的殷切渴望。鲁迅特别喜欢采撷中外美术作品为书面装饰,一生乐此不疲。移用刊物中插图于封面,此法在当时亦为首创,时至今日仍有人沿用。“在这个封面中,鲁迅以一幅外国油画作为衬托的背景。画面中,诗神缪斯从昏睡中苏醒,迎接初升的太阳。但从封面本身而言,这幅油画似乎仅仅是为了装饰。联系鲁迅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正是这幅油画在这个封面中的存在,含蓄地反映了鲁迅当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以催生中国人的希望的目的,反映了鲁迅当时已经由办《新生》杂志时的‘只拥有希望’发展到了实现希望的阶段”[21]49。图案下方的小篆体书名五字乃鲁迅好友、国学家陈寅恪之兄、著名美术家和艺术教育家陈师曾(陈衡恪)题写,深蓝色,从右到左横排,秀挺圆熟,明净柔润。最下端为“第一册”三字。“整幅书面,配置得错落有致,典雅悦目,呈现着一种朴素而明朗的美感,即从封面装帧艺术的倡导来看,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就为新文艺拓展了新生面”[22]115。整个封面的设计匠心独运,别开生面,构图雅洁,搭配得体,浑穆凝重,淳朴沉实,韵致优美,意境清深,特别注重图案纹饰和书名题写,凸显了极强的突破、变革和创新精神,很有现代气质。鲁迅对自己在书籍装帧革命之途迈出的第一步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喜悦快慰之情:“至若装订新异,纸张精致,亦近日小说所未睨也”[23]。
《域外小说集》扉页、版权页和其他插页的设计也很有现代气息。扉页的右下角印着“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相当于署名。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只写巳酉(公元1909年)而拒署满清帝制纪年,第一册、第二册的具体出版时间分别为此年的夏历二月二十一日和六月十一日。除此之外,还分列式地印着有关诸项内容,包括发行人周树人,印刷者长谷川辰二郎,印刷所神田印刷所,总寄售处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纪弄广昌隆绸庄。该书是由与周氏兄弟一道留日的浙江籍好友、著名儒商和银行家蒋抑卮出资付梓并帮助经销的。蒋氏家资甚饶,为人义气,出手大方,动辄曰“拨伊铜钱”(浙江话,意谓“给他钱”),尝从章太炎学古文字音韵,多次向进步刊物和图书馆捐资、捐书。“广昌隆绸庄”乃其家商号之一。由此看来,处于当时民营出版业逐渐取代官府和教会经营的印书业而成为书业主流的历史背景下,鲁迅在筹资出书和自费出书方面,也走在时代的前列。封底里(封三)载有广告二则,即本册的“以后译文”和单行本的“新译预告”。这一做法不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书体空间,而且也起着广告宣传的作用,有助于以后诸册的发行流播,体现了文化意识和商业意识的有机统一。这些要素都透露出与传统古籍的形式分道扬镳的端倪,凸显了现代出版物的性质。
鲁迅对“毛边书”情有独钟,自称“毛边党”,积极倡导毛边装。毛边书又称毛装书、未裁本,本为舶来品,源自欧洲法、德、英等国,相传这些国家的出版社曾印制、供应贵族阶层毛边书,这些有闲之人借以享受手执刀具、边裁边阅之惬怀。它后来传至日本,渐渐推广开来,其意义已偏离了贵族化、沙龙化,而演变为一种主要流行于文人圈、有现代意蕴的书籍文化。毛边书在中国已有百年风流,它始见于晚清,或谓西方传教士传入,或谓来自日本,后来悉数亡佚,故《域外小说集》一般被视为首创。直到如今,我国某些出版社还专门推出过毛边书,或根据作者的要求制作一定数量的毛边书,甚至有些杂志也每期单另印制若干免裁本以馈赠名家和同好。毛边书的特点是装订成册后,免掉最后一道工序——切边,保留书口原样,读者阅览时,必须亲自动手逐页裁割。这种形式的优点是书籍版面显得开阔、疏展、天成,呈现出朴实无华之美、参差错综之美、落落大方之美、自然粗拙之美、简率原始之美,也使读者在边裁边读过程中领悟到莫大的乐趣。所谓毛边,其实也不拘一格,或三边皆毛,或两边毛而一边光甚至一边毛而两边光。像《域外小说集》初版采用书顶、书根和书口全毛的样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5],可谓彻底、正宗的毛边书了。它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第一部毛边书,历来被视为中国新文学毛边书之始祖,有十分突出的开创意义和启迪作用。
图书是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售书广告的作用和地位亦显而易见。鲁迅十分重视广告对于书刊发行、传播的意义,并常常亲自动手拟撰广告。鲁迅的广告观也明显突破了传统,凸显了现代性,其最大特点就是兼顾文化属性和商业属性两个向度。从其《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可以看出他十分看重广告的真实性和信誉度,认为刊登广告是严肃的事情,应对读者负责,不能片面追求促销赢利,要慎重、诚实,鄙薄名不副实、有名无实之辞,反对褒贬过当、不着边际之语,力戒阿谀奉承、炫耀溢美之举,避免矫饰造作、文过饰非之态,摒除掺假掠美、浮夸吹嘘之风。他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撰写的广告堪称精妙绝伦、脍炙人口的佳品。它首先说明本集的性质“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渺”;其次,介绍编译之旨趣是“各国竞先选译,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揭示了这些域外小说在思想底蕴方面的价值;复次,说明自己的翻译工作目标是“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再次,描述书的内容是“先成第一册,凡波兰一篇,美一篇,俄五篇”;又次,谈其创新意义是“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接下来交代书体装订之新异和纸张之精良,乃时下小说之冠;最后说明售价和邮购地址并署名。[23]455全篇激情充盈而文字淳朴,内容详尽而重点突出,抑扬有致而出语平实,客观公正,坦率直白,切中肯綮,令人叹为观止。
《域外小说集》彰显了突出的现代性特质和路向,对推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功不可没,是一笔宝贵的文艺美学资源。若将《域外小说集》置于延伸度和扩展度更大的历史时空坐标去考察,其意义也是异乎寻常的。中国翻译史上曾出现过汉唐佛经翻译、明末清初耶稣教典籍和西方科技知识的翻译、清末民初伴随着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而兴起的《圣经》及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三次热潮。中国近代、现代的翻译文学是第三次热潮的必然产物。这一阶段的翻译热潮,是在“西学东渐”之风的影响下掀起的,并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和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三十年间出现过两大峰巅。鲁迅着手从事翻译出版活动时,正值第二个峰巅时期。此时一大批有跨文化学养、素质的知识分子加入进来,成为了新的生力军和译坛主流,改变了前一个峰巅时期以西方教会操办和洋务派主持的两大译业垄断的格局,并开疆拓土,把域外文学的引进工作也纳入这一领地。他们有胆有识,以卓绝超特的文化担当理念、勇气和志向,承载起推动中国翻译文学现代转向的历史使命。作为这批文化精英中之翘楚和文坛泰斗,鲁迅凭借超人的远见和睿智,敏锐地抓住机遇,寻索到现代转向的突破口,为中国翻译文学增添了新的基质,并通过亲身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诞生其实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晚清是中国挣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极力寻找出路的时期。林纾引动的小说翻译风生水起、波澜壮阔的局面实际上只能给人以“风景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处于老态龙钟的社会背景中,当时的译苑也正值迟暮隆冬。时代呼唤着东风春燕,急切地盼望着革故鼎新、探寻新径的天才。《域外小说集》应运而出是历史的必然。一花引来万花开,《域外小说集》问世不久,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翻译文学也如火如荼地勃兴、发展起来,逐渐与原创文学并驾齐驱,构成文坛的两大主干,使中国现代文学极大地丰富了自身蕴涵,深化了思想底蕴。如前所述,这部文献的历史价值已远远超出了翻译文学领域。我们用今天的眼光回顾和审视《域外小说集》的成就和功绩,考察和领悟其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观念,更深切地认识到这笔文化财富的珍贵价值。
[参考文献]
[1] 冯至,陈祚敏,罗业森.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G]//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鲁迅.呐喊·自序[G]//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戈宝权.关于鲁迅最早的两篇译文——《哀尘》、《造人术》[J].文学评论,1963(4).
[4]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 鲁迅.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略例[G]//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 戈双剑.鲁迅:生存与“表意”策略[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7] 鲁迅.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序[G]//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周作人.关于十九篇小引[G]//周作人自编文选·苦茶随笔.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9] 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0] 郁达夫.小说论[G]//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1]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2] 周羽.清末民初汉译小说名著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D].上海:上海大学,2009.
[13] 鲁迅首先是位翻译家:从没想过“永垂不朽”[EB/OL].[2006-12-05].http://www.huaxia.com/zhwh/whgc/2006/12/93728.html.
[14] 胡适.论短篇小说[G]//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5] 孙郁.译介之魂[J].中国图书评论,2006(4).
[16] 鲁迅.译文序跋集·月界旅行·辨言[G]//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7] 鲁迅.书信·致杨霁云[G]//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8] 鲁迅.书信·致增田涉[G]//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9] 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20] 杨永德.鲁迅对现代书籍装帧艺术的贡献[J].中国出版,2000(4).
[21] 谢清风.鲁迅的封面设计思想[J].编辑之友,1998(3).
[22] 胡从经.胡从经书话[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23]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域外小说集(第一册)[G]//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