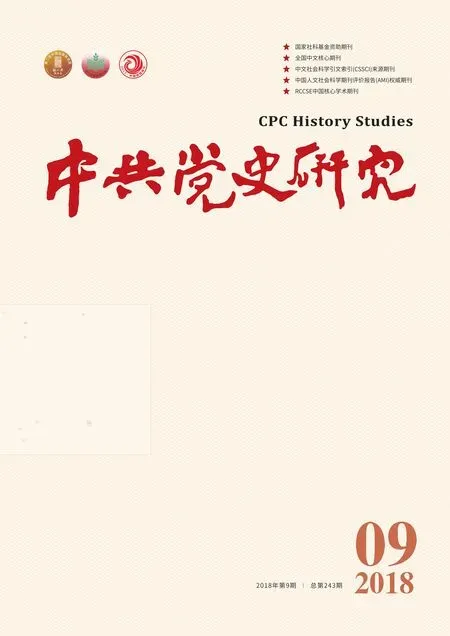知青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郑 谦
一、科学的知青史研究离不开对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
近十多年来,由于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及历史知识的欠缺,在民间或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倾向或思潮,即多少肯定“文化大革命”或其中的一些内容,其中就包括了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某种过多的肯定。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慎重,以往一些权威的分析和结论还应尊重和坚持。例如,邓小平对此说过“三个不满意”。又如,在199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对“文化大革命”中知青运动的结论是:“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47页。。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的相关论述。这些分析和结论都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是应当坚持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运动不是孤立的。如同当时的“三支两军”、干部下放、教师下放、工人下放,以及文艺工作者、医务人员以至工人、城镇居民下放一样,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产物和表现,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举措对“文化大革命”来说是合理的,有的甚至是必要的、必需的。例如,当时的知青运动既有意识形态因素(如消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4页。,解决“再教育”“反修防修”等问题),又有安排大量城市待业人口等十分现实、紧迫的因素。毕竟,不把1700万知青下放到农村,城市消化不了,数百万没有选择的学生既升不了学,又不能就业,后果会更严重。可是,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显然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这样一支庞大的知青大军。这与“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并不是一回事。又如,若是没有实行“三支两军”,动乱局面就难以收拾,后果十分严重。为此,只能让解放军出面恢复秩序。但是,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天下大乱”,无疑也就不必“三支两军”了。再如,当时干部下放的直接原因是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大量裁减干部[注]1968年大多数省级革委会成立时,根据“精兵简政”的要求,全部工作人员只有150人至200人左右,为原省委、省人委工作人员的1/20或1/30。广东阳山县革委会成立后,行政业务人员从原来的1126人精简到284人,全县19个公社原有干部554人,精简为173人。参见《广东阳山县革委会成员深入厂矿、社队广泛听取工人和贫下中农的意见 依靠工人和贫下中农实行精兵简政》,《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一大批精简下来的干部无法安排,大多数只能下放农村或“五七”干校。举例来说,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10月至1969年10月,黑龙江、辽宁等七个省市先后下放的干部有40多万人(基本上是县级以上机关的干部);某省同期先后有87万多名干部、教师、医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下放到农村;另一省则有7万名干部、5.3万名教师、1.2万名医务人员、1.6万名职工,以及15.5万名家属下放农村安家落户;如此等等。更有甚者,如果干部的配偶是工人、营业员,一般都要动员她(他)们与干部一起下放。1968年至1969年,把城市人口大规模下放到农村成为一股空前的汹涌大潮,是否下乡甚至成为“继续革命”的试金石。诸如此类的运动、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和结果,不如此,“文化大革命”便不能维持。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这是党中央严肃的政治结论,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基本背景和依据。当时的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左”倾理论与实践的产物,是轻视文化、轻视知识分子、轻视学校教育、轻视课堂教学、轻视书本知识的结果,是非城市化的产物。用这样大规模人口逆向流动的方法,不可能消灭“三大差别”,也不可能从总体上达到教育好知识青年的目的。如果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那么“三支两军”、干部下放、城镇居民下放以及当时诸多“新生事物”岂不是都要肯定?只要想想知青为了离开农村而普遍“走后门”(即毛泽东所说“全国此类事甚多”[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以及“文化大革命”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出现知青以“病退”或其他形式返城的风潮,理解这一点并不难。诸如此类的做法无非是以一种特殊形式表达不满或抵制。方向、方法上的失误决定了这种下放是不可持续的。没有“文化大革命”,肯定还会有其他各种形式的下乡,正如“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一样,但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中那样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为基础、用政治运动的方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把一千多万人下放到农村的下乡。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广大知青在农村经受了艰苦劳作的锻炼,加深了对农村、农民、底层的了解。他们向农民学习,比较深入地了解到中国的国情,学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这对于他们后来的发展都是有益的。知青运动中,还有不少先进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自己也得到很多锻炼和收获,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但这些并不能成为肯定“文化大革命”中知青运动的根据。
这正如党的历史上,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使革命事业遭受了惨重损失,特别是1931年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白区革命力量损失100%,红区损失90%。但是,这种总体上、方向上的“左”倾错误丝毫不能抹杀广大党员、干部、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斗和忘我牺牲;反之,他们的英勇牺牲也不能成为肯定“左”倾错误的根据。又如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自发地抵制这场运动,坚持工作,维持生产,我国的工农业也有所发展,但这些显然不能成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依据。反之,“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不能成为否定他们努力的依据。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运动是一个很复杂的事物,有许多侧面和观察角度。如果只是从个人的、感性的角度看,绝大多数知青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魂牵梦萦着那方曾经挥洒汗水的土地,怀念那段动荡的青春年华,一方面又为那段蹉跎岁月黯然神伤。这种矛盾是深层的、本质的、普遍的、正常的,是研究知青问题的钥匙、精髓和要义。笼统地提某种精神或“无悔”,可能把问题简单化。作家阎纲回忆“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在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经历时说:“怨也向阳(湖),念也向阳(湖)。”[注]阎纲等编:《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98页。这种矛盾心理多少代表了知青的普遍感受。无论是过来人还是研究者,都应自觉地掌握这种在矛盾中把握事物的能力。
二、怎样处理当时的认识与当下的认识
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历史与现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注]〔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5页。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变迁、思潮往往会投射到对历史的认识中,并对其造成影响。以当下解释历史、认识历史,或用历史来服务当下,往往也是实现历史功能的一种方法和途径。例如,苏联、俄罗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反反复复,往往与其现实需要密切关联。又如,近几十年来,针对道德滑坡,人们四处寻找解决之道,其中就有力图复兴儒学的“新儒学”一派,他们希望用这种历史资源来服务现实。再如,从史学上看,郭沫若1944年《甲申三百年祭》的学术价值并不高,但中共当时为了解决党内骄傲自满问题而推荐了它,让历史为现实服务,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种历史与现实永无止境的对话中,人们一方面深化了对历史本然(真实)的认识,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历史所以然(规律)的掌握。这种站在当前角度反思历史的做法,有可能使人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获得新知,接近信史,也有可能出于某些现实需要而倒向实用主义,以研究为名悄然改写历史。例如,前些年社会上严重的腐败问题、贫富不均问题、特权问题等,就直接影响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看法,甚至出现了一些罔顾事实、为“文化大革命”叫好的声音,希望用这样的方法反对腐败、特权,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发泄不满的出口或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知青史研究也曾出现这种情况,如因对高考制度的不满,对青年思想状况的担心,对农村“空心化”的忧虑等现实问题,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是应当肯定的。这些忧虑固然有道理,但因此肯定“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则是错误的。历史研究必须靠事实说话,从史实出发,而不能误入“需要引导、态度先行、真相缺位”的“后真相主义”歧途。知青史研究应当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应当有“经世致用”的追求,但也要注意在无止境的解释与再解释中保持正确的方向,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科学的历史观照。
三、注意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这里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断完善知青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在近40年的研究中,一些严谨的学术规范已经相继建立起来,但仍有一些尚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要注意一些基本概念的准确性、明确性和同一性,防止因概念不清而陷入无谓的争论。例如笼统地提知青运动,而不区分“文化大革命”中与“文化大革命”前,这就不好进行正常的研究与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前的知青运动有共性,也有明显差别。共同点在于二者都强调与工农相结合,都是到农村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都作出了贡献,从形式上看也有一些共通之处。不同点在于二者的指导思想、历史背景及结果有很大差别。“文化大革命”前的知青运动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村建设人才缺乏及城市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尽管具体工作中有一些缺点,但目标是正确的,也基本上实现了,这是必须肯定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运动则是在“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依靠阶级斗争扩大化方式进行的,“再教育”的指导方针从总体上看是不能肯定的,其后果从总体上看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知青运动中的“走后门”现象和大规模的“病退潮”“返城潮”便是证明。总之,两者的差别是明显的,无法放在同一概念中进行讨论。
现在又有人把青年学生到农村当“村官”等做法称为上山下乡,这同样是未能注意概念的适用性、历史性和严谨性,不加区别地把现在到农村工作等同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这一特定时期出现的特定运动。诸如此类的引申忽视了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如同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的“继续革命”理论,如果仅从字面上看并无不妥,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人仍然继续使用这一概念,但这显然是错误的。“继续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赋予特定的历史内容,不能无条件地照搬到其他历史时期。
再者,要注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避免两极化、情绪化、极端化,要善于在矛盾中把握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是多种侧面的统一体,在大体相同的共性后面,还有多种十分不同的个性差异。如“老三届”与“新三届”的差别[注]“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政策调整,相当一部分“新三届”学生的下放往往是升学或就业前的一个过渡,这已与“老三届”大不相同。,运动前期与后期的不同,有特权与无特权、“红五类”与“黑五类”知青境遇的差别,地方干部政策水平差异对知青运动的影响,下乡知青与回乡知青的分野,到富庶地区与到贫困地区的明显差距,去兵团与到农村的分别,插队时间长短的感受,如此等等。这些具体境遇、经历、感受的差异是后来者很难体会到的。同时,还应特别注意将个人经历、感受与对运动的总体把握区分开来。
四、在不断发掘基本资料的同时,深化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
有一个问题似乎未能引起某些知青或知青史研究者的充分注意,这就是1968年底开始出现的知青下放高潮,只是当时遍及全国各行各业下放大潮的一部分。1968年至1969年间,干部、知识分子、医务人员、文艺工作者、知识青年,以至工人、城镇人口大规模地到农村下放、落户,在短时间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潮流。这在一个国家的和平发展时期是罕见的。为什么在已经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会出现这样一个下放大潮?这里包含了许多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例如: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泛道德主义与泛劳动主义的当代回响,落后农业大国在快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论、思想准备的缺乏,长期革命战争的惯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成功经验的机械照搬,对经典作家有关消灭“三大差别”、限制商品经济论述的教条主义理解和运用,严峻的冷战环境与对外敌入侵可能性过于严重的估计,对书本知识与学校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缺乏应有的信任,对现代化、城市化的陌生(如“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对资本主义缺乏深刻的了解和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警惕,对“修正主义上台”的忧虑,“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在要求,三大改造后城市私人经济严重萎缩带来的劳动力就业空间狭小,对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三大差别”的浪漫主义设想,如此等等。总之,不能就知青谈知青。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对知青史的认识,推进现当代中国史、思想史研究,也能对当前的改革提供一些有益启示。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在当年数千万下放人员中,为什么大体上只有知青群体至今仍在普遍地、津津乐道地谈论当年的下放经历?为什么他们的怀旧情结如此持久、浓烈?
五、后知青时代的研究与写作
我们已经逐渐进入后知青时代,对知青史的认识、叙述与以往研究的差别逐渐显现,其中比较明显的一点是理性成分的增加。
所谓“后知青”,大体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当年的知青在结束知青岁月后开始书写、回忆。时至今日,他们最主要的身份已不再是知青,而是工人、干部、教师、学者等,而且基本都已退休,含饴弄孙,旅游跳舞,颐养天年。他们现在的写作是回顾自己人生中的一段经历,感受已与数十年前不尽相同。这里不仅有人到暮年时比较平和、理性、从容的心态,更有时代巨大变迁所给予的认识高度。
二是知青史研究的任务将由老一代知青学者交到新一代非知青学者手里。后者没有知青经历,面对的是史料、论著、文学作品以及新的社会需要和新的研究方法。他们不会有老知青那样强烈的知青情结、刻骨铭心的个人感受和体悟。这种旁观者的身份既使他们多了一些理性思考的优势和高度,又使他们少了一些还原历史的感觉和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老知青当年那段生活经历是无法替代的。在他们记忆深处,农村生活不仅仅是艰苦的劳作,还有那些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左”的错误而弥漫在整个社会每一个角落中的、难以言说的压抑和迷茫。正如一位老知青所说:“幸好我们还在,不然就死无对证了。”*《邓晓芒谈上山下乡:幸好我们还在 不然就死无对证了》,凤凰文化,2014年12月10日,http://culture.ifeng.com/a/20141210/42684315_0.shtml。话虽说得稍显偏激,却也不是空穴来风。这种个人感受对了解历史而言是不可替代的。两代人之间如何衔接、继承和发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纪念上山下乡48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