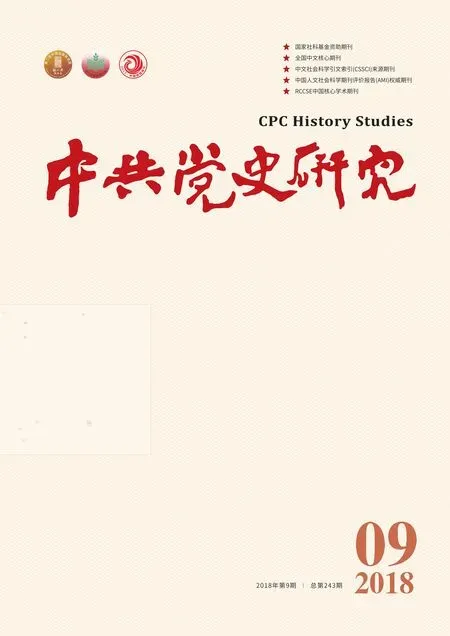对以农民视角为切入点的知青史研究的思考
张 宁
2018年6月,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新史料与新视野:上山下乡与知识青年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埃默里大学徐彬助理教授建议,知青史研究要走出“知青书写,关于知青,服务知青”的局面。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强调,知青史研究必须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涉及的其他人群,例如农民、知青家长、带队干部、城市街道干部等纳入进来。美国密歇根大学王政教授建议知青史研究者投入更多学术兴趣和资源关注无法发声的农民。中国社科院定宜庄研究员亦指出,在现有的知青回忆录中,同时代农民的命运极少得到关注。
上述四位学者的建议,既反映出知青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过于关注知青群体,忽视同时代其他相关群体,尤其是农民群体;又折射出今后知青史研究的发展方向——研究者应当有贯通与整体的眼光,走出知青史,走进中国当代史。下面,笔者尝试从叙事主体和主题、材料和方法,以及研究议题等几个方面展开反思,对以农民视角为切入点的知青史研究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超越知青叙事
农民群体在西方学术语境中被称作“下属群体”(subaltern),在中文语境里这个词常被译作“下层阶级”或“庶民”。农民与知识界的关系,恰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言:“农民群众虽然在生产界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他们也没有‘同化’任何‘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尽管其他社会集团正是从农民中间吸收了许多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传统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农民出身。”[注]〔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雷雨等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农民一直处于被言说、被代表的境地,即便是以农民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亦是从精英视角出发,按照精英的价值观作评判。
作为知青的接纳方,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基本利益无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迁徙运动中受到很大影响[注]本文所称“农民”,主要指户口类型为农村户口的人,包括农村干部(大队、生产队干部)和普通农民。回乡知青则不在其列。驻队的公社干部虽然不是农民,但与知青接触比较多,也可以纳入考察范围。。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对于知青运动的真实认识与反应,先是被遮蔽在国家宏大叙事与政治宣传中,然后又消失在以知青为主体的历史叙事中。无论知青史的文学叙事、史学叙事还是民间叙事,其作者几乎都是有知青经历的人,其中又以有知青经历的知识精英为主,叙事的主题也是围绕知青展开的。
就知青史的史学叙事而言,定宜庄、刘小萌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奠定了知青史的史学基础,而农民在他们的论著中所占分量不多[注]相比于定宜庄和刘小萌的著作,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李枫等译,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与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欧阳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对于农民着墨更多,各有一章讨论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态度与反应。。知青史的文学叙事对农村、农民着墨更多,但呈现出“苦难”与“诗意”两个极端化图景:“伤痕文学”阶段,农村和农民是知青文学中一个苍凉的大背景;“伤痕文学”之后,农村与农民则变为田园牧歌与人间温情的象征。文学界对这种乡村叙事提出过许多批评,比如有论者批评道,知青文学带有明显的城市中心论的优越感,默认城乡二元体制的合理性,忽略“普通乡村百姓这个更广大的社会群体在更漫长的岁月里所遭受的更大程度的不公与歧视”[注]范家进、钱霞:《〈我是农民〉:一部“反知青文学”之作》,《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又如,学者王彬彬根据自己当年作为一个乡下儿童的记忆指出,知青是农村里享有特权的“特殊阶层”[注]王彬彬:《一个乡下人对“知青”的记忆》,《书屋》1999年第5期。;作家贾平凹则以一个回乡知青的经历、处境与感受,反驳知青文学中充满委屈与不平的“控诉”[注]参见贾平凹:《我是农民》,山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第25—26页。。除了专业色彩浓厚的史学与文学叙事,以集体回忆录为主要形式的知青史的民间叙事方兴未艾。民间叙事因为“倾诉苦难”和“讴歌青春”两大主题而遭受学界质疑,但披沙拣金,一些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农业生产状况、农民生活状态与心态的记述,其实极具史料价值。
根源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固化印象,上述三种叙事有一个共同点,即倾向于将农民与知青视为两个对立的、不兼容的群体。但是,二者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农村这一历史场景中是不可分割的。他们共同经历了人民公社体制下运动式的农业生产活动和“四清”、“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整党建党、农业学大寨等政治运动。他们之间的确有很多差异,但也有很多共性,最主要的共性就是都被动卷入知青运动中,面对与个人意愿相悖的政策,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并作出消极抵抗。
具体而言,农民与知青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例如,在知青诉说农民的贫穷、落后、愚昧的同时,农民中间也流传着知青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故事。知青所控诉的饥饿与劳动之苦,对于农民来说,却是不得不经历的日常生活。知青渴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与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农活干得好、安分守己不惹事是农民判断“表现好”的标准。很多知青发现,农民并没有作为“导师”的先进性与优越感,反而和他们一样向往城市。有些地区的农民在各种批斗会上利用知青担任“先锋”,或者把政治身份较低的知青当作批斗对象。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农民与知青又是合作、互助的关系,如面对来自公社的不合理的生产命令时,生产队干部联合知青一起对抗驻队公社干部;“瞒产私分”时,为防止知青告发,生产队也会给知青分上一份。
同掌握了文化资本的知青群体相比,农民在个人情感、认知的记录与传播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发掘农民的声音是史学工作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前辈学者其实早就意识到并指出过“农民失声”的问题,不过受限于材料匮乏与实际操作难度太大,这方面的专题研究暂付阙如。现在,随着搜集到的档案材料、民间资料越来越多,从史料中发掘农民的声音已成为可能。
二、从史料中发掘农民的声音
农民的口述调查资料无疑最能直接反映他们的情感、认知等具体情况。近年来,一些学者采用社会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在“倾听底层”、让“历史中的无声者”发声方面作出了不少研究,极具借鉴意义。例如郭于华对陕北一个村庄的“苦难”的考察,深入农民心灵,探究中共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塑造新人”[注]参见郭于华:《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郭于华:《倾听底层:我们如何讲述苦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贺萧(Gail Hershatter)通过对陕西72位农村妇女长达十年的口述历史考察,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揭示出农村妇女在农业集体化时期的主要贡献,而这一贡献被主流历史叙述遮蔽掉了[注]参见〔美〕贺萧著,张赟译:《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高王凌进行的农业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极大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农民心理世界与行为选择的认知,他所利用的农村调查资料里面也包含大量口述调查[注]参见高王凌:《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目前以农民为被访主体的口述历史调查,主题仍多集中于土改、饥荒、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基层政权运作方面,关于知青运动的专业口述调查,暂时还没见到。当年管理知青的农村基层干部年岁已高,不少已经去世,但与知青同龄的许多农民还在,抢救有关口述资料的工作迫在眉睫。
在有关知青的地方档案中,相当多的内容都能反映农村干部和农民对知青、知青运动的态度。但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各地档案表现出较强的同质性,局限于管理者视角,无法完全代表农民的真实声音,因此仅仅依靠档案是不够的,报刊和知青日记、书信、回忆录等其他类型史料也很重要。就笔者接触到的山东、江西档案来看,各地(具体到公社)安置知青的情况汇报和对知青生活的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在当时的报刊中都有报道,更被知青私人日记所证实。其中私人日记尤其可以弥补官方史料同质性强、视角单一等局限性。例如,一位在江西井冈山插队的上海知青在日记及与父母的往来信件中表示,当地农民并不欢迎知青,双方因工分、住房和自留地问题时常发生龃龉。的确如此,工分问题始终是农民和知青关系紧张的主要因素,一直持续到知青离开。此外,对于知青方面的海量史料,研究者在利用时,应当关注与农民有关的高频词语或普遍情况。比如很多知青都会在回忆录中提到,在当地老百姓眼里,知青“早晚都要走的”;农民和知青一样处在饥饿或半饥饿状态;贫下中农“忆错苦”,在忆苦思甜会上大讲1958年之苦;“忆苦饭”连当地农民都不曾吃过,他们称,这是从外面学来的经验;农民在公社干部眼皮底下各显神通地“瞒产私分”;等等。
只有多种材料辨别、互证使用,才能展现一个更真实、立体、复杂的上山下乡图景。这一图景充分体现了农民的主体性,他们的形象不再是官方宣传和知青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亦非发出单一、顺从声音的“应声虫”。比如,尽管“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革命话语充斥报端,但对于知青运动的原因与目的,农村干部[注]研究中应注意公社干部与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差异性。和农民的认知与官方宣传存在巨大鸿沟。江西农民最初有以下几种不同认识:上海的学生来江西,是因为他们在城市里打派仗,被毛主席惩罚下乡受苦来了,像下放干部一样,是“小牛鬼蛇神”;城市里经济困难,知青下乡是来吃粮、抢工分的;知青是“毛主席的崽”“屋檐下的躲雨客”;等等。很多干部则抱怨知青是包袱与负担,认为知青待不长,对他们没有必要做大量工作。许多材料表明,农民与国家在知青问题上的矛盾呈现出“国家想揩生产队的油”和“生产队想占国家便宜”的张力,农民的态度与反应迫使中央政府对知青工作作出政策调整[注]〔美〕托马斯·伯恩斯坦著,李枫等译:《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第80页。。从这个角度看,知青运动的结束不仅是知青努力的结果,同时也是干部与农民的意愿。
三、相关研究议题的思考与延伸
近年来,研究者借助基层档案与民间资料,“从下往上”看历史,在集体化时期的农民与农村社会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既然城市来的知青被要求融入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队,对知青运动的研究就不能外在于集体化时期的农民与农村社会研究。知青的到来到底是增进还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知青运动到底是削弱还是巩固了城乡差别,都是需要纳入学术研究范围的课题。
目前论者大都认为,从当时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包袱,他们作出的有限贡献远不能抵消给农村带来的负担[注]这方面的专题学术研究还比较少,韩起澜、赵小建正在以黑龙江、江西、云南等省为例展开探讨,他们的书出版后,可为此问题提供一定参考。定宜庄等研究者则指出,相比于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对于农村发展的贡献更大。此外,还可参见万绍陈:《“文革”时期回乡与下乡知青对乡村建设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财经大学,2014年。。但如果拓展视野,以长时段的眼光观察知青运动的影响,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很多地方的知青与当地农民保持着联系,通过投资办厂、做慈善、助学等方式反哺农村,发挥了沟通城乡的桥梁作用。除了经济联系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点是情感联系,即农民与知青的情感来往,这种交往非常重要但难以量化,它是知青返城后仍与当地农民保持联络并关心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至于知青方面津津乐道的他们当时给乡村带来了文明、现代化元素等“神话”[注]王彬彬、贾平凹等认为,知青对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因为当时城市里的大工厂就像一个大村庄,没有多少现代文明值得带下乡。,或许更多体现在农民的下一代身上,这代人受到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吸引,通过考大学等方式进入城市。例如,一个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的江西青年告诉刘小萌,自己的汉语拼音和普通话是上海知青教的,因为当地的小学教师都不会①。
由于不同地方的社会、经济、自然环境普遍存在差异,所以各地知青运动的阶段、政策、问题均有所不同,研究者应当充分关注这些差异性,并以比较的眼光作研究。以1973年全国知青会议为分界点,农村干部、农民对待知青与知青运动的态度变化值得关注。如同知青群体的复杂性一样,农民也非概念化的铁板一块。总体而言,农村干部群体对于知青以及知青运动的影响更大,知青的任用与提拔以及离开农村的机会等都掌握在他们手中,普通农民与知青关系的好坏也多与干部的态度有关。此外,不同安置方式下,农民与知青的交往形式与密度是不同的,研究者要充分关注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和插队落户的区别,以及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区别。比如,青海农建师格尔木农场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与知青之间的矛盾很大,农牧间的矛盾也很大,哈萨克族牧民多次要求去北京上访;山东建设兵团黄河农场附近的农民是从梁山县迁来的移民,因为贫穷与饥饿,他们经常围着农场转,集体抢麦子;安徽黄山茶林场附近的农民会去偷采知青种的茶;内蒙古的蒙古族牧民热情接纳来自北京的知青,待他们像亲生孩子一样;黑龙江延边的朝鲜族农民与知青关系非常融洽,感情深厚;广东某些地方的农民、干部与知青关系良好,知青逃港失败后,农民照旧接纳并保护他们;江西、四川、山东、河南很多地区的农民则认为知青是来跟他们争工分、口粮、土地的,四川的农民甚至把知青称作“知匪”。
中央政府提出基本指导方针后,各省在上山下乡工作中执行这些政策时,毫无疑问要行使一定的自主权,农村的地区、县及公社也会参与有关政策的制定。各地普遍且长期存在的安置经费、劳动报酬与分配、住房规定等难以落实的问题,表明知青政策在贯彻执行中呈现出层层递减的现象,从中可以看出基层政权与中央政府,国家意志与社会、个人之间存在的张力与矛盾。所谓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全能性”,具体到知青运动上,仍有思考与讨论之余地。
同时,知青运动也可以看作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旨在改变农村面貌、缩小城乡差距、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社会实验。这场实验延续多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美国政治学与人类学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针对“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以及农民心理、行为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知青运动,理解农民对待这场运动的看法与反应,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总之,呼吁与期待从农民与农村视角切入的研究,是知青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年轻的研究者应当站在前辈学者所奠定的坚实基础之上,发掘更多史料,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议题,将知青史放置在当代史研究、党史研究的大框架下,并与历史学一般性议题进行学术对话。这或许是知青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献给知青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