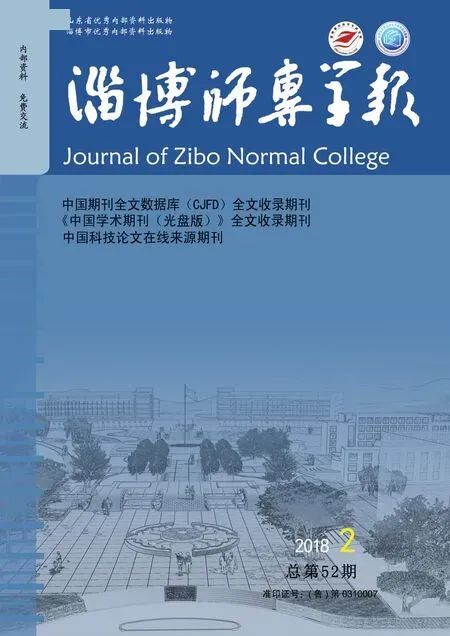浅谈《聊斋志异·梦狼》的来龙去脉
王光福
一、官员化为虎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梦狼》。大致说的是,直隶人白翁的儿子白甲在南方做官,两年没有音耗。一天,白翁在梦中跟随善走无常的丁氏,来到了白甲的官衙:
少间,至一第,丁曰:“入之。”窥其门,见一巨狼当道,大惧,不敢进。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门,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又视墀中,白骨如山,益惧。丁乃以身翼翁而进。公子甲,方自内出,见父及丁良喜。少坐,唤侍者治肴蔌。忽一巨狼,衔死人入。翁战惕而起,曰:“此胡为者?”甲曰:“聊充庖厨。”翁急止之。
心怔忡不宁,辞欲出,而群狼阻道。进退方无所主,忽见诸狼纷然嗥避,或窜床下,或伏几底。错愕不解其故。俄有两金甲猛士努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扑地化为虎,牙齿巉巉,一人出利剑,欲枭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年四月间事,不如姑敲齿去。”乃出巨锤锤齿,齿零落堕地。虎大吼,声震山岳。翁大惧,忽醒,乃知其梦。
其中,官员“化为虎”的情节最早见于南朝齐人祖冲之的《述异记》,鲁迅《古小说钩沉》曾从《海录碎事》卷十二辑出。其文云:
汉宣城太守封邵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时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此则材料,亦见于南朝梁人任昉所撰之《述异记》,中华书局排印有“安义王轶群校”本。其文云:
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旦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之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夫人无德而寿则为虎,虎不食人,人化虎则食人,盖耻其类而恶之。
任昉之《述异记》与祖冲之之《述异记》相比,故事讲述部分,文字虽略有小异,意思却完全一致。任昉之《述异记》比祖冲之之《述异记》多出几句议论,其意思有二:一是说明人为何会变成虎——“人无德而寿则为虎”——坏人活长了就会像虎一样对别人有危害;二是说明人化为虎后为何要吃人——“耻其类而恶之”——自己变成了畜生而害怕同类笑话,当然就得把同类吃掉了。
这大概就是死“甲扑地化为虎”的情节和形象源头。
二、“断头”与“续头”
《梦狼》继续写道,第二年四月间,白甲卸任县官到京城吏部任职,刚离开县境,就遭遇了强盗:
甲倾装以献之。诸寇曰:“我等来,为一邑之民泄冤愤耳,宁专为此哉!”遂决其首。……甲魂伏道旁,见一宰官过,问:“杀者何人?”前驱者曰:“某县白知县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后见此凶惨,宜续其头。”即有一人掇头置腔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领可也。”遂去。……甲虽复生,而目能自顾其背,不复齿人数矣。
除了《梦狼》,《聊斋志异》还有其他故事也写到人头断落后续接复活的异事。比如《诸城某甲》写道:
学师孙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乱,被杀,首坠胸前。寇退,家人得尸,将舁瘗之。闻其气缕缕然,审视之,咽不断者盈指。遂扶其头,荷之以归。经一昼夜始呻,以匕箸稍稍哺饮食,半年竟愈。
再如《辽阳军》写道:
沂水某,明季充辽阳军。会辽城陷,为乱兵所杀。头虽断,犹不甚死。至夜,一人执簿来,按点诸鬼。至某,谓其不宜死,使左右续其头而送之。遂共取头按项上,群扶之,风声簌簌,行移时,置之而去。视其地,则故里也。
蒲松龄善于写“续头”,也善于写“断头”,如《快刀》写道:
明末,济属多盗。邑各置兵,捕得辄杀之。章丘盗尤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杀辄导窾。一日,捕盗十余名,押赴市曹。内一盗识兵,逡巡告曰:“闻君刀最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兵曰:“诺。其谨依我,无离也。”盗从之刑处,出刀挥之,豁然头落。数步之外,犹圆转而大赞曰:“好快刀!”
《快刀》是《聊斋志异》中最为短小精悍、脍炙人口的篇什之一。
它篇幅虽短,却人物形象鲜明:章丘之盗视死如归,临死之际别无所求,只愿痛快而去。“闻君刀最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 这让人想起金圣叹临刑前的喟然浩叹:“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一个是默默无名的民间盗匪,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文坛巨星,不意在临行之际都有这样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不管是俗人也好,名人也罢,只要有了天地正气,都会有浩然不惧、“沛乎塞苍冥”的惊世言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还是盗匪人头落地后的一声赞叹:“好快刀!”这固然写出了刽子手飞刀之快,更重要的是表现了盗匪心情之快,“好快刀”中其实也有“快哉,快哉”的痛快淋漓之感。
刽子手只有一句话“诺。其谨依我,无离也”和一个动作“出刀挥之”,却也形象生动、栩栩如生:他和盗匪既然相识,就不能铁石心肠无动于衷,而限于身份职责又不能纵之逃脱,最好的和最后的送人情的方法,当然就是运用自己熟练的专业技能送盗匪痛快上西天了。这一“诺”一“挥”之间,也有浓浓的人情闪烁。
小说如此精彩,自然就影响深远。清代文学家文康在《儿女英雄传》第七回“探地穴辛勤怜弱女,摘鬼脸谈笑馘淫娃”中,写十三妹何玉凤刀削妇人的面皮:
那穿红女子本就一腔子的忿气,听这妇人说的这等无耻不堪,那里还忍耐得住?只见她一言不发,回手拔出那把刀来,刀背向地,刀刃朝天,从那妇人的下巴底下往上一掠,唰一声,早变了个血脸的人,不曾听她一声儿,咕咚往后便倒。这一倒,但见个东西翻在半空里,从半空打了一个滚儿,吧,掉在地下。大家一看,原来把那妇人的前脸子削下来了,落在平地还是五官乱动。
在《快刀》中,人头是“数步之外,犹圆转而大赞”,在《儿女英雄传》中,人面是“落在平地还是五官乱动”,这真是文康向蒲松龄的深深致敬,后来居上、玄之又玄了。
影响还不止于此。张爱玲译注之《海上花列传》第三十三回“高亚白填词狂掷地,王莲生醉酒怒冲天”中写道:
葛仲英阅过那词,道:“《百字令》末句,平仄可以通融点。”亚白道:“痴鸳要我吃酒,我不吃,他心里总不舒服;不是为什么平仄。”华铁眉问道:“‘燕燕归来杳’,可用什么典故?”亚白一想道:“就用的东坡诗,‘公子归来燕燕忙’。”铁眉默然。尹痴鸳冷笑道:“你又在骗人了!你是用的蒲松龄‘似曾相识燕归来’一句呀。还怕我们不晓得!”亚白鼓掌道:“痴鸳可人!”铁眉茫然,问痴鸳道:“我不懂你的话。‘似曾相识燕归来’,欧阳修、晏殊诗词集中皆有之,与蒲松龄何涉?”痴鸳道:“你要晓得这个典故,还要读两年书才行哩!”亚白向铁眉道:“你不要去听他!哪有什么典故!”痴鸳道:“你说不是典故,‘入市人呼好快刀,回也何曾霸产’,用的什么呀?”铁眉道:“我倒要请教请教,你在说什么?我索性一点都不懂了嚜!”亚白道:“你去拿《聊斋志异》查出《莲香》一段来看好了。”痴鸳道:“你看完了《聊斋》嚜,再拿《里乘》《闽小记》来看,那就‘快刀’‘霸产’包你都懂。”
在这里,这群文人骚客不但表扬了《快刀》,还表扬了《莲香》,可见《聊斋志异》之深入人心、久传不衰了。
张爱玲注释说:
“‘好快刀’事有几分可信性,参看得普立兹奖新闻记者泰德·摩根著《毛姆传》(Maugham):一九三五年名作家毛姆游法属圭亚那,参观罪犯流放区——当地死刑仍用断头台——听说有个医生曾经要求一个斩犯断头后眨三下眼睛;医生发誓说眨了两下。”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四处寻找梅尔基亚德斯:
最后他来到梅尔基亚德斯惯常扎帐篷的地方,遇见一个神情郁郁的亚美尼亚人在用卡斯蒂利亚语介绍一种用来隐形的糖浆。那人喝下一整杯琥珀色的液体,正好此时何塞·阿尔卡迪奥·布恩迪亚挤进入神观看的人群向他询问。吉卜赛人惊讶地回望了他一眼,随即变成一摊热气腾腾散发恶臭的柏油,而他的回答犹自在空中回荡:“梅尔基亚德斯死了。”
我们虽然不敢断定这些外国人就是受了《聊斋志异》的影响,但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中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其描写之鬼斧神工、刻画之异曲同工,都令人击节赞赏不已。
王小波《理想国与哲人王·沉默的大多数》中有这么几句话:
据说,人脖子上有一道纹路,旧时刽子手砍人,就从这里下刀,可以干净利索地切下脑袋。出于职业习惯,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纹,想像这个活怎么来做;而被打量的人总是觉得不舒服。
这段话在“快刀”传承史上肯定和《快刀》没关系,但是其中所说刽子手“干净利索”的刀法和打量纹路的“职业习惯”,似乎也和《快刀》中的刽子手有些形象上的暗合之处。这位刽子手吩咐自己的死罪犯同乡“谨依我,无离也”,其一是为了避免走失,不能亲手痛快杀死他,其二大概也有近在身旁便于观察纹路的考虑。试想,刽子手杀人无数,只有他这位同乡喊出“好快刀”而别人却如同哑巴一般,这似乎也证明,他砍杀这位同乡确实比砍杀别人动作更快一些,这可能也有提前观察清楚了其脖子上之纹路的因素。
当然,在《梦狼》中,强盗的杀人动作是“决其首”;在《诸城某甲》中,诸城某甲是“被杀”,我们根本没见到杀人动作;在《辽阳军》中,我们虽知道沂水某“为乱兵所杀”,却同样没有看到他是如何被杀的;在《快刀》中,我们尽管看到了侩子手的杀人过程——“出刀挥之,豁然头落”—— 但刽子手刀法太快我们还是看不明白,这一次人头落地之后的生动姿态和豪迈语言——“数步之外,犹圆转而大赞曰:‘好快刀!’”——才真让读者大饱了眼耳之福。
在《快刀》中,章丘盗人之头尽管表现绝佳,却最终没能回到脖子上,他彻底身首异处了;在《辽阳军》中,鬼吏“使左右续其头而送之,遂共取头按项上”,这“续头”的动作虽然专业,却也模糊;在《诸城某甲》中,某甲的家人是“扶其头”,虽然轻巧,却不形象;在《梦狼》中,续头动作是“掇头置腔上”,敷衍了事,接活就行。
《聊斋志异·陆判》才是描写“断头”与“续头”的最为精彩细致之作。陵阳朱尔旦与鬼判官陆判交好,而陆判模样丑陋却医术高明,他为朱尔旦洗肠剖胃、换置慧心,使其“文思大进,过眼不忘”,考中举人。因此,朱尔旦要求陆判为自己的夫人换置漂亮脑袋,陆判很爽快地答应了他。
过数日,半夜来叩关。朱急起延入。烛之,见襟裹一物。诘之,曰:“君曩所嘱,向艰物色。适得一美人首,敬报君命。”朱拨视,颈血犹湿。陆立促急入,勿惊禽犬。朱虑门户夜扃。陆至,一手推扉,扉自辟。引至卧室,见夫人侧身眠。陆以头授朱抱之,自于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项,着力如切腐状,迎刃而解,首落枕畔。急于生怀,取美人首合项上,详审端正,而后按捺。已而移枕塞肩际,命朱瘗首静所,乃去。朱妻醒,觉颈间微麻,面颊甲错,搓之,得血片。甚骇,呼婢汲盥。婢见面血狼籍,惊绝。濯之,盆水尽赤。举首则面目全非,又骇极。夫人引镜自照,错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复细视,则长眉掩鬓,笑靥承颧,画中人也。解领验之,有红线一周,上下肉色,判然而异。
这才是亘古未有的描写“断头”与“续头”的绝妙好辞,即使放到古今中外的大文学史上,它也熠熠生辉、顾盼自雄而毫无愧色。
三、官虎而吏狼
在《梦狼》的“异史氏曰”中,蒲松龄说:
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
《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中,乌巢禅师为唐三藏一行送行云:
老虎坐琴堂,苍狼为主簿。狮象尽称王,虎豹皆作御。
这几句韵语,可以作为《梦狼》“异史氏曰“的注脚。反过来,《梦狼》这几句“异史氏曰”,也可以作为《西游记》这几句韵语的形象化说明。
四、奸巧之吏
《梦狼》写完之后,蒲松龄意犹未尽,连类而及,又在文后附录了两则故事。附则一云:
邹平李进士匡九,居官颇廉明。常有富民为人罗织,门役吓之曰:“官索汝二百金,宜速办,不然,败矣!”富民惧,诺备半数,役摇手不可。富民苦哀之,役曰:“我无不极力,但恐不允耳。待听鞫时,汝目睹我为若白之,其允与否,亦可明我意之无他也。”少间,公按是事。役知李戒烟,近问:“饮烟否?”李摇其首。役即趋下曰:“适言其数,官摇首不许,汝见之耶?”富民信之,惧,许如数。役知李嗜茶,近问:“饮茶否?”李颔之。役托烹茶,趋下曰:“谐矣!适首肯,汝见之耶?”既而审结,富民果获免,役即收其苞苴,且索谢金。
这则故事中的门役,也就是官府衙门的看门人,能通过“饮烟否”与“饮茶否”两句简单的问话,玩弄犯罪嫌疑人及官老爷于股掌之间,从而收受贿赂中饱私囊,可谓是奸巧小吏的典型代表。此类人物败坏官府声誉、损害官员威信、挑起人民怨愤,社会危害极大。于是引起蒲松龄的连声叹息:
呜呼!官自以为廉,而骂其贪者载道焉。此又纵狼而不自知者矣。世之如此类者更多,可为居官者备一鉴也。
本来这样的门役只配做一只看家护院的“狗”,可是因为他们奸巧百出,令人防不胜防,不知不觉就堕其彀中、受其玩弄,最后被其害掉身家性命,因此蒲松龄把他们比作狡猾巧诈的吃人的“狼”。
在这则故事中,门役巧诈之计得逞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是蒲松龄现实主义的写实笔法。对同类现象,纪晓岚却有与蒲松龄不同的浪漫主义的理想描写。《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之一记载一则故事:
献县吏王某,工刀笔,善巧取人财。然每有所积,必有一意外事耗去。有城隍庙道童,夜行廊庑间,闻二吏持簿对算。其一曰:“渠今岁所蓄较多,当何法以销之?”方沉思间,其一曰:“一翠云足矣,无烦迂折也。”是庙往往遇鬼,道童习见,亦不怖。但不知翠云为谁,亦不知为谁销算。俄有小妓翠云至,王某大嬖之,耗所蓄八九:又染恶疮,医药备至,比愈,则已荡然矣。人计其平生所取,可屈指数者,约三四万金。后发狂疾暴卒,竟无棺以殓。
纪晓岚为官既巨且久,对衙门的各种巧诈之危害认识更深,因此他让这类“善巧取人财”的小吏倾家荡产,死无葬身之地,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无比痛恨。仔细翻翻《阅微草堂笔记》就会发现,纪晓岚不但对官吏的巧诈心怀恨意,就是对普通百姓甚至丫鬟婢妾的机巧之心也大有不满,因此“巧者,造物之所忌”这句话,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五、为吏所卖
《梦狼》附则二云:
邑宰杨公,性刚鲠,撄其怒者必死。尤恶隶皂,小过不宥。每凛坐堂上,胥吏之属无敢咳者。此属间有所白,必反而用之。适有邑人犯重罪,惧死。一吏索重赂,为之缓颊。邑人不信,且曰:“若能之,我何靳报焉!”乃与要盟。少顷,公鞫是事。邑人不肯服。吏在侧呵语曰:“不速实供,大人械梏死矣!”公怒曰:“何知我必械梏之耶?想其赂未到耳。”遂责吏,释邑人。邑人乃以百金报吏。
这则故事有无本事,不曾见人说过。近读《阅微草堂笔记》,其卷二《滦阳消夏录》之二“外祖张雪峰先生”条讲述一狐精呵气翳镜的故事。故事末了,纪晓岚借题发挥云:
正人君子,为小人乘其机而反激之,其固执决裂,有转致颠倒是非者。昔包孝肃之吏,阳为弄权之状,而应杖之囚,反不予杖,是亦妖气之翳镜也。
这就提醒了我们《梦狼》附则之二的本事来源。本人按图索骥,找到《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包拯传》,其中云:
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10](P)
这与上引“邑宰杨公,性刚鲠,撄其怒者必死;尤恶隶皂,小过不宥”是一致的。再查《梦溪笔谈》卷二十二,沈括云:
包孝肃尹京,号为明察。有编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之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号呼自辨,我与汝分此罪,汝决杖,我亦决杖。”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声诃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捽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宽囚罪,止从杖坐,以抑吏势。不知乃为所卖,卒如素约。小人为奸,固难防也。孝肃天性峭严,未尝有笑容,人谓包希仁笑比黄河清。[11](P)
此故事与《梦狼》附则二从主题到细节基本雷同,不需多言。沈括说包拯为吏“所卖”,蒲松龄说杨公为吏“所用”;沈括说“吏受赇”,蒲松龄说“吏索重赂”;沈括说“与之约”,蒲松龄说“乃与要盟”;沈括说“吏大声诃之”,蒲松龄说“吏在侧呵语”;沈括说“孝肃天性峭严,未尝有笑容”,蒲松龄说杨公“每凛坐堂上,胥吏之属无敢咳者”……连具体文字也相似乃尔,可见,断定《宋史·包拯传》和《梦溪笔谈》“包孝肃尹京”条为《梦狼》附则二之本事,应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六、“犸虎”与“麻胡”
上引《梦狼》附则二末尾,蒲松龄云:
要知狼诈多端,少失觉察,即为所用,正不止肆其爪牙,以食人于乡而已也。此辈败我阴骘,甚至丧我身家。不知居官者作何心腑,偏要以赤子饲麻胡也!
这段文字末尾的“麻胡”,有的注本不加注释,有的解释为“吃人的魔王”等等。不注释固然使人感觉遗憾,解释为“吃人的魔王”也同样不能使人有惬于心。
鲁迅在《朝花夕拾·后记》中说: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曰: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
《聊斋志异》注释者将“麻胡”解释为“吃人的魔王”,不知有何根据。如果确实想给“麻胡”做一条注释的话,鲁迅这段话是可以参考的。但是,鲁迅所说的“麻祜”应是传统的文学系统的“麻胡”,而蒲松龄所说的“麻胡”则应是淄博特别是淄川地区民间方言系统的“麻胡”。这一“麻胡”,现在尚存在于乡人民众之口头,一般写做“犸虎”,是蒲松龄家乡人民对狼的一种俗称。比如说某某是只“喂不饱的犸虎”,就是指某某是一个贪得无厌而又忘恩负义的人。当然这一俗称的来源也可能与鲁迅所说的“麻祜”有些关系,但是在淄川人的俗文化系统中,人们一直认为“犸虎”就是“狼”,“狼”就叫“犸虎”。
比如当地俗语云:
狗咬犸虎,两下里怕。
再如当地童谣云:
小板橙,拔咕噜,
开开楼门看媳妇。
谁来了,老姑夫,
挎的啥?小犸虎。
咬人不?不咬人——
啊呜!
“魔王”之类不会和狗咬起来,即使咬起来也不会“两下里怕”,因为狗不会是“魔王”的对手,魔王不会怕狗;老姑父胆子再大,也不敢挎着个“魔王”咬小孩。所以,这两处的“犸虎”都应该解作“狼”。
前引《梦狼》原文云“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其“异史氏曰”又云“吏且将为狼”,附则一再云“此又纵狼而不自知者矣”,附则二中仍云“要知狼诈多端,少失觉察即为所用”,这多处说的都是“狼”。在附则二末尾不说“狼”而说“以赤子饲麻胡”,一是因为“赤子”是两个字,“麻胡”也是两个字,在音节上对称。二是用当地方言“犸虎”来指称狼,一方面更能让人感觉到狼的贪婪狡诈之性,另一方面在艺术生上也能增加乡土风味,引人噗嗤一笑,足以使人解颐喷饭。
当然,“以赤子饲麻胡”也不是说“拿婴儿去喂狼”,而是说拿皇帝的子民去喂狼一样的奸巧皂隶。《汉书·循吏传·龚遂》:“其民困于饥寒而隶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这里的“赤子”,正是“皇帝的子民”的意思。在《梦狼》附则二中,蒲松龄说:“要知狼诈多端,少失觉察,即为所用,正不止肆其爪牙,以食人于乡而已也。”这里的“食人于乡”之“人”,就是“百姓、乡民”之义,与“皇帝的子民”义同。既然作者都说清楚了,后人就不必另出新见,把此处的“赤子”解作“婴儿”了。在淄川俗文化中“拿着小孩喂犸虎”,正如全国多数地方通用的“肉包子打狗”一样,都是表示“有去无回”的意思。没人真用“肉包子打狗”,更没人真“拿着小孩喂犸虎”,这都是艺术家的比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