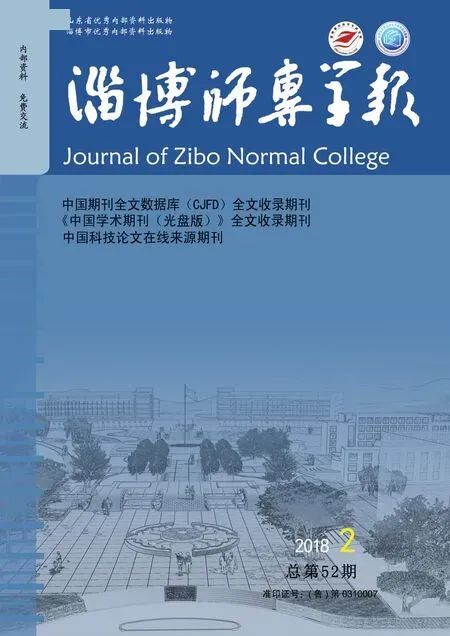聊斋说唱志目研究现状综述
王美雨(临沂大学 文学院 ,山东 临沂 276012)
《聊斋志异》是清代蒲松龄的著名文言短篇小说集,其题材多元化、语言俚俗化,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及文化价值。面世后,被改编成多种形式的聊斋说唱志目形式,它们为《聊斋志异》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学界对其作了诸多研究。
一、《聊斋志异》说唱志目概况
最早将《聊斋志异》改编成说唱形式的是蒲松龄自己,他将《珊瑚》《张诚》《仇大娘》《席方平》《商三官》《江城》《张鸿渐》等篇章改成俚曲,与原文相比,俚曲中的人物形象更为饱满、故事情节更为曲折生动、语言更通俗易懂。故与《聊斋志异》相比,俚曲更接地气,为诸多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所喜爱。之所以如此,是与俚曲本身的特性有关,据刘富伟研究,“聊斋俚曲主要从民间文化传统(小传统)那里摄取营养,将俗曲作为娱人劝世的工具,体现出鲜明的农民立场、草根意识与大众口味”[1](P177)。显然,聊斋俚曲对受众的准确定位,使其从最初受小范围受众喜爱迅速为大范围受众所喜爱,并因此开辟了《聊斋志异》传播的新渠道。在他的影响下,陆续有说书艺人等对其进行各种曲艺形式的改编,形成了独特的聊斋说唱志目。上官缨根据关德栋、李万鹏在《聊斋说唱集》中对搜集到的聊斋说唱志目的分类,明确将《聊斋志异》的说唱形式分为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鼓词及弹词四种[2](P254)。车振华则将其分为两类:“一为话本系统,即‘说聊斋’,有民间故事形式的《聊斋杈子》,有平话形式的《醒梦骈言》;一为唱本系统,即‘唱聊斋’,有子弟书、单弦牌子曲、鼓曲、弹词、宝卷等。”[3](P75)《聊斋志异》改编形式尤其是说唱志目形式的多样性,为曲艺界形成独特的聊斋说唱志目提供了契机。
就现有资料而言,聊斋说唱志目有170多种,曲艺体裁众多,就其艺术价值而言,以子弟书居高;就所含有的具体志目而言,以单弦牌子曲居多。价值和数量的不匹配性,与子弟书和单弦牌子曲各自的艺术特点都有关系。子弟书作者多为满族男性,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所呈现的女性观、伦理观、家庭观等为他们所认同。因此,在改编时,他们往往只是注重对语言的再创造、对故事内容的丰富与创新,却极少改变原作的主旨,并如蒲松龄一样,直接在文首或篇末指出自己的看法。如子弟书《秋容》结尾:“两夫妻,十分感念敬天神。便在那,室中供奉狐仙,他二人,朝夕礼拜把香焚。”根据故事情节,这里的狐仙其实是秋容上一世的姐妹。既为姐妹,又何须供奉?原因在于,这样的设置能更好凸显秋容夫妻所具有的仁义思想。与子弟书相比,单弦牌子曲形式的聊斋说唱志目的语言俚俗性更强、故事情节上更为大胆,作者的观念也更为先进。如单弦牌子曲《杜小雷》中指出:“世界上有一种陋习,就是那爱情不匀。大半皆是重男轻女,父母的偏心太甚。早年间女学又不兴,故此男女界中多不能同云。或曰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吾实难承认。岂不闻增长知识,以学问导其聪敏。通诗书方知守礼,惜纲常才能孝顺。”这样的论述无论是在《聊斋志异》还是子弟书中都未曾见到。
聊斋说唱志目的整体内容,以遵照蒲松龄原意为主,对其进行改编,其目的在于宣传、传播《聊斋志异》。如民国时期的求石斋在《聊斋志异鼓词》中指出:“《聊斋志异》一书,寓义宏深。其笔墨纸精审研练,殊非浅近少年所能领略,故读者每苦艰深,近有求石斋编为鼓词,以期家喻户晓,盖亦香山诗之意,必得老妪解颐而后快耶!”[2](P525)俄国阿翰林也持同样的观点,指出把《聊斋志异》改编成曲艺形式,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听众需要的,是把蒲松龄作品通俗化的最好途径”。[4](P130)聊斋说唱志目的成功,还体现在它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陈恕指出《聊斋志异》的“说唱译本,在达斡尔族中流传甚广”[5](P109)。
总而言之,聊斋说唱志目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及语言风格上与《聊斋志异》原作相比,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为文化水平不高的中下层劳动人们更好地了解聊斋故事、获取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提供了机会。
二、《聊斋志异》说唱志目研究现状
在中国文学史上,与《聊斋志异》同样题材的小说很多,但能够被改编成多种文学形式、且到现在仍然为人们所喜爱、被不停改编成与时代相适应的艺术形式的,唯有《聊斋志异》而已。就学界研究现状而言,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一是对聊斋说唱文学的整体情况进行研究。聊斋说唱志目虽然艺术形式不同,但其都基于《聊斋志异》改编而成,这就使学者对其进行整体研究具有了可操作性。上官缨认为“鼓词的‘聊斋’唱段,其文字略与子弟书相近。弹词产生江南另成一格。单弦牌子曲就浅白通俗得多了”[2](P523)。刘富伟以“转换与熔铸”为题,就说唱艺术对《聊斋志异》的改编做了深度阐释。认为子弟书和鼓词在改编聊斋题材时,都十分注重文本的警世意义与劝诫价值。而单弦牌子曲则是选择聊斋鬼魂题材时在“情”“奇”以及劝诫之间的游移与糅合。毫无疑问,不同曲种的聊斋说唱志目,“在选择、改编聊斋故事时,也是有着种种眼光的,它们在各自的语境、以各自的视角对《聊斋》文本进行了不同的解读和阐释,有时甚至是针锋相对、大相径庭”。[1](P196)在此基础上,高岩在《〈聊斋志异〉说唱研究》[6]一文中对聊斋说唱进行了整体研究,他从《聊斋志异》说唱的概况、创作手法、创作理念、审美特征等方面出发对聊斋说唱文学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聊斋说唱文学的语言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和地域色彩。更为值得肯定的是,聊斋说唱志目的改编着眼于说唱所特有的表演形式和受众群体,使得原著情节更连贯,人物形象更鲜活,语言更通俗顺畅,更符合大众的欣赏水平,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是就某一主题对聊斋说唱进行研究。贾静波在《〈聊斋志异〉子弟书的“市民化”特征分析》(2007)、《〈聊斋志异〉子弟书初探》(2008)两篇文章中均指出:“在《聊斋志异》的说唱民间传播史上,从质量上来看,子弟书里的‘志目’即聊斋子弟书在说唱‘志目’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它表演起来亦雅亦俗,蕴蓄其中的市民化特征深深打动了市民群体的听众。因而它在《聊斋志异》传播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聊斋志异》传播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7]姚颖指出,聊斋子弟书选取的聊斋故事都具有“双美共侍一夫”[8]的模式,且无论故事中的女性是什么身份,都能和睦相处。而这种故事模式的出现,与当时创作群体以及传播受众的观念有着直接关系,与作者身为男性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息息相关。这种观念通过说唱文学作品,由社会中上层传播到社会的下层,无疑对社会伦理道德及传统观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是在相关研究中涉及到有关聊斋说唱的内容。这部分研究成果比较多,有吴刚的《明清小说在东北少数民族说唱文学中的传播》、姚颖的《清代北京说唱文学的发展特点及研究意义》、蒋玉斌的《〈聊斋志异〉的清代衍生作品研究》郑秀琴的《论〈聊斋志异〉在清代的改编:以戏曲为中心》以及陈文新的《从宋元话本到〈聊斋志异〉—论讲唱文学对文言小说的渗透》。罗扬主编《中国曲艺志·天津卷》在提及单线牌子曲《马介甫》时指出:“德寿山、常澍田、谢瑞芝、王剑云、张伯扬均演出,所用曲本多不同。”[9](P190)追根溯源,说唱志目应该是对《聊斋志异》的一种另类研究,它们从改编再创造的角度对《聊斋志异》的故事内容及思想做了深度研究,最终创造出了既没有违背蒲松龄原意,又有自己思想意识的聊斋说唱志目。
四是对聊斋说唱价值的肯定。关德栋、李万鹏认为,它是“通俗文艺特有的艺术手段,给一般文化水平低下的人们扫除了文字上的障碍,使广大群众极大程度地满足了欣赏聊斋故事的渴望,成为群众文化生活的一种重要补充”[10](P1)。李红云在《论聊斋俚曲的说唱艺术》[11]中,指出聊斋俚曲是讲唱用的唱本,其唱词文本和曲牌音乐都具有说唱性。认为这两者的结合,不但为代言体的讲唱创造了条件,而且为聊斋俚曲的思想表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苗怀明认为聊斋说唱志目“除自身的艺术价值外,对研究《聊斋志异》的流传、接受等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12](P284)。
综上所述,聊斋说唱研究体现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聊斋说唱研究的整体性。纵观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主要是从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对聊斋说唱文学进行研究,还处于概况分析、脉络厘清阶段。二是聊斋说唱研究的单一性。因面世的聊斋说唱文学资料较少且时间较晚,故学界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聊斋子弟书或某个案研究,呈现出聊斋说唱文学研究的单一性特征。
三、《聊斋志异》说唱志目研究的发展趋势
对聊斋说唱的已有研究成果分析后,可发现学界对聊斋说唱的研究从整体特征研究逐渐转向对具体艺术形式及个案的研究;在研究中从最初重视《聊斋志异》对聊斋说唱影响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聊斋说唱自身的研究,诸如对其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及语言价值等进行探讨。这与学界对大多数文献的研究轨迹一致,显示出聊斋说唱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我们也要承认,现有研究成果基本围绕关德栋、李万鹏在《聊斋志异说唱集》前言中的论述展开,这种情况一是说明这两位学者在研究聊斋说唱史上的重要性,二是说明由于聊斋说唱志目内容的稀少,给学界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在注重对已有聊斋说唱志目的研究同时,也应该注重对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
[1]刘富伟.《聊斋志异》的文本改编———以白话小说和说唱艺术为中心[D].华东师范大学,2007.
[2]上官缨.上官缨书话[M].沈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车振华.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5.
[4]李明滨.《聊斋志异》在俄国[A].(转引自)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6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2.
[5]陈恕.黑龙江北方民族音乐文化研究[A].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6]高岩.《聊斋志异》说唱研究[D].吉林大学,2011.
[7]贾静波.《聊斋志异》子弟书初探[J].蒲松龄研究,2008,(4).
[8]姚颖.“双美共侍一夫”故事模式的背后——以《聊斋志异》和子弟书”志目”为例[J].蒲松龄研究,2011,(4).
[9]罗扬(主编).中国曲艺志·天津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社,2009.
[10]关德栋,李万鹏.聊斋志异说唱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李红云.论聊斋俚曲的说唱艺术[J].管子学刊,2014,(1).
[12]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