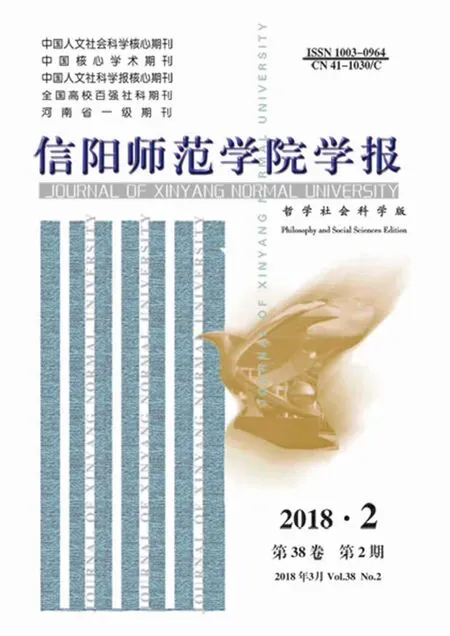国外认知科学哲学中的认知表征问题研究述评
张铁山,张 琳
(1.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2.西南大学 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认知表征问题是认知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基础性论题和前沿性论题,也是当前国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难点论题。在认知表征问题研究的过程中,由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各不相同,研究视角各有差异,表征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更新,故而学界的争论始终异常激烈。在非涉身认知科学时期,认知科学家们围绕着心智的数字计算—表征研究范式和心智的联结主义计算—表征范式对认知计算—表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到了涉身认知科学时期,由于在对认知是否需要表征、是否存在着表征以及如何表征等问题上的不同认识,进而产生了激进的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和温和的涉身认知计算—表征观之间的论争,目前这两种认知表征观的论争仍然持续着且较激烈。本文将着力呈现当代国外有关认知科学哲学中的认知表征问题研究的演进脉络和重要观点,并对它们予以评价。
一、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认知表征问题
非涉身认知科学也称为第一代认知科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革命,是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和取代。作为传统心灵哲学中的认识论在当代的延展,非涉身认知科学是“当代回答长期未解决的认识论问题所做的以经验为基础的努力”[1]6。正是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形成了心智的数字计算—表征研究范式和心智的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
(一)心智的数字计算—表征研究范式及其局限性
心智的数字计算—表征研究范式是非涉身认知科学的第一个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不但从传统的心智哲学中汲取计算—表征思想的养分,而且也把这些思想融入非涉身认知科学的形式逻辑学、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和生成语言学等具体学科之中,为自己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
20世纪50年代,西方逻辑学形式化思想在早期的人工智能中得到了运用,从而产生了阿兰·图灵(A.Turing)检验及纽厄尔(A.Newell)和西蒙(H.Simon)的“物理符号系统假设”。图灵检验认为,参与“游戏”的计算机经程序化之后能表现出和人的智能一样的智能。在这一思想得到检验之后的1976年3月的《计算机协会通讯》杂志上,纽厄尔和西蒙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经验探索的计算机科学:符号和搜索》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提出了享誉人工智能界的“物理符号系统假设”。这一假设指出,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操作的二进制数据串来表征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任何“存在物”。人的大脑与心灵和计算机是一样的,都不外乎是一个由一组符号的实体组成的物理符号系统。图灵检验和物理符号系统假设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在思考如何让计算机具有智能中并不需要考虑人的身体和身体之外的环境方面的参与。
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领域发生了一场反叛行为主义的“认知革命”,这场革命产生了以信息加工为主要特征的认知心理学。这种心理学认为,人们的大脑和心智是一台信息处理装置。对信息的处理就如同对计算机程序中的无意义的形式符号进行操作。这种形式符号操作的实现使儿童心理学中的思维或内化思维变得可能。除了心理学领域的“认知革命”外,在认知语言学领域也出现了以乔姆斯基(N.Chomsky)为代表的“认知革命”。在这场认知语言学革命中,乔姆斯基在《评斯金纳著<言语行为>》一文中,通过对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学习说”进行透彻剖析和批判,提出了他的“转换生成语法”和“管辖—约束”理论。“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是在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提出来的。这一理论认为,我们语言分析的目的必须是发现人的内在能力中具有高度抽象和形式化的普遍性及规律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用有限的规则去生成无限的句子。在生成无限的句子中,体现出“管辖与约束”的语言本质特征。
上述这些思想对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数字计算—表征研究范式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而出现了符号主义(symbolism)、功能主义(functionism)和认知主义(cognitivism)等名称不同但核心范式类同的认知范式。这些研究范式具有共同的特征:(1)一切认知系统都是通过处理符号而获得智能的符号系统,心智对于大脑正如计算机软件对于硬件。(2)认知处理过程遵循精确的、无例外的、用计算程序表示的规则。人类思想系统的语义融贯性在本质上依赖于对某类表达的计算操作。(3)这些研究范式都是基于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并受规则限制、逻辑驱动的,都是被动复制性的认知,都强调计算隐喻的重要性,都是自上而下的心智数字计算—表征,都是一种无视身体的认知观。与此同时,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共同特征使心智数字计算—表征研究范式遭遇了符号接地(symbol grounding)和符号表征问题、常识知识问题、规则描述与专家系统问题(如CYC程序问题)以及“框架问题”等难以摆脱的困境,导致其难以说明和复制人的复杂行为,暴露出能行可计算假设的局限性,从而陷入发展的瓶颈。
(二)心智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及其局限性
为了克服心智数字计算—表征研究范式自身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一些认知神经科学家提出了一种新的计算—表征研究范式:心智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
心智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是探讨心智和智能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这种研究范式和方法是通过建立各种人工神经网模型来研究大脑中的神经网络之间是如何分布和运行的。它的核心概念为大型“并行分布处理”,它的核心思想可概括为:人的认知或智能是从大量的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并行分布处理”这一概念起源于1943年沃伦·麦卡洛克(W.S.McCulloch)和沃尔特·皮茨(W.H.Pitts)的“神经网络”概念。后来,到了1982年,约翰·霍普菲尔德(J.Hopfield)又提出了“霍普菲尔德网络”(Hopfield network)。这些人工分布式网络模型坚持唯物主义路线,以还原论为哲学基础,侧重于结构模拟,是一种“灰箱式”的研究方法。这一研究范式和方法主要是对大脑内部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和探究,因此,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 “涌现论”研究。在对待表征和计算问题上,这种研究范式和方法与心智的数字计算—表征研究范式不同。它放弃主要符号,而采用亚符号,是局部式与分布式的表征。特别是心智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产生的“涌现”思想对涉身认知科学中的动力学范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尽管上述心智联结主义神经网络模型在某些方面和大脑的神经网络具有相似性,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特别是这种神经网络模型并不具有真正神经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它没有揭示出心灵和认知的本质细节,不能充分说明一个系统怎样可能获得它的内在意义。加之心智联结主义计算—表征研究范式和心智数字计算—表征研究范式一样,并没有揭示出心灵与认知的本质细节,忽视了认知主体的大脑、身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它在非涉身认知科学研究中仍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总而言之,由于非涉身认知科学这两种研究范式仅仅关注认知的内在表征,忽视了认知的生物学、神经科学研究,忽视了人的身体和外部环境对人认知的作用,难以解释生活世界中的认知活动,故而受到诸如大脑、情绪、意识、外部世界、身体、动力学系统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研究的挑战,致使认知科学研究不得不寻求新的研究范式。
二、涉身认知科学中的认知表征问题
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思想和皮亚杰与维果斯基的相互作用论等思想的影响,认知科学领域发生了从非涉身认知科学向涉身认知科学的转向。在这个转向过程中,涉身认知科学采取反笛卡尔的哲学立场,强调认知是大脑、身体和环境的系统整体交互作用的结果。另外,在对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非涉身计算—表征观进行反思和批判过程中,涉身认知科学在围绕是否放弃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认知计算—表征这一形而上学硬核的论争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新表征观:一是激进的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二是温和的涉身认知计算—表征观。其中前者批判解构了传统表征观,后者修正拓展了传统表征观。
(一)激进的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
“激进的涉身认知”(radical embodied cognition)一词来自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认知科学哲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激进的涉身认知观认为,要对大脑、身体和世界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给予理解,就必须用动力学系统理论及其研究方法。认为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结构、符号思想及其计算—表征观是错误的,且妨碍了从功能角度对传统人脑—身体—世界进行区分。所谓“物理符号系统假设”也是有缺陷的,其表征和计算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必须给予抛弃。另外,这种激进的涉身认知科学对传统认知科学中的计算—表征思想及其形而上学硬核予以坚决的批判。因此,激进涉身认知观本质上是一种反表征主义的“强耦合”的非计算—表征观。
这种“激进的涉身认知”思想的产生有其重要的哲学来源。如在激进的涉身认知思想产生过程中,海德格尔对日常认知内在机制和外在环境的描述是一个关键的中介环节。该描述展现出了对人类认知活动的一种整体和原初的理解。这种理解明显区别于以主客二分对立为本质特征的非涉身认知的认知主义模式。正是由于海德格尔在心灵、智能和认知的理解上与笛卡尔主义存在着实质性差别,并且他的现象学体现了对认知主义等经典理论框架的基础性修正,所以,他所描述的日常认知观就可能为认知科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建构性解释。海德格尔的日常认知理论具有明显的反笛卡尔主义的特征。因此,它成为批判非涉身认知计算—表征观等经典理论框架并推动认知科学发生转向的哲学原动力。在海德格尔之后,梅洛—庞蒂通过分析身体对知觉认知活动的意义,深化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梅洛—庞蒂通过对传统知觉分析中二元实体论的批判,重点对知觉现象学给予了深入分析,从而将知觉分析建立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基于实体二元论的知觉观,梅洛—庞蒂指出,传统的知觉分析掩盖了参与认知的身体的作用。但是,身体的确在人们的知觉活动中起着知觉、行为的主体的重要作用。他说:“身体本身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肌体中:身体不断地使可见的景象保持活力,内在地赋予它生命和供给它养料……如果不通过身体的体验,我就不可能理解物体的统一性。”[2]261除此之外,梅洛—庞蒂还明确地提出了知觉具有非表征性特征。在他看来,正是因为身体运动功能的“原点”性,我们日常活动的认知才是始于“我能”而不是“我认为”。“身体的运动就是通过身体朝向某物体的运动;就是让身体对物体作用做出回应,而这一回应是独立于任何表征的”[3]139。概言之,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思想为激进的涉身认知的非计算—表征思想提供了直接的哲学基础。
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和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一大批认知科学家提出了他们激进的涉身非计算—表征思想。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专家罗德尼·布鲁克斯(R.Brooks)在《没有表征的智能》和《没有推理的智能》两篇文章中指出,机器人的活动是嵌入在世界中的。但是,它们并没有解决抽象的描述,而是应对直接影响系统行为的当下环境。当我们研究非常简单低等智能的时候,实际上关于世界的明晰符号表征和模型对我们了解智能并没有起到推进作用,而是起到了阻碍作用;当我们从生物种系演化和个体发育尺度来追溯人类认知发展的时候,发现我们具有非常不同的认知能力,并且这些能力是功能主义或计算—表征无法充分说明的。因此,“表征在建构智能系统方面是错误的抽象单元”[4]81。世界是它自身最好的模型。另外,认知动力学家冯·盖尔德(V.Gelder)指出:“表征概念对于理解认知是一种不充分的、诡辩式的东西。”[5]6发展心理学家艾斯特·西伦(E.Thelen)和林达·史密斯(L.B.Smith)宣称:“我们根本不去建立什么表征!”[6]338认知神经科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瓦雷拉(F.J.Varela)认为:“表征观念不仅仅遮蔽了人类经验中许多认知的基本维度,而且表征观念也妨碍了人们对这些维度的科学解释。”[7]134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克默罗(A.Chemero)指出:“认知系统的本性是非表征性的(认知系统不包含表征)……我们对认知系统的最好说明不包含表征。……因为动力系统理论不包含表征,对认知过程的说明也不包含表征。”[8]比利时的迈因(E.Myin)对认知科学的传统表征观念也发起了挑战,认为“我们的认知能力并不必然以负载内容的内部状态为前提”[9]36,我们可以诉诸动力系统理论中的吸引子概念、内部控制参数以及耦合关系等。
上述这些激进的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对于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计算—表征观给予了超越和取代,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觉的学术努力和理论超越。但是,激进的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并未揭示出认知的本质。从耦合机制来看,也不能说明各种各样的复杂认知现象,更不能说明诸如高级语言之类的认知能力。从动力学方法论来看,在解决低层次复杂认知方面也没有提出统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种非计算—表征观尚处于一种超越说明基本经验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论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更像是一种理论观点而不是一个成熟的经验研究纲领。
(二)温和的涉身认知计算—表征观
“温和的涉身认知”(wean embodied cognition)一词也是安迪·克拉克提出来的。克拉克发现,激进的涉身认知无法解决“表征渴求”问题,“在涉身模型中,表征根本没有完全消失。……而是更经济的、更加受行动导向的表征”[10]36。这种表征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节省计算成本的办法,并且这种表征也是克拉克的温和涉身认知观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就是说,涉身认知可能仍然存在表征,只不过这种表征是一种局部的、行动导向的表征。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表征和计算的本质,以便我们能够反映出身体运动在产生和简化要解决的信息处理问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克拉克不但主张在知觉活动中存在行动导向表征的可能性,而且认为我们的抽象认知活动也是离不开传统计算—表征的解释模型的。仅仅从涉身认知的模型来看,这种模型对于意识形式的解决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另外,克拉克还认为:“理解身体、大脑和世界之间的复杂且大量实时交互需要一些新的概念、工具和方法来研究涌现的、离散的、自组织的现象。”[11]511克拉克通过提出上述最低限度表征(minimal representation)的思路,“把行动导向的内在状态的机体纳入连续的模拟信号处理,识别各种变异发生的内在和外在因素……通过克服表征渴求的问题从而间接地达到解决表征不确定性问题的效果”[12]。在复杂多样的系统的诸多要素中,由于一些行动并不是从中央控制器或者明确编程中产生的,而是在系统诸多要素间的交互作用中“涌现”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运用一些新的概念、方法和工具来探究这种“涌现”现象。正如贝克特尔(W.Bechtel)所说:“认知科学探究的是多种形式的表征。动力系统理论通过引进如:轨迹、动力吸引子这些新的概念来不断地探索。”[13]62
认知科学哲学家罗伯特·威尔逊(R.Wilson)认为,涉身认知科学和计算主义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从涉身认知科学的理论中找到“调和”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宽计算主义(Wide Computationalism)。因为这个宽计算主义中的“计算认知过程是能够跨颅的,并非如计算主义所倡导的那样仅仅局限于脑或颅内,它能由脑延展于环境之中”[14]。宽计算主义基本上符合了克拉克对最小化笛卡尔主义或最小化表征的要求。法国索邦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系的皮埃尔·斯特奈(P.Steiner)也认为,“在表征主义和延展认知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的合理性”[15]。这种合理性意味着“内在事件和外在表征之间存在着差别也存在着联姻”[16]。这表明,皮埃尔·斯特奈反对传统的表征主义观点,但是他赞成没有内容和意向性的心理表征存在的合理性。
除此之外,主张温和涉身认知的认知科学家还有加拉格尔(S.Gallagher)、克里斯·埃里亚斯密斯(C.Eliasmith)、迈克尔·安德森(M.L.Anderson)等人。加拉格尔认为,在涉身认知框架下,身体图式的作用是无表征的,而身体意象的作用则是有表征的。仅仅强调身体图式的作用则是一种狭隘的涉身认知,只有兼顾身体意象的作用,才能成为一种整体的涉身性思想。埃里亚斯密斯和安德森在反思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符号主义模型、联结主义模型和动力主义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理论——认知的表征—动力学理论。他们认为,由于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动力主义这三种认知理论都受到各自所依赖的隐喻的制约和限定,因此,它们不能对认知和智能给予完全的说明。我们如果要对认知和智能给予全面的理解,就必须超越它们各自所依赖的隐喻的限制,用认知和心智的本然属性去理解它。于是,他们对表征、计算和认知的概念给予了重新诠释,认为表征是认知神经系统的编码—解码过程,计算是认知神经系统在表征基础上的有偏解码,认知是神经生物系统通过表征和计算的动力运作过程。他们的这些新解释对于激进的涉身认知放弃计算—表征是一种挑战。
总之,温和的涉身认知既对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计算—表征思想给予质疑,同时又与根本放弃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计算—表征思想的激进的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持完全不同的看法和态度。它旨在将涉身进路和表征性分析结合起来,在认知观的计算硬核更加可实现层面上做出调整,以获得比传统计算—表征观更多的解释力。在一定意义上,温和的涉身认知计算—表征观既超越了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计算—表征观的局限性,也弥补了激进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的缺陷,“发展了较为完善的解释性理论,如不完全表征、模拟的表征原则、行动导向的局部表征等”[17]。因此,它是一种“温和的理性主义”、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或广义的计算主义。然而,这种温和的涉身认知计算—表征观也存在着非涉身认知科学中的计算—表征与被扩展的认知表征之间的“不可通约”困境。如如何将动力系统理论方法和符号方法结合来建构“混合模型”,以及如何解决该模型的可行性问题,如何解决认知主义机制和涉身框架机制之间存在的断裂并将之联系起来等。
三、 结 语
通过对上述西方认知科学哲学中的各种认知表征观思想的辩证考察分析,我们发现,由于认知本质和表征的种类是复杂多样的,各种类型的表征在其所研究的范围内都既有其合理性又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激进的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完全放弃计算—表征的思想,从耦合机制来看,它不但不能说明各种各样的复杂认知现象,而且更不能说明诸如高级语言之类的认知能力;从动力学方法论来看,它在解决低层次复杂认知方面没有统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盲目’和停留于感性的初级认知,它无法解释‘人在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中认识者本身还具有一个内在的想象世界’。这正是激进的涉身认知理论的先天 ‘缺陷’”[18]。所以,目前这种激进的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并没有揭示出认知的本质。另外,这种激进的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尚处于一种超越说明基本经验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论的发展阶段,尚不是一个成熟的经验研究纲领,现在把它作为认知中唯一工具还有很大局限性。在没有出现更充分的概念化语言之前,这种新的认知科学研究进路只能采取温和的涉身认知计算—表征观的理念和方法对这种计算—表征问题进行修补。但是,这种小修小补仅仅是在目前涉身认知科学处于不成熟阶段所表现出的较为合理的研究路径,它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完备性,如这种温和涉身认知计算—表征观还存在着传统计算—表征观和被扩展的认知表征之间“不可通约”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可能用一种表征就能够完全揭示出认知的复杂本质。
总之,在对待认知表征问题上,认知主义计算—表征观、联结主义计算—表征观、激进的涉身认知非计算—表征观和温和的涉身认知计算—表征观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对人类认知进行说明,但都不够完备。所以,我们不应该采取那种非此即彼的态度来看待它们,而应该采取“既—又(both—and)”的综合方法,遵循多元论思想。不同理论观点的竞争者通过潜在的证伪促进理论发展对科学研究路径的完善是有益的。
[1] GARDNER H.The Mind’s New Science:A Histroy of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M].New York:Basic Books,1985.
[2]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 MERLEAU—PONTY M.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1962.
[4] BROOKS R A.Intelligence without Representation,Cambrian Intelligence: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New AI[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9.
[5] VAN GELDER T, PORT R F.It’s about time:an overview of the dynamical approach to cognition.In Robert F.Port and Timothy Van Gelder(eds).Mind as Motion:Explorations in The Dynamics of Cognition[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
[6] THELEN E, SMITH L B A.dynamic Systems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on and Action[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4.
[7] VARELA F J, THOMPSON E T.ROSCH E.The Embodied Mind: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M].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91.
[8] 安娜·何布勒.对激进的具身认知科学的一个批判[J].陈 虹,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9.
[9] 魏屹东,等.认知、模型与表征:一种基于认知哲学的探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0] CLARK A.Embodiment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 O’HEAR. Current Issues in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11] CLARK A.Embodied,situated and distributed cognition c//.B.Graham.Companion to Cognitive Scien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8.
[12] 彭超宇.论克拉克对表征不确定性问题的解决[J].心智与计算,2013(1):38-43.
[13] BECHTEL W.Philosophy of Science:An Overview for Cognitive Science[M].Hillsdale,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1998.
[14] 刘 川.涉身认知科学视域下的计算主义研究[J].未来与发展,2017(6):39-43.
[15] STEINER P.A Problem for representationalist versions of extended cognition[J].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5(28)2:184-202.
[16] STEINER P.The bounds of representation:A non—representationalist use of the resources of the model of extended cognition[J].Pragmatics&Cognition,2010(18)2:235-272.
[17] 张 博,葛鲁嘉.温和的具身认知:认知科学研究新进路[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9-28.
[18] 张铁山.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西方涉身认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4):94-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