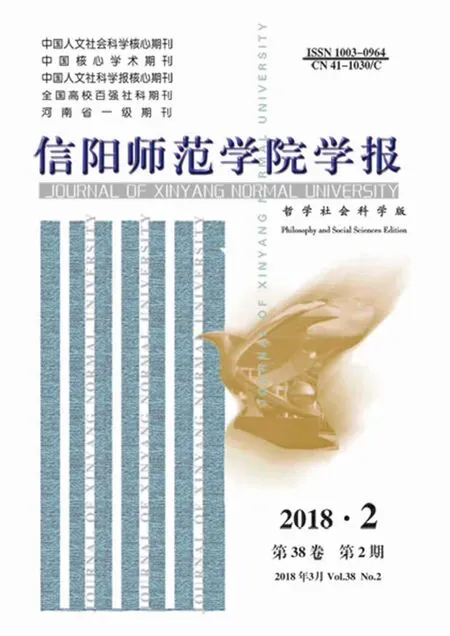美,从未缺席
——论曹文轩《蜻蜓眼》的诗性追求
张继荣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曹文轩新书《蜻蜓眼》于2016年7月出版,这是他在2016年4月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曹文轩说他是一个喜欢珍藏故事的人,这个故事他珍藏了30年,如今跟大家见面了。《蜻蜓眼》的故事时间跨度从20世纪20年代到“文革”结束前,跨越半个多世纪,发生地点从法国马赛到中国上海、宜宾,曹文轩以小女孩阿梅的视角,书写了奶奶奥莎妮的一生。这部小说的叙事相比较以前有所突破:首先是尽管继续用儿童的视角叙述故事,但是题材已不再是他常用的少年成长题材,而是讲述了奶奶的人生故事;其次是故事的发生地点也突破了曹文轩以往小说中的江南水乡的记忆书写,直接描写马赛、上海等都市。
细读文本,发现曹文轩的这部长篇延续了他一贯的写法:永恒的古典美追求、儿童的视角、风景意象的描写、诗意的创造、纯美的女性、对于苦难的降格处理等。在诗意文本的构建中,美的女性形象、美的物象、美的风景都是他着力表达美的理念的重要元素。
一、美的化身:女性形象
在曹文轩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有一位美好的女性形象,比如,《草房子》中的白雀、纸月、红藕,《细米》中的梅纹,《红瓦》中的陶卉、细茶,《根鸟》中的紫烟姑娘,《青铜葵花》里的葵花,《天瓢》中的程采芹和艾绒。这些女性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程采芹等这类在江南水乡“油麻地”土生土长的女孩,她们都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漂亮、质朴、温柔、柔弱、羞涩、纯洁、乖巧;另外一类是城里下乡来的女知青,比如梅纹、艾绒,她们的皮肤、神态、服饰、姿态都与乡下人不同,她们优雅美丽、文静羞涩、漂亮有才华,特别是有艺术特长,柔弱而让人怜爱。这些城乡的女孩子,在曹文轩的作品中,是美的化身,不管是她们美丽的外表,还是艺术才华,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在他的作品中,这些女孩子永远是干干净净的,她们出现的时候,乡亲们都不说话了,静静地注视着她们。她们演奏手中的乐器时,听的人都被征服了,她们的美能够震撼人心,让人敬重。曹文轩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对这些女性形象倾注了他的审美追求,践行他“美感和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1]586的文学观。在他的新作《蜻蜓眼》中也不例外,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他塑造了奥莎妮和阿梅一老一少两位女性形象,在这两位女性形象上再次承载他关于“美”的思考和追求。
奥莎妮是一位法国马赛的女郎,年轻的时候在马赛的一家咖啡馆邂逅了阿梅的爷爷,两人一见钟情,在法国结婚生子。二战之后,因为家族事业的需要,跟随爷爷来到中国,直到死去。
奥莎妮的美是东方式的,她优美、静穆、干净、羞涩、含蓄内敛,带着孩子似的纯真,带着人类永恒的真、善、美。奥莎妮首次出现在书中,是在马赛的一家咖啡馆看书,静静的,带着点羞涩,此后文中也多次写到奥莎妮的羞涩,比如见到太爷爷时,羞涩地躲在爷爷背后。奥莎妮除了具有东方女性的羞涩,她还喜欢中国的旗袍,喜欢在雨天撑着油纸伞,尤其喜欢具有中国味儿的红色油纸伞。她坚持精致体面的生活,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即便是在战乱的时候、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在飘摇动荡的时期,她和她的家人出门必须是干净得体的,每周日要喝咖啡,坚持使用香水,弹奏钢琴演出一定要有演出服装,这看似有些矫情的细节,正是奥莎妮爱美和美的体现,也是不被现实打败的生命尊严的体现,是以“美”对抗“丑”的宣言。
奥莎妮安宁、温柔、纯净、善解人意,她永远都保持着微笑,她用美和优雅、微笑和慈爱滋养了在上海蓝屋子里生活的每一个人的灵魂,用爱让一家子人在困难与磨难中学会守望相助。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一家人没有受政治气候的影响相互揭发,或者因为避嫌而彼此不认,而是相濡以沫,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在最困难的时期,奥莎妮当掉家里值钱的东西,兼职做翻译,用不丰厚的收入精打细算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当她看到孙子孙女们在困难时期穿着寒酸,她想给他们织毛衣,但是没有毛线,她拆掉了自己的毛衣给每一个孩子织了一件漂亮的毛衣。当她知道孙女阿梅要参加学校的钢琴演出时,她觉得演出一定要有演出的服装,就费尽心思把自己年轻时的一条裙子裁剪成一个漂亮的演出服;当她得知阿梅因为身份问题而被学校取消演出时,她不顾当时紧张的社会氛围,在自己家的花园里,给阿梅举办了一场钢琴演奏会,组织家里大大小小十几口人参加。为了给奥莎妮治病,家里人决定卖掉家里唯一值钱的钢琴,奥莎妮出院知道后,几经波折,用母亲留给自己的家传戒指换回了钢琴,因为阿梅喜欢弹钢琴,也因为钢琴在她眼里,是美的生活的象征。在困难时期,她省吃节用,也会在阿梅放学的时候带着她去蛋糕店,给阿梅买一块她喜欢吃的蛋糕,满足一个小女孩的小小愿望。在被人怀疑是特务抓走下放到农场劳动搬砖时,她也保持微笑、用雨水洗澡,在被剃为阴阳头时,她想着借抓她的女孩子的纱巾裹头,从而保持自己仅剩的那点尊严。
奥莎妮在生活中散发出来的美、善和爱的光辉,不仅滋养着自己的家人,而且也感染着家里的佣人。在最困难的时期,即便家里的经济已经捉襟见肘,她也不忍心解雇家里的佣人,只是因为佣人一家也等着佣金养家,在后面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的时候,宋妈和胡妈只能留一个,谁走谁留?两人相互体谅谦让,最终用打赌奥莎妮穿什么颜色的旗袍来决定,但是不管是走的,还是留下来的,后来都还是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撑着度过艰难的岁月。
小说塑造奥莎妮的美,体现在她的容颜仪态上,体现在她永远的微笑上,体现在她的温柔优雅、宁静宽厚上,体现在她对生活的精致追求上,体现在她对艺术的热爱上,体现在她对家人体贴入微的关爱上,更体现在她面对苦难的时候,永远微笑、不怨天尤人,坚韧不屈、宽容悲悯的性情上。
小说中另外一个饱满的女性形象是阿梅,阿梅像曹文轩笔下的很多女孩子,长得漂亮水灵,有一双大大的、水汪汪的眼睛,非常乖巧懂事。阿梅出门走到哪里都能引来他人注视的目光。和奶奶去蛋糕店买蛋糕,第一口总是要喂给奶奶;下雨天,为了追赶被风吹走的红色油纸伞,跌倒了又爬起来,跌破了膝盖不哭不嚷,反而欣喜地把红油纸伞拿给奶奶;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出门看到路边因没有饭吃而饥饿的孩子,虽然自己也很饿,还是会将手里的面包分给他们。
阿梅非常懂事,在她还只有几岁的时候,当她知道家里境况的时候,每每路过蛋糕店的时候,就要绕着走,她不想让奶奶为难。她是奶奶的小棉袄,她和奶奶有一个秘密,只有她们两个在场的时候,她们才会互相叫对方的法语名字。她会陪着奶奶坐在黄浦江的岸边,听奶奶讲述自己的家乡马赛以及马赛家里的温馨,听奶奶无数遍地讲述她和爷爷的故事。她会弹钢琴给奶奶听,会在奶奶心情不好的时候,静静地依偎在奶奶身边陪伴。在得知不能参加学校的演出后,为了不让家里人,尤其是奶奶失望,她独自在外面待了许久,等到演出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回家,假装自己参加了演出。她在奶奶被罚去农场搬砖的时候,不顾路远和农场的环境恶劣,去农场陪伴奶奶,给奶奶带去慰藉。她在得知自己钟爱的钢琴被卖了之后,非常安静,不吵不闹,为了安慰奶奶,不让奶奶难过,说自己不爱弹钢琴了,背地里自己经过打听找到买钢琴的人家,偷偷地在别人屋檐下听钢琴的声音。她在宜宾为了早几天回到上海见到爷爷奶奶,每天早早地到码头找人买退票。她和姥爷一起去抢走蜻蜓眼的年轻人家,帮奶奶要回了蜻蜓眼。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喜欢阿梅,她是美的化身。
阿梅也是承载曹文轩“美”的理念的一个重要人物形象,她纯洁善良、漂亮懂事、善解人意、有艺术才华。她和奶奶奥妮莎一样,永远都是干干净净的,美的。面对一切苦难,从来没有歇斯底里地大声哭喊,悲痛欲绝,而是克制隐忍,用微笑面对苦难,用精致庄重对抗丑陋粗鄙,这也是曹文轩一直坚持书写的“美”的内涵。
二、美的意境:意象书写
曹文轩非常重视文本的美的意境构建,而美的意境构建,很大一部分在于风景描写。在他看来,“风景在参与小说的精神构建过程中,始终举足轻重”[2]117。一篇有美感、有质量的小说是离不开风景的参与。“我们在分析美感来自何处时,会发现许多个方面:一个诗化的主题、一些干净而优美的文字、心灵圣洁的女性形象、一个不同流俗的精神境界……但最主要的方面,却竟然是风景。风景悄然无声地孕育了美感”[1]118。曹文轩对风景描写推崇备至,同时,他也非常擅长描写风景,在曹文轩的“油麻地”系列小说①写作中,风景的描写无处不在,作者运用通感,从触觉、视觉、听觉、味觉等多角度描写水乡的芦苇、水鸭、雨、稻田、蜻蜓、荷叶等风景,对于自然风物的瞬间美感的捕捉也非常传神。但在《蜻蜓眼》这部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点并不在曹文轩熟悉的江南水乡,而在上海这个都市,城市里面没有他擅长的自然风物,于是他便将目光转移到一件件物什上来,并赋予这些物什一定的象征意义,通过物象的描写表达他的情感和审美倾向,使文本具有唯美的意境。
小说命名“蜻蜓眼”本身就是一个美的意象。蜻蜓眼是一种玻璃制品的装饰品,作品中的两颗蜻蜓眼是阿梅的太爷爷从一个收藏家手里得到并带到法国,并作为爷爷和奶奶结婚的信物赠送给了奶奶奥莎妮,太爷爷在弥留之际,嘱托奥莎妮要好好保护蜻蜓眼,蜻蜓眼在被抄家的时候,被人抢去,奶奶念念不忘,几番索要无果。后来阿梅的姥爷带着阿梅用六幅字画换了回来,最后奶奶在准备结束自己生命之前又千里迢迢赶到宜宾将它留给了阿梅。蜻蜓眼在小说中不仅仅是一件宝物,曹文轩赋予了它别样的含义,它见证了爷爷奶奶的爱情,也见证了这一家人在苦难年代的悲欢离合。同时在传承和赠予中也饱含了浓浓的亲情:太爷爷赠给奥莎妮,因为他认为她配得上这件宝物;奥莎妮赠给阿梅,因为她认为阿梅最像她,阿梅也配得上这件宝物。在赠送蜻蜓眼的过程中,亲情在传递,美也在传递。
除了蜻蜓眼,作品还描写了小皮箱、旗袍、杏树、毛衣、油纸伞、钢琴、香水、纱巾、大芦荡等意象,这些意象无一不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无一不承载着曹文轩对美的寄托。小皮箱是除了蜻蜓眼之外,奶奶最为珍视的物品,因为这个小皮箱是奥莎妮离开马赛的时候,她妈妈送的,里面装着她在法国成长的美好记忆,所以她把小皮箱放在卧室里离自己最近的地方,这样她就可以常常怀念家乡,睹物思人,以此感受到家人的温暖。阿梅长大了要去宜宾了,她也像当年母亲送给她一样,把小皮箱转给了阿梅,小皮箱装满了阿梅在上海、在蓝屋的记忆,伴随着阿梅去千里之外。小皮箱在这里承载着浓浓的亲情和爱意。
除了小皮箱的描写之外,曹文轩在小说里还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奥莎妮为孩子们织毛衣的情节,因为家中工厂及厂里的资产已经交给了国家,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日益窘迫,奥莎妮看到孩子们身上的补丁衣服颇觉心酸,非常想给孩子们织毛衣,无奈囊中羞涩,于是她把自己所有的毛衣拆了,用拆下的毛线给十个孙子孙女织了毛衣,毛衣的款式和图案都是精心构思,不满意的织了一半也要拆掉重来。当奥莎妮从早到晚忙着把十件毛衣都织完,让孩子们穿在身上的时候,鲜艳、美好、迷人,“让上海的秋天变得不再萧索和荒凉”[3]33。织毛衣不仅体现了奥莎妮的慈爱,而且体现了她对生活美的追求。
“杏树”这个意象,寄托了奶奶奥莎妮对家乡亲人的怀念,也表现了爷爷对奶奶深深的爱恋。奥莎妮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她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气质上都已经和上海融为一体,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越来越思念自己的家乡、思念家乡的亲人。奥莎妮在马赛家的花园里有一棵杏树,在这棵杏树下,有太多她关于家人的温馨记忆,为了缓解奶奶的思乡之情,爷爷在苏州一户人家找到了棵杏树,用自己心爱的劳力士手表换了它,把它移栽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并精心呵护。在无数个周末的下午,爷爷奶奶坐在这棵杏树下喝咖啡,在回忆中漫谈,在被抄家的时候,那些人破坏杏树,爷爷被打也要竭力保护这棵杏树,其实爷爷要维护的是奶奶对家的牵挂和思念,也是爷爷对奶奶的深情厚谊。
“香水”这个意象不仅体现了奶奶对美和精致生活的追求,而且表现了爷爷对奥莎妮的爱,在那个年代,买到一瓶奶奶用的香水非常不容易,然而奶奶一辈子用惯了香水,怎么能没有香水呢?爷爷到淮海路一家只供应外国人的商店冒着被认为是特务的风险,用非常特别的方式在一个法国女郎那里购得一瓶香水,虽然计划周密,还是被怀疑成里通外国的特务而遭毒打,在爷爷和阿梅的努力下,终于把香水带给奶奶了。在小说里,杏树、香水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象,曹文轩赋予了它们美和爱的内涵,即便生活再困顿,生活的品质和仪式感是不能丢的,是用生命也要去保持和捍卫的,爷爷找杏树、买香水,除了对奶奶浓浓的爱意外,也有他想找回生活中的精致和美的仪式感。
旗袍、油纸伞的意象是奶奶爱美的象征,奥莎妮钟爱旗袍、她说“我从法国漂洋过海,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是因为旗袍在等我”[3]47。人在旗袍的包裹下越发的美,人把旗袍也穿得越来越美。在下雨天偶然邂逅了雨中的红色油纸伞,她就爱上了红色油纸伞,此后的雨天就只用红色油纸伞,在雨天的校门口,奥莎妮举着红色油纸伞,面带着永远的微笑,等着阿梅放学的举动,成了小学家长、孩子们眼中忘不掉的风景。在风雨中,两人追赶着被风吹走的油纸伞,相视而笑,轻唤对方名字,挺着腰背,高高举起的油纸伞,更是风雨中温暖的亮丽风景线。
三、美的内涵:人性善美
《蜻蜓眼》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这期间正是中国风云变幻的时代,回避历史时代的苦难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曹文轩也没有打算回避苦难,相反,苦难正是他所需要的时代背景。在曹文轩看来,单纯的快乐是不可取的,在面对苦难时所选择的情感克制的姿态和在苦难中表现出来的大美人性,对苦难的内消和情感的节制,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人性的美好和伟大,才是值得歌颂的。他认为:“哭泣决非艺术。极度的悲哀写进文学时,应进行一次降格的处理。因为,不顾形象的哭泣只会损坏艺术。文学没有理由夸张痛苦,因为展示不幸,恰恰是为了‘人类的崇高、伟大、坚韧与顽强’。”[4]69人性的高尚和伟大是在有节制的淡淡的伤感情调中凸显的。面对困难和伤痛,曹文轩采取一种降格的艺术处理,好让人们不至于在悲痛中失去美感,他认为:“艺术是一种节制。我喜欢在温暖的忧伤中荡漾,决不到悲痛欲绝的境地里去把玩,我甚至想把苦难和痛苦看成是美丽的东西。正是它们的存在,才锻炼和强化了人的生命。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人领略了生活的情趣和一种彻头彻尾的幸福感。”[5]182这种创作理念一直贯穿在曹文轩的文本写作中,在《蜻蜓眼》中也不例外。
在苦难中对人性美的赞誉,首先表现在对美的坚守上,不因外部环境而对美有所遗弃或者有所马虎。因为战乱、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三年灾害、“文革”等一系列时代风云变幻,奥莎妮一家也在时代的骤变中发生着变化:爷爷家原本开着丝绸厂,生意做到欧洲,家财丰厚,过着体面富贵的生活,后因战乱,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苦,后来把工厂交给国家后,爷爷就成了自己厂里的一名职员,家里的园丁、司机都辞去,仅留了女佣胡妈,一家老小十几口人的生活难以为继,“奶奶觉得,这日子就像一条大河,那大河从前是满满一河清澈的水,并且日夜流淌不息,而现在,这条河忽地将水流尽了”[3]28。然而不管怎么计划着花每一分钱,还是不能应对日益贫苦的日子。即便如此,奥莎妮也不肯让日子过得寒酸,什么时候,都要让一家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不断地典当掉家里值钱的物品,也要让家人感受生活的精致和美好,“在她的心目中,日子的品质,当用生命去保证”[3]50。所以即便再艰难,在平安夜的晚上,她都要为孩子们准备装了糖果的新袜子。为了不让孩子穿补丁的衣服,她拆掉自己的毛衣也要给孩子们织毛衣,让孩子们体面干净地生活。即使没有充足的钱,也要为阿梅买上一块蛋糕,满足孩子的愿望。每周末还是要煮一次咖啡,和爷爷在杏树下细品漫谈,回忆往事。她一定要在阿梅的钢琴演奏会上给她做一条像样的裙子,因为演出要有演出的样子。她对美的坚持,还体现在她对香水的执迷,在她看来,没有香水,和要了她的命差不多。在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典当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也不愿意卖掉家里的钢琴,因为在奥莎妮心中,钢琴不仅是阿梅的心爱,更是艺术和美的象征。
对人性美的书写,还表现在人物对苦难的理解和对生命尊严的体悟上。奥莎妮的美和优雅,不仅体现在她在顺境时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而且体现在她身处逆境时的从容淡定,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变化,奥莎妮永远都是面带微笑、从来没有抱怨,在她用爱和美的滋养下,一家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守望相助。在家里经济捉襟见肘时,她从来也没有抱怨,而是想办法让大家的生活能够过得体面、干净。在被罚到农场去搬砖时,尽管从来没有干过粗活,尽管每天累到无言,但她还是会忍痛完成工作,依然可以把砖搬到船上后转身对着阿梅微笑。在被抄家时,不慌张、不谄媚、不叫骂,被抓走也不失仪态。在被剃了阴阳头后,奥莎妮默然流下屈辱的泪水,跟小姑娘借了纱巾裹头回家,看着家里被糟蹋得一塌糊涂,她叹息了一声,此时她决定去天堂找阿梅的爷爷,艰难困苦和现实磨难都没有将奥莎妮打垮,真正杀死奥莎妮的是被剃了阴阳头,这对于她来说,是对尊严的摧毁,是对“美”的摧毁,于是奥莎妮裹着当年阿梅的爷爷送的纱巾去宜宾,把蜻蜓眼赠给了阿梅。回到上海的家中,一切安排妥当后,洗得干干净净,穿戴整齐、头裹着纱巾平静地躺在床上自杀了。奥莎妮没有对任何人说她被剃阴阳头的经历,她一个人忍受着这份屈辱和痛苦,她用死告诉了家里人她为什么裹着纱巾。家里人谁也没有追问奥莎妮是怎么死的,面对十分体面就像安然入睡的奥莎妮的脸,他们没有痛哭流涕、哭天抢地,只是默默地落下大颗大颗的眼泪,守灵时为奥莎妮唱了一支又一支的歌曲,出殡的时候,阿梅把小皮箱和油纸伞放在了奶奶身边,让爱和美永伴奶奶。奥莎妮和一家人在困难面前的情感克制自持,冷静体面,让人觉得生命厚重、尊严厚重。
《蜻蜓眼》用优美的女性形象和优美的意象构建优美的意境,用人性之善、人性之美来对抗时代社会之丑恶,反映了曹文轩一贯的文学主张,以“美”来净化心灵,引人向上。他不直接描写生活中的苦难,而是将苦难作为一个时代背景,他着力表现的是人在苦难悲剧面前灵魂的高贵和人性的优美,恶和丑陋无时不在,却不能让善和美屈服。曹文轩对苦难中人性的高贵和美的追求,给人以感动、温暖和力量。
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不算典型的儿童小说作家,在他的文本里面还有很多成人的故事和视角,其语言表现也不似儿童文学作家那样带来简单快乐的体验,在其描写成人作品的小说里面,又会出现儿童的视角,经过儿童视角过滤后的纯美,与成人的世界又有些差距。所以他的小说也不能完全算是成人小说,尽管文坛对他的这种叙事处理也存争议,但不可否认,执着追求“美”的曹文轩的创作给当代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在当代文坛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注释:
① 曹文轩的大部分小说如《草房子》《红瓦》《青铜葵花》《天瓢》等描写的都是发生在江南水乡的故事,出现比较多的是油麻地,在这里用“油麻地”系列小说代指曹文轩以记忆中的水乡为故事发生地点的小说文本。
[1] 曹文轩.永恒的古典——《红瓦》代后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2] 曹文轩.与王同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3] 曹文轩.蜻蜓眼[M].南京: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
[4]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5] 曹文轩.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M].北京:21世纪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