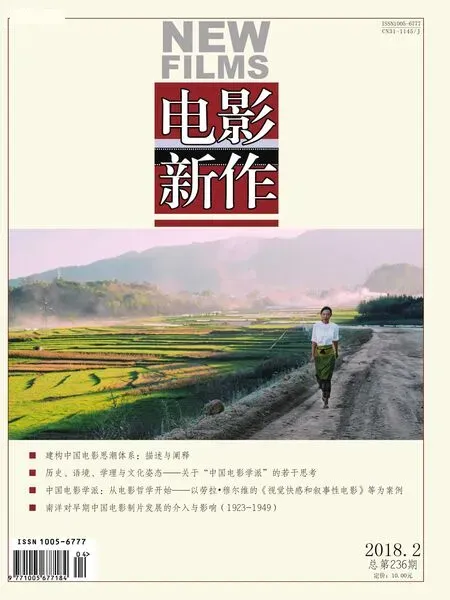亮剑与突击:“新主流大片”对国家形象的建构
张新英
一、“新主流大片”与国家形象建构
随着《湄公河行动》(2016)、《建军大业》(2017)、《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等现象级影片在电影市场上的火爆表现,“新主流电影”的概念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及。“新主流”这一称谓,与在它之前出现的“主流电影”称谓一样,在电影批评界常常与“主旋律电影”“商业片”“类型片”“大片”等概念联系在一起。1999年,马宁在《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一文中,详细阐释了“新主流电影”的概念。彼时,“新主流电影”被设定为“低成本的有新意的国产电影”(建议的成本范围是150万—300万元人民币)。“新主流电影”创意的提出,建立在对中国主流电影存在的成本问题、档期问题、观众问题、模式问题等一系列弊端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但在马宁看来,“新主流电影”并非是对主流电影的否定和颠覆,相反,“‘新主流电影’主张保持创新,与主流电影并肩作战,以质量的实力、互补的战略作为主流电影正面战场的一个好助手,也为主流电影达到模式的新变,提供实验的场所”。“新主流电影”“在未来将与高度分工和模式化的主流电影共同主导票房倾向”,“是主流电影的一个分支,是一种具有新意和现代意识的主流电影”。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制约,马宁期待中的“新主流电影”浪潮并未如期而至,随之而来的是《英雄》(2002)、《十面埋伏》(2004)、《满城尽带黄金甲》(2005)等“大片”的问世,宣告中国电影步入“商业大片”时代。而批评界对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尤其是商业大片的争议和批评,从未停歇。
在各种争论的喧嚣声中,《集结号》(2007)、《梅兰芳》(2008)、《建国大业》(2009)、《唐山大地震》(2010)、《建党伟业》(2011)、《智取威虎山》(2014)等作品的出现,以其对类型电影元素和商业元素的娴熟融合,还有节节攀升的票房纪录,逐渐扭转了人们对“主旋律电影”的固有认知。其后的《湄公河行动》(2016)收获12亿元票房;《战狼2》(2017)更是以史无前例的56亿元票房刷新了中国电影多项票房纪录;《红海行动》(2018)也当仁不让地斩获36亿元票房,攀升至内地影史票房第二的位置。至此,这些令观众耳目一新的主流电影开始与“新主流电影”的称谓画上等号,而诞生于现代电影工业背景下的“新主流电影”,其内涵已与马宁笔下的“新主流电影”大不相同——它明确指向那些打通了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界限、将主旋律电影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诉求与商业电影的大众性、故事性和商业性融合起来的主流电影。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新主流电影”都具备“大片”的典型特质——投资不菲、明星扎堆、场面宏大、宣发到位、票房可观等。也就是说,“新主流电影”既遵循商业电影(大片)的制作模式,又保留了主旋律电影中明确的价值观传达和意识形态诉求,并在二者之间实现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不可否认的是,《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在票房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背后依托的是近年来日渐成熟的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和日益繁荣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国电影在数量、质量及票房上的一系列傲人数据,不仅见证了中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转变,也折射出中国由“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蜕变的事实。可以说,《战狼2》《红海行动》等影片的高口碑和高票房,与其契合了大国崛起背景下中国观众自尊、自强、自豪、自信的国民心态不无关系。电影作为文化产品,一直以来都承担着建构国家形象、传达国民心态的文化职能,“新主流大片”自然也不例外——在中国由“大国”向“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新主流大片”致力于在电影故事中建构和传播一个新型的国家形象,展示一种全新的国民心态。
二、历史与现实:“新主流大片”塑造的国家形象
陈旭光先生在《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阐释与建构》一文中提到:新主流电影由两个序列构成,一种是“由内到外”即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大片化,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影片;一种是“由外到内”即商业电影大片的主流化,如《十月围城》《智取威虎山》等影片;而《湄公河行动》《战狼2》则“开辟了新主流大片中的又一个新的亚类型”。而无论属于哪个序列,“新主流大片”的题材选择基本不外乎两种:一种指向中国的近代历史(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一种指向近年来的现实(如《战狼2》《红海行动》)。正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对比性呈现中,“新主流大片”建构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国家形象。

图1.《战狼2》
在《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这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影片对国家近代历史形象的演绎:《建国大业》以1945年8月抗战胜利开篇,将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进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北平和南京的解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串联起来;《建党伟业》通过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救亡图存的尝试,青年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胡适和辜鸿铭的北大论战等场面,展示了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民初政治图景;《建军大业》全景式地呈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三河坝阻击战、井冈山会师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可以说,“建国三部曲”的叙事时间跨度较大,但三部影片所展现的中国均处于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历史节点。那些为新中国的诞生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的人们,以他们的智识、勇气、青春、热血与生命书写了国家命运最为关键的历史篇章。他们的每一次选择和行动,都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建国三部曲”雄辩地证明:新中国的诞生,是历史和人民主动与必然的选择。这里的国家形象,随着影片中历史时间的进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建党伟业》是在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危局中寻找出路;《建军大业》交织着理想、青春、热血与激情;《建国大业》则是包含着克制与理性、自信与从容。一个国家从混沌到觉醒,从混乱到有序,从迷茫到自信的成长过程,贯穿交织着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对国家永恒不变的热爱与牺牲。至此,“建国三部曲”以爱国主义为基点,实现了全景式描绘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雄心壮志。影片对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书写,亦不乏客观公正的反思,比如《建党伟业》中辜鸿铭对五四运动狂飙突进式的革命做出的“暴徒”评价和面对罗家伦的质问无语离去的背影,引发人们对五四运动的深层思考;袁世凯怒骂日本公使的一幕,也让教科书上一直以反面形象出现的历史人物得到了重新评价的机会。在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境遇中,影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呈现摆脱了此前非此即彼的固有模式,体现出艺术创作观念上可贵的进步。而这种进步,也从侧面映衬出一个愈来愈开放、包容、自信的中国形象。
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整体贫弱无助、千疮百孔的国家和民族形象相比,《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现实题材的“新主流大片”则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个和平强大、无畏无惧、有勇有谋的大国形象。《湄公河行动》中,13名中国船员无辜被害,我公安部部长慷慨直言:“我们要给金三角势力一个强烈的信息:当国民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不会坐视不理。我们会以武制武,出动最精锐的缉毒人员,全力维护湄公河流域的安全通航。”以高刚为首的特别行动小组,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查明案件真相,为遇难同胞讨回了公道;在《战狼2》中,原战狼中队特种兵冷锋,在非洲国家陷入武装叛乱的危局之中,孤身一人深入沦陷区,带领同胞和难民一路杀出重围,成功逃离了武装分子的恐怖屠杀;《红海行动》中的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深入炮火连天的伊维亚共和国执行撤侨任务,在敌众我寡的不利情况下,不仅成功营救了人质,还一举粉碎了叛军武装首领的惊天阴谋……这些影片中的主人公,无论是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还是配合默契的群体英雄,他们最终能取得行动的胜利,除了个体或群体超高的智慧和能力因素,还与其背后强大的国家力量的支持息息相关。在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和令人血脉喷张的动作场面之外,影片还在释放一个明确的信息:中国公民无论身在何处,强大的祖国始终是他们的依靠。在得到拯救和保护的侨民甚至是其他国家难民的欢呼和感激声中,一个强大、自信、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形象巍然矗立,其无畏无惧、所向披靡的强国风范展露无遗。

图2.《湄公河行动》
如果我们将上述作品中繁荣富强、崭露锋芒的国家形象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主流电影中塑造的国家形象做一个对比,或许会对今日“新主流大片”中国家形象的变迁有更加深刻的印象:“第四代”导演于“文革”结束后登上影坛,他们的影片关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对中国历史、中国革命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多有呈现。杨延晋的《苦恼人的笑》和《小街》,张暖忻的《青春祭》和《沙鸥》,吴天明的《人生》和《老井》,谢飞的《本命年》和《香魂女》,滕文骥的《生活的颤音》,黄建中的《小花》,吴贻弓的《城南旧事》,黄蜀芹的《人·鬼·情》,翟俊杰的《血战台儿庄》和《长征》,李前宽的《开国大典》,丁荫楠的《周恩来》以及韦廉的《大决战》《大进军》……在这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现实题材影片中,“第四代”导演以其倡导的质朴而又不乏诗性的纪实美学,塑造了一个从苦难和沧桑中站立起来的中国,一个带着旧日伤痕依然奋力前行的中国。“第五代”导演则将目光转向古老的中国,从蛮荒、偏僻、闭塞的乡土中审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而在80、90年代的中国则呈现为一种忧郁神秘、滞重迟缓的面目——在陈凯歌的《黄土地》《孩子王》、张艺谋的《菊豆》《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李少红的《血色清晨》等影片中,既有陈规陋习导致的人生悲剧,又有残酷历史带来的血泪伤痕。20世纪9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六代”导演,最初以叛逆和先锋的姿态出现,他们的镜头聚焦于现代都市角落或偏远小城中的边缘群体,表现他们的颓废迷茫、叛逆挣扎与压抑失落。张元、贾樟柯、王小帅、路学长、章明、管虎、娄烨等人的电影,无不带着压抑沉重的气息——这里的中国,是浮华喧嚣背后满目凌乱的现代都市,是压抑闭塞到令人绝望窒息的偏远小城,是一群青春年少却茫然无措的边缘人群。新世纪以后,中国电影的创作队伍空前壮大,“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之后被称为“新生代”的青年电影力量同场竞技,他们的影片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手法多变,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不再具有可以辨认和描述的统一面目,而是呈现为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多元复杂形态。而那些海外获奖的中国电影,尤其是《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古装武侠、功夫电影,则与之前风靡海外的中国功夫片(如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人的电影)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外观众对中国形象和国人形象的认知。
不难发现,与上述影片中或闭塞落后,或沉重压抑,或茫然无措,或浮华喧嚣的中国形象相比,“新主流大片”中的中国形象,再次有了可以辨识的特质:即使满目疮痍,却依然带着生猛鲜活的气质,充溢着热血沸腾的激情。特别是在表现现实的军事动作类型中,中国开始展崭露锋芒,不再吝惜向外界展现自己的“肌肉”与力量。
“新主流大片”中的中国形象特质,源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崛起的中国正通过电影,向世界展示一个和平安定、富足强大的国家形象:她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她曾经备受蹂躏饱经沧桑,但在所有热爱她的子民们不懈的抗争中,她实现了艰难的民族自救,并致力于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如今,她朝气蓬勃,激情勃发,却又稳重理性,自信从容。她不仅强大到可以保护身在海外的中国公民,还可以拯救陷入灾难和困境中的异域人民。如果说《开国大典》这样的主旋律影片,让鸦片战争以后饱受西方列强蹂躏和奴役的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重建民族尊严,那么《战狼2》《红海行动》则让国人感受到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敢于“亮剑”、勇于“突击”,构成了“新主流大片”新的精神内核。
三、从内容到形式:“新主流大片”如何建构国家形象
在“新主流大片”中,敢于“亮剑”和“突击”的国家不是一个宏大而虚无的存在,也不再停留在没有多少说服力的空洞口号中,而是电影故事得以成立的逻辑基点和情节得以推展的必要元素: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中国的历史境遇让历史人物做出了各自的选择并最终影响和改变了国家命运;在当代军事题材电影中,英雄人物的拯救行动,背后都依托着国家的意志和力量。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到逐渐觉醒奋起抗争,再到昂首屹立“亮剑”突击,一个日益崛起的大国终于从历史深处走到了当下的国际舞台的中心。因此,《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空天猎》等现实题材影片都不约而同地将故事的叙事空间设置在了异国他乡:《湄公河行动》是毒品泛滥的金三角地区,《战狼2》是战乱频仍、病毒肆虐的非洲大地,《红海行动》是阿拉伯半岛的伊维亚共和国,《空天猎》是局势变幻莫测的马布国……主人公完全置身于陌生的异域,他们不仅要面对复杂险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更要直面凶残的敌人,去完成看似不可能的艰巨任务。

图3.《卧虎藏龙》
为凸显英雄形象和中国力量,在敌我双方的人数设置上,敌众我寡对比悬殊是最常见的配置:《战狼2》一开始是冷锋独自一人深入战区,踏上拯救医学专家陈博士的冒险之旅。到达中国工厂后,虽有退伍老兵何建国和富二代卓亦凡的协助,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冷锋都需要独自一人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湄公河行动》《空天猎》《红海行动》中虽是小组群体作战,但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还是令人胆战心惊:《湄公河行动》中,不足10人的特别行动小组深入的金三角地区是毒品重灾区,各种势力林立,他们心狠手辣,装备精良,戒备森严,那些被训练成杀人机器的娃娃兵可以随时随地发动防不胜防的死亡袭击;而《红海行动》中的8名蛟龙突击队员要面对150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因为是境外行动,他们还必须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服从各种国际法规的制约,如《湄公河行动》中的中国警察海外执法实际上是一次境外秘密行动,枪械武器无法直接从国内运送出境,小分队只能从当地购入各种武器;《红海行动》开篇便是蛟龙突击队在“绝对不能进入他国领海”的前提下追歼海盗,在伊维亚政府无法为其提供正面军事力量援助,而时间又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完成拯救人质的任务……这样的困境设置,在强化影片戏剧冲突的同时,也形象地折射出近年来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它让人们意识到,影片中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爆燃场面”,其实是中国英雄“戴着镣铐的舞蹈”;它也让人们深信,崛起之中的中国即使面临各种未知的困境,也依然能够展示“勇者无惧、强者无敌”的大国境界和强者风范。
让影片中的“强国”形象更具说服力的是,上述作品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并非毫无依据的凭空臆想,而是建立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片中的故事背景、人物、事件均有现实原型的支撑:2011年“湄公河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快速反应和果断行动成为《湄公河行动》故事的出发点;2015年3月,中国军队出动武装军舰执行也门撤侨行动构成了《战狼2》和《红海行动》的故事背景和主线;《空天猎》开篇的空中拦截段落来源于现实中中国空军在东海和南海对美军侦察机的拦截……这些事件原型的存在,让中国整体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强大更具说服力。在当前世界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下,中国从《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中的“自救”状态,变成《战狼2》《红海行动》等军事动作片中的“救人”状态,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深刻意义不言自明。
除故事层面外,“新主流大片”在表现形式上也与时俱进,一方面迎合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升级的需求,打造可以与好莱坞主流商业电影相媲美的视听盛宴,一方面通过对各种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视听符号的运用,来明确无误地彰显国家力量。首先是上述军事动作片中展示的各种重型战略武器装备和敌我之间激烈对决的动作场面。在《战狼2》中,中国海军052D型驱逐舰强势登场,并在关键时刻发射巡航导弹一举歼灭雇佣兵,确保了中非合资工厂工人的人身安全;特种兵出身的冷锋更是同叛军雇佣兵头目弗兰克上演了一场中国特种兵与美国雇佣兵之间的生死较量,无论是拳拳到肉的贴身肉搏,还是惊险刺激的坦克对决,最终冷锋代表的中国获胜,用铁一般的事实打破了弗兰克关于“中国是劣等民族”的偏见,让国人一抒胸中郁气;《红海行动》里的“临沂号”护卫舰严阵以待,守护中国人质的安全,“蛟龙突击队”队员与恐怖分子在异国的街巷、大漠、荒原疾风骤雨般的枪战和格斗,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军人的铁血丹心,影片结尾处,中国军舰在中国南海乘风破浪,霸气驱赶即将进入中国领海的外国船只,明确宣示了国家守护领海安全的决心和能力;《空天猎》中歼-20隐形战机、歼-11B和歼-10C战斗机轮番亮相,中国空军出动精英部队与马布国叛军进行空中对决,展示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这些影片中,各种先进武器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场面的呈现,除了增强影片在军事方面的专业性和视觉上的可看性之外,还是对国家意志和力量的一种体现。

图4.《空天猎》
“新主流大片”也会着意凸显“家”与“国”的意象,通过“家”与“国”的并置,激发观众的家国情怀。在《战狼2》中,当冷锋右臂高举五星红旗带领侨民车队穿过交战区时,这面护佑人们踏上归家之路的红旗已化身为国家的象征;结尾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上打出的那段霸气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当你在海外遭遇危险,不要放弃,请记住,在你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生动地呼应了片中“中国的护照不一定让你能去任何地方,但能把你从任何地方接回来”的主题,与“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伤我国人者,皆为我敌”的大国宣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红海行动》里,奉命营救人质的蛟龙突击队队员不止一次地对人质说“我带你们回家”。影片结尾处人质安全回家,活着的英雄祭奠牺牲的战友,他们身后则是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形象地阐释了中国铁血军人“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牺牲精神。不同于《战狼2》令人激情澎湃的“护照宣言”,《红海行动》结尾打出的提示字幕(中国公民无论身处哪个角落,遭遇紧急情况均可拨打外交部12308热线,向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看似平淡无奇却又掷地有声。通过这些带有“家国”内涵的意象符号,“个人命运”“小家”与“大国”被巧妙地联系起来。尤其是与安定、和平、蒸蒸日上的国内环境相比,电影中的异国经常处于政治动荡、炮火连天的残酷环境中,而民众要经常面对战争、屠杀、瘟疫等苦难的威胁。两相对比,中国观众会进一步认同“这个世界并不和平,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这句话。
在演员的选择上,“新主流大片”倾向于明星组合。《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新主流大片”以其堪称史无前例的豪华明星阵容吸引了观众,可以说,它们的火爆,与观众在影片中“数星星”的心理不无关系;《建军大业》更是因为起用了刘昊然、白宇、马天宇、欧豪、张艺兴、鹿晗、李易峰等一众“小鲜肉”演员而引起极大的争议;《战狼2》由功夫明星吴京担纲主演,搭档同样被归到“小鲜肉”行列的年轻演员张翰;《湄公河行动》由张涵予和彭于晏坐镇;《空天猎》则由李晨、范冰冰领衔;《红海行动》里有张涵予、张译、黄景瑜、杜江等。对于一部志在赢得观众和市场的主流商业电影来说,使用具有票房号召力的明星乃至自带流量的“小鲜肉”是其应有之义,这点毋庸置疑。但对“新主流大片”而言,选择大明星和“小鲜肉”担纲主演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影片通过那些有高度辨识性的明星面庞(如张涵予、彭于晏、吴京等硬汉形象),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批朝气蓬勃、能征善战、智勇双全的英雄形象,他们或是《战狼2》里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孤胆英雄,或是《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影片中心有灵犀配合默契的英雄群像。特别是在近年来中国喜剧电影流行,英雄形象和英雄主义被边缘、被改写甚至被解构的情况下,“新主流”电影重塑了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英雄人物,复活了久违的英雄主义。英雄主义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必须的,一个认同和崇拜英雄的国家无疑是一个有希望、有力量的国家。

图5.《建党伟业》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英雄不是冰冷机械的国家机器,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个体:《战狼2》里冷锋护送战友的骨灰回家,目睹孤儿寡母被恶霸欺辱,忍无可忍之下不惜违背军纪严惩恶霸,只为维护牺牲战友的尊严;他在出狱后远赴非洲,只为找出杀害未婚妻龙小云的凶手并为之复仇;他不忍看到非洲义子与其母分离,承诺会让其母子团聚。《湄公河行动》里卧底的缉毒警察方新武面对害死女友的占蓬,满腹仇恨无处宣泄,明知违规也要以血还血手刃仇人。《红海行动》里张译饰演的“蛟龙突击队”队长,一开始只是单纯地服从命令执行营救中国人质的任务,最后却决定营救更多的人质并摧毁恐怖分子的脏弹计划……与凶残冷血的境外敌人相比,中国的英雄人物是善良、正义、情义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彰显和传达着中国无私无畏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并赋予中国形象以柔性的情感力量和悲悯的价值观情怀。
总之,“新主流大片”通过对影片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的艺术处理,建构起一个刚柔并济、和平强盛的中国形象。作为中国崛起的时代隐喻,“新主流大片”与它们描绘的中国形象一样,渐渐褪去幼稚、浮躁与浅薄,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并成功地获得了观众的历史认同、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四、问题与隐忧:对“新主流大片”建构国家形象的反思
如前所述,“新主流大片”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对于强化新时代背景下民众的国家认同感、提升民族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电影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也必然会对中国的海外形象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而《战狼2》《红海行动》等作品的成功,必然会鼓励和催生更多此类“新主流大片”的出现。而“新主流大片”除了要规避同类题材扎堆、观众审美疲劳等商业片通病,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上也要慎之又慎,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负面效应。
在《战狼2》最初成为现象级电影之时,电影学者肖鹰便撰文对《战狼2》和《敦刻尔克》这两部现象级的战争电影进行了对比。肖鹰在肯定《敦刻尔克》艺术成就的同时,对《战狼2》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战狼2》中“爱国主义”主题的表现,“主要着眼于暴力动作和军事攻击的设计与呈现;与此对应,不仅具有人物角色扁平、空洞、脸谱化的弱点,而且全片贯穿了一系列严重的叙事漏洞”。肖鹰甚至断言“相对于它创造的国内票房纪录,《战狼2》是走不出国门的‘爆款大片’”,他转述国际媒体对《战狼2》的批评:“相对于对它的技术性水平和错误的批评,国际媒体更严重的批评是针对《战狼2》令人质疑的思想内涵,‘《战狼2》不仅充斥着平庸的设计,而且包含着民族主义狂热’。多位批评家指出,《战狼2》是史泰龙在《第一滴血2》中塑造的‘白人拯救者’(White Saver)的中国翻版,‘像史泰龙的早期明星片一样,《战狼2》教训你,敲打你,还要期待你欣赏’。”笔者虽不能完全认同肖鹰对《战狼2》的批评,但其提及的“警惕电影中出现的民族主义”观点,却切中“新主流大片”未来创作的隐忧。的确,如果作品过度张扬所谓的“爱国主义”,过度展示自己的肌肉和力量,甚至流露出对武力和暴力的过度迷恋,便可能误入“民族主义”的歧途,引起观众尤其是国外观众的争议和误解。“新主流大片”致力于建构的崛起中的大国形象,应该是崇尚和平与文明的强国,但在必要时绝不惮于“亮剑”和“突击”,她有能力参与维持国际秩序,维护民族尊严,保护本国公民的安全,但她绝不居高临下,更不会主动挑衅,与他国为敌。
另外,当前的“新主流大片”主要聚焦于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军事题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当下的国际政治现实固然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但其中的国家形象如何避免单一,走向多元,也是创作者应该思考和努力超越之处。惟此,“新主流大片”才能与时代同步甚至超越时代,并获得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注释】
①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J].当代电影,1999(4):4-16.
②同①
③同①
④陈旭光.中国新主流电影大片:阐释与建构[J].艺术百家,2017(5):13-21.
⑤肖鹰.2017:全球两部现象级电影——《战狼2》与《敦刻尔克》比较谈[J].贵州社会科学,2017(12):50-57.
⑥同⑤
⑦同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