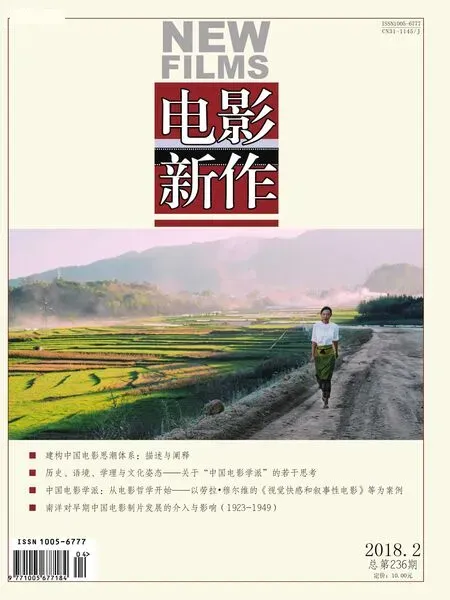《白鹿原》:从小说经典到电影凡庸
——兼论小说改编电影的美学参照系
苏月奂
小说《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彪炳史册的经典文本,而电影《白鹿原》却在一阵商业化的锣鼓喧嚣后沦为中国当代电影中的凡庸之辈。《白鹿原》从小说到电影,其艺术境界和艺术命运产生了云泥之差。这并非个案,而似乎是中国名著改编电影的共同遭遇。对于《白鹿原》的文学改编现象,尽管学界不乏探讨,却没有触及关于小说改编电影的美学参照系的重要元问题。那么,这些元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评价《白鹿原》的改编?可以从哪些方面提升《白鹿原》改编的质量?
一
电影《白鹿原》的上映曾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关于“改编”话题的讨论尤其激烈。学界对《白鹿原》的改编有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一种是褒扬,一种是贬抑。这本不稀奇,一部电影总有其优缺点。怪异之处是,发表在国内知名期刊上的文章竟然对相同的电影元素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评判。这暴露出小说改编电影的美学参照体系的缺失。
吴辉和周仲谋各自从三个方面肯定了《白鹿原》的改编,其中有两个方面是重合的。这两方面分别是电影对小说的提炼式改编和电影对民俗的影像呈现。吴辉还称赞了电影对原小说删繁就简的人物选择,周仲谋认为电影的主题表现也是成功的。更多的人则是对《白鹿原》的改编展开了包括这些方面的批判。谢刚提出,电影《白鹿原》在企图兼顾删繁就简和存续史诗气质的矛盾中陷入了“骑墙叙事”的窘境,影片对民俗的展示也由于时代语境的改变和符号隐喻效能的衰退而沦为对地域文化的直白宣传。潘桦认为,电影《白鹿原》中核心意象和独特人物的缺失导致电影失去了原著的诗性智慧和诗性品格。在主题方面,孙宜君提到,电影《白鹿原》忽视了原著的精神内核。李杨也指出,电影《白鹿原》丢弃了小说的“去革命化”和“再传统化”两大主题,其漏洞百出的欲望叙事是“失魂落魄”的。虽然批评的声音高于肯定的声音,但声音的高低、文章数量的多少不是判定《白鹿原》改编优劣的标准。
对《白鹿原》改编得失的探讨固然应该百家争鸣,可是对诸多相同问题的判定完全相反却并非正常现象。审美和评判的感受与角度再多样,也不应美丑不分,毕竟是非好坏总有个标准。改编似乎没有可以遵循的尺度。原著就一定是完美无缺、至高无上的吗?原著的品质如何界定?改编的依附标准为何,还是完全自由?评论应当以什么为依据,还是各说各话?谁是权威,市场还是学者?这些都是当下小说改编电影各个环节中十分关键却被长久搁置的元问题。这些元问题呼唤一个统一的美学参照体系,没有这个美学参照体系,再多的争论也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合力。

图1.《白鹿原》
翻检古今中外的叙事文本,那些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必然是能够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启迪思想的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形式不论是主观化的,直观化的,还是超现实化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都有“客观真实”的内核。所谓客观真实,就是对本真人性的再现和表现入木三分,进而引发共鸣,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真实。那些堪称经典的艺术文本必然呈现了丰满立体的典型人物和真实透彻的生活本质。如果一本小说原著不符合客观真实,充斥着对人性的虚假描写,它就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如果一部电影能超越小说达到客观真实,它也值得赞赏。电影改编应该以客观真实为美学参照体系,既不离开原著,又不应该迷信原著。一次成功的电影改编既应该赢得市场,也应该征服学者。
不论学者们如何评价《白鹿原》的改编,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客观事实,《白鹿原》从小说经典沦为了电影凡庸。电影《白鹿原》从上映之前的备受关注到现在的几乎无人问津只不过寥寥数年的时间。从客观真实的美学参照体系来看,《白鹿原》的改编有着较大的硬伤。这一方面要从艺术语言形式转变过程中的变化上寻找原因,另一方面要从小说作者与电影导演的文艺素养和对故事的艺术把握上探求差距。
二
《白鹿原》从小说到电影的过程,艺术语言也由文字变成了影像。这使文本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表达和接受都跳入另一种模式。共时性的跳转指文字和影像的指称功能,历时性的跳转指小说和电影的叙事接受。
文字和影像的指称具有不同的本性,这决定了它们之间的转换要损失一些美感。文字的所指和能指是一对多的关系,不同人的脑海可以联想和想象出不同的所指模样。在艺术活动中,想象与联想本身就是审美的进行时,影像也能指示文字所描述的所指,这使文本从小说到电影成为可能。但是在一级符号系统里,影像的能指和所指是重合的,影像中指示房子的那个事物就是所指示的事物,而且此事物不是概念而是具体存在。观众一眼即见,省掉了从能指到所指再联想和想象的过程,也损失了这个过程带来的美感。艺术语言的本性决定了它的制约性,这个损失不能避免,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艺术形式转换的不可行。
虽然小说阅读过程的想象和联想美不可言,但那种想要探究“那时那地那人那事”的愿望却因想象和联想的增强而更加强烈。寻求确定性的欲求作为对安全感的原始诉求,深深镶嵌在人类基因中。这种寻求确定性的基因让接受者对艺术世界从小说到电影的转变充满期待,而且越是名著的改编越引人关注。另外,确定性的影像抹掉了想象和联想的美,却带来了视听享受的可能。电影世界能给予观众很多在现实中无法得见的奇观景象,比如古代风情、奇幻、美人等,其取景框的构图本身就富于美感,声音的加入也使影像世界更加完整逼真。小说世界令人向往,用电影复现小说世界无疑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
因此,从艺术语言的共时性层面来看,从小说到电影是有失有得的,也符合一般观众的愿望。如果转换失败,则要反思一下,是原著文字魅力太高,还是影像水平太差。文字魅力太高的小说以文字为灵,一经改编便把优势丧失殆尽。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语言幽默风趣、讽刺辛辣、比喻绝妙,这是小半人力大半天赋所铸就的精灵般的文字,是任何其他艺术形式都复现不了的。文字水平并不卓越且以情节见长的小说最适宜改编,改编成的影像也容易获得超越小说的魅力。电影《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启用林青霞演绎东方不败一角,林青霞的英气和俊美是文字描摹不尽的。电影《阿凡达》美轮美奂的影像也让文字无力。小说《白鹿原》的文字并非出神入化,还在适宜改编的范围之内。

图2.《白鹿原》
电影《白鹿原》开头那无边涌动的麦浪,极具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房屋建筑、室内摆设,那些古朴农民、古调秦腔都可圈可点。电影中的白嘉轩、黑娃、田小娥、鹿子霖,从形象上也比较符合原著的定位。特别是黑娃的扮演者段奕宏,小说人物的那种自尊与自卑、质朴和鲁莽、善良和反抗在他的外形中都能有所蕴含。电影中白嘉轩的正气和硬气,田小娥的妖媚、大胆和智力不足,鹿子霖的狡猾善变,都比较符合演员的色相特征。但白孝文和鹿兆鹏两个角色却令人失望。白孝文比黑娃小好几岁,在电影中看起来却比黑娃老很多,更重要的是,他的长相远远达不到小说后来提到的“儒雅的仁者风范”的程度。鹿兆鹏的选角是电影最大的败笔,在小说中他是作者最钟爱的角色之一,“眉高眼大,睫毛又黑又长”,这样有些“欧范儿”的帅气面孔与眼角、嘴角、脸颊都下耷且带有喜剧色彩的郭涛实在挂不上钩。当然,电影并非不可以对原著的人物加以合理的改编,但是电影《白鹿原》似乎并没有对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形变”赋予特别的解释和思考,而更像是一场选角“事故”。
除了文字和影像指称功能上的差异,小说和电影叙事接受方式的不同也是改编时需要适应的。读者阅读小说是在沉思中接受故事,观众欣赏电影是在观看中接受故事。在沉思中接受故事时,读者的外部感官处于抑制状态,全部的大脑都处在内向的思考中,而且思考的节奏由读者自己决定。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选择,再加上联想和想象,读者对小说的再创造程度就很高,因此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观看中接受故事时,观众的外部感官是开放的,至少视觉听觉处于高度的兴奋的状态,脑力要分出一部分维持视听兴奋,剩下的才用来思考情节。另外,影像不会等人,观众只能按照电影的节奏去接受情节。如果电影的节奏过快,或者有些复杂,超出了观众的思维水平,观众就只能囫囵吞枣。如果节奏过慢或者太简单,无法挑起观众的兴奋,观众就会感到无聊。即使节奏适中,也难免众口难调,因为观众的思维能力差距很大。电影一旦形成,观众就无法选择接受速度,再加上联想和想象的空间小,观众对电影的再创造程度就相对低,因此,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中,对叙事的把握和改造尤为重要。
基本成功的电影叙事有两个要求,一是将故事讲完整,二是情节节奏要遵循观众的大脑活动规律。讲完整一个故事似乎并不是难事,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且前后照应紧密即可。小说《白鹿原》以白、鹿两家为辐射点,以众多具有不同代表意义的人物为支撑,讲述了从清朝覆灭到新中国建立这段历史时期内白鹿原的兴衰变化。电影《白鹿原》似乎是想不失原著的宏大历史性,所以将重大历史转折都以事件的形式点明,但电影似乎又难以填满这么大的骨架,所以只选取了田小娥的故事加以详细展现。这就造成了整个叙事的畸形,对宏大历史来说,田小娥的角落太“小”;对田小娥来说,许多历史事件都是多余的,宏大的历史大而无当。这同时又造成了情节节奏的拖沓和与观众大脑活动需求的错位。接受者在接受一个历时性文本的过程中,其大脑兴奋程度是不断变化的。刚开始的时候,接受者的兴奋需要被唤醒,因此强调文本开头要设置悬念或者其他刺激。随着情节的进展,接受者的大脑兴奋度升高,直至需要一个情节高潮使大脑兴奋度达到最高值。待接受者脑力消耗殆尽,大脑兴奋度急剧下降,结局就要在这个时候发生。如果电影开始时的情节没有调动起观众大脑的兴奋,或者情节拖沓迟迟不让情节高潮在观众脑力可维持的时间内来到,又或者观众脑力不足时电影还未结束,都会使观众的观影期待与电影的情节设计相错,造成观众审美接受的疲惫和失望。
电影《白鹿原》开头即按时间顺序,开列清朝覆灭、民国建立、军阀混战的历史,结尾又是以日本入侵扣合,这些与电影主要讲述的田小娥的故事几乎没有关联,只有中间的闹农会、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破裂尚还牵扯她的男人和她的故事。从整体来看,宏大的历史支架游离于中心故事,所以电影叙事显得松散,不能有效地刺激和迎合观众的大脑活动。所幸电影的时长只有两个半小时,中间田小娥的故事也有吸引人的噱头,这种松散的叙事倒是没有对观众的接受造成巨大压力。
三
电影《白鹿原》在选择鹿兆鹏和白孝文这两个角色的失察,让影片在叙事上有些松散,使文本从小说到电影的第一步走得有些踉跄。但这第一步的不圆满还不足以对改编造成致命伤害,致命性的问题在于电影的立意和表意与原著有着天差地别。当然,并不是说谨遵原著就是改编的不二法门,本真人性和客观真实才是改编的衡量标尺,何况原著在本真人性的刻画和客观真实的表达上也不一定完美。小说《白鹿原》就存在人物形象扁平化和主题先行的缺陷。陈忠实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都明显地带有他的个人喜恶。那些他喜欢的人物,如朱先生、白灵是完美无缺的、被神化的,白嘉轩也是一个典型的符号化人物,这些人物设置都偏离了本真人性和客观真实。他不怎么喜欢鹿子霖,则让他小善小恶皆备,反而比较符合本真人性。关键人物形象的扁平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陈忠实所要极力完成的“去革命化”和“再传统化”的主题,这就是主题先行的后果之一。原著的缺陷是完全应该在改编中得到修正的,而这首先要求电影创作者经历一个吃透原著的过程。因此,电影改编基本成功的层次有二:一是电影创作者在吃透原著后认为自己的素养层次不及原著作者而谨遵原著;二是电影创作者在吃透原著后认为自己有更高明的修正方法而在电影中有所改进。但电影《白鹿原》创作者似乎根本没有领会小说浑厚的文化内蕴。

图3.《白鹿原》
小说《白鹿原》以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恩怨斗争为主线,串联起了从封建社会崩塌到新社会建立这段波谲云诡的历史时空,糅杂了陈忠实对历史前进势不可挡的哀叹和欣喜之情。白鹿原是一块封建文化气息浓厚的土地,一直以来,以白嘉轩为族长的封建宗族制度维持着原上的道德秩序。陈忠实对白嘉轩这个封建文化的代理人褒多贬少。白嘉轩在精神上深信封建道德,在行动上谨遵乡约,除了暗用手段跟鹿家换取了安置祖坟的一块风水宝地外,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因此,他头一挨着枕头就能睡着,面对田小娥凶恶的鬼魂毫不畏惧毫不妥协,身遭土匪的报复也大义凛然不现惧色。他寄予厚望的长子白孝文和他最钟爱的女儿白灵都因背叛了他所恪守的封建文化而被逐出门外。他仁义、沉稳、坚定,带着古老的睿智鉴证着封建道德惩恶扬善的巨大力量,并有点自鸣得意。白嘉轩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审判者和执行者,他的文化靠山是关中大儒朱先生。每有难办的事情他便问计于朱先生,总能得到有效指点。朱先生在小说中几乎被神化,游走于民间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所到之处无人不对其礼敬有加、崇拜备至,甚至他对死亡和自己死亡后的中国政局都有准确的预测。
朱先生所代表的就是封建文化的魂魄,他的死代表了封建文化的衰亡。陈忠实对他即将离开人世时的描写充满了伤感,对他的一生极尽赞扬,这也代表了他本人对作为封建文化精髓的儒家文化的认同和热爱。曾经的叛逆者——黑娃和白孝文在经历了世事沧桑以后,发现冲破封建枷锁获得自由后的无所适从更加可怕。就像弗洛姆所说,个人一旦把确保安全的原始纽带切断变得孤苦伶仃,就不得不想方设法摆脱这种软弱和孤独的状态。他们骨子里是封建文化中的人,除了封建文化,没有什么能给他们踏实的精神依靠,他们最终转身皈依封建文化。白孝文是投机的皈依者,自私和圆滑的本质注定了他总是向利益靠拢。黑娃是虔诚的皈依者,被朱先生视为“最好的学生”,他的蜕变成功显示了儒家文化的巨大魅力和对男性回归者的包容。田小娥被情欲支配所行的盲目背叛则遭到了封建文化坚决的鄙弃。封建堡垒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引导她回归,新兴力量也没有对这样一个有些愚昧的旧式女人加以援助。她就在封建文化的排挤和新兴力量的无视中走向了必然的悲惨结局——灰飞烟灭,永世不得翻身。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可怜的人物,美丽却有些“是非不分”,想过安生日子却总是被损害,“失足”后想回头却无岸,那些爱过她的男人们最终都否定了她。封建文化对女性如此苛刻,可惜陈忠实似乎并没有给予她足够的同情,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站在了封建文化的立场。
陈忠实对儒家文化满怀深情却也对新生力量充满欣喜。小说中只有两个人物是“白鹿精灵”的化身,一个是朱先生,另一个就是共产党员白灵。白灵出生在白鹿原上“腰杆最硬”的封建族长家里,却最彻底地背叛了这个家庭所信奉的文化。和田小娥、黑娃、白孝文的背叛不一样,她在冲破封建牢笼以后找到了新的精神皈依——共产主义。她安全顺利地完成了这个过渡,既没有像黑娃和白孝文那样“吃回头草”,也没有像田小娥那样被封建文化“处死”。她注定不会死于封建文化,也不会屈服于任何损害她的力量。陈忠实没有让白灵与封建文化正面交锋,而是让她经历了文化的交替。鹿兆鹏虽然是最有建树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但他不是“白鹿精灵的化身”,不如白灵受陈忠实偏爱。陈忠实派他对封建祠堂进行了无情的摧毁,完成了叙事的历史真实。真正的革命是文化的嬗变。朱先生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和白灵代表的新文化都是作者所青睐的,他既对逝去的儒家文化留恋不舍,也对蓬勃兴起的新文化由衷喜爱,他在内心不希望二者交战。两个白鹿精灵的化身透露了他的情感倾向,也启发读者重新审视两种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这对现代中国人重新认识两种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图4.《白鹿原》
如果电影《白鹿原》剪掉了朱先生,白鹿原上的封建文化就失掉了神韵,剩下的多是僵硬冷酷的部分。如果剪掉了白灵,令人振奋的新时代新文化,特别是女性解放的曙光也就没有到场,只留一个田小娥胡乱挣扎、至死不休。电影成了白嘉轩与田小娥的斗法场,田小娥“毒染”了封建文化中的两个优秀青年黑娃和白孝文,白嘉轩像法海一样代表封建文化镇压了田小娥这个“祸害”。但白孝文为了田小娥和他的娃能活下去“卖了自己”,黑娃为了给田小娥报仇亲手打断了白嘉轩的腰杆,也和父亲鹿三断绝了关系。白孝文和黑娃没有“悔改”,反而因为剪辑到此而给人感觉他们在“爱”的道路上继续走着。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封建文化对男女大欲的剿灭不近人情,但青年斗争不屈。田小娥的悲剧就几乎全要怪罪封建文化了。这种简单幼稚的情节和立意曾被无数劣质的影视剧所用,显示了导演把封建文化等同于封建糟粕的错误认知,更泄露了导演文化素养的浅薄。实际上,田小娥、白孝文、黑娃三人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新文化教育,他们脑子里“祖宗”“祠堂”等烙印根深蒂固,他们几乎不可能完成以“新”代“旧”的变革。执行和实现这种变革的是共产党革命者白灵和鹿兆鹏,而他们被弱化到令人不可容忍的程度。
其实,封建文化并非否定男女大欲。小说中孝义媳妇向兔娃“借种”,“棒槌神会”公开允许已婚妇女和其他男人交媾,这些在现代看来都不可思议的性行为在封建社会生殖崇拜、传宗接代的文化环境中都被合理化了。封建文化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在“传宗接代”的原则下才成立,田小娥是因为背离了这一原则才万劫不复。另外,封建婚姻也不是不幸的代名词。小说中朱先生的婚姻以及黑娃的第二次婚姻都是幸福成功的。朱先生择偶,“他已经看过四五个媒人介绍下的七八个女子,都不是因为门第不对或相貌丑陋,在于朱先生一瞅之后发觉,有的眼睛大而无神,有的媚气太重,有的流俗”,他最后瞅中了白家大姑娘“刚柔相济”的眼睛,从那双眼睛里他看到“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上猝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黑娃找了一个知书达理能够“管管”他的女人,漂亮地完成了他回归封建文化的转身。这两桩封建文化中的婚姻以理性为基础,向读者展示了理性的婚姻对人生圆满的建设性作用。与理性婚姻相反的则是田小娥和黑娃感性的婚姻,这种婚姻以一见钟情式的激情为基础,与作者想以婚姻传达的理念是相通的。
叔本华对这两种婚姻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一见钟情的婚姻体现了造物主的意志,令恋爱双方以无可抗拒的巨大激情生育自然界最优质的后代,之后造物主就不管二人是否幸福了,两人开始发现对方的缺点,并为当初的冲动而后悔;理性的婚姻虽然没有那么大的激情,但双方各方面比较匹配,容易走得长远。封建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初的目的是建立理性的婚姻,维护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安定。然而封建文化代代相传的方式是教条的,没有原因和论证,因此现代人觉得很多东西不可理喻。在小说中,朱先生的婚姻和黑娃的第二回婚姻都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合理性一面的佐证。电影中没有孝义媳妇和兔娃,也没有“棒槌神会”,没有朱先生的择偶,也没有黑娃的重新选妻,而田小娥的悲剧歪曲了封建婚姻制度的本质。
在小说中,陈忠实对旧文化和新文化都采取肯定的态度。相应的文化对应相应的社会形态,封建文化适用于封建社会,新文化匹配于“新”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文化的变革。对于“新”社会来说,封建文化不适用了但未必不好。对于那些被封建文化浸淫的人们,坚守他们心中的信念也是一种应当被尊重的生活方式。陈忠实的宽容和厚度正体现在他对两种文化的态度上。电影却恰恰相反,既不看好封建文化又对新文化冷眼相看。电影剪掉了封建文化和新文化的“精灵”,也砍掉了能立体呈现封建文化的枝桠。电影由白嘉轩、田小娥、黑娃、白孝文所构成的是一个严重失实的封建生活群落,其所建立起来的封建文化单薄、畸形,让现代人不仅无法正确理解作者想传达的意味,还隔阂更深,误解更重。电影对新文化的冷漠则主要体现在对鹿兆鹏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小说中的鹿兆鹏外形俊美、勇敢、机智,矢志不渝地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正面形象。电影中的鹿兆鹏除外形不达标之外,还以喜剧形式出场,以逃跑的方式作为最后一次亮相。鹿兆鹏逃跑后再没出现就暗示了他及其所背负的事业都前途渺茫,他所代表的文化也黯淡下去。而历史早已确定无疑地夯实了共产主义事业和新文化在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正确性和光明性。对整个新旧文化的扭曲,从小的方面来说是一部电影的失败;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对中国文化、社会、历史和观众的犯罪。

图5.《白鹿原》
四
当然,将一部五十万字的小说改编成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确实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但是,改编本来也并不要求面面俱到,而是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突出原著中最能震撼人心的东西,并对其震撼力进行进一步强化。而向来以“文艺性”著称的中国“第六代”导演中的优秀代表王全安,因为没能正确理解小说、认知文化,却硬生生将一部富有文化韵味的小说改编成了靠情色噱头吸引人的俗片。这是他向商业屈膝投诚的表现,还是他本身文化素养的露怯?不得而知。
针对以上的分析,本文试图对《白鹿原》的改编做一些修正,以使电影在现有的容量范围内能更接近本真人性和客观真实。首先,鹿兆鹏和白孝文的扮演者应该根据原著的描述重新选择。鹿兆鹏的扮演者应该兼具富家子弟和共产主义革命者形象的双重气质。白孝文的扮演者应该少一些沧桑和木讷,多一些文雅之气。其次,电影中人物所承担的情节任务应该有所调整。朱先生若不出现,白嘉轩身上不仅可以强化朱先生儒家文化智慧的一面,也可以获得其理性婚姻的幸福,作为和田小娥命运的对比。孝义媳妇“借种”怀孕的情节可以嫁接到孝文媳妇身上。白灵若不出现,她的一些革命活动应该和鹿兆鹏的合二为一,加强对鹿兆鹏这一形象的塑造力度。黑娃即使后来不出现,也比亲自出来打断白嘉轩的腰、逼死父亲要合理。再次,电影中的情节重点需要做些变动。电影前面没有必要铺垫那么多黑娃和孝文小时候的情谊,因为电影后面并没有出现他们二人为了田小娥反目成仇等复杂情节,省出的时间不妨将孝文多年后回归封建文化的过程加以详述。
这样的改动或许会稍微扭转一下电影对小说原意的曲解和滥造,但是电影已经公映,无法挽回了。虚假的人性和历史已经用艺术的形式潜移默化地传达给了观众,那些扭曲的文化观念已经植入千千万万观众的心中。如果名著改编仅仅是让电影能借着名著的名气而大赚一笔,如果名著改编不能让观众领略到影像的震撼和启迪,如果名著改编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欺诈行为,如果名著改编损害了观众的精神健康,如果名著改编污损了中华文化,这样的名著改编还有何颜面屹立于中华大地上?这样的创作者还有什么民族责任感和职业良心可言?这样的改编不止《白鹿原》一部,让人大跌眼镜的导演也不止王全安一人。中国电影的改编不应靠学者“马后炮”的修正,而应加强电影创作者的文化素养。电影创作者应在读懂读透原著的基础上,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以本真人性和客观真实为美学参照体系打造真善美的电影。
【注释】
①吴辉、别君红.得,远大于失——也谈小说《白鹿原》的电影改编[J].当代电影,2013(9).
②周仲红.西部乡土史诗与地域文化的影像呈现——论电影《白鹿原》的改编艺术[J].北京社会科学,2013(1).
③谢刚、李硕嘉.骑墙叙事、语境错位与隐喻功能耗散——电影《白鹿原》改编之失一解[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6).
④潘桦、巩杰.诗性智慧与诗性品格的缺失——以小说为参照分析电影《白鹿原》[J].现代传播,2013(6).
⑤孙宜君、高涵.从《白鹿原》改编看电影与文学的非良性互动[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
⑥李杨.《白鹿原》故事——从小说到电影[J].文学评论,2013(2).
⑦马立新.论低碳艺术的本体特征及其建构机制[J].现代传播,2014(4).
⑧[德]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M].邵牧君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6.
⑨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67.
⑩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