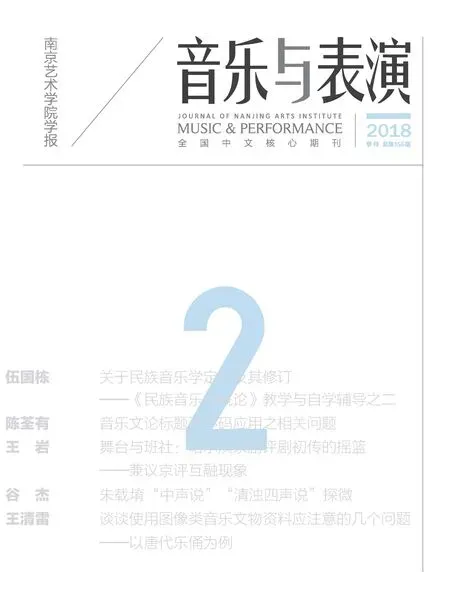舞台与班社:哈尔滨京剧评剧初传的摇篮
—— 兼议京评互融现象
哈尔滨开埠之后是我国西乐发展的先锋城市,有关哈尔滨西乐的研究著述较为丰富。相较而言,对于哈埠同期发展起来的国乐的研究则较为零散,对戏曲艺术在哈初期传播情况的研究更不明朗。为此,笔者从京剧和评剧传播交流的基本场所舞台和茶园入手,考察了创作演出的基本主体——戏班与戏社,分别研究了哈埠早期京剧和评剧两大剧种的发展状况。
一、班社:评剧初传的主体
班社,是戏班与戏社的代称。评剧起源于河北,早期的班社皆以莲花落为特色,警世戏社和洪顺戏社较有影响。20世纪10年代末,评剧班社数量迅猛增加。在警世戏社的带领下,关内的评剧班社纷纷出关演出,活动范围逐渐从冀东扩展到东北地区。哈尔滨是东北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枢纽,吸引了大批来自关内的艺人。评剧的开端,即从警世戏社入哈肇始,在1921—1930十年时间里,来哈演出班社逐渐增多。主要活动班社有警世戏社二班、警世戏社三班、洪顺戏社以及元顺戏社。这四个班社各具特色,依托于各大茶园,不断完善评剧艺术,向市民持续展示了评剧的魅力。
(一)警世戏社
头班(1908—1928)由成兆才在唐山发起,主要成员有金开芳、月明珠等人。该社1919—1920年间来哈,在庆丰茶园演出。虽然在哈活动短暂,但头班将评剧引入哈尔滨,促进评剧的传播与推广,为警世戏社的另外两个班社二班和三班提供了《花为媒》《王少安赶船》《杨三姐告状》等基本演出剧目。
二班(1922—1928)由王凤亭委托李春盛成立于唐山,先期主要演员有王万昌、王万良等,重组后有碧莲花、金灵芝等名角,1925至1928年在哈演出于华乐舞台和庆丰茶园。该班人员流动性强,曾有王万昌、王万良、花云舫、芙蓉花等40余名知名演员集体离班的情况,而几经停办重组。重组后为维持正常演出吸收了一些梆子演员,因而影响相对较弱。1927年12月9日的《滨江时报》对二班的演出做了详细的广告[1],特别提到由天津礼聘初次来哈演出著名的青衣花旦金灵芝等38名演出人员和《东斗星》《辞活》《书囊计》《美凤楼》《还阳自说》《仁杰赴考》《夸北京》《大逛灯》《宦海潮》《生死板》等主要剧目。
三班(1923—1931)由王凤亭委托陆兆丰成立于天津,由盖五珠、紫金花等演员主演,又以筱桂花、筱桃花等演员闻名,1925至1928年在哈尔滨同乐茶园演出。这个戏班善于吸纳名角,有相对固定的优秀的班底,又着力评剧改革,影响较大。1927年1月16日,紫金花演出评剧传统剧目《杜十娘》。同年3—4月,在不足一个月里共演出包括《双婚配》《阴功报》《败子回头》《花为媒》《大逛灯》《孙猴上坟》《茶瓶计》《三河县》《慈虐异报》《哭井》《卖油郎独占花魁》《巧奇冤》《杜十娘》《杨三姐告状》《借当衣》《胭脂判》《借女吊孝》《王小借粮》《老妈开嗙》《刘公案》《赴善会》《保龙山》《书囊记》《蜜蜂计》《炎天雪》《铁牌山》《秦雪梅双吊孝》《得孝双全》《败子回头》《美凤楼》《普天同庆》《循环报》《高成借嫂》《王少安赶船》《驼虎出世》《番驼虎》《六月雪》《对门楼》《夜审周琴》《赴善会》等40余出剧目,为成兆才传统评剧剧目的推广和普及做出了贡献。
(二)洪顺戏社(1919—1938)
该班前身是1909年成立的“振兴班”,经1915年改建为“振兴戏社”,至1919年由孙洪魁担任班主,挑班“洪顺戏社”。该班社于1919—1920、1922、1924、1926年先后四次来哈,在同乐茶园、庆丰茶园、华乐茶园、中舞台都有演出活动。该班管理严格,明确了分配方式、请假制度,制定了十项班规,为后来班社的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经验。艺术上以培养武戏演员为精进,促进评剧行当分工。孙俊山等武戏演员排演了《怀都关》《界牌关》《四杰村》等武戏剧目,成兆才创作后期为该班编写并排演了《盗金砖》《露珠坠楼》《枪毙驼龙》等剧目,使评剧表演和剧目日趋丰富。
(三)元顺戏社(1928—1933)
该班由著名演员李金顺组班,建于安东(今丹东),是唯一在东北成立的评剧戏班。该社1928年入哈,长期在庆丰茶园演出。元顺戏社利用乐队伴奏和人声的完美结合将传统剧目创新,为评剧剧目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李金顺改革了评剧的乐器和音量、音乐处理上巧用休止,摆脱节奏束缚,其首演的新剧《爱国娇》进一步扩大了评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女伶的引入和崛起使得哈尔滨评剧艺术在创新的同时获得迅速的发展。在洪顺戏社和警世戏社二班献艺的金灵芝、警世戏社三班的筱桂花以及元顺戏社的李金顺等都是最为著名优秀的女演员。其中筱桂花在哈尔滨演出时间最长,李金顺将她独具特色的“李派”唱腔带到哈尔滨,并成为其他演员争相模仿、学习的对象。她们都对哈尔滨评剧音乐起到了推动作用,为评剧音乐的创新和普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1925年以后,警世戏社二班、警世戏社三班、洪顺戏社、元顺戏社成为评剧发展的主要力量。这四大班社外加其他一些临时组建短暂存在的戏班在哈尔滨集中演出,使评剧出现了与京剧班社抗衡的盛况,共同掀起了哈尔滨评剧发展史上一个高潮。
二、舞台:京剧初传的中心
在评剧蓬勃发展的同时,京剧以“国剧”的姿态占领了哈尔滨大舞台、新舞台、华乐舞台和中舞台,依附于这些舞台,效仿评剧班社成立了众多京剧班社。
(一)哈尔滨大舞台与“义字班”
哈尔滨大舞台是仿照上海大舞台的样式建造而成的大型剧场,楼高三层,外观建筑相当宏伟,舞台布景十分精美,最多可容纳观众4000余人。因1922年和1927年的两次大火导致重建,执事人李鸣九等人负债巨大,1932年的洪水又使大舞台再难起色,最终于1941年倒闭。在大舞台辉煌时期,连台本戏和新编的时装戏日渐增多,以彩头戏而闻名。在舞台布景方面要求极高,房主张景南因此曾派人到上海学习机关布景、彩头,以招徕观众,成为当时哈尔滨各剧园舞台美术水平的代表。为加大创新力度,1927年在《牛女会》用一头真牛作为道具,后来哈尔滨戏曲舞台上又出现了真狗、真猴等。
哈埠戏曲史上成立的首个班社就是1922年成立的京剧“义字班”,它依托于大舞台,在房主胡仁泽、刁致民、张景南等人的资助下,明海山、程永龙连同大舞台执事李祥阁创办,主班人为李祥阁,总教务长为明海山,教师由程永龙、杜文林、马德成、马德武、杨瑞亭、大七岁红、筱九宵、马春奎等人担任。“义字班”共招收2期学员,第一期30名,第二期80名,学生年龄均在10岁左右,名讳均采“义”字,如靳义鹏、张义奎、王义才、筱义光等。艺徒坐科期间经常登台实践,是大舞台《铁公鸡》《安天会》等“群档子”“大操”等不可缺少的演员群体。“义字班”的教学以武戏为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武戏演员及教师,如沈阳的张德仲、烟台的夏长山、天津的吴德奎及哈尔滨的张永奎等。大舞台第二次被焚后二期艺徒全部出科分散至全国各地,至1930年科班停办。“义字班”“四梁八柱”配备齐全,对当时的京剧艺术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带动了其他舞台建立戏班。哈尔滨大舞台除“义字班”外,又成立了“小科班”,培育了京剧艺员近百人,使哈埠京剧界出现了人才济济、新秀辈出的兴旺景象。
(二)新舞台及其班底名伶
新舞台坐落于道外区正阳大街北三、四道街中间的一个封闭的东西走向的胡同南侧,原址为1908年营业的哈尔滨最早的茶园“辅和茶园”,由于茶园失火被毁,于震霖筹集资金复建,于1920年7月16日竣工开台。舞台为砖木结构,坐南朝北,楼高两层,可容纳观众1000余人。早在茶园时期,便是以京剧演出为主的戏曲剧场,拥有一批“宫中”班底和设备。新舞台建立以后,以哈埠伶界中的魁首王少鲁为台柱。至1928年冬,王少鲁因病去世,生意一度萧条,以致入不敷出。1929年开始,以聘请名伶为主要运营方式,影响最大的是被重金请来的闻名上海的京剧老生高百岁。
高百岁(1903—1969)字幼斋,号伯绥,北京人,自幼学习武工,师从李正义,十二岁曾在喜连成科班搭班学艺。他的嗓音脆亮而宽厚,演唱富有韵味。在与周信芳合作《斩黄袍》一剧后,便拜其为师专攻“麒派”唱腔。后来,兼收其他各流派之精华,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高派”唱腔。“高派”唱腔在演唱中严谨规矩、平稳酣畅、韵味醇厚、声情并茂,更富有感染力。在新舞台演出期间,奉献了《赶韩信》《走麦城》《盗御马》等拿手好戏,并排演了大型连台本戏《封神榜》(图1)①1929年3月17日,高百岁于哈尔滨新舞台演出了大型布景机关连台本戏《封神榜》,此剧大致演绎汤帝的第三子纣王,自幼孔武有力有托梁换柱之能,建都于朝歌。太师闻仲、武成王黄飞虎皆有安邦定国的才干,皇后姜氏贵妃杨氏贞静贤淑,纣王本可坐享太平但却被魅惑于妲己的狐媚,终日沉醉于酒色不理朝政,杀忠臣酿酷刑以致民怨沸腾,此时姜子牙挺身而出,仗义兴师灭此无道昏君。该剧堪称新舞台的空前佳剧,精妙绝伦。戏曲海报中首次用“编导”一词介绍高百岁。舞台园主以重金聘请美术大家绘制精巧玲珑的机关彩景,既有金碧辉煌的宫殿又有美丽优雅的花园,有古装样式的兵器、盔甲及精心制作的行头。此外还请人专门教授新样歌舞,使此剧处处都能引人入胜,其中仅凌霄宝殿一幕便消耗数千余金。1929年3月,高百岁与新舞台台柱青衣小翠花等合演《六国拜相》,高百岁所饰苏秦深得喜爱,其表演使观剧者有亲临其境之感。戏迷们无不欣然观赏,客座拥挤,以致警察于门外驱阻不准后来者进入。新舞台营业日趋发达,开演后收入大洋30000有余,创下多年收入之最。

图1.高百岁演出海报(载1929年3月17日《滨江时报》)
在激烈的舞台竞争中,新舞台班主为争夺观众,启用年仅12岁的小小宝义、12岁的李万春、13岁的粉面哪吒唐韵笙及14岁的坤伶武生王少鲁与之对垒,采取“以小对老”的办法在哈埠掀起一股童伶热,使京剧舞台更加活跃。1930年以后,新舞台改由秦玉峰经营,由于旦角较多,演出了通俗喜剧《五花洞》。
(三)华乐舞台与华乐戏班
位于道外南十六道街,东四家子荟芳里路以北,与哈尔滨大舞台隔道相对的便是华乐舞台。舞台由房产主胡仁泽之子胡少卿出资,因仿照天津侯家落子园样式而建,也被称为“华乐落子园”。开台于1921年9月15日,是哈尔滨最早的集妓院、茶馆、酒楼、戏园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娱乐场所,有坐席2300个,接待的对象也都为权贵富商。华乐舞台设计独特,其舌形舞台向观众席延伸,四周以“红莺下处”“宝升下处”“德凤下处”“索兰下处”四个观众区域相围,宛如盛开的花朵。内部构造精致齐全、雕梁画栋,装饰极为考究奢华。
华乐舞台曾多次改变经营内容,但总体上仍以戏曲演出为主。建成初期,演出落子戏,但因形式单一致使营业萧条,甚至曾一度停业。未免该园闲置,又改为坤书馆,召集荟芳里各妓馆妓女每日午后至此演唱戏曲。1922年,舞台执事张茂发鉴于当时戏曲市场的变化,开始聘请京剧名伶重新开演,观剧往来者络绎不绝②1922年11月,华乐园主不惜巨资重金邀来京津新角贾润仙等于当月十四日登台演戏,致使该舞台竟无容足之地,场面壮观可想而知。详见《滨江时报》1922年11月16日。。虽然重新聚起观众,但聘请名伶开销极大,舞台因此组建了集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为一体的同名戏曲班社以增加收入。班主为杨焕章、李祥阁,演员60余名。演出的主要剧目包括:《拾黄金》《明末遗恨》《打渔杀家》《扫松》《独木关》等数十部。1928年,为了在大舞台竞争,聘请评戏班改演评戏,同样受到欢迎。但半年后,改为“东北大戏院”并播放有声电影,随后不久又改为华乐舞台。
华乐舞台擅演新戏。开业初期,演员小惠芬、小如意编排演新戏《诸葛亮招亲》,后来又排演时事新戏《枪毙阎瑞生》①依据民国初期发生在上海的一件惨杀妓女案改编,不学无术的大学生阎瑞生设计将妓女王莲英骗至郊外将其杀害。此事被编成戏文,并进行排演。华乐舞台由理化民先生指导,张喜龄、顾炳奎、高三奎、石月明等出任主演。,仿照《康熙南巡记》对乾隆南巡时的离奇故事进行编排。由于舞台的不断繁荣,大凡来哈的京、评、梆艺人都以在华乐舞台“打炮”为荣。至1931年,受邀于华乐舞台演出的名角有贾润仙、刘汉臣、蒋宝印、蒋月楼、小小宝义、赵小楼、强云樵、徐君茹、李艳秋、孟兰秋、花翠云、张虹霞、刘艳芳、刘德兆、白玉昆②白玉昆(1894—1971),艺名粉蝶仙,北京人,著名二黄老生。他嗓音宽亮坚实,演唱朴拙大方、念白铿锵有力,当时京剧界以“白玉昆的嘴,杨瑞亭的腿”来赞誉他的唱功。1931年5月受华乐舞台之邀,演出全本《甘露寺》《禹王治水》及三、四本《岳武穆保国》。在他演唱《甘露寺》时,园内之人皆聚精会神观戏,此时舞台失火竟无人察觉,导致发现火情过晚,虽无人员伤亡,但舞台尽毁。等数十人。华乐舞台戏班亦坚持演出至1931年舞台失火而解散。
(四)哈尔滨中舞台与戏班
中舞台始建于1924年,是哈尔滨道外四大舞台中成立最晚的舞台,也是道外四大舞台中唯一至今仍在使用的舞台(现已改为龙江剧场),位于傅家甸中心位置——丰润六道街17号,交通便利。中舞台的房产主为孙质彬,原依东西山墙而建,原约有1000座席,舞台执事为李子玉。30年代中期,由第三代传人孙汝元负责经营与管理。因中舞台建筑以木板为主存在严重的消防问题,被强拆重建。改建后的舞台上下两层,由坐东向西改为坐南向北,可容纳观剧人数增至2800个,改称“中央大舞台”。
中舞台以演出京剧和评剧为主,时常穿插河北梆子及河南坠子等形式,为舞台赢得了生存空间。营业期间京剧剧目以排演传统戏见长,有《白水滩》《连环套》《挑滑车》《战长沙》《取洛阳》《别寒窑》《越虎城》《花停会》《辕门斩子》《定军山》《泗州城》等多部。1927年,中舞台因营业萧条赔累甚巨,以致停演两月有余。1928年2月,评剧艺人金开芳在中舞台演出《杜十娘》,此次演出轰动哈埠,数千人前来观戏,扭转了多年经营欠佳的局面。
中舞台自成立初期至1932年期间,舞台班社由常驻舞台演出的京剧、评剧及河北梆子演员组成,长期于舞台搭班演出的演员有:杨月樵、小杨月樵、宝珠钻、田小梅、董翠铃、李顺来、花艳琴、赵宝庆、韩少芳、周又宸、李云朋等。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哈尔滨,大舞台、新舞台、华乐舞台和中舞台的建立和发展拥有各自不同的曲折经历,但也各具特色,有的以奢华大戏见长,有的以传统剧目为主,有的常演新戏,有的爱搞京评梆混搭。他们共同培养了京剧爱好群体,发展了哈尔滨的戏班组织,见证了哈尔滨京剧早期发展的兴衰历程。
三、班社与舞台:京评互融的基础
班社依托于舞台谋生,舞台扶持了班社求利,二者本乃互生共荣的关系。但正如学者易红霞所言:见“戏”不见“班”,见“艺”不见“人”,是中国戏曲研究的通病[2]。以往的戏曲研究中更关注剧目和艺能,对班社和舞台多有忽视,也就不能充分分析戏曲发展的深层机制。事实上,一个好的班社要能维持票房生计,必须具备三个要素:第一,有固定优秀的演出班底;第二,有固定的编剧;第三,有邀名角入班献艺的能力[3],但班社与外来演员只会因利而聚,利尽即散。显而易见,班社的繁荣和稳定与否,前两个要素不可或缺。如果班社发展壮大,则可以激发舞台与茶园的活力,增加二者的副业收入,扩大其在市场的隐性竞争力;而舞台的扩容与经营,又可直接影响班社的构成和剧目的编创,最终利于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发展。哈尔滨的舞台和茶园因为集中于傅家甸老道外,地理位置极为接近,营业期间自然而然的彼此竞争,擂台戏常年不断,更加促进了班社的成熟和提高。
从戏曲艺术早期发展来观察,京剧与评剧起点高度不同并不构成竞争。京剧在清中期发起,采皮黄腔和梆子腔之长,又受到皇族的青睐和扶持,完善了行当和表演程式,名角辈出、名篇无数,至清末早已拥有了“国剧”的地位。而评剧的主要构成,无论是落子还是蹦蹦,都生于乡间,因过于低俗“鄙俚技艺”之“有伤风化”而多次被城市官方管控乃至禁演。在二者合流之后,评剧才逐步在城市拥有生存空间。聚焦到哈尔滨城市,京剧进入哈市更早,虽然起步于茶园,但很快便占领了面积大、设备先进、装修豪华的各大舞台,四大舞台若同时开演,可容纳近万名观众。相较而言,评剧进入哈市较晚,又多以外来戏班为主要力量,先期在茶园辅助经营,最大的茶园的容量600余人,刚及最小的京剧舞台容量(约1000人)的2/3,演出总体规模较小。而京剧班社财力雄厚,班规管理制度严格,后备人才和外聘名角数量都远较评剧的外来班社可观。综合可见,京剧无可争议地在哈市确立其传统戏曲表演的主体地位,评剧原本无力与之抗衡。
令人意外的是,京剧演出却逐步陷入窘境而评剧稳步上升,出现了京剧舞台要靠评剧拯救票房的情况。特别突出的表现是在中舞台和新舞台,出现了京评同台的“二合水”及京评梆同台的“三合水”现象,打破了二者演出场所的壁垒,促进了京评剧种的互融。促进互融的因素不止于此,重点有三:多次意外的火灾、洪水的发生导致舞台损毁,演出场馆缺失是其一;名角薪酬偏高、舞美装潢开销加剧,舞台戏院收支难抵是其二;观众审美情趣变化,受其他艺术门类和娱乐方式的冲击是其三。再有其他因素叠加,最终导致京剧逐渐脱离其皇族培育的“雅”的特点,更加亲民,而评剧受京剧影响,艺术水准逐渐提升,使“京剧地位恐为评剧所夺”。[4]
京评互融的主要表现也不止于“二合水”和“三合水”,而是在名角、念唱、武功、行当、剧目、服装等各方面彼此吸收优长,各自都有所丰富和提高。比如原本以文戏为主而武戏并不突出的评剧,自吸收了京剧里的“大操”和武生的做功后,不但改变了以往以小生、小旦、花脸为主的唱腔,培养出孙俊山等一批武戏演员,而且其排演的《怀都关》等武戏剧目也丰富了评剧的篇目,扩大了评剧的影响力;又如评剧的念白方面虽然以普通话为主,但是传统戏也借鉴了京剧的湖广韵和中州韵,传统京剧净角名篇《铡美案》被评剧改编,成为评剧的代表剧目;再如白玉霜借鉴京剧的[反二黄]创造了[反调慢板],魏荣元借鉴京剧的[流水]改革了生腔;而一个舞台同时拥有评剧和京剧两套班底、一个评剧班社外聘京剧演员、一个演员既擅京剧又能唱评剧等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值得一提的是,京剧与评剧的互融并非彼此同化,而是更好地发挥了个性优势,成为哈埠传统戏曲音乐艺术的两朵奇葩。
结 语
“不应忽视国乐的地方存在”是新千年以来冯文慈、项阳等诸多学者陆续发出的呼声。传统戏曲艺术在哈尔滨的生存状况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哈尔滨早期的舞台与茶园,不仅止于娱乐管所和茶叶项目的经营,更为市民提供了会友赏乐和观戏论道的极佳环境。这使得哈尔滨音乐文化发展初期并非完全发展日俄音乐文化,而是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色彩。依托于班社,谋生于舞台和茶园的京剧与评剧,共同培养了大批传统戏曲文化的爱好者及其戏曲欣赏的情趣与习惯,共同构成了哈尔滨戏曲音乐文化的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