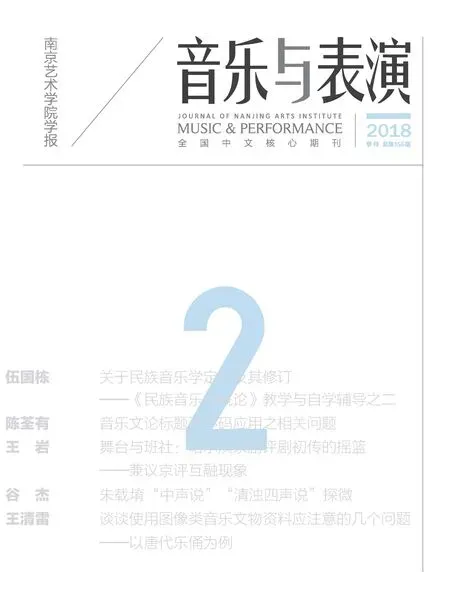朱载堉“中声说”“清浊四声说”探微
黄翔鹏先生在其所著《乐问》中给我们留下一个重要乐律问题:“中声焉系?神瞽焉量?“‘中声’之说是先验的呢,还是有其自然的物质的根据呢?”[1]对于这一问题,明代朱载堉在他所处的时代和条件下提出了独立的见解。他的“中声说”以及“清浊四声说”见于《律吕精义》外篇卷数之中。在相关问题的一系列论辩中,他系统梳理和评析了前世乐律经典学说,提出了“倍半之律则未尝无”“四清声不可废”“应钟之上非无清声,黄钟之下非无浊声”等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为我们澄清“中声说”“清浊四声说”以及旋宫历史上的诸多问题带来重要的启示。
一、“中声”
中声也称“中和之声”,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杜预注:……此谓先王之乐得中声,声成五降而息也,降,罢退。……;孔颖达正义:乐有五声之节,为声有迟有速,从本至末,缓急相及,使得中和之声。其曲既了,以此罢退。五声既成中和,罢退之后,谓为曲已了,不容更复弹作,以为烦手淫声,郑卫之曲也。”[2]《国语·周语下》亦云:“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3]132等。以上有关“中声”的出处及注疏、正义,大多将“中声”解为宫商角徴羽五声,并称之为“中和之声”——可以理解为“适中之声”和“有节制之声”,而中声以下则有失平和,有涉郑卫,不容再弹。
在古代乐律学中“定中声”是制律的起点。蔡元定《律吕新书·黄钟篇》云:“古者考声候气,皆以声之清浊、气之先后求黄钟也。夫律长则声浊而气先至,律短则声清而气后至,极长极短则不成声而气不应。今欲求声气之中,而莫适为准,莫若且多截竹以拟黄钟之管,或极其短,或极其长,长短之内,每差一分而为一管,皆即以其长权为九寸,而度围径如黄钟之法焉。更迭以吹,则中声可得;浅深以列,则中气可验。苟声和气应,则黄钟之为黄钟者信矣。”[4]朱熹曰:“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不得中声,终不是。大抵声太高则焦杀,低则盎缓。”又云:“音律如尖塔样,阔者浊声,尖者清声。宫以下则太浊,羽以上则太轻,皆不可为乐,惟五声者中声也”。[5]2336
从上述诸言可见,“中声”或为乐音音高标准的概念。“中声”与黄钟标准音高相须为命,而其中又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乐音音高上合适的起点(如正律黄钟);其二是指由黄钟起排列而成的音高合适的音阶或音列。就乐音所在的音域来说,“中声”的概念强调合宜而有节制,不能太高或太低。
此外,传统文献中还有将“中声”(中音)与“中德”——君王的平和中正之德相联系,如《国语·周语下》曰:“夫平和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以中德,咏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德。……”[3]130“中声”的概念又往往与天下太平之势相关联,如朱熹言及中声与乐德关系曰:“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唐太宗所定乐及本朝乐,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长”。[5]2336
二、朱载堉“中声之辩”
古代乐律学强调“求中声,须得律”[6]851。朱载堉在《律吕精义》内篇卷一中就辨析历代候气造律之失。如:“王莽伪作原非至善,而历代善之,以为定制,根本不正,其失一也;刘歆伪辞全无可取,而历代取之,以为定说,考据不明,其失二也;三分损益旧率疏舛,而历代守之,以为定法,算数不精,其失三也。”[6]1(以下简称“三失”)在《律吕精义》(外篇·卷二·“古今乐律杂说并附录”)中,他又提出宋代制律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李照、范镇之徒,惑于京房、刘歆之谬说,而不达淮南、太史公之妙论,……而致乐律之乖。”……“夫朴之乐,照已讥之矣,而照之乐不免于讥。何也?岂高者失之清,下者失之浊,皆非中正和平之乐欤?”[6]843。这里朱载堉指出,宋人乐律乖谬的原因,正是在于没能确定合适的中声之位。
接着,朱载堉引入俗乐确定音域之法,探求中声之道:“患在律学诸儒不知而作,非理变乱之耳。若夫俗乐则不然也。初无绳准之拘,由人取便,求其所安,使歌声虽高不至于气竭,虽低不至于声咽,自然而然,此正古人所谓中声者也。礼失求诸野,其斯之谓乎!儒者于乐则异于是。盖为律度所拘,不以人声为恤”。[6]844朱载堉此言字字珠玑,“既不惑于凤鸣幽怪之说,亦不流于候气狂诞之为”[6]862,主张“礼失求诸野”——以当时俗乐歌者自然形成的音域范围作为参照依据,揭示古乐定中声的自然之理,摒弃拘守律度,作茧自缚的做法。
朱载堉的“中声说”见于《律吕精义》(外篇·卷二·古今乐律杂说并附录)中,他引徐充言对张敔的“中声说”进行评析:“《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言因人声而制律也。先生(徐充指张敔)听察洞微,断以人之最低一声为黄钟,下更欲低无声也,高亦如之。故最低声者即黄钟之宫,最高者即应钟之变宫也。……窃尝献疑:南北之风气强弱不同,人恢眇肥瘠老幼,声无不同者,胡敢谓然。”[6]871
张敔认为:“人声最低声者即黄钟之宫,最高者即应钟之变宫”。这显然将中声范围限制在十二正律范围。对此朱载堉予以敏锐的批评:“人恢眇肥瘠老幼形形色色,声无不同者”,指出:“黄钟之下非无浊声,应钟之非无清声”;并以当时神乐观雅乐笙的实际音域作验证,如:“神乐观雅乐所吹笙,以合字为黄钟正律,合字之下有大凡为应钟倍律,大凡之下有大工为南吕倍律,大工之下有大尺为林钟倍律。以此证之,则知黄钟正律之下非无低声也。合字之上有四字为太簇正律,……小工之上有小凡为应钟正律,小凡之上有小六为黄钟半律,小六之上有小五为太簇半律。以此证之,则知应钟正律之上非无高声也,盖笙与律,其理无二,以证张敔之失,亦昭然矣。”[6]897在此,朱载堉以活生生的乐器实物作证据,证实张敔之谬,其实证精神显而易见。
不过,朱载堉汲取了张敔观点的合理成分,以“因人声而制律”的观点作为他的“中声说”的思维起点。此外,朱载堉还引张载言(《张子全书·卷五·礼乐》),论及“中声”与古乐教化功能的关系:“律吕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则入于噍杀,太下则入于啴缓。盖穷本知变,乐之情也。”[6]853这些都反映出他选择性地汲取前人有益之处的学术态度和作为。
接着朱载堉提出他的“中声说”:“夫何为中声耶?歌出自然,虽高而不至于揭不起,虽低而不至于咽不出,此所谓中声也。”[6]872朱载堉认为,“圣人之制作也,律以和歌声”。[6]861在他看来,“中声”是一个相对的音域范围,它应该符合人的嗓音的自然音域,其中的最高音其相对位置应该是:“歌出自然虽高而不至于揭不起”;它的最低音其相对位置应该是:“虽低而不至于咽不出”。这一学说,既迎合了先秦礼乐合德的思想,又将“定中声”引向合理可求的途径。
三、“四清声”之辩
朱载堉针对张敔的观点指出:“彼谓黄钟最低,其下更无低者,应钟最高,其上更无高者,不知律吕有倍半之理也。”[6]861从逻辑上看,若黄钟不为最低,应钟不为最高,这势必要牵涉到十二正律之外倍律、半律的运用而与旋宫相涉。
“半律”这一概念当指“清声”(正律的高八度音),在今天来看已没有什么疑义。可为何在朱载堉所处的时代还需要理论一番呢?这一话题由宋至明争议颇多,因为它涉及到礼乐所强调的伦理。
“半律”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叫作“子声”,如:“……又制十二钟准,为十二律之正声也。凫氏为钟,以律计自倍半。半者,准半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律,制为十二子声。比正声为倍,则以正声于子声为倍;以正声比子声,则子声为半。但先儒释用倍声,自有二义:一义云,半以十二正律,为十子声之钟;二义云,从于中宫之管寸数,以三分益一,上生黄钟,以所得管之寸数然半之,以为子声之钟。”又如:“其正管长者为均之时,则通自用正声五音;正管短者为均之时,则通用子声为五”[7]等。
“半律”在宋代多称作“清声”。《宋史·乐志》有关“四清声”的讨论,其焦点就是站在礼乐合德的立场上争辩雅乐编悬要不要采用“四清声”。陈旸等人反对采用清声,冯元等人主张采用“清声”。而二者都是在维护礼乐所强调的等级与伦理。
从传统礼乐的音高观念来说,乐声要中正平和而不宜过高,过高则失之轻佻。如《朱子语类》有云:“乐声不可太高……乐中上声,便是郑卫”。[5]2339又如《律吕精义》中所言:“数少管短,……有飞越轻佻之意焉;数多管长,有持重深沉之意焉。”[6]866等等。此外,礼乐强调“五音”的尊卑等级,如《史记·乐书》云:“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8]。宋人延续了这一传统,如:“声重浊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9]2950这就是所谓的“五音尊卑说”,它将五音次序与君、臣、民、事、物的等级对应起来,甚至将五音次序联系到血亲伦理与国家兴亡之上。
在五音的尊卑次序中宫商角(君臣民)三者是其核心,三者的尊卑次序(由低到高的排列)不可动摇。而徵羽二声代表“事”与“物”不具有伦理等级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沈括曾说:“其余徵、羽,自是事、物用变声,过于君声无嫌”[10],冯元也说:“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9]2950
正是由于受“五音尊卑说”的影响,反对采用清声的陈旸也好,主张采用“清声”的冯元也好,都将“五音尊卑说”视为圭臬,不敢越其雷池。但他们的作为却相反:陈旸主张去清声以避五音凌犯;而冯元等人则强调要用“四清声”,以确保十二律均回避五音之凌犯。 那么冯元为何限定清声只用四个呢?这当然与“五音尊卑说”有关。具体地说来,在六十调的黄钟至林钟的八个宫调中,它们的宫商角的次序是由浊至清排列,符合尊卑之义。而从夷则至应钟的四个宫调中,它们的宫商角的排列则出现商浊于宫或角浊于宫,而有失尊卑。不过只要在应钟之上加(黄、大、太、夹)清声,就能保证夷则至应钟四宫中宫商角的尊卑次序。这就是冯元等人主张只用四个清声的道理。正如《宋史》中所云:“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9]2950
对于宋人有关编悬四清声的争议,朱载堉鲜明地提出:“四清声不可废”。从表面上看,他与冯元等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其实不然。朱载堉更偏重对旋宫乐学规律的揭示。这在他对“五音尊卑”问题的有关论述中可见一斑。
《律吕精义·外篇》卷三,“辨李文察、刘濂之失第三”曰:“旋宫者,每篇各为一宫,非每句各为一宫也。文察不晓此理,其所撰谱每句各为一宫,遂致宫商角徵羽五音者皆错乱,正古人所谓‘迭相陵’者也。……乐记曰:‘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此之谓也。或曰:‘信如乐记之说,果有吉凶之感应乎?’曰:‘不然也。’何瑭尝辨之曰:‘若此者,以其象言之耳。盖乐之有宫商角徴羽,犹国之有君臣民事物。非谓君臣民事物之失道,真由于宫商角徴羽之乱也。’曰:‘然则何以为声音之道与政通?’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者此也,非宫商角徴羽之谓也。’”[6]904
朱载堉借何瑭之说,道出了先秦“五音尊卑说”的本质。他认为,《乐记》中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之说,仅仅是将音乐与政治比拟的一种说法,实际上君臣民事物之失道并非是由宫商角徴羽之乱而引起。这不过是在强调:宫商角徴羽乱则不可以为荣,犹君臣民事物乱则不可以为国。所以朱载堉说:“(二者)其道相似,故以为比”。显然朱载堉对《乐记》中“五音尊卑说”的看法,远远比宋人的观点要放达而深刻。
由此可知,朱载堉与冯元均主张采用“清声”,但二者的思想不尽相同。冯元主张编悬设四清声,是为保证旋宫之中宫商角的尊卑次序合于古典的传统;而朱载堉提出“四清声不可废”,虽然也与传统的五音尊卑说吻合,但是它的重点却关注着旋宫理论的自洽以及乐律学的系统性。
四、朱载堉“四浊声”之说
“四浊声”的提出与“四清声”一样,是前文中朱载堉“应钟之上非无清声,黄钟之下非无浊声”之观点的延续。在朱载堉之前,宋人只提旋宫之中的四清声,还未见有人提到四浊声。即使更早的杜佑《通典》也仅仅是提到十二正声与十二子声。在朱载堉看来,旋宫所用音域由“中声”十二正律向两端拓展,不仅会有清声还应有浊声,他还进一步提出“清声、浊声各止于四”。前文宋人已提及“四清声”及其“臣民相避以为尊卑”的道理,那么朱载堉是否因袭宋人的“四清”,而对应提出“四浊”呢?以下我们来看看他提出的清、浊四声的依据。《律吕精义》云:
尝以人声验之,十二正律由浊而清,黄大太夹姑仲蕤林夷南无应,皆自然也。继以半律黄大太夹,虽清可歌。至于姑仲,则声益高而揭不起,或强揭起,非自然矣。十二正律由清而浊,应无南夷林蕤仲姑夹太大黄,皆自然也。继以倍律应无南夷,虽浊可歌。至于林蕤,则声益低而咽不出,或强歌出,非自然也。中声止于十二,非难知之事,不待知音者,众庶可知也。[6]872
由上文可见,对于清声为四的原因,他指出清声黄、大、太、夹四律,虽清可歌。如果音域再往上至姑、仲,声过高而难以唱出或勉强唱出,声音就不自然甚至不可歌,所以清声止用四律,显然这相比宋代冯元“四清声说”多出了科学验证的手段;对于浊声,他指出浊声应、无、南、夷四律,虽浊可歌。如果音域再往下至林、蕤,则声音过低而难以唱出或勉强唱出,声音就不自然,所以浊声止用四律。总之,这是依据歌者自然音域与非自然音域的界限来酌情考虑清声和浊声数量的。
上段引文中“中声止于十二”一语,可以看作是朱载堉对中声的相对概念的说明。如果联系他在前文所述的相关内容,我们可知他所谓“中声”,有两层意思。其一,古来十二正律即为中声的相对范围;其二,中声存在于人声的自然音域中。
尽管朱载堉的上述认识有他主观经验的成分,但也不失为对前人“律以和歌声”“言因人声而制律”的一个合理的诠释。而更可贵的是,接下来朱载堉以太常的四首乐谱为例子,来验证他的清声与浊声之说,同时批评张敔之失。现列举其中一首乐谱阐明其意(见表一)。[6]873-882

表一.明代太常乐谱之三
朱载堉对乐谱(太常乐谱之三)的用声进行了统计:“右谱八句,共计32字。其间用中声之宫者10字,用中声之商者8字,用中声之角者4字,用中声之徵者3字,用清声之徵2字,用中声之羽者5字。”他特别对乐谱所用宫、徵、羽乐音处加文字说明,验证“徵羽与宫商角无所陵犯”(见上引沈括之言)。此外,在这首乐谱所用的“六”字(黄钟清声)处,朱载堉也特意标注了文字:“清声之徵,声高于宫”;在其他两首太常乐谱所用“低工”字(倍南吕)处他也特意标注了文字:“浊声之羽,声低于宫”,用以证张敔之失,强调“应钟之上非无清声,黄钟之下非无浊声”。 朱载堉云:“宫清而徵羽浊,实理之自然也。间或用清亦无不可,泥于用清以避陵犯,不亦谬乎?”[6]883从学术研究的价值来看,朱载堉是在用一个活的证据来验证前人观点的是非曲直。
从这段太常乐谱(太常乐谱之三)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八句乐谱中宫商角自始至终采用正律中声,其中宫用字为“上”、用律为“仲吕”;商宫用字为“尺”、用律为“林钟”;角用字为“工”、用律为“南吕”。宫商角这样排列完全符合传统的“五音尊卑说”。 类似的这样的乐谱在《律吕精义》外篇卷之二中一共列出四个谱例。在其他三首太常乐谱中,除了个别处采用了他清声说可以容许的“六字”(黄钟清宫)之外,乐谱其他宫商角音的谱字,均是由低至高的排列,与“五音尊卑说”相吻合。所以朱载堉在这首乐谱注解的最后说:“以今审之,未见其所谓陵犯也。”[6]881
基于上述的论证,朱载堉系统阐述了旋宫之中“清、浊四声说”, 提出相关的一系列观点,如“倍半之律则未尝无”“四清声不可废”“应钟之上非无清声,黄钟之下非无浊声”等。
此外,从上文中我们可以见到,朱载堉认为五音之中宫商角与君臣民的联系,不过是“其道相似,故以为比”而已。这一点反映出他卓尔不群的洞察力。但是,当我们通观他的“清浊四声说”便不难发现,他所提出的清、浊各四声,无论是四清声也好,还是四浊声也好,都与传统的五音尊卑说不相忤逆。他在论辩中也较多引用五音尊卑之说,这也许是时代带给学者的局限性所致。这里我们不妨按照从古至今旋宫止于十二宫的原则,将他的四清声、四浊声分别列为“十二律四清声五音旋宫表”和“十二律四浊声五音旋宫表”,从中观察其结果。(见表二、表三)

表二.十二律四清声五音旋宫表

表三.十二律四浊声五音旋宫表
以上的表二、表三涉及编悬中宫商角的次序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在“十二律四清声”和“十二律四浊声”编悬设置中,由于加了四浊声与四清声便可确保宫商角的尊卑次序。清声与浊声各止于四,倘若清声或浊声如果多用一个,就会出现某一律上的重复旋宫。因此,我们可以说,五音尊卑说在乐学逻辑上对清声与浊声的数量造成一种制约,而必然导致清声或浊声各止于四的结果。
朱载堉在上述论辩之后,又列举前世文献历数了隋以来旋宫理论所经历的曲折的史实,以明辨其是非曲直。其具体陈述的大意为:隋何妥耻己不逮译等,巧言取悦高帝,但作黄钟一宫,五钟哑钟设而不击,遂使古乐尽废;唐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安史之乱至黄巢之余,工器俱尽,文记亦忘;逮乎伪梁后唐,编钟编磬徒悬而已。北宋宫廷面临五代之后乐之缺坏,八十四调泯灭之实,阮逸为穷以律吕旋宫之法推出所谓“编钟四清声谱法”,于是“四清声”之争激起轩然大波……。[6]930-939
朱载堉通过对旋宫历史评析,既为其“清、浊四声说”扫清了障碍,也给我们正确认识旋宫史实带来重要的启示。
实际上,宋人提出的“四清声说”,其本质是在调和先秦“五音尊卑说”与十二律旋宫的矛盾。当编悬限用十二正律,旋宫于夷则至应钟四律上必然实现宫商角(君臣民)凌犯,故无法穷尽十二律旋宫之法。而云:“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宋人的“四清声”虽说是权宜之计。但客观地来说,这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穷尽十二律旋宫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如果说宋人“四清声之设”算是打破唯奏黄钟一宫之僵局的一次解围,那么祖孝孙、张文收恢复八十四调、王朴“十二变而复黄钟”则是度越诸家,着实解决旋宫问题的伟大作为。而直到朱载堉,当他提出“中声说”“清浊四声说”以及“新法密率”诞生之后,宋人所面临的“五音尊卑说”与十二律旋宫的矛盾自然不复存在,使旋宫理论从旧说的束缚中真正解放出来。
然而,通观朱载堉的“中声说”“清浊四声说”便不难发现,他虽然崇古,但不盲从。他虽以“五音尊卑”评析诸说,但不落宋人的俗套。他将“以人声定律”的观点贯穿其论辩之中,系统地阐述其“中声”与“清、浊四声”学说,并以见存太常乐谱加以验证,从而提出“倍半之律则未尝无”“四清声不可废”“应钟之上非无清声,黄钟之下非无浊声”等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从其思维逻辑线索来看,他重视对前人学说的检验,善于提取前世经典的合理成分,而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侧重对音乐自身规律的把握。这一切均显示出其研究的合理与严谨,这是当年宋儒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远不能及的。
——以哔哩哔哩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