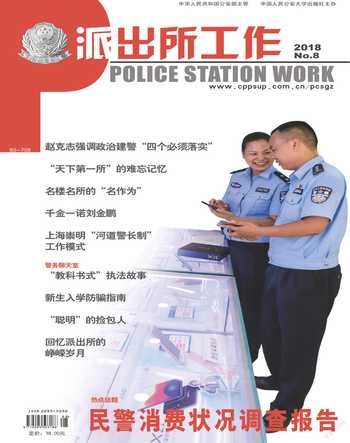回忆派出所的峥嵘岁月
周维秀
1949年8月,经惜阴中学学生会介绍,我成了北京外五公安分局的一名民警。经过一个月的军训,9月中旬分到城隍庙派出所工作。那时派出所大多数都是在庙里。城隍庙位于今天的西城区南横街东口路北,建于元朝初年,称为“佑圣王灵应庙”。庙东院为东岳庙、庙西院为三官庙。派出所占用城隍庙和三官庙,东岳庙为城隍庙小学所用(前几年该庙已拆除)。
派出所是保一方平安的中坚力量
当时,庙南有一片荒凉地带叫南下洼子,我曾是这里的管片民警。旧社会很多天桥艺人、妓女死后都埋葬在这里,被称为乱葬岗子。南下洼子原本是一大片浅水塘,在芦苇地中间有块高出地面的土坡平台,元朝在此修建慈悲庵,名“招提胜境”。后来清朝工部郎中江藻在此建亭,作为临时办公、休息、接待亲友来访之用,并取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诗意,为亭题额曰“陶然”。这就是今陶然亭公园命名的由来。
这里在当时也是社会治安混乱,偷盗、抢劫、凶杀时有发生的地段。在离派出所三百多米的南华东街北口,一伙劫匪曾因分赃不均发生火并,致枪杀一人;在南横街涵洞内,被污水冲出一具无名男尸;黑窑厂尼姑庵厕所内发现弃婴,经查系一尼姑与看门人所生;女民警蔡淑琴(时年15岁)与一老民警夜晚巡逻时,在铜法寺街口听到一声枪响,经观察未发现异常,回派出所后,发现棉大衣下摆处有一个被烧焦了的洞,经判断是子弹穿过的痕迹;还有一次,蔡淑琴与老民警夜间巡逻走到太平街北口,发现在墙边有个麻袋包,不知装有何物,打开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一具男尸,赶紧报分局治安科处理。
当时,所有民警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夜间巡逻时,都是子弹上膛。当时派出所的枪支都是接收过来的,牌子杂而且破旧,除所长配有手枪外,民警都持大枪。其中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兵使用的“老套筒”,枪身很长,没有刺刀,比我都高。据留用警讲:这种枪筒连来复线都没有了,子弹出膛不是旋转直射,而是“横”着拽出去,所以没有人愿意使用。日本造三八大盖带刺刀是性能较好的枪支,射程远,力量大,但枪身长,不适合城市使用。最受欢迎的是“马三八”,就是日本造的骑兵用枪,枪身较短,可以上刺刀,轻便实用,但只有两支,是巡逻时大家的首选用枪。再一种是湖北汉阳造“兰牌”步枪,是仿“马三八”造的,虽然性能外观不及日本造,但也适用。
那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从所长到民警去分局、市局开会都是步行。当时开展灭鼠运动,居民打死老鼠将尾巴剪下交派出所,由派出所集中送到区政府民政科,以尾巴数量的多少计算灭鼠战绩。民警每天要往返两个多小时。到天坛、先农坛、天桥刑場出勤也都是徒步而行。当时对走路,大家都习以为常。
工作时间实行的是6天工作制,每周只轮休24小时,即当天晚6点走,第二天晚6点归队,其余6天工作是“连轴转”,24小时“打铁”。工作不分昼夜,白天下片儿,晚上6点到次日早6点轮流巡逻,共分4班,每班2人,其中最舒服的是6~9点的巡逻,这班下岗后可睡一个“整觉”。最难熬的是12~3点的第3班,两头儿都睡不好觉,白天照常工作不能休息。那时就是“缺觉”。有一位新警在户籍办公室值“瞪眼”夜班(即不能睡觉)。一天夜晚,外地公安机关送来一名被抓在逃人员交派出所寄押一夜。为了防止在逃人员逃跑,新警将其双手捆住坐在地上,被捆双手再系一根绳子,他坐在办公桌后边的椅子上用手拉着绳子。结果由于夜间事不多,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人还是跑了。好在留用警比较有经验,认为派出所离广安门最近,在逃人员可能出此门逃跑。经与广安门检查站联系,在天亮后该人被抓到。
派出所虽然工时长,又“苦”又“累”,但也没有夜餐加班费之说,而且民警的工资待遇也是低水平的。有的民警是包干制,每月按130斤小米价发工资。因此,民警的生活都是很清贫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伙食标准,每人每月只交几元钱的伙食费,天天窝头咸菜(有时放点葱丝、香油),吃一次肉末氽白菜浇面、炸酱面、炸油饼就是改善生活了。管界有个治安积极分子,是个小手工业者,看到派出所伙食“太素”,便将收购来的鲜牛皮上的肉刮下(人称刮皮肉),主动送给派出所一小盆。这是我在派出所工作的半年内吃过的唯一一次“炖肉”。
当时民警都住在一个大屋子里,既住宿又办公,除每人一张床板外,没有办公桌,整理资料就趴在床铺上。冬天因经费不足,基本上不生火,如到三九寒天太冷时,民警就在巡逻前,将一块整砖放在伙房的炉灶台上,下班后,用布将热砖包上放在被窝里取暖。
当时警服只发冬、夏服装各一套,棉服由十一穿到来年五一,夏服由五一又穿到十一。由于棉衣棉裤是“死里死面”不能拆洗,一冬下来满身污垢,到了开春儿“味”不可闻。而且制式还不统一,留用警照穿国民党警察制服,分局干部、新警穿库存旧警服过渡,市局干部着军服。当时全市清洁工人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由国民党警察局管,新中国成立之初也全部着警服。棉大衣的颜色都不一样,有的穿旧警黑大衣,有的穿国民党军队灰色、绿色大衣,有的穿日本的黄色皮大衣。服装只有大、中、小三种号,很不合体。鞋子都是自备的,有布鞋、皮鞋、大头鞋、胶鞋,各色各样,给人一种“邋遢”警察、“杂牌”军的感觉。
那时警察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都比较低,除个别警察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外,其余警察只有小学水平,所以汇报工作多是口头的,写不出像样的材料,要由内勤整理。有一次,一位民警值夜班时接到了电传,误将“劫匪手持类似手枪”,记录为“劫匪手持4支手枪”,并电传到其他派出所,造成了误传。
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并未感到苦与累,认为能参加革命工作有一种光荣感和满足感,所以学习思想工作是积极向上的。派出所的磨炼,使我终生难忘。
参与开国大典保卫无上光荣
9月30日,所长召开全体民警会议,布置开国大典保卫工作,主要任务是社会面的控制。街巷、地段、路口都落实到人负责巡逻。散会后,我被所长留下来。他告诉我,这一天要在所里执行一项重要任务,让我把管界内的30多名管控人员找到派出所来,让他们一整天都在我的“眼皮底下”。
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伪政府科长、伪军连长、伪警巡官、军中统特务、宪兵、王凤岗残部班长以上人员都属管制人员。我负责看管的這些人当中,官阶最大的是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分局局长梁卓(当时是给评剧名角喜彩莲在华北戏剧院操琴)。
30多个人一早就来到派出所,我安排他们在一个房间里。他们有的坐在地上,有的坐在铺板上,有的坐在砖块上。他们都比我年龄大,有的甚至比我父亲的年龄都大。我给他们念文件,让他们分别写体会,他们都认真听从。中午,我让他们回家吃饭,要求一个小时后必须回到派出所。为了不让他们脱离我的视线,我一步不敢离开办公室。直到晚上焰火放完了,参加开国大典安保的战友们回到所里,我才让他们回家。听着战友们兴奋地讲述在街面上的见闻,我的心情一样激动。十六岁的我,知道自己为国家做了件“大事”,感到无上光荣。
反旧警察作风,一生铭记在心
1950年2月,单位送我到公安学校学习,学员大多数是新参加工作的民警。公安学校毕业后,我又回到了外五分局城隍庙派出所工作。这时,所里除了所长、干事三人是老区来的干部和搞地工的同志外,只有两名新民警,其余十几个人都是留用警。
通过学习,我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新、旧警察的是非标准和界限,增强了我识别和抵制旧警察作风的能力。在生活和工作中,留用警身上确实反映出了严重的旧警作风,如夜里巡逻时,有的留用警走到黑暗处或墙角拐弯时,先大声说话或咳嗽两声,用意是把坏人吓跑;有的下管片工作时路经摊贩处,在这个摊拿一把瓜子、抓一把花生米,到那个摊要两支香烟或几块糖;搜集社情时,不是反映社会各界的真实想法,而是自己编造几条上报,弄虚作假等。留用警中在思想作风上和工作作风上严重存在的“奸、懒、油、滑、坏、吃、赊、偷、拿、要”旧警察作风,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向新民警渗透着。这些不良作风不仅影响了人民警察队伍的肌体,也严重地损坏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鉴于这一现状,市公安局采取了果断措施,在1951年12月决定,根据中央开展“三反”运动的部署,于运动的第三阶段,即从1952年2月14日至3月11日进行了反旧警察作风专项运动。现在看来,65年前的这场反旧警察作风运动,为公安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今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是党和政府的一支可信赖的队伍。
当时的外五公安分局城隍庙派出所,现在叫作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陶然亭派出所。
(作者系北京市公安局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