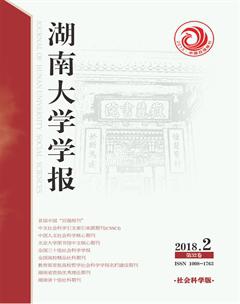王闿运“礼学经世”思想析略
刘焱
[摘要]王闿运是近代湖湘礼学大师。他受湖湘经世学风熏染,抱持“通经致用”的学术理念,力主从古代经典中寻求拨乱致治之道,提出“礼治”本于“自治”的礼学经世论,并以“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措施,将其治经理念落到实处。
[关键词]王闿运;礼学;通经致用;湖湘经学
王闿运(闿832-闿9闿6)早年嗜好词章,后来结识善化彭嘉玉,始有治礼之志,由此走上经学之路。他主张通经应当致用,坚持治经必先研礼,并在书院教学和日常生活中贯而行之,以合乎时宜、兼具个性的方式,将“礼学经世”思想贯彻到实践中,成为近代湖湘礼学大师。
一“于经书中寻求治理”
身处乱世的王闿运,因受湖湘经世学风的影响,青年时期就有经世大志。后来他潜心治经,更是明确提出了“通经致用”的主张,希冀从圣贤经典中寻求到拨乱反正的大道,正如他在光绪六年七月廿七日的日记中所说:“年近五旬,当去世俗之见,莫若于经书中寻求治理,此金石之言。”
王闿运始终认为:“圣学所传,唯期致用。”他提出经典蕴含着圣贤的治世之道,后学必须将先圣的治世之道贯彻到社会现实中,才算真正实现了“通经致用”。他在《论学须论事》中提出:“论学只须论事,事乃见学也。通经不致用,孔子谓之小人儒。”在《论通经即以治事》中,他又批评说:“湖州分经义、治事为两斋,不知其经是何义,事又何事。经者常法,万物所不能违。后世事皆例条,知之无用。”王闿运力主“为学但当治经”,“学能通经,自知文体”,认为论学与论事相辅而成,既要从论学中寻绎处事之道,又要从论事中归纳为学之方。由此,他特别指出行的重要性,强调学行不能相离,应当统一起来,知行并进,才能达到“通经致用”的效果。王闿运大谈经义、治事之法,是要说明“通经”和“致用”是一体两面,经是常法,是指导致用的原则,依经才能自立。他曾说:
齐桓公读书,而轮扁笑;使吾读书,则轮扁服矣。心无所得,而诵圣人之经典,非独人笑,亦将自笑。非独笑书,亦且笑圣人之愚人也。今之学者皆齐桓矣。晨读书,而午接人则忘其书;幼治经,而壮服官则悖其经。经言君子不谋食,而经生之谋食急;书言国不患贫,而书生之患贫甚。糟粕之不存,而何论菁华。故曰:多亦奚为?又曰:不思则罔。是古今之通病也。
“齐桓公读书而轮扁笑”,是《庄子·天道》篇记载的一则故事。王闿运引以发论,指出读圣人经典的要义在于心有所得。圣人经典的精神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认识事物、处理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方法,能够满足人们实际生活当中的现实需要。那些代代相传的精神理念和原则、方法,需要通过人的实践、施行才能落到实处。针对当时空泛的学风,王闿运尖锐地指出“行与学分,由士君子不能辨学故也”,批评读书人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强调要从“学”字人手下功夫,读懂圣贤经典,将经典蕴含的先进理念内化为自身的精神信念,并在应对各种现实问题时加以运用,真正做到“通经致用”。
其实嘉道以来,“通经致用”的学风一直盛行,不过晚清经世学派都把目光集中向外,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王闺运则迥然有异,坚信经学可以通变济世,振衰起弊,并倡导“经学以自治”之说,认为读经明理之士,务必遵循“先自治,后治人”,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此维系社会秩序,扭转民风,挽救颓世。他秉持向经典求治道的内修理念,提出“志则《春秋》,行则《周官》”。所谓“志则《春秋》”,即他立志从经典中寻求治道,“拨乱世,反之正”;而“行则《周官》”,则是他“以礼治世”理念的集中体现。
《周礼》一直被尊为“周公致太平之道”,将其精神落到现实层面,即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建构行政体系,使整个国家管理从上到下处于有序的运行之中,每一个层面的管理者和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各司其职、各得其位。《周礼》设计的制度结构,目的在厚民生、正民德、齐人心。经典的意義在于给现实社会的制度建构提供价值资源,为人们切人现实提供更多的选择。《周礼》正是这样一部经典。时代在前进,礼制有因革,面对这样一部看起来繁密的经典,人们关注的重点应集中于它的制度价值。所以王闿运大讲《周官》为典制之本原,十分推崇它的制度精神和行政理念,其着意之处乃在“礼”的规范作用,这正契合《礼记·郊特牲》所说“礼之所尊,尊其义也”。
二“礼治”本于“自治”
关于“礼治”的内涵,有学者概括说:“所谓‘礼治,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礼制‘礼仪‘礼器等内容和手段,来维护和协调人伦、等级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稳定和统治的牢固。”但落到具体层面,“礼治”要如何实施?历来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与方案。王闿运坚信“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提出要以礼修身,以礼齐家,进而以礼治国。至于“礼治”的根本,他特别定位于“自治”。
王闿运在笺释群经时,始终强调“自治”之说,标榜“君子但自治”,认为“自治不暇,未能及世事也”,无论君卿、士庶,都应把“自治”视作修己安人、经邦济世的根基。例如,对《春秋》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何休及后来的公羊学家纷纷借此立说,畅发“大一统”“通三统”“五始”等思想,王闿运的补笺却说:“书春三月皆有王,存三统也。不先自正,则不足治人,故以王正月见一统之义,而三统乃存矣。”显然是借何休“三统”之说,阐发他的“自治”之义。因为依据礼法,鲁国本应由嫡子桓公继位,但为了保证国家安定,年长且贤德的隐公被拥立为君。对此,《春秋》经文有“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等记载,王闿运认为这是孔子借着鲁隐公的贤德,强调凡事须“先自正”,国君要从正身力行开始,而后才可以治人。又如《春秋》鲁隐公二年“纪履输来逆女”,王闿运也是承继《公羊传》及何休《公羊解诂》的说法,阐释他的“自治”理念:
传: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防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
解诂:《春秋》正夫妇之始也。夫妇正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和,君臣和则天下治。故夫妇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内逆女常书,外逆女但疾始、不常书者,明当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故略外也。
笺:将以礼治人,不可苟从也。凡不亲迎之起,起于亲迎而女不至,女父母背言也。有背言者,虽有信,人不之信矣。不亲迎,则有卫宣、鲁僖之祸,宜先自治以治人,唯《春秋》谨之焉。
依据礼制,举行婚礼时,应当由新郎亲赴女家迎娶新娘,即“亲迎”,即使国君也不能例外,可是纪国国君居然派出大夫代己亲迎,有违礼制。按照《春秋》的书写常规,一般“外逆女不书”,这里却打破常规,特加记载,《公羊传》认为这是“讥始不亲迎”,历来学者也多就此立说,以为是讥讽纪国国君不亲迎的非礼行为,很少察及传文“托始”二字之义。何休则根据《春秋》“详内略外”之法,引申出“明当先自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新义,王闺运受到启发,进一步标出“宜先自治以治人”之义,提出孔子此一特笔“非以讥纪也”,而是借纪国君臣违礼之事,强调“将以礼治人,不可苟从也”,认为在上位者不得有苟从行为,才能感化民众,移易风俗,达到以礼治国安民的目标。这样一来,《春秋》的“谨始”笔法、《公羊传》的“托始”大义,就被王闿运巧妙地落实在礼治的层面,变成“先自治以治人”,经典因此而焕发出新义。
王闿运笺释《礼记》时,也反复论述“自治”之说。如《表记》“子曰:‘祭极敬,不继之以乐。朝极辨,不继之以倦。”一句,他笺释说:“宾礼则继以乐,闲居讲论,欠伸视日,可继以倦也。引朝仪以喻君子自治之不可倦,虽燕居,若朝廷也。”他强调君子即便闲居在家,也要像在朝为官任事那样全力以赴,自治不怠,严于律己。又如“仁者,天下之表也”一语,他注解说:“表所以取正者。凡君子所以自治者,以为天下,非为自表犦。”他力主君子自治的要义,在立志以仁义为标准,为天下做表率,而不止于独善其身,仅仅成就一己之名。在《论语训·先进》篇中,他还引出一个君子处身乱世应当“以自治为贵”的话题:
子曰:“从我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训曰:门以喻道也。言游宦徒劳,教授有益也。从者,子路、子贡、颜渊皆异才,尔时犹未及门,在陈思归,裁其成章,乃皆升堂入室。若终身求仕,不暇讲论,故乱世以自治为贵矣。
朱熹将“门”作本义解,王闺运却说“门以喻道”,取譬似乎更高。他认为子路、子贡、颜渊皆属俊材秀逸一类,只不过闻道有先后,在跟孔子从游间学时,尚未真正领会老师的深邃思想,直到后来困厄于陈、蔡之问,没有入仕的机会,才转而专心向学,着力于领悟孔子大道。人如果终身汲汲于求仕人进,则学业荒废,涵养难进。而生逢乱世,君子须从自治下功夫,以能自治为贵,所以应致力于那些所当为之事,且保证自己的所作所为能问心无愧。
与笺注经典强调“自治”相呼应,王闿运在答弟子问及与友人书札中,也反复强调这一点。例如他答李砥卿问治道,即认为治世之道备载六经,治乡须密,治国须疏,诚如老子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然而治世之道的要点,则在“文质相救,各因其世,要在先自治而已”。又如在答吕雪棠问时,他提出:身处乱世,圣道消沉,个人安身“唯宜自治”;至于治世之要,贵通物情,而“欲得物情,但须自治”。再如他在致张百熙信中,指出治世用才与向学悟道的关键,是要能各安其分、各行其是,“道在自治,安分守己而已”。可见,王闿运已将个人对经典的新解,随时施诸日用教化之中。
三“礼学经世”实践
《白虎通》称:“礼乐者,何谓也?礼之为言履也,可践履而行。”《说文解字》更直接说:“礼,履也。”礼贵践履,礼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社会实践性。因此,重礼关键在于践行,即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遵循各种行为规范,举办各种典礼仪式。王闺运在治经、教学和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视礼的研究、教育和实践,同时对关乎日用伦常的礼俗也十分留意,真正将礼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王闿运一生有三十多年是在书院教学中度过。他在书院教学授徒时,非常重视对院生进行礼的教育,注重开展礼的实践。书院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与书院有关的各种典礼仪式,既能使书院师生们在一种神圣、庄严的气氛中,学会敬畏、尊重,又能强化师生对书院、先贤、国家的归属感、认同感。王闿运从光绪四年至光绪十二年执掌成都尊经书院,就大力推行以礼治院。他进院掌教后,发现院中诸多积弊,如书籍无人经理,甚至不少院生吸食鸦片,因此力行改革,重新制定规章,重视礼仪教育,尤其注重礼仪实践。尊经书院的诸多礼仪活动,正是王闺运“读礼、析礼、明礼、践礼”的具体实施,也是他“通经当求致用”理念的现实回应。《湘绮楼日记》中随时可见这些活动。如光绪六年八月的日记就有以下记载:
九日:夜删定《乡饮酒礼》,似尚可行。
十日:与诸生演释奠礼及饮酒礼,凡二次,手脚生疏。……薄暮复演,稍已成章。
十一日:寅起,俟明行释奠礼,辰正观祠,吴、张、薛监院行礼。午后再演乡饮礼。
十二日:日中行乡饮酒礼,诸生至者四十余人,齐之以礼,甚为整肃。请松翁为馔者。升坐、无算爵后,张生孝楷、杨生炳烈忽酒狂骂坐,一堂愕眙。牌示斥之:“本日试行乡饮酒礼,华阳廪生张、秀山附生杨,傲恨不恭,敢于犯纪。本应除名褫革,念大学有三移之义,且系试行,姑降为附课,并罚月费奖银一月,即日移出书院,俟改过后再议。”
十三日:晨作教示诸生:“昨因释奠,试行乡礼,諸生济济翼翼,几复古矣。乃羞爵之后,司正、纠仪举罚失中,致有张、杨两生肆其狂惑,余甚愧焉。讲学期年而气质仍蔽,教之不行也,教者之过也。然纠仪急欲整齐,司正畏懦不直,毗刚毗柔,亦各有咎。昨所以不言者,以迹而论,两人无失,又初试行礼,未宾贤能,以儿子代丰颇习仪节,王生树滋愿司纠察,亦非谓选求,默而使之也。然人不相知,己不度听,余焉敢自恕乎?诸生之过,皆余过也。今辄自罚十金,助酒脯之费,并请监院抄牌呈遵者,以谢不虔。诸生无亦思为今人之易而学古人之难,各攻所短,匡余不逮。”
释奠礼是古代学校的祭祀典礼,规格最高,又可视作入学仪式,其要在礼敬先师,彰显对文教传统的承继与发扬。乡饮酒礼属乡党兴贤典礼,也可理解为乡人聚会宴饮的礼仪,意在明长幼之序。王闺运在书院推行此礼,想要教导、感化诸生有所取法、知所遵循。因此在正式行礼前,他郑重其事,将礼典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确定典礼仪节,然后与院生一起反复演练。不料行礼当天仍然出现意外,张、杨两生因醉酒而发狂骂坐。王闿运当即对这种违礼之举进行惩罚,第二天又郑重发布教示,反躬自省,教院生们引以为戒。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熏陶,尊经书院的院风得以扭转,这在同年十二月和次年正月举行的释奠礼就可以看出。《湘绮楼日记》所载如下:
光绪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大昕,与监院、诸生释奠。朝食后,于讲堂行燕礼,未正乃罢。筋力已觉不支,幸馔羞未备,得少息耳。穆、孙、刘三宾来观礼,入谈。已,复集堂上会食,礼成,颇有整肃之观。
光绪七年正月十五日:晨雨作,旋止。释奠时,班甚整肃。礼毕后,以羊豕祠三君,监院行礼,待人,至辰正方至。祠已,出堂点名,诸生威仪济济,殊征为学之效,余心甚喜。以系半月,仍试词章。院生共四十五人,院外生五人,会食毕,各散。张生祥龄与杨生锐不和者四年,似是不解之怨,今日置酒修好,尤为大喜,赐风鸭一头奖之,唯张、杨不至为歉耳。
这两次典礼,院生呈现出整齐严肃的精神面貌,特别是结怨数年的张祥龄、杨锐和好如初,较之此前大有变化,可见王闺运在尊经书院推行的礼学教育和礼学实践,已经使院生达到了检束身心、变化气质的目的。
在日常生活中,王闺运也非常重视礼的践行,并在用古礼于今之时,对礼俗作了合乎事宜的吸纳。例如光绪二年他的儿子王代功成婚,就依照《仪礼·士昏礼》的仪节,并结合了长沙的习俗。《湘绮楼日记》有以下记载:
十一月十五日:为功儿纳征黄氏女,媒不至,请孙涵若往。纳币首饰二合,衣裙四袭,羊豕鸡鸭鱼各二,礼饼二百,茶瓶一百,盐一瓶,酒二瓮,雁一,加以燭爆花红拜书册封,从长沙俗也。午后会燕,陪客陈芳畹、陈鲁瞻、彭辛叟、王伯戎,戌散。
十二月丁亥朔:黄氏送嫁奁,来者四十人,请陈鲁瞻及十子管帐,彭郎、左生司书帖。
十二月二日:乡俗通用翠冠绣衣,人家或有,不胜其借,皆旧不堪着,妇女必欲得此以成正配,舍新取故,不可理喻。明日新妇上头,当送冠衣,借于庄、黄,皆黯淡不可用,更赁之店肆,竟日遣人奔走,亦甚可笑也。
十二月四日:择辰时亲迎,媒人迟至,发轿已将巳初矣。外舅、文心、心盒、子筠、芳畹均来会,彭、左、陈、夏诸郎相礼,午后奠菜三庙,遂见宾亲,女宾张、黄、陈、彭、杨诸嫂,设三筵,合卺具特豚,女母来送,戌去,子初客散。
重视礼仪的运用,使子女们在潜移默化中明礼达事,也是王闿运家庭生活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对家中祭祀的重视,即是显著的事例。《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各种祭祀活动的意义,在于借助祭器、祭品、服饰等有形的载体和时空、仪节等无形的方式,表达人们敬天畏祖、事神致福的心理诉求。王闿运每逢先祖、亲人忌日,总是“心怵而奉之以礼”,只吃素食,设奠祭祀,并不厌其烦地记在日记中,除表达慎终追远、敬念亡亲之思,也是想借这种方式教育子女,使他们明白追养继孝之道,体悟贤良有能之德,可谓育子有方、身教先行。除了各种常规祭祀活动,王闺运还拟有四时家祭仪节,每年依礼举行。如《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十月三日记载:“今年始考礼,定四时祭,春、夏用孟月丁,秋仍用孟月十三日,冬孟三月上巳。今日烝祭,久雨忽晴,吉祥止止,坐待羹旺,巳初行事。”王闿运沿袭古礼,不废旧俗,在家中时常举行各种祭祀,就是要让家人在参与祭祀活动的过程中熟知礼仪、心存敬畏,维系家庭人伦秩序,建设良好家风,由此化民成俗,安定乡邦社会。
四结语
王闿运一生治礼不懈,非常注重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经世,这在他平日的学术研究、教学论政和日常生活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尽管他对宋儒的经说大为排斥,但对身心修养的追求却丝毫不减宋儒,对“通经致用”的主张,也有踵继汉儒建功立言之志。他研究礼学,大倡礼治,就是要以儒家经典作为文本依据与思想资源,寻求能适应现实政治需要的经世之术、经济之学,从而实现学术与政治的贯通融合,达到通经致用的现实目的。王闺运研究三《礼》的学术成就,和他推行礼治的社会影响,都值得后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