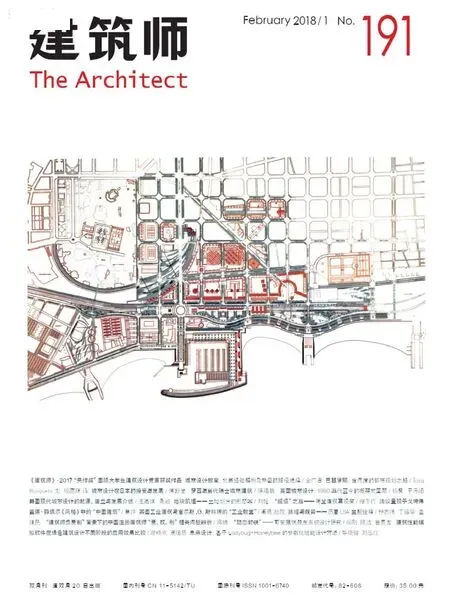罗西与当代瑞士城市建筑
陈瑾羲
“我做城市规划的同时也是在做建筑设计。对于空间的观点以及城市空间的氛围都与建筑息息相关。建筑布局、外观类型、引起某些回忆或情绪的建筑材料以及理解某地的媒介,这些都可以体现城市空间及其氛围。在确定城市类型时,我必须要想,公寓或办公室内部是什么样的呢?我如何从街上进入大楼,又如何走出来呢?建筑师必须积极参与城市设计。”[1]Städtebau,德语中的城市设计,其中Stadt词根对应城市,bau对应建筑、建造、形成等。因而Städtebau包含了建筑和城市空间营建。本文讨论的城市建筑,正是指城市营建作为不可略过的重要条件的建筑设计。
谈瑞士的城市建筑,不能离开阿尔多·罗西。“人人都同意,瑞士当代建筑的根基可以被追溯至阿尔多·罗西。”[2]1960年代末,随着二战后西方现代主义危机的爆发,苏黎世高工的建筑学科遭遇了“瘫痪(Lähmung)和精神‘真空’(Vakuum)”[3]。1972年罗西来到苏黎世高工,重建了学科的自主性,并带来了“对城市建筑的兴趣,对类型学以及建筑的历史维度的专注”[4]等趋势。此后,罗西的传人在瑞士的传统和文脉中发展了“类比”“氛围”“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历史维度”等思想,结出了瑞士当代城市建筑实践的多元果实。
一、理论的真空
1960年代,西方建筑和城市学科正在经历一场专业危机。一方面,二战后现代建筑的乌托邦之城已然轰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人对现代主义发起了猛烈批判。另一方面,随着托马斯·戈登·卡伦(Thomas Gordon Cullen)的《城镇景观》面世,倡导性规划和自己动手等思潮涌现,建筑与城市学科似乎要走向“无计划的感性世界”[5],转而向社会、政治或技术等其他学科寻找发展依据。
1960年代末,来自苏黎世高工的两名助教冯(Rut Fohn)和弗兰克(Hartmut Frank)在瑞士杂志《教科书》(Kursbuch)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客座讲师巴赫曼(Heini Bachmann)在建筑系开设的一门研讨课:“在《规划决策的经济标准》[6]的题目下,研讨课以案例分析的形式调查了苏黎世近郊沃克茨维尔(Volketswil)的快速发展,将其与总承包商恩斯特·古纳(Ernst Göhner)公司的建造活动联系起来。”他们总结到:“这证实了,建筑系学生的官方教学目标和职业前景以及对社区和国家民主的信念,将被严重动摇。”[7]作为教学总结与成果,《
与此相对的,建筑系在专业方面的建设实际从未短缺。1961年,霍伊斯里(Bernhard Hoesli)离开“德州骑警”回到苏黎世高工任教两年后,开始全面负责本科一年级设计入门教学。霍伊斯里制定了建筑设计、建造设计、艺术设计三门课程共同构成设计入门教学的课程框架,并在建筑设计课中教授现代建筑的基本设计法则和空间理解。霍伊斯里的建筑设计教学成为当时的前沿,时至今日对世界各地的教学仍有影响。理论方面的建设亦有重要举措。1967年,霍伊斯里、霍费(Paul Hofer)和福柯特(Adolf Max Vogt)等教授一起,在建筑系成立了“历史与理论研究所”(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r Architektur(gta)),与同年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纽约成立的 “建筑与城市研究所”(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IAUS))遥相呼应。研究所后来成为新理性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桥梁和纽带,阿尔多·罗西、柯林·罗(Colin Rowe)等学者和两个研究所均有联系。[11]当时两个重要研究所的成立,可被视为学科危机下需要确认新方向的共识,表明找到新的(现代主义之后)、共通的学科标准已迫在眉睫[12]。但是,还需要一位大师,一位临门一脚决定胜负的人物,来彻底扭转局面。
在苏黎世风景如画的霍费教授的助理室里,赖希林和莱恩哈特(Fabio Reinhart)有天在晚饭后像往常一样开始闲谈。他们开始议论下一位大师的可能候选人。勒·柯布西耶已经去世,路易斯·康不入赖希林的法眼,尽管他对提契诺学派的实质性影响至深,赖希林轻蔑地将其称为萨满巫师而非大师本尊。“我们拿起几个名字,直到突然间似乎是同时从嘴里喊出来的,罗西!”[13]
赖希林在回到苏黎世高工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担任助理之前,曾在佛罗伦萨大学建筑学院研习过一段时间。期间他仔细重读了《城市建筑学》,并追本溯源地学习了书中罗西的引用文献。赖希林也阅读了罗西发表在《Casabella continuita》杂志上的多篇文章,诸如罗西写作的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或是他设计的建筑。赖希林认为文章是“精辟”的。他如此敬仰罗西,竟去问杂志编辑托索妮(Myriam Tosoni),罗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阿尔多吗?’托索妮回答到:‘一个漂亮的男孩。非常专业和精准,写得一手清晰和准确的意大利语,从来没有任何需要修改的。”[14]在佛罗伦萨跟随寇尼克(Giovanni Klaus Koenig)教授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通过苏黎世高工历史与理论研究所的另一名助理施坦曼(Martin Steinmann)的介绍,赖希林回到研究所成为福柯特教授的助理。于是和莱恩哈特聚在了一起,有了上述关于大师候选人的对话。
现在,邀请罗西来苏黎世高工来任教,成为赖希林和莱恩哈特想要极力促成的事。当时罗西在意大利米兰理工已是教授,似乎并无契机来到苏黎世高工做个客座讲师。但命运已有自己的安排。1971年秋季,包括罗西在内的7名米兰理工建筑学院教师遭到投诉,指控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罗西是一名共产党员。意大利报纸声称,数罪并罚加以严惩,并列举了监禁年数。罗西被无限期地从米兰理工停职了,恐怕还有牢狱之忧。但赖希林想必高兴坏了,他摩拳擦掌地写道:“这是我们的机会(Das ist unsere Chance)。”[15]
通过当时已在苏黎世高工担任客座的施耐伯力(Dolf Schnebli)教授牵线,赖希林和莱恩哈特小心翼翼地与罗西取得联系,生怕把这事给搞砸了。俩人随即给系主任霍伊斯里写了封信,称呼其为“最权威的!”(Onnipotentissimo!),落款为“你谦卑的仆人”(Gli "umili servitor Vostri")。信中表示已经找到先前霍伊斯里委托他们物色的设计教席的客座教师人选。此前学生游行和社会运动造成教学混乱,苏黎世高工已经解聘了3位投身于社会政治的客座教师。因而寻找仍然坚信建筑学科的教师,成为建筑系的现实需要。在信中,俩人明确指出:“通过罗西已经发表的设计和文章,我们(知道)……他主张建筑的自主性以及建筑师的特定角色,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与设计分离。”[16]同时提到罗西对瑞士和德国文化所知甚多,德语流利,并特别提及他私人藏书中有不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出的书,包括“您的”(指霍伊斯里通过研究所出版的)《透明性》。所有这些,都表明罗西是个完美的候选人。只有一点,罗西之所以有时间来苏黎世而不得不被提及的原委,被放在了信件正文的最后。他被米兰理工停职了,当然是和其他不少知名教授一起的,这是由意大利学校的危机导致的。而罗西的共产党员身份可能给建筑系带来的“政治”问题则只字未提。
赖希林和莱恩哈特还为罗西策划了一个展览和讲座来测试建筑系对他到来的反应。展览于1972年2月8日在苏黎世格娄布斯临时仓库(Globus-Provisorium)开幕,展出了一些罗西的图纸和方案模型,包括史勘迪奇(Scandicci)的市政厅、赛格拉特(Segrate)的喷泉设计等。建筑系分外期待罗西对所谓的学科“瘫痪和精神真空”能够开出来的处方,有许多学生和老师来听讲座。在讲座中,罗西明确提到了建筑学科的“自主性”。他反对“声称机器和电脑,就是技术专家,取代了建筑师的工作”,指出“建筑,就像其他任何技术,艺术或工艺,与现实密切联系;它是其有组织的和历史决定的形式的劳动分工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然而,它的自主性仍然存在。”关于现代主义,他反对“代表着一种乌托邦式的、梦幻般远景的立场,反对与现实毫无联系的大型项目,并且……将现代性的实际成就置于危机之中。”在进一步关于历史和设计的关系上,罗西指出,历史作为“设计的坚实材料,作为一种必须指涉的领域,不能被忽略”[17]。
单凭“自主性”理论,罗西就对瑞士建筑贡献良多[18]。该观点当时对听众而言,被赖希林形容为有如在马里亚纳海沟中发现动植物那样陌生又有魔力。罗西倾向的“理性”“现实主义”后来多次在瑞士城市建筑展览和各种标题中出现。他强调历史作为设计的基石,并将现代建筑也视为历史的一部分,对研究所后来的研究方向以及1980年代后的瑞士城市建筑影响深远。
基于罗西对建筑学科的坚定信念,给系所教授们留下的新奇但良好的第一印象,以及霍伊斯里和施耐伯力等教授对有决断力的年轻人的厚望,建筑系和学校决定邀请罗西当年秋季就来任教。苏黎世高工建筑系展示了一个自信的姿态,尽管罗西是一个“左”派的共产党员,但只要在学科上是专业的,且和系所的立场一致,就不逃避这个在政治上令人不适的决定[19]。
二、科学的方法
1972年秋季,罗西来到苏黎世高工教授三、四年级设计课。第一次教学持续了两年,1974年由于学校预算的原因罗西离开了苏黎世高工。1976年,在研究所城市设计历史教席霍费教授的邀请下,罗西回到苏黎世高工担任了两周讲师[20]。1977年,罗西再次受邀任教,和霍费、霍伊斯里共同指导了一次设计课。1978年课程结束后,罗西再次离开了苏黎世高工,没能获得大家期望的苏黎世高工教授席位,此后没再回来任教。
罗西在苏黎世高工的设计课教学,数次讲座,“在苏黎世高工影响空前,因为他切实填补了理论真空,并且建立了标准”[21]。罗西彻底扭转了当时瑞士建筑学科的社会政治和技术趋势,对瑞士那一代学习建筑的学生影响深远。“我们68届这一代人都深植于理性主义的传统之中。”[22]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一直将罗西称为他们在苏黎世高工期间的“决定性老师”(prägenden Lehrer)。除了他们,罗西执教过的学生还包括迪那(Roger Diener)、博思哈德(Max Bosshard)、梅利(Marcel Meili)、史克(Miroslav Šik)等瑞士当代知名建筑师和理论家。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谈道:“直到阿尔多·罗西到了苏黎世,建筑设计才又慢慢兴起。”[23]
1972-1974年罗西在苏黎世高工第一次任教期间,两年设计课都以住宅为题。城市设计和建筑需要综合考虑,建筑物是“组成城市整体的元素和部分”[24]。调查和设计内容包含城市街区到居家空间,涉及城市肌理、住宅类型的探索。类型与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直接联系,罗西在《城市建筑学》中已论证过这个观点[25]。第一年设计课选址在苏黎世老城区中,第二年关注瑞士更小城市如阿劳(Aarau)的城市扩展区。
在设计课中,罗西传授一种基于城市和历史的批判性设计方法。他将设计过程分成分析、设计概念和设计3个阶段。3个阶段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通过分析,提出设计概念,继而发展出深入的设计,整个过程看上去既“客观”又“科学”。正如罗西曾引用汉斯·梅耶(Hannes Meyer)的话来佐证他的观点:“建筑已成为一门科学。建筑不是感觉,而是知识的问题。”[26]在分析阶段,学生需要对设计场地进行不同层次的调研和分析。首先需要选择一个具体的城市地区,定义其组成、边界、主要元素以及或是纪念物;然后是类型调查,指出重复的元素,并与城市数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发展比较;城市被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将介入的设计是其延续或是对比[27]。重要的是,分析过程是在建筑层面上完成的。与苏黎世高工当时地块分析时常常采用抽象色块不同,罗西要求学生绘制切实的建筑图纸——“密集的对街区或地区的建筑底层平面的素描‘写作’”[28]。通过不同尺度建筑和城市的平面图和剖面图的再现,城市形态得到了陈述,各个城市元素得到分辨,住宅和建筑古迹得到区分。当不同年代重要阶段的呈现并置时,城市的发展被揭示,其中恒定和持久的元素如水系、纪念物、街道和广场等就被辨析出来。分析揭示了城市建筑中变与不变的元素,是确定设计的建筑类型的重要基础。同时,罗西还要求学生调查和分析该场地已实施和未实施的方案,这些方案背后的设计理论和文化历史背景得到认知,并将反映到设计中去[29]。
分析阶段几乎占据了整个秋季学期,直到学期末才形成设计概念。详尽的分析使学生掌握了大量关于问题的知识,接下来要从海量的“客观”分析结果中试图“科学”地推导出设计概念。“设计概念是分析结果的互动的创造性综合。它不包含细节,而仅限于基于分析的建筑创造转译的基本法则。”设计概念阶段要确定设计原则,提出“所谓逻辑的外形,建筑决策的核心以及类型选择。”[30]如博思哈德(Max Bosshard)、昆(Felix Kuhn)、齐默曼(Martin Zimmermann)小组选择苏黎世第10区的莱登街区(Lettenquartier)作为设计介入的城市地区,“在分析阶段,3名学生都注意到,调研的立面往往强调水平方向,有时候窗户的行列被楼梯打断。”因此在设计中,齐默曼和博思哈德的方案立面都注重水平性的表达。他们的建筑场地相邻,在设计概念阶段,齐默曼确定其建筑群由一个合院、一栋长条形的建筑和一条廊道构成(图1),博思哈德则由10个合院组成一条长长的建筑(图2)[31]。
在春季学期的设计阶段,设计概念被发展成设计,细节被确定下来。在齐默曼的方案中,廊道被保留为连接合院和长条形建筑的元素,西侧端头增加了一个幼儿园(图3)。合院建筑的高度被统一确定下来,建筑的底层空间与廊道共同设计,公寓和工作室都朝向合院内部,不同的平面在内院的立面中得到反映。在建筑的转角可以清晰地看到入口和进出通道。博思哈德的连续排布的合院,分布在方格网上,整合了场地。底层采用柱廊,开口很高,立面上还出现了方形窗的元素,很像罗西在米兰设计的加拉拉特西公寓(Gallaratese Quarter)的立面[32](图4)。

图1:齐默曼秋季学期设计概念

图2:博思哈德设计方案

图3:齐默曼春季学期设计深化

图4:博思哈德方案立面与罗西加拉拉特西公寓立面
整个设计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从分析中演变出形式。在罗西3阶段设计方法中,从分析向设计概念过渡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也正是这个环节的科学性饱受质疑。上文提到,齐默曼和博思哈德在苏黎世10区莱登街区的公寓设计中,都选择了合院建筑类型,底层都采用了柱廊。但是,原先的街区中并无合院,而是沿坡地方向排列的行列式建筑,该地区的住宅也从未使用过柱廊作为建筑过渡。这不得不让人生疑,这两个类型是如何或者根本不是从分析中推导得来的。在罗西与设计课并行的讲座中也许可以找到线索——他介绍过在蒙扎圣洛克(San Rocco,Monza)的公寓设计中合院的排布以及在加拉拉特西公寓中柱廊的使用。似乎罗西的建筑态度比分析结果在类型选择时更有决定性的影响。质疑也随之产生。分析是一个“客观”的过程,然而走向设计概念的那一步,形式选择,仍然取决于主观选择。比如,模仿老师的设计?如此,远非“科学”。后来罗西和霍伊斯里教授在1978年的设计课教学中意见不合,首要原因正是这点。
三、观点与碰撞
1977年罗西再次在苏黎世高工教授设计课,这回他要跟霍费和霍伊斯里教授一起带一个“索洛图恩”(Unternehmen Solothurn)的实验性设计课。所谓实验性,是因为课程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比较霍费和罗西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城市介入(设计)方法。”[33]霍费作为城市设计历史教席的教授,一直试图寻求历史研究和设计之间的结合,此前曾尝试过与设计教师合作开展设计教学。他希望通过和罗西的合作教学,能够综合发展出一套更系统的方法。
而霍伊斯里的加入改变了这门课程的气氛。作为建筑系“最权威的”教授之一,他显然注意到了罗西自1972年以来给建筑系带来的新趋势:“对城市建筑的兴趣,对类型学以及建筑的历史维度的专注”。作为“使现代建筑可教”的奠基人之一,这位被塞利克曼(Werner Seligmann)形容为“将历史重新整合入建筑设计教学”[34]的教育家,对这些趋势保持审慎,罗西的“类比城市”作为“一种转化设计形式的合理的方法”[35],引起了他的兴趣。关于罗西及其教学,霍伊斯里的印象是概念连贯性和逻辑清晰性不足。在一次罗西讲课的笔记中,他写到:“言之有物,但仍然不可捉摸(人人都可以说他对囊中之物了如指掌)。”[36]现在霍伊斯里打算通过设计课教学与罗西进行面对面的学术探讨,他认为这会载入史册。
3个大牌教授指导的设计课只有14个学生报名,与罗西1972年执教时80个学生济济满堂听他讲课的状况大相径庭。课程开始之前,学生已经知道他们观点不同,大多是冲着罗西来的。课上得相当尴尬,联合评图的时候常常是“长时间的沉默,数分钟后,才有人打破沉默”[37]。到了春季学期,罗西和霍伊斯里几乎不同时出现了,他们轮流来指导学生作业。根据霍普芬盖特纳(Judith Hopfengärtner)的总结,课程指导中观点相左主要围绕以下3对关键词展开:科学方法与诗意直觉、建筑实体与城市空间、形式与意义。
罗西的分析向设计概念转化,成为霍伊斯里质疑到底是科学方法还是诗意直觉的第一个问题。上文已经提及学生作业的形式结果与罗西方案的相似性。霍伊斯里认为,罗西的形式结果是由“意图”(Absichten)决定的,即上文所说的主观选择而非分析推导,而且常常相当“突然”(unvermittelt),根本就不科学。甚至在分析阶段,所谓类型确定,就是在为主观选择背书。霍伊斯里本来希望这位标榜清晰科学“设计理论”的旗手能够心平气和地同他交流,能够让他确认,设计是可以推理的。但罗西逃避了直面质疑,在为什么这样做的问题面前,转向了回答如何做。尽管罗西确实启发了一些学生的创造性,但霍伊斯里认为光靠“艺术自觉”(künstlerische Spontaneität)那是无源之水(kreativen Müssiggang)[38],在一个教学环境中,一个可信的方法才是面向大多数普通学生的责任,才是真正使得设计“可教”。
其次,具体方案在处理建筑实体和城市空间的关系时,罗西的“秩序”创造触到了霍伊斯里的逆鳞。众所周知,霍伊斯里和柯林·罗在“德州骑警”时期一起扛过枪。柯林·罗和弗瑞德·科特(Fred Koetter)的《拼贴城市》虽然在1978年才正式出版,比《城市建筑学》晚了12年,但写作于1973年,1975年在《建筑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霍伊斯里在自己的教学中采用了这篇文章。他敏感地将“类比城市”和“拼贴城市”两个概念通过数次研讨课进行比较。然后他站到了说英语的同事这边,认为解决现代建筑作为孤立“物体的困境”的出路,是通过“实体”与“空间”之间有张力的“对话式”(dialogische)图底关系处理。虚实矛盾统一构成连续的空间,透明性,是霍伊斯里设计教学中的另一重要信条。而在罗西指导的方案中,建筑布局在城市中有着明确的形状,隐含轴线对称,建筑甚至有点纪念性。罗西的“秩序”营造,拒绝了所谓建筑与空间之间的矛盾模糊性,被霍伊斯里认为是“追求立体主义之前的时代”,是对“现代意识的强奸(vergewaltigen)”[39]。后来霍费发表了一篇题为《对话式城市设计》[40])的文章,作为对罗西的回应,称“笛卡尔式的理性的,虚实清晰对比的模式”是对“城市品质的核心价值的根本威胁”,一定会被“对话式”的城市空间取代[41]。
最后,在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上,罗西再次与霍伊斯里分道扬镳。霍伊斯里奉行透明性原则,要求设计必须呈现图底交织的复杂形态,以反映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对话”。形式是最重要的,现代的形式将哺育现代的生活,意义随之而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霍伊斯里指责罗西的设计中找不到“现代的生活方式”,全然不“朝向未来”。但在罗西看来,城市建筑是“整个历史分析”的结果,建筑的意义和内容在城市中的各个场所已经存在。“任何在历史城市中心的介入都是一种判断”[42],对城市空间的建筑干预,都在表明立场并且产生意义,不管建筑师是否愿意,甚至是否自知。因此罗西选择类型作为媒介,并且再三强调,类型包含生活方式,反映社会文化,基于城市历史。对类型的分析,是通过学科审视意义,设计对类型的选择,是通过专业表达意义。
罗西当时在教学上遭到挑战,历史与理论研究所的同道们并没有提供支持。本以为罗西对历史兴趣浓厚、知识广博,又甚为了解研究所教授们的工作——在1972年2月份的讲座中他曾谈到福柯特教授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及霍费教授写作的《伯尔尼城市景观》[43])和《日内瓦湖和莱茵河之间的中世纪城镇建设》[44]重要文献,设想罗西到了研究所会如鱼得水。然而“仅仅是在学期中,罗西才偶尔发现和同事交谈”[45]。1967年在历史与理论研究所成立时的演讲中,福柯特曾用一个方形来描述研究所的定位:“一般情况下,历史的反面是当下,理论的反面是实践。想象这4个概念作为方的4个角,我们研究所的主题将描述对角线的交点。”[46]福柯特希望研究所的工作能成为一个平台,但他自己更像一个为建筑师提供历史联系(contact)的历史学家,并不热衷于将历史研究指向设计。他和罗西的共同兴趣有限,没有发展出更深的学术交流,更多停留在传统的历史学家及评论家与建筑师的关系上[47]。
霍费和罗西有许多相似的观点,更具合作基础。霍费相信“历史不是过去,而是另一个更强大的当下”[48],“对城市本质及其结构的理解构成了一个不证自明和必不可少的设计基础”[49]。他们的共同兴趣还包括城市“连续的底层平面”(zusammenhängende Grundrissaufnahme)计划,1973年罗西调研了苏黎世,后来霍费调研了索洛图恩。基于此,霍费1978年邀请罗西参与索洛图恩设计课。然后霍伊斯里加入了,霍费在设计课中扮演着调停者的角色。相比罗西,他似乎和霍伊斯里更有共同语言。罗西离开后,霍费和霍伊斯里一起合作了“对话式城市设计”(Dialogischen Stadtentwurf)的教学。这成为霍伊斯里生平最后5年里最为重要的教学活动,直至1984年突然离世。
霍伊斯里和罗西的碰撞,提供了宝贵的观察机会。相较霍伊斯里的换一种方法推行升级版的理想信条,罗西更倾向于现实主义。他写道:“对城市的研究使我们能够掌握那些我们使用在建筑中发挥现实力量的要素。即便是建筑最特别的创新者,也不能毫无根基,如果他们不想走向无菌的乌托邦的话。”[50]相比起来,霍伊斯里更像是“方法体系”和“系统学”[51]的捍卫者。罗西反而更接近罗在《拼贴城市》中描述的“拼贴匠”——“一种建筑师、城市规划师所事、所为的更加‘真实生活’的属类”[52]。

图5:《城市建筑学》 & 《一部科学的自传》封面
四、刺猬与狐狸
实际上,相关的回忆和细节表明,在科学方法和诗意直觉的质疑面前,罗西并非没有挣扎。根据赖希林的文章,课程作业对罗西的模仿遭到了某个教授(赖希林没有指出具体是谁)的抱怨,“他没有直接针对相关人员(罗西),但在他忠实的助手(赖希林)面前隐约暗示了。”助手们对罗西的回应感兴趣。但当他们问他的时候,“他展示了奥林匹克般的高级微笑[……],躲闪开来”,保持“克制和沉默”。为了逼罗西表露心声,在一辑由施坦曼和冯·莫斯(Stanislaus von Moos)策划的,以“建筑的现实主义”[53])为专题的《建筑命题》(archithese)专刊(图7)组稿时,他们邀请罗西写一篇文章,谈谈历史知识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相应的教学措施,为此还专门准备了他们想听到大师见解的问题列表。罗西一直拖着,被电话催稿时非常“易怒”。最后他交了“可怜的”两页纸,题为“现实的教育”[54])。文章“使用的现实主义这个词充满了各种模糊性和交叉联系”,“令编辑感到不安”,“似乎是对期待他的完美理论大厦的追随者的警示”[55]。罗西否定了此前人们印象中的罗西标签,声称“无论是历史研究、形态类型学,还是‘类比城市’,都无法解释罗西的建筑;所谓‘好的教学出发点’就更不能了;‘理性建筑’一度是金字招牌,但从来不是追随者及其先驱‘导师’的舒适区”[56]。

图6:纪念1975年“趋势”展览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所2017年11月7日研讨会海报

图7:《建筑命题》“建筑的现实主义”专刊
1970年代两次在苏黎世高工任教期间,罗西处在他最重要的转折点。从他前后出版的两本书的书名中可以窥见他的变化。罗西当时一定竭尽全力,试图建立科学设计方法的理论大厦。但他的经验和感觉同样成为了设计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部分,不能也不应用系统方法去排斥它们。不仅如此,罗西对一切艺术如电影、文学都感兴趣,建筑因而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介入现实探寻和表达意义的媒介之一,甚至可以被“忘却”。1966年出版的《城市建筑学》的备选书名是《城市设计手册》(The City Planning Manual),听上去像是《建筑手册之城市设计》(Der Städtebau,1890年)一类的科学指南延续。而1981年出版的《一部科学的自传》备选书名竟成了《忘却建筑》(Forgetting Architecture)[57]。从《设计手册》到《忘却建筑》,科学与自传的结合走向“感性层面的逻辑思维”[58]。柏林(Isaiah Berlin)定义中的“刺猬”褪去层层面纱,露出“狐狸”的真面目。
在进入“狐狸”的多面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之前,除了前文已经涉及的历史与理论研究所、霍伊斯里、霍费、福柯特、罗和科特、康,以及年轻一代的赖希林、莱恩哈特、施坦恩等,还有必要提及同时代一些其他重要人物(如下但未能尽述),以便更好地梳理出影响瑞士当代城市建筑实践的多重线索。1972年10月的《Werk》期刊,刊登了希恩(Otto H.Senn)、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施坦曼讨论当年辞世的瑞士“新建筑”(Neuen Bauen)运动先驱施密特(Hans Schmidt)的文章,以及施密特写作的摘选[59]。施密特作品中“重获形式的希望和幻想”得到强调。罗西极为欣赏他“重获形式的希望”没有流于“幻想”[60]。施密特是瑞士本土现代建筑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和同时代建筑师的“新建筑”被当代瑞士建筑师不断回顾[61]。罗伯特·文丘里对瑞士当时建筑师和理论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被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称为当时“将历史重新写入建筑”的重要人物之一。冯·莫斯在担任《建筑命题》期刊主编期间起到了向瑞士宣传文丘里的主导作用(Protagonist)。莫拉万斯基认为,冯·莫斯的继任者施坦曼后来提出的建筑的现实主义,是基于瑞士现代主义者施密特(Hans Schmidt),罗西的理性主义以及文丘里的“大众”(Populist)后现代主义发展而来的[62]。还有斯诺奇(Luigi Snozzi)等一批提契诺建筑师,1970年代罗西离开后,他们在苏黎世高工担任客座讲师。赫尔佐格和迪那等也是斯诺奇的学生。“对城市建筑的兴趣,对类型学以及建筑的历史维度的专注”等思想,通过后续几年提契诺的客座讲师们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和加强。
五、传承与发展
深受罗西影响的赖希林、施坦曼等1940年代出生的研究助手,还有梅利、史克等不少1950年代出生的年轻学生,都在研究所工作过。由年轻学生组成的小团体,被梅利称为“游击队”(Guerrilla)[63]。他们的观点和方法与教授们完全不同,反抗精神与“德州骑警”如出一辙。只不过这一次,霍伊斯里等站到了被反抗的权威那一侧。而到了罗西身上,反抗和尊重权威却奇怪地融合在了一起,“那些反抗权威的学生,如此惊叹于罗西的方式,以至于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喜爱罗西的权威教条。”[64]
“类比”“类型”“建筑的历史维度”“理性主义”“现实主义”“氛围”以及相关的“对话式”城市设计等,都在瑞士得到了本土的发展,深刻影响了瑞士当代城市建筑。历史翻向了下一代。
赖希林和施坦曼两位助理,和研究所的教授们不同,更倾向于罗西的建筑师立场。他们坚称自己是“在设计当代建筑时对历史作为一项工具感兴趣的建筑师,而不是对历史作为一门学科感兴趣的历史学家。”[65]赖希林是罗西1972年到苏黎世高工任教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罗西首次任教期间的首席助手。他和莱恩哈特在研究所,和罗西一起完成了在米兰三年展中展出的“类比城市”(Città Analoga)制作。1974年,赖希林和莱恩哈特在《建筑命题》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作为建筑理论的组成部分”[66])一文,写到,“要了解建筑对话的固有逻辑(他们甚至谈到建筑语言),必须知悉和了解建筑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要理解场地的历史以及类型。”[67]
1975年,当时还是福柯特助手的施坦曼和托马斯·博戈(Thomas Boga)一起,策划了一场题为“趋势——提契诺地区新建筑”[68])的展览。展览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展览手册的介绍文章“现实性作为历史:建筑中的现实主义的讨论纪要”[69])中,施坦曼引用了赖希林和莱恩哈特的《历史作为建筑理论的组成部分》以及罗西的名言“建筑就是建筑”(l’architettura sono le architetture),强调了“建筑的意义是通过与其自身传统的关系来定义的”。1976年,赖希林和施坦曼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建筑内部现实性的问题”[70]),刊登在《建筑命题》杂志的“建筑的现实主义”专刊上(图7)。罗西的“现实的教育”也刊登在同期。赖希林和施坦曼强调:“要了解一个作品的意义,就要在一张交织的关系网络(历史与传统)中定义它的位置。”历史不是已有案例的集合,而是权衡当代设计决策的一个框架。这被视为真正的理性主义[71]。
赖希林和施坦曼的研究偏离了研究所的工作,后来都在苏黎世高工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的事业。罗西称赖希林他们为“趋势”的博罗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72],赖希林自嘲冠上了“理性主义建筑师的种姓(Kaste)”[73]。赖希林和施坦曼是瑞士语境中类型和意象的重要发展者,他们阐释了建筑的自主性、传统和意义的关系,成为后来瑞士德语区建筑师的“坐标体系”(Coordinate System)[74]。
罗西的另一助手莱恩哈特和学生史克等发展了“类比建筑”(Analogous Architecture)。1983年,莱恩哈特获得了设计教席的教授职位,和奥特利(Luca Ortelli)、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史克等一起,重新阐释了“类比建筑”,重新讨论了延续、指涉(Reference)、氛围(Atmosphäre)等概念。“从意大利语的氛围‘Ambiente’到德语的‘Atmosphäre’……罗西的后继人将重点从意大利的经典建筑转移到瑞士的城郊建筑。”[75]史克对“类比建筑”的瑞士当代转译通过地方的城郊建筑实现。“类比”的切入点根植于掌握一个给定场所的日常特质下的诗意力量”,“绝不能和大规模的城市规划相提并论。”[76]类比建筑应当轻柔地融入当地的环境,默默地融入相对稳定的城市状态。在类比方法中,氛围,成为处理场地、建筑或空间的重要工具。“从类型学方向对城市进行抽象解析被一种以日常生活及生活经验为特点的具体方法所代替。”[77]“在今天,各种建筑类型很难区分……氛围帮助我们认知所处的建筑是什么样的。它产生微妙的暗示(不同于符号)少许模糊却情感强烈。”[78]有趣的是,梅利在追忆罗西时曾谈到过:“在罗西的课上,瑞士的年轻建筑师对‘氛围’一词处理得更好,而‘类型’却处理不好。”[79]
赖希林和莱恩哈特1975年设计的维齐奥住宅(Vezio),可被视为一个从类型和环境两方面切入的作品。设计包含了提契诺城郊村庄住宅中既有的类型和多个形态元素,同时“设计的层次暴露了诗意的过程”,以氛围的方式表达了场地中建筑和文化的延续性,“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幼稚的文脉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80]。
史克在哈尔登施泰因(Haldenstein)设计的市民住宅(Bürghaus,2008年)是“类比建筑”的当代代表案例之一。史克将建筑处理成3个交错的体量,围绕出一个内部的庭院。体量操作一方面出于尺度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源自周边乡村地区过去带花园的贵族房屋的类型。窗户、栏杆、屋顶等元素的处理都可以从周边环境中找到依据。在该场地,建筑轻柔地、无缝地融入环境。同时通过“陌生化”(Verfremden)的操作,通过统一的立面材料和窗户变化的细微处理,使得要素有别于传统,又有了时间的层次。市民住宅成为一个“想象中的参考框架,为居民提供生活过和记忆中的空间念想。”[81]“类比建筑”以历史为维度,以类比为方法操作类型和元素,“模糊了社会和时间的框架”,创造“既新又旧”(altneu)的建筑[82](图8、图9)。

图8:市民住宅总平面

图9:市民住宅街景
斯诺奇在布里撒戈(Brissago)的宾安切尼公寓(Apartment Building Bianchini,1987)设计,与史克的市民住宅有异曲同工之处。场地中原先有一个塔状的18世纪公寓楼。斯诺奇将插入的新公寓建筑设计成L形,在塔楼南侧限定出了一个通向村中教堂的小广场,保留了人们从街道经由塔楼到达教堂的记忆。在建筑要素操作时,类型的方法被采用。公寓中各个立面的窗户都可以从周边建筑中找到参照。同时通过混凝土材料的使用,对窗户檐口的异化操作,使得新建筑清晰地区别于村庄既有建筑[83]。(图10、图11)建筑的体量布局、城市空间营建、功能的安排、材料使用和细部操作,都系统地表达了建筑设计的城市策略。对斯诺奇来说,“城市肌理是他感兴趣的,在那儿单体建筑的‘扭捏作态’没有容身之处”[84]。

图10:宾安切尼公寓总平面及底层平面

图11:宾安切尼公寓街景
斯诺奇和提契诺学派的建筑,是区别于瑞士德语区后来极简主义建筑的一个重要“趋势”。斯诺奇为卡拉索山村镇(Monte Carasso)所做的城市设计以及持续30年的在地实践,已成为一个特殊代表。1979年,斯诺奇的卡拉索山小镇整体城市设计方案获得通过,将在原有修道院的遗迹上重建村镇中心,包括小学、展览空间和酒吧等公共设施以及城市公共空间。有趣的是,导则中写道:“如果一个项目比规则限制的要好,那么规则将会改变,而不是建筑。”[85]这一条对其他所有导则的颠覆可能,让人联想到区别于“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斯诺奇为市长古依多提(Flavio Guidotti)设计住宅时,方案就突破了导则的限制。市长承认,也许这样的成功“是偶然的结果”。卡拉索山村镇也许是斯诺奇心目中“民主城镇的典范”,却需要一个有远见的市长和一个专业建筑师的长期在地投入[86]。这种矛盾性,也许正是罗和柯特在《拼贴城市》中揭示的:“经验主义者钟情于基地,而理想主义者关心普遍情况”[87],通往“真实生活”[88]的属类是“不会局限于仅为该项目目标而准备的原材料和工具的”[89]。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被乌尔施朋(Philip Ursprung)称为是超越了罗西的“现实主义”的建筑实践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早期深受罗西的影响,1977年发表的“理性建筑及历史参照”[90]一文,可被视为罗西设计理论在巴塞尔的应用[91]。自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 “图像”的概念被引入他们的设计。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声称受到视觉艺术的影响,并提到文丘里“将流行艺术引入建筑”[92]的做法。“我们通过各种手段对一个场地产生主观感知,然后将新的图像投射在这个地方。”[93]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巴塞尔诺华办公园区(Novartis campus,Basel)设计的办公楼(Asklepios 8),突破了城市设计导则中建筑限高的一倍。该高层办公楼成为诺华制药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巴塞尔作为国际都市的城市意象中的一部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建筑因而被视为“社会面貌的图像”投射,“鼓励(世界各地)观众带来自己的故事和经验”[94],“因而兑现了罗西自始至终的追求——现实主义建筑。”[95]需要指出的是,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图像”仍需回应建筑的自主性。他们谈道:“建筑就是建筑,罗西如是说。我们感兴趣的,是寻找我们的建筑,在建筑媒介之外别无其他语言;我们不做拼贴,我们试图创造整体的、特定的建筑。”[96]这与形式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式的拼贴截然不同。
瑞士德语区当代令人印象深刻的极简主义建筑,是与美国式的后现代主义保持距离的另一趋势。这可以被追溯到瑞士本土的现代主义传统。施坦曼谈道:“罗西在苏黎世高工的教学发展出了对历史的关注兴趣,也包括现代主义的。”因而“瑞士德语区的建筑师需要写作他们自己的历史,在他们能够开始指涉历史之前。”自1970年代开始,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开始重视瑞士本土现代主义传统,年轻一代助理们研究了萨维斯博格(Otto Rudolf Salvisberg)、施泰格(Haefeli Moser Steiger)等一批瑞士本土现代主义建筑师及其设计。施坦曼、苏米(Christian Sumi)、冯·莫斯等将萨维斯博格的设计称为“另一种现代性”(图12),“建筑师将传统的建筑细节简化到绝对的极简主义,但仍然保持了建筑的可读性。”[97]年轻的学生自1980年代中期开展实践后,这成为他们事务所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如吉贡和古耶事务所1992年在达沃斯设计的基希纳博物馆,设计做了合理的简化,被认为是过去20余年间瑞士最好的博物馆[98]。这种简约和极简主义的形式,被施坦曼称为“强有力的形式”(forceful form),解释了一大批被称为“瑞士盒子”(swissbox)的当代建筑。梅利甚至认为,“瑞士建筑学从来没有真正背离现代主义”[99]。

图12:研究所1995年出版的《萨维斯博格:另一种现代性》(« O.R.Salvisberg : die andere Moderne »)

图13:萨维斯博格绘制的苏黎世高工实验室外窗保温设施细部图
瑞士当代建筑实践愈发多元化。有对自然与建筑关系的思考,“将建筑视为是实现和衰落之间潜在的一种状态”,如卒姆托的圣贝内迪克教堂(St.Benedict Chapel )等。有对瑞士乡村风貌特征的重视,对城市与农村相互作用的探讨,反映在设计中的“科技田园风”[100]等。还有如奥加提(Valerio Olgiati)和克雷兹(Christian Kerez)的实践,被卡鲁索(Adam Caruso)视为“在不再想要重要建筑的世界中创造有一些重要性的作品”[101]的尝试,作为对上一代极简主义和平凡主义的批判。
六、小结:理论与实践
本文以罗西在苏黎世高工的教学为线索,尝试呈现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的传承和发展关系。
罗西1972至1974年在苏黎世高工的第一次教学被后人广为流传,被认为重建了瑞士当时建筑学科的自主性,唤起了对城市建筑的关注,指明了类型学以及建筑的历史维度的重要方法。罗西1977至1978年在苏黎世高工与霍伊斯里的思想碰撞也同等重要。科学方法与诗意直觉、建筑实体与城市空间、形式与意义孰轻孰重的观点与争论,实则是对城市建筑的设计方法、结果和目的的探讨。这超出了“类比城市”和“拼贴城市”二者的比较,揭示出二者的一些内在共性。罗西对直觉和经验的敏感和拥抱,与他试图构建科学设计方法理论大厦的尝试,一同构成了“感性层面的逻辑思维”,实则更接近罗倡导的“拼贴匠”。而罗的前同事霍伊斯里,毕生竭尽全力尝试构建面向普通学生的可教的设计方法,排斥“艺术自觉”启发的创造性。相比罗西,霍伊斯里反而更像罗和科特描述的“关心普遍情况”的“理想主义者”和“方法体系”的捍卫者。
罗西对瑞士城市建筑的影响因而是多方面的。首先,罗西本人就是“多面的”,他的思想多元而丰富。罗西“同时倡导理性主义以及直觉,历史以及永恒,彩色粉笔以及绝对冰冷,现实主义以及诗意,共产主义以及米老鼠。”[102]其次,罗西的多元思想和理论通过他的瑞士传人们得到了本土转译和传承。以斯诺奇等为代表的生于1930年代的提契诺建筑师,以赖希林、施坦曼、莱恩哈特等为代表的生于1940年代的理论家,以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史克、迪那等为代表的1950年代,以克雷兹等为代表的1960年代,以及更年轻的1970年代生人的如克里斯特和甘腾拜恩(Christ & Gantenbein)等,都对 “类比”“氛围”“类型”“建筑的历史维度”“理性主义”“现实主义”等罗西思想和理论的关键词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并呈现出对上一代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回应的线索。另一方面,与罗西不同的观点也发展了自己的理论。罗西离开苏黎世高工后,霍伊斯里与霍费开展了“对话式城市设计”的设计课教学,通过教学、发表文章等来回应观点碰撞。“对话式城市设计”的影响在当下瑞士城市建筑实践中屡有回响。
以罗西在苏黎世高工的教学为线索,瑞士当代城市建筑的部分图景得以解析。诚然,瑞士当代城市建筑多元而复杂,并非一种视角可以尽述。“瑞士德语区建筑的真正力量是实践者的智慧,是这样一个事实——始于苏黎世高工的探讨指向实践,并且切实地都在实践中得到了深化。”[103]上文的分析也证明了这点。面对学科危机和“精神真空”时的理论提出,在本土语境中得到转译并指向实践,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并应用到新的当代实践,理论与实践的交织构成了瑞士当代城市建筑发展图景的另一重要线索。
图片来源
图1~图2:Pia Simmendinger.Entwurfsarbeiten aus Rossis Jahreskursen an der ETH Zürich[A].Ákos Moravánszky, Judith Hopfengärtner.Aldo Rossi und die Schweiz Architektonische Wechselwirkungen[M].Zürich: gta Verlag.2011: 62, 64.
图3~图4:Pia Simmendinger.Entwurfsarbeiten aus Rossis Jahreskursen an der ETH Zürich[A].Ákos Moravánszky, Judith Hopfengärtner.Aldo Rossi und die Schweiz Architektonische Wechselwirkungen[M].Zürich: gta Verlag.2011: 65.
图5~图6:Ákos Moravánszky.Formen exaltierter Kälte: Rossis Rationalismus und die Deutschschweizer Architektur[A].Ákos Moravánszky, Judith Hopfengärtner.Aldo Rossi und die Schweiz Architektonische Wechselwirkungen[M].Zürich: gta Verlag.2011: 212.
图6:苏黎世高工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s://www.gta.arch.ethz.ch/tagungen/tendenzen-1975-die-autonomieder-theorie.
图7:Ákos Moravánszky.Formen exaltierter Kälte: Rossis Rationalismus und die Deutschschweizer Architektur[A].Ákos Moravánszky, Judith Hopfengärtner.Aldo Rossi und die Schweiz Architektonische Wechselwirkungen[M].Zürich: gta Verlag.2011: 220.
图8~图9:Tibor Joanelly.Älter werden : "Bürgerhus" in Haldenstein von Miroslav Sik[J].Werk, Bauen + Wohnen.2008(10).60-62.
图10~图11:Claude Lichtenstein.Luigi Snozzi[M].Basel:Birkhäuser Verlag.1997: 120-121.
图12~图13:Claude Lichtenstein.O.R.Salvisberg : die andere Moderne[M].Zürich: gta Verlag.1995.
注释
[1][瑞]昆塔斯·米勒, 波拉·马兰塔.只有稳健的建筑才经得起实践的考验[A].马克·安吉利尔,乔格·希默尔赖希 编.张贺 译.建筑对话[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12-329.326.
[2][瑞]劳伦特·斯塔德.为博物馆而建:1970年后的瑞士建筑[A].马克·安吉利尔,乔格·希默尔赖希 编.张贺 译.建筑对话[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32-143.133.
[3]Ákos Moravánszky, Judith Hopfengärtner.Wie man wird, was man ist: Eine Einfiahrung[A].Ákos Moravánszky,Judith Hopfengärtner.Aldo Rossi und die Schweiz Architektonische Wechselwirkungen[M].Zürich: gta Verlag.2011: 9-22.9.
[4]Judith Hopfengärtner.Das «Unternehmen Solothurn»:Ein experimenteller Entwurfskurs mit Aldo Rossi, Paul Hofer und Bernhard Hoesli an der Architekturabteilung der ETH Zürich[A].Ákos Moravánszky, Judith Hopfengärtner.Aldo Rossi und die Schweiz Architektonische Wechselwirkungen[M].Zürich: gta Verlag.2011: 77-96.80.
[5][英 ]柯林·罗 著.童明 译.拼贴城市 [M].北京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36.
[7]同[3].13.
[8]«Göhnerswil - Wohnungsbau im Kapitalismus».
[9]Bruno Reichlin, «Amarcord»-- Erinnerung an Aldo Rossi[A].Ákos Moravánszky, Judith Hopfengärtner.Aldo Rossi und die Schweiz Architektonische Wechselwirkungen[M].Zürich: gta Verlag.2011: 29-44.36.
[10]Philip Ursprung, Die Rückkehr des Realen: Rossi und Herzog & de Meuron[A].Ákos Moravánszky, Judith Hopfengärtner.Aldo Rossi und die Schweiz Architektonische Wechselwirkungen[M].Zürich: gta Verlag.2011: 197-208.199.
[11]Emmanuel Petit.La Tendenza: Italy and Switzerland[EB/OL].http://radical-pedagogies.com/search-cases/v12-tendenza-italy-switzerland/
[12]同[10].192.
[13]同[9].33.
[14]同[9].32.
[15]同[9].34.
[16]Bruno Reichlin, Fabio Reinhart.Brief an Bernhard Hoesli[A].Ákos Moravánszky, Judith Hopfengärtner.Aldo Rossi und die Schweiz Architektonische Wechselwirkungen[M].Zürich: gta Verlag.2011: 23-38.24.
[17]同[9].35-36.
[18]同[2].133.
[19]同[9].36.
[20]同[4].77.
[21]同[10].199.
[22][瑞]雅克·赫尔佐格, 皮埃尔·德·梅隆.从艺术到具有世界水平的建筑[A].马克·安吉利尔,乔格·希默尔赖希 编.张贺 译.建筑对话[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2-85.62.
[23][瑞]彼得·卒姆托.设计氛围[A].马克·安吉利尔,乔格·希默尔赖希 编.张贺 译.建筑对话[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86-101.93.
[24][意 ]阿尔多·罗西 著.黄士钧 译.城市建筑学 [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37.
[25]同[24].42-43.
[26]同[9].35.
[27]同[9].41.
[28]同[9].38.
[29]Pia Simmendinger.Entwurfsarbeiten aus Rossis Jahreskursen an der ETH Zürich[A].Ákos Moravánszky, Judith Hopfengärtner.Aldo Rossi und die Schweiz Architektonische Wechselwirkungen[M].Zürich: gta Verlag.2011: 55-68.58.
[30]同[29].60.
[31]同[29].62-66.
[32]同[29].64-66.
[33]同[4].78.
[34]Ruth Hanisch, Steven Spier.‘History is not the Past but Another Mightier Presence’: the founding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Architecture (gta) at the Eidgen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ETH) Zurich and its effects on Swiss Architecture[J].The Journal of Architecture.2009(14): 655-686.666.
[35]同[4].80.
[36]同[4].80.
[37]同[4].84.
[38]同[4].89.
[39]同[4].87.
[40]«Materialien eines dialogischen Stadtentwurfs».
[41]同[4].91.
[42]同[4].92.
[43]«Das Berner Stadtbild».
[44]«Die Stadtgründungen des Mittelalters zwischen Genfersee und Rhein».
[45]同[9].37.
[46]同[34].656.
[47]同[34].662.
[48]同[34].662.
[49]同[4].79.
[50]同[4].92.
[51]同[5].105.
[52]同[5].105.
[53]Realismus in der Architektur.
[54]«Un‘educazione realista».
[55]同[9].37.
[56]Bruno Reichlin.Unberechenbar, unnachahmlich//Marcel Meili, Bruno Reichlin, Fabio Reinhart.Viele Mythen, ein Maestro : Kommentare zur Zcher Lehrtigkeit von Aldo Rossi,Teil II[J].Werk, Bauen + Wohnen.1998(85): 37-44.39.
[57]Cameron McEwan.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at IUAV[EB/OL].2011-11-02.https://cameronmcewan.wordpress.com/tag/form/.
[58]同[5].104.
[59]Otto H.Senn.Der Architekt Hans Schmidt; Manfredo Tafuri.Hans Schmidt-ein «radikaler» Architekt; Martin Steinmann, Hans Schmidt: Zur Frage des Sozialistischen Realismu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von Hans Schmidt: Die Wohnung als Gebrauchsgegenstand, Industrialisierung des Bauens, Gesellschaftliche und wirtschaftliche Grundlagen des Neuen Bauens, Modularkoordination in der Architektur, Stadt und Raum[J].Werk.1972(10).548-562.
[60]同[3].11.
[61]Jacques Lucan.Obsessions: Conversation between Jacques Lucan and Martin Steinmann[A].[瑞 ]雅克·卢肯, 布鲁诺·马尔尚 著.姜欣 等 译.凝固的艺术——当代瑞士建筑[M].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8-27.9.
[62]Ákos Moravánszky.Concrete Constructs: The Limits of Rationalism in Swiss Architecture[J].Architectural Design.2007(77).30-35.32.
[63]同[34].670.
[65]同[34].669.
[66]«Die Historie als Teil der Architekturtheorie: Anmerkungen zu neuen Projekten für Zürich, Bellinzona,Modena und Muggiò».
[67]同[34].668.
[68]Tendenzen-Neuere Architektur im Tessin.
[69]«Wirklichkeit als Geschichte.Stichworte zu einem Gespräch über Realismus in der Architektur».
[70]«Das Problem der innerarchitektonischen Wirklichkeit».
[71]同[34].668.
[72]同[56].39.
[73]同[9].38.
[74]同[34].668.
[75]同[2].136.
[76]Analogous Architecture[A].[瑞 ]雅克·卢肯, 布鲁诺·马尔尚 著.姜欣 等 译.凝固的艺术——当代瑞士建筑[M].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44-51.46.
[77]同[2].136.
[78]同[76].47.
[79]同[2].135.
[80]同[61].10
[82]同[76].47
[83]Claude Lichtenstein.Luigi Snozzi[M].Basel: Birkhäuser Verlag.1997: 120.
[84]Pierre-Alain Croset.Luigi Snozzi and Monte Carasso: A long-running experiment[J].Le visiteur n° 16.2010: 122-124.124.
[85]同[83].84.
[86]同[84].124.
[87]同[5].72.
[88]同[5].105.
[89]同[5].103.
[90]«Rationale Architektur und historische Bezugnahme».
[91]同[10].201.
[92]同[22].76.
[93]Herzog und De Meuron.Die Vorteile der Sinnlichkeit//Hans-Peter Btschi, Dolf Schnebli, JanVerwijnen.Viele Mythen, ein Maestro : Kommentare zur Zcher Lehrtigkeit von Aldo Rossi, Teil I[J].Werk, Bauen + Wohnen.1997(84):37-44.42.
[94]同[93].42.
[95]同[10].192.
[96]同[10].203.
[97]同[34].672.
[98]同[1].329.
[99]同[61].8.
[100]同[2].138.
[101]Adam Caruso.Whatever happened to analogue architecture[J].AA Files.2009(59).74-75.
[102]同[4].93.
[103]同[101].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