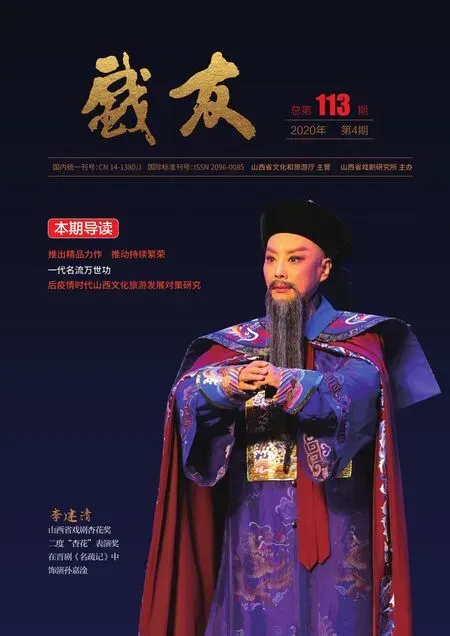沉痛悼念我的良师益友余从先生
郭士星
昨日,从北京传来不幸的消息:我国著名的戏曲史论家余从先生于近日去世。噩耗传来,我十分悲痛!
余从先生是与我多年深交的师友。他是一位学习刻苦、笔耕不辍、不知疲倦的老学者、老专家。多年患有糖尿病,经常带病工作,埋头写作,潜心戏曲研究。这种情况我是早已知道的。前几年,他曾给我打电话,说还想再回山西看看,我一直等待他回来。去年冬天,他老伴任宝林曾给我打过两次电话,一次说余从先生病重,住了医院;一次说,余从先生的病情有所好转,还能想起山西的老朋友。我一直期待着他能早日康复,再回老家与朋友们相聚。没有想到,他竟悄悄地离我们而去,再也无缘相见了!
余从先生原名徐灵寿,余从是他的笔名,余从二字合在一起,即为徐字。1931年出生,祖籍山西五台建安,与五台历史文化名人徐继畲是同族宗亲。他母亲也是五台人,太原理工大学的老校长赵宗复先生是他的舅舅。他多年从事中国戏曲史论研究,是我国著名戏曲史论家周贻白先生的大弟子。他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戏曲音乐学会会长。出版有《戏曲声腔剧种研究》《戏曲史志论集》《余从文选》《中国戏曲史略》(与周育德、金水合著)等多部学术专著。在戏曲声腔剧种、戏曲音乐等研究领域卓有建树。1979年以来,全力投身于全国十大文艺志书集成编纂出版任务,成为构筑“文化长城”工程的主将和大功臣。

余从先生热爱山西,热爱家乡,热爱三晋文化,青年时代就对山西的地方戏曲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在少年时期,曾在晋南上小学,读初中,受过晋南民间艺术、地方戏曲的薰陶。1956年曾随中国艺术研究院张庚、郭汉城等老一辈戏曲专家到晋南参加过蒲州梆子传统剧目鉴定工作,走访过许多名老艺人。并对晋南地区古老的戏曲文物进行过实地考察,曾与蒲剧界老前辈墨遗萍、张俊英、潘尧黄等友人在万荣县风伯雨师庙舞庭发现了写有“尧都大行散乐人张德好在此作场,大德五年二月清明施钱十贯”字样的石柱(这件元代珍贵文物现存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文物陈列馆)。正如他所说:“二十世纪40年代,我在晋南读小学、初中的时期,山陕梆子腔的嫡传剧种蒲州梆子进入了我的生活,我似懂非懂,懵里懵懂地引入了一个戏曲艺术的梦境。从50年代以来,命运带给我机遇,我圆梦了,从此干上了戏曲研究这一行,后来又为戏曲的志书和音乐集成的编纂工作了二十余年。在此期间,晋南成为我向戏曲实际学习、调查研究的基地。晋南的戏曲遗产、蒲州梆子的艺术传统、晋南的师友们,促使我体会到中国戏曲及其梆子腔艺术的博大精深。”(见《蒲州梆子志》序言)。
我与余从先生相识于1980年前后。当时我已由山西省文化厅艺术处调到省戏研所从事戏曲史论研究工作,全国十大文艺志书集成编纂工程即将展开,与余从先生有了更多工作和学术上的接触机会。
1980年前后,为适应全国广大戏曲工作者和戏曲爱好者学习戏曲知识的需要,上海艺术研究所等单位先后组织编纂出版了介绍中国戏曲知识的三种辞书。一种是由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戏剧家协会联合编写的《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一种是由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编写的《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一种是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这三部辞书的编辑部都给山西省戏研所来函,请我们组织作者撰写有关山西地方剧种方面的条目释文。《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还聘请我担任了该书编辑委员,负责组织撰写介绍山西地方戏曲剧种的文稿。为此我曾于1981年、1983年两次赴上海、南京参加该书编委扩大会议。《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全国戏曲剧种的工具书,共收录近代以来流布全国各地的戏曲剧种335个。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全国大多数省市区戏曲研究单位以及许多从事戏曲史论研究的专家学者几乎都参加了该书的编写工作。该书的顾问是资深戏剧家马彦祥、赵景深,常务编委是章力挥、蒋星煜、汤草元、张成濂、黄菊盛。编委共34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戏曲专家。令人高兴的是,余从先生也是编委之一。1981年,我第一次赴上海参加该书编委扩大会议时,就在上海艺术研究所会议室见到了他。他性格温和,学识渊博,讲话心平气和,不慌不忙,虽然是山西人,但会讲普通话,年龄虽然比我大九岁,但长相年轻,气质不老,像一位永远不会变老的老专家。我们与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戏曲研究的专家们一起,结合剧种史,进行学术讨论,对全国各剧种的形成、发展、流布情况、艺术特点、音乐唱腔、代表人物等进行交流、讨论,很快熟悉起来,成为志趣相投、无话不谈的朋友。
参加《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的编写,不仅使我与余从先生彼此熟悉起来,成了朋友,而且以余从先生为核心,与全国许多省市区的知名戏曲专家也都相互沟通,相识相处,成为志同道合的好友。比如,江西的流沙、万叶,浙江的沈祖安、洛地、周大风,山东的李赵壁,陕西的田益荣、杨志烈,河北的谷建东,辽宁的任光伟,福建的林庆熙,吉林的王肯,河南的韩德英,湖北的王俊等等,他们都是《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的编委,通过多次学术交流活动,后来都成了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道友。
江西的流沙先生是专门研究弋阳腔、宜黄腔和梆子腔的大专家。在上海开会认识后,我曾陪他到山西晋城、长治考察上党梆子,又到陕西考察秦腔和同州梆子。有一次我们到北京开会,他将我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汪效倚、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常静之、江西赣剧团的万叶共四人收为他的弟子。在流沙先生指导下,我们在学术上受益匪浅。
1980年前后,为了圆满完成上述三部戏曲辞书的撰稿任务,山西省戏研所决定,动员全省戏曲研究人员,对全省各地的戏曲剧种逐一展开摸底调查,并决定从编写《山西剧种概说》入手,彻底弄清山西戏曲剧种的“家底”。《山西剧种概说》一书的编写,把全省60多位熟悉和爱好山西地方戏曲并有一定写作能力的戏曲工作者都动员起来了。他们查阅资料,找老艺人座谈、访问,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所记剧种的形成年代、源流沿革、流布范围、艺术特点、代表剧目、主要班社、主要演员、唱腔谱例等各项内容按照统一要求,写出初稿。初稿写成后,我们又于1981年4月,组织撰稿人在太原召开了全省戏曲剧种学术讨论会,并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请来余从等戏曲史论和戏曲音乐专家,对全省戏曲剧种进行了认真鉴定,对剧种的发展规律进行了认真探讨,对各篇文章和疑难问题进行了集体讨论,大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宝贝的意见。这次学术会议有两个最重要的成果,一是经过认真论证,初步认定我省有地方戏曲剧种52个;二是对一些小剧种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定名。比如,流布在晋北的戏曲道情,有神池道情、右玉道情、代县道情、应县道情等不同名称,经道情专家武艺民同志从音乐体制、唱腔曲调等方面认真分析研究,认为这几种道情实际是一个剧种的不同流派。这几种道情流布在山西晋北地区,因此统一取名叫“晋北道情”。又如,流布在武乡、襄垣一带的秧歌,当地群众习惯称武乡秧歌或襄垣秧歌,其实,这个剧种是在武乡、襄垣交界地区形成的,是同一个剧种。为了解决两地矛盾,大家商定命名为“襄武秧歌”。
这是我省历史上召开的第一次戏曲剧种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在余从先生指导下召开的。这次会议为在我省开展剧种史研究组织了队伍,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后,我们组织专人对《山西剧种概说》所收编的文稿逐篇进行了修改,这样又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劳动,最后定稿,1984年初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我省剧种史研究的空白,为后来编纂《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创造了条件。此书的编写过程,就是我们对山西戏曲史调查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团结、培养、锻炼全省戏曲研究队伍的过程。《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有关山西戏曲剧种方面的条目释文大都是《山西剧种概说》一书的作者们撰写的。这些作者是我省戏曲研究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余从先生为这支队伍的组建付出了心血。
1983年6月,我被任命为山西省文化厅副厅长,分管艺术教育和艺术科研。上任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主持十大文艺志书集成山西卷的编纂工作,并担任《中国戏曲志·山西卷》、《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西卷》主编。

为了完成文艺集成志书的编纂任务,需要培养一批具有戏曲史论知识的戏曲理论人才。为此,我们在省戏曲学校开设了一个戏曲史论专业班,招收了二十多名有志于戏曲研究的高中生。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该班所须教师大都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戏曲学院等单位聘请。当时余从先生已是全国知名的戏曲史论专家,我们特地从北京把他请来,为该班讲授中国戏曲史课程。同时,也请来胡芝凤老师讲表演课,请朱文湘先生讲导演课,请王蕴明、周育德等老师讲戏曲理论课,请柴泽俊先生讲古戏台建筑课,请韩玉峰先生讲文学课。每次上课,我都坐在教室里与同学们一起听讲。余从先生是专讲中国戏曲史的,他讲得概念清晰,逻辑性很强,他把中国戏曲形成、发展的复杂历史用精炼的几句话就高度概括起来了,讲得脉络清楚,易懂好记,大家都很爱听。此后,我们举办编剧、导演、师资培训等各种戏曲班,大都请他来讲戏曲史。余从先生是《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常务副主编,我是这两部志书山西卷的主编。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山西卷有什么问题也经常向他求教。这样,我们彼此交往,彼此信任,友情日益加深。余从先生治学严谨,为人平实厚道,他不仅在做学问上是我的老师,在个人修养上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余从先生十分关心山西戏曲事业的发展。在他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期间,曾与山西省戏研所于1982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在太原联合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全国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历时20天,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辽宁、甘肃、陕西、山东、河北、内蒙、河南、湖南、湖北等18个省市自治区的戏曲专家学者共120余人。这次会议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对梆子声腔剧种历史的研究,包括早期梆子腔面貌的探讨,对梆子声腔剧种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二是对梆子艺术革新的研究,即梆子戏如何适应时代,改革创新,在梆子戏创作与改革实践中有哪些经验与体会。讨论会共收到学术论文41篇。与会者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了论文宣读、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大家拿出了自己多年从事梆子声腔剧种研究的成果,互相交流,各抒己见,会议开得热烈而愉快。会议期间,结合讨论,观看了各地梆子戏的录像,观摩了山西省晋剧院、太原市实验晋剧团、临汾蒲剧院、运城蒲剧团的演出。讨论会在晋祠宾馆开了13天,11月2日结束了讨论,乘4辆大轿车开赴晋南,用了7天时间,先后参观了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元代戏剧壁画、洪洞大槐树移民遗址、临汾魏村元代戏台、襄汾丁村人遗址和戏曲木雕、侯马金代董墓戏俑、稷山马村金代段家墓戏曲砖雕、万荣飞云楼、河津县汾河湾、解州关帝庙、芮城永乐宫。在运城地区参观期间,恰遇秋雨霏霏,天气骤凉,然而大家游兴不减。人们以极大的兴致饱览了山西晋南丰富的戏曲文物,对山西珍贵的文物资源赞叹不已。

我国著名戏曲理论家张庚、郭汉城先生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了这次会议。张庚先生除致开幕辞外,在会议期间还做了两次学术报告。张先生指出,大家从全国各地来到太原,齐集一堂,本着百家争鸣的宗旨,交流在梆子声腔剧种方面的学术成果,探讨梆子腔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研究各种梆子戏的推陈出新问题,这样的学术活动,是梆子声腔剧种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他说:“戏曲研究由少数专家研究、各省区自己研究,到这次打破省区界限的研究,给戏曲研究划了个新时代,或是里程碑。”张先生在报告中还就从事戏剧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出了具有指导性的意见。他说:“研究戏曲,研究中国文化,除了应当追根溯源,搞清它的历史发展之外,还应当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两种方法,一是历史的方法,一是比较的方法,双管齐下,一个是纵的方法,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它的发展变化;另一个是横的方法,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我们研究的对象是艺术,人们欣赏艺术离不开主观的爱好,这是无法避免也不必避免的。但是我们从事的研究工作本身却是一门科学,是研究艺术的科学,而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凭主观,更不能凭感情上的偏爱来作结论。我们提出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研究的方法,是为了使我们的结论具有科学的可靠性。”张先生还讲到:“研究声腔流变要着重唱腔的分析。把各种不同剧种的唱腔曲调、板式进行比较,研究它们的调式、调性、旋律走向、节奏,研究它们使用的乐器,以及唱词与唱腔如何结合等等,看看这个剧种和那个剧种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亲密,还是疏远,这样的做法是比较可靠的。”他希望搞声腔研究的同志,首先要学会普通乐理和简谱、工尺谱,学会了这些,我们搞声腔研究就像多了一根拐棍,会帮助我们攀越崎岖的道路,化险为夷。张庚先生的第二次学术报告是讲戏曲现代戏问题的。听讲者除参加会议的代表外,还扩大到省城的戏剧工作者。张先生一再强调戏曲工作者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他对戏曲唱腔问题、戏曲语言问题、戏曲现代戏人物塑造问题,以及舞台空间、时间的运用等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的报告内容丰富,说理透辟,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
这次会议,规模大、时间长,给省戏研所乃至全省戏曲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极好的学习机会。我省不少戏曲工作者积极撰写论文,踊跃参加会议。在余从先生的精心筹划和省戏研所领导同志的认真组织安排下,这次会议开得十分圆满成功。通过这次会议,我们与全国各省区戏曲研究机构及戏曲研究人员建立了联系,扩大了交往,增进了友谊,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山西戏研所的声誉,推动了全省戏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与余从先生一起从始至终参加了会议,恭听了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增长了知识,受到了教育,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无比荣幸。
我与余从先生交往三四十年,有许多往事印象深刻,永生难忘。下面再讲四例。
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山西稷山马村、新绛吴岭庄等地的古墓葬中发现了一批宋金元时期的杂剧砖雕。当时《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已开始编写。为了给该书提供图片资料,我曾陪同中国艺术研究院老专家龚和德先生在稷山马村住了一周,依靠该村村民开通地道,安装发电机,将墓内金代戏剧砖雕拍摄下来。有一次我陪同余从先生前往新绛县吴岭庄元代卫家墓考察元代杂剧砖雕(此墓建于元至元十六年,墓内有一块砖雕,上刻两个戏剧人物,脚蹬短靴,形象类似传统戏中的武生)。该墓刚被打开,尚未清理。为了近距离观察人物造型,我和余从先生伏身爬进墓室,两手竟抓出两把尚未风干的人体遗骨。此举虽然令人恐惧,但为了实地考察戏曲文物,余从先生并没有后退。
二、2000年12月8日至16日,由台湾大学、台湾戏曲专科学校发起并承办,在台北市举办了一次“两岸小戏大展暨学术会议”的大型活动。这是海峡两岸的一次梨园盛会。共有大陆5个剧种、台湾4个剧种共9个剧种剧团参加演出,还有大陆的11位专家学者参加学术研讨。我有幸与余从先生一起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可喜的是,我和余从先生一起被安排住在台湾大学外宾招待所。这里环境优美,到处是绿树、鲜花。校园里有一条椰林大道,高大的椰子树,一排排,一行行,耸立在大道两旁,放眼望去一派南国风光。我们天天早晨沿着椰林大道散步,说说笑笑十分愉快。我们一起在台湾大学总图书馆国际会议厅参加了三天十场学术讨论,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我的论文是《谈小戏之振兴》,余从先生的论文是《小戏的特点与演进规律》。12月12日,我宣读论文时,大会由余从先生主持。
这次活动规模大,人数多,很隆重,影响很大。活动期间,我们天天在一起,共同观看9个团的演出,共同参观台北故宫,共同游览美丽的日月潭,共同品尝台湾的各种小吃,共同会见山西同乡会的老乡。在台湾期间,余从先生抽一天时间在台北祭拜了他父亲的陵墓。此时,我才知道他父亲早年去世在台湾。12月16日夜,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彰化县观看了两岸小戏告别演出,于第二天早晨8时半乘坐同一架飞机,回到北京。
三、从2003年7月到2007年9月,在我主持下,我们用四年时间编写出版了我省第一部剧种志《蒲州梆子志》。这部志书是参照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的体例编写的。共分“综述”“图表”“志略”“人物”四大部类。“综述”部分主要是从总体上记述蒲州梆子由孕育、形成到发展壮大的演变过程。由历史写到现状,由蒲州梆子产生前的历史文化背景写到明清两代、建国前后,直至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蒲州梆子的发展变化、艺术成就。“志略”部分主要有剧目、音乐、导演、表演、舞台美术、机构、演出场所、行规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口诀、行话、谚语、戏联等十多项。其中“音乐”部分收入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蒲州梆子各个不同行当代表人物的70多段各具特点的唱腔选段。在“表演”部分除详细记述了蒲州梆子的脚色行当、身段基本功、各种身段和各种特技外,还选择了20多个代表剧目,用文字详细记述了各个剧目中各个人物的舞台调度、心理刻画和表演动作。“人物”部分,突破了“生不立传”的传统编志原则,除200多位已故人物外,还收入了100多位对蒲州梆子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在世人物。除四大部类外,本书还设置了“附录”。内容包括重要的碑文、诗词、评介文章、录音录像资料名单、历次戏曲汇演、评奖名单等等。时间跨度上自蒲州梆子孕育期,下至2004年底。全书共设各类条目1500多条,配图900多幅,总字数为154万。比较全面、客观、系统地记述了蒲州梆子的历史、现状和研究成果,基本反映了蒲州梆子的艺术风貌、艺术形态、艺术特色和繁衍流变的轨迹,是蒲州梆子史上第一部较完整的剧种志。对于抢救和保护蒲州梆子这一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蒲州梆子的繁荣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对于其它剧种志的编写也有参考借鉴价值。
为了保证《蒲州梆子志》的编写质量,我们特别聘请了余从和韩军两位特约编审员。他们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先后三次参加了本志编纂会议,对大部分文稿进行了认真审阅,特别是对“综述”和“音乐”部分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余从先生身体不太好,但出于对山西戏曲事业的关心,他千里迢迢,克服困难,一次又一次地带病从北京前来指导《蒲州梆子志》的编写。除认真审稿外,还将多年积累的编志经验向编纂人员作了深入具体的讲解,使全体编纂人员受益匪浅。余从先生为编纂《蒲州梆子志》付出了艰辛劳动,做出了特殊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四、被誉为“文化长城”工程的全国十大文艺志书集成的编纂工作,从启动到完成历时三十年,参加人数达到十万人。全书共出版298卷400余册4.5亿多字,这是我国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举措,是前无古人的壮举。
2009年金秋十月,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组和中国民间艺术发展中心在北京召开了“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总结表彰大会”。这是我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大盛事。作为这项工程的参加者,我荣幸地应邀进京,在人民大会堂光荣地参加了这次大会,见到了此项工程的挂帅者、94岁高龄的周巍峙老部长,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同道老友,也见到了此项工程的主将——余从先生。我们怀着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共同参观了十部文艺志书集成编纂成果展览,共同回顾了二十多年所走过的艰辛历程,共同在国家大剧院看了庆祝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的文艺晚会,满怀丰收后的喜悦,饱含胜利后的泪水,共同分享了“文化长城”工程全部完工的荣誉感、幸福感、自豪感。当时,我与余从先生已有两年多时间未见了,但是我看见他精神焕发,步履轻盈,依然那么年轻,那么充满朝气。那天,我们与许多老朋友一起交谈,一起进餐,一起合影留念,很晚才回到住地休息。当晚,由于心情激动,我还即兴赋诗一首,贺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
十万大军同出征,十部巨著齐动工。
奋力耕耘三十载,文化长城终告成。
敬谢周公好领导,谦和务实领佳风。
礼贤下士聚英才,攻艰克难自躬行。
风雨难阻老来志,走南奔北忙不停。
今日京都来相会,各路精英诉衷情。
举杯畅饮庆功酒,忆及甘苦泪盈盈。
没有想到,这次聚会,竟成了我与余从先生的诀别。在国家大剧院门前拍的一张照片,也成了我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合影,以后再也没有见面。
余从先生走了,我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戏曲专家,我失去了一位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但是,我坚信,余从先生的艺术成就和他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卓越贡献,必将永载史册,永放光辉!
余从先生安息吧!
2018年7月5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