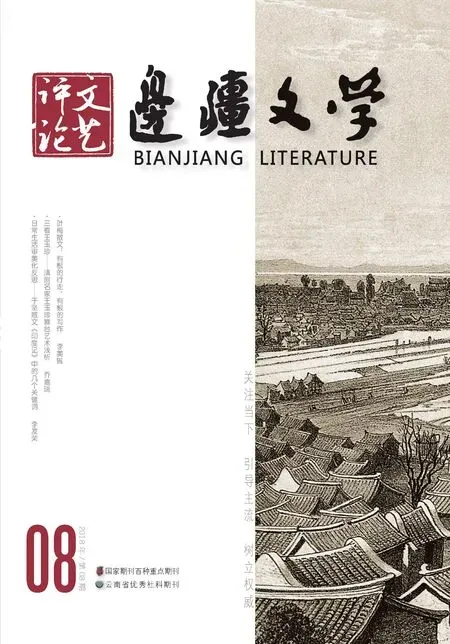唱出边地山村忧郁的歌
——论云南青年诗人王单单的诗歌艺术世界
鲁玉祥
作为中国诗坛上的80后新生代诗人新秀,云南优秀青年诗人代表之一的王单单,近年来引起了诗坛的广泛关注,他从一名云南昭通偏远山村的中学语文教师,依靠积淀多年的诗歌经验与才情,实现了奔袭式的诗坛进军,其创作成就有目共睹。2015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为其公开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山冈诗稿》,全书收录了其创作于2010年至2014年间的一百二十六首新诗,其中包括诗人最引以为傲的诗歌作品《滇黔边村》《病父记》《雨打风吹去》《丁卡琪》《堆父亲》《卖毛豆的女人》《遗像制作》《母亲的孤独》《数人》等,全书分为《晚安,镇雄》《一个人在山中走》《寻魂》和《祈祷》四个小辑。这些重返生活现场的泣血之作,状如延绵起伏的一座座山冈,极富莽撞、原生态、坚硬、柔软、粗粝、细腻的多元质感,向读者全面展示了他虔诚、严肃、坚韧、悲悯、厚重、沉郁的创作风貌。诚然,王单单作为一个气质独特,且正在茁壮成长的新秀,如果仅仅通过一部代表其创作初期成果的首部诗稿做全面的评鉴略显轻浮草率,但毋庸置疑的是,《山冈诗稿》突出了王单单自诗歌创作以来的突出风格与质地。
一
从《山冈诗稿》出版至今,关于解读王单单诗歌主题意蕴、意象解读、语言艺术特色;乡土情结、死亡意识、孤独气质等创作心理机制的评论逐渐呈现出视角多元化的趋势,先后有诸如雷平阳、霍俊明、朱零、灯灯、杨昭、田冯太、朱江、尹宗义、熊炎、魏巍、玉珍、刘年、闫克振、刘汀、蔡丽、方婷、方岩、徐霞、景立鹏、茅草等一批诗人、学者的评鉴。
其中,当首推霍俊明,他指出王单单的诗歌所对应的正是现代性中并不乐观的那一面,他是一个拿着凿子、锤子和斧头在城市和乡村中间地带制作“乡村遗像”和錾刻墓志铭的人。在《“这个来自苦难帝国的异教徒”——论王单单的诗》一文中他指出:“由此出发,王单单有一种‘地方’的‘土气’和癖性,这既是他日常性格的一部分,也是他诗歌的底里,甚至这一癖性在这个诗歌世界中显得不无‘疯狂’‘撒野’。”“他在滇黔‘边地’特殊环境下所塑造的某种躁烈甚至暴动性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象在语言和修辞上迫不及待地迸发出来。他的灼烧、隐痛、荒诞、分裂、叫嚷还有沉默似乎与这个时代达成了空前紧张的关系。他个性化的语言方式所达成的‘精神现实’使得这个时代带有了诡谲和不可思议的寓言化特征。”他层层剖析了王单单在“云南血统”“地方血统”及时代“影响的焦虑”下对日常经验、乡愁、痛感、现代性、底层写作伦理和道德化倾向、诗歌空间开阔等方面所做的可贵而独到的处理。
其次,刘汀对王单单诗歌中的“气”所表现的诗力和独创性的挖掘,“我曾说,王单单的诗最大的特点是有五气:血气、匪气、酒气、土气、烟火气。血气,是他的诗里能尝到一种血液的咸味,质地黏稠,入口即入心,《堆父亲》《数人》是也;匪气,是他的诗里有桀骜不驯的意思,有混不吝的精神,虽打扮成一种豪气,本质仍是。匪气,《晚安,镇雄》《自画像》是也;酒气,乃他诗歌里的江湖情义,乃他人对其诗的浸泡,《在江边喝酒》《将进酒》《滇中狂想曲》是也;土气,是他的诗歌里存着卑微的生命,泥土的潮湿和干燥,日常的挣扎和痛苦,《卖毛豆的女人》《回家》是也;烟火气,是他的诗歌里有最基本的日常,即便那些悬念和形而上,最终仍是落在日常上,而以上诸诗皆有也。这五种气的存在,让王单单在诗坛立足,并且树立了自己的独特形象。”诚然,血气,匪气,酒气,土气,烟火气的杂糅共生彰显出了王单单诗歌得隐沉、凌厉、真实、锐利的鲜明格调。
再是,茅草指出“王单单前期的‘稚嫩’是新鲜的生活、是精神的愉快、是诗意的浓郁,王单单后期的‘金黄’是丰富的内心、是反思的沉重,是语言的闲淡。这种转变,是‘外’与‘内’、‘轻’与‘重’、‘浓’与‘淡’的转变。”而尹宗义则逐一解读了王单单诗歌背后的故乡、爱情、以及超越痛苦之后的“苦楚”;蔡丽认为王单单的诗歌实践了一种真正的透彻人心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贾晓梅在《王单单诗歌创作观念中的乡土情结》一文中认为王单单童年的乡村生活经验使他诗歌创作带上了浓郁的乡土情结;魏巍的《底层苦难的生命书写——读王单单的诗》一文,从《滇黔边村》一诗出发,探讨了王单单诗歌创作中的苦难意识、生命体验、底层抒写、身份意识。闫克振《孤独的自我——王单单诗歌的一个侧面》从王单单的生存场域说开,探源王单单的孤独气质,他认为正是“乡村生活、城市体验,以及放荡的性格、草莽的气质使王单单诗歌散发着浓郁的孤独特质。这种孤独不是哀婉绵柔的憔悴,也不是封闭孤绝的辛酸。它充满了力的爆破和气的升腾,它与金属、高山、旷野、美酒、黑暗相关联,形成了王单单诗歌多层次的孤独书写。”显然,王单单的孤独气质是其放达锐利的诗风根基。无疑,这些评价均反映出了王单单的诗歌在时代语境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独到之处。
二
自带痛感特质的王单单擅将自己的诗歌与一个更为深广、复杂、丰富的情感世界缔结,真实呈现自我的心理现象和情感体验,他的诗歌作为一种自我救赎的渴求和旨归,为其提供着精神的避难所和心灵的栖息地。对于自己数年来诗歌创作的艺术渊源与诗观,王单单有着清晰明确的思量,“诗人就是诗歌的集装箱,同时也是诗歌的搬运工。写完一首诗歌,就卸下了灵魂负重的部分。我怀着为自己写祭文的诚意去写诗歌,每写完一首,都像刚刚赶赴过一场葬礼,完成了一次庄严的祭祀。”“这五年,曾经虚掷时光的狂狷之徒似乎一夜之间醍醐灌顶,懂得人有悲欢,生死无常。壬辰冬末,家父的突然薨殁将我打回原形——骨子里我是一个悲伤的人。有了更多针对生命深层意义的思考,我的诗歌重新返回生活现场,我把命运留给我的痛,分成若干次呻吟。这五年,我的工作从乡村转移到城市,而家人却天各一方,这种在故乡漂泊的无根感,迫使我在诗歌中建立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父亲的薨殁引起了王单单痛苦、愁闷、焦虑的情感体验,这种人生的缺失感和创伤体验极大程度上改变了王单单的诗歌语境,他用这些萦绕着痛感的诗清洗父亲生前纵横交错的伤痕,历数往事为其寻魂,祭奠、超度祖母、伯叔、胞兄,抚慰家族里七零八落、无处安放的亡灵们。
“在我家的院子里,有这样一棵树/果子缀满枝头,每一颗都有自己的名字/比如爷爷、奶奶、爸爸、叔叔、哥哥/将来还会有一颗叫王单单/死亡是一棵树,结满我的亲人/这些年,只要风一刮过/总能吹落几颗/”王单单梦中的这棵“死亡之树”总让他颤栗难安,俨然,这些疾病和生死的困顿,深深地刺激了王单单的心灵和自尊,大量“悲愤”情绪的累积,在家族成员的陆续凋零后肆无忌惮地爆发开来。他诗歌中所郁结的“悲愤”包涵着其内心的苦痛和悲伤,及对社会人生的不满、愤恨的两层意蕴是其诗歌精神的一个内核,也是一种主要的创作动力。因此,为排遣“悲愤”他将诗歌作为了救赎自我的方式:“诗歌让我知道,天藏悲悯,人心向上;诗歌点燃我,让我发出炸裂的声音,让人们听到我背后的寂静;诗歌,让我在生命中最悲痛的时刻,为灵魂找到了另一条出路,甚至曾有一段时间,我把写诗看作上帝救我的一种方式。”
在这样的诗观统摄之下,《病父记》《父亲的外套》《祭父稿》《堆父亲》《遗像作》《自白书》《数人》《死亡之树》《母亲的孤独》《母亲走后》《母亲的晚年》《给母亲打电话》《哥》《守灵夜》等一些诗在着力于对死亡主题、生命阵痛体验的吟唱之余,更多出了一层自我救赎的意味。他以流水、雨雪为肌骨“重塑”父亲,以缝补破碎的心灵,寄予他对亡父绵绵无尽的哀思,以及难以消隐的椎心泣血之痛:“流水的骨骼,雨的肉身/整个冬天,我都在/照着父亲生前的样子/堆一个雪人/堆他的心,堆他的肝/堆他融化之前苦不堪言的一生/如果,我能堆出他的/卑贱、胆怯,以及命中的劫数/我的父亲,他就能复活/并会伸出残损的手/归还我淌过的泪水/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痛一回。我怕看见/大风吹散他时/天空中飘着红色的雪/”在这首由泪水、苦难、伤痛编织而成的《堆父亲》中,“流水的骨骼”“雨的肉身”“红色的雪”这样突破日常经验,扭曲正常,不够真实自然的特异表达方式,最大限度地表达了王单单苦闷、彷徨情绪的真实性,对父亲“救赎”的迫切渴望。
三
王单单的诗极具浓郁的悲悯情怀,其间不仅承载着丧父之痛,也承载着乡村的凋敝之忧。王单单的诗歌自始至终都回响着一个清晰明朗,贯穿始终的声音:返乡。“返乡”情绪作为支配,主导他创作的立脚点、内驱力,尚不能完全归结为他个人主体的声音,生命动能。显然,“返乡”情绪是整个时代所造就的文化语境赋予这个时代的漂泊者、旅居者、乡土诗人听到并极度想传达的声音、袒露的心理症结。在现代性下的城市生存空间里,王单单践行着城市化的乡村写作路径,登高怀旧,怅望故土,踊跃在回乡的路上,守望乡土,为乡村代言。试图通过诗歌揭示“乡土”生活,从而干预乡村生活,介入和反哺“乡土”社会,批判城市化对“乡土”生态系统的破坏,现代性对人的异化。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将人彻底变成了都市生活的奴隶,摆脱心灵牢笼,回归精神的“乡土”已变得亟不可待。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单单诗歌中的“返乡”情绪也是一种以寻觅“诗意的栖居”为旨归的“怀旧”情感的升华,他思乡恋旧的情绪是对“乡土”记忆中的山川、河流、草木、鸟兽、鱼虫的留恋与不舍。他为故土、故我、故人树碑立传,重建自我乡土的目的在于寻求保护、抵御危险,这是一种与时间保持对话的策略。在城市与农村的结合部、夹缝地带,他试图用文字从时间层面、地理层面,社会历史层面,再铸精神 “原乡”,对现代性下的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彰显一种对抗时代洪流的姿态。
王单单不停地游离于“守望者”与“漂泊者”角色两端,寻找平衡的新支点,建立心灵的保护机制,将“返乡”作为治疗时代顽疾的手段,意图治愈精神的荒漠化,寻求内心的安宁,释缓与“故乡”断裂所带来的历史痛感、寂寥感、无根感,并通过“自传性叙述”的言说方式,调整城乡语境中“返乡”情绪的尴尬境遇。对他而言,其“返乡”情绪的释放是一个艰难、苦闷而绵长的过程,面对“乡土”的凋敝、破败的惨景,深受自然灵性熏陶的王单单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孤寂和恐慌:“石头丰胸,饱满而挺立/双乳山就像她的名字/两只奶子突兀在群山之上/只要春天到来,就会把双乳山/挤紧。乳汁,像劣质的饮料/染绿了乳房和她周围的肌肤/可是,双乳山却喂不饱/山脚下那些饥饿的嘴/其实,双乳山也没什么了不起/她只是离天空更近一些,离现代文明/更远一些,离贫穷更近一些/离幸福更远一些/双乳山全年日照不足一百天/海拔高,气候寒冷/山上经常下雨。遗憾的是 /我从来没有看见,哪一场雨/能够洗白双乳山下的黑夜”在这里,“双乳峰”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精神的扎根地、来源地和想象的空间。
在故土难离、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作用力下,王单单的诗歌拥具了崇尚“返乡”主题书写的特质。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乡土”底层社会彷徨的生命个体、焦虑感笼罩的生命状态的关怀忧思,对“乡土”底层人生的痛苦、困惑、迷茫、荒诞性的披露揭示,亦是当王单单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的思想倾向、重要写作纬度。他基于“乡土”世界的“底层写作”已经普遍表现出了强烈而持久的焦虑、苦闷、沉重、疼痛的情绪特征。比方这首痛感萦绕的《采石场的女人》:“把日子扔进碎石机/磨成粉,和上新鲜奶水/就能把一个婴孩,喂成/铁石心肠的男人。她/抬着一撮箕沙,重量/是离她十米远的草堆上/婴孩的若干倍。现在/婴孩像一架小小的碎石机/初来人间,已学会把上帝/反锁在天堂,用哭声/敲碎大地的门/但她暂时顾不上这些/她只知道,石头和心一样/都可以弄碎;她只知道/熬过一天,孩子就能长高一寸/”他在诗中描摹了一个为生计艰难挣扎的女人,不停地榨取自己的生命能量为孩子输送养分的坚韧母亲形象,通过这样的“乡土”创伤图景,痛苦地揭露了被贫富割裂的“乡土”社会多元化的一隅。
从《祭父稿》《雨打风吹去》《晚安,镇雄》《卖毛豆的女人》《采石场的女人》《赵小姐》《401号病房》《哥》《二哥》《申请书》《井》《致童年朋友》《某某镇》《赤水源广场》等诗,他反复置身于贫瘠、凋敝、丑陋的“乡土”世界,面对一幅幅由冷漠、阴暗、残酷、堕落、背德、荒唐、绝望、贪欲构筑成的“乡土”人际关系图景,对异化、颓败了的“乡土”发出了强烈的质疑之声,表现出深刻的焦虑与无所适从的情绪,矛盾复杂的情感常漫溢诗歌的言语间。王单单时常调动“乡土”经验,多次莅临“乡土”社会的底层现场,行文所到之处弥漫着草根民间的厚重感,时间流变造就的隔阂感,沧桑感。他常施以悲悯的回望眼光,俯视底层,重新打量众生百态。诚然,王单单有着清晰明确的诗歌精神向度,寻到了一种精准的、适度的“乡土”的停落方式,开阔的“乡土”世界的观察视角,在“乡土”的创伤性体验中,从传统“乡土”诗歌写作中追寻美好、浪漫、牧歌式的“乡土”旨趣转向黑暗、卑微、羞耻、苦难、困顿的“乡土”现状的写实,不仅复现“乡土”世界坚韧顽强的生存状态,精神的荒芜和物质匮乏,亦揭露“乡土”藏污纳垢的复杂性。
他刻意淡化鲁迅式的“归乡模式”,不再以启蒙者的居高临下的精英姿态批判、拷问“乡土”世界,还之于善良、温暖、平和、哀怜之姿。在面对闭塞、破碎、忧伤、黑暗、充斥着挣扎与彷徨的“乡土”底层社会时,王单单采取了一种在场的叙述方式,其立足“乡土”场域的“底层写作”不仅仅是一种痛苦经验的释放与升华,也是在凭借丰富的“乡土”术语表达着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借助“乡土”的词语序列校准自己的诗学谱系、思维定式、价值准则和审美范式与趣味。他将“乡土”比拟为剧场,用夹杂着泥土气息和血污的笔触,“将乡土人生比拟为剧情,将民间底层的各色人等比拟为主角或者群众演员,在纸上表演着一出有一出的文化人类学大戏。”这些诗歌背后所折射出的是在高度物质化的语境下,“乡土”的疼痛和焦虑。身处“乡土”被边缘、颠覆、消灭的时代,其诗歌中所浸透的人文视野、历史意识、家国情怀,无一不是对“乡土”最后的坚守。
王单单在艺术构思、情感表达、形式选择、词语与意象的组合、灵感与素材的匹配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乡土风味”,这体现在那些立体的、驳杂的、历史化的、寓言化的、象征着“乡土”本源意义的词汇和与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关涉的意象的选择上,土地、山川、沙石、河流、村落、乡镇、小县城、田野、丘陵、老屋、学校、道路、坟墓、寺庙、草木、花鸟、鱼虫、雪花、庄稼、落日、月亮、黑夜、死亡、农民、匠人、货郎、异乡人、流民、打工者、犯罪者等等组成了他的诗歌中最为普遍且体量庞大的“乡土”意象群,这些最根深蒂固且极具标志性的“乡土”意象是其诗歌精神的归宿地,生存的土壤。以“匠人”意象为例,作为最古老的行当、农耕文明的组成因子,“匠人”无可奈何地成了“乡土”即将逝去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只能附魂于诗人在汉语的诗歌国度里为其建造的最后一个的栖身之所。比方《路边的理发匠》中的“这个在别人头上开荒的男人/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春天”的理发匠,他在路边设摊二十多年,从来不问过客的姓名和出处,他沧桑的手上,剪刀飞舞的速度早已赶不上生活的浪潮了,“他所抚摸过的头颅 /有些已身居庙堂之高/有些已埋于黄土之下/剩下余温,烘干他潮湿的眼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在路边/购买他过时的技艺了/就在昨天,他对着镜子/打扫额上堆积的雪花/看见后山长满野草”,这个“理发匠”靠一面镜子一张凳子一把剪刀过完了一生,他在自己建立起的庞大的虚构神坛上,持刀四顾,令万众俯首,最终却淹没“乡土”消隐的浪潮中。
王单单作为以为一个风格多变,富含刚建、清新、朴野之气且比较接近农村现场的云南青年诗人。长于以云南高原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用自己的独有的方式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为乡土生活的原汁原味、风情民俗纪实;在乡情乡音的细致描绘中寻找、言说“乡土”,展示他真诚的乡思乡愁。在故乡的地图上,他摩拳擦掌,挖掘它的记忆,模仿它特有的语气,重组生活经验和材料,并融汇成一张庞大的巨网,捕捞乡愁;同时,他也以农民、民工、流民、商贩的疾苦、困惑为诗歌内容,写出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与愚昧。对他个人而言,云南“乡土”诗歌的淹没性影响,冲突和焦虑张力在他的身上已经得到了短暂缓解,在某种程度上,相比其他的云南青年“乡土”诗人他已经取得了更为实质性的突破。
在诗歌的文本建构过程中,王单单对诗歌程式的小说化践行了诸多的成功实验,如诗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鲜明的小说化倾向。他用小说的技法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过程等多个方面,对“乡土”诗歌进行全面小说化的处理的同时,更加注重诗歌意境的营造。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在对这些诗歌的处理上,作者不停地进行反常规操作,诗歌和小说的程式混搭,刻意模糊文体边界,这种小说叙述内容与诗歌意境两者兼并的写作手法,使得作者和阅读者能够肆意进出两种文本,扩大了诗意的阐释空间。这无疑是他个人创作的又一突破之处。
【注释】
[1][2]霍俊明.“这个来自苦难帝国的异教徒”——论王单单的诗[J].《滇池》,2017年第11期
[3]刘汀.王单单,或他诗中的“气”[J]《诗探索》,2017年第07期
[4]茅草.嫩绿的美,金黄的美——评王单单的诗歌写作流变[J]《中国诗歌》,2015年第07期
[5]闫克振.孤独的自我——王单单诗歌的一个侧面[J]《诗探索》,2017年第07期
[6]李 骞 .王 单 单 访 谈 [EB/OL].(2014-05-04)[2016-06-29].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d7f7d40101h9wq.html.
[7]王单单.山冈诗稿[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8月版,封底语
[8][10][11][12][13][15]王单单.山冈诗稿[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107页,第104页,第101页,第38页,第43页,第30页
[9]何瑞涓.“一滴叛逆的水,与其它水格格不入”[N].《中国艺术报》,2017年07月19日
[14]雷平阳 主编.边疆·第二卷[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