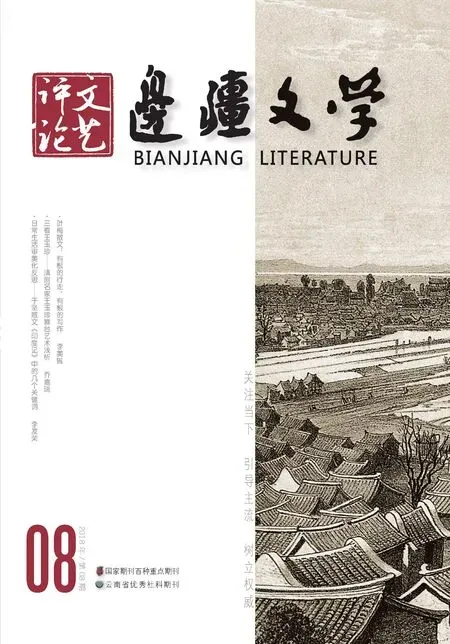《伤痕》在新时期文学的史学意义
李濛濛
卢新华发表于1978年的短篇《伤痕》是讲述新时期文学,甚至整个当代文学史无法跳开且不得不说的作品,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时期文学伊始的“伤痕文学”的命名便是源于《伤痕》,从而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大幕。文学史不是断裂的,《伤痕》除了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之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对于前期文学的反思,对于作家社会责任的觉醒,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伤痕》是新时期文学,甚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无法跳开且不得不说的作品,“不得不说”即是揭示了它的重要性,而这重要性就在于它的文学史意义。命名源于《伤痕》的“伤痕文学”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大幕,而后文学史上繁荣发展的80年代便是紧续着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尽管在整个文学史上有各种分期和不同的文学主潮,但文学史从来都不是断裂的,《伤痕》的重要性便体现在它是前后两个文学时期之间的桥梁,在叩开新时期文学大门的同时,也在对“五四”启蒙文学做着一种并不遥远的呼应,但同时它也是“十七年文学”的某种延续,并且有着“文革”文学的痕迹,可以说是夹在政治与启蒙之间的“回归”。《伤痕》在承前启后的重要性之外,它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启示性,那就是作家的社会责任,这是卢新华从《伤痕》一直延续到今天都不曾抛弃的,这其中还涉及到对于文学的作用的思考。
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压抑已久的人民怀着被解放的喜悦以及强烈的愤恨投入到对“四人帮”的声讨之中。而中国作家长期被压制的创造力和生命活力也迅速喷发,将“揭发和批判万恶的‘四人帮’对我们社会犯下的滔天罪行”诉诸笔端。刘心武于1977年发表的短篇《班主任》便是“最早通过艺术形象来揭露‘文化大革命’给我国人民带来的累累伤痕”,紧接着1978年8月11日还是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于《文汇报》,通过母女亲情的角度来揭露“文革”对于青年一代心灵上带来的巨大的“伤痕”。如果说《班主任》仍是一篇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它所强调的仍是一种外部冲突,那么卢新华则向内转,在整个国民创伤的大背景下,将视角聚焦于最能打动普通人的家庭个人之中,注重于个人内心情感的深刻阐述。小说选取了“母女”这一本应是人世间最温暖最牢固的情感的角度,但血缘亲情却由于政治而退居其后,最终导致母女决裂,天人永隔的悲剧。而正是这一世间最普通的悲欢离合真正打动了所有人,从《伤痕》开始,文学不再是冰冷和硬邦邦的,人情人性的描写使人们真正读懂了《伤痕》。不论是卢新华自己在构思过程中流下的泪水还是成为“复旦校园一大奇观”的“众人面对着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场景”,他们流下的泪水都是真诚的。正因为《伤痕》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伤痕小说”这类暴露“文革”时期对于人们身心带来严重创伤的小说便由《伤痕》而得以命名,紧接着文艺界掀起了“伤痕文学”的潮流。由于小说表达的思想大大区别于前两个文学时期,因此由《伤痕》开创的“伤痕文学”真正开启了“文革”后新时期文学的大门。
《伤痕》在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是连接前后两个文学时期的桥梁,它无疑打破了此前文学的题材禁忌,成为发端之作,但由于它努力冲破旧土壤的性质,使它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此前文学的痕迹。这样从“文革”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转变就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过渡与合理的阐释。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并没有从“文革”文学中真正脱离出来,特别是1977年“两报一刊”提出的“两个凡是”实际上捍卫的是新的极“左”路线。为了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1977年5月在邓小平等人的主持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样的背景下《伤痕》以一种细腻的人情人性关怀适时发表,以文学的形式参与了这场讨论,在文学界冲出了一个新的突破口,在束缚文学的桎梏中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大门,它本身努力挣脱的勇敢和打破禁忌的温暖关怀,真正使它成为了两个文学时期的桥梁。而正是因为它的“努力挣脱”使它不能完全摆脱此前文学的意识形态。《伤痕》小说中对造成父母辈身体以及青年一代心灵上“伤痕”的根源是直指“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的,并且也仅只停留在对“四人帮”的批判之上;以及小说结尾处革命理想式的庄重“宣誓”等等,都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在意识形态上的某种延续,尤其是小说在发表前被要求改动的十六点意见更是体现出文学在政治面前的某种拘谨和局促,这种亦步亦趋和政治性的介入恰是“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特点,但同时也正是这种局限性才为政治和文学的双赢提供了可能,才使得两个文学时期的过渡有了一个合理的借口和缓冲的余地,正因为如此,《伤痕》才能成为众人流泪感动的宣泄口和给予他们情感爆发的理由,用陈晓明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把仇恨记在‘四人帮’的账上,把痛楚留给历史与政治,蒙受着心灵伤痕的青年一代,作为一个受害者而被赦免,并且作为有历史创伤因而也是有历史经验的一代人,有了走向未来的资格和勇气”。这样一来也就完成了政治与文学的双赢局面,这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政治需要的。并且也正是由于它的局限性才给后来文学对于这段历史更加深刻的反思和思考提供了一个已有的平台。于是,《伤痕》承前启后,真正提供了一个合理的突破口和充当了桥梁的角色。
《伤痕》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它对人性人情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五四”启蒙时期。《伤痕》对“四人帮”摧残人性的控诉像极了“五四”时期对封建文化的强烈反叛。在“文革”“三突出”原则指导下,文学描写变得不近人情,没有人性、亲情更没有爱情,人物描写都是远离现实生活的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而《伤痕》对最普通也是最贴近人心的亲情爱情的描写与此前的这些文学形成了巨大反差,它从英雄叙事转到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以及他们内心的情感变化,这种强烈的张力以及贴近人的描写让我们迅速想到“五四”先驱们抛却“阿谀”“陈腐”“迂晦”的旧文学转而描写“平易”“立诚”新文学的火热激情。《伤痕》取材于现实生活,回到生活本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新提倡,那种针对社会弊病的无情揭露,热情干预现实生活的战斗激情可以说都是对“五四”时期一种并不遥远的呼应。
《伤痕》在新时期文学开启了揭露“文革”的先例,尽管它身上带有当时历史的局限性,但正如之前所说正是由于它的局限性才给这种转变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突破口,也正是缘于此才给后来文学更进一步的反思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也就是《伤痕》在新时期文学另一个重要的意义:作家社会责任感的觉醒。《伤痕》发表之后,作家们像受到鼓舞一般相继用笔下的文字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文坛开启了“伤痕”“反思”潮流。更为重要的是《伤痕》体现了新时期文学作家社会责任的觉醒。韦勒克认为“国家无法成功地创立一种既符合意识形态上的要求,又不失为一种伟大艺术的文学”,极权主义给文学带来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他举了苏联文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既然如此,作家的作用就凸显的十分重要。面对“四人帮”对人性的摧残,卢新华觉得有责任也有必要揭露与批判,这是作家的社会责任使之必然的结果,从这一点看,这仍然是对“五四”文学人的觉醒,作家社会责任的觉醒的在时空上的呼应。新文学时期的卢新华如此,直到今天他也依然自觉延续着对时代对社会的责任感。这从他后来发表的《财富如水》《紫禁女》《伤魂》等等都可看出,他的社会责任感从对一时期文学的思考上升到了对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观照,有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揭露,对中国为在努力打开自己走出去所承受的种种艰难的担忧,他的这种对社会的主动关注是从新时期文学始就贯穿至今的。卢新华曾说过“《伤痕》是在泪水中完成的,因为深恶痛绝当时文章的假、大、空,写作过程中,我曾努力要求自己直接师承三十年代作家们真实朴质的文风”,这也是他对自己,对文学负责任的态度。
《伤痕》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泾渭分明的标志,它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足以说明它的价值,现在我们再来重读《伤痕》,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悲悯情怀仍会再次打动我们,我们会怀念从《伤痕》开启的那个文学时代,因为“文学在这个时代里真正地占有了大众”。
【注释】
[1]卢新华《关于〈伤痕〉创作的一些情况——答读者问》,《语文学习》,1978.07.15
[2]朱栋霖 朱晓进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2(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53页
[3]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天涯》2008年第3期
[4]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251页
[5][美]勒内·韦勒克 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刘象愚 邢培明 陈圣生 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08页
[6]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天涯》2008年第3期
[7]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