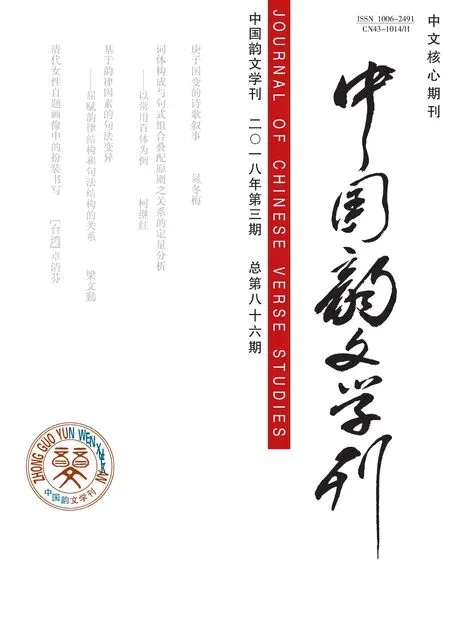庾信诗赋互参的创作方法及评价
袁 丁
(淮海工学院 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庾信高超的文学素养与文学史上的卓越成就,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对其文学创作的方法,尤其诗赋互参的创作特点较少研究。笔者以为文体间的影响与渗透是文体得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庾信作为大文学家,众体兼善,对文体的特点有很好的把握,这为其文体间的相互借鉴提供了可能。因此本文打算从诗赋两种文体发展特点与庾信诗赋创作实际情况出发,探析庾信诗赋互参的创作方法,并从文学史发展角度予以评价。
一 庾信诗歌参用赋体的方式与表现
赋是中国古代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体。因为赋是作家文学才能的重要体现,所以备受后代文人青睐。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方面取得成就的大文学家,多数都是赋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赋的创作成就决定了作家文学创作的高度。由于赋体融知识性与审美性于一体,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需要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与很高审美能力,这本身也为其他文体的创作奠定基础。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庾信的赋学修养的解读,探析其诗歌的创作成因。
庾信在诗歌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除了受其天赋、人生经历等因素影响外,其赋学造诣也是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诗歌中大量用了赋典。庾信诗中大约有22首诗用到赋中故事或是化用赋中语句。如《幽居值春》“长门一纸赋,何处觅黄金”,化用司马相如《长门赋》典故,《长门赋序》云:“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陈皇后复得幸。”《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连云虽有阁,终欲想江湖”,化用曹植《节游赋》“连云阁以远径”,潘岳《秋兴赋序》“高阁连云”“譬犹池鱼、笼鸟,有江湖山薮之思”。《伤王司徒褒》“惟有山阳笛,悽悽《思旧》篇”,则是化自向秀名篇《思旧赋》,《思旧赋序》云:“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这些诗句或是用赋中词句,或是用赋之意,都恰到好处,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
其次,从题材来看,庾信诗歌创作与赋的传统题材有一定相关性。
(一)校猎题材。这是赋中很早就产生的题材,枚乘《七发》中就已经通过丰富的句式变化与绚丽的辞藻,充分展现“至壮”之校猎场面,荡气回肠,动人心魄。枚乘的表现手法也成了后来校猎题材的写作范本。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写狩猎的场面更加惊心动魄。到了扬雄则出现了校猎专题的赋作《羽猎赋》《长杨赋》,对校猎的过程与场面表现得更加丰富。校猎题材在诗中的表现并不多,曹丕的诗中有些残句,张华曾经作过《游猎诗》。到了庾信,用诗写狩猎题材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如《和宇文京兆游田》《伏闻游猎》《见征客始还遇猎》《冬狩行四韵连句应诏》《和王内史从驾狩》《从驾观讲武》等,可以说赋中狩猎题材在庾信诗中得到继承与发展。
(二)宫殿、苑囿建筑题材。这一题材也是汉赋重要题材之一,《文选》中首列都城赋,并设有宫殿类。特别是从东汉开始,都城赋繁兴,其中往往涉及宫殿描写,如班固《两都赋》中描写宫室建筑,空间弘大,境界开阔,语言夸饰,文采斐然。后来以都城为题材的作品,如张衡的《二京赋》,徐干《齐都赋》,左思的《三都赋》等,其中都有对宫殿建筑的描写。同时东汉以来还出现了专门以宫殿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如李尤的《德阳殿赋》《平乐观赋》《东观赋》、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边让的《章华台赋》、繁钦的《建章凤阙赋》、杨修的《许昌宫赋》、何晏的《景福殿赋》等,对宫殿的建筑特点展现得更为丰富生动。庾信诗中也有一些诗作以建筑为描写对象的,如《奉和同泰寺浮屠》是作者梁朝时所作,主要描写了同泰寺的弘大规模。《北园新斋成应赵王教》《登州中新阁》《北园射堂新成》也皆为新建成的建筑所作。
(三)吟咏物象。这类题材虽然不像散体大赋那样以恢弘的气势著称,但其所写皆为生活中的物象,范围十分广泛,在赋体中长盛不衰。汉初梁王文人集团的创作中,就涌现出了一批咏物之作,如枚乘《笙赋》《酒赋》《柳赋》,邹阳《几赋》《月赋》,路乔如的《鹤赋》等。后来这种题材在赋家中吟咏不绝,特别是到了魏晋时期,赋家吟咏生活中的植物、动物、文化用品、科技发明等,品种繁多,还出现了赋家共同吟咏一个物品的现象。这种风气在齐梁时期的文人中得到了继承,并将其融入诗歌的写作中,所以齐梁时期也出现了许多吟咏同一物象的诗作。庾信的诗作中继承了这一传统,出现了一批吟咏生活中物象的作品,如《咏园花》《咏画屏风诗二十四首》《镜》《梅花》《咏树》《斗鸡》《杏花》《尘镜》《咏羽扇》《赋得集池雁》《咏雁》《忽见槟榔》《赋得荷》《春梨》等。
再次,赋对诗歌艺术的影响。题材相同,反映了诗、赋在表现功能方面的融合,同时也为诗歌对赋之艺术的借鉴提供便利。从庾信诗歌创作的总体情况来看,除了篇幅较短的抒情作品,如《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等,其余作品受赋的影响较大。特别是以上所列举的三类与赋传统题材相似的作品,赋化特点表现最为明显。如《奉和同泰寺浮屠》:“岧岧凌太清,照殿比东京。长影临双阙,高层出九城。栱积行云碍,幡摇度鸟惊。凤飞如始泊,莲合似初生。轮重对月满,铎韵拟鸾声。画水流全住,图云色半轻。露晚盘犹滴,珠朝火更明。虽连博望苑,还接银沙城。天香下桂殿,仙梵如伊笙。庶闻八解乐,方遣六尘情。”此诗主要以梁代的同泰寺为表现对象,前六句主要从同泰寺整体的架构出发,展现了同泰寺高大、壮丽,语词夸张,境界开阔,深得宫殿赋以壮笔展现宫殿的皇家气象的品格。后面描写寺中物象特点,将各种物象排比勾连,又深得赋作善于铺陈的品格,而其选取物象的纤小特点,又着实领悟了小赋细腻入微的写作特点。又如《北园新斋成应赵王教》也与上首类似,先从建筑整体结构写起:“虹粉跂鸟翼,山节拱兰枝。画梁云气绕,彫窗玉女窥。月悬惟返照,莲开长倒垂。”后三句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语句“玉女窥窗而下视”“壁皜曜以月照”“反植芙蕖”化用而来。后面描写新斋中的景物亦如上首诗之方法。《登州中新阁》亦以铺陈描写与赋相通:“跨虚凌倒景,连云拒少阳。璇玑龙鳞上,雕甍鹏翅张。千寻文杏照,十里木兰香。开窗对高掌,平坐望河梁。歌响闻长乐,钟声彻建章。赋用王延寿,书须韦仲将。”侈陈物象,文辞雕饰,展现了新阁的壮丽与华美。
庾信有些长篇抒情诗也接受了赋的艺术因素。如他的《夜听捣衣》,写女子为远行的丈夫制衣,寄托相思。这一题材,在赋中最先出现,西汉班婕妤就曾作《捣素赋》。将庾信的这篇诗与班婕妤的赋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夜听捣衣》也融入了赋的表现手法,特别是对于捣衣声音的描写,诗写到砧与杵的材料时称:“石燥砧逾响,桐虚杵绝鸣。鸣石出华阴,虚桐采凤林。北堂细腰杵,南市女郎砧。”突出了捣衣材质出处的独特性,这种写法在赋中写乐器题材中经常出现,如王褒的《洞箫赋》首先就是通过夸饰的手法表现洞箫材料竹子生长环境的独特:“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囚墟……托身躯于后土兮,经万载而不迁。吸至精之滋熙兮,禀苍色之润坚。”马融的《长笛赋》:“籦笼之奇生兮,于终南之阴崖。讬九成之孤岑兮,临万仞之石磎。”庾信对捣衣声音的展现也深得赋之妙韵。班婕妤《捣素赋》对捣素音调变化的表现十分精妙,虽然庾信此诗没有达到那样细致的程度,但是从中亦可以看出庾信试着从不同角度展现捣衣音调的努力。庾信通过三个层面来展现捣衣声音的特点。其一,与琴瑟声调的对比,班赋中也有类似的手法:“含笙总筑,比玉兼金。不埙不篪,匪瑟匪琴。”其二,通过人物心情展现,说明捣衣音调的哀伤,这在《长笛赋》中也有相似的表现:“于是放臣逐子,弃妻离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其三,总体描述捣衣声音的特点。通过三个层次的铺陈,捣衣声音的特点就被生动的表现出来了。
二 庾信赋参用诗体及前后期的不同表现
庾信诗中参用赋体,使得部分诗歌表现出宏壮的境界,获得了与柔弱婉媚的宫体诗不同的气韵。同样,融诗入赋,也改变了赋的体制特点与审美风格。不过,从庾信在梁朝与北朝两个时期赋的创作来看,其赋前后参用诗体的表现又有所不同。
(一)庾信前期参用赋体的表现
庾信早期作品多为宫廷之作,在内容方面比较单薄,但在形式方面十分讲究,并融入了一些诗的品格。
首先,从句式来看,这一时期庾信赋中融入了五言、七言诗句,与赋中常用三言、四言、六言句式连用组织成篇。如《春赋》开头即以四韵七言展现了宜春苑中春色盎然的气氛;然后接以六言或四言句式,叙写春天来临,宫中人物的容貌、活动与具体物象的情态;最后又以七言、五言诗句交互使用的形式,整体勾勒日暮时分曲水游春的场景。《对烛赋》共十六韵,其中四言四韵,三言三韵,五言与七言占九韵,多于传统赋句形式。其中七言、五言与四言交替组合运用,有两处连续用五言、七言,如第一处在赋开头,以三韵七言诗句为赋设置了一个写作背景,营造男女相思的情境:“龙沙雁塞甲应寒,天山月没客衣单。灯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针觉最难。刺取灯花持桂烛,还却灯檠下独盘。”第二处为五言、七言相继使用,每种句式两韵,写烛光的明亮:“烬高疑数剪,心湿暂难然。铜荷承泪蜡,铁铗染浮烟。本知雪光能映纸,复讶灯花今得钱。莲帐寒檠窗拂曙,筠笼熏火香盈絮。”其它还有三处用五言或七言,但均为一韵,与三言或四言交替运用。五言、七言句式的运用,说明庾信赋从形式上吸收了诗歌的特点。如果从功能角度来看,五言、七言诗句与赋的传统句式并无太多特异处,如四言、三言擅长铺陈描写,五言、七言也可以起到相似的效果,就是在节奏方面要舒缓一些。另外五言、七言诗句在赋中往往还具有增强抒情功能的作用,如《对烛赋》开头的三韵七言就通过边塞风沙、孤客衣单的情景,展现了男子远离家乡、战斗边关的凄凉;以女子挑灯制衣的场景,表现了男女相思。虽然整篇赋不以情感表现为主,但给予读者无限的遐想。
其二,庾信赋吸收了诗歌注重韵律的特点,尤其是其中的五言、七言。如《春赋》就十分重视韵律的和谐,其中“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是标准的律联。庾信在赋中不仅能够将五言、七言诗句融入赋的创作中,而且对赋中的各种句式都作了律化处理,将沈约等人提出的音律论融入赋的创作之中,提高了赋的音乐性与节奏感。
在庾信前期作品中,多数篇幅是以咏物、写景为主,通过句式、音律来达到诗化的效果,但是像《荡子赋》这样的作品则不仅用诗句,而且大有熔前代荡子思妇诗作于一炉的感觉。荡子思妇题材在汉末文人五言诗中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一主题在后代诗中得到了延续,如曹植《七哀诗》、陆机《拟古诗》都是对这一传统题材的模拟与再现。但是在齐梁以前赋中很少表现这种题材。而到了齐梁时期,随着诗赋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诗中题材与艺术也逐渐融入诗中,庾信《荡子赋》就是其中代表。《荡子赋》从行文结构、情境设置到语句运用,都可以看到诗的影子。赋首先交代故事背景,从荡子出征边塞、驻守长城写起,并展现了凄冷苍凉的环境。长城意象在诗歌中比较早出现,相传秦代时就出现了《长城谣》,魏代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以朴实的对话体展现了征人建筑长城、妻子独守空房的悲痛。其中“复乃空床起怨,倡妇生离”,则是出自《古诗十九首》:“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赋。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罗敷总发”用的是汉代乐府《陌上桑》的典故。“新歌《子夜》,旧舞《前溪》”用的是晋代的民歌,《晋书·乐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孝武太元中,瑯邪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则子夜是此时人也。”《宋书·乐志》:“《前溪歌》者,晋车骑将军沈玩所制。”从现存的《子夜》《前溪》来看多为男女相思的艳歌,此处主要用以衬托女子对荡子的思念。“奁前明镜不须明”通过明镜意象写征人走后,女子愁情难解,没有心思关心容貌的的情态。魏代徐干《情诗》:“镜匣上尘土生。”《室思诗》:“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 “合欢无信寄”通过生活物象寄托相思,这也是古诗中表现情感的形式,《古诗十九首》中有:“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上尔。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回纹织未成”,回文是诗中一种特殊形式,南齐王融有《春游回文诗》《后园回文诗》,沈约《相逢狭路间》中有“中妇回文织”,吴均《与柳恽相赠答诗六首》中有“书织回文锦,无因寄陇头”,梁元帝萧绎曾作《后园作回文诗》,梁简文帝作有《和湘东王后园回文诗》。这说明回文诗在齐梁时期已经成为文人的文字游戏,并且用回文寄托相思也成为诗中表现情感的方式。庾信用“回文织未成”也正是为了表现男女相思的主题。同时,此赋还注重场景的营造,如“纱窗独掩,罗帐长垂。新筝不弄,长笛羞吹。常年桂苑,昔日兰闺”,通过纱窗关闭、罗帐长垂构成一种封闭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女子徘徊不定,无心弹筝、吹笛,营造了一种寂寥、孤独的气氛。“游尘满床不用拂,细草横阶随意生”,通过场景描写,满床灰尘,细草生阶,无心扫除,衬托了女子心情的失落与孤独。
(二)庾信后期赋参用诗体的变化与表现
生活环境与人生的变化往往是促成作家文风变化的重要因素。从南朝的宫廷走向北朝殿堂,虽然同是宫廷,但是庾信心境变化很大。这也让庾信赋的创作与前期相比,呈现出不同风格。从赋参用诗体的角度来看,与其在梁代相比,也有很大改变。
庾信南朝时候的赋较少抒情,多与诗体相似,展现宫廷生活,情感单薄。赋体形式的变化主要是因为吸收了诗歌在句式、音律方面的因素。而到了北朝,形式方面的追求虽然还有,如学者所辑《愁赋》残篇,从其所写情感来看,应为北朝所作。《愁赋》残篇皆为五言、七言诗句,并且较符合音律。但整体来看,庾信的赋作转向了另一维度,更注重内心情志的抒写,表现出越齐梁而直追诗骚精神的趋势。这意味着庾信后期赋作参用诗体的方法,由师其形式向得其内蕴变化。
庾信由南入北以后,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主要源自其精神境界的升华。同时也与其诗学思想向前代追溯,深得屈原精神相关。庾信《赵国公集序》:“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庾信认为在其之前的文学体式发生了三次变化:第一变来自屈原、宋玉,他们以哀伤为特点,对此我们可以从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也正如刘勰所说:“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第二变则是苏武、李陵,他们以写离别题材为特色。对于李陵、苏武之间的离别,庾信在赞中也予以宣扬。庾信赞体共十三篇,其中人物赞多为历史上的政治人物,作家赞仅李陵与苏武,《哀江南赋》也曾用李陵、苏武典故:“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由此也可以看出庾信对苏李吟咏离别之诗的欣赏。第三变是从魏代建安与晋太康以后,这一时期被庾信认为是“雕虫篆刻”,即注重辞藻的雕琢。庾信对文学史的这种认识反映了他独特的诗学观念,其中第三变实际为庾信在南朝之所为,而在北朝庾信则由魏晋以来的注重雕虫篆刻,向苏李乃至屈宋回归。他在《园庭》诗中云:“穷愁方汗简,无遇始观爻。”《哀江南赋》:“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而这种文学思想,恰可以追溯到屈原“发愤抒情”理论,屈原《九章·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
庾信的《伤心赋》《哀江南赋》就取自《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伤心赋》是哀悼在金陵被侯景占领丧命的子女而作。赋一开头就化用宋玉、屈原之辞:“悲哉秋风,摇落变衰。魂兮远矣,何去何依?”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屈原《招魂》:“魂兮来归,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哀江南赋》更是千古绝唱。屈原之后,以《楚辞》体为代表的赋作多还具有屈原遗意,但是多数作家没有被异族奴役、侵略的经历,更多地关注个人命运,从而淡化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怀。即使像元嘉之乱,也没有出现过像屈原那样将国家命运置于制高点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庾信的《哀江南赋》最得屈原精神。屈原通过比兴寄托、神游虚境的方式叩问生命的意义,反思国家衰败的原因,倾诉个人悲凉身世;庾信则通过史实的叙写,追索梁朝败落的根源,通过人生轨迹的变化,寄托相关之思。他们表现方式不同,笔法各异,反思的程度有深浅,但是同是对家国情怀的展现。楚国的江南,也是梁朝的江南,屈原与庾信这两位文学家可谓异代知己。
庾信后期赋作还表现出意象化倾向,这也是诗歌吸收赋之艺术的一种表现。《邛竹杖赋》取象邛竹杖,实际为作者人生经历的隐喻,从赋最后以两个典故作结可以看出:“岂比夫接君堂上之履,为君座右之铭,而得与绮绅瑶珮,出芳房于蕙庭。”倪璠评曰:“子山本赋杖,而引用好客报仇之事,喻己不能如黄歇豪侠之举,朱履满堂,又不能如崔瑗报仇之后作铭自戒,而悠悠无所用之,仅如竹杖扶老而已。意旨深长,假比发端以摅怀旧之蓄念,非徒赋邛杖也。”《枯树赋》则以树木的繁茂与枯萎象征家国与人生的变迁,寄托家国之思与人生飘零之感。在赋中,赋家将树木的盛衰与人生的变化紧密联系,从而于枯树中寄托了人生飘零之感。钱锺书评论庾信时称:“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赋》《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可谓独具慧眼,一语道破庾信赋学渊源与内在意蕴。
三 庾信诗赋互参创作方法的评价
从诗赋互参的历史来看,在齐梁以前诗与赋两种文体之间就开始互相参用了。但是由于赋体处于文体优势地位,主要表现为诗歌参用赋体,这在魏晋宋诗人中已经有很好的表现。但是赋体很少参用诗体,除了有些文人赋中偶尔会用到五言句式,还有一些俗赋以五言写赋外,其他赋作还是延续传统赋的句式。到了齐梁时期,诗体参用赋体的习惯依然得到延续,但赋参用诗体的情况也逐渐普遍化,并成为赋体变革的重要标志。在这一过程中,庾信是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他与萧纲、萧绎等重要作家一起推动这种文学创作潮流,从而使得诗、赋之间的关系,由以赋体影响诗体为主转向诗、赋两种文体互相影响。这也反映了两种文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从诗赋互参所产生的艺术效果来看,既有好处,又有弊端。其中诗参用赋体与赋参用诗体表现又不相同。庾信诗参用赋体多为宫廷创作,而且在前代赋创作题材相同的诗中表现最为明显,他在田猎、宫殿、咏物的诗作中,将赋典、赋法融入赋中,从而创作出文辞富丽、风格较为雄壮的作品。这与齐梁时期的宫廷诗创作主流——吟风弄月、风格绮靡的作品不同,形成了宫廷诗中另一种独特的风格。但是若与庾信诗中另一类篇幅短小述怀诗相比,这类融赋入诗的作品,又显得缺乏情韵。如庾信的《拟咏怀诗》为诗人由南入北所作,诗人将国家败亡的悲伤、滞留难归、身仕异国的无奈与乡关之思,在简短的篇幅中表现得十分深沉、真挚。这些诗作没有繁富的辞藻与夸饰,但是却以真挚的情感成为继阮籍之后咏怀题材又一经典之作。而在乐府诗歌行体《燕歌行》《杨柳枝》中,庾信则将赋之辞藻富丽、铺排的品格与情感表现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情辞兼备、音韵流转的风格。这说明诗歌在艺术上融入赋体因素,一方面让诗歌的表现艺术更加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诗歌的表现特点,另一方面它也会减弱诗歌的抒情性。但是如果二者能够结合得当,就会使作品同时具备诗、赋两种文体的优势,形成辞藻丰富而又情感深挚的特点。
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庾信这种诗、赋互参的手法也成为后代文人创作的重要方式。当然,我们不能说后人的这种创作方式就是受到庾信的直接影响,但是由于庾信的巨大影响力,至少我们可以说他是诗赋互参这种创作方法应用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诗中参用赋体在唐代得到了继承,对唐诗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赋中参用诗体的情况在唐代也得到了延续。唐初文学创作受齐梁时期影响较大,在赋中参用诗体的现象表现比较明显,如王绩《元正赋》、骆宾王《荡子从军赋》、王勃《春思赋》《采莲赋》、刘希夷《死马赋》参用五七言诗句。盛唐时期的刘长卿《酒赋》以七言为主,杂用三言句式。此外还有赵洽《丑妇赋》,佚名的《秦将赋》《月赋》也参与七言诗句。其中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在题材上与庾信的《荡子赋》相似,只是庾信偏重写女子相思,而骆宾王的赋同时还写了荡子军中生活,有学者曾称赞此赋说:“写得虎虎有神,是现存赋中第一篇描绘边塞征战生活的成功之作。”王勃的两篇赋作与粱代萧纲、萧绎同题,并且也以七言为主,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齐梁赋体的继承,对赋体参用诗体方法的继承。
综上所述,庾信在诗、赋二体方面取得的成就,既源于他对各种文体自身发展脉络的把握,也得益于文体彼此之间的互参与交流。通过文体间的艺术借鉴,各取所长,庾信诗、赋实现自身的突破。庾信的创作实践具有典范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文体间的互参是文体革新的一种方式,对文学史的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