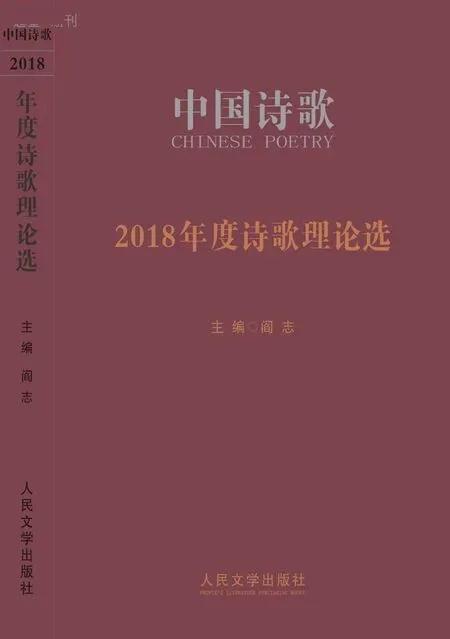现代汉语诗歌的民谣倾向及其启示
甘小盼
民间歌谣是篇幅短小、 以抒情为主的民间诗歌的总称, 实际上由 “民歌” 和 “民谣” 两部分构成。 古人是将 “歌” 与“谣” 分开看待的, 配合乐章来唱的叫“民歌” 或 “民间歌曲”, 不配合乐曲自由吟诵的叫“民谣”。 因不需要合歌而唱,民谣的语言形式, 相对而言更加灵活自由, 也需要有一定的节奏而便于朗诵。 诗歌在历史发展中, 用于吟唱的曲调实际上已经散落了, 在一般情况下只被用于吟诵。 在诗歌革新的过程中, 这种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体裁被运用于新诗的创作, 诗人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实验。
在新诗革新的历史中, 发生了三次歌谣运动。 第一次起始于“五四” 新文学运动。 首先是由于传统诗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格律” 诗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抒情达志的需要。 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白话文的写作, 旧的语言表达方式、 诗歌形式等被打破, 新时代的诗人们寻求一种新的方式发出时代之音, 必然要求新诗打破旧体诗的各种藩篱。 其次是诗人们意图以民间文化的“焕新”成为文学反抗的时代号角, 遂发起了这一场“全民” 运动。 白话文的诗歌写作首先要求形式的革新。 在新诗实验初期, 歌谣以其灵活的表达、 真挚的情感引起了诗人们的注意。 新诗的创作最初就是在本国文化中寻找传统而逐渐发扬光大的。 在这种历史过程中, 一批诗人为新诗的创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并留下了许多精妙的理论建构和经典的文学作品。 新诗的构建是由一批文人完成的, 他们从搜集、 整理民间文化开始, 积极汲取民间文化的养分, 借鉴民间歌谣的表达方式和形式进行新诗创作, 因此, 这些诗歌在韵律和结构方面与格律诗迥异, 实际上仍然是文人的创作。 但是, 这种从民间传统中生发的对现实的转达、 浪漫的抒情一直延续到今天。
诗歌的民间化提出来后, 得到极大的支持, 然而好景不长。二十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文学主张的分野, 文学的“雅俗” 之争出现, 再加上新诗创作初期实践的不成功, 一些诗人开始提出了疑问。 同时, 西方理论的引进, 使民歌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土文化”, 与西方化的主流文化相悖, 民间化的新诗在发展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一些中坚学者投入文人文学的怀抱, 例如周作人和朱自清。 因此, 轰动一时的歌谣运动以失败落幕。
四十年代, 在解放区发生了第二次歌谣运动。 新诗诞生即带有反叛性, 体现在新诗创作的各个方面。 新诗诞生之初, 中国正处于风起云涌的动乱年代,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反映民间疾苦、痛斥时代黑暗成为新诗的主要表现内容, 也是新诗的使命所在。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民歌体诗歌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也在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民歌真正对诗歌创作产生影响与抗战直接相关, 尤其是《讲话》 之后,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解放区政府的支持下, “ ‘诗的歌谣化’ 发展到了极致”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工农兵群众性的新歌谣的创作运动; 另一方面, 组织知识分子下乡采风, 搜集整理民间歌谣。 在这种情形下创作的诗歌有明显的目的性与政治色彩, 民歌体长诗是解放区文坛对政治话语的响应。 《讲话》 之后, 郭沫若、 周扬等学者大声疾呼开展新民歌民谣的征集与创作活动, 一批诗人们更是在吸收、 借鉴当地民间文化的基础上, 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 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阮章竞的《漳河水》、 张志民的 《王九诉苦》、 田间的《赶车传》 等。 这些长诗诉说现实生活, 地域性、民间性色彩浓郁。 诗人们大都借鉴当地民歌, 大胆采用方言, 灵活变换结构, 塑造了一批经典的文学形象, 唱响了时代之音。
第三次歌谣运动发生在建国后, 是在毛泽东的提倡下发起的一场诗歌创作运动。 诗歌的民间化没有止步于政治的宣传, 围绕着新诗的讨论, 也没有停息。 新中国成立后, “新诗该如何发展” 依然是诗人们关心、 探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 中国作家协会曾于1953 年底到1954 年初召开三次诗歌形式座谈会,报章、 杂志也对此表示了足够的关心。 这些讨论虽然没有为新诗的发展做出最后的定论, 却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于是诞生了这场“新民歌运动”。 在这声势浩大的“诗歌大跃进” 期间, 全国掀起了热烈的民歌搜集和民歌体诗歌创作的热潮, 上至中央, 下至地方, 涌现了数量巨大的“诗人” 群体。 这些诗歌极度突出理想和豪情, 运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 却严重脱离了时代的生活真实。 新诗在这种极度膨胀之下走入极端, 对诗歌的真正创作产生了不利影响, 再加上接踵而至的大饥荒, 轰轰烈烈的民歌运动宣告落幕。
蝴蝶振翅, 采言民间
新诗歌运动是随新文化运动开展的, 诗歌的破旧迎新就是从语言和形式开始的。 这场诗歌运动由知识分子主导, 他们深入民间搜集民间歌谣, 并广泛借鉴民间文学的养分, 以求探得新诗发展的道路。 因此, 在歌谣运动伊始, 由文人们主导的诗歌革新还是以文人文学为中心、 向民间取法的诗歌运动, 以文人创作为主采用民间歌谣的形式和语言特色。 刘半农不仅是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同时也是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奠基人。 在新文化运动中, 胡适和刘半农都十分重视语言在新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胡适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 刘半农从语言本身强调语言的本体意义, 他对诗歌韵律的重改在诗歌发展中举足轻重。 刘半农重视民间语言的审美性, 他说: “它的好处, 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 把最自然的情感抒发出来。”、 “而这有意无意之间的情感的抒发, 正的的确确是文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唱歌的人, 目的既不在于求名, 更不在于求利”, 在歌谣中“往往可以见到情致很绵厚, 风神很灵活, 说话也恰到好处的歌词” (《国外民歌序》 )。 刘半农从文学性出发, 着力挖掘民间语言的审美特点, 截取其中的自然、 轻快、 活泼, 表达深厚真挚的情感。 在实际的运用中, 这种独特的抒情方式被大量运用令人耳目一新。 刘半农提出了重建新韵的三点主张: “ (一) 作者各就土音押韵、 而注明何处土音于作物之下。 此实最不妥当之法。 然今之土音、 尚有一着落之处、 较诸古音之全无把握、 固已善矣。(二) 以京音为标准、 由长于京语者为造一新谱、 使不解京音者有所遵依。 此较前法稍妥、 然而未尽善。 (三) 希望于‘国语研究会’ 诸君、 以调查所得、 撰一定谱、 行之于世。 则尽善尽美矣” (《思想的声音——文化大师演讲录》 )。 刘半农设定了三个步骤, 从土音到京音, 最后“定谱”, 这是他对于音韵的设想,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实践。 他自觉地运用民间语言, 发掘其审美性, 赋予其诗性特征。 他的不少诗歌深得民歌民谣自然亲切的韵味, 音调上汲取了民歌讲究重复、 一唱三叹的特征。 以《教我如何不想她》 为例: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啊! /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 /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她? / /枯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 /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 语言直白轻快, 意象贴近生活, 像“云”、“风”、 “燕子”、 “鱼” 等。 接近口语的表述, 和口语中常用的语气词“啊” 的重复使用, 在看似平白的语言中流淌着月光似的柔情。
在新诗写作的音乐问题上, 刘大白也谈到过对音韵的重视。在论及闻一多诗歌的用韵问题时, 他谈到: “咱们要反对在纸面上已经死去了的死诗韵, 咱们要用那活在口头上的活诗韵。 在这个条件之下, 自然最好用国音的韵。 但是各处方音的韵, 只消现在活在口头上的, 也不能一律禁止。 咱们如果搜集起民歌来, 他们所用的韵, 差不多大多数是方音的。 咱们不承认民歌是现代的活诗篇便罢; 要是承认的话, 那么, 用韵的条件便不能太严。 所以咱们用韵的条件, 只是要用现代的活诗韵, 便是最好国音韵,其次方音韵。” ( 《读评闻君一多的诗》 ) 刘大白主要是从音乐性的角度对诗歌的音韵做出比较视野下的分析。 “诗” 与“歌” 原本是密不可分的, 刘半农和刘大白都是在这样的历史下深入对诗歌音乐性的探索, 某种程度而言, 这也是一种“返古” 的倾向。在文人诗歌的创作中, 诗歌逐渐显示其独立性而与“歌” 相分离, 但在民间, 民歌自不必说, 民谣仍然具有相当的音乐特质——例如其节奏感和音乐感。 刘大白从音乐性的角度, 将诗歌分成三类: 一, 歌唱的诗篇; 二, 吟诵的诗篇; 三, 讲读的诗篇。他还总结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十种音乐规律(参见《刘大白研究资料》 )。 刘大白总结的诗歌的音乐性规律已经相当系统完备,并可以运用到新诗的实际创作中。 以《卖布谣》 为例: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卖布买米, /有饭落肚。 /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小弟弟裤破, /没布补裤。 /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是谁买布? /前村财主。 / /土布粗, /洋布细, /洋布便宜, /财主欢喜。 /土布没人要, /饿到了哥哥嫂嫂。” ( 《声乐曲集·卖布谣》 ) 诗歌由结构相似的四个小节组成, 每节句尾押韵: “布”和“肚”、 “布” 和“裤”、 “布” 和“主”、 “细” 和“喜”, 押韵全在韵脚, 这种押韵方式在古典格律诗中常见, 在民间也是常见的。 刘大白的诗歌几乎都是在音乐性上独辟蹊径, 一方面令人惊叹于其深厚的文学修养, 一方面折服于其对音乐的熟谙。 他的诗作通俗易懂, 像极了民间流传的短小歌谣, 常常被谱曲传唱。这首《卖布谣》 即由赵元任谱曲, 还有刘雪庵谱曲的《布谷》,有些诗歌还被配上了外国的名曲, 如以贝多芬的《土拨鼠》 配乐的《卖花女》 等等。
“五四” 新文学时期对语言的改造, 主要在寻求新的韵律感和押韵方式, 诗歌的押韵, 大体也就这两种——通行的汉语普通话的音韵和方言韵。 方言押韵并不是从新诗运动开始的, 在古体的格律诗创作中就有许多案例, 在新诗运动中, 这种押韵方式被提高到理论层面指导诗歌创作是新诗运动的一大贡献。 到四十年代, 诗歌的创作不仅在押韵方面多有注重, 更突出地表现在对方言的借鉴与处理。 解放区在《讲话》 的号召下开展的歌谣运动是新诗与民歌民谣的真正结合, 在语言上突出表现为对方言的大量运用与灵活变通。 此时涌现出的杰出的作品在语言上无不具有这种特色—— 《王贵与李香香》 对陕北方言的应用; 《漳河水》对太行山地区方言的借用; 张志民写《王九诉苦》 时, 将诗歌念给农民听, 也正说明了诗歌的语言采自民间、 贴近民间。 同样的, 田间的《赶车传》、 李冰的《赵巧儿》 也都是如此。 虽则都是大胆采用民间方言进行再创造, 但作者对这些语言的处理都保留了各自的风格。
解放区民歌体对方言的运用, 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对方言中词语的运用。 如李季在《王贵与李香香》 中大量使用陕北方言, 方言的意味在诗歌中十分突出。 例如在构词中经常加上词头“老、 阿、 第”, 或加上词尾“子、 儿” 等; 擅长使用重叠的字词, 如“绿苗苗”、 “嘶啦啦啦”、 “红艳艳” 等; 对词汇的选择也十分有“乡土味”, 例如王贵与香香结婚时说的一句“半夜里就等着公鸡叫, /为这个日子把人盼死了!” (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 再比如香香送参加革命的王贵归队时说的“沟塆里胶泥黄又多, /挖块胶泥捏咱两个; /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 /捏得就像活人脱。 /摔破了泥人再重和, /再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 /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捏完了泥人叫哥哥, /再等几天你来看我” (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 其中没有意义的“来” 字的使用, 是借鉴了陕北地区民间口语的说话方式, 自然贴切。 “哥哥”、 “妹妹” 之间的爱情诉说方式是我国民间文化中的一大特色, 作者借“哥哥”、 “妹妹”、 “捏泥人”的诉说方式, 既是取材于民间, 糅合了民歌民谣中典型的抒发爱情的方式, 又通过“捏泥人” 这种方式将两个爱人之间缠绵的深情表露了出来, 真挚动情。 二是叠词的使用。 李季在诗歌中保留有大量的原始的方言符号, 保留了原味的方言是他的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 同样大量借用方言的阮章竞在其《漳河水》 中还表现出古典诗词的韵味。 如诗歌开篇的《漳河小曲》: “漳河水, /九十九道湾, /层层树, /重重山, /层层绿树重重雾, /重重高山云断路。” “清晨天, /云霞红艳艳, /艳艳红天掉在河里面, /河水染成桃花片, /唱一道小曲过漳河沿。” 阮章竞在《漳河水》 的写作中灵活借用了流传在漳河两岸的多种民谣形式《开花》 《四大恨》 《漳河小曲》 《牧羊小曲》 等, 加以改造, 使诗歌中的叙事和抒情显得更加自由灵活。 他选取地方有代表性的意象, 如“漳河水”、 “艳艳红天”、 “漳河沿” 等, 大量使用叠词“层层”、 “重重”、 “红艳艳” 等, 非常活泼。 三是对谚语、俗语的灵活运用。 对民谚俗语的运用, 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直接运用, 插入诗行中, 或者直接从民间谚语中生发。 刘半农的《瓦釜集》 拟民歌的新诗创作中, 部分诗歌就是根据江阴谚语而作。 例如《只有狠心格老子呒不狠心格娘》 就是根据谚语“只有狠心格老子呒不狠心格娘” ( 《胡适、 刘半农、 刘大白、 沈尹默诗歌欣赏》 ) 而创作的。 全诗四节, 每节以“只有狠心格老子呒不狠心格娘” 起首, 循环往复, 有一唱三叹的效果。 此外,还有一些诗歌保留有原始的民间谚语, 如《瓦釜集》 第十九歌中“山歌好唱口难开, 樱桃好吃树难栽, 白米饭好吃田难种,鲜鱼汤好吃网难抬”, “山歌好唱口难开, 樱桃好吃树难栽” 就是民间劝谏劳动的民谚俗语, 不独在江阴, 在很多客家方言区、湖南甚至到云南都收录有这两句民谚。 另一种是对民间谚语或俗语的改造。 李季在《王贵与李香香》 中“手扒着榆树摇几摇, /你给我搭个顺心桥” 就是对民间《信天游》 中“手把上榆树摇几摇, /你给我搭个顺心桥” 的改写。 这样的例子在李季诗歌中非常常见, 他在借鉴民歌中加入了知识分子的思考与选择, 因为“信天游” 民歌中对同一种感情的抒发或咏唱往往有几种甚至几十种, 其艺术性和思想性往往良莠不齐, 这样的情况也要求诗人们做出甄别与改造。 四是对民间歌谣的灵活处理。 阮章竞的民歌体长诗几乎都以“小调”、 “小曲” 开篇, 《漳河水》 中开篇即《漳河小曲》, 又以《牧羊小曲》 结尾。 正如作者所说,《漳河水》“是由当地的许多民间歌谣凑成的”(《漳河水·小序》)。 诗歌采用民间小曲的形式, 辅之以民间歌谣的语句, 结合了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句法, 因此诗歌虽然由口语化、 民间色彩浓厚的语句组成, 却蕴含了古典风情, 不似民谣的简单, 渲染了富有诗意的意境, 更有韵味。 《王贵与李香香》 中对“信天游” 的借鉴与改造也是如此。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 早期的诗歌民间化探索者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刘大白在《中诗外形律详说》 等著作中,系统地总结了中国诗歌的音乐性的规律, 他本人也正是从诗歌的音乐性为切入点进行诗歌的创作, 他的很多诗歌甚至被谱成曲传唱。
信天而游, 古体新用
新诗向民间“取经”, 重点体现在语言与形式两个方面。 自新文化运动始, 要求打破格律诗的“镣铐”, 要求自由的格律与形式以便于更好地抒情就是新诗最初始、 最基本的要求。 一些早期的白话诗人热衷于从民间文化的土壤中汲取养分, 借鉴民歌民谣的表现方式, 建构新诗的形式结构, 如刘半农、 沈伊默等。
(1) 散文体。 第一次歌谣运动中, 新诗仍然存在着“格律化” 与“非格律化” 的讨论, 不论如何, 诗歌实际上仍朝着更加自由化的形式发展着。 民歌散漫、 自由、 活泼的形式对诗歌产生着影响, 深厚的文学传统也并未就此退出舞台。 文人们即使搜集民歌, 仿民歌体进行创作, 严谨的古典格律诗仍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在形式上表现出既是自由的散文体, 也有大量形式齐整、句尾押韵的作品, 而在民间方言的介入和口语化的表达下, 也有一些十分散漫的诗作。 刘半农仿家乡民歌四句头山歌的曲调, 用江阴方言创作新诗六十多首, 并编选其中18 首拟民歌出版《瓦釜集》。 这些诗歌常带有强烈的叙事色彩, 又夹杂有民歌一唱三叹的回环往复的结构, 在结构上并非都是四句一小节, 每行诗的字数也都不同, 在结构形式上更加多变。 刘半农的《瓦釜集》叙事意味很强, 因此结构、 句式的安排完全是以叙事的抒发为主, 有的齐整, 有的参差, 有的一句七言或九言, 有的一句能有十个甚至二十多个字, 全凭所述内容而定。 如第四歌《姐园里一朵蔷薇开出墙》, 这是一首情歌, 全诗一节四句, 每句十言、十三言、 十六言、 十六言。 类似的诗作还有不少, 但这些诗由于对口语的直接使用, 有的句式长一些有的短一些, 恐怕不是作者的精心安排。
(2) 问答体。 问答体诗歌很明显地借用民歌形式的结构,由一人发问, 另一人回答, 在一问一答中以主人公自述的叩问交代事情始末或缘由。 《瓦釜集》 第七歌《隔壁阿姐你为啥面皮》就是一首问答体的叙事诗, 全诗共四节, 首句一女工问“隔壁阿姐你为啥……” 另一女工答“你阿姐勿晓得我……” 在一问一答中倾诉隔壁阿姐的苦难生活, 进而揭露社会黑暗与平民困苦。 问答体在民歌中尤其是山歌对唱中出现得比较多, 如《刘三姐》 和湖南、 云南地区一些具有临时性质的山歌对唱, 就是这样的形式。 整体而言形式是比较齐整的, 每一小节的结构是相同的, 在相同结构下每一句的字数基本一致。 这种结构的好处在于它比较齐整, 要求语言的选择和字数的控制, 并且一问一答可以循环再循环, 一联联接下去。 新文化运动早期的诗歌在音韵和语言上有较大的变化, 形式结构相对显得有些平板。 与此相对,四十年代解放区的民歌体长诗不仅在语言的使用上沿袭了对民间口语、 方言的借鉴与改编, 在形式上也取法民间歌谣, 更为多变与灵活。
(3) 信天游体。 结构的变化是诗人们向民歌学习的重要成果。 在诗歌的民谣化倾向中, 诗人特别注重诗歌创作对民歌民谣在形式上的借鉴与改造, 成功的民歌体新诗在形式和语言上尤其注重。 在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中, 民歌体长诗的成功, 与其民谣化的形式结构有重要关系, 尤其对陕北民歌“信天游” 的学习和借鉴, 具有典型的意义。 信天游是陕北地区特有的一种民歌,具有特殊的形式: 每两句诗组成一个诗联, 固定不变; 一首诗可以是一个诗联或两个、 三个、 四个以至多个诗联, 长短自由; 每一行诗一般是五言、 七言、 九言或十一言, 交错使用, 大致保持形式严整, 音节均齐( 《新文学开拓者的诗歌艺术》 )。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 在语言上使用陕北方言, 在形式上更是借鉴了极具陕北特色的信天游民歌。 诗人自称, 他亲自收集并深入研究过将近三千首信天游民歌, 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丰富的源泉。 信天游的句式十分灵活, 两句一组, 常常上句比兴, 下句叙述: “一句话来三瞪眼, /三句话来一马鞭! / /狗腿子像狼又像虎, /五十岁的王麻子受了苦。 / /浑身打烂血直淌, /连声不断叫亲娘。 / /孤雁失群落沙窝, /邻居们看着也难过。” ( 《中国新诗百年大典·第十卷·王贵与李香香》 ) 李季对民间文学的汲取是多方面的, 他的叙事诗的形式主要来自民歌和民间说唱文学, 在对形式的借用中有直接取用, 也有创造改编, 针对不同的叙事特性和讲述素材而选择风格各异的形式结构。 《王贵与李香香》 重点在传述事件, 于是借用信天游畅想天外、 诗联无穷的结构形式, 两句一联, 有比兴有叙述, 有写实有抒情, 将故事的结构与叙述的主体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杨高传》 中, 作者树立了高大光辉的革命者形象, 在形式上则基本采用“四三、 三三四、 四三、 三三四” 的句式和节奏, 根据叙事的需要, 句式时常变化, 并不是固定的“四三、 三三四” 句式, 相对齐整的四句一节的结构也是多见的, 但也有插入的“小曲” 两句一节。 三四句一节的结构形式配之以句尾的押韵, 整首诗具有鼓词意味, 句尾韵脚又常是开口呼, 形成了一个个“鼓点”, 渲染了激奋而又富有动感的情绪, 更有力量感, 更便于高昂情感的表达, 不再是两句一联的灵巧歌唱。 “不唱姊妹领棉花, /这一回唱一唱三边风光。 /这本书说的三边事, /该讲讲三边是什么地方。 / /人说三边风沙大, /终日里雾沉沉不见太阳。 /这话是真也是假, /没风时沙漠风光赛过天堂。 / /平展展的黄沙似海浪, /绿油油的草滩雪白的羊。 /蓝蓝的天上飘白云, /大路上谁在把小曲儿唱。” ( 《李季文集·第一卷·杨高传》 ) 《杨高传》 与《石油大哥》 体现了诗人对民间歌谣的又一种探索。 在诗歌创作中, 诗人不以某一具体的民歌形式作为借鉴主体, 而是以歌谣的普遍性特征作为借鉴对象, 将民歌的章法与古典诗词的句法相融合, 创作出来的诗歌不仅具有民歌的活泼, 还有古典诗歌的情境( 《论李季的叙事诗创作》 )。 无独有偶, 阮章竞在《漳河水》 的创作中同样是将民间歌谣与民间戏曲的结构相互借鉴、 交融, 使诗歌既具有民歌的轻快, 也有戏剧结构的全局统摄, 在叙事上别具一格。
万花一筒, 百态一诗
民间歌谣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在语言和形式上最为明显, 但诗人们对民谣的取法是多方面的, 不仅表现为对方言和民谣形式的活用, 民间歌谣在叙事、 抒情主人公的塑造方式、 传情达意的手法、 所歌颂的主题等方面对诗人们的创作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民歌民谣进入诗歌, 扩大了诗歌的表现范围, 拓展了诗歌抒情达意的方式, 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活泼灵动的血液。
(1) 革命主旋律。 民歌对新诗创作的影响, 最明显的就是内容(主题、 题材) 的置换, 突出表现在长篇叙事诗的高度发展上。 解放区的诗歌以叙事长诗为主, 其表现的题材也是民众喜闻乐见的、 最贴近生活的。 在新诗的民谣化中, 由于诗人们抱着“向下” 的创作姿态, 作者们自觉地选择普通民众最容易、 最愿意接受的内容; 同时, 出于知识分子的修养、 爱国情怀的具体化和政治的要求, 表现生活事实、 讴歌共产党的领导、 表达纯真的爱情和歌颂新生活成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旋律。 对主题的表达有明显的时代分段特征, 这是由特殊的社会背景决定的。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 民谣化诗歌以反映民生疾苦为主题, 如刘大白《卖布谣》 中对贫富差异的表现; 抗战时期, 以阶级斗争和抗战为表达主题, 如《赶车传》 《王贵与李香香》。 这一时期著名的作品故事主题并不单一, 常是两个或多个主题共同出现在一部长诗中, 多为“革命+爱情”、 “斗争+爱情” 等, 因为爱情故事是长盛不衰的文学母题, 在民间文学中尤为如此。 《王贵与李香香》 就是典型的“革命+爱情” 模式。 长诗以刘志丹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时代背景, 反映了死羊湾农民反抗地主迫害的斗争,并描写了王贵与李香香在斗争中萌发的坚贞爱情。 其他的一些典型的民歌体叙事诗, 基本上也是这种结构和这种模式。 将个人命运与革命相联系, 将民间歌谣和戏曲中“情人历难而团圆” 的模式变为“在革命(与爱情) 的考验中成长为新人” 的革命诗歌的模式(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
(2) 卡片式的人物。 在整个新诗的创作中, 作者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比较单一的卡片式人物, 一方面是由于诗歌体裁的限制, 一方面是因为诗歌重抒情而不注重刻画人物。 不同于作家文学的个性化书写, 民间文学中的人物性格一般都比较单一, 是典型的“扁平人物”, 重点突出人物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种性格,而将其他的侧面淡化或干脆不写, 向民歌学习的诗歌也具有明显的民间叙事的特征。 王贵与香香是作者塑造的正面人物, 着重表现了二人性格中的正义、 刚强与坚贞。 王贵面对地主的折磨与暴行选择反抗与革命, 香香虽是女性却不脆弱, 勇敢地加入游击队打击土豪劣绅, 两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获得爱情的满足, 正符合广大群众对故事圆满结局的希望。 王贵与香香这两个人物, 也以正义、 勇敢、 坚贞的单一形象展现在读者和听众面前。 阮章竞在长诗《漳河水》 中塑造了三个女性形象, 代表了三种性格和三种命运——大胆泼辣的荷荷、 憨厚热情的苓苓和善良软弱的紫金英。
(3) 比兴的手法。 比兴手法是所有民歌民谣的共同特点,相对于文人创作的文学气质, 民间歌谣对比兴的应用更加灵活,所选取的意象更加具有地方特色, 所抒发的感情更为质朴。 比兴手法在“信天游” 中尤为突出。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是“信天游” 中经典的唱词, 主要是用来表明歌颂对象的美丽。 “山丹丹” 即山丹, 是一种细叶百合, 主要生长在中国北部地区, 长于山坡, 因其花色鲜红、 生命力极强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山丹鲜艳明亮, 常被用来比拟美丽的少女(一般也是吟唱者爱慕的对象), 因此,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一句后一般紧接着对少女的描写, “香香人材长得好”, 就紧接了这句。 香香(少女) 的美丽, 在“山丹丹” 的比兴中以极少的词语表现出了强烈的视觉效果。 比兴的手法不仅在人物描写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抒情叙事中同样如此。 阮章竞在《漳河水》 中有大量的比兴描写,例如: “河边杨树根连根, 姓名不同却心连心”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 以杨树根茎相连比喻三个少女心意相通、 命运相连, 十分贴切; “断线风筝女儿命, 事事都由爹娘定” (同上),以“断线风筝” 比拟三个少女伶仃无定的命运。
(4) 脉脉的抒情。 民间文学的突出特色在于杰出的叙事,叙事手法也作为民歌民谣的重要成分而被众多诗人吸收。 随着诗歌的不断发展与对民间歌谣借鉴的不断深入, 具有明显民谣倾向的诗歌不再局限于叙事, 同时发展了民歌体抒情诗, 重要的代表有阮章竞和贺敬之。 阮章竞最重要的作品《漳河水》 在叙事外萦绕着悠扬婉转的情绪表达, 作者主要借助情景相生的表现手法在叙事与写景中抒情, 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 表述人物心情。 在父母包办婚姻下, 苓苓、 荷荷和紫金英三人婚后并不幸福, 作者没有直接描述婚姻的不幸, 而是先写三人相聚, 在漳水边哭诉婚后的苦楚: “三人拉手到漳水边, /眼泪忽忽落衣襟。 /桃花坞, /杨柳树, /漳河流水声呜呜。 /漳河流水声呜呜, /荷荷啜啜诉冤苦。”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 这棵杨柳树见证了三人畅想婚姻时的少女情怀, 此时又见证婚姻给她们造成的磨难, 物是人非的悲戚之感由此蔓延开来, 情绪饱满, 又有节制。
将民歌体新诗向抒情方向发展的还有贺敬之。 贺敬之抒情类民歌体新诗的特征突出表现在对叙事的打破和对抒情境界的拓宽上。 贺敬之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分为两类: 抒情短诗和政治抒情诗。 他的抒情短诗往往具有民歌和古典诗词的韵味, 节奏明快、音调昂扬、 感情饱满, 如《回延安》 《桂林山水歌》 《三门峡——梳妆台》 等。 其抒情诗从始至终贯穿着同一个抒情主体,采用贴近生活的口语化的语言, 形式上两句一联, 每句从七言到八言、 九言、 十言、 十一言不等。 “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 /分别十年又回家中。 / /树梢树枝树根根, /亲山亲水有亲人。 /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 /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 /手把手儿教会了我, /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 /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 /天南海北想着你……”( 《抗战诗篇·回延安》 ) 民歌体新诗的成功之处还在于灌注了民间文学积极乐观、 向上奋进的精神态度和民间文学充满理想和浪漫的精神。 纵观中国文学史的发展, 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发展和一些文学体裁的出现乃至扩大具有重要的作用。 民间文学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向上的一面, 但也有庸俗消极的一面,需要斟酌选择。
未来诗歌的民谣化问题
汉语新诗的民谣化倾向自“五四” 新文化运动始, 以发现、光大本民族文化为目的, 激发民族自信心。 民谣化的新诗创作自诞生起就与复杂的社会环境结缘,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 它被作为讴歌革命、 斥责反动与苦难的工具。 中国的新诗在民间文学中吸取了养分, 迅速发展出了抒情与叙事两大类型, 无论哪一类型的诗歌书写都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 这种文学形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和控制逐渐加强。 而1958 年新民歌运动的失败, 表明了诗歌需要真正源自民间, 需要有自由发展的空间, 那样诗歌才能焕发活力。
改革开放后, “外国的月亮圆” 成为民众普遍的心理, 中国本土的文化与传统又一次受到冲击和质疑, 在西方意识形态横扫中国大陆之后, 中国本土的文学一度消沉。 这与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面临的局势何其相似! 不同的是, 随着国力的增强, 人民的文化心态逐渐端正, 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渐渐取得应有的地位。诗歌的发展仍然是诗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 尤其在网络时代的今天, 诗歌创作、 发表的门槛降低, 写诗的人剧增, 发表的诗歌越来越多,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与新的尝试, 诗歌的出路何在又一次成为人们关心和探讨的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 诗歌的发展逐渐表现出两个极端——一是极度晦涩, 一是极度平白。 诗歌创作走向晦涩的一端在古体诗创作中曾有先例, 一味堆砌玄理将诗歌推向浩渺的哲学、 玄学中反而失却了诗的本位; 一味“强调生活” 藐视提炼, 平白铺陈生活琐屑其实也丧失了诗的性质。 中国一直是诗的国度, 诗歌发展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缘何到了现代社会反而一再受阻呢? 四十年代诗歌取法民谣获得的成功依旧可以成为现代新诗继续发展的学习案例。 文学始终是源于生活的, 贴近生活的民歌与民谣在现代社会地位却急遽下降, 被贴上各种“非遗”、“民族瑰宝” 的标签而收藏于各大纪念馆或变成荧屏中的图文保留于硬盘。 近年来, “民谣” 一词又一次粉墨登场, 这里的“民谣” 不是无曲的诗, 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诗歌, 而是音乐意义上的谣曲。 新时代“民谣” 一词伴着草根文化崛起, 吟唱的是社会底层或说社会下层人的生活与情感, 吟唱者不是诗人, 而是歌手。 他们选择了不同于一般流行音乐的表达方式, 使用比较简单的乐器(常常是一把吉他), 偏好有苍凉感的嗓音唱出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与明知不可追的悲哀。 多数民谣歌唱的是求而不得的爱情、 繁重压力下压抑的生活以及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追念, 因其歌词富有诗意常常引起现代人的共鸣。 民谣歌曲的成功可以为新诗的发展提供某种思路。
社会在不断地发展, 人们关心的与想要表现的主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诗歌的创作必须紧扣时代脉搏, 诉说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才可能引起当代人的共鸣。 新世纪诗歌的发展, 依然可以从民谣中得到某些启示: 首先, 诗歌应取之民间。 诗歌的发展不能满足于四十年代对方言和形式的改造, 更要契合时代要求, 取材民间, 贴近生活、 表现生活、 表达生活。 其次, 评价系统应向民间开放。 诗歌不应脱离群众在小圈子中发展, 因此, 评价诗歌的系统不能封闭, 不能将诗歌高高捧在文学之巅令人望而兴叹,正如于坚所宣称的: “民间一直是当代诗歌的活力所在, 一个诗人, 他的作品只有得到民间的承认, 他才是有效的。” ( 《当代诗歌自九十年代以来向民间转移》 ) 再次, 以一颗质朴的心在诗道匍匐。 诗歌创作总有各种潮流风行, 然而千帆过尽, 大浪淘沙之下, 留下的还是那些最质朴最纯真的诗歌。 因此, 新诗创作或可尝试洗尽铅华, 保留本真。 最后, 应当包容。 在开放的现代社会环境中, 闭门造车势必导致失败。 诗歌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古体诗、 新体诗的变革, 本土的诗、 外国的诗都参与了新诗的创作, 其他学科如音乐、 绘画、 心理学等, 都在诗歌中闪现身影。 诗歌写作的表现手法应更加多样、 境界更加拓宽, 各方面的表达也应更加深入。 总之, 诗歌创作也需要宽阔的胸襟, 有海纳百川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