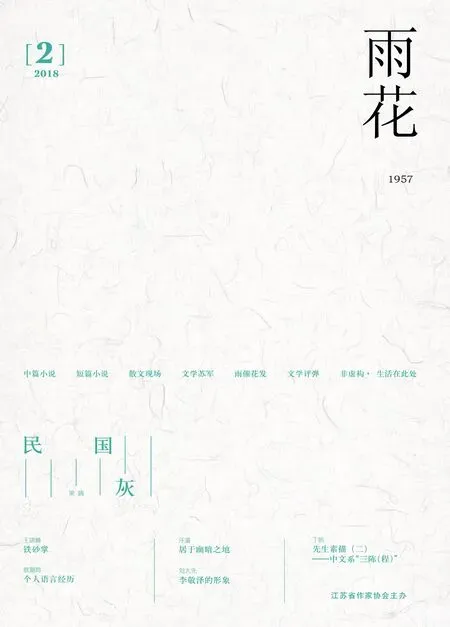巍巍蜀冈(散文)
汤成难
一
长江到达扬州的时候,舒缓了奔腾之势,江面变得宽阔起来,向你展开它沉稳的浩瀚。和江水一同奔腾而来的还有一条山脉,它与长江比肩而行。这条古远而神奇的山脉从蜀地一路走来,经过庐山,滁州,六合,一直到达扬州。江水在此处平缓盘桓后,又向东入海,而这座山冈却执念地恋上了扬州,从此定居下来。它便是蜀冈。
这是关于蜀冈的一个传说,“地脉通蜀”;“自皤汉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扬州而尽,正谓蜀冈也”;“冈形来自蜀,山色去连吴”等等,这样的说法言之凿凿,似乎确可信据,使人脑海里不禁出现以上的画面。关于蜀冈,又据说是源于五千年前地壳的一次沉降,江淮大地被海水淹没,形成浅水海湾,受西侧丘陵缓缓隆升的影响,又逐渐露出海面,成为陆地,蜀冈便成了扬州这一带平原之上唯一凸起的高地。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种说法,比如“井水连川”,比如“茶似蒙顶”,等等,每一种说法都给这座山冈增添了扑朔迷离的神奇意味——它究竟是山的部分,还是海的部分?蜀冈沉默不语,兀自在这片平原地带高高耸立,似乎有意要留下一个供人想象的空间。
蜀冈东西雄踞,傲视江海。冈上茂林修竹,禅寺亭台,一派古意;冈下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沿冈而行,时而起伏,时而隐没,给扬州这座水做的城市平添了山的豪迈气势。《扬州画舫录》中有记载,蜀冈之上,三峰凸起,西峰有五烈墓、司徒庙、胡、范二祠;中峰有万松岭、平山堂、大明寺诸胜;东峰有观音山、功德山等景——这是狭义上的蜀冈。西起六合,“其脉复过泰州及如皋赤岸而止”,这样的描述均不能给蜀冈一个最正确的概括,蜀冈它已不是地理位置上的名字,而是一个地标,一种象征。欧阳修、苏东坡、韩琦、鉴真、石涛、李北海……无数的身影出现在蜀冈之上,使人身游其间,神越千载。
二
这座高耸在“淮南江北海西头”的古冈,是扬州历史上最古老的见证者。我们知道扬州城的岁数,却无法估计蜀冈的寿龄。如果蜀冈肯告诉我们这片土地上第一批人类栖息的情状,那该是多么精彩。 “鲁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这是最早的有关扬州城的文书记载。似乎可以想象,2500年前的一天,骄阳似火,万里无云,这片土地上迎来了一群外来客,他们在统领者的带领下,挥起手中的工具,在蜀冈之下开挖邗沟,在蜀冈之上建筑邗城。这个统领者便是吴王夫差。这一锹开挖下去的邗沟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运河,即大运河的发端,使扬州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也是中国唯一与古运河同龄的运河城。而另一锹在蜀冈之上修建的邗城,也成了扬州这座城市的原点。
夫差选择了这一块靠近长江、有利于沟通南北交通的蜀冈之上建立邗城,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长远打算,他将吴文化引入了长江以北,加快了这一区域的开发;同时,也促使吴文化和中原文化进一步结合。西汉时期的吴王刘濞在邗城基础上扩建为广陵,在邗沟基础上开挖东至向海的运盐河,使吴国成为西汉初期各诸侯国中最富强的一个,也使扬州进入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繁荣期。
邗城的南沿在蜀冈南麓断崖上,断崖下即是长江,站在蜀冈上眺望长江,视野十分开阔。暮色之中,大江两岸,鲜花盛开,春意正浓。这是日落后的长江,经过了一天的潮涨潮落,终于等候到了夜晚的休憩时刻,暮霭沉沉,江水浩淼,波潮带动了镶嵌在静静水面上的星月倒影,形成无数道流光。这幅画面开阔而又壮观,绮丽而又奇异:明月和群星不再高拱在夜空,却成了流动在水上的精灵,它们从潮水中诞生,在流波中消融;来来去去、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这场景感染着万物,也感染了一个人,即隋炀帝杨广。他站在蜀冈之上,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写下了这首《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这首诗在描绘春江花月夜景色方面,具有开先河之功,潮水这一景象启示了后来的张若虚开拓出一个极为阔大的春江意境。总之,蜀冈这处高地让这位爱写诗的帝王流连忘返,后来在此修建行宫,称为迷楼,被后人改为鉴楼,所谓“鉴”者,“以史为鉴”的意思。这大概是历史对隋炀帝的不够公正的评断了,胜者为王败者寇,这是传统的价值观,但多少胜者,虽尊为君王,却被历史长河所湮没,却有一些“败”者,成就了利及千秋的功业,被历史所铭记。夫差与刘濞对古代扬州交通的发达与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功绩,隋炀帝又在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基础上,开筑了沟通南北的古运河,为古代扬州进入隋唐第二个经济繁荣期和清康乾第三个经济繁荣期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吴王与隋炀帝的脚步远去了,新的脚步又近了,这片古冈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帝王的登临,有史可据的能列出一大串名字,李世民,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当然,人们的目光也许会落在又一个爱写诗的皇帝身上。乾隆写过关于扬州的诗词一百来首,翻开《扬州历代诗词》,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位皇帝似乎十分钟情于蜀冈,脚步一次次地寻访这片高地——《平山堂》《游平山堂》《题平山堂》《再游平山堂》《再题平山堂》……这使人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吸引着这位帝皇的到来,是“江南山色秀无尽,二月韶光美不禁”的蜀冈风光?还是“梅花才放为春寒,果见淮东第一观”的绝佳地理位置?或许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一种尊重和敬仰,是蜀冈的悠久历史和恢弘文气。
三
扬州历史上出过多名“文章太守”,这个称号是对一个地方最高领导者的最高赞颂,能称得上文章太守的既要在诗文上独领风骚,又得在政业上成绩卓著。此时首先想到的,应是欧阳修以及他的那句“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了,这是欧阳修调离扬州后写给即将上任的太守即他的好友刘原甫的,文中对当年扬州的生活进行了追忆和感慨。如果把欧阳修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知滁州、扬州、颍州时的正当壮年,文学上也处于鼎盛时期;另一个是知亳州、青州、蔡州时政治生涯的终结时期——此时的欧公已进入花甲,身体多病,仕途上心灰意懒,于是在晚年的孤寂与平静中写下许多追忆早年太守生涯的诗作。欧阳修知滁州、扬州前,是一个在京城做官的人,生活也是风流旖旎,然而官场失意忽遭贬谪,如果说欧阳修在知滁州时还有少许的失意,四十不惑却自称“醉翁”,满眼的秋色以及几声雁鸣的确能勾起他心中的萧索之意的话,那么欧阳修在知扬州时内心已没有这份凄然了,他已从京城的喧嚣纷争中坦然走进山村水郭和寻常巷陌了。他的视野更加开阔,胸襟更加浩荡,他在蜀冈之上建筑平山堂,以讲学宴客之用,也留下了“坐花载月”这样的美谈。站在堂前,白云苍苍,江水泱泱,“远山来与此堂平”,这是何等的气势。欧阳修在扬州任期仅一年多,他对扬州充满了深厚感情,从《大明寺水记》和《朝中措·平山堂》等作品中可以窥知一二,当然,他“宽简”的政治主张更是深得民心,扬州人曾把他的像列入“三贤祠”世代祭拜。后人对平山堂一直讴歌不断,除了传诵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外,更多的是纪念和缅怀“文章太守”的品格。
另一位与蜀冈有过密切关联的“文章太守”,应是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了。他和欧阳修既为师生,亦是良友。如果说欧阳修是英勇无畏的旗手,那么苏东坡则是名副其实的闯将,他们携手铸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而欧、苏两代宗师忘年之交,至今仍传为佳话。当历史的长镜头摇向北宋的扬州作聚焦探寻时,则会惊奇地发现,蜀冈之上平山堂和谷林堂犹如两颗璀璨之星闪耀在苍翠之间。谷林堂与平山堂相连,在其之北,欧阳修离开扬州四十四年之后,苏轼步恩师后尘,从颍州徙知扬州,为纪念恩师欧阳修而建。“深谷下窃宛,高林合扶疏”,谷林堂取“谷”“林”二字。此时欧阳修已辞世十载,平山堂内欧公手迹令苏轼顿生感慨,抚今追昔,深感岁月蹉跎,人生如梦。于是写下这首《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
在这里,还有一段关于这对师生的佳话,欧阳修的《朝中措》中写道:“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然而好事的人则认为:平山堂距离江左诸山非常近,在平山堂眺望那些山一目了然,怎么会看不清楚呢?原来欧阳修是高度近视啊。这话传至苏东坡耳中,他极为生气,作《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为其辩诬:“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何谓有?何谓无?山色可以有中无,也可以无中有;人生亦是如此,处江湖之远无须哀哀切切,居庙堂之高也应该保持淡定与从容。他们都年少中第,扬名天下,仕途之路却走得异常艰辛,苏东坡与欧阳修之间没有文人相轻,有的是穿越时空的缅怀,是天才对天才的仰慕,是大师对大师的敬重。再回到“文章太守”这个话题上来,“文章太守”无疑是一顶无比风雅的桂冠,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当我们的目光在蜀冈之上进行搜寻时,一个个的身影从眼前飘过,杜佑,韩琦,刘原甫,等等,他们都具有相似品格与情怀,这不仅是一种个体性的精神通融,更定格为流韵千古的文化风景。
四
如果你仔细阅读过《中国艺术史》,你一定会发现有两条线一直若隐若现,它们生长着、延续着,时常交织,时常平行,但最终汇聚在蜀冈之上。这两条线便是书法和绘画。
沿着书法这条线向前追溯,便能发现它的另一个源头——李邕。李邕少时居扬州,其父李善为《文选》注者之一,扬州旌忠寺南如今还有纪念曹宪和李善的曹李巷。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杜甫在齐州(今济南市)和李邕于历下亭的一次聚会后写下了千古佳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李邕时任北海太守,后人称李北海。李邕与杜甫为忘年之交,当时,李邕68岁,名满天下,杜甫33岁,初出茅庐,但李邕慧眼识珠,对杜甫可以说是有知遇之恩。
古人有“右军如龙,北海如象”的说法(董其昌《跋李北梅缙云三帖》),李北海是唐代书法家中惟一一位与书圣王羲之比肩并立的人物。他打破前人用正楷写碑的惯例,首用行书写碑,将自己的性情与品格浸透在笔墨之中,成为“碑版照四裔”的行书行家,在艺术上达到了无人能及的高度。他的《出师表》《麓山寺碑》《李思训碑》被称为阳春白雪,并对后世行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间有苏东坡、黄庭坚、黄宾虹、林散之、卞雪松等,一代一代的书家从源头汲取营养,尔后形成了一条条重要的支流。
再说绘画吧。中国绘画史上名家辈出,大匠如林,但要做到不为物蔽,不被法拘,当数明代的徐渭、清朝的八大山人、石涛以及“扬州八怪”。这其中石涛以及“扬州八怪” 都长期生活在扬州,均有遗迹——蜀冈之上有石涛墓,蜀冈之下有“八怪纪念馆”。
明亡后,石涛对新的王朝抱有过幻想,屡屡碰壁之后四处漂泊。曾自叹“只今对尔垂垂发,头白依然未有家”。个体的孤独是伟大作品产生的基础,仕途上的失落促使石涛与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的接触,“搜尽奇峰打草稿”,自然界的山山水水赋予他深厚的绘画素养,强调“师法自然”,“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石涛52岁作《余杭看山图卷》,58岁作《卓然庐图轴》,59岁作《溪南八景图册》,件件精绝,他的《画语录》从自然与哲学高度观照了绘画艺术的本质和要义。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把他看成清代以来300年间第一人的说法,并不过分。后来的“扬州八怪” 秉承石涛的理念,成为他艺术的追随者,理论的实践者。于是,在中国绘画的版图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狂放不羁,他们自由自在,他们的生命奔涌出瑰丽的色彩和深厚的线条与墨块。
当然,除了以上所列书画家之外,与蜀冈有着紧密关联的还有虞世南、阮元、邓石如、赵补初、启功、龚贤等近百位,他们的名字熠熠生辉,镌刻在蜀冈之上。
五
站立于蜀冈之上,风从四面扑来,虽是晚秋,却有了几分凛冽。视线每微调一个角度,都能与过去相撞——远处塔影斜阳,近处古木荒井,这些石碑、古塔以及地方志里,一定潜藏着青衫翩然的身影。
文人墨客都极爱登高,李贺“倚剑登高台”,杜甫“百年多病独登台”,李白“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登高者举不胜举,只有登高才能望远,只有登高才足以驰目骋怀,只有登高才得以呼应内心深处的某种辽阔。而蜀冈的极佳地理特征,使得登高远眺更加与众不同。一千多年前的蜀冈还是长江的水岸线,蜿蜒曲折的蜀冈之东则是入海口,所以站在蜀冈上,足以将长江与大海尽收眼底。“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一位诗人对着这壮阔景象感叹道。诗人叫张若虚,面对滔滔江水有所感悟:水与月,花与影,江与岸,船与人,什么是长久?又何谓瞬间?月尚有阴晴圆缺,花亦有开谢轮回,江水流走春光,春光将要流尽,江水已非昨日的江水,舟楫与思妇是否还依然如故?在时间的长河里,人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沙;在浩淼的长江前,人也只是一滴纤细而弱小的水珠。一种敻绝的宇宙意识,一种更深沉、更寥廓以及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使人憧憬、怅惘、激励和欢愉。试想,在写那首压倒了全唐的诗篇之前,张若虚一定登临过蜀冈,然后才去了白沙滩头,否则,他怎么会遥望到千万里的波与相思处的海?是蜀冈之眼给了诗人高入云端的辽远视野。于是,张若虚挥笔写下了这首被誉为“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
历史上三首《春江花月夜》都与这片高地有关,看来观看江岸美景是需要一个极佳地理位置的,使人不禁想起秦少游为蜀冈写下的那句“游人若论登临美,须作淮东第一观”。
再说另一则登高的事吧。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月,白居易与刘禹锡第二次在扬州相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有过一次接触,那是四年前两人相约同游扬州、楚州,白居易在过江时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四年之后,两人于扬州的再次相遇,更是亲热无比,分外珍惜,甚至“携手”登栖灵塔。白居易写下《与梦得同登栖灵寺塔》,而刘禹锡写下《同乐天登栖灵寺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干。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白居易,刘禹锡,一个是“诗魔”,一个是“诗豪”,同样命运多舛,同样兼济天下,他们在蜀冈之上的栖灵塔留下千古美谈,青衣白衫还未离去,塔顶风光无限,尽收眼底,那些举目张望的游人还在,仰望了千年。
据史料记载,到过扬州的文人墨客几乎占了唐宋名家的大半数以上,为这座被誉为“中国之尤峻峙者”的栖灵塔留下了诗作,高适写下《登广陵栖灵寺塔》,刘长卿写下《登扬州栖灵寺塔》,李白写下《秋日登栖灵塔》。李白曾六次游扬州,这座繁华开放且浪漫的城市实在使人流连忘返,李白第一次来便逗留半年,此后又多次前往,甚至怂恿他的好友孟浩然,希望他能去看一看烟花三月的扬州城,为此,还留下一首千古绝唱——《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今天,登栖灵塔而四望,一种难以平抑的崇高感油然而生,自然呈现于视觉之中,历史藏于胸臆之间。两千年来的人声鼎沸和车马喧腾仿佛穿越时空,清晰地出现了,杜牧提着酒壶匆匆而过;李白仰面长啸,回响遏云;温庭筠穿街寻路;白居易斜在石椅上看河上风光。蜀冈上的青石台阶坐满了人,李商隐、骆宾王、王昌龄、孟浩然、崔颢、高适、韦应物、刘禹锡、张祜、罗隐、韦庄、苏辙、秦观、周邦彦、姜夔、徐凝、李渔、蒲松龄、曹寅、龚自珍……无数流水般的脚步将这里踩磨得坚实光亮,像一盏盏灯,璀璨如昼。
六
1935年暮春,郁达夫来扬州后写了篇《扬州旧梦寄语堂》,文中对扬州有赞美,也有失望,他写信给林语堂劝其“不必再来”。林语堂回复说:“吾脚腿甚坏,却时时想训练一下。虎丘之梦既破,扬州之梦未醒,故一年来即有约友同游扬州之想……不管此去得何罪名,在我总是书上太常看见的地名,必想到一到。怎样是邗江,怎样是瓜州,怎样是廿四桥,怎样是五亭桥,以后读书时心中才有个大略山川形势。即使平山堂已是一楹一牖,也必见识见识。”
郁达夫眼中所见的是现实,是不再繁华甚至有些苍凉的蜀冈,而林语堂则强调了一个文化人心中的情结——即使腿脚不便,即使冒着危险,也要来看看这常在梦中出现的扬州。
何止是郁达夫,林语堂,从南朝鲍照的《芜城赋》到南宋姜夔的“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许许多多的诗人都曾经写过蜀冈,写过这座城市的荒芜。历史上,大凡处在特殊地理位置的城市,都经历了过多的血雨腥风。扬州南临长江,北连江淮,运河开挖后,经济繁荣,民运昌盛。这样的城市必定会享有特别的荣华,也必定经历太多太深的苦难。回望扬州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大大小小的战乱不下百余次。其中毁灭性的有十多次,这些大小不一的战乱犹如这座城市所经历的每一次寒冬,犹如一场又一场的雪,我们看见了每一场大雪对这块土地的覆盖,我们也看见了行走在大雪纷飞中的身影,鉴真,李庭芝,石茂华,史可法,还有长眠在蜀冈之上的无数先烈。他们与这座城市同生共死,用信念铸造出这座城市的铮铮铁骨,用生命诠释着这座城市的精神。
或许,我们无法理解鉴真大师五次东渡失败之后的执着,也无法体会他踏上异国土地后的心情,失败与成功,悲伤或喜悦,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为弘扬佛法而坚定不移的精神,看到一千多年后,在他的纪念堂的院子中,那盏长明灯恒久地释放着光芒。
同样,我们也无法想象,假如史可法接受劝降,扬州城是否还会遭受屠城的命运。但一座城和一个人的一生一定有命定之说。兴亡多少事,抵御外侵是一座城市的实用功能和精神寄托所在,为国尽忠杀身取仁是每个读书人一生恪守的信念。或许,我们能够想象,城将破之时,史可法写完给妻儿最后一封信,独自登上城墙,长久地伫立,长久地望着蜀冈,之后决然转身。
七
美好的历史都是从废墟中升起来的。从古邗国至今,蜀冈始终记录、书写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这座城市既有莺歌燕舞,也有金戈铁马,既有古运河的清波荡漾,亦有滚滚长江的惊涛拍岸。
古老的蜀冈,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停车驻足,对它进行过仰望,又有多少人曾一步步登临,探求过它的前世今生。究竟是什么样的景致,什么样的风物,吸引着一代代的文人骚客或帝王将领——是万松叠翠,双峰云栈;是古木森森,芳草萋萋;还是山冈之上翩翩起舞的白鹭,运河上的点点帆影;还是琼花的奇异,大明寺的清寂;还是那层层叠叠的黄土和青砖。或许,蜀冈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壮阔的,充满灵性的生命体,具有不朽的精神与灵魂,古往今来,始终与人们的血液和生命相连,它站立于大地之上,高耸峻拔,巍峨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