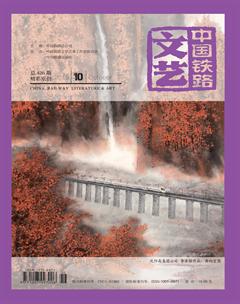乡愁就是人间烟火味道
酿米酒
酒,于乡村总有一种扯不清的情愫。家乡米酒是村庄来去的见证者。
在乡下,每逢佳节将至,端午、中秋、春节,十分看重的三大节日,父亲必定做一盆米酒。父亲做酒的程序,我已烂记在心。称米,洗净,浸泡一天一夜,把糯米浸透。放在木蒸笼里用大火蒸。水汽蒸腾,灶中火焰照亮了一个家的温暖。不到一个时辰,糯米香气就盈满了农家院落。这是孩子们格外喜欢的时刻。蒸好的糯米俗称“淘饭”。和一般米饭不一样,它硬一些,还有些米形,饭一粒一粒不粘连,却好吃。做酒,是孩子享受吃淘饭的一个美好时光。父亲却不多给,为我们兄弟几个,每人捏上一坨糯米饭,热热的,吃到口中柔软细腻,比普通米饭香甜。在那个白米饭都难以为继的日子,一坨热热的糯米饭真的温暖好些时日。至今想起那个时分,总有一种幸福回味绵长,如一碗米酒,岁月越长久,愈来愈芬芳。感谢父亲给我童年留下一段飘香的日子。
在我们快乐地吃淘饭过程中,父亲等糯米饭凉下来,不烫手,就把糯米和碾碎了的酒曲混在一起,细细搅匀,再一层一层地摁进一口洗净的大脸盆,表面细细地抚平,又撒上一层酒曲粉。有意思的是,每次做完父亲特地在糯米中间留一个洞,父亲称它叫酒窝。我似乎看到父亲脸上的微妙神态。人脸上也有酒窝,在腮上,一笑酒窩显出来,增添几许妩媚。父亲说:“酒缸里的酒窝如泉眼,酿出的酒液都渗到酒窝里,称为酒娘。”初成的酒液称为酒的“娘”,这叫法很动人,酒有了娘,就源源不断地生出酒液来。酒娘是甜的,十分嫩滑,没有日后成酒时的呛辣。想象乡村女人,新娘小媳妇,初进婆家门,温婉羞涩,如嫩叶新花,时间久了就老辣起来,甚至有了泼,就破败了。
拌完酒曲,脸盆盖上木盖板,放入空闲床上,用棉被紧紧包裹,让它们在温暖的被窝中做发酵梦。我起初不明白为什么要盖棉被。父亲说做酒,窝要温暖,太冷了不出酒。太热了,酒会变酸。有时冷了窝,父亲找两个打吊针用的玻璃瓶,灌上开水,放进被窝。这个期间不能松窝,否则会变成半生不熟的酒饭。
父亲做完这一切,总会泡上一杯热热的川芎茶,透过袅袅水雾,父亲平静脸上隐藏着满足。而在父亲的水雾后面,是我们的期待,等待也是一种美好过程。每天我们总会跑到房间里溜达几趟,闻一闻正在日子深处的香。一两天,就能听到棉被下面隐隐约约冒气泡。三四天后,悄无声息。这时酒香却一阵比一阵浓郁,香甜灵盈的米酒大功告成。此刻农户家土房子里,低矮、阴暗,然而有了这盆米酒,生活也似乎更多了一层期盼一层乐趣。每逢佳节,酒的醇香弥漫乡间院落,穿梭在整个村子,菜园子、水井旁,甚至牛栏,也不会放过。农家的日子,因为一盆自酿的米酒,把原本清苦的生活酿出一屋子的馨香和欢愉。
这样的场景至今难忘。午后的光景静谧而慵懒,屋顶明瓦上的阳光漏下来,父亲手在光线里麻利地伸伸缩缩,空气中氤氲着隐隐喜悦。父亲做酒的整个过程,口中喃喃有词,像是一个十分庄严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一个蓄势已久的故事就有了一个淡淡的情节,浮出的是一缕暗香。父亲说这是喊酒。我不懂。乡村有太多隐喻,让你永远也禅悟不透。
做米酒的南方呀,醉了岁月。在南方时空的行走,浸染的是一身香甜。
腌洋姜
洋姜的真名叫菊芋,是一种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从字面上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并非本地土生土长的植物,它的真实身份是一个舶来品,据说来自遥远的北美。
洋姜如大自然所有的植物一样,春天来了,发芽;夏季到了,开花。秋天里,洋姜叶变黄了,秋风吹过,叶子一片一片掉了下来。地下的根,却是呼之欲出。在这个季节,乡下,正是收获季节,稻谷黄了,苞谷摘了,瓜果也进入尾声了。洋姜也不例外,却深藏在地下不露声色。直到深秋,父亲空闲下来,抄一把锄头,把冷落在一边的洋姜细细地挖出来,一锄头下去,翻过来,都是可爱饱满的洋姜。
刚挖出来的新鲜洋姜炒出来有很重的土腥味,口味平淡无奇,但腌制后的洋姜却特别出众,又脆又嫩,清香爽口。母亲会做很多关于洋姜的菜,炒的,拌的,腌的,味道清脆爽口,最好的吃法莫过于腌制。洋姜的最好归宿是躺在红彤彤的剁辣椒坛子里。母亲的经典语言永远难以忘怀。洋姜的卑微身世,也许决定了它的出路。洋姜好像就是为了做咸菜而生。
洋姜腌制过程很简单,也如它的生命,卑贱。母亲把完好无损的洋姜选出来,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几天后,泥土干了,用小刷子刷净。母亲告诉我,鲜洋姜一定要晒透水分,否则,水多,易酸,不脆,且难以储藏。洋姜不能沾水,否则会变黑发烂。干净的洋姜再放入坛中,加入剁辣椒、醋、盐、生姜和大蒜等,盖好放上几天就是一坛上好的菜肴。本是黑黢黢、软蔫蔫的洋姜被酸辣鲜红的剁椒浸泡,便脆生生、水汪汪,顿时让你唇齿一紧、生出不少口水。
母亲是腌菜高手。在乡下,姑娘媳妇如果不会做几道腌菜,乡亲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落下一个不会持家的骂名,在婆家做不起人,挺不直腰杆。所以在乡下未出嫁的女孩子,母亲一定会叫她学会做腌菜。那时乡下粮食拮据,尤其是在冬天,本来瓜菜就少,雪一飘,到处是白茫茫一片,难免会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一到秋天,正是瓜菜丰收之际,乡下女人就忙着霉豆腐,做剁辣椒,腌酸豆角、酸黄瓜、酸菜等,她们用灵巧的双手,使乡村生动鲜活,也让自己亲人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从冬天到来年的春天,这些腌菜就成为农家的下饭菜开胃菜。炊烟升起,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摆下一两碟香扑扑的坛子菜。乡下的腌菜,大抵是酸、辣、咸,唯一只有腌洋姜却是甜甜的又脆又嫩,清香爽口。洋姜甜、脆、爽,一直是我童年记忆中的美食佳肴。
至今记得某一个冬天的夜晚,喝着母亲熬制的一锅喷香的玉米红薯粥,再就着一小碗儿脆生生的腌洋姜,点上几滴香醋和麻油,真是暖到心坎里。窗外雪花儿飘,室内却是满屋生香。这是多么温暖惬意的生活场景。
又脆又嫩腌洋姜,依然清晰而温馨。
打葛粉
葛,一种绿色藤本豆科植物。葛,所到之处攀岩爬树,所向披靡。万顷土地,狂野不羁。它似乎从不管其他草木,一股脑儿地,就趴了一地,又怎么不像极了乡村顽劣的少年。
其实在乡村,葛再霸气,再张扬,也是卑微的,仿佛是丢在路边的半截草绳,只能用来做系系绑绑的事。譬如,我的父亲从深秋的菜园子里来,总会剁几根葛条系几棵饱满瓷实的大白菜,带回母亲的厨房。还有把那些翠绿肥嫩的萝卜缨切下,也是用葛条编成串,一串一串,挂在房前屋后的果树上风干,留着过冬。但埋在泥土中的葛根,却是另外一种待遇。
葛根发达,去泥削皮,柔滑細腻,玉脂纤嫩,泡在水里,又变成了十足的睡美人。将葛根磨碎,滤去茎渣,白色的葛浆在水里沉淀下来的便是葛粉了。秋风起,桂花香,艳丽的阳光下,乡村的院落里到处是葛粉,匾里晒的是粉,竹笆上晾着的是粉。有的村民将粉从缸里盆里倒出,整个儿将“粉坨”风干撂在家里。有大粉坨撂着,日子也仿佛踏实了许多,有一股沉甸甸的味道。月光下,睡觉也格外香格外沉。
打葛粉就是这一种美好。这是年少时的我最喜欢的活之一。
秋天的日子很是惬意,阳光暖暖的,透过树叶筛在地上的斑影,如白白的馒头。但白馒头只是一种奢望,葛粉才是摆在现实的美味。白天大人上工去了,我们兄弟几个便到山坡上挖葛根。挖出葛根后又搬到河里去清洗刨皮。捶葛粉是个体力活,必须要等到大人们晚上下工后才干,捶的捶,洗的洗,磨的磨,淘的淘,十分忙碌也十分热闹。葛粉加工也是个细活,那时没有粉碎机,全凭人工加工,先把大的葛根用斧头剁成小块,放在青石板上用木榔头把它捶得很烂,然后用布袋装起来,放在装满清水的水缸里摆袋。刚打出的葛粉要漂洗好几道水,不漂水的葛粉很黑,吃起来又苦又涩,必须换3~4遍水,当水色由褐色变白色后才能取粉。摆袋就是过滤,细细的,白白的葛粉透过布袋的缝隙渗漏到水缸里沉淀,最后布袋里剩下的就是葛渣,葛渣再用石磨磨细后加上碎米面拌和后用蒸笼蒸成“葛巴”,在当时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食品,虽然有点糙,但还是吃得津津有味。这时已是夜半时分,月色满院,如一地秋水,招惹得秋虫碎碎。满满一缸的葛粉乳慢慢沉到了缸底,让梦中多了一丝甜美。第二天早上取出葛粉放在竹席上晒干,几个太阳就变成了洁白的葛粉。打葛粉的故事在我小时候每到冬天都会年年延续着,有苦有乐。
在饥荒的年代,葛根是生活中的充饥物。“十碗大菜九碗粉,搛块肥肉捞捞本”。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原本就十分拮据,葛粉自然就成了宴席间的主角。葛粉让我的童年多了一丝洁白的记忆。
摘山椒
立夏刚到,山椒就结出一粒粒小果子,绿豆大小,圆形,青色。柔韧有弹性,皮嫩肉脆,包着的核也像软骨一般。正是这个时节,山椒子成为乡下人一种很好的餐桌美食。
父亲总是这个时节,进山,采摘山椒,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摘回来的山椒子除掉枝叶杂质,用清水洗净,晾干水,然后用适量的盐渍一个小时,加上剁椒和拍碎的大蒜、芝麻油,搅拌均匀,腌制半小时,就是一道爽口的美味了。大蒜莹洁剔透,有着玉的质感,山椒子青翠鲜活,充满了动感,加之红亮亮的辣椒点缀,盛在乳白色的瓷盘,这哪里是菜肴,分明是一件雅致的艺术品,让人不敢轻易举箸。不过,山椒的清香实在太过诱人,怎能忍得住,伸筷便夹,入口有一种很浓郁的辛香味,微辛微辣微麻特香,非常爽哦。最好是现腌现吃。色香味俱全,让舌尖心尖不由自主地痉挛。我甚至觉得这种味道不是通过舌头感知的,纯是嗅觉,吃得惯的人觉得特别香。吃不惯的人会觉得它味道有点冲,有一点像芥末。初次相遇,是不容易接受,但随着时间转换,多次品尝,味蕾渐渐由陌生到熟悉,再到喜欢。
大山深处青青的山椒与红红的辣椒相逢,成了最刺激味蕾的美食,绝对是味觉和神经的绝妙碰撞。大蒜和山椒子,好像它们是天生的一对孪生姊妹,都有辛辣味,但融合之后,会有美妙的辛香味滑入口中。一个精心地种在菜园里,一个生在荒芜的山野中,在同一个时节,它们机缘巧合地碰撞,然后相融,成了一道别的食材难以复制的美食。鲜嫩的山椒子,犹如花期,只有那么几天绚烂着开放。为了长期贮存,一般是用坛子泡制,放置时间一久,会渐渐变黑,失去了颜色,但味道不变,甚至会更加醇香。做红烧鱼、鱼火锅的时候撒上一把,鱼的味道会无比鲜美爽口。甚至炒茄子豆角也是极好的佐料。炒牛肉是极具地方风味和文化特色的菜式,爆炒牛肉时加上山椒子和少量小米椒,既保持辛辣的鲜香,又有一种混合了柠檬、罗勒和香叶的浓郁香味,是夏日里一道十分开胃的美味。
每每看到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他制作的山椒,应该有些劳累的父亲坐在椅子上却一脸幸福地笑,那笑多么像秋天灿烂的金丝菊呀!很久我才明白,父母亲不愿进城住那个高楼上的新房,原来他们是舍不得这些朴素、自然、纯粹的草木,这些一日三餐延绵不断的烟火的幸福。鱼腥草根、香椿芽、地米菜……这些原本生长在野外,味苦、辛辣、刺激的植物,其实很普通,经父亲的精心调理,一转身,从山野中屈身厨房的小木桌上,毅然变成了我们不舍的味道,很独特、深刻。这是父亲用心做出来的美味,才能让舌尖和情绪共出美好。简单的生活,透着自然、质朴、欢乐、团圆。这些源自乡野的平凡之物,在那个物质贫乏的时代,总是能给我们的胃带来一些温暖,更是唇齿留香的美味。
霉豆豉
豆豉是我童年中最佳美食之一,一直延伸至今。辣椒炒肉、清炒苦瓜、炒空心杆、腊味合蒸等诸多美食中,更是少不了豆豉的身影。一小把干豆豉,黑黑的,不上眼,却爽口。
每年大暑一到,母亲就准备忙着做豆豉。
这时,田间地头早熟的黄豆已饱胀着一串串豆荚在田野里摆动,言语不多的父亲顶着烈日割回一捆捆黄豆,放在地坪上太阳下曝晒,猛烈的阳光拥抱着它们,黄豆迫不及待地“噼里啪啦”从豆荚中跳出来。除掉豆杆豆叶豆荚,一粒粒圆润饱满的黄豆呈现在母亲的眼前。洞庭湖的山丘上孕育生长的黄豆多为黑色,扁圆形,不像北方用来榨油的黄豆,色泽淡黄,外表好看,但是南方的黑黄豆不仅可用于做豆豉,还可以打豆腐,是南方人最佳的食材之一。
母亲将洗净的黄豆,先用清水浸泡一个晚上,第二天中午,用铁锅大火煮。做豆豉时,豆子煮的软硬程度很讲究,煮黄豆的时间要把握好,不能煮烂,烂了,豆豉不成形一包渣,而且不美观;煮太硬,吃的时候会觉得没熟,甚至会有苦味。如何掌握,全凭经验。母亲说,熟能生巧。黄豆煮到刚过心,尽量不要让豆子破皮,这样做出来的豆豉才能颗颗色泽黑亮剔透。黄豆煮熟后,熄火,取出沥水晾干,放进竹盘箕并均匀地铺开。
黄豆在厨房开始飘香。用不着母亲吩咐,我们立马去寻找黄荆。割黄荆要在阳光最好的时刻。早上露水太浓,傍晚割,又伤了精髓。唯有正午时分的黄荆清清爽爽,没有了一滴露水。我们很细心地砍回黄荆,此时,摊放竹盘箕中的黄豆在阳光下晒了半干。母亲把竹盘箕搬进屋中,用黄荆的枝叶密密地盖住。黄荆的香与黄豆的香裹住母亲。
母亲也会给我们一丝犒劳。当我们扛着黄荆归来,母亲已盛好一碗香喷喷的黄豆,放一匙红糖。香呀!这个香已在我的脑海飘浮了四十多年,一直未散。
黄豆在黄荆的呵护下,慢慢地长出一层密密的、细细的茸毛,浅黄色。这是黄豆的发酵过程,先人的话说是“沤豆豉花”。发霉最为关键,最好是黄霉。白霉的豆豉不好吃。这便是豆豉制作的关键所在。大约一个星期,掀起早已枯萎的黄荆,拿出发霉的黄豆,拌上红辣椒、生姜、大蒜、花椒、盐,拌均匀后,放入早已洗净且在太阳下高温晒过的坛子,封盖,坛沿注入清水,放在院子里,日晒夜露,使其接受自然的精华,星光和月光,雾气和露水一定会溜进坛中,怪不得豆豉如此美味。
霉豆豉的过程是一个神秘的过程,这是我至今没弄明白的事情,黄荆在这个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重要的角色,至少黄荆的香浸润豆豉饱胀的身体,封存了一个乡村故事的记忆。乡下有许多诸如酿酒、霉豆腐、熬谷糖等风味小吃,是一代传一代的技艺,经由千年演化而来的民间智慧,染着农人的汗水,饱吸着阳光的热情,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望,终成一种农人般朴素亲切的美味,温暖农家人的平常
生活。
豆豉是家的标志,离家的儿女,简陋的包裹必定有母亲放进去的一瓶(包)豆豉。它们随着远行的足迹翻山趟河,潜入到陌生城市,不时慰藉孤独漂泊的灵魂。
乡愁,其实就是人间烟火味道。
作者简介:葛取兵,湖南临湘人,在《人民日报》《小说界》《文学界》《青春》《芳草》《文学港》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有作品入选过50多种选本、中高考模拟试卷、高职语文教材,有著作5部,系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理事、岳阳市作协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