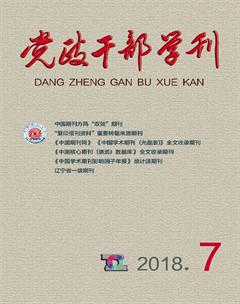组织化利益表达: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宋桂祝 柳玉芬
[摘 要]在当代社会,分散的个人利益走向组织化趋势,一般说来,有组织的、集团化的利益表达方式要比个人通过政务官员和议员、代表向政府提出要求或请求,要更加有力量,更具有效性。组织化利益表达可以增强社会弱势群体的力量,推动组织性社会力量的成长,增加国家的内聚力和并提供改革动力,但同时也潜藏着很多的危险。理论假设和现实经验中存在的冲突和张力,要求我们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理性决策,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利益组织化表达的路径。
[关键词]组织化利益表达;多元主义;政治稳定;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8)07-0033-06
进人现代社会以来,组织化利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位居于政治社会学分析的首位。学者们发现,在当代社会,分散的个人利益走向组织化趋势。公民和公民团体向政府表达利益诉求,可以是原子化(Anomic)的利益表达方式,可以是松散的非团体式(Non-associational)的利益表达方式,也可以是制度性(Institutional)利益表达和团体性(Associational)利益表达,概括地说,公民的利益表达可以简化为两个层次:即以个人为单位的利益表达方式和以组织化的利益团体为单位的表达方式。一般说来,有组织的、集团化的利益表达方式要比个人通过政务官员和议员、代表向政府提出要求或请求,要更加有力量,更具有效性。因此,在多元主义者看来,相对于个人化的利益表达方式,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是实现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途径。为什么多元主义要将有组织的利益表达视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对于中国政治意味着什么?它是否与多元主义者猜想的那样,可以推动组织性社会力量的成长从而有助于提供克服既得利益的改革动力?在组织化利益表达中潜藏着那些不利因素?理论假设与现实经验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与差异,是进行理论修正还是理论替代,关键是看理论价值和现实适应性。在笔者看来,多元主义的利益表达理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尽管不断遭遇挑战,但愈久弥新,经过理论修正,愈加具有包容性和吸引力。
一、关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理论假设
是否存在一种超越不同集团利益或者代表全体一致的整体利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利益集团政治可能不会发生且多元主义也即失去了现实的理论价值。这种整体利益通常在战争时期会被集团或组织用来作广泛的社会动员,在和平时期为组织或集团行为提供合法性解释。但在多元主义者看来,这种代表完全一致的整体利益是并不存在的,利益集团政治是美国政治生态的主要表现形式,阶级政治是欧洲国家主要的政治主题,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也面对着诸如政治稳定、政治开放和特殊利益集团等问题。卢梭曾强调用“公共意志”来超越社会构成中的“特定意志”,但现今世界上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能否作为一个整体被代表?1970年美国建立的“公民院外组织”——同道会宣称代表了所有人促进良好统治的意愿,拉尔夫·纳德建立了与法律、核能源、税收改革以及医疗等相关的公共利益院外集团,这些集团进行了大量杰出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表达了那些被忽视的力量薄弱的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本应被强调的公共性利益或国家利益,但这些公共利益集团显然不能成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所以美学者迈克尔·罗斯金指出: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其整体利益是否就是一些没有共同声音的利益集团“马赛克”式的拼凑?
既然超越性的整体利益并不是那么真实的存在,各种利益集团和组织也就并非完全代表了自私和特殊利益。在政治系统理论中,利益集团在民主政治中的意义和价值非同一般。就如本特利(Bentley)在政府之过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1995)一书中阐释的那样,民主政府就是平衡社会中各种竞争性的利益,而组织化利益的相互竞争是社会中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1];组织化利益团体中的多重成员身份是在多元民主政治中的一个平衡因素,它使得没有一个固定的利益集团永远并在任何地方都处于支配地位。民主通过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得以实现,这是多元主义建构的理想模型。民主多元主义理论假设,在特定条件下,具有相似的潜在利益群体通过组织化的形式联合起来进行相互竞争,一方面可以增强那些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的力量,避免特殊利益群体操纵和控制政治,另一方面防止原子化的、散漫的或者暴力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形式对政治稳定和政治程序的破坏性影响。在多元主义者看來,利益集团是每个现代民主社会所固有的部分,国家是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舞台,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是多元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
二、理论与现实的冲突
独立而单一的理论遇到复杂交错的现实,往往会变得灰色而无力,但这也是理论能够不断修正、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利益集团理论主要是对美国现实政治的提炼和总结,并展示了学者们对未来民主发展模式的预期,但这对处于社会政治经济转型期的非西方国家,这种理论模型是否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在理论的应用过程中,“应然”与“实然”的差距是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积极作用与其潜藏的挑战,正是相关经验研究中学者们争议的问题所在。
1.关于组织化利益表达与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认为,组织化利益表达可以增强社会弱势群体的力量,通过推动组织性社会力量的成长,缺乏政治资源和政治影响的社会群体可以依靠“数量”和“规模”的力量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从而以此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同时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也逐步分化,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也愈发严重。那些分散的、数量上众多的群体,如工人、农民以及农民工等由于缺乏或无法利用有效的政治资源和政治影响渠道,就可能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就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权利保障依赖主体的参与,而个体利益如果得不到有效组织化,则将失去有效参与的能力、信息、支持等资源;进而,分散个体的利益将在相互冲突和高成本游戏的过程中被吞噬和淹没。[2]”对于农民、工人、农民工这些弱势群体而言,畅通组织化利益表达渠道是维护其群体利益的最重要的渠道。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应将组织农业利益集团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症结的出路。许多地方发生的村民集体抗争事件也表现出村民为保护自身利益对“组织性”的需求。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40年的改革,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背后隐藏的潜伏性的危机也显露出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折射出在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中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果处置不好,则有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的振荡。“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更加关注“三农”问题,“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上,一方面需要树立和强化国家的主导作用,加强基层政府和党组织建设,以整合各方利益为前提,吸纳体制外的力量,保证农村基本政权的有效运作,实现政治整合;另一方面,在强化党和政府主导性、引领性作用的同时,要防止替代性利益表达模式的主观性、时滞性和间接性对社会群体和个人表达利益诉求动力的抑制。
组织化利益表达也是维护失去原有庇护关系的下岗工人和政权体制外的农民工的利益的重要方式。随着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化,原有的单位体制、国企管理方式、产权制度和人事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企事业单位和职工之间依赖性的庇护关系逐渐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提出通过推动工人、农民工的组织化来保障劳工的权益,这其中可能会涉及到工会组织的功能和性质的转变。
组织化利益表达最重要的作用是能够推动组织性社会力量的成长,以此来增强那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力量,但这是否意味着由此可以防止和制约那些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并不能带来预想中的相互竞争和平衡,由于人数众多而获利不确定性,那些弱势群体所形成的组织性的社会力量往往难以形成切实的行动力量,也就无法抗衡那些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财力雄厚、行动紧密有效的以资本为核心的特殊利益集团。组织化利益表达中潜藏了不平衡的利益代表所导致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萧功秦先生也曾指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环境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只能是使那些以垄断性排他性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在“民主政治”的护身符下更加肆意妄为,借助于特殊关系和“软政权化”,不断蚕食国家权威力量。萧功秦进一步指出,只有在发达的公民社会、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和长期经济发展形成的信守契约关系等社会因素下,利益集团民主政治才能够有效施行。也就是说,利益集团要在民主政治系统中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定的配套因素与之适应。多元主义者在西方民主模式下形成的利益集团理论有其时空局限性。利益集团的非均衡性是一个难以破解的结。对竞争性利益集团民主政治比较乐观的学者又提出:是否因为对利益组织化表达的压制才导致缺乏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来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膨胀?拉美国家的情况以及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组织化利益表达并不总能发挥这种遏制作用。俄罗斯社会转型,民主制的确立并没有带来组织性社会力量的成长,相反却出现了所谓的“国家分封化”现象。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瓦解,新政权建立后虽然开放了利益组织化渠道,工会等组织的力量依然薄弱难以对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在一些后发国家,政府为特殊利益集团捕获而失去自主性,国家为特殊利益集团支配,丧失了超越社会经济利益的公共性。
这样,对利益集团政治比较谨慎的研究者和比较乐观的研究者,在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出路上产生了分歧。但他们都认为保持国家的自主性,使国家拥有超越集团的利益和目标是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根本方式。问题是,如何才能保持国家的自主性,是通过畅通组织化利益表达渠道来防止原子化利益表达方式的侵蚀,并提供克服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改革动力,还是通过国家建设,塑造一个有效政府来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对国家的支配和操控。[3]这里又涉及到对组织化利益表达和国家自主性的认知问题。
2.组织化利益表达与国家自主性和内聚力。在关于中国利益表达的研究中,研究者们注意到,在组织化利益表达缺失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这样两种消极的局面:一方面,分散的、未经组织的大多数,只能采取原子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如通过庇护关系追求个人利益,或者通过非制度化的“无所事事”和“无所顾忌”的极端方式表达利益,从而侵蚀国家的自主性和凝聚力;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采取有效、理性行动的能力,未能提出步调一致的主张和诉求,分散的利益也无法得到组织化的整合、放大与协调,因而也就难以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
在国家权力集中的情况下,国家垄断了广泛的资源和权力,在“工厂政治”“单位政治”形式下不会有完全原子化的个体,当然也未能出现数量众多独立自治的社会团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可以通过类似于庇护关系的社会网络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其中包含各种策略性的利益表达。为什么说这种以庇护关系网络为主要渠道的利益表达方式会不利于国家的自主性和内聚力呢?庇护关系网络不是为公民提供了一种追求自身利益的空间和渠道吗?研究者发现,这种庇护关系网络会产生两方面的消极后果:其一,虽然庇护关系使得人们从中获取一些边际利益,但它却分割了社会,使得人们不愿意在社会上形成平行的利益同盟,从而难以组织起来进行组织化利益表达以求影响政府决策?鸦其二,人们通过特殊主义导向的庇护关系侵蚀着国家的内聚力,显现出一个貌似强大却很虚弱的国家,即国家垄断了广泛的资源和权力,但实际上却难以实现它。[4]
在印度和许多拉美国家的政治文化中,通常存在两种类型的庇护关系,一种是“依赖性庇护关系”(Dependent clientelism),它强化了官僚机构中的权威等级和官员对上不对下负责的政策执行方式,在事实上加强了国家的基础权力;另一种是“共生性庇护关系”(Symbiotic clientelism),在这种庇护关系中下层官员倾向于通过对政策的扭曲执行来维护部门利益,或者通过权力寻租,在市场中寻求利益回报,在事实上损害了国家的基础权力。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可以看到。社会学者孙立平先生认为,在社会转型期过程中,地方部门利益和庇护关系是蚕食国家自主性的最主要因素。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缺失使得各种关系盛行,国家内部的改革派无法获得来自社会的组织化利益表达所提供的改革动力,多数情况下难以克服地方和部门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形成的改革阻力。只有通过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渠道,才能使国家和社会关系走向制度化和常规化。组织化利益表达是改变既有利益格局的动力和压力来源,会为改革力量提供支持,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化和公平公正等价值目标的实现。
但在另一些学者看来,组织化的社会力量并不是在所有国家转型中都能够提供改革的动力,也并不总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现实政治发展中,自主的国家更能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发挥关键性的力量。在发展中国家,一个强有力的占据主导性的政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鲜明的事实就是中国改革实践的成功。有学者指出,如果不能把组织性的社会力量吸纳到政治经济改革过程中,如果民众利益在得不到有效表达,中国的一些改革措施,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价格双轨制,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离,军队改革,“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渐发展的格局等就不可能成功,而事实上理论上这些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改革已经发生或已实现或正逐步进行。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逐步推行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理论假设上,将政府视为会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掠夺者而阻碍改革,只有聚合利益团体的组织性力量,才能对政府构成控制防止政府的“异化”。这种理论设定并不符合现实的情况,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改革过程。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一個强有力的政府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不会形成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也不会为大资本集团所控制,形成“管制俘获”。
3.组织化利益表达与政治稳定。开放組织化利益表达是有利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还是会成为社会政治动乱的根源?同样的理论设定和管治模式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在什么情况下对利益集团政治的限定和压制会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绩效?在多元主义者看来,组织化利益表达是政治系统平衡稳定运行的基础,是政治系统缓解压力的泄压阀。但在另外一些研究者看来,组织化利益表达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时候才能发挥民主功效和政治稳定作用,若一国政治制度化落后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的发展,则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甚至体制的崩溃。
系统功能分析理论认为,政治系统的正常运作需要一个有效的输入机制,能够将社会各种需求和要求输入到系统中,经过调节和决策的转化过程最终变成政治系统的输出,输出又会影响环境产生新的输入,新的输入又会进一步导致政治系统新的输出。在此过程中,组织化利益表达是整个系统关键的输入机制。在输入、调节、决策、执行和反馈这些政治系统的核心环节中,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缺失会导致系统输入的不足,系统也就难以通过内在的机制调节压力。有众多利益诉求却无法通过组织化等有效的途径表达,暴力和游行示威等破坏性方式就会成为人们的选择,从而导致政治的不稳定。阿尔蒙德认为,对组织化利益表达的压制并不能消除实际上的社会分裂和冲突,只是暂时的把矛盾掩盖住而已,最终可能会因“参与的爆炸”而导致政治系统发生突变。在第三世界官僚权威主义的研究中,为了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和推进经济改革进程,会对任何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尤其是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都表现出高度的强力控制,这种措施在改革初期会见经济成效,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群体的形成和组织化的增强会对官僚系统构成极大的压力。也就是说对利益组织化表达的压制会埋下政治不稳定的种子。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因土地征用、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城市管理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对党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形成干扰,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为此,政府每年要支出大量的维稳费用,造成财政上的压力,同时,相关利益受损者的诉求也不一定总能得到有效解决。这就需要运用法治思维,保持有效的政治沟通,通过制度化建设,畅通包括组织化利益表达在内的利益表达渠道,维护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
组织化利益表达的开放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时机。条件不成熟或时机不对,则会对政治稳定不利,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对整个政治体系也会形成很大的冲击。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在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以国家自主性、内聚性和适应性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不断膨胀的组织化表达诉求的发展,从而导致国家自主性的丧失,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控制,从而造成政治的不稳定和改革的失败。许多后发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会在政治上对利益组织化进行压制,以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和对改革过程的主导性,因为此时段对劳工运动和劳工组织妥协,相应的经济改革政策则会陷入停滞状态,同时国家必须恰当地平衡这种政治势力,避免政治激化和社会稳定。到经济自由化完成后,政治民主化、制度化程度提高,政治系统则需要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渠道,吸纳社会其他阶层进入决策过程,平衡社会各方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否则政治统治联盟就会发生分裂。研究者对韩国、日本、希腊、叙利亚以及台湾地区的比较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
三、方向与趋势:制度框架内的组织化利益表达
通过以上的理论与实践的考察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所潜藏的危险与其积极的民主功效一样是真实存在的。在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需要保持有强大的自主性和控制力来应对这个过程中的若干挑战,包括制定正确有效的政策、维持自身的权威性、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和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带来的社会动荡。一个后发国家的成功转型不仅意味着在经济上要取得显著成效,政治系统的制度化建设水平也应得到极大提升。
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和社会的失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必须在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之间做好恰当的平衡,缓解利益表达组织化和经济改革之间形成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国家如何处置社会分化和利益表达组织化问题,二是如何控制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如何处理好国家自主性与政治系统的包容性之间的关系。
对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一方面是国家制度化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国家制度的内聚性和适应性仍需要大力加强,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利益组织化程度还很低,与事实上的社会利益分化程度不相称。鉴于这两方面问题的同时存在,需要我们在国家政治建设和推动利益组织化改革上进行理性的选择。因为在加强国家自主性,提高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主导性和操控力,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对权力的侵蚀,同时也可能会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化形成压制,进而会忽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如果我们承认当前社会利益分化和继续发展的事实,承认通过利益组织化可以带来深化改革的动力,我们可以选择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实现组织化利益表达模式的改革与突破。事实上,“法律型的组织化利益表达”也是现行体制所承认和容纳的利益组织化类型,尽管存在着独立性弱、依赖性强、公众信任度低等问题,通过适当的改革与制度设计,提升其利益代表性和行动能力,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选择。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型组织化利益诉求”的组织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利益组织化的一个“样板”。当然,要推动中国社会利益组织化的发展,还需克服体制上和观念上存在的一些障碍。
参考文献:
[1]Authur Bentley The Processof Government 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c1995.
[2]王锡锌.利益组织化、公众参与和个体权利保障[J].东方法学,2008,(4).
[3]Shaoguang Wand″The Problem of State Weakness”Journal of Democracy Vo1.14,No.1,2003.
[4]Vivienne Shue The Reach了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tandFord Galif.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c1988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93.
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