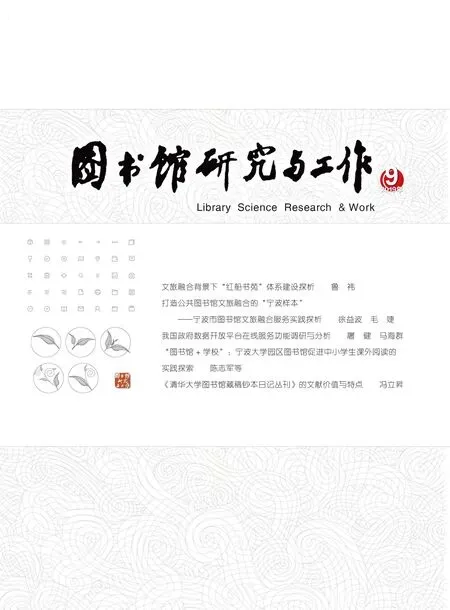吴大澂批校本《文选》考
南江涛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吴大澂(1835—1902年),初名大淳,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代官员、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民族英雄。清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吴大澂精于鉴别和古文字考释,亦工篆刻和书画,其书法以篆书最为著名。诗词及散文也颇具特色。著有《愙斋诗文集》《说文古籀补》《字说》《愙斋集古录》《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试验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吉林勘界记》《十六金符斋印存》等。传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七、《清代七百名人传》、《续碑传集》等,又有自著《愙斋自定年谱》、顾廷龙撰《吴愙斋先生年谱》等,记述其生平著述尤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著录,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吴大澂批校本《文选》,笔者认真翻阅此本,作一点初步的考察,供大家参考。
1 吴批《文选》概况
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吴大澂批校本《文选》六十卷附《考异》十卷,南朝梁萧统撰,唐李善注,清同治八年(1869年)湖北崇文书局翻刻胡克家刻本,两函二十四册。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版心记卷次、页码。检胡克家原刻本[1],与此翻刻本行款基本相同,但板框为左右双边,版心除了卷次、页码,还有大字小字字数和刻工姓名,在细节上略有不同。
此本卷端有吴湖帆跋语:“愙斋公手书批注本,吴氏梅景书屋家藏。”卷内有“梅景书屋”白文长方印、“吴湖颿”朱白文方印、“某景书屋”朱文长方印、“吴潘静淑”白文方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朱文白方等印。吴湖帆(1894—1968年),系吴大澂之孙。初名翼燕,字遹骏,后更名万,字东庄,又名倩,别署丑簃,号倩庵,书画署名湖帆,是20世纪中国画坛重要画家之一。他收藏宏富,擅长鉴定和填词。著有《梅景画笈》《梅景书屋全集》等。潘静淑(1892—1939年),名树春,潘祖年次女,是吴湖帆的夫人。吴湖帆的跋语和印记可以确定其为吴大澂批校无疑。
除了批校内容,卷内尚有吴大澂朱笔识语十处,颇有价值,今移录于此:
卷一第十三叶上:“同治辛未八月既望,校十二叶。是日阴雨杜门,鹤巢来。”
第二十三叶上:“十七日校十叶。”
第三十一叶下:“十八日校至此。”
卷二第十叶下:“十九日校十叶。”
第二十九叶下:“二十一日校至此。”
卷三第十叶下:“二十七日校十叶。”
第二十叶下:“二十九日校十叶。”
第三十五叶上:“九月初二日校至此。”
卷四第十二叶上:“初三日校至此。”
第二十一叶下:“初十日校十叶。”
从以上识语,吴氏清楚记录了他批校此部《文选》的具体时间,即清同治辛未(1871年)八月十六日起到九月初十日止。查《吴愙斋先生年谱》,本年吴氏在京师散馆考列一等第三,受编修。八月间,具折奏请裁减大婚典礼工费,由翰林院掌院代奏。期间直隶先是亢旱成灾,继而大水,顺天、保定尤甚,绵延四五百里,故而吴氏疏画救灾方略。政务之余,吴氏仍批阅《文选》数卷。他批校《文选》,如同读其他经典一样,将逐页校读当作一段时期内的日课,定量阅读。如他二十一岁(1856年)时,随陈奂读段注《说文》,每日读二三十叶,除了向硕甫先生问学《说文》,仍坚持读《程子易传》[2]6。在《吴愙斋先生年谱》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读书法,足见其是早年养成的学习习惯。
2 吴大澂关注《文选》情况考察
吴氏对《文选》的关注与阅读,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苏州一带文人士子对“选学”的普遍重视;二是周边关系密切友朋的影响。
首先,所处苏州的地域特殊性。明清两代的江南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其中尤以苏锡常地区为著。苏常地区受人文历史多重因素影响,特别推重六朝文学。具体到《文选》,则明代有张凤翼《文选纂注》被广泛翻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待到清初,苏州钱陆灿、俞瑒、何焯、潘耒等人发扬评点《文选》之学,尤其何焯本后来被刻印或收录到《义门读书记》、叶树藩刻海录轩本《何义门评点文选》和于光华《文选集评》三书,沾溉后学良多。以现在存世的《文选》批校本来看,以学习过录何批者最多,而钱陆灿和俞瑒也占有相当比重。这些为苏州地区习读《文选》提供了先天优势。翻检《中国古籍总目》所录清人文选学著作和批校本,苏锡常地区的学者所占比重超过了1/3。这样的人文地理环境对吴大澂的浸润作用不容低估。
其次,周边友朋的影响。上文识语所言“鹤巢”,乃许赓飏,即许玉瑑(1828—1894年),字起上,号缉庭、鹤巢,苏州人。同治甲子年(1864年)举人,入中书舍人,转至刑部侍郎。清末词人、藏书家,藏书数万卷,室名“诗契斋”。其与端木埰、王鹏运、况周颐三人唱和词集刻成《薇省同声集》行世,成一时风雅之事。著有《诗契斋诗钞》六卷、《诗契斋骈体文录》十八卷、《丛稿》三卷等。许氏对《文选》颇有研究,今湖北省图书馆藏有清何惟杰跋并录许赓飏批校本《文选》,又王同愈也曾据其批校本过录,在王同愈批校本《文选》序有:“甲辰三月十六日,用许鹤巢丈校勘本录校。许以旧校湖北重刻胡本点勘。”[3]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湖南图书馆藏有一部同治十一年(1872年)赓飏批校本《文选》。检《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未见此本,按照版本排查,我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罗琴老师帮忙翻阅了该馆所藏清同治八年(1869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4]。虽然《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没有著录批校信息,但卷内确实有朱笔圈点校勘,但卷内无序跋印章,或许为他人过录本,有待仔细比对考察。又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一部光绪十九年(1893年)许玉瑑朱笔批本《文选》。于此,足见许氏对《文选》一书的关注及其影响。由于同乡关系,吴大澂在京师时与许鹤巢交往密切。《吴愙斋先生年谱》云:“先生旅京后……师友之往还最密者,李虎峰而外,为镜笙(平步青),哺盦,伯寅(潘祖荫),芍亭(彭祖贤),鹤巢(许玉瑑),缉庭(顾肇熙),叔涛(刘廷枚),安圃(张人骏)诸人。”[2]24
特殊的地域、友朋的影响,加之自身的需要,吴大澂对《文选》一书自然也颇为关注。在批校该本的前一年,也就是同治九年(1870年),吴氏由武汉出襄阳过洛阳入陕西登华山途中,四月十七日他在襄阳登昭明台,上有古楼,即文选楼[2]31。此文选楼原为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建,集刘孝威、庾肩吾等十余人,于此辑《文选》一书,故名。途中在西安,七月初六日傍晚到古董铺购得汲古阁《文选》一部,潘稼堂手批本[2]34。潘稼堂即潘耒(1646—1708年),清初学者,字次耕,一字稼堂、南村,晚号止止居士,吴江(今属苏州)人。师事徐枋、顾炎武,博通经史、历算、音学。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主纂《食货志》。其文颇多论学之作,也能诗。善藏书,藏书室名遂初堂、大雅堂。著有《类音》《遂初堂诗集》《文集》《别集》等。潘稼堂既是乡贤,其手批《文选》于吴大澂来说,无异于如获至宝。当然,从下文分析来看,吴大澂批校《文选》时,并非据此藏本。
3 批校内容辨析
此本并非通批,吴氏批校主要在卷一至卷四第二十一叶,另卷五十五略有几处,其他卷次均未校读,或许是当时赈务繁忙所致。吴氏批校,包括圈点和批语两部分内容,用朱、墨二色。其中以朱笔圈断《文选》正文,朱笔点断注文;间以朱、墨笔标抹,又用墨笔过录批语于天头和行文之中。篇末总评,偶用墨笔过录。下面我们分别择要过录数条,分为天头批语、篇末评语两类进行辨析,以明吴氏批校内容之来源。
首先看天头批语:
卷一:
(1)《两都赋并序》题上:“《两都》一开一合,以‘宾’‘主’二字见意,其赋之意处全在末二句中,见作赋之由,存劝戒之体也。”
(2)“赋者,古诗之流也”:“本于《三百篇》,所以可重。”
(3)“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纪年”:“以歌荐庙、以瑞纪年应‘乐府协律之事’,言语侍从诸臣应‘金马石渠之署’。”
(4)“国家之遗美,不可阙也”:“宽转数句,文势雍容,然后总收到作赋之由。”
(5)“折以今之法度”:“此宾主设问难之由,全以‘眩矅’‘法度’为二赋眼目。”
(6)《西都赋》“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铺叙中仍见西京典故,此于极力眩矅中不失前辈典型所在。”
(7)“辇路经营,修除飞阁”:“自内及外,自周庐阁道渡下离宫,接法紧。”
(8)“自未央而连桂宫”:“自未央、桂宫、长乐以及建章,未央即上文所称,下乃专写建章也。”
(9)《东都赋》“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功、德二字收住建武一段。有笔力。”
(10)“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此下言永平之事,乃寔举当时制度也。与序中清平无事数语相应。”
(11)“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提纲。”
(12)“填流泉而为沼”:“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诸事已备见于此段中。”
卷二:
(13)《西京赋》题上一:“《西京赋》全祖孟坚而语加峭拔铺张尤甚,此长篇之极轨也,孟坚意主和平,平子多含讽刺,看其《两都》开合之处,用意深婉。”
(14)题上二:“《西京赋》与《西都赋》体制略同,然《西都》主炫耀,而颇饰以怀旧之思,此则全以心奓体汰为主,极力铺张而出。”
(15)“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怂兢”:“写楼台高峻,大都本之相如,然各自有笔法,而铺张之盛至平子而极。王文考《鲁灵光》又加诡隽矣。”
(16)“天梁之宫,寔开高闱”:“天梁一段撰写千门万户,阁道相通,为建章生色。”
卷三张平子《东京赋》:
(17)“于是观礼礼举仪具”:“针砭奢侈,特拈礼字,此赋中主意。”
(18)“春日载阳,合射辟雍”:“前言明堂,此及辟雍,为三宫点缀也。大射古礼永平所举行言之较详,以见礼备乐举意。”
卷四左太冲《三都赋序》:
(19)“《三都》立局与《二京》不同,意是推重魏国,然亦不肯略吴、蜀也。吴、蜀、魏三层洗发,顺看长短详略处、相称处。”
(20)“太冲意致绵密,异于班、张,然思愈周则力愈缓,气愈敛则格愈平,至其典确征实,为前人所难,故足多也。”
以上所录20条,比对《文选集评》《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义门读书记》等,所见不多,可见其来源并非以何批为主。以赵俊玲《文选汇评》[5]中各条比对发现,除了第11条源自郭正域《新刊文选批评前集十四卷后集十三卷》,第20条为钱陆灿批语,其余各条均见于俞瑒评本,只有个别字词略有差异。第18条虽然未能在《文选汇评》中对应位置找到,但从批语内容判断,应该也是俞瑒之语。
其次,看卷末评语:
(1)卷一末:“相如、子云之赋,宕逸纵横,不可方物;孟坚始绳趋矩步,温雅淳深,有典有则。正如变《史记》为《汉书》,奇俊虽灭,而体裁俱备,后人不得不奉为楷模也。”
(2)卷二末:“《西京》一赋可谓呈靡丽之思矣,然须看其用意一线贯穿,措词分曹按部,寓纵横与整肃之中,斯为能事耳。”
(3)卷三末朱笔:“虽以班赋为骨,而使事铸辞倍加功力,《西京》则故实该详,《东京》则辞锋条畅,仿而不袭,故能与《两都》并传。”
(4)墨笔:“平子《东京》与班氏《东都》不同。班氏全祖《长杨》,以虚运成文,平子却于首尾用虚,中间用实,历叙典制,炜煌陆离,自成一格,古人之不肯蹈袭如此。”
从所录4条篇末评语来看,第2条和第4条源自俞瑒批语,第1条源自邵二云[6],第3条未能查到出处。
上面所录可见,这些批语并非吴大澂自己的发挥,而是对前人校读《文选》一书成果的过录承继。将这些条目比对《文选集评》《昭明文选集成》等书所录“俞曰”,明显多出不少,且文字差异较大。俞瑒,字犀月,苏州吴江人,生活于清康熙年间,曾与顾嗣立同选《元诗初集》,又有评点《杜诗》等。他最突出的成就,是对《文选》的评点,对后世《文选》评点影响较大,但可惜的是除了上述选学著作摘录一些条目,没有专书刻本传世。赵俊玲《俞瑒〈文选〉评点探析》以浙江图书馆所藏佚名录俞瑒批校为主要对象,对其评点的内容和价值做了探索[7],并在其《文选汇评》一书中将俞瑒批语一一过录。通过比对,我们可以推测,吴大澂批校《文选》所据应当是前人过录的以俞瑒评点为主要内容的《文选》本子。从批语高度重合的情况来看,此本对俞瑒评点内容过录比较全面,并兼顾了少量郭正域、何焯、钱陆灿、邵晋涵等人的评点内容,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较高的研究价值。遗憾的是,吴大澂并未能将全书悉数过录,我们只能从幸存的吉光片羽去推断其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