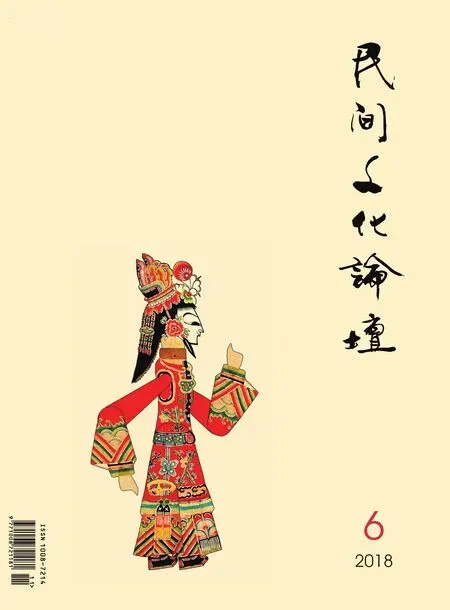民俗关系:定义民俗与民俗学的新路径*
王霄冰
“历史进程中的‘民俗’概念”
民俗的定义与民俗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困扰学界同仁久矣。当代的学科理论研究几乎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民俗学内部曾提出过多少方案,外部对于民俗学的了解却越来越模糊。民俗学到底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民俗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仍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实际的研究当中,除民间文学之外,民俗学的传统领域如物质文化、民间信仰、家庭与社会组织、岁时节日与人生礼仪等,都不断地被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新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所蚕食和分割。民俗学在现代学术中有被日趋边缘化甚至被取代的危险。为此,在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建立百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民俗研究的对象与视角,以探寻定义民俗和民俗学的新路径。
对我的这一思考有直接启发的,是美国民俗学会现任会长陶乐茜·诺伊斯(Dorothy Noyes)的《民俗的社会基础》一文。她从“民俗”的最早构词形式Folk-Lore出发,道出了一个长久以来为民俗学者们所忽略的潜在事实,即:“‘民众’(folk)和‘知识’(lore)之间的连号也预示了这个学科的关键问题。知识体系和民众群体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常识性关系?学者又应该怎样定位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原来民俗学所要研究的并不只是民俗事象,描述其生存形态并解释它们的来源,甚至也不仅仅只是要去解读“语境中的民俗”,而是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预示着这将是一门以研究民与俗的关系即社会与文化的关系为己任的学科。诺伊斯的这一发现令我茅塞顿开,之前很多没有理清的问题好像瞬间都有了答案。她紧接着又问了一个问题:“这种联系是否会随着时间而消逝?”遗憾的是,诺伊斯在这篇论文中虽然提出了这些问题,但并没有进行回答。她的文章主要聚焦于作为民俗之社会基础的“民”是否是一种实质性的存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流派的民俗学者如何界定“民”的社会存在。她在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民俗学家应持续地关注民俗的社会基础,因为这是我们学科生存的根本。①
本文试图使用社会发展的观点重新审视民与俗的关系(以下我将称之为“民俗关系”),并决意以此为突破口,结合民俗概念的研究史,探寻重新定义民俗和民俗学的新路径。
一、概念史的反思
在我们试图理解民俗为何物时,“民俗”这个术语本身就成了解题的关键。这是由于民俗并不是一个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词汇,而是学者为了概括各种千奇百态的生活文化现象而特意创造出来的学术用语。它在造词法上由Folk和Lore两个带有意义的词根合成,于是,这个概念就给民俗学家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和阐释空间。围绕着“谁是民”“何为俗”的问题,民俗学者们展开了对于民俗学学术本位的思索。
董晓萍在《现代民俗学讲演录》中曾对民俗的概念史进行过全面的梳理。她把外国民俗学对“民”的定义分为“殖民主义、欧洲发现时期与自然科学时期”“现代化时期”和“全球化时期”三个阶段。人们对于“民”的理解,从最早的“野蛮人、原始人,未受学校教育,没有文化”“迷信的人们”“农民”“常民”“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人群”“民族全体成员”等,到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社会的“小人物”,“任何拥有独特的口头传统的人”,按照职业、年龄、地区、国籍划分的民众群体,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语境下的“传统的匿名的群众”(德国)、“所有民间群体,被民俗定
① 参见 Dorothy Noyes, “The Social Base of Folklore”,in: Regina F. Bendix & Galit Hasan-Rokem (eds.), ACompanion to Folklore, Malden, Oxford &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2, pp.13—39.型的社会成员”(美国)、“世界民族志的平行承担者”(英国、法国)和“享有共同民俗的人”(日本、韩国)。在中国国内,民俗学对于“民”的认识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分别为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二分法”、20世纪70年代后的“文化三分法”和现代化阶段的“民族共同体的一分法”。甚至在钟敬文先生主编的几本《民间文学概论》和《民俗学概论》中,也可找到5种不同的“民”的定义:“劳动人民”(1980)、“中下层阶级”(1992)、“非官方群体”(1998)、“农民主体”(1998)、“民族共同体”(1999)。①详见董晓萍:《现代民俗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35页。
高丙中在其对当代民俗学有重要影响的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分别用专章探讨了“民俗之‘民’:学科史上的民俗学对象(上)”和“民俗之‘俗’:学科史上的民俗学对象(下)”的问题。他首先批评了英美民俗学史上把“俗”作为可以脱离“民”而独立存在的文化现象来研究,认为“他们的研究目标通常是文化性的‘俗’,而不是现实性的‘民’”。从汤姆斯时期的“大众古俗”和“民众的知识”,到人类学派民俗学家笔下的“古代遗留物”,和美国文化人类学所关注的“口头文学”,以及多尔逊、邓迪斯等当代美国民俗学者主张的“传统民间文化”和“传统民俗形式”,也就是民众群体的传统,对于民俗的概念史高丙中提出了他的质疑:“为什么民俗学家们总不能勇敢地面对民俗构成了人的基本生活这一事实呢?人类群体约定俗成的东西那么普遍,那么广泛,为什么人们却只承认那些具有古老形式的东西才是民俗呢?”②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6—75页。他继而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俗学界江绍原、杨成志等人根据欧洲大陆的民俗概念提出的“民学”的观点出发,根据钟敬文先生在80年代提出的“民俗的范围应该是整个民间文化”的主张,并参考了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孙末楠)的民俗理论,最终形成了如下的民俗概念体系:
民俗——“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
民俗生活——“民俗主体把自己的生命投入民俗模式而构成的活动过程”。
民俗模式——“生活世界中的完整的表演程式或程式化表演的剧本结构”。③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42—146页。
把民俗研究在范式上从朝向过去而扭转为朝向当下,并在民俗概念中引入了“民”这一实践主体,把民俗从静态的文化事象变为了活态的、人的行动过程,是高丙中这一论著的最大贡献。他最早明确提出了“在俗之民”即民俗主体的概念,指出民俗学应研究民俗过程中的人而不是生活中的任何人:
民俗之‘民’并不等于生活中的人,只有当生活中的人表现出民俗之‘俗’时,民俗学家才在这个意义上把他看作‘民’。生活中的人是完整的、完全的,民俗之‘民’是生活中的人的局部或片面;生活中的人是终日终年终生意义上的,民俗之‘民’是某时某刻意义上即是时间片段意义上的。所以,以‘俗’定‘民’,以‘俗’论‘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④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8—29页。
这一发现得到了吕微等民俗学家的高度评价,因为它“彰显了民俗学的基本问题——人自身的主体性存在意义和价值”。“就民俗学是一门通过研究民俗而反思人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的学问,为民俗学辩护也就是为人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存在意义进行辩护。”⑤吕微:《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上),载朝戈金主编《中国民俗学》(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3页。
然而,即便在高丙中的上述概念体系中,民俗关系也未能成为关注的焦点。以往的学者们或者专注于作为文化事象的“俗”,或者像诺伊斯那样,聚焦于作为民俗之社会基础的“民”,虽然都在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但很少专门去研究民与俗之间的关联方式及其所产生的意义。甚至有民俗学者主张,民俗学者在实际的研究当中必须在民或俗之间有所侧重。民与俗虽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二分法“有助于保持立场鲜明,使人坦诚正直”。“尝试消除两者间的鸿沟,并合二为一,或者彻底地杜绝二分法的出现,这些都是没有益处的。”①[美]爱略特·奥林:《民或俗?二分法的代价》,张茜译、张举文校,《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说这话的人是美国人类学家爱略特·奥林,但他的文章讨论的并不是民俗的概念或研究对象问题,而是民俗学者应如何处理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即到底应“以道德的方式”还是“以理智的方式”研究民俗的问题。
也许正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民与俗是天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二者缺一不可,所以民俗关系才长期地为民俗学家们所忽视。然而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要解释事物与事物或者人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不能因为这种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就不再去深究、描述和阐释它们。况且,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应强调系统性,既然前人已对“民”的性质和“俗”的范围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已经注意到了“民”作为行动主体和“俗”作为行动对象之间的关联性,那么,进一步探讨不同历史阶段中和社会形态下具体的民俗关系,即民对于俗的认知态度及其作用于俗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不同的文化意义,也就是必要且可能的了。
二、宏观民俗史视角下的民俗关系
当我们把民俗关系这一概念引入到民俗学的本体研究时,还必须同时引入一种社会发展的观念与视角。这是因为民俗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着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属性。中国的当代民俗学由于受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影响颇深,所以虽然在民俗史与民俗学史的资料梳理、个案研究方面已有十分丰富的成果,但真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民俗生存形态变迁的宏观民俗史研究却相对缺乏,只少数民俗学家有所涉及。例如萧放在其论著《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曾试图阐释岁时观念从史前、上古直至中古时期的变迁及其对岁时节日体系的影响。他认为,“民俗的前期形态经历了史前民俗、上古民俗及上古民俗转变的若干阶段。”在谈到“史前至上古时期是民众岁时观念发生的时期”时,他使用了社会分层的概念,并注意到了岁时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
......虽然月令时代,时间总是掌握在王官手中,由社会上层颁发的时政往往首先考虑的是统治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周秦以前的社会里,上下层的分化与对立没有后世那样明显,相当部分的政令带有集体性、全民性的特点,如对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活的安排,以及对家园的保护等。月令的政治性质如前所述在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上得到具体体现。月令与后来岁时生活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②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页。
在探讨汉魏时期的岁时民俗时,萧放也循着这条思路,分析了春秋战国以来宗族公社的解体与个体小家庭的成长对民俗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国家民户的巨量增加不仅为新的统一的国家建立提供了社会物质基础,同时脱离宗族控制的自由民的大量出现,也使传统的礼制变得不合时宜。”“月令时代的社会生活虽然仍定期举行宗教祭礼,但此时的祭礼正在朝王家祭仪的方向演变,原始的全体参与的古代宗教祭祀集会正逐渐转化为王朝统治集团的世俗的政治性的时间典礼。......岁时节日系列逐渐形成,魏晋以后新的岁时观念才真正确立,中国岁时节日体系初步完成。”①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7页。
虽然萧放这部论著的重点,仍然放置在了对于岁时观念和节日体系的描述上,而未能着重分析社会结构与民俗生活的对应关系,但它从上古向中古时期过渡的社会形态出发探索节日体系形成过程的尝试,对于后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民俗作为一定社会阶层的文化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必定也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因此,历史民俗学的研究不仅可以结合当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来展开,同时也可以从宏观上去把握一定历史时期的民俗总体特征。在此,我们或许可以借用历史学中的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的理论②宏观史学的代表为法国的“年鉴学派”,倡导总体史、“长时段”与跨学科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直至80年代,该学派推动了一场“新史学运动”,为史学界贡献了新的理论视角与方法论。参见张正明:《年鉴学派史学理论的哲学意蕴》,黑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提交。,视前者为“微观民俗史”,而将后者定义为“宏观民俗史”。
结合当下的状况,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正经历着从传统的礼俗社会过渡到复合型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当中。社会学家滕尼斯把这一变化归纳为是从共同体(德语:Gemeinschaft;英语:community)到社会(德语:Gesellschaft;英语:society)的转变。③[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共同体”在中文中又被翻译为“社区”“自然社会”“礼俗社会”,④参见朱刚:《从“社会”到“社区”:走向开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界定》,《民族艺术》,2017年第5期。指的是前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社会,基于地缘或血缘等天然的联系,人与人之间联系紧密、守望相助。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又被阐释为“人为社会”“法制社会”“市民社会”等,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之上而相对缺乏有机联系的现代型社会。
如果我们把过去大约一百五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概括为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个阶段,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民俗存在形态,尤其是民俗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迁。在前工业化时代的礼俗社会,人们自然而然地隶属于某一社会阶层或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践行着属于这一社会阶层或群体的固有文化形式。民与俗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联系且相对稳定,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也呈现出较强的规律性和群体一致性。也就是说,传统社会的每一社会成员都几无例外地担负着传承民俗文化的天然职责,而民俗实践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文化的秩序与记忆。无论是大文豪鲁迅笔下的“鲁镇”还是社会学家费孝通眼中的“江村”,都是这一社会形态的典型代表。这里不妨就以鲁镇的“祝福”礼为例,说明传统社会中的民俗关系:
......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⑤鲁迅:《彷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在这里鲁迅用文学的语言描述了“鲁镇”这一地方性社会共同体及其中的每一个人与祝福礼的关系。首先,祝福作为年终的大典是必不可少的,家家、人人都要参与,它具有迎春接福、求拜好运的神圣意义;其次,祝福礼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包括物质的、时间的、性别角色等方面的秩序与规则;第三,祝福礼作为社区的传统得以年复一年地传承,年年如此,今年亦如此。这样的一种民俗关系我们可以定义为是天然的或默认的,表现为每个社会成员都会不假思索地投身其中,既没有选择的可能,也没有反思的必要。
在工业化时代到来的现代社会,也就是鲁迅本人所处的时代,民与俗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断裂。传统的日常生活秩序开始解体,像鲁迅这样的进步人士开始反思身边的民俗传统并加以批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俗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或是现代人重构日常生活时的一种参照物。传统的日常生活文化变成了“旧俗”和“陋俗”,变成了人们建构新生活时所必须摈弃和改革的对象,正像“破旧立新”一词所表达的那样。于是,“革命”就成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爱使用的一个关键词。20世纪初的“男剪辫、女放足”是“革命”;30年代国民党政府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也被宣传为是当时“革命者”先进性的一种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革命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50年代的男性时尚穿着的“人民装”和女性爱穿的“列宁装”,便是革命者的一种外在身份标志。在“文革”时期,国家甚至一度提倡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即春节期间不放假、不休息而坚持生产。
对于发生在20世纪的这场日常生活革命,高丙中最早敏锐地意识到了它对于民俗学的深刻影响。他在《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一文中,通过观察春节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变迁发现:
……随着现代化在中国的发展,人口中能够与现代性的指标(居住在城市,受现代教育较多,直接受雇于政府部门)发生直接联系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对现代性的想象越来越多地成为现实或具有更多的现实性。他们对民俗的不认同使只要是与民俗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容易被认同为现代生活而被接受。作为这种社会过程的结果,原来的日常生活逐渐失去了普遍性,成为与现代性相对的传统,最后真的在社会生活中向文化遗留物退化。①高丙中:《日常生活的现代与后现代遭遇:中国民俗学发展的机遇与路向》,载高丙中:《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民俗学的路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8—190页。引文出自第182页。
在《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关系的表述》一文中,高丙中系统研究了过去九十多年中元旦和春节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竞争关系,以及最后趋向于“复合”的事实。“元旦以及推崇它的新国家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与春节以及习惯它的民众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之中。双方的关系在近百年里从原初的替代转变为今天的互补,从各自独立的两个节庆转化为一个过渡礼仪的完整结构的两个部分。”“从文化资源(要素)的来源而言,我们生活在一种复合文化之中。”②高丙中:《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关系的表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这一结论可以说是对中国人民俗生活百年变迁图像的一个最好描述。近年来,周星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把‘生活革命’视为民俗学的一个专业用语”,用以解读“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持续变迁以及中国人生活方式多彩的变化”③周星:《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他本人所从事的“生活革命”系列研究,涉及到服装、饮食、厕所等常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采取了把事象放置到不断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去观察的研究范式。
到了高度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后现代社会,乡愁与传统复兴又悄然兴起,变成一种社会潮流。结合新世纪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民俗复兴”的现象。然而,无论如何,今天的社会已绝不可能回复到传统社会那样一种秩序当中,也不可能回复到革命年代那样一种高度一体化的状态,而只能维持一种多元化的、认同型的、相互制衡式的社会关系结构。传统社会中的那种民与俗的天然联系也已不可能得以重建,新型的民俗关系只能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因此,民俗作为认同标志在其中既发挥着润滑剂的功用,同时也成了不同群体或个人自我表达且与他人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方式。与此相关联的,便是今天在世界各地广泛存在的、把民俗作为身份认同标志和文化资本进行再生产的“民俗主义”现象。①周星、王霄冰:《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民俗主义·本真性·公共民俗学·日常生活》(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综上,我们把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种社会形态下的民俗关系归纳为传承、革命与认同三种类型。其中传承型和认同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然传承,在很多情况下并未具备文化认同的前提,而后者是在主观认同基础之上的自觉接受。张举文提出的“民俗认同”概念,指的就是最后这种民俗关系。他从民俗认同的特质出发,进而将民俗定义为“是以共同和共享的交际方式和习俗而构成的‘小群体’中‘面对面’的维系和重构认同的行为活动”②张举文:《民俗认同:民俗学关键词之一》,《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1期。。作为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张举文对于后现代社会中小群体的民俗交际行为及其文化认同本质十分了然,因此他也最早发现了“民俗认同”的存在及其意义,并将其作为分析工具引入到了民俗学的个案研究当中。③张举文、桑俊:《影视民俗与中国文化认同》,《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张举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土影视的民族认同情结:浅谈古琴和古埙的运用》,《文化遗产》,2013年第1期;张举文:《龙信仰与海外华人认同符号的构建和重建》,《文化遗产》,2015年第6期;张举文:《迈向民俗认同的新概念:美国散居民民俗研究的转向》,《文化遗产》,2016年第4期;张举文:《从刘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象看民俗认同的地域性和传承性》,《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正如表1所示,以上三种类型的民俗关系所对应的分别是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时代,代表着传统/保守主义、科学/建构主义、多元主义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传统型社会中,民俗的社会基础为同质性较高的血缘性或地域性共同体,民俗以“规范”和“传统”为表征,其根本意义则在于维系一种社会秩序和文化记忆。④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在革命型社会,民俗被普遍化为民族国家中的旧传统,被贴上“旧俗”和“陋俗”的标签,成为科学与理性的反面参照物,以及建构新生活的出发点与踏脚石。在后现代型社会中,民俗又被作为象征符号和文化资本得以“再现实化”,其意义在于建立民族共同体象征体系、社会及个人的文化身份,并成为小群体内部及与外部之间进行交流的媒介手段。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类型划分应全部作为“理想型”来理解,其中的概念体系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工具指南,但不能代替复杂多样的生活本身。现实中的民俗关系和民俗形态远比这些抽象的概念要复杂得多。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种社会形态与历史时期的对应关系也并非绝对,更不能完全以时间为划分标准。即便在传统时代,也不乏“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思想。①张勃:《风俗与善治: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而盛行于当代的“民俗主义”现象实际上也自古就有,因为传统社会也存在对民俗加以模仿、展演和再创造的需求与可能。另一方面,在后现代社会,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可能得到部分的保留,就像大都市中的“城中村”;或者人们依旧采取传统社会的民俗观,就像在今天的很多人眼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传承下去,而不是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那样,仅仅为了实现文化共享、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促进社区发展。或者今天也会有部分人承续革命年代的思维方式,把一些他们认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民俗视为需要革除的对象,例如前段时间在地方殡葬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激进行为,还有民间信仰长期遭受污名化的现实,等等。

表1 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民俗关系图表
三、从民俗关系出发重新理解民俗与民俗学
在厘清不同社会形态下的民俗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学术史上会出现几种完全不同的民俗定义。这些都是身处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学者,对于当时社会环境下民俗存在形态的把握与理解。从传统型的民俗关系出发,民俗最早被定义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遗留物”,所强调的是其传承的本质与文化记忆的功能。从革命型的民俗关系和建构主义出发,民俗被解构为“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文化”,所强调的是它的开放性与可塑性。但这一定义也容易导致概念的泛化与不确定性,因为事实上并非一切“普遍模式化的生活文化”都可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只有那些具备一定的民俗关系和民俗意义的生活文化才可被看成是“民俗”。从认同型的民俗关系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文化观出发,民俗则被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默思定义为“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②[美] 丹·本-阿默思:《民俗的定义:一篇个人叙事》,王辉译,《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这个定义初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实际上,它一方面继承了早期民俗学对于精神文化现象的特别关注,另一方面又从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出发,开启了表演理论指导下的研究范式,可以说是当代民俗学的一项重大理论突破。正如其倡导者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所言,表演理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以指导对一种交流的特殊方式的辨识、描述和分析,这种交流方式是是围绕着艺术性地、技巧性地展示交流技巧和有效性而进行的说话和行动的方式。”在此影响下,民俗学家和语言人类学家一样,所感兴趣的是“话语生产形式”(modes of discursive production)。③[美] 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译本序言”,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所谓“话语”(discourse),指的就是“交流性的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现代民俗学所要研究的,正是特定人群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的话语行为、以及话语实践如何使用各种符号来表达和建构社会关系。
德国当代民俗学家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huba)也强调,作为研究日常文化的科学,民俗学必须踏入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在他看来,话语指的不仅是语言、文本,而且也包括图像,比如绘画、雕塑、照片、电影,等等。他指出:
根本上来看,此类对于文化实践的描述形式所牵涉的也是文化事物的特别话语质素,即是这样的一种必要性,在固定的、不可追问的准则或传统与可以“商讨”(可以进行论证性或者象征性加工)的准则或传统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不断需要重新加以实现的。①[德] 沃尔夫冈·卡舒巴:《话语分析:知识结构与论证方式》,包汉毅译,《文化遗产》,2018年第3期。
商讨、交流、表演与话语艺术,这组概念为当代民俗学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真正使得静态的民俗事象变成了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这种商讨与交流不仅仅只是共时性的、面对面的,有时候也可以跨越时空,例如通过媒体、网络等,或者通过对过往的民俗文化进行重塑和加工而与传统对话。然而,这种以话语为中心、强调商讨和交流的民俗观只适用于资源丰富、文化多样、自由开放的后现代社会,却难以用来解释前现代社会那种相对封闭和静态的日常生活状况。因为在传统社会,交际或曰交流虽然也是重要的民俗动机之一,但却不是唯一的。只有在“当社会是以多样的思想、可变的价值观以及信息交流为根基的时候”,“理性话语”才能成为“关键性的交际、道德手段”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②[德] 沃尔夫冈·卡舒巴:《话语分析:知识结构与论证方式》,包汉毅译,《文化遗产》,2018年第3期。
由此可见,以上三种不同的民俗定义都有其局限性。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民俗的生存形态不断在发生着改变,另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民俗学者对于民俗的认知和观察视角也有所不同:有的倾向于历史,有的主张面向当下;有的注重整体性,有的注重特殊性;有的关注静态的事象,有的强调动态的过程。或许正像盲人摸象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任何一种观点可能都带有某种片面性,但它们或多或少地也都道出了部分的真理。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追求的是完整的真理及其完美无缺的论证过程,但却必须学会时时刻刻与不完整性、不完美性和不彻底性打交道。因为,只有认识到了这些,我们才能向着更高的目标出发。
基于上述对于不同社会形态下民俗关系、民俗表征与民俗意义的分析,笔者在此尝试性地提出一个新的民俗定义,以求教于诸位同仁:
民俗是一个共同体中的大部分人以传承、革命或认同的方式所维系的、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日常生活实践,其意义在于记忆、建构或相互交流共同体的生活文化。任何一项民俗都具有物质的、身体的、社会的和精神的四个维度,并包含以下四个要素:(1)谁,即民俗主体;(2)做什么,即民俗行为;(3)怎么做,即民俗过程;(4)为什么,即民俗意义。其中的民俗行为和民俗过程所反映出的,正是专属于特定时代和特定群体的特殊的民俗关系。
这个定义想要表达的是:日常生活本身往往并不具备特殊意义,民俗学只有揭示出一种生活文化实践背后的社会关联性(民俗关系)以及社会心理、价值观和精神信仰因素(民俗意义),才能将这些文化现象建构为“民俗”。在通过田野观察建构民俗文本的过程中,物质、身体、社会、精神四大维度以及主体、行为、过程和意义应成为民俗学者关注的焦点,它们共同构成了民俗实践的整体,并透射出民俗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所践行的生活文化之间的关系,包括行为背后所包含的文化意义。
在此我想举一个自己几年前调查到的例子,来说明民俗概念中各部分的结构关系。2012年农历春节期间,笔者在浙江省磐安县榉溪村的农民孔JB家过年,观看了这家的谢年祭,当地人称“谢佛礼”。笔者此前曾用法国人类学家莫斯-于贝尔的“献祭的图式”分析过这个案例,以探讨人类学理论在研究本土宗教(民间信仰)中的适用性问题。③王霄冰:《本土宗教研究的人类学视角——以儒家祭祀文化为例》,《宗教人类学》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现将该文中对谢年祭过程的描述简编后抄录如下:
大年三十这一天,我和这家的大人小孩一起,上到附近1400米高的高姥山祭拜“娘娘庙”,庙里供奉的是一位当地人称为陈十四娘娘(陈靖姑)的女神及其姐妹。男主人两兄弟、女主人和年过六十的老妈妈四人轮流挑着盛放祭品的一对箩筐,内放猪头、全鸡、发糕、豆腐、苹果、橘子、糖果、馒头、米饭、酒、茶、金箔纸做的“银两”、香、烛、黄表纸、爆竹等。因重量不轻,主人叫了年轻力壮的弟弟来帮忙挑担。随行的除他俩之外还有女主人、男主人的母亲和妹妹,再加上笔者。在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么“虔诚”地祭拜神灵其实男主人多年来也是头一次,因为他在外打工,对于家乡的旧俗也不是非常了解,而且他也不觉得祭拜神灵是一件重要和必做的事,反而觉得这有点“迷信”色彩。但今年因为有我这个客人在,为了让我能体验到他的家乡文化,所以特意按照旧俗准备了这个上山祭拜的活动。这种殊荣增添了我的兴致并让我对这一家人充满了感激之情。一路上我们踩着皑皑白雪,说说笑笑,很是快活,感觉好像不是去朝圣,而像是登山观光的游客。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步行,中午时分到达山顶的小庙。老妈妈在案前摆上祭品,点上香烛,领着儿女、媳妇一起磕头、祭拜,口中念念有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报上,求娘娘保佑。然后烧纸和“银两”、插香、燃放爆竹。拜完后,我们吃了守庙人提供的简单的“斋饭”,即稀饭、馒头和素菜,便告辞下山。带来的猪头等祭品则留给守庙人享用。
到家后,女主人就开始在厨房忙碌,准备晚上“谢佛”用的食品:除了煮猪头、猪尾巴和全鸡之外,最费时的则是在猪大肠里灌满糯米、然后放在肉汤里煮熟。因“谢佛”必须在吃年夜饭之前完成,如果有人在此之前偷吃了祭肉,以后他/她会再也不想吃肉。她怕时间来不及,特意叫在同村居住的妈妈来帮忙。娘俩忙乎了一下午。傍晚时分,男人们开始在门口贴春联、在门上贴写有倒“福”字的红纸,然后把四方的供桌抬到门口,摆上祭品:最前方是一对锡制的、带有凤凰图案的烛台,上插红烛。中间一个整猪头,猪尾巴从它的口中穿出,周围盘绕着装有糯米的大肠,旁边是一只整鸡,头被别过来朝着天空。其它的祭品还有:一碗水、两块豆腐、两块自制发糕、三碗米饭。祭祀由男主人在他母亲辅佐下完成,共分三步:先在门外祭天祭地,祭词曰:“天地造佛,旧年换新年,保佑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保佑家人身体健康,财源广进。”然后在门外烧纸和“银两”、放爆竹;第二步把供桌搬进门内,祭祀门神,祭词曰:“保佑好人进门,坏人不进门,保平安,保青春(健康)。”之后在火盆里烧纸和“银两”;第三步在厨房的灶君位前点上一对蜡烛,放一块发糕、一碗米饭、一块豆腐,因相信灶君在小年那天回到天上“度假”,今天又被接回来,所以祭词曰:“灶君菩萨,上天奏好事,下地保平安。家里添水不添米(意指富足、粮食不会减少)。”之后又在火盆里烧纸和“银两”。全部祭祀完毕之后,全家人一起围坐到餐桌上吃年夜饭,菜肴以祭祀用过的猪头肉、鸡、发糕和豆腐等为主。我在开饭前特意又到街上走了一圈,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以同样的方式谢年,甚至所用的祭品和祭拜方式也几乎完全一致。①引自王霄冰《本土宗教研究的人类学视角——以儒家祭祀文化为例》,部分内容经改写。
在这一事件中,民俗主体就是以孔JB一家为代表的榉溪村民,民俗行为即为拜佛、谢年,民俗过程是我们一行人上山祭拜、回家准备祭品和在家中谢年的流程,民俗意义则是通过感谢、祷告神灵,祈求来年的好运。该项民俗的物质维度主要体现在了祭品中,身体的维度在于男主人一家登山、磕头、祭拜时对于身体的调度,但在我的描述中不是很详细,因为当时忽视了这方面的细节。社会的维度,包括一同上山的家人、祈祷时念及的人员和准备祭品时来帮忙的娘家人,当然还有以同样方式谢年的同村所有家庭。精神的维度则主要体现在了主人的讲述和祈祷词中,因为这些反映出了他们祭拜时的心理动机,也代表着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核心价值观。
从民俗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又可被分解为两部分来理解:第一部分的上山祭拜礼在当地实际上已是一种消失的传统。就像男主人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个外人的到来,他是不会从事这项活动的。那么,为什么他会因我而如此大动干戈呢?很显然,一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民俗学者的身份,二是因为他本人的社会身份。作为一名长期出外务工而怀有某种乡愁情绪的当地人,他希望能通过这个活动,和我这个外来的文化人进行一场关于家乡民俗的对话和交流。为此他不惜人力物力,准备了丰盛的祭品,带我上山。在这里,作为民俗主体的这家人和他们所从事的文化实践的关系,已不再是真正传统意义上的传承关系,而更像是一种利用传统的符号资本进行一场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文化展演。我的兴致勃勃和满怀感激之心又让他感觉得到了回馈,在交流中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从中获得满足。所以我们一路欢声笑语,气氛非常轻松。但也并非所有人都如此,主人公的老妈妈显然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具虔诚之心,她代表着上一代人,无论是对传统还是神灵都仍然抱有敬畏之心。因此,即便是在同一个场景之中,不同世代不同身份的人们之于同一种文化实践的关系也是不尽相同的。而在第二部分的谢年礼当中,榉溪村的几乎所有村民都采取了同样的祭拜方式,或多或少也都怀有同样的一种虔敬心理。这说明,谢年礼的民俗在这一带仍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不论何种出身和身份,村民们都仍然像过去一样,将谢年礼视为他们生活与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加以传承。
如前所述,同样的案例和同样的资料,当我在几年前尝试从人类学视角进行考察时,我试图以法国人类学家莫斯-于贝尔的“献祭的图式”理论为参照,对比分析了中国本土宗教实践的独有特征。今天当我改用民俗学的视角来考察时,我会更多地去关心民俗主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与他们所保持的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民俗关系: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们如何建构自己身边的生活文化并赋予其意义?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反过来又怎样对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行为方式发生着影响?
总之,定义民俗是为了给民俗学研究圈定目标对象,避免概念泛化。日常生活千变万化,范围十分宽广,它就像一片广袤的田野,不仅仅民俗学者而且语言学者、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等等都在这同一片土地上耕耘。因此民俗的定义应赋予这门学科以独特的视角、工具和解读日常生活文化的方式。一般来讲,人类学习惯于从整体上去把握文化形态,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只被作为文化的构成要素纳入到考察范围中。社会学正相反,它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过程、社会中的群体和个人,等等,而这些最终都被作为社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文化在其中只充当着极为弱小的角色。然而民俗学所要研究的,恰恰就是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民俗学通过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各种社会/文化共同体中的人们的模式化的生活实践,旨在揭示其中的民俗关系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而探究该项文化实践之于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的确是一门很特殊的学问。它天生带有跨学科性质,具有联结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作用,将它归入人文或社会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将限制这门学科的发展。只有充分尊重它的相对独立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俗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