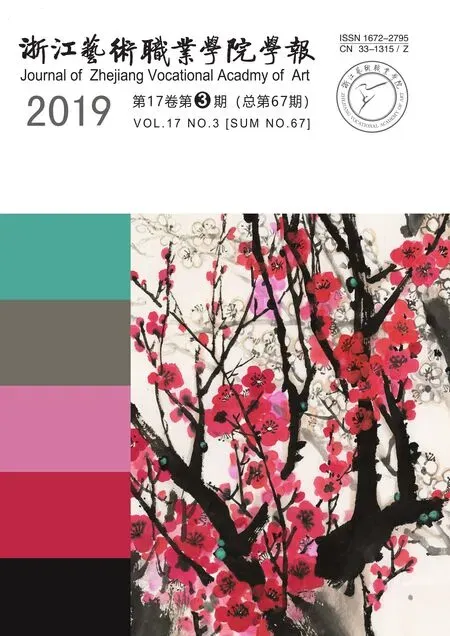平原气在胸,毛颖足吞虏
——书法艺术中的中国梦
史长虹 王芳芳
沙孟海先生说过:“书学是中国最早的一种艺术,六艺中不就有一艺是‘书’吗?”[1]那么,享有“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①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说:“西方艺术只有雕刻绘画,在中国却有一门书法,是处在哲学和造型艺术之间的一环。比起哲学来,它更具体,更有生活气息;比起绘画雕刻来,它更抽象、更空灵。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是中国灵魂特有的园地。”之盛誉的书法艺术受到万众瞩目,应当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其地位如此显赫,那么书法艺术对于文化的贡献当然也就不同寻常了。试述如下:
首先,书法与文字相互辉映,客观上起到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
书法的前提是文字,汉字是汉民族统一和文化延续的奠基石。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者,汉字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于其他三个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来说,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发挥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古埃及使用象形文字,现在官方语言则用阿拉伯语;古巴比伦当时使用楔形文字,现在的相应地区伊拉克使用阿拉伯语,伊朗则使用波斯语;古代印度使用梵文,现在梵语只是印度多种官方语言之一,只有极少数学者使用;只有古代中国当时使用甲骨文,尽管经历了几千年,至今一直保留了甲骨文演化而来的汉字。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令天下庄严宣布:“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并以严刑苛法予以监督,为促进国家的统一提供了根本保证。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书法教育史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字书教育段”“字书和法帖并行教育段”和“法帖教育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书法以文字学为基础、与书体演进和古今书体并行密切相关,代表性教材有西周《史籀篇》、秦《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汉《急就篇》《说文解字》以及唐《干禄字书》;第三阶段自东汉至清,书法以名家楷模为主,系翰墨之道深入人心所致;[2]第二阶段则介于二者之间。
兹以唐代为例。当时不仅要求士人研习书法,而且身居内宫的宫人也设置内教博士教习书法,楷、篆、飞白书皆有专人负责。至于唐代科举,无论是贡举还是铨举,书法都被列为重要科目或作为任用的先决条件。另外,唐代还设有制度之科,作为拔擢善书官吏的一种措施。至于流外官,即使一般的令史、书令史也以书法为首务[3]。唐代如此,其他朝代也有类似举措。
可以说,不同朝代的系统书法教育和人才选拔考试,既保证了官员的基本素质,也从根子上维护了书法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其次,文字和书法形态的丰富性有益于民族融合和团结。
汉民族书法经历了产生、成熟、繁荣的历程,各少数民族也形成了自身的书法符号与系统,如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巴思文、满文、女书、水书等。
于是,来自民间的交流是最自然不过的,就像雨后不同河流交汇一般,既然有区别,那么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文字与书法的氛围就应运而生了。就如不同的美食、风俗以及语言之间的交流和影响,等等。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当今,通过民族书法文字研究促进民族交流的佳话还在不断延续,远在西北边陲的敦煌研究院一直是此中翘楚。随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发掘,出现了新的史料,更有研究者长年累月、孜孜不倦地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字,取得丰硕的成果,改善了民族关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逐步向纵深推进,相信类似的良性循环还会延续下去。
当然,记载最详细的还是官方对书法发展的影响。在这方面,帝王们功不可没。唐太宗李世民本来是少数民族后裔,但是他因为酷爱《兰亭序》,乃至于立下遗嘱令太子将这“天下第一行书”殉葬昭陵,由此引发了书法爱好者的无限神往,也延续了王羲之“书圣”的千古辉煌。而且,李世民本人也以《晋祠铭》《温泉铭》扬名天下。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勤于学习汉族文字与书法艺术,造诣颇深。同时,一些著名的官员也对书法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宋元时期的赵孟頫本是赵宋子孙,后在元朝做官,尽管忍受了常人无法承担的压力,但其书法的影响力在元朝首屈一指。他在南北一统、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同时,他能团结包括高克恭、康里子山等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其中,康里子山的书学师承,《书史会要》认为“正书师虞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笔画遒媚,转折圆劲”。以墨迹看,他的师承不仅仅是这几家,还广泛吸收了晋唐名家和当朝赵孟頫之长,最后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他的书法对元末明初的书坛产生过很大影响,宋濂、宋克、解缙以及后来的文徵明,都不同程度地从中受益。
再次,书法实践与书法作品提升了人民的幸福感。
书法的修身养性功能向来被大家称道,在压力巨大乃至抑郁症越来越引起大家关注的今天尤为突出。从唐代的柳公权提出“心正则笔正”观点以来,一直影响深远,书法也被引申到人格层面。同时,书法中也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能给人注入不竭的生命力。书法史上三大行书《兰亭序》《祭侄稿》《寒食帖》,文、书俱佳,堪称典范。在元朝为官的赵孟頫、被迫降清的王铎①传说王铎临终前长叹三声,对儿孙说:“我一无颜见先帝,二无颜见祖先,三无颜见天下人。我死之后,一不着明服,二不穿清装。青衫遮体,方巾包头,这就行了。”(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河南卷[M].北京:中国ISBN 中心,2001:137.)、中年出家的李叔同也是终生挥毫不辍、乐此不疲。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家卫俊秀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没有颓唐、沉沦,而是凭借书法撑起了生活的希望和信念。[4]这些年来,书法家的长寿已经广为世人传颂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在古都大同,大家常常会被一种情景所吸引,那就是背负点滴设备的老者清晨挥毫于广场地砖,笔法之强劲有力、挥洒自如,令人难以忘怀。近来越发多见艺术爱好者——如传统书写功底本来扎实的曾翔等令人眼花缭乱、瞠目结舌的探索,尽管大众对于其书写效果评价不一,但就书写者本人酣畅淋漓的过程来说,着实有些让人陶醉。而这种畅快的情绪无疑会让书写者产生心旷神怡、物我两忘的正面效应。或者不必用以文字为基石的书法标准来评判他们,姑且视为传统的文房四宝与时俱进的一种艺术拓展形态,可能会与艺术家产生更多的共鸣。
书法给爱好者以成就感。书法家的涉及面极其广泛,不论职业、性别、年龄,只要字写得好,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获得认同感与美誉度。书法的土壤在民间,书法家和老百姓水乳交融。各种节日习俗一直没有离开过书法,还涌现出很多书法家贴近民间、帮扶大众的美好传说。其中,书圣王羲之的传说流传甚广,陕西周至有他被中“摹体”误及妻子从而受到启发自成一体的传说[5],浙江绍兴至今犹有题扇桥之佳话及“晋王右军题扇桥”大石碑①《晋书》《书谱》等多种文献均记载:王羲之在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扇卖之,书其扇各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谓姥云: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姥如其言,人竞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将笔抛进笔飞弄,人躲进躲婆弄,现该二地名一直沿用至今。从此该桥改名为“题扇桥”。题扇桥今位于浙江省绍兴城区蕺山街。因王羲之在此为老妪题扇而得名,说明此桥在东晋已存在。据嘉泰《会稽志》中载,现桥始建于宋朝嘉泰以前,在道光八年(1828)重修。该桥桥拱为纵联分节并列砌筑。弧形桥栏较为少见。桥上原有石灯杆,为路人照明。现桥边仅存灯杆石插座一个。从该桥的风化程度可定其为宋朝以前桥梁。该桥长3.8 米,宽4.3 米。桥坡石阶各为19 级。从宋朝以后的志书中可以肯定题扇桥在此地未作过变动。在清光绪年间的《策府统宗》一书中的《浙江古迹》条目里仅列题扇桥为绍兴古桥代表。可见此桥在外界的知名度极高。题扇桥现桥为清道光八年(1828)原址重修,桥体为单孔半圆形石拱桥,全长18.5 米。桥旁竖有著名书法家萧娴题写的石碑一方,旁设圆桌和鼓形石凳,可供游人小憩。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拱圈石上有浮雕幢形,望柱头为明朝式莲花形。《绍兴县志余辑》记有:道光八年戊子(1828)仲夏创建。晋王右军题扇处,方向南北,质料用石,有石碑,中隶书,旁草书,今存。一圆洞,全长20 米,桥面广度一丈三尺,东置17 级,西置19 级,上有石栏,有道光时题碑。,突出了书圣关怀民间疾苦的一面;在河南沈丘则有他当字的记载——杭州的书法崇拜者花五十两银子特地到苏州去赎回一个原已当了三十两银子的“当”字[6],在山东临沂王羲之嫁女[7]和甘肃天水王羲之为皇帝写字[8]的传说中的行情则提升为“一字千金”,体现了书圣作品在社会的广泛认同度。
20世纪80年代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以来②据查,中国书法家协会1981年5月成立于北京,舒同为第一任主席。,每年都有各级书协组织为百姓撰写春联的义举,深受人民好评。通过下基层送春联,书法家大大拉近了与人民大众的距离。既展示了书法艺术的巨大魅力和书法家们的人格魅力,又能吸引更多的人成为书法爱好者,从而为书法艺术培植肥沃的土壤。春节期间农村简直就是红色的海洋,大小春联自不用说,即使鸡、猪、驴、骡、狗、马、兔的处所乃至大小车辆上也有各类吉祥祝福,令人忍俊不禁。随着城市的迅猛发展,有些地方不再张贴传统春联,但是与时俱进的替代品——如以斗方、条幅形式出现的吉语亦随处可见。
复次,书法已经而且仍在发挥着越来越强的文化辐射力。
有研究者指出,汉字大概是在战国中期就开始逐步向境外传播。北起朝鲜半岛,南至越南,东至日本,这三个国家当时都没有文字,他们借用汉字的时间虽然先后不一,但至少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9]。鉴真和尚的东渡,为日本首次引进了王羲之的行书真迹及王献之的法书(三通)。留学生中以研究书法而著名的首推随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吕来唐而且与学问僧空海同船的橘逸势,他在唐留居两年期间,偕空海交游儒、佛人士,归国后以书法名世,与空海、嵯峨天皇并称为“三笔”[10]。在学问僧中,当属最澄、空海贡献最大。最澄于唐顺宗永贞元年即日桓武延历二十四年(805)六月归国时,所携诸物中含有书法名品拓本和名僧墨迹17件,其中包括《真草千字文》《王羲之十八帖》《欧阳询书法》《褚遂良集》《古文千字文》《王献之书法》等。空海之才能,备受唐土士大夫称述,如朱千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序云:“能梵书,工八体。”胡伯崇在《赠释空海歌》有云:“天假吾师多伎术,就中草圣最狂逸。”空海在唐研习密宗的同时,大量收集诗文和名家书迹,其中书法尤以真迹居多,书体也众。其《性灵集》所记呈献于嵯峨天皇的有唐名篇或名书家之真迹,其中包括《欧阳询真迹》《不空三藏碑》《急就章》《古今篆隶文体》《梁武帝草书评》《王右军兰亭碑》《李邕真迹屏风》等。
同时,唐朝的书法也传到了朝鲜半岛。其中尤以欧阳询和唐太宗的影响为最。唐高祖曾感叹高丽遣使远求欧阳询的书法:“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10]
反过来,日本的书法也曾传播于中土,同样也影响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日本僧仁忠《睿山大师传》记最澄入唐时,皇太子(后为平城天皇)曾托带经卷供养于天台山之事:“春宫殿下择好书之上(手),书写《法华》《无量义》《普贤观》等大乘经三部二通。即以一通附送大唐,和上坚持,渡海入唐,安置天台山修禅寺一切经藏。”这些日本善书手所抄录的经卷,其书法也影响着潜心研习的天台宗高僧和恭敬谨录的唐土经生。
就近代而言,这种中日之间的互相影响依然存在。如成立于1904年、现在囊括多国社员、享有“天下第一名社”美誉的西泠印社从一开始即有长尾甲与河井荃庐两位日本友人加盟。据《西泠印社志稿》载:“长尾甲(1869—1942),字子生,号雨山。……性爱石,又号石隐。善山水,工诗书,尤精篆刻,尝游本社,题‘印泉’二字勒于崖。所著有《古今诗变》《传学本论》《何远楼诗稿》。”“河井仙郎(1871—1945),字荃庐。……精仓、史之学,工篆隶,善鉴别金石碑版。数游中国江浙间,曾入本社,受知于吴俊卿。刻印专宗秦汉,浑厚高古。金石家皆乐于缔交焉。先后参与组织并担任东泰书道院、东方书道会顾问。著有《中国南画大成》《继述堂印谱》《荃庐先生印存》等”[11]。此二人在传播中国书法乃至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日建交之前,由民间组织的书法交流几乎没有中断,客观上凸显了书法的外交功能①笔者《西泠印社的对外交流》中有过这一提法,曾得到陈振濂先生的认可。文载《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版。。
1972年4月,“毛泽东主席诗词书法展览会”在东京举行,这项活动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书道文化联合会、日本书道联盟主办,朝日新闻社为后援单位,随后又赴大阪、仙台、名古屋、冲绳等城市展出。两年后,毛泽东主席又赠予来访的大平正芳外相一部怀素《自叙帖》影印本[12]。这两条史料无疑是中华书法文化在当代输出的强有力证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书法又一次对中国产生影响,风靡全国的“现代书法”即是其轰动效应,而且这种效应一直延续至今。
当代国际书法学习热潮已由星星之火转为燎原之势。2009年,中国书法和中国篆刻都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②据2009年10月4日《半岛晨报》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09年9月30日在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 个项目,包括中国申报的22 个项目,其中有书法、篆刻、剪纸等。,在更多的国度和地区引起了新的学习研究热潮。同时,书法课程也进入中小学教学大纲,越来越引起广大师生的关注。
综上所述,承载着实用和艺术功能的中国书法,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幸福和产生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书法,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瑰宝,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的今天,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应该得到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