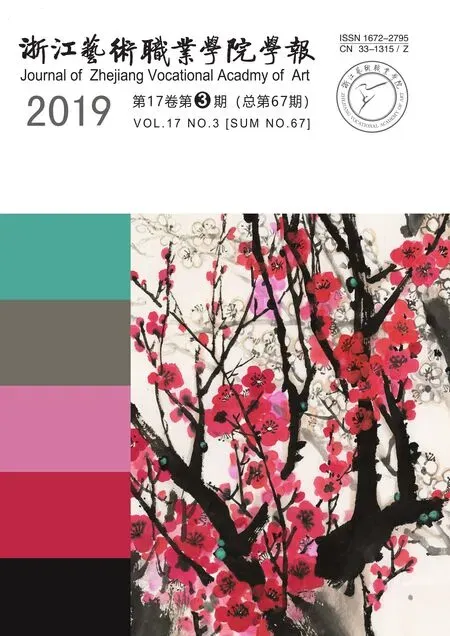见山如山在,看水如水流∗
——中国梦的戏曲曲艺溯源
虞 婷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化就像一个绵延不断的河流,源头来自远古,又由许多支流、干流汇合而成。……文化交流是民心工程、未来工程,潜移默化、润物无声。”[1]认真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凝聚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必将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我国戏曲曲艺是文化的瑰宝,它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乃至世界艺坛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集文学、舞蹈、音乐、美术、武术、杂技为一体,以其独特的综合性、开放性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曲艺则是各种说唱类艺术的总称,是我国古代民间口头文学和民间歌唱艺术长期发展和演变而来的,起源于民间,成长于民间,是我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艺术之一。
中国梦的提出,回溯到文化源头,既是基于沉淀下的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又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戏曲曲艺是传统文化的分支,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梦一定会渗透和体现在戏曲曲艺之中。而戏曲曲艺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处于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铸造中华文明新辉煌、新梦想的今天,追溯戏曲曲艺如何表现和彰显中国梦,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一、戏曲曲艺承载中国梦,谱写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精神文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伴随着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戏曲曲艺也经过不断的更新与发展,才逐渐形成现在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体系,谱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良传统。
先秦是戏曲的萌芽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祭神时歌舞唱词《诗经》的“颂”,《楚辞》的“九歌”。从春秋战国至汉,祭神时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悦大众的歌舞。从汉魏至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和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等。戏曲始于唐,发展于宋,成熟于元,极盛于明清。明代中叶,传奇剧本和优秀作家大量涌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汤显祖,其家喻户晓的《牡丹亭》讲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剧中两位主人公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令人印象深刻。作家赋予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爱情最终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这样的剧作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直至今天,“游园”“惊梦”等片段依然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耀眼的艺术光芒。
戏曲是集说与唱、歌与舞、技与艺的融合体,又是音乐与舞蹈、中国古典文学、美术等各种艺术门类的综合艺术,具有绚丽多彩、丰富而又独特的美学特征和艺术价值。中国传统戏曲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历史上的三种古老戏剧文化”。传统戏曲是具备东方美学特性的艺术样式,以其最通俗的、最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体现出来,它集中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精髓,演绎了人生百态,是中华文化历史信息的载体,更是中国优秀文化的典范。
曲艺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古代,我国民间的说故事、讲笑话,宫廷中俳优的弹唱歌舞、滑稽表演,都含有曲艺的艺术因素。到唐代,讲说市人小说和向俗众宣讲佛经故事的俗讲形式出现,大曲和民间曲调流行,使说话伎艺、歌唱伎艺兴盛起来,自此,曲艺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开始形成。宋代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说唱表演有了专门的场所,也有了职业艺人、说话伎艺,鼓子词、诸宫调、唱赚等演唱形式极其昌盛,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都对此作了详细记载。明清两代至民国初年,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城市数量猛增,大大促进了说唱艺术的发展。今天所见到的曲艺品种,大多为清代至民初曲种的流传。
戏曲与曲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内涵都彰显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精忠爱国、舍生取义、克己复礼、仁爱孝悌、勤俭廉正、明礼守信、积德向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民族精神是华夏民族的梦,更是我们华夏儿女的梦。戏曲曲艺作者们将如此情怀与梦想谱写在一曲曲优秀的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民族精神宣传的载体,所以说,中国梦是中国戏曲文化精神的魂。反之,中国戏曲又是中国梦传播的手段。在戏曲舞台上,中国梦与中国精神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大众的日常行为中并影响到他们的文艺心理构成。中国传统戏曲与曲艺是中华文化大树上的枝条,它们像其他分支一样,从中华文化的主干上汲取着生长的养分,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为中华文化增添了绿意。
二、戏曲曲艺彰显国家富强梦
英国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认为:“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一直保持着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2]四大发明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而且大大加速了近代文明在欧洲的兴起。马克思称之为“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其他的如农业技术、水利工程、建筑技术、圆周率计算、丝绸、瓷器、纺织等工业技术、天文仪、地动仪、历法等都是世界公认的。由古代中国四大盛世——西汉文景之治、东汉光武中兴、唐代开元盛世、清代康乾盛世,足见中国之繁荣富强,这些国家富强的强音也体现在诸多的戏曲曲艺作品之中。
(一)古代中国盛世之梦,促进国际交流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矢志追求富强,历史上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方面曾长期处在世界前列,促进了对外交流的发展。戏曲也以中国古代外交使者的故事为原型,谱写了华夏文明的灿烂外交史。如“晏子使楚”“张骞通西域”“唐玄奘取经”“一人灭一国的王玄策”与“郑和下西洋”等。其中,以郑和下西洋为题材的剧作《奉天命三保下西洋》(以下简称《下西洋》)收藏于明代著名藏书家赵美琦所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下西洋》是一部北杂剧,属于宫廷剧,用于公众庆典庆宴时供奉,内容上具有浓厚的盛世气息。这部内府之戏共四折。第一折是从宫廷出发,第二折是郑和一行人前往天妃宫祈祀和郑和梦见天妃,第三折是在西洋国(也就是海外)经历,第四折是回朝受赏。由于是在宫廷特定的环境中上演,剧中充分表现出宫廷文化氛围与气息。郑和率领的使团在南洋诸国停留驻扎期间,除了完成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任务之外,还有意无意地充当了文化交流的使者,对当时及后来南洋诸国的社会及华人移民的影响不可忽视。在宫廷中上演此类剧目,一方面反映了大明朝的国力昌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华夏民族共同的国家繁荣富强梦。
(二)精忠报国,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中国戏曲诞生的时期是一个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局势动荡的时期。进入近代后,中国更是频遭西方列强入侵和侮辱。面对一次次民族冲突和国家危难,戏曲艺术家借助戏台和剧目,谱写了一曲又一曲令人荡气回肠的民族正气歌,成功塑造了许多刻骨传神的人物形象,如戚继光、林则徐、郑和、文天祥、袁崇焕、冼夫人等精忠报国、抵御外侮的英雄人物,这些人物形象不仅表达了戏曲艺术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而且对弘扬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警句名言,林则徐虎门禁烟、胸怀天下苍生的义举,便是这句名言的最好见证。民国时期福州手抄本评话记载了清道光时期林则徐禁烟、大破洋人阵、打败入侵者的过程。福州评话是福州地区的曲艺艺术,也是南北评话群芳中的一枝奇葩,并在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然而,天津青年京剧团新编京剧《钦差林则徐》却剑走偏锋,没有选取林则徐虎门禁烟情节,而是选取林则徐赴任钦差途中的际遇,讲述了一段林则徐清正廉洁的律己事迹,为虎门禁烟的主人公展示了一个心系民生、奉公自律、尽职尽责、耿直清正的侧面,提供了一种对历史人物全方位、立体式的艺术解读。因而,这出戏受到天津观众的热烈追捧与喜爱,所获赞誉也不绝于耳。如果说真、善、美是人们一直追寻向往的优秀品质,也是戏曲表现平凡人故事时一直追求的美学精神的话,那么,大仁大义、为民请命的清官更是人们一直期盼与渴望的人物形象,也是戏曲表现官员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人物类型。
2.维护统一,反对分裂
为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我国人民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作出巨大的努力。古代中国涌现了大量为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壮举和英雄,如唐朝时文成公主入藏、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和回部贵族叛乱、设置伊犁将军、建立对达赖和班禅册封制度及“金瓶掣签”[4]制度、设立驻藏大臣等。其中,岭南圣母冼夫人就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巾帼女英雄。
冼夫人是南北朝时代岭南地区俚人领袖,历经梁、陈、隋三代,一生协助朝廷消除地方割据势力,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团结,促进汉俚民族融合;坚持肃除社会陋习,推动俚人社会文明进程,推动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在海内外闻名遐迩,在广东历史文化版图中更是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被周恩来总理称颂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为了弘扬冼夫人爱国爱民的精神,海南省戏剧家协会特编排了历史琼剧《冼夫人》。该剧以冼夫人来琼治理崖州为主线,在塑造冼夫人高尚艺术形象的同时,又注重展现海南古朴的民俗民风,赞扬其“维护统一,爱国爱民”的精神,既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也是对那些数典忘祖的分裂主义者的有力鞭挞。如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种族问题依然是世界和局部地区动荡不安之源。用戏曲的形式大力弘扬冼夫人维护统一和爱国爱民的精神,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3.同仇敌忾,抗御外侮
戏曲曲艺中也成功塑造了许多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民族英雄,如抗倭名将戚继光,他是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更是民族英雄。以戚继光抗倭故事为主题的戏曲很多,其中大型台州乱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编历史剧《戚继光》以“文戏武做、武戏文唱”的表演风格,再现戚家军抗倭的恢宏场面,还融入了很多民间习俗。《戚继光》的叙事如史诗般宏大,截取了戚继光剿灭倭寇“台州大捷”这一篇,通过“三箭射三酋”、招练义乌兵、“鸳鸯阵”、花街破敌等情节,集中体现了戚继光所向披靡的辉煌战绩和大智大勇的家国情怀。大型京剧和评剧版的《戚继光》也以不同的戏曲形式,展现了民族英雄戚继光的大智、大勇与大义。
每当民族危在旦夕,爱国主义戏曲及其弘扬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抵御外敌的锐利精神武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系列救亡戏曲就是典型的例子。那时,现代著名戏剧家田汉编写了借古喻今、宣传抗日的京戏《江汉渔歌》;一代宗师梅兰芳则根据《娘子军》《黄天荡》等剧目整理、改编并演出了京戏《战金山》;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演出了京戏《明末遗恨》《徽钦二帝》;全国各地的地方戏曲团演绎了《木兰从军》《守湖州》和大量新编的救亡戏曲,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
三、戏曲曲艺演绎民族振兴梦
莎士比亚说:“戏剧是时代的综合而简练的历史记录者。”[5]世界上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戏剧形式,如:希腊的悲剧、意大利的歌剧、俄国的芭蕾舞剧、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等。这些雅乐往往是他们民族的骄傲和自信的源泉。戏曲曲艺是中国传统戏剧,从中品味民族的精神与文化,用戏剧唤醒民族振兴的自觉和自信,这或许是千百年来中华儿女共同的梦。
(一)忠孝节义、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
中国社会,人与人最基本的五伦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和朋友,而“忠”“孝”“节”“义”成为古代调节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6]。
在古代戏曲曲艺中,有大量经久不衰、妇孺皆知的忠孝节义戏曲,举其要者有:写岳飞故事的《精忠记》(明人传奇)、《精忠旗》(明冯梦龙作)、《续精忠》(明唐子垂作);写文天祥故事的《冬青树》(清蒋士铨作);写屈原故事的《汨罗江》(清郑玉作)、《纫兰佩》(清周乐清作)、《怀沙记》(清张坚作);明徐渭作杂剧《四声猿》中,有《雌木兰替父从军》,写传说中的花木兰故事等。人们乐于用戏曲曲艺来传颂忠孝节义的仁人志士,鞭挞那些倒戈变节、背叛民族的败类。这些戏曲曲艺篇章也能与千古流芳的民族英雄一样,传诸百世而不朽。
(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
中华民族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在我国的民族戏曲曲艺中有着充分而精彩的体现,许多描绘古代杰出人才的戏曲曲艺作品中,都显现了如此“大丈夫”的民族气节。“南戏”《牧羊记》,就描述了汉代的苏武威武不能屈,被放逐北海牧羊十九载,经历饥寒交迫而坚贞不屈、誓不辱命,最终持节返汉的故事。元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与《西游记》,就描述了唐代的玄奘法师,西天取经,行遍十万八千里,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取得真经荣归大唐的故事。王实甫作的元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描述了吕蒙正在风雪寒窑中,贫贱不移,凿壁偷光,苦读诗书,最后状元及第的故事。
戏曲曲艺不仅塑造了一代代仁人志士形象,而且一代代传承下来,对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魂、民气,发扬中华民族美德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激励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
(三)急公好义、扶危济困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的急公好义、扶危济困的民族精神,也是古代戏曲曲艺的一个突出主题。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是我国最早流传至欧洲的戏剧作品,剧情主要取材于《史记》。该剧描述了在奸佞当道的社会大环境下,公主托孤后自缢而亡,将军韩厥放走孤儿后自刎,程婴舍子救孤,公孙杵臼受尽酷刑触阶而亡的故事。程婴除了舍子替换、救出孤儿之外,还一度背上卖友求荣的骂名,二十年后才得以真相大白,铲除奸佞,伸张正义。此戏曲是歌颂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典型篇章,流传千古。明代的徐元据此戏曲改编为传奇《八义图》,清末有京剧《八义记》,近代戏曲中,京剧、秦腔、汉剧等诸多剧种都有救孤的剧目。其中,豫剧《赵氏孤儿》被评为国家舞台艺术的精品剧目。
其余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要数水浒戏和包公戏。水浒戏有高文秀的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李文蔚的元杂剧《同乐院燕青博鱼》、康进的元杂剧《李逵负荆》等,元明间有无名氏的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等,明代流传甚广的有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许自昌的传奇《水浒记》、沈璟的传奇《义侠记》等,清代有范希哲的传奇《偷甲记》、金蕉云的传奇《生辰纲》等。
四、戏曲曲艺弘扬人民幸福梦
常言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戏曲曲艺编写的故事里,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戏曲曲艺的世界里,现实与梦境的边界变得模糊,情感纠葛被放大,大众对美的感知和共鸣彰显出来。戏曲曲艺构建着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渗透在中华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审美经验里。不管是帝王富贾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老人少儿还是足不出户的大家闺秀,都喜欢戏曲曲艺。戏曲曲艺成为乡村生活中规模大、范围广的公共生活方式,也成为社会上层文人雅士会友和追求个人艺术享受的方式。清代王应奎在《柳南文钞》卷四《戏场记》中曾形容人们看戏的情景:“观者方数十里,男女杂沓而至,男子有黎而老者,童而孺者,有扶杖者,有牵衣裾者,有衣冠甚伟者,有竖褐不完者,有躇步者,有蹀足者,有于众中挡拨挨枕以示雄者,约而计之,殆不下数千人焉。”[7]通过戏曲曲艺传播的情感价值观,在人民大众中产生广泛的共鸣,传递着人民追求幸福之梦。
(一)反对礼教规定,追求爱情幸福
戏曲曲艺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颂爱情题材的名篇佳作,如《墙头马上》《牡丹亭》《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天仙配》《西厢记》等。这些作品激烈地控诉与抨击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等封建礼教,肯定并热情赞颂自由恋爱、自择佳偶。虽然这些作品不能够从根源上撼动封建礼教,但对促进社会的思想自由和人性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坚持扬善惩恶,捍卫社会正气
中国戏曲曲艺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并且长于从道德方面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这些作品对好人和善行进行充分肯定,如《窦娥冤》中窦娥宁肯自己屈招认罪也不愿连累婆婆,《秋胡戏妻》中梅英贞洁如玉、抗拒诱惑,《白兔记》中李三娘吃苦耐劳、赡养父母,《李逵负荆》中李逵急公好义、嫉恶如仇,《琵琶记》中张大公施仁施义、扶弱济贫等。同时,也对坏人和恶行给予无情鞭挞,最常见的是对背信弃义、以怨报德、富贵易妻者的批判,如《秦香莲》中的陈世美、《张协状元》中的张协、《赵贞女》中的蔡伯喈、《潇湘夜雨》中的崔通等。中国戏曲曲艺中的道德评判,直接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善恶标准和爱憎情感,常常能够在观众中引发强烈共鸣。
(三)积德行善,积善成德
通过戏曲曲艺表现的思想,激发人们内心向善的渴望,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深入人心,它不仅给人们带来通俗化的历史和音乐,还教会了人们区别善恶的道德标准。“善”可以塑造人的心灵。戏曲曲艺教化人们去恶行善,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用善恶分明的故事人物形象,来教导人们心存善念,树立与人为善的概念。如《芦花计》以教人之为继母者,《打柴训弟》以教人之为兄者,《杀庙》以教人之为仆者,《八义图》重友谊之道,《目连救母》重为子之道。戏曲曲艺教化的最终目的是唤醒人们做人的良知。在戏曲曲艺潜移默化的教化下,人们即使没有多行善举,起码也少行了恶事。戏曲曲艺中的孝子、节妇、忠臣、良将无一不是能保持自身善心的代表,正是通过戏曲对这些人物的塑造才使他们成为人们学习和效仿的对象,才能激起民众对善的认可和赞扬。当然,诸如“明礼诚信”“重义轻利”“谦虚谨慎”与“勤奋节约”[8]等在民族戏曲曲艺中,都有精彩的体现,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戏曲曲艺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精神家园。几千年来,人们逐渐培养起了对戏曲曲艺强烈的情感依赖和原乡情结。中国人走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只要听到地方戏曲曲调,心底就会涌现出浓浓思乡情。在如今,华人的足迹已经遍及全球,中国戏曲曲艺也在世界各地唱响,戏曲曲艺也变成了中国人在他乡寻找情感寄托、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的对象,成为最重要的精神家园。
结 语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也大有可为。[9]当今世界科技的日新月异、传播媒介的现代化一定程度导致传统戏曲曲艺与当代社会的距离远了。面对中西方文化的交融,面对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当代戏曲曲艺工作必须立足本民族文化,才不会丢失自己。在传统戏曲曲艺中寻找传统赋予我们的智慧,寻找传统中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因子,寻找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象征,这对实现中国梦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