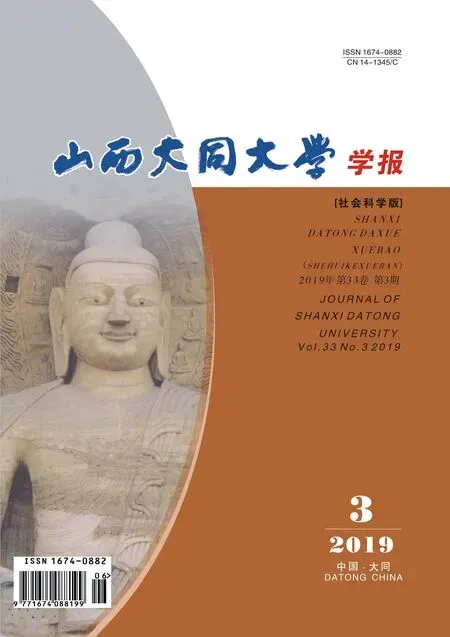个人主义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影响与对策
——基于自我主义视角的分析
沈玉梅
(宿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宿州 234000)
党的十九大把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而在“政治建设”中,更为强调的是“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应该说这在党的报告中也是第一次。这一规定早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已经作为“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之一成文通过了。那么,为什么新形势下党中央对“个人主义”问题如此重视?换言之,新时代为什么党的政治建设要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笔者对这一问题予以分析,以利于广大民众,尤其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这一问题,进而在实践中真正做到自觉抵制个人主义。
一、个人主义自身具有歧义性
个人主义是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观念在近代社会早期出现,产生于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不过,作为术语,个人主义则在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出现。托克维尔认为,个人主义是“我们的祖先”为了自己使用而创造出来的新词。[1]据史蒂文·卢克斯考察,个人主义最早的用法是法语形式的“individualisme”,这是源于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以及启蒙运动思想的普遍反应。19世纪20年代中期,圣西门的追随者开始系统地使用这一术语。由于受圣西门主义的广泛影响,这一术语此后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使用。
但是这个术语一产生就充满了歧义性。史蒂文·卢克斯说,“个人主义”一词的用法历来就缺乏精确性。[2](P2)马克斯·韦伯也说,个人主义这个词“囊括了可以想象的各种不同的事情”。[3]哈耶克更说,这个词不仅被使用者用来描述好几种社会观点,而且被它的反对者歪曲得面目全非。[4]不过尽管如此,作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念,个人主义还是具有基本一致的内涵和特征,史蒂文·卢克斯将之归纳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抽象个人五个方面。这些内容反映在社会生活和理论认识的不同领域,就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主要有政治个人主义、经济个人主义、宗教个人主义、伦理个人主义、认识论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等等。[2](P5)
由于个人主义自身就存在歧义性,因此在西方不同国家,个人主义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在法国,个人主义是消极的,标示着个人的孤立和社会的分裂,意味着强调个人就会有害社会团结。在德国,个人主义是积极的,是社会团结的最高实现。在美国,个人主义既有天赋权利学说,又有自由企业之信念,还有美国梦等不同时代的所有理想,是一种具有巨大意识形态意义的象征性口号。在英国,个人主义主要指没有或少有国家干预的各个领域,而且,无论是赞成个人主义还是反对个人主义,常常都把它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提并论。[2](P5-36)
马克思主义认为,“极为相似的事情发生在不同的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5]因此,个人主义的歧义性并不是个人主义概念自身造成的,而是由其存在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也因此,当个人主义来到中国后,这一概念同样也发生了变化。
二、中国“个人主义”的实质是“自我主义”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个人主义”这一词语。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个人主义”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的舶来品。这一舶来品是通过日本人借用汉字对西语的翻译形成的。但是“个人主义”一经舶来中国,就在中国语境中发生了变化,成为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关于这一点,梁漱溟早就有过解释:“假若你以‘个人主义’这句话向旧日中国人去说,可能说了半天,他还是瞠目结舌索解无从。因为他生活经验上原无此问题在,意识上自难以构想。虽经过几十年西洋近代潮流之输入,在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亦还把它当作自私自利之代名词,而不知其理。”[6](P48)那么,为什么西方的个人主义传入中国后会成为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对于这一问题,梁漱溟认为是“中西社会构造之悬殊”导致的。可是,“中西社会构造之悬殊”何以会让中国人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对此,费孝通有过非常系统的论述。
关于费孝通,中国学者没有几个不知道的,尤其是他的《乡土中国》一书,在社会学界更是尽人皆知。这本专著是费孝通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讲授“乡村社会学”课程的部分讲稿结集而成的。在这本书中,第四篇“差序格局”和第五篇“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讨论的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自私自利的问题。
在讨论这一问题过程中,费孝通运用人类学研究的经典方法——比较法,提出了一对譬喻式概念——“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他认为西方社会结构是一种“捆柴”式的“团体格局”:“西洋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中国社会结构则是“水波纹”式之“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7](P25-26)在两者的比较中,费孝通阐述了东西方社会构造的悬殊之处:西方社会群己界限清晰分明,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清楚明白;中国社会群己界限模糊不清,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常常沦为攀关系、讲交情。
那么,什么原因导致这两种社会构造截然不同?费孝通认为是这两种社会存在的文化基础不同导致的。在西洋社会,文化基础是基督教。作为团体象征物的上帝,既保障了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又将这种平等推进到社会的世俗生活中,并使之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也就是说,在团体格局中,爱不分差序,同一团体的人是“兼爱”的,即是相同的,因而我们找不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这样的社会,实行的是普遍主义的价值原则,因而群己界限清楚明白。在中国社会,文化基础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最讲究的是“伦”与“仁”。“伦”重在分别,以“己”为中心逐渐外推。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是从“己”一个一个推出的,社会范围则是由一个一个“己”之联系所构成的私人联系的网络。这种人伦又是通过“仁”体现出来的,“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差序格局社会中,爱有等差,每根以“己”为中心的私人联系都被一种不同的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普遍的道德观念。这样的社会,实行的是特殊主义的价值原则,故而群己界限不清不楚。而群己界限问题就是公、私关系问题。换言之,西方社会公、私关系确定分明,中国社会公、私关系模糊不清。
那么,为什么基督教文化传统会让西方社会公、私关系确定分明,而儒家文化传统却会让中国社会公、私关系模糊不清?费孝通认为,这是由于两种文化中的道德基础不同导致的。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一方面,平等观念的存在保证了每个人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另一方面,宪法观念又规定了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因而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清晰明了,公、私关系当然也是确定分明的。
中国社会则以“自我主义”为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为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因而公、私关系呈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是以“己”为中心的内收所产生的“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私”是顾及自己眼前利益的现实而功利的小我格局。二是以“己”为中心的外推所形成的“公”。“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公”是关照于他人与社会以及家国天下秩序的大我格局。由于内收产生的“私”和外推形成的“公”都是以“己”为中心的,所以当中心的“己”发生变化时,“公”和“私”之范围和界限也要随之而变化。因而“公”“私”关系就会因中心之“己”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或“公”或“私”的模糊不清状态。
但是,又由于一切价值都是以“己”作为中心,即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况,“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因而无论“公”“私”关系如何变化,也最终会因为“己”之“北斗星”的“中心”地位而由“公”向“私”回归,即“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7](P29)所以,“自我主义”终会将“公”导向“私”。换言之,儒家文化之“自我主义”道德基础的逻辑之因必然导致人们行为的自私自利之果。
至此,“中西社会构造之悬殊”导致西方“个人主义”在中国变成“自私自利”的代名词之缘由便清楚明白了。也就是说,当个人主义传入中国后,其原有内涵就在中国语境中被儒家文化的“自我主义”逻辑所解构,使之成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自我主义”,从而成为了“自私自利的代名词”。这也正像余英时所认为的那样,individualism 不应该翻译成“个人主义”,而应该翻译成“个体主义”,而“个人主义”对应的英文应该是personalism。也就是说,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社会上的个人是指人的通性,因而是抽象的)应该是个体主义,而中国的个人主义personalism(个人是具体的,每一个个人都是特殊的)才是个人主义。[8]如此看来,此说也不是没有道理。
基于此,笔者认为,西方传入中国的“个人主义”其实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从它传入中国的那一刻起,即被中国人赋予了“自我主义”的文化内涵,因而对于中国而言,“个人主义”只是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中国真正的实质则是“自我主义”。
三、“自我主义”(个人主义)对党的政治建设的影响
如上所述,既然儒家文化传统中的“自我主义”逻辑导致国人自私自利,那么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后中国社会出现的私德盛行、公德没落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在任何社会里,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9]它都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约定俗成,并在潜移默化中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凝聚在一起。换言之,儒家文化传统中的“自我主义”逻辑并没有因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开启以及市场经济的实行而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因早已内嵌于中国人的民族性之中,成为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一种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思维方式。
托克维尔在分析美国共和制度得以维护的重要原因问题时使用了一个概念——民情。他把这一概念“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10]借助于这一概念,我们同样可以把“自我主义”逻辑当作中国重要的民情。由此我们可以说,作为一种重要的民情,“自我主义”已经广泛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人一种集体性的思维习惯。[11]所以,无论我们对这种“民情”予以怎样的道德评价,都无法否认其在当下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长期而广泛的影响,这一点在党的政治建设中表现的更为突出。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组成的,因此政党的整体利益和其每一个个体的个人利益之间应该是一种互动和谐的关系,否则就会给党的团结带来很大影响,进而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伤害。所以,要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就要维护政党的整体利益。而维护政党的整体利益就要正确处理好党的整体利益和每个党员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防止不当的个人利益的膨胀影响、破坏甚至侵占整体利益,影响党的有机团结和统一。故而,防止和反对自我主义(个人主义)就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内容一直贯穿在党建工作中。
但是尽管如此,党内自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仍大量存在,新千年以来似乎更为严重,近年来日渐昭彰的党内“圈子文化”就是一个典型代表。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12]习总书记所说的这种“圈子文化”就是自我主义衍生品的重要表现。“圈子文化”在党内的存在与盛行,既影响党的向心力,破坏党的团结和民主,弱化中央权力和权威;又破坏政治规矩,异化公权力,使党组织、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空心化;还恶化官场生态,使“潜规则”解构党纪国法,造成制度缺失。因此,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对自我主义(个人主义)。
四、克私奉公是党的政治建设的伦理保证
尽管儒家的“自我主义”逻辑导致中国人自私自利,并给当下中国经济社会以及党的建设带来很大危害,但是,有一点笔者要特别指出,那就是“自我主义”逻辑除了内收之“私”的一面外,还有外推之“公”的另一面,恰恰是这一面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理想。正是这种道德理想,使历史上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能够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敢于担当,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勇于献身,无私奉献。正如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荣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3]
因此,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逻辑无限放大了“私”的一面而消解了“公”的另一面时,新时代的中国应该着重于塑造并弘扬克私奉公的时代精神,培养当代“中国的脊梁”。这里,克私指的是限制“自我主义”之内收倾向,奉公指的是发扬“自我主义”之外推精神。正是这一原因,晚年费孝通在谈论中国社会结构之“差序格局”时,不再讲以“己”为中心的内收之“私”,而是着重于强调以“己”为中心的外推之“公”:“能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序格局’就出来了。”这种“差序格局”“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14]也是在此基础上,晚年费孝通提出了“场”的概念:“‘场’就是从中心向四周扩大,一层层逐渐淡化的波浪,层层之间只有差别而没有界限,而且不同中心所扩散的文化场在同一空间互相重叠。”并把这个概念作为对“差序格局”概念的补充。[15]
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新时代的中国,“自我主义”逻辑给中国带来的重要影响或许并不是广大民众囿于自我主义的“内收”之私以至于整个社会公共性的空场,而是更大程度上在于能够发扬自我主义之“外推”精神并进而引领社会推行公共事业之“中国的脊梁”式精英人物的缺失。换言之,当下中国危险的并不是私德盛行、公德没落,而是能够推行公德之载体的缺失。在传统中国,这样的载体是士绅阶层。中国转型现代社会发展后,士绅阶层已经解体。因此,当下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寻找到士绅角色的替代性力量。而承担着“三个代表”重任的广大党员干部应该而且必须成为这样的替代性力量之一。但是,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自我主义”逻辑以及由其衍生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腐化销蚀着广大党员干部。
对于这一问题,党中央不仅非常清楚,而且尤为重视,因此,才有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从“四个意识”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到“中央八项规定”之严整“四风”与反对特权;从巡视利剑的高扬到“打虎”、“拍蝇”与“猎狐”之重拳反腐;等等。也因此,才有把“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上升到党的政治建设的高度予以强调。因而才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及十九大报告都把“自我主义”逻辑衍生的各种“主义”和“文化”列入反对的视野之内,旗帜鲜明地指出,全党必须“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16]这一系列重大举措的目的,就是要从政治上和法律上规范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以使其发扬儒家的“外推”精神,克私奉公,真正担当起“三个代表”,成为当下中国之新士绅阶层的重要部分,进而带领中国广大民众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逐步发展。惟其如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顺利实现。
——概念跨学科移用现象的分析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