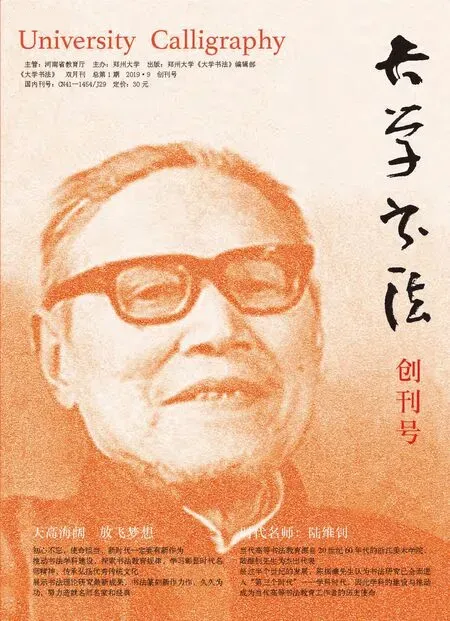后世对朱彝尊碑帖考证的质疑
⊙ 聂国强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醧舫,晚号小长芦钓鱼师,又号金风亭长。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市)人。朱彝尊一生跨越明清两朝,生于明崇祯二年(1629),卒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他是清初访碑活动重要参与者,观其一生的访碑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之豫章,之粤,之东瓯,之燕,之齐,之晋,凡山川碑志,祠庙墓阙之文,无弗观览。”[1]朱彝尊在访碑期间椎拓了大量的碑刻,并撰写了许多金石跋文,这些文字大都收录在《曝书亭集》之中,后来光绪年间的朱记荣又将这些跋文辑为《金石文字跋尾》,共计140余篇。
一、对汉代碑刻的析疑
(一)《右汉酸枣令刘熊碑》
朱彝尊跋《右汉酸枣令刘熊碑》云:“上元郑簠汝器所藏,碑文全泐,存字不及百名。”[2]朱彝尊这句话中包含了两个地名:广陵、上元。根据明申嘉瑞《(隆庆)仪真县志》记载:“武帝元狩六年,立子胥为广陵王,地属广陵国,统县四。东汉建武初为广陵郡。”[3]可见汉代时“广陵”为郡。至于“上元”,根据清武念祖所撰《上元县志》,“上元”即为邑。可见在朱彝尊的题跋中两个地名前后级别并不一致。所以,翁方纲认为朱彝尊的这种说法并不妥当,在《两汉金石记》提出自己的观点:
朱竹垞跋云“右汉酸枣令广陵刘熊孟阳碑”,愚谓题汉碑者,当以汉碑之例题之,应称“海西”,不应称“广陵”,即以其下文称“上元郑簠”可证也。每憾竹垞《经义考·承师门》内于汉唐以后经师,忽而书“郡”,忽而书“邑”,尝据其可知者为悉更正之,附识于此,以见著录有体,非敢漫议前人也。[4]
翁方纲指责朱彝尊《经义考》中行文不规范,经笔者查阅,如徐侨,字崇甫,义乌人[5];江默,字徳功,崇安人;郑文遹,字成叔,福州人;倪思,字正甫,吴兴人。义乌和崇安均为县,而福州和吴兴均为郡,类似“忽而书‘郡’,忽而书‘邑’”,在《经义考》中确有此事,翁方纲所言不虚。
(二)《汉华山碑》
历代学者对于碑后出现“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一句的理解,众说纷纭,是“郭香”察书,还是“郭香察”书?争论不休。让我们来看朱彝尊的理解:
“郭香察书”字义,诸家论说纷纷,关中赵孝廉子函以“郭香察书”配“杜迁市石”,其说近是。载考司马彪《续汉书·律历志》,灵帝熹平四年,有太史治历郎中郭香姓名,殆即察书之人欤?[6]
朱彝尊没有说明该碑书者何人,但他根据《续汉书·律历志》的观点认定为“郭香”察书(察即督察之意)。这样的观点又见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
华州郭胤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华阴王无异家。某末曰:“京兆尹勅监都水椽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东汉人二名者绝少,而“察书”乃对上“市石”之文,则“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书者尔。汉碑未有列书人姓名者,欧阳叔弼以“香察”为名,殆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与掾,则市石、察书,有不必言者矣。《律历志》:“有太史治历郎中郭香,岂其人欤?”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因书之,以遗无异,而又惜允伯之不获,同时而论正也。[7]
顾炎武否定欧阳修“郭香察”所书的看法,和朱彝尊一致,同样将《续汉书·律历志》记载作为重要证据,而论定为“郭香”察书。其实,从宋代洪适就开始认为是“郭香”察书,只是没有提及《续汉书》一事。较早以《续汉书·律历志》来论证“郭香”察书之说,要见于明董斯张所著《吹景集·察书》一书。董斯张较为认可洪适的观点:“洪说颇近之,犹未快。”接着引用道安法师所撰《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来论证“察书”一事早已有之,最后提到《续汉书·律历志》:“熹平元年,有治历郎中郭香,岂即其人耶?”[8]总而言之,从明代董斯张到清代朱彝尊、顾炎武都因《续汉书·律历志》的观点一致认为《汉华山碑》是“郭香”察书。翁方纲也赞同朱彝尊、顾炎武的观点,见《苏斋题跋》云:
虽不能定为果中郎书,然顾亭林、朱竹垞皆谓《律历志》,郭香即此人。考郭香之名,见于五官郎中冯光、沛相上计掾陈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议,其时坐侍中西北,与光、晃相难问者,即蔡邕耳,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说,则香何不可以察邕之书哉?[9]
清陈文述高度赞同翁方纲这一评论:“其理甚明,说亦最正矣。”[10]然而,民国欧阳辅在《集古求真补正》中有一篇非常详实考证的文章,文中反对朱彝尊和顾炎武的观点:
顾亭林、朱竹垞又搜得《汉书》有郭香与蔡邕同坐论事,邕可以理香之说,香何不可察邕之书?此亦一偏之言。中郎学通天人,故能正香律历之误,香无名术士,岂足察中郎书哉?况香与香察自为二人,不得混而为一,如李广与广利不得谓有飞将,而无二师也。古今单双名同一字者,何可胜道。[11]
欧阳辅认为“郭香察书”四字已经明确了该碑的书写者就是“郭香察”,本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后人偏要将“郭香察书”中“察书”二字分离开,以此争论“郭香”其人。此外,欧阳辅认为在其他任何汉碑中均无“察书”二字出现,所以,“察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这一问题,从宋代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直到启功先生还写文章来论证此事,启功先生的回答某种程度上也回复了欧阳辅的质疑,即自宋到清否定“郭香察”此人书写《华山庙碑》一事,就是嫌弃此人的名气太小了。[12]启功先生一语中的,古人学书往往推崇名家书法,以求名正言顺,所以许多汉碑也附会给了在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蔡邕、锺繇等人。
(三)《汉泰山都尉孔宙碑》
(四)《竹邑侯相张寿残碑》
朱彝尊跋:“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见熊方《后汉书·同姓诸王年表》。”[15]朱彝尊所说的《同姓诸王年表》又称《同姓王侯表》,由宋熊方根据《后汉书》所撰写,清耿文光云:“《后汉书》无表,宋熊方作《同姓王侯表》二卷、《异姓诸侯表》六卷、《百官表》上下二卷,其书采入《四库全书》外间,未易得见。”[16]而《同姓王侯表》中关于彭城靖王恭以及其子阿奴的情况是依据《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之《彭城靖王恭传》: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赐号灵寿王(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东观记》曰:“赐号,未有国邑也。”),十五年封为巨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为国。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师正南,不可以封。”乃徙为六安王,以庐江郡为国。肃宗崩,遗诏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国。恭敦厚威重,举动有节度,吏人敬爱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为竹邑侯。[17]
由此可见,朱彝尊所参照的文献并不是原始材料,对此,郑业斆曾质疑朱彝尊的做法,见《独笑斋金石考略》云:
朱竹垞跋云:“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见熊方《后汉书·同姓诸王年表》。”案:明见范史《彭城靖王恭传》,盖即熊方所本。竹垞必舍此而据处何邪?[18]
二、魏晋碑帖
(一)《魏封孔羡宗圣侯碑》
朱彝尊跋:“考魏王受禅,在汉延康元年十一月,既升坛即阼事讫,改延康为黄初,而碑辞叙黄初。”[19]朱彝尊认为魏王受禅时间为汉延康元年十一月,而梁章钜认为朱彝尊所云有误,见《三国志旁证》云:
《后汉书·献帝纪》:“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乙卯,皇帝逊位。”《魏志·文昭甄皇后传》:“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魏受禅碑》:“十月辛未,受禅于汉。”《五代史·张策传》:“曹公薨,改元延康。是岁十月,文帝受禅。”皆是十月受禅之证。此纪《先书》“十一月癸卯”,《后书》“十一月癸酉”,两书十一月既于文为复,而癸卯、癸酉相距三十一日,亦无同在一月之理。《宋书·礼志》云:“汉延康元年十一月,禅帝位于魏。”《册府元龟·帝王部》云:“延康元年十一月,受禅。”并沿陈志之误。朱竹垞跋《孔羡碑》云:“魏受禅在延康元年十一月。”亦失于不考耳。[20]
从上文中可见,汉延康元年十月为魏王受禅时间无疑,朱彝尊的观点显然有误。梁章钜上面观点实际来源于欧阳修,宋代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跋《受禅碑》中已有详细的论证。欧阳修认为,《后汉书·汉献帝纪》记载魏王登坛受禅时间为“延康元年十月乙卯”,《魏志》记载时间为“延康元年十月庚午”,《受禅碑》中记载时间为“延康元年十月辛未”。可见三家说法并不一致。显然“延康元年十月”无疑,只是具体日期有差异,欧阳修经过考证最终认可《受禅碑》时间,即“十月辛未”,如欧阳修说:“汉、魏二《纪》皆缪,而独此碑(《受禅碑》)为是也。”[21]根据欧阳修的观点,再参照梁章钜的文字发现,梁章钜实际平移了欧阳修的考证来批评朱彝尊。
(二)《吴宝鼎砖字》
朱彝尊跋云:“有螭文,知非民间物。考是年六月,皓起昭明宫,方五百丈。”又云:“砖者之为用,古人取材必精,故羽阳、铜雀、香姜之瓦,皆可制砚。而是砖,相之理觕质暴,若似乎火气不交,垺不孰者,殆为圬者所弃,流转民间,未可知也。”[22]朱彝尊通过砖的花纹,认为非民间之物。清吴世宜对此有所质疑,见《爱吾庐题跋》云:
朱竹垞以《吴宝鼎砖》有螭文,定为非民间物,则此当亦内庭所用。然张芑堂孝廉得《哀子汤猛龙凤砖》文,乃墓砖,是不可晓。[23]
而钱泳比吴世宜的观点更加直接,钱泳《履园丛话》云:
《吴宝鼎砖》,康熙四年,吴之村民于小应岭掘地得之,文曰:“大吴宝鼎二年岁在丁亥作。”计十一字,书法在篆隶之间,一面有螭文,笔势劲挺。朱竹垞《曝书亭集》亦载此砖,以为宫殿上所用,引孙皓起昭明宫为证,然魏晋以前砖上大率皆有文,不独此砖也。[24]
朱彝尊有这样的错误判断,自然是由于当时出土砖文数量有限,以及朱彝尊自身对砖文认识的局限性。当钱泳提出朱彝尊的问题时,已经是清中期,随着金石材料的出土数量不断增加,不断会有新的发现,那么对于前期的许多研究成果一定会提出质疑,需要重新定位和认识,这也就不难理解钱泳对朱彝尊观点的质疑了。
(三)《魏李仲璇修孔子庙碑》
朱彝尊跋此碑云:“右《曲阜县修孔子庙碑》,魏兖州剌史李仲璇撰文并书……仲璇,《魏书》有传,自兖州还,除将作大匠,卒,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青州刺史。”[25]朱彝尊认为李仲璇为该碑的书写者,而全祖望认为朱彝尊的观点有误,《鲒埼亭集》云:
是碑兴和三年,以颂李刺史仲璇修孔庙功,而竹垞即以为仲璇所作,误矣。其书法庞杂,最为纰谬,亭林讥之者备矣。[26]
虽然全望祖判断朱彝尊判断有误,但是他也没有确定该碑的书写者是谁。又据黄易在《岱岩访古日记》中记载:“碑侧有王长儒书一行。”[27]后多依据黄易的观点认定该碑书写者即为王长儒。
(四)《裹鲊帖》
朱彝尊跋云:“‘裹鲊味佳,一一致君,所须可示,勿难,当以语虞令。’凡一十九字,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书,今藏宛平孙氏。”[28]最大争议点在帖中“一一”字,朱彝尊认为是两字,赞同如此观点者,如王士祯,他在《池北偶谈》中的观点和朱彝尊完全相同。[29]针对朱彝尊的释文“一一”二字,王澍有不同的看法,并加以论证:
《裹鲊帖》乃右军晚年书,笔力沈劲,独最他帖,故薛绍彭赞有“右军为书,暮年更妙,《裹鲊》一出,众帖咸少”之语。真迹在北平孙少宰承泽家……帖凡一十八字,“致君”上,玩其笔法,当是“今”字,朱竹垞释作“一一”,作一十九字,误也,十八字。凡五句:“裹鲊味佳”句,“今致君”句,“所须可示”句,“勿难”句,“当以语虞令”句。言:“裹鲊味致佳,今以致君,若复须此,可更示我,勿欲之而不言也。”“难”当如忿,斯难之“难”,去声。“当以语虞令”者,言不特我致君,并当以语上虞令亦致君也。古人短札古雅,简到乃如此。若出今人手,不知费如许纸笔矣。[30]
按照王澍的考证,《裹鲊帖》的释文并断句应为“裹鲊味佳,今致君,所须可示,勿难,当以语虞令”,共十八字。实际王澍这一释文和断句是继承了宋朱长文《墨池编》的观点。[31]在清代如此释文者还有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有记载。[32]
三、隋唐碑帖
(一)《唐太宗晋祠碑铭》
朱彝尊跋云:“唐太宗自晋祠兴师定天下,贞观二十一年七月,御制碑文及铭,勒石于叔虞祠东隅。”[33]清洪颐煊认为朱彝尊所说立碑时间(贞观二十一年七月)有误,见《平津读碑记》云:
《晋祠铭》在乾阳门街,贞观二十年太宗幸并州所置,御制并书。《册府元龟》亦云:“太宗贞观二十年正月幸晋祠,树碑制文,亲书之于石。”今碑有太宗飞白书“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题额。《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戊申,幸并州。”“二十年正月上,在并州。”“三月己巳,车驾至京师。”碑正其在并州时所作。《金石萃编》以碑首题“贞观二十一年七月”,盖未见此额,沿朱竹垞题跋之误。[34]
又见陆耀遹撰《金石续编》云:
按《唐太宗晋祠铭》碑阴诸臣题名并太宗飞白题额“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萃编》皆失拓,但见碑首有“贞观二十一年七月”题字。据以《编年》与孙氏《访碑录》皆沿竹坨之误也。[35]
关于《晋祠铭》的立碑时间,早在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就有记载:“右《唐晋祠铭》,太宗撰并书。晋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初起兵祷于叔虞祠,至贞观二十年,太宗为立碑。”[36]笔者又根据《晋祠铭》拓本见碑额确为“贞观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可以进一步证明朱彝尊记载有误。然而,曾经一起与朱彝尊访晋祠的曹溶,在《金石表》中却记载:“《晋祠铭》,行书,太宗制并书,贞观廿年,太原县。”[37]可见曹溶记载与朱彝尊不一致,由于朱彝尊和曹溶之间的关系之密切,可以说《金石表》的成果是朱彝尊和曹溶共同访碑的记载,所以笔者认为朱彝尊之所以记载“贞观二十一年”,是由朱彝尊当时的误写所致。
清代金石著作中论此碑者,沿袭《晋祠铭》立碑时间为“贞观二十一年”的不在少数,如顾炎武撰《求古录》[38]《金石文字记》[39],林侗撰《来斋金石刻考略》[40],(清)鲁燮光撰《山右访碑记 一卷》[41],赵绍祖辑《金石文钞》[42],钱大昕编《范氏天一阁碑目》[43],(清)孙星衍撰《寰宇访碑录》[44],杨宾撰《大瓢偶笔》[45]、《铁函斋书跋》[46],等等。
(二)《唐骑都尉李君碑》
朱彝尊跋云:
李君讳文,字纬。东汉以后,字必以两字,称一字者罕矣。载于《唐书》,房玄龄字乔,颜师古字籀,李众字师,李琇字琇,张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审字审,李恢字祚,李条字坚,窦思仁字恕,张义方字仪,此本不多见也。[47]
朱彝尊认为东汉以后,而称“一字”的人非常少,他举了《唐书》中十一人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但是清赵绍祖并不认可朱彝尊这一说法,他在《古墨斋金石跋》中进行反驳:
按竹垞所数凡十一人,然《唐书》所载以一字者甚多,就余所知,如佑庶人字赞,任瓌字玮,颜师古弟相时字睿,武士彟字信,武士逸字逖,李思训字建,姜协字寿,杨元琰字温,杨仲昌字蔓,郭晤字晤,郭暧字暧,颜杲卿字昕,张均字均,鲜于仲通字向,李叔明字晋,陆长源字泳,崔伦字叙,崔衍字著,又十八人也,乙卯十月琴士识。[48]
可见,朱彝尊关于“称一字者罕矣”并没有深入钻研《唐书》,就急于下定了结论,虽然他所谓“此本不多见”的观点并没有错,但是用词依然不够严谨,导致赵绍祖抓住这个“把柄”对朱彝尊进行抨击。
(三)《唐龙门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记》
朱彝尊跋云:“建自咸淳三年,以调露二年赐额。”[49]“咸淳”是南宋皇帝赵禥的年号,并不是唐代的年号,钱大昕认为朱彝尊有误,《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有详细考证:
右《大卢舍那像龛记》云:“高宗天皇大帝所建,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始于咸亨三年四月……”娄机《汉隶字原》云:“汉碑凡‘元亨’字皆作‘享’,至‘子孙享之’之类,又皆作‘亨’。”考之九经字样,凡“元亨”之“亨”,“享献”之“享”,“烹饪”之“烹”,《说文》作‘亯’亦作“ ”,只是一字,经典相承。隶省作“享”者,音“响”,作“亨”者,音赫(平),又音魄(平),后人复别出“烹”字,其实皆可通用也。予初见《张阿难碑》书“咸亨”为“咸享”,疑其下笔之误。今此碑亦作“享”,又《唐书·杜审言传》称“咸享初”,盖唐时虽用楷书犹存篆隶遗法,“咸享”即“咸亨”,正是从古。朱锡鬯跋误作“咸淳”,不知高宗纪元有“咸亨”,有“永淳”,无“咸淳”也。[50]
钱大昕论证了“享”“亨”“烹”皆可以互通,所以《大卢舍那像龛记》有时称“咸亨”年间所建,有时也用“咸享”。而笔者认为,朱彝尊所谓的“咸淳三年”这样的错误,是朱彝尊记忆有误造成的。
钱大昕还找出了朱彝尊类似的记忆之误,朱彝尊跋《晋义成节度使驸马都尉史匡翰碑》云:“然史称其历郑州刺史,而碑不书何欤?”[51]而见宋薛居正《旧五代史》云:“史匡翰字符辅,雁门人也。……俄授检校司徒、郑州防御使,未几,迁义成军节度、滑濮等州观察处置、管内河堤等使。”[52]因《旧五代史》记载“郑州防御使”与朱彝尊所云“郑州刺史”观点不符,所以钱大昕认为朱彝尊有误:
朱锡鬯云:“史称历郑州刺史,而碑不书。”按《五代史》本云郑州防御使,不云刺史。此朱氏记忆之误。[53]
(四)《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颂》
朱彝尊云:“立碑之岁,大历十三年也。”[54]而钱大昕认为立碑时间为“大历十一年”,而非“大历十三年”,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云:
后题:“大历十一年岁次丙辰五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建。”朱锡鬯跋以为十三年者,因碑石微损而误读耳。碑云:“河东节度副大使兼工部尚书太原尹北京留守薛公兼训”,兼训以大历五年镇太原,十一年冬以病去,鲍防代之。碑立于是年五月,兼训犹在镇也。[55]
根据钱大昕的说法,因为碑石剥蚀而致朱彝尊误读。一般而言,朱彝尊和曹溶的观点是一致的,果然曹溶在《金石表》中也记载为“大历十三年”。再如赵魏撰《竹崦盦金石目录》也记载“大历十三年”[56],均有误,根据目前所存碑拓以及其他金石学著作已经确定《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颂》立碑时间为“大历十一年”。
(五)《镇东军墙隍庙记》
朱彝尊跋云:“《东军墙隍庙碑》,施宿《会稽志》,张淏续之,均不载其文……。”[57]见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云:“《镇东军墙隍庙记》,钱镠撰,开平二年,岁在武辰月(月字上下皆空)。”[58]曹溶《金石表》云:“《镇东军墙隍神庙记》,行书,开平二年,绍兴府。”而为碑命名往往以碑额为准,该碑额为“崇福侯庙之记”,所以该碑碑名应为《崇福侯庙之记》[60],由此碑名的命名,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推测顾炎武、朱彝尊并未见到碑额。[61]
概括来讲,朱彝尊被后人质疑的问题主要包括文字释读、立碑时间、形质材料、书丹作者等几个方面。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朱彝尊个人原因造成,如记忆之误;另一方面是时代局限所造成的。清初金石学仍处在一个复兴开始阶段,出土材料也相对有限,难免在认识上受到制约。当然,就朱彝尊总体的学术成就而言,即便出现这些问题,也不能改变朱彝尊在金石学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注释:
[1]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M].卷8.清宁都三魏全集本.
[2][6][15][19][22][25][33][47][49][51][54][57]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M].卷2.清光绪十六年刊翠琅玕馆丛书本.
[3]申嘉瑞.仪真县志[M].卷1.明隆庆刻本.
[4][14]翁方纲.两汉金石记[M].卷16.清乾隆五十四年南昌使院刻本.
[5][13]朱彝尊.经义考[M].卷31.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9][58]顾炎武.金石文字记[M].卷1.清嘉庆中虞山张氏刊本.
[8]董斯张.吹景集[M].卷14.明崇祯二年韩昌箕刻本.
[9]翁方纲.苏斋题跋[M].清钞本.
[10]陈文述.颐道堂集[M].卷7.清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11]欧阳辅.集古求真补正[M].卷3.民国十二年江西开智书局石印本.
[12]启功.记汉刘熊碑兼论蔡邕书碑说[G]//启功.启功书法丛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17.
[16]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M].卷23.民国排印本.
[17]范晔.后汉书[M].卷50.百衲本景宋绍熙刻本.
[18]郑业斆.独笑斋金石考略[M].卷2.清光绪十三年刻本.
[20]梁章钜.三国志旁证[M].卷3.清光绪二十五年文澜书局石印本.
[21]欧阳修.集古录跋尾[M].卷4.清光绪四年古香书阁印.三长物斋丛书本.
[23]吴世宜.爱吾庐题跋[M].清光绪五年刻本.
[24]钱泳.履园丛话[M].卷2.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
[26]全祖望.鲒埼亭集[M].卷37.四部丛刊景清刻姚江借树山房本.
[27]黄易.岱岩访古日记[M].民国十年山阴吴氏西泠印社木活字排印遯盦金石丛书本.
[28]朱彝尊.曝书亭集[M].卷53.四部丛刊景上海涵芬楼藏原刊本.
[29]王士祯.池北偶谈[M].卷11.金溪李氏自怡草堂刊本.
[30]王澍.竹云题跋[M].卷2.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31]朱长文.墨池编[M].卷5.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孙承泽.庚子销夏记[M].卷1.清宣统中顺德邓氏排印风雨楼丛书本.
[34]洪颐煊.平津读碑记[M].卷4.清嘉庆二十一年刻本.
[35]陆耀遹.金石续编[M].卷4.清同治十三年毗陵双白燕堂刊本.
[36]赵明诚.金石录[M].卷23.三长物斋丛书本.
[37][59]曹溶.金石表[M].清末抄本.
[38]顾炎武.求古录[M].清光绪中吴县朱氏槐庐家塾刊槐卢丛书本.
[40]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M].卷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1]鲁燮光.山右访碑记[M].民国十八年序会稽顾氏金佳石好楼石印顾氏金石舆地丛书本.
[42]赵绍祖.金石文钞:总目[M].清嘉庆六年海宁陈氏慎初堂刊本.
[43]钱大昕.范氏天一阁碑目[M].清抄本.
[44]孙星衍.寰宇访碑录[M].卷3.清嘉庆七年兰陵孙氏刻本.
[45]杨宾.大瓢偶笔[M].清道光二十七年粤东粮道署校刊本.
[46]杨宾.铁函斋书跋[M].卷3.清道光二十七年粤东粮道署校刊.
[48]赵绍祖.古墨斋金石文跋[M].卷3.清光绪中贵池刘氏刊聚学轩丛书本.
[50][53][55][61]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M].卷3.清嘉庆十年刻本.
[52]薛居正.旧五代史[M].卷88.百衲本景印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
[56]赵魏.竹崦盦金石目录[M].卷3.民国十四年钱塘汪氏刊食旧堂丛书本.
[60]王士俊.河南通志[M].卷30.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书写、复制与文化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