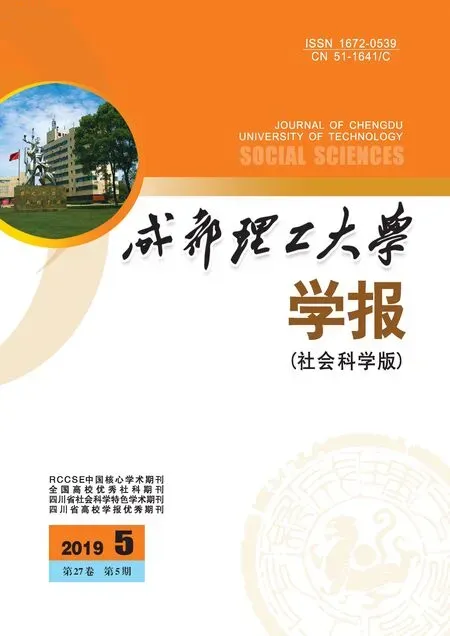余华小说的古典因素与先锋意识
——以《鲜血梅花》《古典爱情》为例
卫琳琳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的实验者与践行者,余华初载于1988年《北京文学》第12期的中篇小说《古典爱情》与1989年《人民文学》第3期的短篇小说《鲜血梅花》是其前期先锋小说的典型代表作。两篇小说均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外在模式,在虚拟的现实场景中展开精神漫游的历程,同时兼具先锋内核,以欲望与暴力叙事为载体,杂糅零度情感的叙述姿态,构建了崭新而异质的叙事空间,反映现代主义的多个侧面与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人道主义关怀。古典与先锋是两种截然相异的文学形态,是余华实验文本的先锋性尝试,实现了通俗与先锋的创造性同构。
本文选取《古典爱情》《鲜血梅花》两篇小说作为典型文本展开分析,余华的先锋小说自发表后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备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但对该小说的研究数量和质量远低于对长篇小说的研究,存在可拓深的空间。同时,两篇小说共同运用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古典与先锋两种相悖离概念的融合是一种新异的建构形式,余华在戏仿与改写古典文类的同时也赋予其先锋内质。两篇小说创作时间相近,也是余华创作转型期风格过渡的表现,在余华的文学创作研究中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与魅力。本文试从《鲜血梅花》与《古典爱情》对古典小说外在形式的借鉴为切入点,分别从古典文类的戏仿与颠覆,重复叙事的音乐性,先锋意识与现实意义三方面探讨两篇小说中兼具的古典因素与先锋性内核,从而发掘余华前期小说中展露的先锋意识与暗涌深流的人性关怀。
一、古典文类的戏仿与颠覆
源自于对古典武侠小说叙事模式的戏仿,《鲜血梅花》以江湖复仇情节为主题、主人公的江湖游历与武林高手的偶遇贯穿其间,以鲜血浓缩为袖珍梅花的喻示渲染了浓郁的武侠传奇色彩。小说开篇即是一代宗师阮进武遭武林黑道人士暗杀的起因,儿子阮海阔承载母亲的重托,肩负名扬江湖的梅花剑踏上寻找杀父仇人之路,兼具武侠小说一以贯之的复仇主题与梅花剑的武侠因素。惩恶扬善的正义之举本是江湖侠客的法则,而小说背景的虚化并未赋予阮海阔复仇之恨的情感,江湖的自由气息反而激活他肆意漫游的天性,严肃崇高的复仇行为被长途跋涉的虚无感消解殆尽。正如学者赵毅衡指出,“《鲜血梅花》是对武侠小说的文类颠覆,小说中符合文类要求的情节都成为‘没有意义的象征’,整篇小说成为‘非语义化的凯旋式’”[1]。小说复仇模型与鲁迅的《铸剑》异曲同工,摒弃了传统武侠江湖中快意恩仇、刀光剑影的经典戏剧性模式,当阮海阔若即若离的复仇使命被逐渐模糊化而随波逐流时,反而在帮助胭脂女和黑针大侠途中借由他人之手完成复仇,他得知真相后“内心一阵混乱”,同时漫无目的漂泊之旅也行将结束,复仇意义被消解的虚无与荒诞感油然而生。因此,复仇作为小说叙事动力却伴随着行为主体的缺失,唤醒了对复仇恶行本质的抗拒与人性自由的呼唤,复仇主线由江湖漫游替代,传统武侠小说的经典模式被彻底颠覆。
中国古典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叙事序列大多为主人公偶然相遇的起因、相知相恋的发展、经历劫难挫折的高潮后复归团圆的结局。《古典爱情》借鉴《西厢记》式才子佳人的爱情小说模式与聊斋式的人鬼之恋情节,小说中有丰富的古典因素,包括赴京赶考的寒门书生,闺房伤春、温婉似玉的千金小姐,热心机敏的丫环,书生小姐一见钟情的幽会情缘,缘绳而入绣楼的古典环境,以断发为信物的缠绵悱恻,演绎出一段才子佳人自由浪漫而悲戚的爱情传奇。男主人公柳生的姓名也出自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柳生》一章,有写得一手好字的风流雅趣、擅于描摹花卉的闲情逸致,却是疏于八股的穷儒书生典型。而他背井离乡的起因也是受“母亲布机上的沉重声响”带来的“灼伤般疼痛”与“父亲临终前的眼神”中被迫承担的光宗耀祖的使命的凄凉,营造了古典小说的环境氛围。
但在传中国古典小说、戏曲与神话传奇中,多数作品的宿命指向皆与“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叙事模式相同,无论情节发展的坎坷曲折,故事均以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为情感导向,即使为悲剧结局,也以人鬼团聚、生死同穴的温情表达作结。而《古典爱情》则以“古典”的外在形式与先锋性的荒诞内质彻底颠覆并改写了传统爱情,主人公柳生赴京赶考屡次不中,喻示他与小姐惠难结百年之好,背负着仕途与爱情的双重打压;小说摆脱了书生与小姐私定终身却因攀附名门望族而受到家庭阻力的典型情节,却以小姐沦落为血肉模糊的“菜人”、家道惨败的血腥暴力情节所取代;柳生经历人生幻灭悲苦以守坟为生,终于盼来小姐还魂的夜夜相会,当小姐正在新生不久将生还人世的零星希冀时,被柳生打开坟冢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导致无法生还的悲剧。小说在遗憾的戛然而止中透露出自由、爱情、人性被泯灭的潜含意蕴,这是人的主观诉求与客观现实相背离而导致精神撕裂的残酷,小说抽去才子佳人文类中忠孝、爱情的道德伦理精髓,只模仿传统小说的程式与情节,读者接收到叙述形式的抽象、新奇与内质的虚幻,以此消解传统小说模式。
《鲜血梅花》《古典爱情》等五篇小说是余华“文学经历中异想天开的旅程,或者说我的叙述在想象的催眠里前行”,“仿佛梦游一样,所见所闻飘忽不定,人物命运也是来去无踪。”[2]《古典爱情》是借鉴中国式传统叙事模式与古典审美情趣建构的仿梦小说,受卡夫卡创作风格影响,余华的小说存在荒诞与现实结合、形式与想象共存的模式,在中国现实中展开精神幻想游历的过程。当柳生走入深宅大院的后花园时,虚幻想象的梦境便不再遵从常规时空叙事逻辑,打破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的界限,符合先锋小说的叙事与意蕴建构原则。《古典爱情》与《鲜血梅花》对传统小说模式的戏仿表现出后现代主义颠覆文类与主题的特征。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擅长虚构现实,使真实失去客观性,一切存在都是符号的形式,是失去所指的能指。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小说形式的彻底解构、戏仿与颠覆在余华这两篇先锋作品中得以实现,如《鲜血梅花》中以“父仇子报”的传统伦理道德结构故事起因,而阮海阔在母亲自焚的压力下开始的报仇、漫游并未表现出以复仇为己任,而是遵从人性散漫随性的自由状态,失去行动的目的。
二、重复叙事的音乐性
美国当代批评家J. 希利斯·米勒认为,重复的艺术存在两种不同的形式:“从细小处着眼,我们可以看到言语成分的重复:词、修辞格、外形或内在情态的描绘”;从大处看,则有“事件或场景”在文本中的复制、“由一个情节或人物衍生的主题在同一文本的另一处复现”和“重复他其他小说中的动机、主题、人物或事件”[3]。重复的叙事艺术是余华写作的典型特性与风格,营造重复的氛围是小说节奏感的重要根源。如果说其后期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十二次卖血的情节重复是重复叙事的典型品格,前期作品《古代爱情》与《鲜血梅花》中重复手法的运用则已经表现出余华作为实验文本的无意识尝试。古代章回小说通常以百余回将全书分为若干章节,每回独立叙述相对完整的故事片段。余华小说的重复叙事一方面源于古典章回体小说结构回环的艺术,使小说独具形式的往复感,同时受故乡地方戏越剧的民间叙事艺术影响,余华曾表示“决定我今后生活道路和写作方向的主要因素在海盐时已经完成了”,“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4]越剧通过擅于抒情的唱调与回环的句式实现流连往复的艺术效果,从而提升审美效应,营造浓厚的艺术氛围。《古典爱情》与《鲜血梅花》中重复的音乐美表现在语词意象的重复、情节场景的重复以及整体旋律意蕴的重复中。
首先,小说语言擅于采用语词和意象的复现。意境是中国古典文论发展的产物,童庆炳对意境的界定为:“意境就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能诱发和开拓出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的整体意象。”[5]小说的抒情意象富于古典意蕴,趋于古今融合,在古典意象后潜藏着现代意识。而语句的重复则使小说产生回环复沓的效果,如《古典爱情》中“母亲布机的沉重声响”在柳生初次赴京赶考、体验街市人流熙攘与自身寂寞的反差时似心头之警钟般如影随形。特定意象复现的设定既像音乐篇章的休止符,独具回环的旋律美,又因小说基调情感对意象的寄托在特定情境中发挥作用,“黄色大道”“包袱里笔杆敲打砚台的孤单声响”的重复出现既奠定了小说悲剧色彩的基调,也预示金榜题名与抱得美人归的曲折。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系统,重复句式与特殊的语音结构对小说的语调、节奏、韵律的强化有内在的规定作用,创造了如音乐一般流淌的作品。同时,回环重复营造的乐感与1993年后“余华迅猛地热爱上了音乐”后接触到的西方古典音乐中的节奏美不谋而合,正如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中以“著名的侵略插部,侵略者的脚步在小鼓中以175次的重复压迫着我的内心”[6],紧锣密鼓的夸张式重复成为乐章中的重要旋律,展现出单纯叙事与重复的巨大力量。
其次,情节、场景在文本中的复现也是意义增值与强化的过程。余华以重复的手段有节制地将叙事结构层层推进,使情节的展开始终围绕主旋律,从而产生强大的艺术张力。《鲜血梅花》中是阮海阔路经胭脂女与黑针大侠的居所,找到青云道长觅得杀父之仇的谜底后再次回归的场景重现。而《古典爱情》中则重复叙述了柳生三次赴京的经历,路边景致变化与重叠的回环往复、梦境对往日景象的重现等,重现包含着变化,变化与重复融为一体,相似情节的复现使小说形成跌宕起伏的发展曲线,构成抒情的旋律感、情感的节奏性,类似于音乐表情达意的方式,由此形成特殊的叙述品格。小说结构整体采用线性叙事,但如同以乐章为间隔的协奏曲,故事时空具有鲜明的时段性,以柳生的行踪为支点,“数月后,柳生落榜归来”,“三年后,柳生再度赴京赶考”,小说叙事产生鲜明的间离感与节奏感,在从家到京城的地点转换之间展开不同的人物命运。柳生的三次赴京经历中,第一次赶考肩负养家糊口的重任,自身状态的风餐露宿与路途风景的秀丽、庙宇的富丽堂皇、酒店伙计的热情招徕、富人的衣冠富足形成对比鲜明的凄然;三年后再度赴京赶考时柳生已丧失意气,同样的景致已是残垣断壁、苍凉颓败;而三度赴京时又复归繁华构成了世事轮回的循环,小说场景与情节再现并非机械地重复,而有情节推动与对比、强化的功效。
中国戏曲与西方音乐均将重复艺术作为叙事与情感表达的手段,西方古典音乐为余华的创作带来灵感,传统地域文化的旋律与韵味也为其创作提供基石。《古典爱情》中重复的旋律贯穿全文,小说叙事风格单纯宁静而注重细部雕琢,与其叙事张力构成独特的艺术形式,呈现出韵律起伏的情感。小说中场景、情节与语词的重复使散乱的片段式书写与主题情节的陪衬编织为相互勾连的网络,如同交响乐的主旋律般,使小说蕴含单纯而深厚的艺术力量。
三、先锋意识下的现实观照
受传统章回体小说影响,两篇小说的叙事模式运用丰满的细部描写与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古典爱情》与《鲜血梅花》均采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方式,即“无我的叙述方式”,以冷漠的陌生者姿态,甚至对复仇本身、传统旧社会的吃人现象都剥离了叙述情感,波澜不惊地描述暴力、死亡与血腥,作者所展现的是人的丑恶本性与血腥泛滥的世界,通过黑暗世界的客观呈现让读者触及人性的真实,以丰富的语言与细节描写结构全篇。如《鲜血梅花》的语言表达已极尽绚烂,阮进武之妻“首次用自己的目光抚摸儿子”,黑针大侠“头上的黑发开始显出了荒凉的景致”,阮海阔在客店醒来后看到“月光透过窗柩流淌在他的床上”,《古典爱情》中柳生耳中肢解活人的“声音如手指一般短,一截一截十分整齐地从他身旁迅速飞过”,柳生赎回小姐的断腿时“小姐的声音已先自死去了”,诸如此类的通感修辞带来的“间离”效果在武侠小说的通俗化语言中构成了陌生化手法,缓慢的叙述节奏、精致的细部描写赋予读者残酷的距离感。
小说对古典叙事艺术的承继蕴含有浓郁的先锋性。《古典爱情》中直接表露暴力因素,家道中落的小姐惠沦落为“菜人”,血腥暴力的“人吃人”场面在极端的叙述中揭露人性的残暴,余华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饥馑之年民众相食的事实,血腥暴力场景与人性欲望的贪婪共存下对理性的颠覆与启蒙的召唤。“吃人”事件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构成跨时代的共鸣,这是对鲁迅《狂人日记》的一种当代解构,由鲁迅笔下的臆想转为现实的残酷。余华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笔下对意象的冷静叙述,也正是冷漠的零度叙事状态使小说主题获得锐利的批判锋芒。而《鲜血梅花》对暴力的表现极为含蓄隐晦,梅花剑上红色的渲染是对暴力的隐喻,梅花剑上最终没能新添一朵梅花而锈迹斑斑表明对暴力的否定和生存的缺憾,余华将暴力血腥因素转向幕后叙述,隐晦地暴露人性的冷酷,这也是余华创作风格转型前的过渡。
先锋具有尖锐的彻底的文化批判精神,它始终保持着对于主流文化的挑战者姿态,对一切现成的理性逻辑和社会秩序都抱怀疑态度[7]。在暴力形式之外,先锋意识常受虚无主义支配而反叛一切传统文化观念,先锋小说打破传统文学格局,在思想上以“后现代之行”行“现实性之实”,以激进的解构对传统、历史和现实进行否定,披揭存在的荒诞现实和荒诞人生的焦虑与无奈。《鲜血梅花》中有复仇情节却无仇恨的情感,有寻找的目的却失去了复仇的对象主体,只有武侠小说的模式却消解了爱恨情仇的意义,外在形式的存在最终指向的是对自身的否定。而《古典爱情》中柳生倾慕爱恋惠小姐,在她被砍断玉腿时倾囊保全她的肢体,而她新生时又无意中破坏其生还的机遇,这是对人物自身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崇高、理想等终极话语都由先锋小说消解甚至彻底颠覆,因而显露出虚无的内质。两篇小说结尾的收束方式都是主题意义的骤然消解而产生虚无感,《古典爱情》本是柳生为陪伴孤寂的小姐惠而守坟的浪漫爱情,在守候小姐还魂、人鬼再续前缘的关口却落得自掘坟墓而无法生还人世的悲剧性结局,柳生再次复归一无所有的否定意味,爱情主题被超出期待视野的荒诞感消解。《鲜血梅花》中阮海阔的复仇使命受惠于两位武林高手胭脂女和黑针大侠,在漫游中偶遇青云道长时帮他们寻得仇人之所,同时也助自己完成了复仇使命。结局处仇人已死的答案是他三年后在白雨潇处得知的,复仇的间接实现也使其意义訇然消解,遁入虚无的荒诞境界。
余华早期小说将苦难、绝望隐匿于血腥残暴的视觉表达中,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以暴力解读苦难,以此反映作者对生存与人性的思考,在叙事表层下蕴育着现实内涵。“余华小说的变化只是表现形式的不同,而表现内容在本质上仍然故我,关心的仍然是人的生命,仍然是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7]347暴力、死亡等是人性苦难的集中表现,两篇小说透露出余华的宿命意识,人的生存就是要承受生活的苦难,以及世界的阴谋、荒诞、杀戮、暴力,承受隔膜的伤害、亲情的沦丧、美好人性的扭曲,余华将现实中的苦难寄托于主人公饱受摧残的内心世界,反映了作者对生存之痛的咀嚼与思考。源于对现实与思维间紧张关系的认知,“不难感到在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叙述底层汹涌着一股心灵的潜流。呼之欲出,却又无以名之。这股心灵的潜流无疑是余华所发掘的人类特有的情感世界。”[8]柳生在荒年时偶遇深宅大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管家,席地坐在酒店柜台外,讨得柳生施舍的几文钱后精神焕发,“站起把钱拍在柜台上,要了一碗水酒,一饮而尽”,其颓败形象与《孔乙己》中的落魄书生孔乙己产生跨越时代的共鸣,既是对文人式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也有在人文主义光环下民间悲苦的启蒙与关怀。
四、结语
总之,《古典爱情》与《鲜血梅花》两部作品是余华前期小说创作中熔古典、先锋于一炉的经典之作,代表其富于形式创新的文本类别。本文通过分析小说外在的古典形式与内核的先锋性表达,在小说对文类的颠覆、重复叙事艺术的解读中发掘其先锋性和对现实人性的反思与咀嚼,从而阐释《古典爱情》与《鲜血梅花》的文学史价值与现世意义。余华正是在消解、颠覆与重建的形式探索过程中完成了先锋性的创造,也用他的悲悯之心寻找对生命与存在苦难的救赎,这不仅得益于作者在人文主义光环下对生命的尊重与观照,也归功于他对先锋的创新形式与话语潜在力量游刃有余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