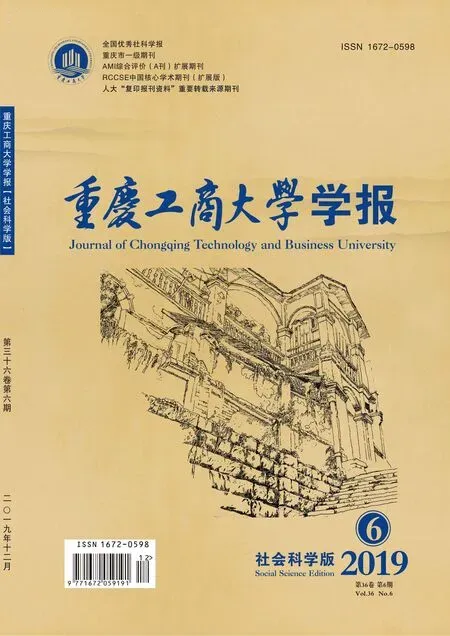南宋前期吉州唱和圈中的布衣诗人及其身份创作
——以民间教师欧阳鈇为中心*
吕肖奂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成都 610207)
两宋时期的民间教师是个散落各地的极其庞大的群体(1)民间教师属于布衣诗人。民间教师常被称作蒙师、塾师、隐士、处士、乡先生。乡先生内涵丰富,宋代主要指未入仕的民间士人,包括私塾书院等各种民间教师。近年来学界对乡先生现象颇为关注,如李芳巧智《宋代民间基层知识分子——“乡先生”群体初探》(2005年学位论文),易卫华《乡先生与宋代诗经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06期:49-53);张建东《一个被忽略的群体》(《华中师范大学》2013);许怀林《试析南宋民办书院与乡先生》(《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1年4期:122-132);杨万里《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清华大学学报》,2010第2期:149-155);杨万里《温州太学九先生的学术与文学创作》(《文学遗产》,2010年第6期:75-83)。布衣诗人(包括处士游士)在北宋后期已经十分可观(参《北宋处士网络》),到了南宋就更加发达,其数量应该超过官员诗人数量,但其诗歌留存却远不及官员诗人。,他们不仅对基层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2)杨万里在《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一文中指出:“两宋之交永嘉地域文化之兴起,端赖塘奥先生、儒志先生、经行先生这类乡先生的言传身教和辛勤培养。考当时,此类乡先生、乡贤颇多。”参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而且曾经是文学创作的强大力量,甚至曾是足以与士大夫创作力量相抗衡的诗歌创作主力军。他们的存在不仅具有历史社会学研究价值,而且具有文学与文化研究价值。但这样一个社会群体乃至阶层,却因为他们自己的创作现存极少,其生存状况与总体形象、创作风貌与精神世界令后世难以捕捉与把握。
南宋前期江南西路吉州(3)郡名庐陵,下设庐陵、吉水、安福、太和、龙泉、永新、永丰、万安等八县。详参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祝穆《方舆胜览》,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及其周边曾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官民唱和圈,其中有王庭珪(1080—1172,吉州安福人,隐居泸溪50年)、胡铨(1102—1180,吉州庐陵人)、周必大(1126—1203,吉州庐陵人)、杨万里(1127—1206,吉州吉水人)、赵蕃(1143—1229,寓居信州玉山,淳熙6-8年为吉州太和簿)(4)五人生平详参傅璇琮主编《宋才子传笺证》之北宋后期卷(王庭珪660-674页)、词人卷(胡铨497-510页)以及南宋前期卷(周必大385-396页,杨万里411-425页,赵蕃673-685页)。辽海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等仕宦时间长短不一、官位高低不同的士大夫诗人,也有欧阳鈇(1126—1202,吉州庐陵人)、葛潨(1126—1201,吉州庐陵人)、刘承弼(?-?吉州安福人)、刘伯山(?—?吉州庐陵人)、杨愿(?—?临江军清江人)等长期登门或开门教授的民间教师。而后者的“群体”出现,在这个唱和圈中尤其引人注目。作为社会弱势群体,民间教师诗人诗作几乎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无人问津。考察这个官民唱和圈中的官民交往唱和文献以及布衣诗人留存的点滴作品,可以对民间教师这些底层士子群体乃至阶层有较多的认识和了解。
一、吉州唱和圈中的民间教师诗人的群体存在与基本形象
吉州唱和圈主要由出生于吉州的官员与布衣组成,与一般地方唱和圈由出任某地方的外籍官员与当地士子组成不同,乡谊、学缘成为这一唱和圈形成的纽带。民间教师欧阳鈇曾是这个唱和圈中的一员,虽然不像周必大、杨万里等士大夫那样声名显赫,但其特殊的身份却使得这个唱和圈有了特别的意义。
欧阳鈇与周必大同乡、同学且同龄,但周必大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及第,此后仕宦通达至于位极人臣;而欧阳鈇则屡试不第,以登门教授终其一生(5)详见第二小节。,两人成年后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周必大仕宦期间,两人之间身份悬殊,生存空间鲜有交集,所以鲜有唱和,加上欧阳鈇《脞辞集》久已遗失,周必大《文忠集》中虽然存在却也找不到在此期间与欧阳鈇唱和的痕迹。两人再次往来唱和,是在周必大致仕(庆元元年1195)返回家乡时,主动与欧阳鈇、葛潨组成齐年会唱和,此时三人都已经七十岁了。
葛潨是与欧阳鈇一样的民间教师,他曾做过胡铨、周必大的西宾。周必大《葛先生墓志铭》云“(葛潨)贯通经子历代史书,端醇详雅,士大夫子弟争愿从。胡忠简公及其群从号儒先甲族,竞以书币延致。亦尝不鄙,过予家塾。晚即所居讲授,八邑暨傍郡秀民著录盈门。先生迪以行谊,非但章通句解而已,后多登第游宦荐春官不论也。”[1]葛潨晚年由登门教授的家庭教师变成开门教授的私塾教师,声名远播,教学成果显著,是一位成功的民间教师。
周必大《葛先生墓志铭》云:“予自上印绶,与先生及欧阳伯威,岁讲同甲之会,月为贞率之集。”在论及年岁之时,周与葛、欧之间官与民的身份悬殊似乎完全不存在,周必大不断重申三人同乡同学同寿之谊以及晚年唱和之乐:“诗场曾作推敲手,文会今随出入肩”“艾耆天俾如三寿,谈辨人惊似八仙”“情均雁序兼莺友,寿贯犀颅映鹤肩”(6)三诗分别见《文忠集》卷四十一《庆元乙卯(阙)与欧阳伯威(鈇)、葛徳源(潨)俱年七十,适敝居落成,乃往时同试之地。小集圃中,再用潞公韵成鄙句,并录旧诗奉呈》,卷41《三月二十八日春华楼前芍药盛开,招欧葛二兄,再为齐年之集,次旧韵》,卷四十二《己未二月十七日会同甲,次旧韵》;但对于葛潨和欧阳鈇而言,其感受无疑不同。经历了中年天壤之别的生活之后,晚年三人似乎回归当初,而周必大的屈尊降贵带给两位家庭教师的应当不只是荣耀。就在当年三人参加解试之地,周必大建成了他的养老华居(7)《文忠集》卷四十一《庆元乙卯(阙)与欧阳伯威(鈇)、葛徳源(潨)俱年七十,适敝居落成,乃往时同试之地。小集圃中,再用潞公韵成鄙句,并录旧诗奉呈》:“诗场曾作推敲手”之自注云“吾三人皆以诗赋试于此。”,由此地而发迹的周必大自然充满自豪,而对于同试而落第的葛潨、欧阳鈇而言,此处无疑是个失意心酸之地,二人的和诗虽已经不存,但可以推想到其中可能会包含着一些悲凉的身世之感。
周必大称赞葛潨云:“先生文华有余,凡予小圃草木猿鹤,悉为赋诗,语新而事的,卷轴盈箧。”[1]可知葛潨是位工于摹写外物的勤勉诗人。葛潨还曾为三人齐寿唱和绘图以示纪念(8)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十二《戊午仲春同甲小集次旧韵》“香山已写丹青像”自注“阙。徳源近绘写三寿图”。,此外,这位民间教师“所著有《草茅卑论》三卷,《祭斋笔语》四十卷。先生存心恕而勇于义,尝集本朝死王事者,著《旌忠录》三卷”[1],这些著作也都和他的诗歌一起荡然无存,但我们由此可以得知这位民间教师在教书之余不仅兼善诗画而且还勤勉撰述。
欧阳鈇与周必大的唱和诗也不存,从他的临终诗句“故人应好在,谁念此生浮”[2]可以感受到他终生抱憾:“故人”虽是贵人且并未将他遗忘,但他自己的一生却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而是无奈潦倒地虚度了。
杨万里与欧阳鈇是同乡,年龄相仿,虽不像周必大欧阳鈇关系那样多重,但他对欧阳鈇的赏识与褒扬时间更久且更不遗余力。他为其《脞辞》写序,还摘其诗句以大力褒扬,欧阳鈇因此而享有盛誉。
欧阳鈇去世后,杨万里《欧阳伯威挽词》云:“泸水奇唐律,香城赏楚辞。前身定东野,又得退之碑(自注:益公作志铭)”[3],诗中所说的“泸水”与“香城”就是王庭珪、胡铨(9)泸水,即泸溪,亦作卢水、卢溪,杨万里《卢溪文集序》:“先生王氏讳庭珪,字民瞻,登政和八年第,调茶陵丞,与上官不合,弃官去,隐居卢溪者五十年,自号卢溪真逸。”香城,周必大《文忠集》卷四十四《香山楼铭》(嘉泰辛酉二月):“庐陵南四十里有香城山,其名见唐皇甫持正所作寺碣。峻拔广袤,中一峰尤奇秀,谚所谓文笔者。胡氏世居其下,至忠简公(胡铨),遂以直节修能名震当世,归,即旧地筑冠霞楼,坐致爽气。”。这两位前辈乡贤很早就褒赞过欧阳鈇,王庭珪欣赏欧阳鈇接近唐律的诗风。胡铨欣赏欧阳鈇的辞赋:“(欧阳鈇)尝著《遇谏词》《蜂螫蜘蛛赋》,胡忠简公极口称奖。一时名公推重如此。”[2]作为一介布衣的欧阳鈇,其诗赋能得到这么多著名士大夫的称许,对他的创作无疑是极大的鼓励。
除了王庭珪、胡铨等前辈,周必大、杨万里等同辈乡贤外,与欧阳鈇唱和的士大夫还有赵蕃。赵蕃虽非吉州人,但曾为吉州太和县簿,与欧阳鈇往来唱和频繁。赵蕃以恩荫入官,仕途坎坷且短暂,作为后辈,他在《次韵欧阳伯威因书见寄》中云“病过一春事,不惟嗟索居。酒杯疏到手,药裹每关予。曹务宁知马,悲歌岂为鱼。故人能枉问,安否报何如”,向欧阳鈇倾诉既病且不开心的“马曹”生活;《呈欧阳伯威》云“传得新诗字字惊,佛廊骤识病身轻。李邕昔已求工部,文举今宜荐祢衡。只道迷邦尚蓝缕,试令吐气即峥嵘。一官不作来南限,取友得交齐鲁生”(10)以上分别见赵蕃《淳熙稿》卷十、卷九、卷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则为无人举荐欧阳鈇入官而抱屈;赵蕃对欧阳鈇诗歌推崇备至,《次韵欧阳伯威见和》云“宗派滔滔是,于今得障流。无悲和者寡,故愈暗中投。我愿下取履,君其高卧楼。穹冈(11)穹冈,其他相关诗歌皆作“穷冈”。如诗割,肯爱一官休”,敬佩到愿意和欧阳鈇一起隐居穹冈。
赵蕃在谈到欧阳鈇时,经常提及另一位诗人刘伯山(12)伯山,未考证出其名。洪迈《夷坚志》乙卷四云:“吉州士人刘伯山之女弟将嫁。”中华书局,2006年。,《淳熙稿》卷二十《寄简欧阳伯威刘伯山》:“问讯穷冈病主人,若为买得竹溪邻。是中剩有堪诗处,恨不与之相主宾。”《淳熙稿》卷十三《刘伯山》书来云有施主为造一亭,刘子澄(13)杨万里《卢溪文集序》:“清江刘清之子澄评先生之文,谓庐陵自六一之后,惟先生可继。”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八十,中华书局2007年,第3 241页。《宋史》卷四三七《儒林传》中有刘清之传。名曰竹溪,索诗,《为赋二首》中有“杜老不应栖锦里,谪仙终合见金銮。兹亭便与图经载,何况制名繇孟韩”,“旧诗颇愿穷冈割,后约要容王翰邻。更唤能诗子欧子,不因对月自三人。”赵蕃还多次拜访刘伯山,如《晚过刘伯山》云“晚向穷冈访竹亭,竹间忽有打禾声。凶年独使诗人饱,可见天公非世情。”[4]刘伯山去世后,赵蕃《简赠欧阳伯威二绝句》还提及:
江西人物况欧阳,少有诗名老更昌。左辖虽能诵佳句,子虚胡不荐君王。
三年身不到穷冈,诗友飘零半在亡。杯里纵能谈矻矻,镜中无复鬓苍苍。(自注:亡友谓刘伯山)[4]
从这些诗句中可知,刘伯山与欧阳鈇都住在穷冈,相距不远,是赵蕃一直都想与之为邻的“诗友”。欧阳鈇肯定曾与刘伯山有不少唱酬。王庭珪《卢溪文集》卷四十八《跋刘伯山诗》道:“刘伯山诗调清美,不减其父升卿(14)刘升卿在当时当地颇有诗名,除与王庭珪交往唱和外,还与刘才邵唱和。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卷一《赠刘升卿》:“吾宗富清制,金璞饱镕炼。髙轩肯见临,大轴获初见。”刘伯山子承父业。,其源流皆出于江西。……伯山方少年,如骏马驹,日欲度骅骝前,异时于江西社中横出一枝,为鲁直拈一瓣香可乎。”可知刘伯山之父也是诗人,与王庭珪同辈,刘伯山则应与欧阳鈇年岁相近。杨万里有《题刘伯山蕃殖图二首(画禾黍稷菽麦)》,则可知刘伯山与葛潨一样诗画兼善。王庭珪、杨万里与赵蕃、欧阳鈇、刘伯山等人都有交往唱和。众人笔下的刘伯山亦耕亦读,被视作隐士,虽不能确定其是否做过民间教师,但可以肯定他也是个布衣诗人。
周必大《欧阳伯威墓志铭》所云“泸溪王敷文庭珪、西溪刘孝廉承弼、杨愿,皆教官诗豪,或以孟襄阳、贾长江比君。他文率过人。”[2]三位将欧阳鈇比作孟浩然、贾岛的“教官诗豪”,一个是王庭珪,早年中进士而隐居泸溪五十年,曾以教学为生,为官时间短而隐居时间长[5]。
二是刘承弼,终生为家庭教师。刘承弼在科举道路上比欧阳鈇稍好一点:“安福县刘君彦纯讳承弼,绍兴丙子(1156年)、乾道戊子(1168年)两荐于乡。既下第,即隐西溪。淳熙三年(1176),邑人举其节行,旌表门闾。”(15)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二《刘彦纯和陶诗后序》(庆元二年四月日)。另外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四《刘氏旌表门闾记》:“西溪刘氏讳承弼字彦纯,尝再与计偕,报闻,则归隐于安福之西溪。今谏大夫谢公谔,尝倡郡士百十人列其孝行节义于朝,有诏旌表其门闾。”两次解试成功,但礼部试失败,刘承弼仍然无法进入仕途。周必大、杨万里称刘承弼“隐西溪”,而实际上这位隐士与很多被称作隐士的士子一样,主要是以教授更多士子为生,杨万里《诚斋集》卷七十四《刘氏旌表门闾记》云:“承弼所学殚洽,江之西、湖之南士子辏集,执经问学,户外履满,瑰才隽士,小大有就。”刘承弼与欧阳鈇一样都是民间教师,但他主要是开门授徒,不像欧阳鈇那样需要登门为家庭教师。
杨万里、周必大都十分欣赏刘承弼的和陶诗,周必大云:“(刘)常慕五柳先生为人,尽和其诗百篇,焕章阁待制杨公廷秀为之序(16)即杨万里《西溪先生和陶诗序》。序云“淳熙戊申(1188)九月晦日,友人朝奉大夫新知筠州军州事杨万里序”。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八十,中华书局2007年,第3 246页。,盛行于江西。而其弟之壻赵伯琢复求予题其后。予告之曰:‘彦纯此诗,殆得于唐人,非得之五柳也。’伯琢骇而请其说,予曰“平澹简易,忘怀仕进,彦纯之性也;不揠不画,尽吾之才,彦纯之习也。昔鲁男子夜闭户拒邻妇,妇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男子曰:‘子与吾皆幼,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将以吾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称其善。今吾彦纯盖有得于此,信予斯言,然后知渊明春兰秋菊,松风涧水,果在彦纯破琴断弦中。廷秀真知音哉。”[6]王庭珪有《故左奉议郎刘君墓志铭》提到乡贡进士刘承弼,还有《答刘彦纯》;杨万里二十一岁与刘承弼交往(17)杨万里《水月亭记》“年二十有一,乃始得友吾彦纯。彦纯之为人,非今之所谓为人者也,其为文,非今之所谓为文者也。”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七十一,中华书局2007年,第3 004页。,关系最为密切,有《约刘彦纯会建安寺》《跋刘彦纯送曾克俊作室序》等诗。刘承弼在周、杨等人的褒扬举荐下,在当时其声名超过欧阳鈇,他将欧阳鈇比作孟浩然、贾岛,自然有更多身份上的因素。
三是杨愿,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二《杨谨仲诗集序》云:“谨仲讳愿,五十余方入官。” 杨愿与周必大同年(1151)中进士(18)周必大《同年杨谨仲教授以诗庆予得郡次韵二首癸巳二月》《同年杨谨仲教授生日癸巳六月二十八日》。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二《杨谨仲诗集序》“一为县主簿,两为郡博士,朝廷尝以车辂院起之,即上书请老,转通直郎,家居累年,赐服绯鱼,寿七十有九,亦不可谓诗能穷人也。”,而他五十多岁及第仕宦之前,也做了多年的基层教师:“谨仲自少为先进所推,未第时,乡之英俊争受业于门,名闻四方,愿交者众,二千石以下皆尊礼之。盖其行艺俱优,而尤喜为诗。”[7]当时的确有不少官员像杨愿一样,在中进士或入仕前曾做过或短期或长期的家庭教师或私塾教师。杨愿是与吉州相邻的临江军人(19)祝穆《方舆胜览》卷二十一:“国朝以清江县置临江军,隶江南西路,仍以新淦、新喻属焉。今领县三,治清江。”周必大《杨谨仲诗集序》:“同年杨谨仲,家世文儒,才高而气和,于书无不读,于名胜无不师慕之,嗜古如嗜色,为文昼夜不休。清江置郡今二百年,二刘三孔以来文风日盛……。”可知杨愿为清江人。,杨万里与他也有唱和如《乙未(1175)和杨谨中教授春兴》,周必大称赞他的诗歌“本原乎六义,沉酣乎风骚,自魏晋隋唐及乎本朝,凡以是名家者往往窥其藩篱、溯其源流,大要则学杜少陵、苏文忠公。故其下笔初而丽,中而雅,晚而闳肆,长篇如江河之澎湃浩不可挡,短章如溪涧之涟漪清而可爱,间与宾客酬唱,愈多愈奇,非所谓天分人力全而不偏者耶。”[7]
以家庭教师欧阳鈇的交往唱和为视角的吉州唱和圈,可以看到其中民间教师诗人之群像:他们是极其优秀的民间教师,在城乡基层教育中拥有相当高的声望;他们还是十分优秀的诗人,在教学之余创作大量值得称道的诗歌,他们多才多艺,甚至著书立说;民间教师之间不仅有着交往唱和(尽管唱和诗歌基本散轶),而且与当地士大夫也有紧密联系,他们的交往创作并不局限于自身阶层。
二、社会阶层流动中民间教师的典型人生轨迹
袁采《袁氏世范》卷中云:“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资,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8]在阶层流动性明显加剧的宋代社会,只有一小部分士大夫子弟能够“取科第致富贵”,而大部分的士大夫子弟则只能“开门教授”或“登门教授”,成为民间教育工作者。吉州唱和圈中的民间教师都属于后者。在士大夫的序跋题记以及墓志铭等现存文献中,民间教师曾经是一个为数不少的存在,他们有唱和圈、有别集,有个体心声和群体风貌。欧阳鈇是其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
“伯威名鈇,吾州永和人也,其族与文忠公同系。其先策第者凡七人,有曰中五者,附入元祐党籍。”[9]与欧阳修同一族系的欧阳鈇出身于“官族”[2],在当时户籍上属于官户或形势户,与民户或平户在很多方面享受不同的待遇。但是官户或形势户中也有高中低层之分。欧阳鈇祖上的官位并不显赫:“世为郡人,高祖登,以其子澶州通判粲遇恩赠奉议郎;曾祖来用,举守本州助教;祖元发,虽不仕,而弟将作监承珣,靖康间以忠义著”[2]。其祖辈中并无飞黄腾达的官员。到了欧阳鈇的父辈,“父宣教郎充字彦美,擢绍兴壬戌(12年,1142)进士第,戊辰岁(18年,1148)卒官广西。”[2]才及第的欧阳充却在释褐不久就病逝,终任于“广州经干”[9],并没有给欧阳鈇留下更多的资产和资源。
低级官员的子弟比中高级官员子弟更容易沦为平民百姓。杨万里《夫人左氏墓志铭》云:“乾道戊子(1168),亡友刘彦纯尝与予语:‘州里儒家者流,其子孙能世其业者鲜焉。’”[10]“儒家者流”在这里主要指参加科举的人,因为无论及第还是不及第,参加科举就需要学习儒家经典。及第者“世其业”较容易,而落第还能继续研习儒学则很难,因为维持家业的资本有限。
“伯威侍母何氏,携诸幼,护柩千里,返葬永和镇”[2],二十二岁的长子欧阳鈇由粤护父柩返乡的过程十分艰辛,资金的缺乏甚至让他无以为葬。他可能求助于乡贤王庭珪,王庭珪为之动容乃至为其募捐:“欧子扶亲丧,崎岖度湘巘。岂无当涂人,孰肯为封传。跣足行万里,仅能及乡县。埋玉谋荒山,此计堕弥漫。世无郭元振,一举四十万。积微会众力,庶可咄嗟办。”[11]
欧阳鈇回到故乡永和镇,集资安葬父亲后,从此挑起家庭重担。对于士大夫子弟而言,失去做官的父亲就意味着失去经济支柱,而作为长子,在父亲过世之后必须变成这个家庭新的经济乃至精神支柱。年轻的欧阳鈇显然缺少管理家庭经济的才能:“爱母弟铎,恣其费,弗问,遂窘伏腊。”[2]对弟弟的溺爱,直接导致家庭破产。欧阳鈇虽然“学广才赡”,有中举的基本功,而且他心存高远:“锐欲拔蝥弧而先登”,然而却“已乃连战不利”,进身之路从而断绝。尽管“士悼其屈”[2],但欧阳鈇无力改变自己命运。
有养家责任和义务的欧阳鈇,无法成为高蹈出世的逸人山人,他也没像同时的庐陵二刘(刘过、刘仙伦)那样游走干谒。为了养家糊口,别无其他谋生技能的他,被迫选择做一个基层教师,所谓“聚为仰事俯育计”[2]。杨万里再见欧阳鈇就是在其被聘为西宾之时:“始予识欧阳伯威于傅彦博之座中,见其扬眉吐气,抵掌论文,落笔成诗,屈其座人,予敬之慕之,私窃自愧其不如也。后二十年,闻吾里萧岳英(20)《萧岳英墓志铭》:公讳许,字岳英。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二八,中华书局2007年,第4961页。为子弟择师,得异人焉,急往谒之,则吾故人伯威也。[9]”就在杨万里两见欧阳鈇的二十年间,欧阳鈇由意气风发的士子变成了当地著名的家庭教师,众人口碑中的“异人”。周必大谈到欧阳鈇的家教生涯时亦云:“名卿大家争延训子弟,时官闻名,皆来礼请。”引起“名卿大家”和“时官”关注和延聘的欧阳鈇,与葛潨、刘承弼、杨愿等人一样,其职业生涯十分出色是当时在士大夫看来十分杰出的民间教师。
周必大认为欧阳鈇能够成为知名的家庭教师,除了“学广才赡”外,还因为欧阳鈇有他自己的待人接物原则:“其间贤否不同,徇物必招谤,绝物或贾怨,君皎皎其躬,温温其容,束修外毫发无预,物莫能凂,人自亲爱。”[2]欧阳鈇不随便接受“束修”之外的任何收入,很好地处理了教师与学生家长尤其是那些“名卿大家”“时官”的关系,这一点足以证明欧阳鈇有良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才学兼备加上人际关系良好,欧阳鈇的家庭教师职业发展顺利,收入也至少足以维持大家庭基本生活:“伯威事母至孝”“毕二弟三妹嫁娶,人以为难。”[9][2]一个基层或底层的士子,尽到长子、长兄的生活责任。这应该是南宋城镇中一个优秀家庭教师的普通生活。
周必大致仕后回到故乡,见证了晚年欧阳鈇的生活:“逮予来归,而君视瞻茫洋,不复教学,簟瓢怡然。时时相过道旧。以目眚疏麹生亲玉友,步趋亦蹒跚,独豪气如初。予每怜之。”[2]因为年老体衰,晚年的欧阳鈇已经结束了家庭教师生涯。家庭教师的一生看起来就是如此平凡简单。
杨万里欣赏欧阳鈇的“豪气不衰”:“予既涉患难,鬓发之白者十二,而风霜凋剥之余,落然无复故吾矣。伯威之气凛凛焉不减于昔,独其贫增焉耳。不以增于贫而减于气如伯威者,鲜乎哉。”[9]周必大印象最深的是欧阳鈇的一生“豪气如初”:“嗟乎伯威,少慕太白,才不羁而行不亏;中游饭颗,午不炊而乐不饥;晚邻文昌,医不治而笔不衰。”[2]欧阳鈇早年的“豪气”是士大夫子弟的狂放自傲,中年的“豪气”是生存困境中的清贫自强或清高坚忍,晚年的“豪气”则是贫病之中的精神屹立不倒。
事实上,民间教师的收入不高,即便是声名远播的“异人”欧阳鈇,其生活也不会像官员那样富足有余,因此周必大在显达之后也曾试图振拔欧阳鈇:“予在政府,数欲官之,谢曰:‘欲吾数口无饥足矣,焉事虚名。’”[2]但“豪气”长存的欧阳鈇以知足常乐为由而婉拒为官,坚守一个自尊有操守的底层士子的尊严。这使欧阳鈇一生享有清名,欧阳守道云:“寓庵逸才清名,盖东坡于子野所谓‘遍交公卿,靡所求希者’,身没而无遗其子,固其理也。”[12]
欧阳鈇的清贫程度,在其去世之后不久就显现出来:“既而见其子行甫,贫甚不自拔。前广文赵先生知其名,招致学馆,今广文陈先生又免其月书,俾常在讲下,皆盛德事。然学故例,春秋丁祭食鼓不鸣者旬月,或值假休,又无所以廪。嘻,其可悲也已。”[12]欧阳行甫虽然“贫而能守,老而苦学,以无忝于前人”[12],却至于在学馆丁祭与假休期间衣食无着,需要拜谒欧阳守道以帮其谋求活路,欧阳守道希望行甫能在“今郡县学与二书院养士不一所”中得到一个足以生存读书的位置。基层士子的贫困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吉州唱和圈中周必大、杨万里等人对欧阳鈇的书写,让人们看到士大夫眼中欧阳鈇具体而细节化的生活,领略到一个民间教师的真实存在及其典型意义。
三、民间教师的身份创作及其表达意向
吉州唱和圈中几位士大夫诗人的别集及著述基本得以保存,而民间教师诗人除欧阳鈇尚有几首诗歌以及一些诗句留存外(21)周必大《欧阳伯威墓志铭》云:欧阳鈇“平生篇什《脞词》外分五编,号漫成、遣兴、暮景、自娱、松筠,别有杂著五卷,见闻录之。”杨万里曾为其《脞词》写序。但《脞词》与大多数民间教师别集一样已经遗失。,其他人的别集著述基本遗失。多数作品遗失,使得民间教师的职业特性、群体属性乃至社会阶层尤其是其精神世界都变成无法确知的缺憾,从这个意义上讲,欧阳鈇遗留的诗句以及他的交游唱和都有着超越自身存在的探索价值。
民间教师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处于官民之间,十分尴尬,官员以及世俗社会对家庭教师有或多或少的职业歧视,士大夫在与民间教师的交往唱和中,多数为了礼仪或消融歧视,有意无意地美化民间教师形象。譬如在杨万里、周必大的诗文中,欧阳鈇是一个不汲汲于名利、不叹穷嗟贫的处士,尤其突出其尽管生活贫困,但其干云豪气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杨万里眼中的欧阳鈇是“酒魄飞穿月,诗星流入脾。豪来无一世,贫不上双眉”[3],一生诗酒豪纵似乎从没意识过或考虑过自己的生存困境。周必大也说欧阳鈇是个贫贱不能屈、疾病不能移的世外高人。
周必大、杨万里都从士大夫的角度“书写”欧阳鈇:处于贫穷之地而不以贫穷为意,能够像隐士高人一样乐观积极,像道学家一样识得孔颜乐处,是个超然物外的高人。而这些,显然是士大夫诗人对非官员诗人的劝慰、鼓励或褒赞之词。士大夫笔下的布衣诗人基本都是这样超越世俗、超然世外的隐士与高人,这无疑在掩饰布衣诗人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乃至精神生活上的困顿。
实际上,杨万里、周必大都聘用过家庭教师,都了解民间教师的真实处境与清贫生活。杨万里甚至曾与欧阳鈇探讨过如何才能解决民间教师的穷困问题:
予因索其诗文,伯威颦且太息曰:“子犹问此耶?是物也,发人以穷,而吾不信,吾既信而穷已不去矣。子犹问此耶?”已而出《脞辞》一编,曰:“子不怜其穷而索其诗,子盍观其诗而疗其穷乎?”予退而观之,其得句往往出象外,而其力不遗余者也,高者清厉秀邃,其下者犹足以供耳目之笙磬卉木也。盖自杜少陵至江西诸老之门户,窥闯殆遍矣。他日伯威过我,曰:“子真不有以疗我之穷耶?”吾笑语之曰:“穷之疗与否?可疗与否?吾且不吾及,吾庸子及哉?吾有一说焉,杜子美、李林甫、谢无逸、蔡太师四人者,子以为孰贤?”伯威怒曰:“子则戏论也,然人物当如是论之也哉?”予曰:“人物何不当如是论也?当李与蔡之盛时,天下肯以易杜与谢哉?今乃不然耳。然则子之穷姑勿疗焉可也。虽然,穷之瘳,如李焉如蔡焉,不既震曜矣哉,杜与谢之穷至今未瘳也,子之穷疗焉亦可也,杜与谢之穷则至今未瘳矣,使二子而存,肯以此而易彼乎?子之穷勿疗焉亦可也。”伯威曰:“吾当思之。”[9]
欧阳鈇像多数布衣诗人一样,秉承“诗能穷人”的惯性思维,将自己的贫穷处境归咎于诗歌创作,他希望士大夫杨万里为他“疗穷”,可能是希望杨从物质上或仕途上救其脱离贫穷之境,而杨万里则机智地回答说他连自己的贫穷状态都无力改变,更不可能改变欧阳鈇的穷者命运,因此杨万里只能用历史人物的生前身后名声变化来劝慰欧阳鈇,以期改变欧阳鈇的处穷心态。
欧阳鈇偶然也有安贫乐道的诗句,如《示二子》云:“先君以官贫,我仍遗以安。但愿两儿健,扶持一翁孱。何须待门生,悠然柴桑间。”(22)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九《欧阳伯威(鈇)》一节从《余话》《玉林》中转录杨万里的摘句。厉鹗辑撰《宋诗纪事》卷四十八转引《诗林万选》欧阳鈇《示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 219页。但他这类享受贫穷生活的诗句现存并不多。他的处穷心态也没有杨万里等士大夫期待的那么超然或者克制。诗人欧阳鈇显然不想有意成为士大夫眼里的隐士高人,他不仅向杨万里等人诉说贫穷、祈求疗救,还经常用诗歌抒写他作为底层文人的悲哀。
从“千里归来人事改,十年犹幸此身存”看,欧阳鈇曾经有过将近十年的远游,他可能像当时的游士一样游学或者游谒以谋求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在异乡生计无着时,他写诗自伤:“生计嗟乌有,谁人问子虚。西风五更雨,南雁数行书。衰朽儿童笑,飘流岁月馀。秋深新病起,吾志在吾庐。”他曾远赴夔州,像王粲一样思念故国亲人:“夜起集万感,胡为淹此留。诗成夔子国,人在仲宣楼。络纬声中泪,芭蕉雨里愁。遥知屡门倚,应念有方游。”(23)《宋诗纪事》卷四十八引自《诗林万选》,称之为《禾山秋兴》,但禾山在吉州永新县附近,离欧阳鈇家乡不远。而第二首诗中的“夔子国”是指夔州,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八山南东道七夔州云:“夔州云安郡,今理奉节县,春秋时为夔子国,其后为楚灭,故其地归楚”。所以《禾山秋兴二首》题目不妥,至少后一首不是禾山作。厉鹗辑撰《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19-1220页。还有“梦回千里外,灯转一窗深”(24)出处同上。被人称颂的残句,也是远游他乡漂泊无依时所作,带着浓厚悲凉的乡愁。
显然,十年游历并没有改变欧阳鈇的生存困境,他最终选择以家庭教师为生。而家庭教师的聘用、聘期、聘资都取决于聘主,居住与收入都不稳定,所以欧阳鈇一生都觉得流离失所,无法安定,其《卜居》云:“此生老矣益飘零,汤饼来年又何所。是身如寓敢求安,更著小轩名以寓。凭谁叫阍与帝语,有客多艰乃如许。”“汤饼”可以说是“腐儒”这一贫寒穷酸身份的特定食物,黄庭坚《谢送碾赐壑源拣芽》曾云“春风饱识大官羊,不惯腐儒汤饼肠”(25)宋梅应发、刘锡同撰《四明续志》卷十《谢惠计院分饷新茶》云:“平生腐儒汤饼肠,不堪八饼分头纲。”,而对于未能入仕的“腐儒”欧阳鈇来说,每年都要为“来年”充饥的“汤饼”而一筹莫展。一生安居对他来说是一种奢望,因而他只求有屋寄居,所以自号寓庵(26)杨万里应欧阳鈇之请为其作《寓庵铭》。;深感人生多艰的欧阳鈇在诗末至于呼天喊地。他并没有试图掩饰他的穷困艰辛。
欧阳鈇现存的多数诗句都在倾诉他的艰难不幸的人生。如《绝句四首》其一云:“恋树残红湿不飞,杨花雪落水生衣。年来百念成灰冷,无语送春春自归。”随着春去的“百念成灰冷”,有着一种对生命对生活的绝望。其三云“为怜红杏卧枝斜,看到斜阳送乱鸦。又是一春穷不死,天教留眼看莺花”,如此极端怨恨“穷”,真正表达出处“穷”者的心声。再如“谁知花过半,才与酒相寻。故人惊会面,新恨说从头”“月白玄猿哭,更残络纬悲”“青山如故情非故,芳草唤愁诗遣愁”“扰扰征人相顾语,萧萧落木不胜秋”[13]等诗句,都表达着欧阳鈇的悲凉苍凉心绪。
特别是欧阳鈇《和伍武仲》所云:“未知一岁于此水,几回照影惭栖栖。失身竟堕管城计,错路不为田舍儿。”可谓最痛彻心扉的道白。如果是“田舍儿”的话,欧阳鈇至少有一些田产维持生计,但作为士大夫子弟,他只能拿着毫“无食肉相”的“管城子”而谋生,一生凄凄惶惶如丧家之犬。
如果从欧阳鈇的身份角度去体验这些诗句,会有异乎寻常的感受,这些诗句既无士大夫理性沉淀后的“自持与自适”,也没有一般隐士高人刻意避世的那种平淡安闲,而是民间教师阶层的心情写真与心理写实。
杨万里《跋欧阳伯威诗句选》云:“予既序其《脞辞》,复手抄此数纸,自有用处。每鸟啼花落,欣然有会于心,遣小奴挈瘿樽酤白酒,釂一梨花瓷盏,急取此轴,快读一过以咽之,萧然不知此在尘埃间也。”[14]而上述的欧阳鈇诗句,多数都是杨万里抄写来用以快读下酒的,所谓“诚斋尝摘其警句抄之”[15]。如此悲凉的诗句,杨万里居然用以下酒,读起来好像十分惬意舒心。由此看来,杨万里可能是忽略了欧阳鈇的身份与真情,而将这些诗句当作“措词之精绝”的美言以消遣了。
作为士大夫的杨万里,是无法体会底层士子的痛心与酸楚,还是真正地做到了超然红尘之外?杨万里欣赏另一位民间教师刘承弼的和陶诗时,态度也接近他读欧阳鈇之时,《西溪先生和陶诗序》云:
余山墅远城邑,复不近墟市,兼旬不识肉味,日汲山泉煮汤饼,傧以寒韲,主以脱粟,纷不及目,嚣不及耳,余心裕如也。偶九日至,呼儿问有酒乎,曰“秫不登,无所于酿”,余仰屋喟曰“安得白衣人乎?”已而所亲送至新醅,余欣然又问“有菊乎?”曰:“秋未凉,菊亦末花”,余又喟曰“既得陇复望蜀可乎?”因悠然独酌,取几上文书一编观之,乃予亡友西溪先生和陶诗也。
当重阳节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之时,杨万里将刘承弼的和陶诗当作九日的菊花替代品来弥补遗憾:
读至《九日闲居》,渊明云“尘爵耻虚罍,寒花徒自荣”,东坡和云“鲜鲜霜菊艳,溜溜糟床声”,西溪和云“境静人亦寂,觞至壶自倾”。则又喟然曰“四者难并之叹,今古如一丘之貉也。”儿跽而请曰“东坡西溪之和陶孰似?”余曰:“小儿何用强知许事?渊明之诗,春之兰、秋之菊、松上之风、涧下之水也;东坡以烹龙庖凤之手而饮木兰之坠露、餐秋菊之落英者也;西溪操破琴、鼓断弦以泻松风涧水者也。似与不似,余不得而知也。汝盍于渊乎问焉。”[16]
由此可见,杨万里其实十分了解社会身份对诗歌风貌的塑形作用,只是他兼容并蓄,对每个阶层的诗歌都能从纯粹审美的角度来欣赏。对他而言,不同身份的诗人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的身份语言,都是值得欣赏的。美的诗歌像菊花像美食美景一样令人赏心悦目,即便是悲苦凄凉之语也不会影响杨万里的审美心境,苦情的极致表达反而能增强他的美感体验。因此,欧阳鈇充满世俗生活苦痛的悲情苦语在杨万里的审美世界里竟然也能远离“尘埃间”。欧阳鈇没有刻意掩盖他的社会身份,故作高士,他自然流露的身份语,可能正是杨万里感到痛快处。
民间教师的日常生活及其交往唱和圈不同于士大夫,他们的诗歌创作自然既不同于士大夫创作,也不同于契合士大夫审美标准的隐士高士创作。一个社会阶层的集体身份写作,即便会受到另外一个社会阶层的审美趣味或思想影响,但不会完全受到那个阶层的同化,因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写作其实是一种社会身份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自然流露。作为民间教师的欧阳鈇及其同行创作的诗歌如果大多数存在,一定会让宋诗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景象,改变其以士大夫诗歌为主导的诗坛一元化格局。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