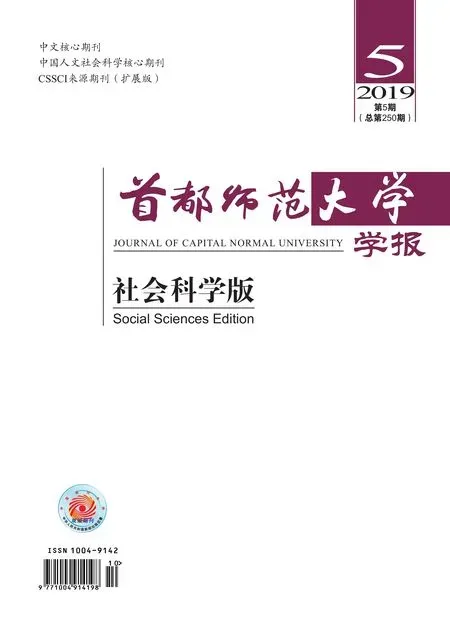台阁与山林:元明之际文坛的主流话语
左东岭
一
学界论及台阁体,一般的看法是流行于明代永乐、宣德及成化年间,以当时的台阁重臣三杨为代表的诗文流派,其典型特征乃是以理学为基本价值核心,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以平和工稳为体貌特征,迄今为止这种被四库馆臣所定位的台阁体已经成为文学史的基本常识。但随着近2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学界已经使该问题逐渐引向深入。在这期间不仅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也有研究明初地域文学与诗歌史研究论著均会给出专章来论述台阁体及其文学观念,最近几年还出版了以台阁体为专题的研究论著。(1)以台阁体为专题的论著如郑礼炬的《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的翰林院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汤志波的《明永乐至成化间台阁诗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还有像黄卓越的《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虽不以研究台阁体为书名,但其中前两章内容都是集中论述台阁文学观念的,并且相当系统而深入。这些成果代表了目前台阁体研究的学术水平。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有两点:第一是研究立场的转变。自五四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台阁体一般都是作为被否定的文学现象被提及的,而近20年来则基本已经站在中性的立场对该体派进行较为客观的研究与评价。第二是研究的深入与细化。以前学界研究台阁体大都以“三杨”为对象,而尤其以杨士奇为研究重点。最近20年来不仅“三杨”之外的作家得到了关注,而且也对他们各自的诗文作品予以认真细致的解读分析,使该领域研究的基础更为扎实,思维更趋缜密。
但在研究过程中显然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进一步克服的问题。其中研究视野亟待拓展便是一个需要在此重点提及的问题。目前的台阁体研究在横向展开上进展明显,研究者不仅能够对其文学风格、文学体裁及审美形态加以深入述论,而且还能对其与政治制度、理学观念的内在关联认真清理与研讨。但在纵向拓展上则存在明显不足,往往就台阁体论台阁体。向下至多延续至李东阳,而对明代后期的台阁文学明显关注不够,更不要说与清代的台阁文学进行比较研究了。向上则至多上溯至宋濂与方孝孺,而对于元代的台阁文学则基本未能进入研究的视野。这显然对于完整地把握台阁文学的研究是有缺陷的。如何宗美论台阁体之核心概念“舂容”之内涵时说:“综合上述数例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看法,第一,‘舂容’是明代台阁体文学的文风特征和审美特征;第二,台阁体的‘舂容’文风是明代‘全盛’时期的‘承平’气象在文学中的反映;第三,体现‘舂容’文风的除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外,还有黄淮、金幼孜、周叙、岳正、徐溥、吴俨、祝萃、孙继皋等,他们多为明前中期人,也有极个别属明后期;第四,所谓‘舂容’与‘平易’、‘和雅’、‘闲雅’、‘宏敞’、‘妥帖’等相关,与前文提到的‘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洪钟斯扣,每尽舂容之音’、‘盖其器闳深,其声舂容’并非同一含义。它不再是指宏大响亮、铿锵有力以及磅礴大气的一种美,而是指温文有度、优游娴雅的另一种风格,概言之,即是优美而不是壮美。”并认为其原因:“是中国古代审美史和文学创作史中对‘舂容’美认识在南宋以后发生了嬗变的结果,其促因则是理学兴盛背景下儒家审美思想的不断强化,道学对文学、美学的介入和内化通过台阁作家成为事实。”(2)何宗美:《明代文学还原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2-193页。此处对明代台阁体“舂容”特征之把握、对“舂容”博大内涵与平和内涵之区分,可谓考察细微而深入,体现了明代台阁体研究的当今最高水平。但其对台阁体形成原因之探查、对台阁体流行史实之认知则尚可进一步商量。明初之宋濂、刘基、刘嵩、方孝孺等人已经对台阁文学博大宏畅之体貌进行了许多理论的探讨,尤其是方孝孺之探讨更为全面而系统。同时,陶安、宋濂、高启、方孝孺等人的诗文创作也已经呈现出盛大宏伟之体貌,可以说“鸣盛”成为洪武初期的主流文学观念。因此,明初文学思想史的史实是,展现了一个从盛大昌明到雍容和平之舂容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关的则是理学意识与事功观念的融合分化的过程。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的问题,乃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对跨代的文学现象研究很不充分,不能有效连接起台阁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线索;二是对于元代台阁文学的研究尚未能达到深入系统的程度,以致影响了与明代台阁体研究的比较视野。
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台阁与山林是涵盖相当广泛的一对概念,明代的台阁体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段落而已。从其生成时期看,只有与山林相对应,台阁的特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否则不足以显示其完整的意义。孙明君在其一篇论文中,曾如此概括早期的山林与台阁的状况:“两晋之时,郭象哲学中首次提出了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模式,此一人格模式在东晋南朝士族中影响深远。隋代权臣杨素不仅具有廊庙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 同时,在诗文创作中形成了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兼之的文学范式。初盛唐时代,贵族社会推崇廊庙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但缺少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兼善的诗人。王维是杨素之后廊庙山林文学范式的继承者和发扬者。”(3)孙明军:《杨素与廊庙山林兼之的文学范式》,《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在此需要关注的是郭象所提供的玄学人生观对于台阁与山林兼之的文学启示,他在诠释《逍遥游》时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 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 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4)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页。这便是玄学之名教与自然为一的所谓士当身名俱泰的人生追求,从而也成为山林与台阁此一对文学观念的哲学基础。然而,士当身名俱泰仅仅是玄学的理想人生状态,其实在现实中真正能够实现者可谓少之又少,于是就有了宋代吴处厚的两分的提法:“余尝究之,文章虽皆出于心术,而实有两等: 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则其气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书立言者之所尚也。 朝廷台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5)吴处厚:《青箱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版,第 46 页。由此可知,正式提出山林与台阁之文并进行了体貌描述的是在宋代,而且是与士人的仕隐状态联系在一起予以表述的。换言之,山林与台阁无论是论人还是论文,都是在两两对应的语境中展开的,而明代前期所流行的台阁体仅偏于台阁一方的倾斜状态并不是其理想表达。也正由于此,至明代中期的李东阳,已经又回归到传统的提法,所谓“至于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淡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不可少也”(6)李东阳:《麓堂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84页。。
二
关于山林与台阁的表述,最为集中的历史阶段大约应属于元代中后期尤其是元明易代之际了。而较早又较为系统的论述则为浙东文人黄溍,他在《恭侍郎文集序》中说:
昔之论文者,盖曰:“文之体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夫立言者,或据理,或指事,或缘情,无非发于本实。有是实,斯有是文。其所处之地不同,则其为言不得不异,乌有一定之体哉!侍郎早从文靖公至京师,而与英俊并游于成均,逮释褐授官,而践敭中外,在朝廷台阁之日常多。故其蕴蓄之素,施于诏令,则务深醇谨重,以导宣德义而孚重听;施于史传,则务详赡精核,以推叙功伐而尊国执;施于论奏,则务坦易质言,以别白是非邪正,利病得失,而不过于矫激。他歌诗、杂著、赞颂、碑铭、记序之属,非有其实,不苟饰空言以曲徇时人之求。至于宦辙所经名区胜地,大山长溪,空林邃壑,风岚泉石,幽遐奇绝之概,有以动其逸兴,而形于赋咏,与畸人静者互为倡答,率皆清虚简远可喜,亦非穷乡下士草野寒生危苦之词可同日语也。盖其为文,初不胶于一定之体,安知其孰为台阁,孰为山林也耶?(7)王颋:《黄溍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页。
该文是黄溍至正十五年为恭师泰文集所作的序文,二人皆为台阁作家,论文观念较为一致,不需要照顾对方立场,故其所言应为真实思想的流露。此处所表达的看法有四层:一是继承了前人论文可分为山林与台阁二体的传统看法。至于是否直接承袭自吴处厚的说法则不得而知。二是所处之地不同,所作文体亦异。三是作文必须讲究得体,针对不同文体,讲究不同写法,达到不同效果。四是大作家可诸体兼备,兼具山林与台阁之体貌。应该说此处所论系统而完善,可以代表元代文人台阁文论的观点与水准。而且由于其台阁重臣的身份和浙东文坛的领袖地位,其台阁文论的观点对于当时与稍后的诗文批评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就今所见,与其同时或稍后的台阁作家柳贯、恭师泰、危素、欧阳玄、张翥、张以宁均有以山林与台阁论述诗文的大量文字。而其后学弟子宋濂、戴良、王袆、胡翰、苏伯衡等人也都踵其师说,成为以山林与台阁论文的积极追随者。宋濂在元末时即如此论诗:“士之生斯世也,其有蕴于中者,必因物以发之。譬犹云既滃而灵雨不得不降,气即至而蛰雷不得不鸣。虽其所发有穷达之殊,而所以导宣其湮郁,洗濯其光精者则一而已矣。是故达而在上,其发之也,居庙堂则施于政事,谋军旅则行于甲兵,严上下、和人神则见于礼乐,交邻国则布于辞命。或穷而在下,屈势与位,不能与是数者之间,则其情抑遏而无所畅,方一假诗以泄之。诗愈多,则其人之愈穷可知也。”(8)宋濂:《马先生〈岁迁集〉序》,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8页。宋濂在此不仅将文学分为达而在上与穷而在下两种状态,其实也就是台阁与山林的具体展开与细化,而且还指出了元代台阁文学与山林文学的文体差异与创作目的不同。也就是台阁文学主要以散文创作,尤其是那些应用性强的诏、诰、表、策等文体为主,而以诗歌创作为辅助,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满足朝廷的实用需求。而山林文学则主要以诗歌创作为主,而以宣泄诗人的自我情感为其目的。尽管宋濂在本文中并不是以这些内容为重点,但他的感受与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指出了台阁与山林文学的主要特征与异同。
黄溍的另一位门生王袆也曾以台阁与山林论诗曰:“国家致治比隆三代,其诗之盛,实无愧于有唐。重熙累洽,抵今百年。士之达而在上者,莫不咏歌帝载,肆为瑰奇盛丽之辞,以鸣国家之盛。其居山林者,亦皆讴吟王化,有忧深思远之风,不徒留恋光景而已。”(9)王袆:《张仲简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忠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110页。王袆的论诗思路与宋濂不同,他主要是着眼于台阁与山林之诗的趋同的一面,而且都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加以比较,“咏歌帝载”与“讴吟王化”是创作目的之相近,而“瑰奇盛丽”与“忧深思远”虽体貌有异,但有关于王朝政治则又是一致的。或者会认为王袆之赞语有理想化成分与溢美之嫌,但他所评论的这位张仲简是一位吴中诗人,其诗歌之体貌“温丽靖深,而类乎韦、柳”,则的确是元代隐逸诗人的主流风格,所以王袆的评价也不能算言不及义。以上所引两篇诗序,都应该是宋濂与王袆作于元末的诗论,当时他们还都是布衣的身份,或者说属于山林之士,他们既无责任也无必要从官方的角度去谈诗论文,则其以台阁与山林的方式谈论诗歌,显然是受到了当时流行风气的影响,尤其是黄溍、柳贯等师辈的影响。但考虑到宋濂与王袆这些浙东文人在明初都曾主持朝廷文柄,对当时文坛具有主导的作用,则其文学的观念也会成为明初的主导思想。从此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浙东文人联结起了元明两代台阁文论的主脉。
三
如果仅仅是台阁文人与浙东作家以山林与台阁的标准论文评诗,那依然不能完全说明当时此种观念的流行程度,而铁崖体领袖杨维桢,在野文人倪瓒,吴中文人王彝,天台隐士徐一夔等人也均有此方面的论述文字,就足以证明此种观念的深入人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吴中诗派代表作家高启也曾有题跋曰:“论文者有山林、馆阁之目,文岂有二哉?盖居异则言异,其理或然也。今观宗人士敏《辛丑集》,有舂容温厚之辞,无枯槁险薄之泰,岂山林、馆阁者乎?昔尝有观人之文而知其必贵者,吾于士敏亦然。嗟夫,吾宗之衰久矣?振而大之者,其在斯人欤?”(10)高启:《题高士敏辛丑集后》,金檀注:《高青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25页。高启本是元末著名的隐逸诗人,依当时标准理应归入山林诗人的行列,但他在此却居然也按山林与台阁的分类论文,则可知当时这已成为流行的惯例。该文虽不具备理论上的深度与价值,但无意间却恰恰说明了此种论文模式的流行程度。”辛丑”为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显然该文乃作于元末,故可考知当时论文之一般状况。尤可注意者,当时人不仅用山林与台阁的分类标准评述当代作家的诗文创作,还用于学术研究的论述,宋讷《唐音缉释序》曰:“诗人立言,虽吟咏性情,其述事,多索古喻今,或感今思古。其写景,则所历山川原隙,风土人物之异,所见则昆虫草木,风云月露之殊,各萃于诗。至于诗人居台阁、列朝廷者,所历所见,莫非城观宫阙之雄,典章文物之美,器械车马之壮,华夷会同之盛,殆非山林所历所见可概论也。”(11)《全元文》,第50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宋讷所序乃唐人诗歌之研究著作,他既没有必要说讨好的话以结纳作者,所论也不大合乎唐代诗歌的分类习惯,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他已经形成了以山林与台阁的方式去论述诗歌的思维惯性。该文所属写作时间为“至正甲午夏六月”,亦即至正十四年六月,由此可知当时文坛之一般情状。
不少学者在研究台阁体时,也曾追溯其源头至宋、元之时,尤其时常与明初宋濂的文论联系起来予以考量,但同时又认为作为文学流派的台阁体依然需要限定在明前期的“三杨”之后。这当然是有其道理和依据的。然而,如果认真检阅元明之际的相关文献,却又不得不说当时的作家不仅创作出了大量的台阁体诗文,而且也在理论上提出了明确的台阁体内涵、特征与标准。元末台阁体作家张翥有一段文字集中代表了当时人的台阁体认识水平:
昔人论文章,贵有馆阁之气。所谓馆阁,非必掞藻于青琐石渠之上,挥翰于高文大册之间,在于尔雅浑厚金浑玉润,俨若声色之不动,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长,视夫滞涩怪癖,枯寒褊迫,至于刻画而细,放逸而豪,以为能事者,径庭殊矣。故识者往往以是概观其人之所到,有足征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迄于今,诸公辈出,文体一变,扫除俪偶,迂腐之语不复置舌端,作者非简古不措笔,学者非简古不取法,读者非简古不属目,此其风声气习,岂特起前代之衰,而国纪世教维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实有系乎此也。(12)张翥:《圭塘小稿序》,《全元文》,第4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页。
张翥是元末重要的台阁作家,曾官至翰林侍读兼祭酒,并参与修撰宋、辽、金三史,最终以翰林承旨致仕,其卒年则为至正二十八年,也就是洪武元年。他之论台阁文章,已经超越了作者身份的层面,并不仅仅限于那些身居高位者所作诗文才能称之为为台阁之文,而是说只要真正具备了“尔雅浑厚金浑玉润,俨若声色之不动,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长”的体貌,也就是所谓的雅正和平、温润从容的特征,就可以称之为台阁之文。而且他明确指出自至元、大德而“文体一变”,不仅起点清晰,而且指出此乃“文体”层面的变化,其要旨则在于对“简古”文风之追求,形成了所谓“作者非简古不措笔,学者非简古不取法,读者非简古不属目”的整体社会风气。而这种文风的形成,则最终能够起到“化成天下”的实效。对此段文字加以归纳,则可知台阁文体之核心在于文风的简古,简古的内涵则在于拥有“尔雅浑厚金浑玉润”的体貌,其反面则是“滞涩怪癖,枯寒褊迫,至于刻画而细,放逸而豪”,其目的则是起到“化成天下”的政教效果。张翥的序文当然不能代替元代其他作家对台阁文体的判断,而且也很难说全面准确,但就其自身而言,还是完整而系统的台阁文论。以此与明前期“三杨”的台阁文论相比,不仅主旨明确,而且论述全面。明人对“三杨”台阁体的认识,在当时并不明确,一直到弘治时的陆深才开始予以概括:“惟我皇朝一代文章,自太史杨文贞公士奇实始成家,一洗前人风沙浮靡之习,而以明润简洁为体,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13)陆深:《北潭稿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俨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246页。且不说他对元代“风沙浮靡”文风判断的主观失误,也不说他忽略“我朝”文章的创始者宋濂的大意粗心,仅就对台阁文体自身的概括,也显得过于简略而政治意识过强,算不得真正的文学见解。拿此与张翥的论述相比较,则高下深浅可以立判。当然,就目前所见,对明代台阁体论述最为全面系统的,还要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杨文敏集》提要曰:
荣当明全盛之日,历事四朝,恩礼始终无间,儒生遭遇,可谓至荣。故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沉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14)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84页。
在此,作者强调了台阁文风与时代的关系,也指出了台阁体内容中应制之作与私人写作的构成,更重要的是概括了台阁体由“醇实无疵”之内容与“逶迤有度”之笔法所构成的“雍容平易”的体貌特征。尤可注意的是,他是拿具有“富贵福泽志气”的台阁之气与“枯槁”的山林之气相对而言的,这就回归到了中国古代山林与台阁文学并举的传统模式。在此如果将四库提要的此段论述与张翥的论台阁文章的文字相比,可以看出其论述思路的一致与理想文风的趋同。“尔雅浑厚金浑玉润”与“富贵福泽”“雍容平易”只不过属于表述语言之差异,而其思想内涵则相当接近。以此作比当然不是说元代的台阁文学与明代的台阁体完全相同,而是说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台阁文学的组成部分。明代的台阁体并非中国文学史的特有现象,而是其中的一个段落而已。而实际上,元明之际的台阁与山林文学的关系,则自有其独特的内涵,也是当时文坛的主流话语。
四
由上所论可知,台阁文学是贯穿于元明两代的创作类型,绝非仅属于明代前期一个历史时段。而且元代的台阁文学自有其特点,与流行于明永乐之后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不尽相同。元代的台阁文学与山林文学是一组并列的概念,一直被文坛所广泛使用,以致最终在元明之际形成一种流行的批评话语,而且与王朝政权更迭、文人身份转化以及南北文化交融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元明易代的文学思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杨维桢曾经集中讨论过关于宋濂诗文作品台阁与山林的属性问题,可以彰显他对该问题的认识水准以及从中所包含的台阁文学的历史内涵:
客有持宋子潜溪诸集来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帙,宋子近著馆阁之文也。其气貌声音,随其显晦之地不同者。吾子当有以评之。……昔之隐诸山林者,奕乎其虎豹烟霞也;今之显诸馆阁者,灿乎其凤皇日星也。果有隐显易地之殊哉?不然,以宋子气枯神寂于山林,与志扬气满于馆阁,是其文与外物迁,何以为宋子?抑余闻婺学在宋有三氏,东莱氏以性学绍道统,说斋氏以经世立治术,龙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见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实践,而取信于后之人而无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干诸治术,以超继三氏于百十年之后,世不以归于柳、黄、吴、张,而必以宋子为归。嘻,三十年之心印,万万口之定价,于斯见矣。客何以山林、馆阁歧宋子之文而求之哉!(15)杨维桢:《潜溪新集序》,黄灵庭:《宋濂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7-2738页。
作为元明之际最负盛名的诗文作家与批评家,杨维桢的确是眼光独到,谈锋犀利。他在此颠覆了自宋代以来论述台阁与山林文学的基石,即所谓所居之地不同而其为文亦异的论述模式。也许以此论述一般的作者不无道理,但以之概括宋濂的创作便殊为不妥。因为如果宋濂由于地位的不同就会显示出文章体貌的差异,则“何以位宋子”?那宋濂不是与一般作者毫无区别了吗?在杨维桢的眼中,无论是隐居山林时的“虎豹烟霞”,还是志扬气满时的“凤皇日星”,都自始至终展现出宋濂的以道为文的独自心得,都是万口相传的优异之作。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乃是浙东学术沉积百年的必然结果。杨维桢认为,浙东学术是吕祖谦的心性之学、唐仲友的经世之学与陈亮的事功之学的综合,都是学有实得而可以独自名家的杰出学派,宋濂继承了浙东学术的精神而予以发扬光大,形成了所谓的“根性道干诸治术”的文章特色,也就是既以儒家的道德性理为根底,又与文章的各种实用功能相结合的创作方式。这些特点发自南宋,而又被柳贯、黄溍等婺中文人所继承,最后归结于宋濂而集其大成。
杨维桢的这些看法是否合乎宋濂创作的实际呢?这有宋濂本人的文论观念作为旁证,他在概括其师黄溍一生时说:“先生之所学,雝其本根,则师群经;扬其波澜,则友迁、固。沉浸既久,超然有会于心。尝自诵曰:‘文辞各载夫学术者也,吾敢为苟同乎?无悖先圣人,斯可已。’故其形诸撰述,委蛇曲折,必畅所欲言。出用于时,则由进士第教成均,典儒台,直禁林,侍讲帷幄,以文字为职业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盖一世,可谓大雅弗群者矣。今之论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圆密切,动中法度,如孙、吴用兵,而部伍整然不乱。至先生之独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16)宋濂:《文献集序》,王颋点校:《黄溍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7页。宋濂认为,一般人仅仅从文章笔法与体貌上理解评价黄溍,只不过得其皮毛而已,黄溍的独得之秘在于道、文、用的三位一体,即师群经而雝其根本,以司马迁、班固之笔法以传先圣之道,最终“出用于时”。这与杨维桢的“根性道干诸治术”的概括何其相似。宋濂感叹“至先生之独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当然是自认为已经得了先圣之“端倪”。那同样也可以说,杨维桢也认为一般人仅依照常规的山林台阁思路概括宋濂之文章,也属于“焉能察其端倪”的浮泛之论,而自己的见解才揭示了宋濂的“独得”之秘。从此一论述思路看,杨维桢的确是抓住了婺中文学思想发展的主线,也揭示了宋濂创作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价值意义。同时他还展现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揭示了易代文学的重要特色。这包括:元末以宋濂为代表的文人群体,尽管名义上属于山林隐逸之士,但其诗文创作与文章观念却具有浙东传统的经世意识与实用追求,因而在入明之后能够迅速成为服务于大明王朝的台阁作家,从而贯穿起元明两代的台阁文学。
如果再深一层看,该论题还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理论内涵,台阁与山林文学并非是某一作家或某一流派的个体行为,而是自南宋以来所形成的丰富传统在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具体展开与变化。可以说,杨维桢的论述对于元明之际台阁与山林文学观念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解思路,打开了该学术领域的广阔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