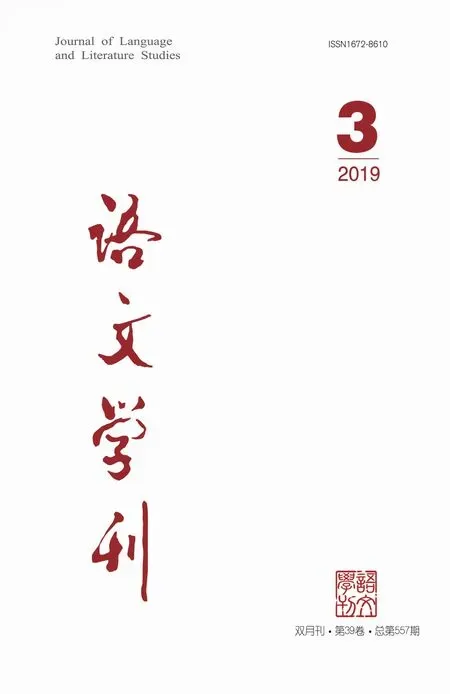略论章学诚的文学观念
○刘凤泉
(韩山师范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不同于正统考据学派,章学诚《文史通义》,打破学术壁垒,贯通文史理论,体现了学术融通的文学观念。
随着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特点越来越突出,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逐渐趋向明晰。魏晋之后,文、笔分论;唐宋之后,诗、文分论。这样尽管加深了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认识,却也忽略了文学与整个文化系统的联系。乾、嘉时学界文坛,学问家专逞博学,文学家溺于文辞,理学家空谈义理,皆以树木为森林,见解难免片面偏激。恰如庄子所言:“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494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章学诚主张学术融通,强调“窥乎天地之纯,识古人之大体”[2]649。他说:“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所不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达于大道,故曰通也。”[2]389可见,尽管学术不同,而皆通达于道。于是,他从道器关系立说,阐述了独特的文学观念。
一、辨道器
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器。《原道中》曰:“《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而且他将六经皆器具体阐述为六经皆史,明确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1;“非国家之政典,即有司之故事”[2]138。将六经概括为政典史事,其实包含着经世致用的深刻用意。
乾、嘉时期,正坐考据、词章、义理交讥相攻之弊病,所谓“服、郑训诂,韩、欧文辞,周、程义理,出奴入主,不胜纷纭”[3]84。在学术分裂的背景下,章学诚强调学术融通。他既反对“溺于器而不知道”,如汉学之沉溺于训诂、考据;也反对“舍器而言道”,如宋学之空言义理;而主张学术的融通,“即器而明道”[2]472。他说:“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功,或可庶几耳。”[2]138从道的高度来看,学术具有统一性和互补性。《与朱少白论文》云:“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显,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须闲习,皆学也;皆求道之资,而非可执一端谓尽道也。”[3]335可见,三者皆道中之一事,也是学中之一事。“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2]166
章学诚强调学术融通,致力学术通达于道。他说:“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具体而言:一是沟通不同领域。他认为考订、义理、文辞不可分割,“主义理者,著述之立德者也;主考订者,著述之立功者也;主文辞者,著述之立言者也。”[3]84二是贯通不同时代。他将历史上所有著述贯通一体。“夫文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也。……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2]139诸如叙事的、说理的、尚真的、重美的、尚虚的、实用的,全部包笼无遗。三是会通片面道理。他主张著述要“窥乎天地之纯,识古人之大体”[2]649,不能眼界狭隘而偏执于一端。
从道器关系的学术整体来审视文学,自然强调文学与整个学术整体的密切联系。钱穆先生说:“章实斋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他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也等于章实斋讲文学,他也并不是站在文学立场来讲文学,而是站在一个更大的学术立场来讲文学。这是实斋之眼光卓特处。”[4]293可见,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认识,章学诚表达了一种学术融通的文学观。
二、溯流别
章学诚致力校雠之学,总结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945的方法。他说:“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对于文学源流,他细致加以考辨:“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2]60通过追寻文体演变的轨迹,他提出战国之文源出六经,战国之文多本诗教,后世文体备于战国等重要的文学观点。
他说:“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2]60六经皆器,乃言道之器;战国之文,源于六经,言道体一端,亦为言道之器也。他说:“战国之文,……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九流之学……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2]60-61春秋行人赋《诗》,善用比兴;战国纵横游说,变本加厉;战国之文当其用世,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故而继承了《诗》之表达方式。他又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2]61战国之文,上承六经而下启辞章,实为辞章之学的渊薮。
战国之文是文体演变之关键,它源于六经,出于《诗》教,深刻影响了后世之文。在章氏看来,六经为文章典范,六经皆器则文章皆器,六经皆史则文章皆史。他以史学为著述之大宗,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3]335,如“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文人别集也与史学相通,《文选》等文学总集“以辅正史”。他说:“史迁发愤,义或近于风人;杜甫怀忠,人又称其诗史。由斯而论,文之与史,为淄为渑。”[3]298他竭力强调文学与史学的密切联系。于是,他以史学为古文辞的传统,指出:“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左丘明古文之祖也,司马因之而极其变;班、陈以降,真古文辞之大宗。”[3]334
以史学为宗,论文便以叙事为主。他说:“文辞以叙事为难,今古人才,骋其学力,辞命议论,恢恢有余,至于叙事,汲汲形其不足……然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其源本于《春秋》‘比事属辞’”[3]55。可见,古文辞原是一种源于史学的,以反映社会生活为主的著述之文。
章学诚有《古文十弊》,批评古文领域存在的不正风气,重点阐述了古文辞的义例。所谓“义”是指史家从史实中概括出来的思想、观点、规律。他说:“《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2]470所谓“例”,则有多方面的意义。主要是指运用事实、表述观点的方式方法,也包括文章体例、称名惯例、格式常例等。
所以,写作古文辞,他强调作者志识。他不厌其烦地比喻说:“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云云。[2]350文辞与志识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志识为主而文辞为佐,这是章学诚的史学认识,也是他的文学认识。
三、倡文德
章学诚言文德,并非空洞谈论文人之德性,而是指作者著述的正确态度。《史德》曰:“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对此,《文德》更做了具体阐述:“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2]278
一是临文主敬。此就创作而言,作者临文,调整心气,从容中道,谨防偏激,做到心平气和,才能变化从容,“以是为文德之敬”。
临文主敬,来源于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5]872柳宗元以文羽翼夫道,故强调临文不可不慎。“主敬”也是程朱理学调心摄性的修养方法。朱熹的治学宗旨为“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所谓“养气二项: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主敬原是养气的基础。章学诚吸收前人思想的营养,用它来讨论作者著述的真诚态度。
二是论古必恕。此就批评而言,指出文学批评的严谨态度。他说:“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2]278。古人著述的具体情况不同,批评要设身处地理解古人,才能对古人著述做出正确评价。
论古必恕,何谓“恕”? 《论语》释“恕”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既含有道德意义,也含有实践意义。将“恕”用之于文学批评,最早是孟子“知人论世”的方法。章学诚进一步将“恕”确立为文学批评的原则,将儒家的忠恕精神贯穿于文学批评领域。
三是立言为公。“临文敬恕”,必以公心为基础。《公言上》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2]169
树立为天下立言的思想境界,文人写作要出于公心。无论记事、写人、议论,都要客观公允,中正平实,不作矫诬之笔,不逞个人私见,才能合于天下“大道之公”。也只有立言为公,著述才能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他说:“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古人巧而后人拙也,古人是而后人非也,名实之势殊,公私之情异,而有意于言与无意于言者,不可同日语也。故曰:无意于文而文存,有意于文而文亡”[2]182、184-185。程千帆指出:“实斋所谓文德,则临文态度之必敬以恕也。而要其归,则‘修辞以立其诚’一语以括之。”[6]135
四、明文理
文章为载道之器,自然不应离道而专意文辞。他说:“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2]340然而,文辞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原道下》曰:“即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熏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之治,圣贤功修,未尝无悦目赏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2]139
文章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文章的独特艺术规律。他说:“就文论文,别自为一道也;”[2]489“盖文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恶,人之见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2]340文理,即文章的艺术规律,对此他做了深入具体的阐述。
一是立言有物。文章由衷而发,写出真实感受,方为言之有物。他说:“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乞求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不能彼此相异,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沉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慎乎?”[2]287
二是气行情至。文章要具有文势,文势由辞气形成。他说:“文固用以明理,或以记事,然有时理明事备而文势阙然,乃若有所未尽。此非辞意未至,辞气有所受病而不至也。求义理与考订者皆薄文辞,以为文取事理明白而已矣,他又何求焉?而不知辞气受病,观者郁而不畅,将并所载之事与理而亦皆病矣。”[7]354-355文章需具有文情,文情未至,则事理表达不够。他说:“今人误解辞达之旨者,以谓文取理明而事白,其他又何求焉?不知文情未至,即其理其事之情亦未至也。譬之为调笑者,同述一言而闻者索然,或同述一言而闻者笑不能止,得其情也。譬之诉悲苦者,同叙一事而闻者漠然,或同叙一事而闻者涕夷不能自休,得其情也。昔人谓文之至者,以为不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夫文生于情,而文又能生情,以谓文人多事乎?不知使人由情而恍然于其事其理,则辞之于事理,必如是而始可称为辞达。”[7]353
三是比兴取象。文章运用比兴,需要观物取象。《易教下》云:“《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犹为表里。夫《诗》之流别,盛于战国人文,所谓长于讽喻,不学《诗》则无以言也。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2]19
文章取象多为人心营构之象,它又来源于天地自然之象。他说:“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然而心虚用灵,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人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是则人心营构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2]18-19
四是寓言假设。不同于历史著述,文学具有虚拟想象的特点。《言公下》曰:“又如文人假设,变化不拘。《诗》通比兴,《易》拟象初。庄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庐。楚太子有疾,有客来吴。乌有、子虚之徒,争谈于校猎;凭虚、安处之属,讲议于京都。《解嘲》《宾戏》之篇衍其绪,镜机、玄微、冲漠之类濬其途。此则寓言十九,诡说万殊者也。”[2]197对于文学虚拟想象,“善读古人之书,尤贵心知其意”,体现了章学诚对语言艺术的理解。文理是文章的独特规律,对这些规律的掌握,需要读者自身努力。他说:“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而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2]287只有读者自身的真切感受,才能被运用到文章写作中去。
梁启超说:“学诚不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其言‘六经皆史’且极尊刘歆《七略》,与今文家异,然其所著《文史通义》,实为乾嘉后思想解放之源泉。”[8]69诚哉斯言!在清代文论中,章学诚的文学观念可谓独树一帜。他打破了学术壁垒,融通文史领域,为从文化整体来认识文学开辟了路径,这对文学理论发展也颇具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