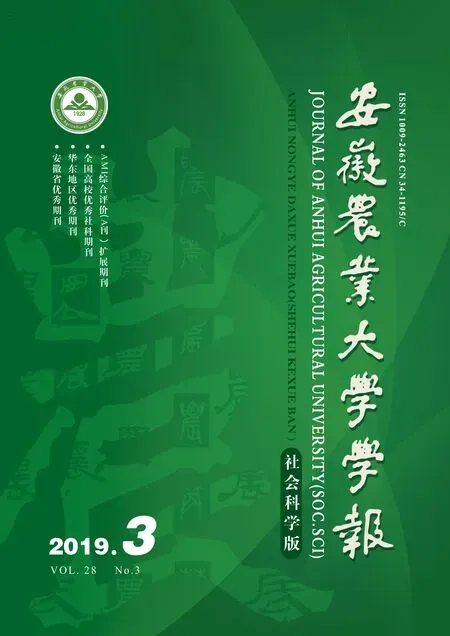“绿色”理念下的美丽乡村生态治理*——基于对马克思笔下普罗米修斯形象的生态解读
徐玉祺
(安徽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一、马克思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
马克思一生有很多文字都用普罗米修斯作隐喻,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对普罗米修斯不畏宙斯权威的反叛精神大加赞赏,称颂其为“哲学史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1]12。不仅如此,马克思一生的不同阶段其个人思想情感和实践中也表现出普罗米修斯般的殉道者意志和革命精神。马克思的三篇中学毕业作文中,最能体现其情感倾向的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文章将普罗米修斯牺牲自己为人间盗火的奉献精神化为“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1]459的选择。他的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之间的差别》通过对伊比鸠鲁偏斜式的原子运动方式的认可,称赞普罗米修斯对传统和权威的挣脱,马克思本人的革命的意志在此文中开始显现[1]3。大学毕业之后马克思任职于《莱茵报》,尽管那时他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文章涉及关税贸易法案、林木盗窃法案、出版自由和社会等级法案、市政问题等关系最底层劳动人民权益的议题,已经深刻地显露出马克思对劳动者的同情和社会不公的鞭笞。由于触怒普鲁士当局,《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拒绝了一切威逼利诱,像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了信念和理想而远走他乡,过着颠沛流离的穷苦生活。在流亡法国编写《德法年鉴》期间,马克思发表的两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从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和鲍威尔宗教解放的批判,主张通过实践引向一般人的社会解放问题[2]。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了哲学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使命转变[3]133。在马克思的思想演变中普罗米修斯式的道德和良知是贯穿始终的情感要素,《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宣告了全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道路[3]399。《资本论》对资本增殖的秘密——剩余价值的揭示,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斗争武器。对旧世界和一切不公正的拒绝和痛斥,使其充满了普罗米修斯般反叛权威和拯救弱小的精神。马克思忠实于人民立场去对抗当时的社会体制遭受的政治打压和生活窘境,就像他的偶像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而做的牺牲,马克思的理论之光如同普罗米修斯的圣火照耀人类解放之路。
二、马克思笔下普罗米修斯形象的生态解读
西方后马克思学者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拒斥理性和本质、解构元意义和文本的过程中,靶向不可避免地指向马克思。马克思基于社会生产对社会演变的解释让后马克思主义者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是唯生产力论者,导致马克思著作中象征反叛与革命的普罗米修斯被狭义地解读为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力。女性生态主义者卡洛琳·麦茜特在其名作《自然的死亡:女人、生态学、与科学革命》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态’代价并感到痛心的同时,却又接受了启蒙运动通过对自然的控制取得进步的神话。”[4]生态社会主义学者雷纳·格伦德曼在《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理论》中写道:“马克思的基本前提是对自然进行‘普罗米修斯’式的控制。”[5]维克托·福基斯认为:“马克思对世界的态度始终保有这种普罗米斯式的劲头,一直赞扬人类对自然的征服。”[6]无政府主义者约翰·克拉克则直接将马克思比喻为普罗米修斯,抨击其自我实现的意志对自然生态造成的损害:“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是个不认识自然的人,是不将地球视为生态之家的人。他是个倔强的、一定要让自然依从自己对自我实现的追求的精灵。对这么一个人来说,自然的力量——无论是其自身难以控制的内在自然力量还是险恶的外在自然力——必须得到控制。”[7]173-174
西方学者的普遍误区在于把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视为对自然的反叛,指责马克思对机械力征服自然的崇拜。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提倡的对世界的改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亦是对客观规律的掌握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崇拜普罗米修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普罗米修斯是被作为挣脱束缚的革命者的形象而出现。希腊神话中,宙斯用锁链绑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设法挣脱并重获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普罗米修斯是被奴役和暴政统治下的反抗者。马克思也因为其创造的无产阶级斗争理论被称为“人间的普罗米修斯”[8]。再者,普罗米修斯盗火作为一种技术象征,是人类劳动能力和改造世界的创造精神的体现。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找不到他们支持唯生产力论的语句,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技术革命快速发展的19世纪“控制自然”已经是个非常普遍的说法。我们可以找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和自然辩证关系的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写道:“人类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至死亡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55-56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绝不是人类中心主义者,相反,他明确将人置于自然之中。让这种关系异化的是资本控制下的人类生产。“挣脱者”普罗米修斯在这里是为人类美好家园穿上绿色衣服的生态守卫者,人与自然在绿色生态中获取平衡发展。
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在于其异化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的支配下一切关系都被金钱化,这种冷酷无情的疲于奔命的劳动与现金支配下的社会不是人类的最终取向,理想的社会秩序是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状态。在《资本论》中,他在谈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说:“社会化的人,也就是,共同结合的生产者,将会按照合理的方法来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安置在他们共同管理下,不让自己受一种盲目力量的统治,并用能力的最小的消耗,在最无愧于人、最适合于人性的条件下把它完成。”[9]962这种挣脱盲目力量不是对自然的控制,而是反对对生产资料个人占有的、盲目欲望下的生产模式。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还有更为细致的表述:“从一个较高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观念来看,个别人对于地球的私有权,是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完全悖理。甚至整个社会、整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全体,都不是土地的私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他们必须像一个家庭的贤父一样,把土地改良,然后把它传给后代。”[9]776在这里,马克思将农业视为“把人类累世累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作为经营对象”[9]716的生产活动,与资本支配下的“只注意直接目前货币利益”[9]716的生产思维是相对立的。
在现代农业资本的渗透下,剥夺性的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生态的破坏。马克思一再强调的生产者不能损害保证人类后代幸福的自然与土地。尽管那时的土地破坏和环境问题远没有今天如此严重,但是马克思的预见是惊人准确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起点,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10]637农业的产业化即“大土地所有制”使得农业人口锐减的同时也逐渐“耗尽了土地的自然力”,农业的边际效益也随之降低。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农业生态问题的探讨不局限于土地,他们也探究了森林、河流、山谷、小溪、垃圾处理、环境污染等许多生态问题。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经典论述:“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聚集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砍光了在北坡十分细心保护下来的松林,他们也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适用自然规律。”[11]对生态问题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马克思、恩格斯有深刻的洞见,从人的生存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反思,“生态危机实质是人的生存危机”这种观点即便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也是为了祛除人的欲望枷锁,回归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二、绿色理念下的生态治理
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奎奈提出农业生产体现了以自然法为基础的人类自由秩序是财富的真正来源,“在所有获得财富的应有方法中,几乎没有比农业更好、更丰富、更愉快、更适合人类、更自由,以及更值得追求的了”[12]。而重商主义正是继承了奎奈的自然法则和自由秩序思想,开创出“自由放任主义”和“看不见的手”[13],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铺垫了思想基础。资本的自然性来自人性中的好利与竞争欲望,而天人关系的和谐不争是农业的自然本性。人类在敬畏自然中产生了农业,但是商业分工的出现割裂了天人统一的状态,自然和谐的局面被索取和征服取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把农业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最初形态,“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然后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14]22。农业生产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性活动。这种农本思想在中国也很普遍。被胡适称为中国 “千古奇书”[15]的《淮南子》在《原道训》中记述了对神农发现“五谷”对人类生活的重大影响,在《人间训》中对后稷“辟地垦草”之功进行颂扬,在《地形训》中谈及土地类型与人的关系,《主术训》和《时则训》要求按照二十八星宿天象去从事农业生产。农业是人聆听自然教诲的方式,是自然馈赠于人的最好礼物。在农业中人的自然性和能动性得到充分彰显,但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经济人假设将农业带入基于市场原理的自由体系中,使农业屈从于工业和商业,并按照市场法则进行农业生产。用工商业的竞争主义去从事农业生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滥用农药、污染环境等破坏天人关系的行为。
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化浪潮,1800年只有不到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900年达到14%,2000年提高到50%以上,2050年将达到70%。人们聚居在城市中似乎永远没有了对粮食短缺和农业生产问题的担忧,农业附属于工业,在工业中获得成功的机械化、科技化模式看似可以完美地复制在农业中。1962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问世像是一声惊雷唤醒了人类长期以来对农业的疏忽、对大地的疏远。作为“死神的特效药”的DDT表现了工业科技怂恿下的人们对待粮食生产的急功近利、对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粗暴无礼,没有虫鸣鸟飞的春天敲响了对人类的警钟。1971年威廉·奥博特提出“生态农业”的构想,认为土壤、水源、大气、动植物和人是统一的整体[16]。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素有“欧洲农场”之称的法国和荷兰开启了有机农业,并成立了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经历了重商主义和现代科技的剥离后,人们再次确认我们无法与土地分离,农业是维持人的生存的基点,绿色就是生态、有机、可循环的表征,生命在绿色中得到符合自然的成长,社会和经济不再被利欲熏心的利维坦主义控制,绿色的普罗米修斯完成了对人类社会的技术更新和命运的拯救。
新时代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是背景色,农业是根基和母体,在农业生产中遵照绿色循环模式,不仅是转变农业发展理念,更新农业生产的技术模式,从根本上说“绿色”理念是对人类存在状态的更新认识和界定,绿色农业是农业产业化的必然选择和最终的衡量标准[17]。对绿色农业的唤起,也是传承文明,找寻我们自身的文化根脉的需要。生生不息的农业文明是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源头活水。现代性世界观造成了主、客间的分离,科学技术站在自然的对立面,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思维起点推行无机农业,肆意喷洒农药渗入作物和土壤,颗粒飘浮在空中,损害生物多样性和人的健康,切断了人与大地的有机关联。农药化肥的滥用和过度开垦导致土壤盐分聚集,板结化与沙化日益严重,人类正在扼杀赖以生存的母体——土地。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我们对牲畜家禽进行无以复加的规模化养殖,人与其他生物的伦理关系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而这些在人工囚笼里被饲料喂养,肢体和精神都一直处于被虐待状态下成长的动物最终会用来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成为破坏人体健康的重要来源。绿色农业倡导动植物养殖实现有机循环体系,中国古人即有鱼、羊两利的养殖方式,“南方有草鱼塘,宜修羊栈于塘岸上,每晨以羊矢扫塘中以饲鱼,草鱼之粪以饲鲢鱼,此一举而羊、鱼之利两收。将羊系于处所,煮豆拌盐合草,日日饲之,勿多饮水,一月即肥”[18],现代绿色农业中的“稻虾共作”“稻鸭稻鳖共生”“秸秆沼气循环”模式是绿色农业的创举,实现了粮、畜、渔共赢的良性循环。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的异化,被利润驱使下的“踏轮磨坊”[14]38式的劳动方式无暇去顾及生态环境,“看不见的手”[13]456不会为了环境去放弃利润,也不会自发产生出对生态治理的意愿。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造成如下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4]39绿色普罗米修斯担负的不仅是生态危机的治理,还要与资本制度下的短视和贪婪进行斗争。生态治理从社会意识层面需要唤起的是对自然的情感,但根本上还是要祛除利己主义背后的制度根源。普罗米修斯要赋予人类用火的能力,更希望在黑暗中带给人类光明。马克思给予人类的火种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是能够从源头上实现可持续的、稳固的生态原则。
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指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后果的关键。”[19]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明追求财富不是人类最终的命运[20]。人类的物质生产和城市化破坏了土地与人的关系,绿色普罗米修斯作为一种形象隐喻,是将生态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升级,提升马克思自然观、生态观和历史观在21世纪的解释力,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农业对人类的意义,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如何在农业领域摆脱资本陷阱,回归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对农业生态进行治理和补偿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给予生态战略的指导。
绿色普罗米修斯带给我们的技术启示是要善待自然,避免技术的非理性利用,资本渗入农业生产匹配的是集约化的农业生产设备和生产过程,农机、化肥、农药和种子公司的利益凌驾于土地之上。“机器生产是大工业的标志,也是农业技术工业化的标志。……工业化的农业技术使农业生产分工展现在纵横两个维度上,横向上的分工是指劳动生产种类、农作物栽培品种的单一化,纵向上的分工则是指农艺流程技术环节上的专门化”[21]。弗里德里希·舒马赫在《小是美好的》一书中提出“适度技术”和“中间技术”的概念告诫发展中国家不要迷信工业化的规模和效益,浪费资源加剧环境破坏的市场优先主义是本末倒置的,无论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放在第一位,‘财富’放到第二位”[22]。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马克思对农业工业化的警告,工业化的技术和工业化的分工使得“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23]。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绿色理念的生态农业有了制度性前提和现实政策条件作为支撑,没有宜居的自然环境,马克思论述的人类的两大部类的生产都无法进行,绿色普罗米修斯解决了人们的生产与生存发生冲突,既要尊重自然规律,又要符合人的生存需求,环境是“人为的”,更应该是“为人的”,树立绿色理念,让人在得到自然馈赠的同时也可以回馈自然。美丽乡村是绿色的、宁静的,题中之义是让漂泊的心找回精神家园和内心归宿,乡村振兴战略明确了“生态宜居”的要求,凋敝的农村开始恢复生机,“田园农庄”“厕所革命”都体现出人居与生产的有机统一,彰显出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深远性和彻底性,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美丽乡村
习近平的“两山论”阐明了生态优先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存在前提是生态环境的维系,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逻辑次序不能颠倒,为经济发展而做的生态牺牲是得不偿失的短视行为。“绿色”理念是对“两山论”的概括和实践指南,许多地区在“绿色”理念指导下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取得了切实的成效。习近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保持加强对环境治理的战略“定力”[24]。环境不隶属于经济,它是人存在的依据,任何经济、政治、社会的活动都是从属于环境的,激进的物质主义和财富拜物教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执着于追求财富的人们有一天会意识到对绿色家园的守护才是人类最应该坚守、最具价值的事业。人类文化始于农耕,在土地上的产物富饶才孕化出城市文明,但在城市经济生活中人们的心灵被物欲蒙蔽,以经济利益侵害生态环境的思维和实践从未间断:森林破坏、土地荒漠化、河流污染、冰川融化、生物多样性锐减,古巴比伦文明、楼兰文明都是在环境退化中消亡的。我们回顾文明史可以得出一个简单而明确的规律:“生态兴则文明兴,文明兴则国家强。”可以说人类文明兴衰史就是对大地忠诚与叛变的历史。
安徽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相对缺乏,许多土地缺乏长期科学使用规划,以机械耕种和收割,集中耕种产业化经营的农业方式较为普遍,在以机械耕作为现代化农业导向思维下,向农村生态输入过多的无机能量造成土质退化、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对粮食安全、人居环境构成了很大威胁,也不利于美好安徽的构建。新世纪伊始编订的《安徽省生态农业发展规划》中提出“稻田养殖”“果园立体种养”“立体农业”“观光生态农业”“矿区塌陷地综合治理”等生态技术建设目标在逐渐地落实和完善,《安徽省“十三五”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也提出“绿色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农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安徽要打造宜居宜业充满活力的生态强省”。近年来在习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指导下,积极推进农村生态改造,绿色环保机械化技术、引导农民种植绿肥、施用有机肥得到广泛应用。“水长流、山长青、景长美”的美丽乡村在江淮大地不断涌现。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美好安徽生态农业建设有了显著的提升。安徽同时提出“创新强农、协调惠农、绿色兴农、开放助农、共享富农”方略。在农业供给侧改革方面处处体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农业之路。作为国家典型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省,安徽加大在淮河生态经济带的污染治理,确保淮河粮食主产区生态安全。对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开展“引江济淮治巢”工程,投入500多亿元进行疏通淤塞、清理水藻和农田面源污染防治[25]。在新安江流域大力开展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水产养殖污染减排、地表径流污水净化利用等工程建设,加强生态治理和修复。践行绿色理念引领乡村振兴是对自然赐予的感恩和人民勤劳智慧共同作用的结果,安徽古有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安丰塘,被列为“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现代小岗村迈出了国家农村发展的制度性变革第一步,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26]。安徽在生态农业建设中有着丰富的资源禀赋和精神传承,在新时代将绿色理念勾勒在江淮大地的美丽乡村中,让乡村振兴更有诗情画意,人民更加幸福宜居。
甘地说:“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27]89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物质和精神的融合与升华,良好生态是孕育富足和文明的土壤,农业生态文明是“生态宜居”的前提,也是“产业兴旺”的必由之路,生态化的美丽乡村才能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绿色普罗米修斯是绿色理念的化身,是乡土的守护者,他净化大地,涤荡遮蔽在人们心灵上的风尘,在生态治理中修复人与自然的裂痕,使我们回归文明的初心,对土地心存敬畏和眷恋。我们无论生活在何处,乡村总是人类的故乡,土地总是最可依靠和信赖的母亲,善待我们的母亲,我们才能真正“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